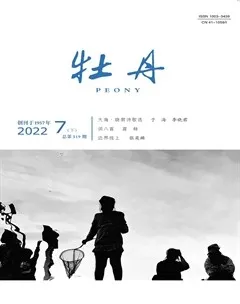余華小說《第七天》時空敘事研究
《第七天》是余華繼《兄弟》后,時隔六年發表的一部長篇小說。作品以名為楊飛的中年男性的視角,向讀者講述了死后的七日見聞。《第七天》一經發表便在學術界引起熱議,作家本人更是將該作品視為當前創作之最。在該作品中,余華延續早期時空敘事格局并有所創新。從時間敘事來看,故事時間和敘述時間呈現疊合特征,作家通過回顧性敘事引入大量插敘,并通過時間并置讓復雜的時間及人物關系變得清晰且真實;從空間敘事來看,在構建現實空間與心理空間之下,引入第三空間,由此承載作家對于人性之善與美的思考。
以敘事學中的時空敘述視角研究余華作品《第七天》,具體探究該小說中兩條并行交錯的物理時間線,即從主人公死亡的時間出發,兩條時間線分別走向過去與未來。在空間敘述層面,該作品從全知全覺的敘述視角出發,主人公自由游走于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之間,以亡靈的身份穿梭于真實與虛構的世界,從而全方位洞察現實人性,該作品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
一、時間敘事策略
《第七天》的章節標題是一個明確的“時間標尺”。小說采取串珠式的結構,每一天都自成章節,每個章節又自成一篇。該作品中,余華摒棄傳統線性時間描寫,創造性運用時空交叉手法,將多個人物故事線索在不同時空完成敘事建構,這樣豐富且立體的時間敘述模式為原本晦暗的主題增添了閱讀趣味。在敘事方面,故事時間與文本時間的雙重性使敘事內容與結構富有張力。與此同時,作者采用第一人稱回顧性敘事,向讀者傳遞出楊飛的主觀認識,增強了故事真實性。時間并置使得貌似彼此獨立、實則有著深刻聯系的人物故事線,在復雜的時間倒錯中完整展現。
(一)故事時間與敘述時間
敘事學家分析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的關系后,進一步將敘事時間劃分為時序、時距等,下文從時序和時距入手,分析《第七天》的時間敘事策略。
在《第七天》扉頁,作者借用了《舊約·創世紀》中的一句話:“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小說七個部分便是以“第一天”至“第七天”為標題。主人公楊飛死后,他以魂靈的身份重現人間。在人間,他以旁觀者視角審視生前經歷,包括妻子離去、失業賣房,以及父親重病,為緩解他的壓力不辭而別等不幸遭遇。除此之外,途徑譚家菜館時,回憶起與老板一家人交談的點點滴滴,第二章還憶起與前妻相識相戀的往事等。作者在基本敘事架構的基礎上,不斷通過回憶追述的方式,將已經發生的故事娓娓道來。如第二天:“我坐在這寂靜之中,感到昏昏欲睡,再次閉上眼睛。然后看見了美麗聰明的李青,看見了我們曇花一現的愛情和曇花一現的婚姻。那個世界正在離去,那個世界里的往事在一輛駛來的公交車上,我第一次見到李青的情景姍姍而來。”因此,宏觀來看,敘述時間是第一天至第七天即主人公死后思緒飛馳的經過,而故事時間隨著楊飛靈魂的自由擺渡而展開。比如這樣一段敘述:
濃霧彌漫之時,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虛混沌的城市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殯儀館……
昨夜響了一宵倒塌的聲音,轟然聲連接著轟然聲,仿佛一幢一幢房屋疲憊不堪之后躺下了。我在持續的轟然聲里似睡非睡,天亮后打開屋門時轟然聲突然消失……
我出門時濃霧鎖住了這個城市的容貌,這個城市失去了白晝和黑夜,失去了早晨和晚上。
這部分是小說的開頭。第一段講的是楊飛離開出租屋,需要在9點之前趕到殯儀館,第二段前半部分講的是昨晚令人難眠的轟然聲,隨后又銜接第一段內容,寫離開出租屋關門時看到的紙條。第三段繼續寫踏上了殯儀館的路。這里的敘述文本是人物內心活動,敘述時間是今早離開出租屋,前往殯儀館。而故事時間已從昨夜的轟然聲開始,顯然故事時間要長于敘述時間。
關于時距的分析較為復雜。時距是指作者的敘事時間與故事實際發生時間的長短關系。從整體寫作思路來看,主要以場景設置為主線,即敘事時間基本等于故事時間。楊飛死后從出租房到殯儀館再從殯儀館出發開始一段漂泊,作者將場景設置安排在每一個章節的首尾。作者進行場景設置的主要目的是聯結過去,而具體段落的場景大體是通過語言描寫,即以對話形式展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第二天在老房子門前,楊飛與前妻重逢時大篇幅的語言描寫。敘述者對過往的回憶是插敘,在不斷游走的過程中,楊飛仿佛可以看到自己生前的一幕幕,他回憶起生前與工廠夫婦的那通電話,回憶起與妻子從相識到相愛再到分別的過程,回憶起與父親相依為命的那段日子。敘述者的身份為游走世間的亡靈,不斷游走的過程中便會勾連起一系列回憶,因此插敘部分的描寫較為詳細具體,極其符合敘述主體作為逝者的身份。如此,向讀者介紹敘述者生前經歷的同時,讓我們感受到了他生而為人的善良與不幸的遭遇。
(二)兩種敘事視角結合下的插敘
對故事時間與文本時間分別梳理后可以發現,敘述文本要生成意義離不開敘述主體。敘述主體向讀者提供文本信息,布局好作品時序后,向讀者傳遞出對故事較為主觀的感知、認識、判斷。申丹在《敘述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中指出,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包含兩種敘述視角,它們在文本中交替出現。“一為敘述者‘我’目前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為被追憶的‘我’過去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分別被稱為“敘述自我”與“經驗自我”。在小說《第七天》里,作家通過第一人稱敘述的雙重聚焦方法建構了這兩種自我形象,具體表現為“我”在靈魂游走的過程中以旁觀者的身份看到了過去的自己。比如第三天的段落:
這時候兩條亮閃閃的鐵軌在我腳下生長出來,向前飄揚而去,它們遲疑不決的模樣仿佛是兩束迷路的光芒。然后,我看見自己出生的情景。
……
她從臥鋪上下來,挺著大肚子搖晃地走向車廂連接處的廁所。火車停靠后,一些旅客背著大包小包上車,讓她走向廁所時困難重重,她小心翼翼地從迎面而來的旅客和大包小包里擠了過去。當她進入廁所里,火車緩緩啟動了,那時的火車十分簡陋,上廁所是要蹲著的,一個寬敞的圓洞可以看見下面閃閃而過的一排排鐵路枕木。我的生母沒有辦法蹲下去,是肚子里的我阻擋了她的這個動作,她只好雙腿跪下,也顧不上廁所地面的骯臟,她脫下褲子以后,剛剛一使勁,我就脫穎而出,從廁所的圓洞滑了出去,前行的火車瞬間斷開了我和生母聯結的臍帶。
這段敘述了生母在火車上生產的具體過程。敘述自我站在鐵軌上講述該場景,而此處經驗自我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驗自我,因為經驗的“我”此時不具備感知世界的能力。這兩個“我”均以全知視角見證過去,符合“我”的特殊身份。余華采用全知視角與第一人稱回顧性敘事相結合的兩種外視角敘事,使得原本只是感傷的回憶性插敘富有神秘色彩,產生獨特的審美效果。
(三)時間的并置模式
查希里揚認為:“時間仿佛是以一種潛在的形態存在于一切空間展開的結構之中。”人物記憶具有穿越時空的功能,它打破了時空之間的界限,過往的人、事、物、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只要有意識存在,它便可以徜徉于世間內外,在敘述者的口中娓娓道來。
作者巧妙利用回憶再現的方式,在線性時間發展的同時,通過回憶將往事由“發生”轉換為“再現”,與現在的時間交匯,并且將各條故事線在文本結構中進行章節并置,使得原本龐雜的人物關系與事情序列變得清晰可循。死后在出租屋“醒來”是故事的開端,由此以“我”的行蹤軌跡為主線引出其他人物的生前故事,以“我”的故事為參照,引出父親、李青、李月珍以及伍超與“鼠女”的故事。在“我”的主敘述時間內,他者的出現豐富了“我”的故事情節,關于他者的背景,作者在另外章節有更為詳盡的敘述。生父楊金彪與“我”的故事在第二天詳細闡述,但實際上楊金彪在第一天時便已經出現,后第五天再次交代該人物;關于商場起火、人員傷亡的故事,早在第三天便有提及,在第五天和第六天中又揭示了事故的真相;工廠夫婦的故事,第一天已交代他們不幸罹難,第五天奔赴“死無葬身之地”后,“我”又見到了將要化作骨骼的兩人。在最后的“死無葬身之地”,所有人物矛盾都
自然化解。
每個人物都有一段故事,作者將他們的故事穿插在一個章節中,一條主線與多條副線相互連接,該條副線又會變成主線被其他副線豐富情節。如果說以“我”死后七天的游歷作為文本的現實邏輯,那么“我”生前周遭的故事線索則貫穿了文本的始終,將生前與逝后貌似與“我”毫無關系的亡靈連接起來,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二、空間敘事策略
空間承載著事物,文學作品中的故事情節和人物活動均在一定的空間背景下開展。一般意義上文學敘事中的空間主要分為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心理空間,本文結合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及空間存在的屬性,從宏觀角度將《第七天》中的空間敘事模式分為現實空間和虛擬空間。
(一)現實空間
在文學領域,現實空間指的是客觀存在的活動領域,通常可分為大空間(時代和社會背景)和小空間(具體活動的場所)。《第七天》主要以敘述者楊飛生前去后的人生經歷為線索,創造了既可以包容逝者生前活動軌跡,又可使漂泊的亡靈棲息的“死無葬身之地”這一典型環境,這一空間能夠揭示現實社會的真實面貌,同時能夠窺探個人內心的善惡。個體空間和社會空間彼此觀照,構成了極富層次感的空間敘事模式。筆者把現實空間分為個體空間和社會空間進而展開論述。
作者通過第一人稱敘事將敘述者的心理活動直觀地展現出來。比如看到女孩獨自一人在寒風中等待父母,他心生憐憫:
我跨上全是鋼筋水泥的廢墟,身體搖晃著來到她的身旁,她抬起頭看著我,她的臉蛋被寒風吹得通紅。
我問她:“你不冷嗎?”
“我冷。”她說。
我伸手指指不遠處的肯德基,我說那里面暖和,可以去那里做作業。
他雖不善言談,但親切友善。雖自身貧困潦倒,但仍關懷著幼小的孩童。在整部作品中,即便他生活不幸,但從未抱怨。文中,楊飛兩次向他人闡述了自己記憶中的死因,雖較為荒誕離譜,但他本人不以為意,由此可見他性格的耿直與坦率。在真實世界,他灰頭土臉、貧困潦倒,沒有高遠的志向,但心靈真誠而圣潔。余華構建了多維的心理空間,強調了這部小說獨特的想象向度,并將語言描寫作為輔助,揭示出敘述者較為深層的心理特征。
社會空間是一個整體,內部的各個單元相互獨立但又彼此滲透。分析以獨立個體為單位的碎片化小空間,揭示個體空間的內在關聯,便可找到極具風格的社會面貌。
作品中沒有交代故事發生的具體年代,但通過一些富有時代特征的景物,讀者可以判定故事發生在21世紀最初幾年。可突出的超現實主義風格淡化了時代背景,使讀者沉浸于余華所營造的文學世界,只覺得這個世界離我們并不遙遠。暴力拆遷、新聞播報時模糊概念;母子親情與兄弟之間的手足情在物質利益的驅使下變得畸形;城市“鼠族”在黑暗潮濕的地窖里茍延殘喘;善良的人被算計,作惡的人殘存于世……作者批判世人不辨是非善惡的愚昧與無知。在這個社會空間里,好人去了“死無葬身之地”,愚昧者與作惡之人留存于世。
(二)虛擬空間
虛擬空間又稱非現實空間,指的是在現實空間的基礎之上通過文化再建構的意識空間。筆者將《第七天》中的虛擬空間分為與現實世界相仿的虛擬空間和烏托邦空間展開說明。
楊飛死后前四天,他仍游走于人世間。所過之處除了看到生前場景,他還去到了一個與現實世界相仿的虛擬世界:殯儀館。
貴賓區域里談論的話題是壽衣和骨灰盒……價格都在六萬元以上。
我們這邊也在談論壽衣和骨灰盒……最貴的八百元,最便宜的兩百元。
候燒大廳區分沙發貴賓區和塑料椅子區,有錢人死后依舊頤指氣使,窮人死后個個正襟危坐,但在權力面前,金錢也只能自慚形穢。人們常說死后便可放下一切得安息,但在余華筆下,不幸永無止境。讀到最后,在絕望的盡頭,讀者看到了美好而安詳的一方凈土——“死無葬身之地”。
烏托邦本意是“沒有的地方”或者是“好地方”,它象征著人類理想中所追尋的境地。可在《第七天》中,這個在國人文化建構中貌似極具苦難的“死無葬身之地”,竟成了愛與希望的棲息地。
我驚訝地看見一個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樹木茂盛,樹枝上結滿有核的果子,樹葉都是心臟的模樣,它們抖動時也是心臟跳動的節奏。我看見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還有一些有肉體的人,在那里走來走去。
我問她:“這是什么地方?”
她說:“這里叫死無葬身之地。”
這里的樹葉都有心跳,會對靈魂招手,石頭也會微笑,行走的骨骼彼此之間親切友好。即使肉體終會腐爛,但骨骼不死、靈魂不滅,雖永不安息,但自得其樂。余華在該作品中構建的烏托邦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理想社會,通過建立“死無葬身之地”中亡靈之間親密友好的關系,向讀者展示出一個充滿關懷、愛與同情的第三空間。在現實世界中,人們遭遇不幸,但在此處,一切均可化解,親情、友情和愛情在這里得以圓滿。這個生命離去的盡頭沒有衰敗,盡是鳥語花香,一切最終都可以得到補償。
三、《第七天》時空敘事的價值
研究時空敘事,有助于對文本的敘事結構進行整體分析。《第七天》中章節的標題即死后的天數,讀者初讀作品更容易關注時間線索。比如死后第一天,人物先在出租屋里行動,在殯儀館候燒無果,便開始漂泊。但在梳理時間線索時,讀者或是評論家都沒法逃避其中的空間領域。比如在進一步閱讀的過程中,人們會總結第一天的行蹤軌跡,即“我”從出租屋到殯儀館再到盛和路,然后到達譚家菜館。因此,時間敘事與空間敘事是彼此融合的統一體,單獨對其進行研究是不可取的。
從整體上來看,時間與空間在彼此交融的基礎上隨著故事情節的演進發生變化,使得人物之間的關系在時空變換中變得愈加龐雜,卻又在情節的推進中變得愈加清晰。就空間的轉移路徑來看,從整體上看是從人世間到“死無葬身之地”,從具體的細節上看,“我”不斷行走漂泊至熟悉的場所并產生了一系列回憶,這些回憶不受拘束,即刻把讀者帶至不同空間,在到達“死無葬身之地”后,空間呈現出一個圓形的閉環。這象征著生前悲慘、死后圓滿的生存路徑已經達成,在一定程度上,時間與空間都呈現疊合的特征。
余華早期作品似乎有意規避線性時空敘事,通過精心的布局,展示了現實社會的荒誕性。而《第七天》所營造的時空格局,在充分尊重現實世界的基礎上,又創造出異于客觀世界的“第三空間”,這個空間充滿無限可能,他以此守護人性的真善美,這使得該作品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
(通遼市明仁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