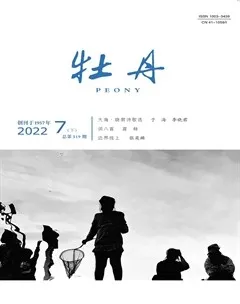《包法利夫人》中不同類型人物的結局對現實的映照
《包法利夫人》是19世紀法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作之一,小說在連載之時就引起了轟動。追求虛無的浪漫主義者——愛瑪的結局令人惋惜,而偶遇浪漫的現實主義者查理和一心逐利的利己主義者郝麥的結局同樣讓人深思。這三種人代表著三類不同的生存觀念,他們的結局可以映照出當時鄙俗的現實社會。
一、愛瑪的死亡:浪漫主義的衰落
愛瑪是一個農民家的女兒,從小被父母送到修道院接受大家閨秀的教育,在成長過程中喜歡看《保爾和薇吉妮》這類書寫浪漫愛情的書,生活領域的狹窄和接受教育的單一使愛瑪漸漸認為自己也能擁有驚心動魄的愛情。在少女時期,愛瑪去聽布道時聽到:“諸如未婚夫、丈夫、天上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等,總在她靈魂深處喚起意想不到的喜悅。”婚后參加侯爵的舞會時,愛瑪萌發了對物質和上層社會的渴望。她認為:“所以月下的嘆息、長時間的擁抱、流在伸出來的手上的眼淚、肉體的種種不安和情意的種種纏綿,不但離不開終日悠閑的大莊園的陽臺、鋪著厚實地毯和有活動簾的繡房、枝葉茂密的盆景、放在臺上的寶榻,也離不開珠玉的晶瑩和號衣的飾帶。”可以說,愛瑪是一個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熱烈追求心中世界的浪漫主義者。
從現實角度看,愛瑪是一個富農出身的女子,屬于小資產階級,她的周圍也多是無產階級者或小資產階級者,而愛瑪向往的是在大資產階級或貴族階級的奢侈生活中談情說愛。可她并沒有意識到,在當時,追求與本人階級身份不符的浪漫就是追求虛無的理想。愛瑪嫁給查理、出軌羅道爾弗和賴昂都是為了追求心中浪漫的幻影,但卻都脫離了現實。
之后,愛瑪發現查理無趣,羅道爾弗拋下了她,連賴昂也不能給她想要的生活。對浪漫的追求一直無法實現,于是愛瑪逐漸墮落,沉溺于原始的情欲和物欲。在和賴昂私通的后半程,愛瑪知道她對賴昂的愛的幻想已經消失,但她卻無法擺脫沉迷情欲的惡習,“她總在期許下次幽會無限幸福,事后卻承認毫無驚人之處。愛瑪覺得掃興,可是一種新的希望又很快起而代之,回到他的身旁,分外熾熱,分外情急”。愛瑪依舊給賴昂寫信,但是信的實際對象已經不再是賴昂,而是“另一個男子、一個她最熱烈的回憶、最美好的讀物和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這是她對心中的浪漫理想殘留的最后一點執著。關于物欲,在與賴昂的相處中,愛瑪花錢愈發大膽,盡管家里并不富裕,她還是“一味買,一味欠,一味借,一味出票據,續票據”。愛瑪自己也意識到,在這樣消沉的生活中,即便自己什么也沒做就已經非常疲憊。
人不可能沒有扎實的經濟基礎,僅僅活在由虛無的浪漫建筑起來的空中樓閣。當籌不到錢,她的情夫拒絕幫助她,家里的物品也面臨抵押的時候,愛瑪隱約意識到,如果陷入了沒有金錢的窘況,她所追求的浪漫生活就會隨之消失。之后,愛瑪神志恍惚,選擇了自殺。
愛瑪是個浪漫主義者,但她所追求的理想生活過于虛無。她對現實情況缺乏清楚的認知,不愿也不能融入現實生活。她在丈夫的包容下不了解賺錢的辛苦,因為很少關注大眾生活不了解人心的險惡,之后她被騙、被利用、被現實的生活摧殘,最終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愛瑪的悲劇是浪漫主義幻想和現實生活發生沖突的必然后果,反映了浪漫主義因無法承受現實重壓而最終消亡的結局。
二、查理的死亡:現實主義的重創
查理·包法利非常平庸,小時候父母不算疼愛他,他不聰明,成績一般,無論是工作還是娶妻,他都順從父母的安排,規規矩矩地生活。查理的世界里沒有不切實際的愿望,在遇見愛瑪之前,他對婚姻生活也只是抱有如“結過婚,環境改善,他就自由了,身子可以自主,用錢可以隨意”這種極實際的期待。
愛瑪的出現讓查理的生活有了期待。查理喜愛愛瑪,喜愛她的外貌、衣著、愛好和言行舉止,甚至喜愛她買回來裝點家里的小玩意。可以說,娶了愛瑪是查理人生中第一件讓他感到身心舒暢的事。查理回顧自己以前的生活,發現過得并不順遂。“他生活哪一點稱心如意?難道是中學時期?關在那些高墻中間,孤零零一個人,班上同學全比他有錢,有氣力,他的口音逗他們發笑,他們奚落他的服裝,他們的母親來到會客室,皮手筒里帶著點心。難道是后來學醫的時期?錢口袋永遠癟癟的,一個做工的女孩子明明可以當他的姘頭,因為她陪他跳雙人舞的錢,他付不出,也告吹了。此后他和寡婦一道過了十四個月,她那雙腳在床上就像冰塊一樣涼。”總之,因為愛瑪,查理的生活變得明亮,他感到愉快、幸福,也因此更喜愛愛瑪。“宇宙在他,不超過她的紡綢襯裙的幅員;他責備自己愛她愛得不夠,想再回去看看她。”所以愛瑪提出的要求他都盡力滿足,比如搬家、由愛瑪支配家里財產、在家里左支右絀時還是幫愛瑪實現心愿等。
查理愛著愛瑪,記得她的喜好,滿足她的要求,但他卻從未深入了解愛瑪。查理用自己的方式愛著愛瑪,從未想過對方想要的是什么方式,也從未想過在愛瑪浪漫優雅的形象背后是什么經歷和思想在支撐。查理對愛瑪,就像平庸的現實主義者遇見浪漫主義者,現實主義者無法理解浪漫主義者豐富的內心世界,浪漫主義者鄙夷現實主義者的平凡俗氣。正如愛瑪審視丈夫時,她認為:“一個男子難道不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啟發你領會熱情的力量、生命的奧妙和一切秘密嗎?可是這位先生,一無所教,一無所知,一無所期。他相信她快樂;然而她恨的正是他這種穩如磐石的安定,這種心平氣和的遲鈍,甚至她帶給他的幸福。”因此,盡管現實主義者會因為浪漫而激起自身對美的本能渴望,但他們對浪漫的盲目縱容對雙方都是一種殘害。就像本書的結局,愛瑪從未真正在乎過查理,查理用盡自己的金錢和精力,卻發現了愛瑪兩次出軌的事實。徹底失去愛情、美夢破滅的查理,最后支撐不住,在悲痛中死去。這樣不幸的結局也反映出一種現象:當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發生沖突時,雙方矛盾的不可調和,造成現實主義受到重創。
三、郝麥的順遂:利己主義的“勝利”
福樓拜寫作重視中間色調,認為中間色調的真實性也不容忽視。郝麥就是作者刻畫得非常出色的資產階級中間人物之一,這個人物從小說第二部開始出現并貫穿全文,呈現了除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以外的第三條道路——利己主義。
郝麥是藥劑師,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證生存并向成功進一步發展。在為人方面,他總賣弄自己,追求時髦。比如勒弗朗索瓦太太問郝麥是否懂得耕地,郝麥肯定地回答道:“當然懂,因為我是藥劑師,就是說,化學家!而化學,勒弗朗索瓦太太,目的就在認識自然界一切物體的分子的相互作用,農業自然也就包括在它的范圍內!”在處事方面,郝麥所做的事都展現出很強的目的性。比如在查理一家剛到永鎮時就熱情地關照他們,是“為了使他感激在心,萬一日后有所覺察,也就難以開口”。又比如卡尼韋博士來給伊波立特做割腿手術,雖然郝麥在這件事上也有責任,但他去巴結卡尼韋先生時,選擇“不幫包法利辯護,甚至不發一言,放棄原則,為了商業上更重大的利益,犧牲他的尊嚴”。后來,他成功將自己的仇敵關進監獄,之后愈發大膽,在鎮上以“科學”為借口欺世盜名,一步步鞏固自己的地位。“自從包法利死后,一連有三個醫生在永鎮開業,但是經不起郝麥拼命排擠,沒有一個站住了腳。他的主顧多得不得了。官方寬容他,輿論保護他。”這是郝麥的結局,也是全書的末尾。
論人物結局,郝麥無疑是三者中最順遂的。冷靜客觀是福樓拜的寫作風格,他對這樣的結局并未表露任何態度,但在讀者看來,利己主義者在社會上如魚得水,查理和愛瑪這類善良的人卻以死亡結尾,這是個徹頭徹尾的悲劇結局。郝麥的成功是一種世俗空洞的成功,對他結局的設計實際上反映了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是對社會赤裸裸的諷刺。
四、三類人物的結局映照現實
全書的三位主要人物有著三種結局:浪漫主義者愛瑪因為幻想中的浪漫破滅選擇自殺,現實主義者查理在浪漫的消亡和現實的窘境中抱恨而終,而利己主義者郝麥一步步達到了他想要的世俗意義上的成功。這讓人不禁思考:這只是個別人的悲劇,還是當時的社會醞釀出的慘案?
福樓拜給《包法利夫人》提寫的副標題為“外省風俗”,且小說的靈感來源于真人真事:一個鄉村醫生夫人的服毒案。這似乎表明了福樓拜想反映的是真實的社會現象。故事發生在1848年,這時法國處于第二帝國時期,革命浪潮褪去,資產階級將二月革命的勝利果實收入囊中,地位得到提高,生活變得平庸而鄙俗。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把整個社會都納入了價值計算當中,其社會觀和價值觀逐漸成為當時社會認識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主流標準,金錢變成衡量一切的準繩。文學思潮上,奧爾良王朝前期,浪漫主義運動在法國蓬勃發展。資產階級得到政治勝利以前是消極浪漫主義主導法國文學,而在之后,積極的浪漫主義逐漸取得主導權。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變革之后,一些文學家希望通過審視現實社會展現自己的社會理想,于是現實主義登上歷史舞臺并快速發展,與浪漫主義分庭抗禮。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愛瑪的成長受到消極浪漫主義的影響,她不能正視社會現實,將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理想生活立足在虛幻的想象和感受中,而愛瑪所幻想的一切美好愿景恰恰是資本主義社會所建構的。這個社會給了愛瑪幻想金錢的機會卻沒有給她創造財富的能力,給了她看似光明的方向卻沒有告訴她出路。因此,在消極浪漫主義必然消亡的歷史趨勢下,不愿意遵從現實秩序的愛瑪選擇了自殺。福樓拜批判了消極浪漫主義對人的不良影響,卻對愛瑪的遭遇表示惋惜。他在寫給高萊夫人的一封信中說:“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時在法蘭西二十個村落里受苦、哭泣。”
現實主義者查理的死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在和浪漫主義的交鋒中敗下陣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他在空虛鄙俗的社會環境中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現實生活。在當時的社會,金錢代表著地位,身為鄉村醫生的查理原本可以過著平淡穩定的生活,妻子花盡家財吞毒自盡后,查理變得更固執,生活更落魄,愛瑪的出軌成了壓死查理的最后一根稻草。盡管查理對幸福生活的追求立足于現實,但他發現自己一直以來擁有的幸福生活里隱含著妻子的背叛和無情,這使他原本已經由灰暗變得光彩的人生徹底陷入黑暗。現實主義者并非沒有理想,但卻無法承受自己傾盡一切得到的理想生活在充滿物欲的、鄙俗的社會中不堪一擊,轟然倒塌。
在這樣平庸瑣碎的社會生活中,飛黃騰達的是利己主義者郝麥,而他只是一個打著“科學進步”旗號,不斷鉆營、自私自利的庸夫俗子。這才是本書揭露的無情現實。它與浪漫主義者、現實主義者所追崇的世界截然不同,這樣的現實鄙陋、空洞、猥瑣、無聊,隱藏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繁榮表象下,無數個包法利先生、包法利夫人悄無聲息地被淹沒在社會潮流中。
五、結語
《包法利夫人》通過社會生活中三類小人物的不同結局,映照了19世紀前中期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社會弊病,這個社會汲汲于物質,誘使懷著夢幻思想的浪漫主義者走入陷阱,讓現實主義者的理想破滅,而功利主義者順應所謂的社會潮流,一路飛升、名利雙收。福樓拜以筆為矛,深刻揭露了當時的社會風氣,痛斥資產階級生活的淺薄和鄙陋,發人深省。
(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
作者簡介:覃毅(2000—),女,廣西柳州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為文藝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