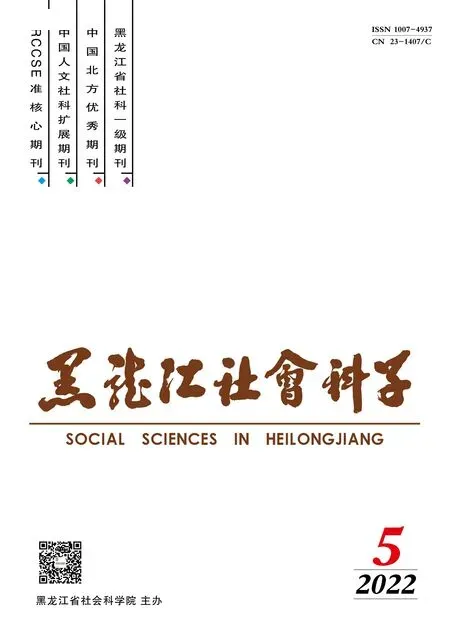“以人為本”的文化批評理論的生成與建構
——兼論《關雎》的文化內涵
孫淑奇,楊玲玲
(1.遼東學院 師范學院,遼寧 丹東 118000;2.朝陽師范高等專科,遼寧 朝陽 122000)
“文化”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詞語,在普通人觀念中,文化與教育“相互依存,互相制約”。在傳統教育理念中,成為“人”是古代人文化育人的核心,現代教育不但要培養成“人”還要培養成有知識的人。無論古代、現代,文化的產生發展和滿足群體的需要密切相關,文學藝術在沒有獨立于其他精神活動之前,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形態,突顯出其文化功能。在獨立后,文學藝術的審美性逐漸構成其主要的本質特征,與它的實用特征在互異中同構。“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的衍化史證明,文化實用主義和審美主義都深深烙印在文學的發展演變中。
一、人類學視閾下的文化含義
德國人類學家赫爾德爾在《人類歷史哲學概要》中認為,文化首先體現為“模式”化的社會生活,每個人的言行都受這種模式的規范,影響到人們的日常思維和情感反映。這種認識強調文化的普遍性和類型化特征。其一,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文化是在特定群體中產生發展的,反映其共同的精神和心理。其二,文化有地域和邊界特征。地域和邊界是空間概念,地域更突出地理特征,邊界還內涵特定的意識形態。有的學者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赫爾德爾的界定已經“古調不彈”,尤其在虛擬的互聯網世界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突破時空的局限,使文化共享變為現實,文化潛在的世界性和共同體特征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中理所必然。但在冷戰思維主導下的國際政治現實面前,世界文化共同體還只停留于理想主義,文化仍具有民族性、邊界性、意識形態性。在國家外部層面,文化的民族特征是國家主權的精神標識,文化的邊界意識與地理意義上的邊界同構;在國家內部層面,文化的民族特征、區域特征是族群文化和地域文化空間分布的象征,是民族共同體內部文化差異的體現。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文化的起源》中認為:“文化……包括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習慣的復合體。”[1]把人類一切文明成果視為文化,超越地域和民族界閾。美國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克洛依伯和克萊德·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義批判分析》中認為:“文化存在于各種內隱和外顯的模式之中。借助符號的運用得以學習和傳播,并構成人類群體的特殊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他們制造物品的各種具體式樣。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傳統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其中尤以價值觀最為重要。”[2]這個概念包含以下三方面內容:其一,文化是一種符號,便于傳播和學習。其二,傳統是文化的根脈,具有繼承和創新性。文化批評學者陳曉明認為,“文化變化發展進程中有延伸和更新能力的本己能量”即為“傳統”[3]。其三,文化包括內隱的精神和外顯的物質兩種模式。《辭海》對文化這樣界定:“從廣義來說,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綜合。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廣義概念的文化即文明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內容,財富說明文化是人類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勞動成果,具有歷史繼承性和創造性。狹義概念的文化主要指反映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各種意識形態的總合,和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及組織機構,當然也包括非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和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及組織機構,這是馬克思主義視閾中的文化含義。
結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活動的觀念和上述各種關于文化的理解,本文認為文化首先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精神活動,具有人的目的性和自由性內涵,是人類真善美統一的精神實踐活動的歷史呈現;其次,文化是特定群體的精神象征,具象于個體的行為、思想和心理;再次,文化雖有地域和民族的差異,卻趨向認同性;最后,文化性質的最終指向是時間域,它的遺傳性在于歷史,實用性在于現實,理想性在于未來,歷史、現實、未來構成文化精神的三個維度、三種面向。
二、“以人為本”的文化批評觀的生成
以文化為視角進行作品解讀,顧名思義就是主要分析作品中所體現的文化精神[4]。張岱年先生認為:“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精微的內在動力,也就是指導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民族思想。”[5]陳曉明總結為“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剛健自強、以和為貴”,強調人的生存與客觀世界的關系包括個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遵循和諧同構的發展規律,達到“獨樂樂不如眾樂樂”的集體主義精神追求,與貫穿于西方文化精神的“以人為本”所強調人的主體性有明顯的區別。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學是人學,只有實現“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人才能在活動中成為真正完整的人,文學正是以這樣的尺度觀照人。個體的人無法超越社會存在的客觀事實,人與客觀世界有本質差別,這只是邏輯上的對立沖突,但不等于關系上的必然矛盾,和諧本身也是差異關系的另一種表現即轉化關系的結果。所以,受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熏染,人與人之間在和諧關系中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體,當人民成為共同體的最大受益群體時,以民為本就有了具體的實踐特征。人民不但是社會利益的主體,而且是被服務的主體,那么“文學為人民,服務于人民,屬于人民”,文學的人民性中的人民內涵的“人”之為人,是與客觀世界達成和諧關系中的“人”,所以說人民文學本身體現的“以人為本”,更為符合馬克思主義所言的社會性和個體性統一的人。
以什么樣的文化視角展開批評,要視具體文本而厘定,不能穿鑿附會。“以人為本”的文化批評并不以西方邏輯上二元對立視閾中的“主體性”為人之尺度,它體現的是以人的自我和客觀世界和諧關系中的主體性為“人”之尺度。前者偏于崇高中的矛盾,在張力中追尋人的主體價值,后者是在矛盾轉化中尋求主體的詩意棲居,在和諧中構筑理想的精神品格。
三、文化批評的歷史典例素描
先秦時期儒家文化批評的詩教色彩濃重,孔子從儒家倫理的角度講評《詩》有“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德育教化的功效。通過《詩》能“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學習和掌握許多自然知識。《禮記·王制》中說“陳詩以觀民風”,說明《詩》含有民風民俗等文化內容,被統治階級借以考察時弊,從而調整自己的政治。魏晉時期曹丕打破儒家“三不朽”以德為首要的觀念,提出文章才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關鍵,雖體現魏晉時期人的自覺意識,但仍然沿襲文的功用主義思想。唐代韓愈提出文以貫道的主張,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提出“文以載道”的觀點,認為文學是“道”的表達。總之,中國古代文化的實用理性精神,輻射于文學,影響到實用主義文化批評觀念的構成,一脈相承到文學作為宣傳新文化、啟蒙民智工具的近代改良主義和五四啟蒙主義,如20世紀30年代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等。出現了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小說功用論、陳獨秀胡適等的白話文學論、周揚等的無產階級文學論等。到20世紀90年代以后,面對大眾化、市場化的文藝現狀,在西方現代和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下,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化批評潮流。
18世紀之前,西方文學被視作一種技藝活動,直接融于其文化語境中。古希臘的史詩和悲劇是歷史、神話、哲學的形象再現,這個時期的藝術論充溢著濃濃的哲學氣息,映射著古希臘人愛智慧求真理的理性精神。柏拉圖認為文學是“影子的影子”,不真實,還會激發人們有害的情緒,影響其理想國的統治,“詩人的創作是真實性很低的;因為像畫家一樣,他的創作是和心靈的低賤部分打交道的。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拒絕讓詩人進入治理良好的城邦。因為他的作品在于激勵、培育和加強心靈的低賤部分,毀壞理性部分”[6]。而亞里士多德認為詩比歷史更具真實性,肯定文學的認識價值。自18世紀起,文學作為美的藝術從技藝中獨立出來,更凸顯表達的審美性而弱化其實用功能,文化作為影響文學的外部因素介入于文學批評活動。啟蒙主義反對古典主義的規則化,秩序化,倡導自由、民主、博愛等人本主義思想,康德說:“啟蒙就是人類擺脫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無法運用自己的理智。”[7]萊辛站在啟蒙立場,他的《拉奧孔》回擊高特舍特與溫克爾曼的保守主義觀點,歌德評價說:“這部著作把我們從一種可憐的觀看的領域里引到思想自由的原野。”狄德羅打破悲喜劇界限,提出介于悲劇和喜劇之間為“第三等階級”服務的正劇主張,是其啟蒙思想的智性結晶。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提倡天才、想象、情感的創作觀念,偏重啟蒙中的自由主義,倡導回歸自然、崇尚古代。現實主義文學直面資本主義社會現實,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問題,這個時期的文學批評在實證主義哲學影響下,以社會學為視閾,形成研究文學與政治、制度、環境等外部因素關系的理論,體現出文學批評的科學主義精神。恩格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在對《城市姑娘》《人間喜劇》以及《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批評中,提出了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文學主張。20世紀西方現代文化批評以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和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為核心,以弱勢群體文化為切入點,對精英和霸權主義文化發出質疑,對大眾文學進行批判。
四、《關雎》作為文化文本的解讀
《詩經·關雎》中寫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雎》講述了發生在匹配度相當的君子和淑女之間的一場勢均力敵、互相尊重和珍惜彼此的愛情故事,雖沒有轟轟烈烈的浪漫主義,但卻溫暖和煦雙向奔赴。因為雙方在處理情感的時候,都恰到好處地把握分寸,彼此成就,既符合當時社會倫理也充分表現出個體的情感訴求。君子雖飽受相思之苦,但恪守禮儀,未有非分之舉,以琴瑟示好,說明雙方情感追求中的精神需要,這是一場具有靈魂質感的愛戀。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關雎》作為篇首,情愛觀經得住儒家思想的檢驗,所以“思無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符合儒家“中和”“適度”的倫理觀,說明《關雎》所表達的“食色性”是向善而美的。漢代《詩大序》評《關雎》別出一格,以女性為視點,認為《關雎》宣揚符合封建倫理的女德觀,“《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從君子“輾轉反側”的追愛之路可以看出淑女是一個含蓄委婉、賢良淑德的女子,具備賢內助的德行,是那個時代婦女的典范。在以家庭為基本單元的封建社會,賢妻良母是家庭和睦的關鍵所在,在《大序》論者思想中淑女的節制之舉,會有效防止夫君因縱欲而疏于家國的治理,這種解讀雖有偏頗之嫌,但寄予之意尚可理解。所以《詩大序》有“危言大義”的言過之失,卻也有些許道理。但“《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這種牽強附會的闡釋,大可質疑,但也充分體現出儒家解讀文本的文化訴求。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隋所以而皆可也。于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于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真可謂儒家解讀之精髓。
對于《關雎》藝術“形式”的文化內涵,就樂律而言,“風”是“具有地方特點的土風歌謠”,體現屬地“樂”的民間特征。就創作的感興而言,這種象意互文的藝術表達,注重主客體的互融共生,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一元思維的特質和直覺體驗的審美傳統。
如果從內容層面解讀,《關雎》可以釋讀為兩種愛情文本:一種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版;另一種是失戀版,可以釋放出不同的文化意蘊。前者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含蓄文雅的謙謙君子和品德美好、委婉含蓄的淑女。兩個人共同“演繹”了一場門當戶對的愛情故事。在戀愛過程中,君子以禮節欲,符合儒家君子的言行標準,淑女同樣壓抑自己的欲望,遵守古代女德規范,雙方“發乎情,止于禮”,在交往中,以“琴瑟”答酬互為友之,尋求靈魂的共鳴,是一種非常純凈的情感交流,體現了雙方對美好愛情的崇尚和尊重。當雙方已經達到琴瑟和鳴的內在認同后,自然而言走進“鐘鼓樂之”的莊嚴的婚姻殿堂。這無疑是中國傳統“家”文化觀念的具象呈現。而如果把《關雎》作為失戀文本來解讀,一個被拒絕的君子,盡管痛苦,卻沒有一廂情愿、死纏爛打的行為,既保留自己的體面,同時也充分尊重淑女的抉擇,不自覺地體現出非常樸素的現代社會才具有的男女平等觀念。把悲傷留給自己,不傷害對方,有仁愛之心。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不偏激,不走極端,雖遺憾卻美好,不消沉,積極樂觀,對美好愛情充滿向往,堅信屬于自己的那份情感終會到來。天涯何處無芳草?放下那份不該有的執念,終會迎來自己心儀的淑女(“鐘鼓樂之”),既體現道家的安時隨份,又體現儒家達觀向上、與人為善、以和為貴的文化精神。陳曉明在《建構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一文中認為:“把‘信奉天地造化,以仁愛為本;厚德化育,為萬世開太平’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精神傳統。”[3]由此可見《關雎》這一愛情文本之所以被儒家重視,其思想內容是符合傳統文化精神的價值追求的。
五、文化批評的實踐特征
(一)一般文化批評
通過對《關雎》文本的文化解讀,本文對如何進行一般文化批評提出一定的參考建議。首先針對具體文本確定文化批評方向或視角。《詩》據傳由孔子收集整理而成,后經漢儒的注疏,形成三家詩(失傳)和毛詩即流傳至今的《詩經》。作為儒家經典,自然會以儒家文化釋詩進而形成闡釋傳統。所以,進行文化批評的第一步先要確定文本與具體文化的關系,整理解釋評價相關文獻,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新的意義挖掘,自然具有批評的新文化視角。其次,經過文本細讀,思忖文本藝術形式和內容所蘊含的文化觀念。《關雎》的文化批評內容具體涉及兩個方面:第一,《關雎》藝術形式的文化特征;第二,《關雎》文本內容和文學形象及其主題思想所體現的文化內容。
當然,對《關雎》文本的文化批評不足以囊括當下文化批評的全部實踐特征。借鑒王先霈《文學批評原理》中的相關觀點以及我國目前學術界以文化為視角研究文學的論說,總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的批評要點:第一,針對民族意識較為濃厚比如阿來的《塵埃落定》、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等類似的文本,主要“挖掘特定民族文化心理對作家創作及文本意義的影響”。第二,具有鮮明地域風格的創作,比如東北作家群的小說、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等,主要“揭示地域文化對作家創作及文本意義的影響”。第三,關于敘講家族史、民族史、人類史等尋根性質的文本,比如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歌德的《浮士德》,或者像上述阿來、遲子建的創作等,可借鑒弗雷澤和榮格理論,對其所蘊含的“原型”(原始意象比如“神話或者儀式”“智者或者救世主”等)加以探析。第四,在更迭交錯歷史時期的文學,比如五四新文學、20世紀80年代新時期文學等,分析“文化沖突與變遷”所帶來的歷史影響,是文化批評較為重要的內容。總之,文本蘊含的文化屬性,既體現文本思想的普遍性,同時也會形成共文本的藝術規律,即文化是文學文本內外不可或缺的本質要素,所以在各種批評思潮此起彼伏的漲落中,文化批評仍然保持新潮魅力,直到如今,仍是學術界較為關切的話題。
(二)原理論建構下的現代文化批評
嚴格意義上,具有系統理論支撐并形成流派的文化批評是指西方20世紀30—40年代在德國興起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和20世紀60年代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針對西方現代技術主義的產物——大眾文化,法蘭克福學派采取嚴厲的批評態度,認為大眾文化以娛樂化的策略,制造各種形式的娛樂消費,借以麻醉大眾,使大眾喪失反思社會的能力。伯明翰文化研究范圍極其廣泛,各種突出的社會現象都成為其研究的對象。他們關注英國工人階級的群體文化,以及各個階級和集團的文化權利等問題,反對霸權主義,質疑主流文化,把文學泛化為一種文化創造活動。可見,西方現代文化批評,具有批判解構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精英文學受到巨大沖擊,大眾文學、俗文學異軍突起,與西方后現代思想不謀而合,引起學界廣泛的關注,中國當代文化批評由此而興起。
現代文化批評具有批判、對話、平民主義等色彩,旨在為弱勢群體發聲,來對抗文化霸權主義,是一種泛文學批評。如何針對文學文本進行操作?首先,要從其原理論與文學關系入手。喬納森·卡勒認為:“從最廣泛的概念上說,文化研究的課題就是搞清楚文化的作用,特別是在現代社會里,在這樣一個對于個人和群體來說充滿形形色色的,又相互結合、相互依賴的社團、國家權力、傳播行業和跨國公司的時代里,文化產品怎樣發揮作用,文化特色又是怎樣形成、如何構建的。所以總的說,文化研究涵蓋了文學研究,它把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實踐去考察。”[8]卡勒的觀點提示批評者,現代文化批評視文學為一種文化現象而進行闡釋,研究其在社會、集團、群體、個人中如何產生、構建、發生影響和作用的,比如在現代文化批評理論影響下出現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新歷史主義文學批評等,都是較為典型的文化批評觀。其次,現代文化批評理論源頭在歐美國家,是針對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而進行的研究,本身已經構入西方社會的文化體系中,我們不能按圖索驥,要結合中國當下文學的現實,有尺度有針對性地借鑒批評,進而融合中國傳統文化,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批評理論。最后,要切實進行調查分析,做好歷史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實事求是撰寫具有現實針對性的文化批評文本。
結 語
目前中國當代文化批評缺乏本土文化的參與,雖有批評的深度和厚度但根基薄弱,后續動力不足,且脫離文學本身,出現為理論而理論的“傳聲筒”的研究現象,逐漸失去文學批評的期待,使文化批評日漸式微。在講好中國故事、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的大背景下,文化批評應該乘勢而為,起到監督引領文學創作的先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