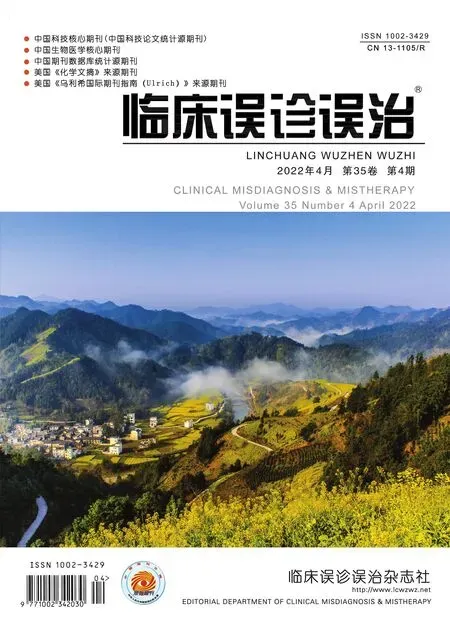軀體疾病誤診為癔癥的臨床分析
蔡占魁,閻同軍,陳方斌,汪 莉,丁松柏,歐陽暉
癔癥是一組以意識、記憶、身份、情感、感知、軀體表現、運動控制以及行為的解離、破壞、中斷為主要癥狀的精神障礙。在一些軀體疾病早期,器質性疾病證據不夠充分,且患者常由于軀體疾病而出現焦慮、情緒不穩、認知功能下降、言行紊亂,此時臨床醫生極易將其誤診為癔癥。本文回顧性分析2007年5月—2020年6月我院收治的4例軀體疾病誤診為癔癥的臨床資料,分析誤診原因,并總結防范誤診措施,現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本組4 例中男2例,女2例;年齡24~46歲。入院前均有心理刺激因素,后出現煩躁、情緒不穩、抑郁及言行紊亂,伴有乏力、抽搐及幻視等癥狀,各項基礎檢查結果基本正常。4例入院后病情均呈進展狀態,原有癥狀、體征漸加重并典型化或出現新的有鑒別意義的癥狀。
1.2被誤診疾病 4例初診均診斷為癔癥,后確診為Guillain-Barre綜合征、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病毒性腦炎、抗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體腦炎各1例。總體誤診時間為1 d~1個月。
1.3誤診及確診經過
1.3.1Guillain-Barre綜合征:女,46歲。因“多處軀體不適、夜間睡眠差2個月”入院治療。患者2個月前因兒子婚戀問題而出現異常,主要表現為夜間睡眠差,入睡困難,有時整夜不眠。多處軀體不適,耳郭下墜感,耳悶,舌麻,喉嚨異物感,進食梗阻感,心悸胸悶,經常惡心,有時嘔吐,四肢乏力,腰酸背痛。全身時冷時熱,熱時大汗淋漓,隨后又出現寒戰。進食量少,尚能堅持工作。曾在當地醫院診治,行頭顱CT、頸椎CT、血常規、心電圖等檢查未及異常,予靜脈滴注藥物(具體不詳)治療5 d未見好轉。遂來我院,門診以“癔癥”收入院。既往史、個人史、家族史無特殊。查體:體溫36.2 ℃,脈搏72/min,呼吸18/min,血壓140/90 mmHg;心肺腹無明顯異常。神經系統檢查:意識清,顱神經無異常,四肢痛觸覺對稱存在,四肢肌力5-級,肌張力正常,病理征未引出。精神檢查:意識清,一問一答,自訴病史,焦慮明顯,繁多軀體不適主訴,情緒低落,智力正常,自知力不存在。入院后診斷為“癔癥”,予鹽酸帕羅西汀片每次10 mg,每早1次,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每次1片,每日2次改善焦慮。治療1 d后癥狀未見好轉,且出現口角略向左側歪斜,入院第2天即突然出現呼吸困難,痰多,口唇發紺,意識不清。搶救成功后轉入神經內科治療。腦脊液檢查示蛋白2800 mg/L,細胞計數正常,呈蛋白-細胞分離現象。根據癥狀、體征及腦脊液檢查,明確診斷為Guillain-Barre綜合征,給予糖皮質激素等治療后痊愈出院。
1.3.2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女,35歲。因“受刺激后言行反常8個月”入院治療。患者父親去世后漸出現異常、敏感,特別在意白色的東西或與白色有關的字詞,易激惹,經常為瑣事與家人爭吵,出現幻聽和幻視癥狀。在我院門診行頭顱CT未及異常,以“癔癥”收入院。既往史、個人史無異常。家族史:姐姐曾患產后抑郁。查體:體溫36.8 ℃,脈搏72/min,呼吸18/min,血壓130/72 mmHg;心肺腹無明顯異常;神經系統檢查無異常。入院精神檢查:意識清,一問一答,答話切題,有原素性幻聽及幻視,病情有明顯的心理誘因,情緒焦慮,有超價觀念,智力正常,定向良好。入院后血常規示紅細胞2.68×1012/L,血紅蛋白84 g/L,白細胞3.5×109/L,余實驗室檢查未見異常。頭顱MRI、腦電圖無異常。診斷為“癔癥”,給予奧氮平片每次10 mg,每晚1次,氫溴酸西酞普蘭片每次40 mg,每早1次控制精神癥狀;硫酸亞鐵片每次0.3 g,每日3次改善貧血。經治療1個月后,效果不佳,仍有幻視癥狀。且漸出現四肢麻木、乏力、走路沉重感。神經系統檢查示四肢肌力正常,肌張力正常,雙下肢腱反射活躍,四肢共濟運動不協調。查腦干聽覺誘發電位示雙側1~3峰間期小于3~5峰間期,視覺誘發電位未見異常,體感誘發電位示四肢波形分化欠佳。血清維生素B12水平30 ng/ml,明顯下降。確診為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給予維生素B12、葉酸、硫酸亞鐵等治療后幻聽、幻視等精神癥狀消失,肢體麻木感減輕,步態恢復正常,痊愈出院。
1.3.3病毒性腦炎:男,37歲。因“言行反常1 d”入院治療。患者8 d前無明顯誘因出現眩暈,伴耳鳴、視物旋轉、惡心、嘔吐。就診于當地醫院,診斷為“眩暈綜合征”,行頭顱MRI、胸部CT、腹部、頸部血管彩超、心電圖檢查均未見明顯異常;心臟彩超示二尖瓣輕度反流。患者對心臟彩超結果非常焦慮,反復問醫生。1 d前出現精神異常,答非所問,行為異常。既往史、個人史、家族史無異常。查體:體溫36.7 ℃,脈搏61/min,呼吸18/min,血壓103/56 mmHg;心肺腹無明顯異常。神經系統檢查:顱神經檢查無異常,四肢肌力、肌張力正常,病理征陰性,腱反射活躍,腦膜刺激征陰性。精神檢查:意識清,接觸不合作,數問一答,答非所問,思維散,未及幻覺妄想,呈不協調精神運動性興奮,定向正常。入院頭顱MRI正常,腦電圖顯示廣泛輕度異常腦電圖,血常規示白細胞15.4×109/L,肝、腎、心肌功能正常。無頭疼、發熱等癥狀,病理征及腦膜刺激征陰性,入院后考慮為“癔癥”,給予奧氮平片每次20 mg,每晚1次,氯硝西泮片每次1 mg,每日2次。治療10 d后效果欠佳,且認知功能明顯下降,行腰椎穿刺檢查,腦脊液壓力130 mmH2O,細胞計數21×106/L,蛋白含量120 mg/L,修改診斷為病毒性腦炎。給予阿昔洛韋及糖皮質激素治療后精神癥狀消失,痊愈出院。
1.3.4抗NMDA受體腦炎:男,24歲。因“發作性四肢僵硬、抽搐、言行紊亂5 d”入院治療。由于近期患者與女友爭吵,加之工作不順利,于5 d前出現精神異常,主要表現為煩躁不安,易怒,入睡困難。時常感頭脹,頭面部、四肢皮膚麻木不適,有時四肢緊張、僵硬,至當地醫院就診,考慮為“應激障礙”,予鹽酸氟西汀膠囊、阿普唑侖片等治療(具體劑量不詳),效果不佳。后出現躁動不安,言語及行為異常,四肢僵硬、抽搐,無大小便失禁,無口吐白沫,送至當地醫院就診,給予苯巴比妥、地西泮處理后(具體劑量不詳)收入ICU,住院期間經常出現躁動不安,言語及行為異常,并多次出現四肢抽搐發作(具體發作頻率及時間不詳)。查頭顱CT、腦電圖無異常,經該院神經內科會診后考慮為“癔癥”,轉入我院。查體:體溫36.9 ℃,脈搏88/min,呼吸18/min,血壓131/84 mmHg。在藥物作用下處于嗜睡狀態,查體不配合。心肺查體陰性,雙手雙膝有多處皮膚擦傷,已結痂,四肢有多處瘀斑,下唇及口腔黏膜潰瘍。神經系統檢查:四肢肌力、肌張力正常,病理征陰性。精神檢查:臥床,處于嗜睡狀態,大聲呼喊、搖晃時能睜眼觀看,有時能轉動頭部,偶爾出聲,吐詞不清晰,不能通過搖頭、擺手等表達想法,無蠟樣屈曲及違拗表現;無模仿動作重復語言,大小便不能自理;對外界事物無情感反應,無表情變化,令其做張口伸舌動作不配合,對時間、地點、人物及自身處境無辨認能力;無典型幻覺妄想,存在意識障礙,注意損害及認知功能紊亂。入院后考慮外院診斷“癔癥”理由不充分。修訂診斷為“器質性精神障礙,癲癇”,行腰椎穿刺檢查,腦脊液壓力260 mmH2O,白細胞計數8×106/L,蛋白273 mg/L,抗NMDA受體抗體IgG為1∶100。確診為抗NMDA受體腦炎,轉至外院治療。
2 討論
2.1疾病概述 癔癥為《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3版[1]中的診斷名稱,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和《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統一將癔癥命名為分離障礙[2-3]。癔癥是一類由精神因素,如重大生活事件、內心沖突、情緒激動、暗示或自我暗示,作用于易感個體引起的精神障礙,可表現為解離癥狀與轉換癥狀。解離癥狀指部分或完全喪失對自我身份識別和對過去的記憶,轉換癥狀指在遭遇無法解決的問題和沖突時產生的不快心情,以轉化為軀體癥狀的方式出現。這些癥狀沒有可證實的器質性病變基礎。其患病率為0.8%~2.8%[4],青春期和圍絕經期女性更高發。相關研究認為,癔癥的病因有多種,是生物因素、精神因素和社會文化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結果[5-6]。梁文香等[7]報道顯示,癔癥有家族聚集傾向,血緣關系越近,患病率越高,推斷癔癥的遺傳方式可能為多基因遺傳。癔癥人格特征是癔癥發病的重要基礎,有研究證實,癔癥患者常存在異常的人格特征,故而對應激因素出現不恰當的反應,在癔癥的發病過程中起重要的作用[8-9]。癔癥患者腦的結構及功能影像學改變常表現為眶額皮質、海馬、海馬旁回和杏仁核等腦區的活性和體積異常[10-12]。
癔癥診斷較復雜,大多數情況下仍屬排除性診斷,各種癔癥有時也可能與某些器質性疾病的早期癥狀非常相似[13-15]。臨床診斷常用以下標準:①由心理因素誘發,②找不到器質性疾病,③可接受語言暗示影響;故而臨床醫生僅憑以上標準便做出癔癥診斷,并不十分可靠。目前,癔癥的治療尚無特效藥物,主要是在心理治療的基礎上給予對癥處理[16-18]。
2.2誤診原因分析 ①癔癥癥狀變化多樣,且缺乏特異性診斷標準。癔癥可以出現其他各種疾病的表現,而器質性疾病起病初期,其癥狀特征未充分出現時,常表現為一些軀體不適癥狀,易誤診為癔癥發作。加之前期心理應激因素及焦慮、抑郁、言行紊亂等癥狀,更易誤診為癔癥。②許多患者家屬在提供病史時常側重于受刺激及精神癥狀,而醫生對伴有精神癥狀的患者常做出“精神疾病”診斷,不能深究其精神癥狀為原發性還是繼發性。本組病毒性腦炎和抗NMDA受體腦炎患者由外院神經內科轉入我院,表明醫生缺乏對精神癥狀背后器質性原因缺乏關注及深入探究。③對一些神經內科疾病認識不足,不能及時發現疾病的典型癥狀及體征,無法做出準確的鑒別診斷,均以癔癥診斷做出合理化解釋。④存在認知偏差,認為僅憑頭顱MRI、心電圖、實驗室等常規檢查就可以排除器質性疾病,且對一些異常檢查結果未探究原因,輕易放過。如本組脊髓亞急性聯合變性患者入院時紅細胞及血紅蛋白均降低,未進一步分析并查明是何種原因引起的貧血。⑤缺乏動態觀察,如忽視對病情的縱向了解和觀察,只著眼于當前和某一個橫斷面的癥狀,未對疾病的演變狀況進行動態全程的觀察和分析,也會導致誤診。
2.3防范誤診措施 ①臨床醫生尤其是精神科醫生要加強對神經內科相關知識的學習,提高對神經內科疾病的認識,豐富臨床實踐。某些器質性神經疾病除精神癥狀之外,還會有一些原發疾病的特征,只有系統掌握神經內科知識,才會及時發現這些特征。②要詳細詢問病史,認真進行全面的體格檢查及必要的輔助檢查,而且體格檢查及輔助檢查要多次進行,才能發現其漸進性變化。③要認真對待新出現的癥狀,不能一以貫之認為是精神疾病導致的,仍以癔癥來解釋出現的新癥狀,就會出現誤診,尤其是一些與功能性疾病診斷相矛盾的癥狀及體征。④糾正認知偏差,不能僅憑頭顱MRI、心電圖、實驗室等常規檢查就排除器質性疾病。⑤及時進行多學科的聯合會診。
綜上所述,做出癔癥診斷時要慎重,不僅要考慮其應激因素、精神癥狀,還要重視其軀體不適主訴,并進行嚴格的體格檢查。同時進行疾病的動態觀察,摒棄先入為主的思維,拓寬診療的思路。當癥狀進展或出現新發癥狀時要評估該癥狀是否符合原診斷,尤其在出現矛盾現象時要考慮診斷的正確性,并進行有針對性的檢查,以鑒別器質性疾病,避免誤診漏診,延誤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