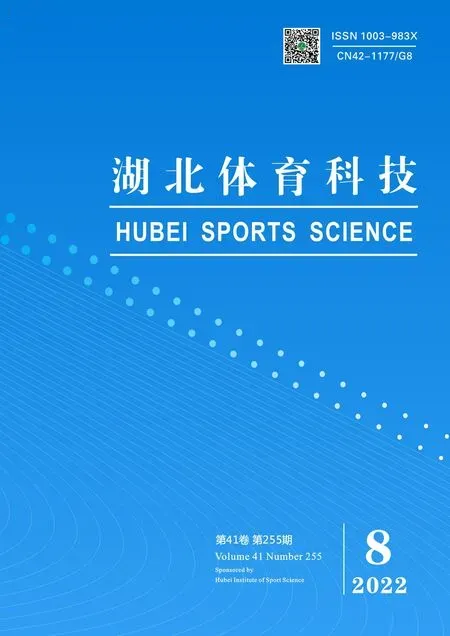自治單元下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新路徑
向楊周,廖 萍,秦小平
(三峽大學 體育學院,湖北 宜昌 443002)
在21世紀初稅費改革時,我國農村地區大規模興起了“合村并組”浪潮,雖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導致了傳統自治單元的地域擴大、人口增多、干部減少,給農村的自治造成了困境。為解決這一困境,2014至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連續提出了“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的任務要求,學界和政界為此進行了大量積極有益的探索,自治單元下沉就是其中最有效的路徑之一。自治單元下沉是指在以行政村為基本自治單元的基礎上,將村民的自治活動通過自然村、村落、村民小組、農村社區、院落、理事會等形式進行下移[1-2],該方式能提高村民與村內公共服務之間的利益聯結度,促使農民自愿參與村莊治理,成為鄉村治理的“主人”,增強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實現了農民的有效自治,因此也被廣泛應用于農村的治理實踐中。在農村公共服務方面,自治單元下沉能使公共服務直面農民群體,回應了農民的切實需求,提高了農村公共服務的精準度[3]。
農村體育公共服務面臨著精準度不高,難以滿足農民需求的難題。為此,有學者提出通過農民參與體育公共服務治理的方式來提升現有的治理水平[4-6],但自治單元擴大帶來的村級自治功能弱化以及農民參與農村治理事務邊緣化,使得農民這一治理主體長期缺位。自治單元下沉正可為農民參與體育公共服務治理提供平臺,促進農民參與體育公共服務治理。鑒于此,課題組選取合村并組后自治效果好且有特色的部分行政村進行實地調研,涉及秭歸縣、大冶市、松滋市3縣(市)5個行政村,既有偏遠山區、合村規模較大的秭歸縣白鶴洞村與趙家山村(其中白鶴洞村是全國首個農村社區,公共事務自治基礎好,治理效果佳);也有分村民小組建設體育設施、開展體育活動較多的大冶市山區朱鋪村;還有平原地區的松滋市火連坪村、楊家河村(其中楊家河村為臨鎮村)。本文將以此剖析自治單元擴大背景下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的問題及其成因,探討以自治單元下沉促使農民開展體育公共服務自治的可行性,以期為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提供新路徑,提升現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水平與治理效能。
1 自治單元擴大背景下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問題透視
1.1 內需未得滿足
農民對體育公共服務的滿意度是衡量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標[7]。但合村并組以來,行政村擴大帶來的體育公共服務設點過少、項目單一、指導缺位等問題,致使農民對體育公共服務的獲得感并不強,其內生性的體育需求也未得到滿足。
1.1.1 設點過少,場地設施資源不可及
《全民健身計劃綱要》提出要把體育場地設施建到農民身邊,目的在于解決好農村體育公共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問題,提高體育公共服務的可及性。賀廣瑜[8]等人提出的農村一次生活圈,即以次中心村為服務單元,步行時間在30min內,服務半徑為2km,能夠滿足農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但在實際調研中發現,除朱鋪村擁有9處體育場地設施外,僅趙家山村、火連坪村、楊家河村設置有1處體育場地設施,并多集中于村委會,致使體育公共服務在空間上仍然距離農民較遠,無法滿足農民的體育健身需求。尤其是處于偏遠山區的趙家山村,距離村委會較遠的村民更是無法近距離享受到政府提供的體育公共服務。
1.1.2 項目單一,服務內容不可獲
合村并組以來,無論是2003年湖北省啟動的“兩打兩曬(賽)”工程,還是2006年以來全國范圍內開展的農民體育健身工程,均只涉及籃球與乓乓球這兩個項目,缺少對其他體育運動項目的提供,導致現有體育公共服務的供給與農民的實際需求匹配度不高。在調研的5個行政村中僅大冶市朱鋪村提供有足球項目(足球場為扶貧期間修建),另配套有部分健身器材。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農民對體育公共服務的需求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不同人群所愛好的體育運動項目存在差異,不切實考慮實際農民的體育需求,仍提供單一運動項目的體育公共服務,難以滿足農民的體育需求。
1.1.3 指導缺位,服務質量難保障
農村體育公共服務的指導缺位主要體現在組織、技術、人員的缺位,其中社會體育指導員的缺位較為突出,直接影響著農民接受體育指導服務。現階段90%的社會體育指導員集中在城鎮[9],未推進至鄉村一級,課題組調研的5個行政村均未配備社會體育指導員,僅朱鋪村的扶貧工作隊在暑假期間組織該村學生進行體育活動,可見農民在健身知識、信息與技術等方面缺少專業指導,加劇了農民在體育公共服務上不可獲的狀況。國家體育總局在2017年提出了“在2020年實現80%以上行政村配備有一名以上的社會體育指導員”的工作目標,但即使每一個行政村配備有一名及以上的社會體育指導員,村域面積大與人口之多也增加了體育指導服務工作的難度,導致農民享用體育公共服務指導的切身體驗感不佳。
1.2 外力制約自治
行政村過大帶來了社會聯結程度松散、村干部無力顧及自治事務、農民參與治理的積極性受挫等問題,弱化了村莊的自治功能,制約著農村體育公共服務自治的開展。
1.2.1 社會聯結程度松散,不利于開展自治工作
社會聯結是指村民在生活交往中所形成的緊密關系,社會聯結的程度越緊密,越利于村民自治的開展[10]。在秭歸等地調研發現,合村并組前居住在同一村莊的村民互相熟悉,彼此了解,親緣關系濃厚,經過了長期的磨合,村民之間的社會聯結度較高,因此在開展村莊公共事務時,能夠很快達成一致意見,利于集體行動的開展。而合村并組以后,來自于不同村落或村民小組的村民之間囿于空間距離,交流起來比較困難,共同利益較少,彼此認同度較低,相應的村民之間的聯結度也較為松散,也就難以將村民匯聚在一起開展農村體育公共服務的自治工作。
1.2.2 村干部疲于行政事務,無力顧及自治事務
合村并組后,管轄范圍的擴大增加了村干部的工作量,加劇了村級自治工作的難度。另外,合村并組帶來了行政化色彩過重與自治懸浮,村干部在實際工作中常疲于應對行政事務,而無暇顧及村級組織的自治事務,進而失去了開展自治工作的動力。
體育公共服務治理問題多被淡化或忽視處理,其具體表現在:一是在5個行政村的村級干部職責宣傳欄未發現有關體育治理事務具體職責的劃分,在村級事務公開欄中也未了解到有關體育公共服務的運行情況。二是在與調研地的村干部的交流中,村干部表示村內面臨的公共事務多,行政壓力較大,在水、電、路等公共服務與行政事務上投入精力較多,對體育公共服務治理關注較少。
1.2.3 農民積極性受挫,體育自治落地難度較大
受體育公共服務供需錯位與需求表達渠道不暢的影響,農民在獲取體育公共服務上的積極性受挫。一是過大的行政村單元,不同村民小組的農民在體育愛好興趣上各有差異,由于受到地域、資金、人手的限制,在進行體育公共服務供給時,很難照顧到全體村民的感受。二是農民在表達體育公共服務的需求時,面臨著需求表達渠道不暢等問題,加之來自于不同村民小組的農民,共同利益少,自治性較弱,重自我利益,輕集體事務,很難就體育公共服務治理達成一致意見,使得體育自治落地難度較大。
2 自治單元下沉作為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路徑的可行性
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中的自治單元下沉是指通過劃小體育公共服務的治理單元,在更小的治理單元內開展體育公共服務的自治,并將現有的體育資源下沉到自然村、村民小組、農村社區等進行微治理,最終實現精準服務的過程。
2.1 自治單元下沉的價值
2.1.1 促進體育善治
善治的本質特征是指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11],體育善治的實現離不開政府與農民等治理主體共同進行體育公共服務治理。自治單元下沉為體育治理提供了一條農民參與治理的路徑,在以自治單元下沉開展體育治理的過程中,農民依托農村社區或村落參與體育治理,進行自我服務以滿足體育需求,可實現由享有者到主人翁的身份轉變,成為體育治理的主體。政府通過有效介入治理可以更好地了解農民的體育需求,因地因需制宜進行精準化體育公共服務供給,從供給端進行優化來滿足農民的多元化體育需求,提高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的精準度。
2.1.2 延伸體育服務
已有的實踐表明,通過“服務下沉”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村公共服務的“最后一公里”難題[12]。自治單元下沉正是將體育公共服務的服務半徑進行縮小,進而將服務延伸至農村社區。一是在農村社區內利用獨特的地理環境,挖掘豐富的體育運動項目資源,開展農民喜聞樂見的體育活動,能夠彌補體育設施不足,供給項目單一問題,有助于提高體育公共服務的可及性。二是創新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體系,在農村社區設立體育服務站,從農村社區內培育體育指導員,發揮社區“能人”的帶頭示范作用,在社區內帶領村民開展體育相關的運動項目,可進一步將體育公共服務延伸至戶,以打通體育公共服務的“最后一公里”。
2.1.3 盤活體育資源
農民利用社區內現有的資源進行自我服務,有利于盤活體育自然資源與體育人文資源。通過合理利用農村社區內的地理環境因地制宜開展體育運動項目,能夠彌補體育場地設施建設與運動項目供給等方面的不足,滿足不同人群的多元化需求。例如,水資源豐富的農村社區可開展劃船、賽龍舟與游泳等體育項目,環山的農村社區可開展登山、徒步與跑步等休閑運動項目。
再如滾鐵環、跳房子、打陀螺等一些民間豐富的體育游戲;山東鼓子秧歌、秭歸花鼓舞、長陽巴山舞、陜北腰鼓這類一地域性民俗舞蹈;以及苗族的射弩、回族的打木球、哈薩克族的叨羊等民族體育娛樂活動,深受當地農民群眾的喜愛,構成了各地區各民族豐富的體育人文資源。在農村社區內開展這類特色體育運動項目,能彌補現有體育項目的供給不足,還能起到建設社區文化與宣傳地域文化的作用。
2.2 自治單元下沉的基礎
2.2.1 關系基礎
社會聯結是影響村民自治基本單元的關系基礎,與村莊范圍的大小緊密相關[10]。在適宜大小范圍的村莊內,人口規模適中,村民間有著較高的認同感與凝聚力,彼此之間的社會聯結度相對緊密,能夠為維護公共利益而組織起來采取集體行為進行自主治理,便于解決農村公共事務[13-14]。一個社會聯結度較高的自治基本單元,將有利于農村體育公共服務自治的實現。
農村社區的面積為1至2km2,人口規模在30至50戶,約為100至200人[15],有著地域相近、人口適當、便于管理等特點。在農村社區中,農民之間的團體凝聚力、彼此的認同感、利益聯結度、社會聯結較高,有著共同的處事模式,建立有共同的行為準則,組織集體活動與開展自主治理較為容易,為體育公共服務自治奠定了良好的關系基礎。
2.2.2 歷史基礎
在自治單元下沉的實踐探索中,湖北秭歸與廣東清遠兩地建立起新的治理體系并進行了人員的配備,縮小了服務范圍,實現了當地的有效治理,能夠為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提供經驗借鑒。
湖北秭歸依托村落、社區開展自治工作,現有村落(社區)的平均服務面積為1.18km2,較合村并組前縮小了51%[16]。并建立起“行政村—村落(社區)”的治理體系,設置有以理事長為首的“二長八員”制度[13],開展了“村落夜話”與“屋場會”等自治活動。通過這一些列的改革創新舉措,實現了自治權的下放,促進了公共服務的到位,激發了村民的積極性,增強了農民的主體意識,因而在信息傳達、公共服務、村落工作方面大大提高了治理效能。
廣東清遠則建立了“鄉鎮—片區—行政村—村民小組(自然村)”的治理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創新了以“鄉鎮公共服務中心—片區公共服務站—行政村公共服務站—村民小組(或自然村)服務代辦員”的公共服務體系[15]。清遠的這一做法理順了自治機制,將公共服務的重心延伸至村民小組(自然村),實現了服務村民與村民自治的均衡治理,有效增強了村民小組內公共服務的管理與服務能力,并在2016年入選了全國“創新社會治理典型案例”,被評定為最佳案例。
自治單元下沉的“秭歸模式”與“清遠模式”對體育公共服務自治有著幾點啟示。一是將治理體系延伸至農村社區,縮小服務半徑。通過在農村社區內開展體育公共服務治理,能提高體育公共服務供給的精準度,實現體育公共服務的微治理。二是將服務體系向下進行延伸,設置農村社區體育指導員。通過在農村社區內開展體育指導工作,便于了解農民的體育需求和開展體育指導工作,有利于提高體育公共服務的可及性。
2.2.3 政策基礎
農村體育公共服務自治的實施需要鄉村治理體系做支撐,更需要建設體育人才隊伍,這一切都離不開相關政策的保障。近年來,國家從最高層面連續出臺了各類相關政策確保鄉村治理體系的完善與人才隊伍的建設。
2014年到2018年,連續5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支持探索以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開展自治的相關工作,表明國家從政策上高度重視村民小組的自治工作,對自治單元下沉在農村治理中發揮的積極作用給予了肯定。在政策的指引下,經過5年的自治實踐探索,為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深化村民自治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也為基于農村社區的體育公共服務治理帶來了發展機遇。
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17]第二十條明確提出要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把更多資源下沉到鄉鎮和村,推動人才下鄉,動員群眾參與鄉村治理。2021年召開的全國兩會提出要健全城鄉社區治理和服務體系,多渠道建設鄉村治理人才隊伍。同年頒布的《關于加快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意見》文件,提出要加強文化旅游體育人才隊伍建設,推動人才下鄉服務。上述文件政策均為鄉村體育人才隊伍建設提供了指引,有助于完善和建設鄉村體育人才隊伍,為農村社區開展體育指導服務創造了前提條件。
2.2.4 現實基礎
課題組對5個行政村的調研發現,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與農民健康健身意識的覺醒,部分農民開始自發組織成小團體進行體育鍛煉。這類小團體由臨近或同一“社區”和“村落”的熟人組成,構成了體育運動單元,具有人數少、地域近、易管理的特點,開展著廣場舞、羽毛球、跳繩等體育運動項目,并能夠通過集體的體育鍛煉行為滿足個體的體育需求。由此看來,該團體能夠在體育鍛煉上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具備了自治的相關條件,為體育公共服務的自治奠定了基礎。此外,地理環境、海拔氣候相似、人口規模適當的農村社區,利于組織和開展相同或相近的體育運動項目,有助于提高農民體育運動的參與度。在此基礎上因地因需制宜提供體育公共服務,能更好地滿足農民的體育需求,從供給端提升體育公共服務的效率,亦能提高農民參與體育治理的積極性。
3 當前制約農村體育公共服務自治單元下沉實施的因素分析
前文探討了自治單元下沉作為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路徑的可行性,但仍存在“人、財、制”等因素制約著自治單元下沉路徑的實施。其一是“人”的因素,體現為體育人才匱乏;其二是“財”的因素,表現為資金投入不足;其三是“制”的因素,即當前的機制體系不完善。
3.1 “人”是下沉的基礎,體育人才制約著自治的服務水平
體育公共服務自治過程中的體育技能傳授、健康知識普及、體育意識培育均需要體育人才作支撐。但調研發現,現階段農村體育人才的外部供給不足,內部亦缺少懂體育知識、技術與技能的人員,這不利于自治服務水平的提高。一是自村級小學被撤銷實行鄉鎮集中辦學以來,村一級僅有的數名體育教師和愛好體育運動的教師被集中到鄉鎮,導致村一級缺少懂體育知識與教授體育技能的人員。二是在高考政策恢復后,農村地區走出了不少知識分子,這類群體進入城市并定居,對體育的認識要高于農民,多忙于生活與工作且生活在農村的時間較短,尚無余力建設家鄉。三是農村青年進城務工或進入城市完成學業,學習或掌握了部分體育技能,但這類群體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待在農村的時間較短,其體育意識與體育文化知識未能在農村得到有效發揮。
3.2 “財”是下沉的關鍵,資金投入制約著自治的設施建設
農村體育場地建設、體育活動開展與人才隊伍培育離不開資金投入作保障。但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建設所需資金絕大部分來源于國家財政撥款[18],市場投入較少。首先,政府撥付的財政經費多用于民生類緊需和必需的公共服務上,諸如飲水工程、醫療衛生與道路硬化等,在資金預算有限的情況下,就會減少體育健身工程這類非必需公共服務的投資。其次,體育公共服務的公益性與企業的逐利性之間存在矛盾,企業考慮到農村體育公共服務的投入大,收益小且周期長等特點,就很難將資金投入到農村體育公共服務上。
再從農民的經濟收入水平來看,該群體的收入水平較低,難以負擔起體育場地建設等費用。2020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 131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 189元[19],與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農民的經濟收入較為有限。而在農民的消費中,用于生活、教育以及醫療等的開支占了很大比例,體育消費能力較弱。此外,農村地區體育消費空間有限,農民的體育消費理念不強,對體育消費和投資的積極性與欲望也較低。
從理論上來看,通過治理單元下移進行體育公共服務的自治,其理想化狀態是在各農村社區或村落建設體育場地,但資金投入的不足,直接影響到農村體育場地設施的建設與完善。
3.3 “制”是下沉的保障,機制體系制約著自治的落地實施
農村體育公共服務的治理機制與治理體系是自治單元下沉末梢延伸至農村社區的重要保障。當前農村體育公共服務的治理存在著農民需求表達體系欠缺、評價機制欠缺、決策機制僵化等問題[6],加劇了供需錯位現象。在農村體育管理體制上,我國長期實行“縣(區)—鄉鎮—村”三級管理體制,但體育管理工作并未在村一級得到實質性的開展,多由鄉鎮政府統一進行管理。在農業稅費改革后,受國家政策與行政任務增加的影響,鄉鎮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鄉鎮政府也多以重點任務尤其是中心工作的推進為著力點,在此過程中注重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收益[20],而體育公共服務具有公益性,投入大,難以用最小成本換取最大收益。再者,部分管理者對體育工作的認識程度不高,未能重視開展農村體育工作,亦導致了相關體育公共服務體系與體制不健全。村一級的體育組織長期處于空位狀態,農民缺乏“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渠道,未能使離農民最近的體育組織的作用得到有效發揮。也正是由于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的機制體系的不健全,體育公共服務的自治未能得到進一步推進。
4 農村體育公共服務自治單元下沉治理路徑的優化策略
4.1 發揮人才優勢,提高服務水平
發揮農村各類人才的優勢,能夠彌補體育人才匱乏的現狀。農村大學生村干部、大學生村醫,以及農村地區的大學生、退休人員(教師、干部、企業家等)、下沉到農村的機關干部與教師為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在人力資源上帶來了可能。在體育公共服務的自治中,退休人員及農村精英常被農民認為是“鄉賢”,有著號召力強與文化修養高等諸多優勢,能帶領所在社區開展體育指導與自治工作;農村大學生亦可發揮他們在體育技能、技術、知識方面的才能,在寒暑假開展體育指導工作;大學生村干部熟諳相關政策與自治工作,能作為農民進行體育公共服務自治的指導員以及政策的宣傳員,協助農民開展自治的相關工作;大學生村醫,懂醫療衛生,可以為農民提供體質監測服務。除此之外,還需從農村社區中挑選出后備體育人才,對他們進行專業培訓,教會他們科學的體育知識與技能,讓這類群體能夠在社區中發揮他們的體育才能。
4.2 拓展資金來源,推動設施完善
在體育公共服務自治的過程中,需要拓展資金來源渠道彌補資金的投入不足。一是吸引企業投資農村體育事業。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推進,越來越多的企業將入駐農村,為農村各項事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通過相關政策與機制進行激勵,以此獲取企業對農村體育事業的支持,如對支持農村體育事業發展的企業進行宣傳、獎勵、樹立典型以及給予政策傾斜。二是向有關部門爭取體育事業發展經費。如爭取體育彩票公益金對農村體育發展經費的支持力度,用以完善農村體育設施,建設體育人才隊伍。此外,通過與文化、旅游、農業、鄉村振興等部門進行協商,拿出部分資金支持體育公共服務建設,服務于鄉村文化、體育旅游、鄉村振興等的同步建設。
4.3 健全機制體系,暢通民意表達
健全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機制與體系,讓體育公共服務更加接近基層,接近農民的生活。一方面要健全由“鄉鎮體育公共服務中心—行政村體育公共服務點—社區體育指導員”的服務體系與“鄉鎮—行政村—社區”的治理體系,由鄉鎮政府進行統籌、行政村負責協調、社區負責落實,并由體育指導員負責執行,進而將農村體育公共服務的供給延伸至農村社區,以此拉近農民與體育資源的空間距離,降低農民獲取體育公共服務的成本。另一方面,通過“社區體育指導員—行政村體育服務點—鄉鎮體育服務中心”來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體系與評價機制,以此來了解農民的體育需求,獲取農民對體育公共服務治理的意見,進而為體育公共服務精準供給與精準治理奠定基礎。
5 結語
農民主體參與體育公共服務治理對提升農村體育公共服務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義,為此,自治單元下沉提供了一條體育公共服務治理的農民自治路徑。通過自治單元下沉的方式,在更小的治理單元內開展體育公共服務的自治,并將體育資源下移至農村社區,進一步滿足農民的體育需求,提升農民的幸福感、獲得感與安全感,進而促進農民參與體育鍛煉與體育治理。在這一治理邏輯下,體育公共服務能直面農民群體,增加農民的主體性與主動性,但將治理層級延伸至農村社區,會增加相關政策落實與場地建設的成本,在資源配置的效率上可能會降低。因此,在后續的研究及理論探索中,要解決好上述問題,自治單元下沉作為體育公共服務治理的新路徑才能得到進一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