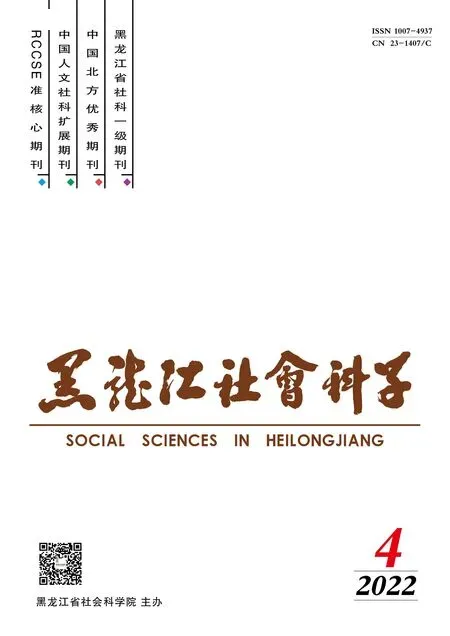中國傳統均平思想的概念史視角論析
林建華,李 敏
(遼寧師范大學 a.馬克思主義學院;b.政府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
問題的提出
每一個概念都有屬于自己的一段歷史,歲月帶來的痕跡深刻且無法磨滅。概念史研究的重點在于概念形成的歷史過程及其歷史應用以及概念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也就是概念如何形塑了社會并被社會所形塑的問題。作為架構語言和歷史現實的橋梁,概念史研究方法可以在很多領域發揮作用,尤其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作用明顯。
從概念史視角出發可以發現,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基本的話語要素,傳統均平概念形成時間長、涵蓋內容廣,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每個思想領域都能發現其身影。公正、平等自古以來就是人們不斷探求的價值追求,也是被社會各階層所普遍接受和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傳統均平觀念相較于古代社會的等級特權意識具有很強的進步性,是現代社會公正公平思想的雛形,體現了我國國民的遠見和智慧。由于受限于時代和歷史,傳統均平思想往往具有保守色彩,只注重分配結果的平等,從而使其實踐效果大打折扣,最終成為烏托邦式的空想。但是,傳統均平思想作為中華文化的優秀成分之一,其中所蘊含的道義的合理性和目標的合理想性是不可否定的,為當下中國構建公平機制和穩定的社會秩序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思想素材。
目前,國內關于傳統均平思想的研究已經粗具規模,尤其是對先秦儒家均平思想的產生背景、內涵及影響的研究,為后續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學術價值和資源。但傳統均平思想從產生至今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其理論內涵、應用實踐在不同時期都有所變化。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例如以前學界在研究均平思想時教條化和簡單化情況嚴重,一些學者甚至覺得平分財富這種思想是農民特有的思想,均平思想也是屬于農民的思想,只有小生產才會講究均平這種思想觀念。可是,追溯歷史上發生的實際情況,人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因此,概念史為中國傳統均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其不僅可以拓寬對該問題的研究視野,而且可以進一步推動對該問題的深入研究。
一、傳統均平思想的歷時性分析
歷時性分析是從縱向看待持續演進活動序列的一種認識方法,對于一個概念而言,其勢必會隨著時代的歷史條件而不斷發生變化,甚至會與最初的含義大相徑庭。因此,在研究概念時,要從縱向的歷史角度將概念放置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全面考量,將其“前世今生”貫穿起來,以便更好地突出“概念氛圍”的識別,從而避免發生時代誤植的錯誤。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均平”就是這樣一個相當特殊而又重要的觀念,歷朝歷代關于均平的主張有很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解讀主要有以下四種。
1.春秋時期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說
孔子雖然不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倡均平觀念的思想家,但孔子的說法毫無疑問是影響最大、最深遠的。《論語·季氏》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論述就是孔子最為集中、最為經典的表達。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歷代政治家的田賦主張以及宋代以后農民起義的綱領大多與這句話有著些許聯系[1]。
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說的背景是季氏要討伐顓臾,針對這件事,冉有和子路二人向孔子尋求意見。在孔子看來,季氏基于“寡”和“貧”的考量去討伐顓臾是不合禮制的,因為對于季氏而言,其最大的“患”在于“不均”和“不安”。此處的“不均”是指季氏越過魯公謀求不屬于他的財富和人口,“不安”是指造成諸侯們的效仿,從而導致政治動蕩。此外,朱熹在《論語集注》中也指出,這里的“寡”指的并非是財富,而是人口這一特殊的資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于一方諸侯而言,相較于封國的勢力范圍和領土面積等因素,擁有一定的人口基數更為重要,因為人口就是最大的財富,其不僅可以提供賦稅供養國家,還可以提供兵役維護國家安全。但結合當時的季氏與魯國的關系可以看出,季氏統治的主要問題不在于缺少人口,而是“無道”和“不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說集中體現了儒家學說的核心價值,即百姓才是政治統治的根本,實現百姓之“均”“安”“和”才是治國安邦之道。同時,孔子認為趨利是人的本性,追求富貴也是正常的人性體現。但在追求富貴的過程中要堅守正道,正所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可見,孔子提倡在富貴與“道”之間實現平衡,在“道”的基礎上滿足人之本性。個人如此,國家亦如此。對于一個國家而言,經濟繁榮、政通人和是必然追求,但在實現這一追求的過程中也應遵循“道”之要求,其中的重要內容便是使百姓過上“均”“和”“安”的生活[2]。尤其是在進行分配的時候,應該將這些等級和差別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從而達到抑制社會貧富差距的目的,以此來穩定社會秩序。
2.西漢時期董仲舒“調勻均富”說
西漢時期思想家董仲舒的“調勻均富”說,是對孔子均平思想的繼承與超越。漢初的黃老之學和與民休息的政策促使漢朝經濟發展、人口增多,但土地兼并嚴重、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問題亦由此產生。到了漢武帝時期,統治思想由黃老之學轉變為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儒家在成為官方學說之后,貧富差距懸殊就成為維護社會穩定有序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因此董仲舒在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學說的基礎上指出,貧富差距大將不可避免地帶來兩種極端嚴重的后果,從而進一步論述了實行“調勻均富”思想的合理性。另外,董仲舒還強調,解決貧富差距懸殊的關鍵不在于徹底地消滅貧窮,而是要實現普遍的富裕,因為貧與富往往是同時存在的。因此,他認為要解決貧富差距懸殊問題,就要實現貧富之間的平衡,并據此提出了“調勻均富”說。所謂“調勻均富”說,其實質是將貧與富限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也就是對于“大富”來講,要將其限制在“不至于驕”的范圍;對于“大貧”而言,要將其限制在“不至于憂”的范圍。因為“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春秋繁露·度制》)如此,則貧與富就能夠并行不悖,實現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的“調勻均富”說是以嚴格的社會等級劃分為前提的。他雖然強調均貧富,但實質上只是一種相對的平均,并不是平均分配財富,其目的還是維護王權統治與社會安定。但我們仍然要承認,董仲舒的“調勻均富”學說具有積極的歷史意義,其通過調節貧富、改善貧富之間的差距,充分考慮到百姓的基本生活,體現出儒家學說仁政德治的核心內涵。
3.西魏時期蘇綽的“斟酌貧富”說
西魏時期的“均平”概念可以概括為“斟酌貧富”說。相較于先秦和西漢時期,這一時期的“均平”著重體現在賦役制度上的調整。蘇綽“斟酌貧富”說與三國時期曹操的理念較為一致。在平定冀州進而基本統一北方之后,曹操發布了《收田租令》,指出袁紹統治時的失敗正是在于過度放縱地方豪強,由此導致“豪強擅患”“親戚兼并”的問題,而普通百姓則“代出租賦”,使得富者更加富有跋扈,貧者更加貧困凋零,以致民怨沸騰。因此,為了平息民怨、鞏固統治,曹操推行了平貲制度,即通過按戶評估家產來確定具體的納稅稅額,使富者多納稅、貧者少納稅,以此來達到“均平”之效[3]。
西魏時期“斟酌貧富”說最早見諸蘇綽“六條詔書”中的“均賦役”一條。蘇綽首先對孔子的“均無貧”作出解釋——“夫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征貧弱,不縱奸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圣人曰:‘蓋均無貧’”。(《周書》卷23《蘇綽傳》)這實際上也指出了稅收中的一條重要原則,就是在收稅時應當注重“豪強”和“貧弱”之間的關系,要防止富者將稅賦轉移到貧者身上,進而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可見,蘇綽是要以均衡的稅收制度來達到“均平”的效果。基于此,他更為明確地指出了地方官員在稅收中的重要性,作為百姓的“父母官”,對所轄百姓之具體情況是最為清楚的,誰窮誰富亦應當了如指掌。正所謂“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于斟酌貧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長,系于守令。”(《周書》卷23《蘇綽傳》)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地方官員是實現“均賦役”的關鍵,如果能夠按照實際情況進行“斟酌”,就會達到“政和而民悅”的效果;反之,凡是在此過程中做不到公正斟酌的人,都是“王政之罪人”。可見,蘇綽是通過稅賦的角度來論述“均平”的,其主要觀點是依據百姓實際貧富狀況來確定納稅的多少和服役的輕重遠近,通過這種“再次分配”的方式來調整“初次分配”時的不均,以縮小貧富差距、緩和貧富矛盾,進而保持社會穩定。
4.歷代農民起義的“均富”說
在歷次農民起義中,“均平”也是一個極具號召力的口號,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農民的主要訴求,唐末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就第一次提出了“均平”口號。在討伐的“宣言書”中,黃巢歷數唐王朝的諸多弊病,例如“吏貪沓”“賦重”和“賞罰不平”等。農民對于唐王朝之苛捐重稅和諸多“不均”情況積怨甚深;因此,在農民起義中打起“均平”旗幟就能夠一呼而百應,甚至能夠達到傳檄而定、使王朝統治土崩瓦解之效[4]。在提倡重農抑商的中國傳統小農社會中,土地是農民的根本,但地主也同樣看重土地,如果沒有切實嚴厲的限制措施,土地兼并就不可避免。唐末之后,土地所有制發生變化,土地兼并更加嚴重。因此,在黃巢之后的歷次農民起義中,往往把爭取土地和財產平等以及人身平等作為農民起義的主要目標。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就將“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作為口號,以彰顯其起義的正義性,表明自己是實現均平的代言人和推動者;方臘則高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起義大旗;南宋鐘相、楊么起義則明確提出要“等貴賤,均貧富”;明末李自成起義則更加直接地提出“均田免糧”,等等。由此可見,將均平作為農民起義的口號,能夠激起農民的認同感,從而產生強大的號召力與感召力。
在歷次農民起義中,近代太平天國起義將“均平”口號和理念渲染得淋漓盡致并推向巔峰。“均平”理念和追求集中體現在《天朝田畝制度》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社會理想中。對于專制制度下的農民而言,能夠吃飽飯、能夠居有定所、能夠有衣避寒,不再受統治階級的壓榨剝奪就是他們眼中的美好世界;但事實上,由于統治者“不均”的壓榨,使得“農家少閑月”成為一種生活常態,“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成為一種“必然現象”。因此,《天朝田畝制度》的頒布對于農民而言,有著無窮的吸引力[5]。
由此可見,概念既是社會發展的“指示器”,又是社會發展的“助推器”。概念史分析有助于厘清均平概念歷史事件的結構和語境。通過從孔子到與農民起義有關之“均平”概念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發現“均平”思想最初是作為思想家的治國理念受到重視的,之后轉變為歷代政治家治國安邦的策略方法,最后才轉變為廣大農民反抗專制暴政的思想武器。
二、傳統均平思想的共時性凝練
詞語、術語以及一般意義上的語言符號是概念史研究的基石,同一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可能會有不同的具體內涵,但是其中總有交集的存在,這就是所謂概念之“共時性”。之所以突出強調傳統均平思想的共時性,主要是為了將概念變遷與社會變化結合在一起進行考察,重點考察社會轉型和概念變遷之間的關系。傳統均平思想有其內在的規定性,也有其自身廣泛存在的社會共性,通過共時性分析,可以在宏觀上把握傳統均平思想的全貌。
1.政治上的均平思想
傳統均平主張是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是思想家們在發現社會貧富差距懸殊等社會不安定因素的情況下,為了調節社會現狀而提出的一種治國安邦之策。儒家一向推崇“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和“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的“王道正直”。(《尚書·洪范》)也就是說,在儒家學者眼中,統治者只有做到公平公正,避免厚此薄彼,才能真正讓民眾信服,統治才具有可信度和效能。歷代儒家普遍認為“各得其分”是實現“均平”的基礎,董仲舒“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演”的主張就是“各得其分”均平思想的具體反映。這種均平思想所體現的是同一社會階級內的平等,在統治者看來,統治者、貴族和勞動者等的存在是“天道使然”,具有絕對的合理性,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不同階級之間的均平,而在于同一階級的均平。只有各個階級穩定地居于社會中,不相僭越,才是達到政治均平的不二法門。關于這一點,儒家經典《禮記·祭統》中有一段典型的記載,“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后。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就是說,骨頭與人一樣,都有貴賤之分,要做到骨頭與人之間的一一配對,各自去拿與其身份相匹配的骨頭。無論貴賤者,均能拿到骨頭,實現均平。儒家所謂政治上的均平,其本質在于維護社會等級秩序,并通過“貴者不重”和“賤者不虛”的方法來使其各有所得。這樣做的結果不僅能夠實現同一階級中個體的均平,而且能夠縮小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對立差距,實現“惠均”的目的。
但事實上,在王權專制制度下,地主階級剝削農民階級是基本規律,其不會因為道德上的倡導就減輕甚至停止對農民階級的剝削。換個角度,對于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農民而言,單純靠道德教化而使之“樂于”貧苦生活自然是不現實的。
2.經濟上的均平思想
經濟上的“均平”以政治上的“各得其分”為前提,即按照不同的社會等級,各自要獲得與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經濟利益。具體來講,傳統經濟均平思想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均產和均田。這里的均產和均田并不是指人人都能分得相同數量的財產和土地,而是按照“禮”制所規定的身份等級的差異進行分配。均平井田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制民之產”的相關思想。孟子指出,“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也就是說,百姓通過擁有固定的產業來滿足生活所需,百姓富裕了,就不會有作亂的想法,就能更好地進行管理。否則,缺乏一定的經濟支撐,到最后只能成為社會動蕩的不穩定因素。有鑒于此,孟子希望利用均平井田的方式,構建一個民有恒產、安居樂業的均平社會。二是平均財富和平均賦役。繁重的賦役一直是老百姓的生活負擔,加之統治的殘酷,使得民怨沸騰。春秋時期思想家管子提出平均財富的思想,他認為要使百姓“交能易作”,就要使其獲取與之相適應的財富。而只有百姓生活富足,國庫才能充盈。此外,墨子更進一步地將平均分配財富與“明君”掛鉤,使之成為衡量統治者能力的標準,他認為如果君主不能夠做到財富分配均平,就會產生“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以致于“男女無別”的嚴重后果[6]。可見,古代思想家將平均財富作為治國安邦的一種手段,主張在維護統治的基礎上還要兼顧民生。
3.社會上的均平思想
社會上的均平思想是政治、經濟方面均平思想的延伸。傳統社會均平思想可以概括為“公正”二字,是古代思想家所倡導的社會管理的重要方式,主要包括:第一,“無私”之社會均平。對于公正的論述,孔子經常從“無私”展開。例如,《禮記·孔子閑居》中記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也就是說,天是無私的,因為它覆蓋著世間萬物;地是無私的,因為它允許任何生命在其上生長;日月也是無私的,因為它們照耀著世間萬物。由此類比,孔子認為為君者就要像天地、日月一樣無私地照拂自己的百姓,也就是對待自己的臣民要一視同仁。第二,“均遍”之社會均平。對于如何實施“均遍”,在當時社會制度框架下,荀子將君主作為推行“公平”、實施“均遍”的主要推動者,也就是將社會公平之事系之于君主一身,將君主視為公正的“代言人”。所謂“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荀子·君道》)由此看來,荀子將社會公正視為君主的公正。也就是說,社會能否實現公平和“均遍”主要依靠君主的道德操守,看他是否身體力行地推行公正。目的就是要實現“以禮分施,均遍而不偏”。(《荀子·君道》)就是說,在治國方面,君主應當避免厚此薄彼,要公平地給予治下同樣的對待。從現代意義上講,公正是一種價值追求、是治國理政的方式和手段,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基礎和體制機制,單靠一個“明君”或幾個人的努力并不能實現公正。第三,“無偏”之社會均平。傳統均平思想將“無偏”作為社會治理的重要標準,所謂“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嘗試觀于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呂氏春秋·貴公》)也就是說,社會治理之得在于能夠做到公平。相反,社會治理之失則在于偏私和厚此薄彼。在這里需要明確的是,古代思想家們關于“公正”的社會均平思想與我們今天所指的作為核心價值觀的“公正”在內涵上有著天壤之別。相比之下,中國傳統社會均平思想中的公正,沒有也不可能擺脫當時社會制度的局限。可見,傳統社會均平思想只是一種相對的平等。
總之,古代思想家們均看到了由于社會不公所帶來的貧富之間的巨大差別和對立,并對解決之策進行了有益探索,體現了古代思想家們經世濟民的情懷,對此應予以承認和肯定。
三、傳統均平思想的總體再體認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承載著語言和文字的歷史,它保存和沿續了人類多姿多彩的社會生活。概念史的出現使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對于“語言”在理解“現實”重要性方面的認可日益增長。均平思想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不僅是諸子百家的理論建樹,還是歷代統治者治國施政的理念和方法,也是農民領袖揭竿而起的“戰斗檄文”,更是受盡壓迫的農民對于生活的美好期盼,從中反映了傳統均平思想的豐富內涵和價值訴求。
1.理想追求的共同性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經世致用之價值追求。縱觀傳統均平思想主張,無不指向現實社會,無不來自于對歷史興衰規律的考察、來自于對現實社會狀況的分析。歷史上眾多思想流派及其思想家對于均平之具體見解和論述或許存在不同之處,但最終理想目標則是同一的。道家在“均平”這一問題上主張無為而治、順應天道,反對人為的干預。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不為取天下。”(《老子·六十一章》)這里強調了天道的作用,指出應順應天道,不要加以干涉,社會自己就會達到均平的狀態。“天道”在均平的過程中發揮的就是這樣的作用,老子將其概括為“損有余而益不足”。他認為,通過“天道”自發的調節作用,人類社會能夠實現均平[7]。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雖然也強調均平,但這種均平是一種相對的均平。儒家強調的“修齊治平”,其中的“平天下”大多數人將其理解為“平定天下”,其實不然,應當是“均平天下”之意。周朝末期,禮崩樂壞,社會動蕩,生活在此動蕩年代中的孔子,親身經歷了禮崩樂壞所帶來的社會動蕩。為了恢復周禮時期的盛況,孔子基于對現實中社會等級秩序混亂、社會動蕩等問題的審視,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均無貧”的思想。孔子用“仁、義、禮”的思想來指導政治活動,他認為要施行仁政,用禮儀來規范人的行為,從而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隨著歷史的發展、朝代的更迭,孔子的均平思想也通過董仲舒等大儒的改造與延伸實現了內涵上的擴展,在最初的“經濟公平”的基礎上,擴充為“政治公平”,正如漢代孔安國所說“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憂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這不僅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更體現了中國的思想家們在對時代和社會的觀察與考量中的敏銳性與獨到之處。
縱觀中國傳統均平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將其放置于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考量,可以看出,對于均平的認識不同階級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這絲毫不影響均平思想成為其共同的理想追求。
2.治國安邦的策略性
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迭大多是通過推翻前朝的統治來實現的。建立政權以后,統治者思考的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維護和鞏固自己的政權而避免重蹈前朝的覆轍。所以,為了避免重蹈前朝之覆轍,也為了彰顯新政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必須鞏固統治,將“均平”作為治國安邦的主要策略和手段。
一是賦役制度中的均平思想。對于實現賦役制度的均平,歷代統治者的看法和做法相對一致,都是充分考慮到富者和貧者之間的平衡。通過按戶評估財產的方法來確定納稅的具體數額,并按照實際狀況來確定徭役的輕重。總之,就是基于現實條件的考量,對優勢地位者稍“殘酷”一點,對弱勢地位者則稍“網開一面”一點,不至于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情況[8]。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貧富之間的嚴重對立,保證無論是貧者還是富者都能夠“各得其分”,能夠融入到自己的政權體系。二是田制沿革中的均平思想。縱觀歷史發展,田制主要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1)戰國時期的“按產量納稅”。在納稅方面國家并未規定一個明確的數額,只是實事求是地根據畝產量來決定納稅的數額。(2)北魏時期的“均田令”。這是給農民平均分配土地并記錄在案,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防止土地兼并。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也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3)唐朝時期的“均田令”和“租庸調令”。在唐朝時期,均田擴展到從農民到官吏再到王公貴族等社會不同群體之中。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均田并非按照人數平均分配土地,而是按照農民、官吏的不同階級進行劃分,再按照相應的標準進行土地分配。在“均田令”之外,唐朝還創造了租庸調制這種絕對均平的方式,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并最終實現“均一”的效果。(4)至唐朝所普遍使用的“兩稅法”。“兩稅”指的是地稅和戶稅。具體的征收是基于“人無中丁,以貧富為差”的原則,即以實際耕種的土地數量為依據進行納稅。如此,就可以實現“損有余而補不足”,即擁有耕田多的人就要多納稅,耕田少的人就少納稅,使納稅稅額與實際條件相掛鉤,進而實現均平[9]。三是選官任職中的均平思想。選官任職的均平思想實質上是向普通民眾開放政權,給予其轉變社會階級的機會。通過設置各級各類的管理機構,實現“民轉官”,使一些賢能之士開始逐步參與政治生活,進入統治階級。這是個緩慢的發展過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節點有漢朝的察舉征辟制、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和隋唐的科舉制度等。這其中,由隋朝開創并由唐朝完善的科舉制度最具歷史意義,科舉制度的實施讓國家選官的數量和范圍大大增加,在各個層級的科舉考試中能夠最終位列皇榜的人少之又少,均可謂是人中精英[10]。不少寒門之子、布衣之士及具有真才實學的棟梁之材均可以通過科舉而做官任職,徹底地改變個人命運和家族命運。因此,選官任職上的均平思想不僅能夠提高國家行政管理水平,還能夠維護和鞏固統治。
所以說,均平思想為歷朝歷代的社會經濟變革提供了理論指導和依據,并在具體的政策實踐中得以再現與呈現。此外,均平思想還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打開了賢能之士參與治國安邦的大門,同時也維護了社會穩定、推動了文化繁榮。
4.農民起義的鼓動性
當均平這一思想被當作農民起義的口號和指導思想提出時,便具有十分強大的鼓動性。因為廣大農民一直是專制統治的基礎,歷代統治者雖然宣稱“養民”“重民”“愛民”,但實際上對農民卻是無情的壓榨和盤剝,農民時常會面臨重稅重役、甚至喪失土地的危機,因而十分渴望能夠生活在一個均平的社會。于是,起義在打出均平的口號時往往能獲得農民的積極支持[11]。而均平思想就是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農民起義中不斷豐富和發展起來的。歷史上影響巨大的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就對統治者提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強烈質疑,體現出了農民渴望身份平等的政治訴求。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不難想象陳勝在說出這句話后會掀起多大的波瀾,農民心中長期壓抑的那份對于政治不均的積怨亦由此得以宣泄。
相較于陳勝、吳廣起義只是在話語之間流露出對不均的積怨和對均平的追求,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更是直接而明確地將“均平”作為口號加以提出。此后,從北宋王小波、李順起義到李自成起義,最后再到將農民起義推向巔峰的太平天國運動,均平的思想越來越深刻,其實踐藍圖也越來越清晰[12]。盡管這些農民起義最后都因為各種原因而走向失敗,但不難看出均平思想在發動農民起義中的強大號召力,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均平思想已經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13]。
總之,在中國古代社會歷史進程中,不論是思想家還是政治家,都基于自身階級和立場,出于不同的目的,對均平思想進行了“應然”性的理論探索和“實然”的操作實施,不僅使均平思想成為一種治國理念,更成為一種治國方式,使“均平”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之一。但受制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均平思想在理論建構上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實質仍是維護統治的一種工具,旨在縮小貧富者之間的差距并保持社會穩定。所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統治者、思想家或者農民領袖如何高喊和標榜“均平”,都不可能真正實現。因此,“均平”也就成為國人心中永遠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