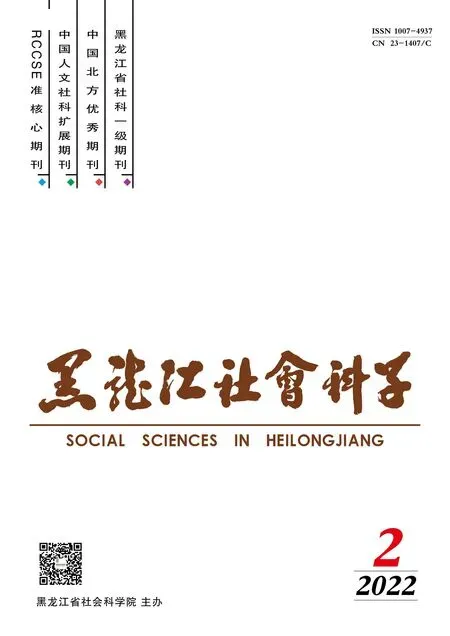清末巴爾魯克山的租借與收回
張 帥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邊疆研究所,北京 100101)
光緒十九年(1893),清朝從俄國手中收回了被租借十年的塔爾巴哈臺的巴爾魯克山,這是晚清在外交領域取得的一項不小的成就,此舉極大地鞏固了西北邊防,也緩和了當地哈薩克與蒙古兩民族之間因爭奪牧場而導致的緊張關系。目前對于該事件的研究,以過程敘述型為主,討論了中俄雙方的談判和交涉過程、條約文本的簽訂、所屬哈薩克部眾的安置等問題[1],但對于事件中的關鍵人物——伊犁將軍長庚所發揮的作用和清朝能夠成功收回巴爾魯克山的原因則分析不足。故撰此文,以就教于學界。
一、俄國租借巴爾魯克山的緣起
18世紀中期統一天山南北之后,清朝在當地設置了大量卡倫(滿語karun,意為哨所),承擔沿邊地區的稽查、瞭望和守衛等功能,卡倫也成為維護西北邊疆穩定和安全的一道重要屏障。這些卡倫大致可以分為三類:常年設置的固定卡倫、季節性移動的非固定卡倫和時而安設時而裁撤的添設卡倫。從乾隆時期開始,生活于邊境附近的哈薩克民眾由于當地缺乏冬牧場,故需要經常進入到清朝界內越冬,第二年春季后再返回原址,清朝則按實際入卡放牧牲畜的數量,依照固定的比例收取一定數量的牲畜,謂之“租馬”,這種政策維持了清朝與哈薩克汗國之間百余年的和平局面。然而,19世紀中期俄國兼并哈薩克汗國后,與清朝之間劃定了比較嚴格的邊界線,規定雙方人員都不能私自越界,原先哈薩克民眾這種較為隨意的“跨界游牧”方式于是受到了影響。
同治三年(1864),中俄簽訂《勘分西北界約記》,俄國強迫中國承認以中方的常駐卡倫為雙方的國境線,據此強占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44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該條約第五條規定:
以免日后兩國為現定邊界附近地方住牧人丁相爭之處,即以此次換約文到日為準,該人丁向在何處游牧者,仍應留于何處住牧。俾伊等安居故土,各守舊業。所以地畝分在何國,其人丁即隨地歸為何國管轄。嗣后倘有由原住地方越往他處者,即行撥回,免致混亂[2]44。
此即“人隨地歸”原則,由此中國在失去西北大片領土的同時,也失去了對居住于這些領土上的哈薩克、布魯特和烏梁海等部的實際管轄權。此時,由于中俄之間劃定了嚴格的邊界線,俄國治下的部分哈薩克民眾不能再隨意越界游牧了。而且,已經吞并了哈薩克汗國的俄國希望趁清朝內憂外患之際,憑借武力脅迫和外交施壓,將原來的季節性租借地變為常年租借地,如果可能則直接據為己有,水草豐美的巴爾魯克山就成為目標之一。
巴爾魯克山位于塔爾巴哈臺西南部,在中俄劃界之后其西面直接與俄國領土接壤。該地“踞伊犁、塔爾巴哈臺、庫爾喀拉烏蘇、精河四界之間,形勢險要”[3],且“地勢平衍,河流錯出,草色蔥蘢,彌望無垠,常為蒙、哈散帳之所”[4]1132。按照中俄簽訂的界約,該地歸屬于中國,但俄國公使斐里德卻宣稱,雙方劃界后清朝并未在此地設立牌博(界標),且當地的哈薩克民眾在劃界之前就已經歸附俄國。這種說法顯然是蓄意不遵守“人隨地歸”原則,“意欲將此山劃分,以資安插俄屬哈民”[5]180。這種無理要求在被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升泰依理駁斥后,斐里德轉而又提出了租借之說:
塔城變亂后,久為投俄屬之哈薩克住牧,一經定界,遽難遷移,所以欲將此山劃分歸俄者,實欲藉以安插此輩起見。如肯將此山借讓給俄,則此哈民冬夏游牧俱有定所,不致亂越生事,亦屬中外兩益,其余悉允照舊約分辦[6]677。
升泰與塔爾巴哈臺辦事大臣錫綸商議后一致認為:俄屬哈薩克民眾既然一時難以外遷,如果我方強行驅逐,反而會成為邊境安全的一個隱患;俄國既然已經承認了中國對巴爾魯克山的所有權,不妨允許暫借放牧。后在與伊犁將軍金順商議之后,三人就此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遂擬定:準照舊約第十條,塔城原住小水地方居民之例,自定界之日起,以十年為限,租借期內應陸續遷移至俄境,期滿后一概遷出;山中所有樹木均歸中國。俄國表示同意。于是,雙方于光緒九年九月簽訂《塔爾巴哈臺西南界約》,關于租借巴爾魯克山的內容如下[6]679、681:
(漢文本)查從前巴爾魯克山內及它屬各處駐牧俄屬哈薩克等因為利己,未令中國官員管轄,亦未交稅。今議定此約后,其巴爾魯克山及塔爾巴哈臺所屬地方仍屬大清國地方,即令該哈薩克等遷移俄國之地,亦屬礙難。今換此約日起,其巴爾魯克山之哈薩克予限十年,仍舊巴爾魯克山內游牧,俟限滿后兩國官員如不另行商辦,則將該哈薩克遷住俄國地方。十年限內,中國官員將中國人民毋庸遷住巴爾魯克山內,亦無須設卡,除巴爾魯克哈薩克外,其余塔爾巴哈臺所屬各處駐牧哈薩克等,即欲遷住俄屬地方,亦屬礙難。
(俄文譯本)俄屬哈薩克民冬夏在巴爾魯克山及塔爾巴哈臺屬之別處游牧,逐水草之利者,中國地方大吏向來不預其事。現在接照所定之界,所有之地,雖已退歸中國管轄,而哈薩克民等一時遽難移入俄界,擬將巴爾魯克山之哈薩克民自換約之日起,限十年內妥為安插,所有俄國哈薩克民于此定限期內準其在塔爾巴哈臺屬現在游牧處所照舊游牧。所有巴爾魯克山游牧之俄國哈薩克民,如滿十年之限,未經續準,即應安插俄國界內。
分析上述條約文本,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無論是漢文本還是俄文本,都沒有寫明十年到期后俄國必須無條件歸還,只載明“如不另行商辦”或“未經續準”,則將俄屬哈薩克民眾遷出,這為日后俄國提出繼續租借提供了依據,“是借地之始已伏另商之根”[6]1616。其二,在租借前后,清朝都未在此處設立卡倫,使得中國失去了對出入當地人員的稽查和控制權,從而構成安全隱患。
二、長庚對形勢的分析與力主收回
光緒十七年四月,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額爾慶額提出,現在十年租期將滿,請總理衙門預先照會俄國,敦促其準備遷移事宜,以免臨期推諉,滋生事端:
自借地后,地方愈形狹隘,本屬哈薩克不敷住牧,四出潛逃,往往因爭占草場互相構釁。每當冬令雪深,有搬至科布多境內者,有移至庫爾喀拉烏蘇及奇臺古城一帶者,雖經陸續收回,究未能全歸舊處。奴才訊問逃戶,僉稱人口牲畜糊口無資,出于萬不得已,情詞確實,亦未忍概事刑誅。奴才到任后,督飭沿邊卡倫兵弁等,嚴加防范,寬以撫循。數年以來,幸無事故。伏思國家土地,尺寸不可以假人,況巴爾魯克地段綿長,水草暢茂,形勢扼塞,最為緊要。若令久假不歸,不特邊疆失此要隘,誠恐本屬哈薩克無所依棲,轉非綏靖藩部之道[6]1554。
意即若能收回巴爾魯克山,則不但邊疆防守有所依靠,哈薩克民眾亦可移入,不致再有逃亡。
此時的出使俄國大臣許景澄,本計劃與俄國公使吉爾斯直接面議,但由于時值夏令,吉爾斯在鄉下避暑,遂先向俄外交部發出照會:
現在期限漸近,自應預為籌畫,以臻妥協。是以本大臣奉到國家之論,先期知照貴大臣,請飭貴國邊界官,盡此有余之時,早為設法,將貴屬哈薩克陸續遷徙俄境,以便屆時騰空該地,安置華民[5]86。
然而,由于俄國蓄意拖延,八個月未給予回復。許景澄知“延宕支吾是西國慣伎”[5]180,遂再次照會俄方,重申清朝將如期收回。俄使喀希尼知租借問題無法回避,遂表示:《塔爾巴哈臺西南界約》中有“到期之后,另行商辦”的條款,俄方續租該地十年,并以“取鹽”和“讓路”兩項條件作為交換,即允許中國人在俄國所屬的七河、斜米兩省湖內取鹽和從察罕鄂博山口自由出入。
此時,主管新疆軍政事務的地方官是伊犁將軍伊爾根覺羅·長庚。長庚長期任職于新疆,對當地的山川地理和軍事防務十分熟悉。擔任伊犁的巴彥岱領隊大臣期間,他在向朝廷所上奏報中“所稱阿勒泰山宜早防守,伊犁邊防宜籌布置,躔金等處宜開屯田,漠北草地宜善撫綏,及哈薩克應仿例編為佐領等語”,得到如下批復:“該大臣于西北邊隘地勢,尚稱熟悉,所陳各節,不無可采,邊防關系極重,自應預為籌畫,以固疆圉而杜覬覦。”[7]光緒時期,英國和俄國都在覬覦新疆,先后派兵進入帕米爾地區,企圖挑起戰爭,借機牟取利益。長庚鑒于新疆剛剛經歷同治回變之亂,清軍在當地的防務力量還十分薄弱,根本無力應對英、俄之挑釁,遂致書甘肅新疆巡撫陶模,告知其務必要克制忍耐,暫時退讓以積攢力量:“屬地當爭,邊地當守,兵釁萬不可開……當此民窮財匱之時,尤不可輕戰。只能備豫不虞,徐圖轉圜。毋以小忿遂起大釁,增兵徒增民困。”[8]對于巴爾魯克山的戰略地位,長庚分析道:
查伊、塔兩城毗連俄界,為新省門戶。由伊犁到省,精河及庫爾喀拉烏蘇是其要沖;由塔城到省,老風口、瑪雅圖及庫城各處,亦其要沖。而巴爾魯克山則介居伊、塔、庫、精之間……四通六辟,防不勝防,此形勝之在所必爭者也。俄人藉讓路、取鹽兩端,為展限十年之請,是以畫餅虛名,而欲我受棄地之實害也[5]258-260。
對于俄方提出的兩項交換條件,他也向清廷詳細分析了其中的利弊:首先,新疆地方多有產鹽之地,根本無須仰賴從俄國進口食鹽;伊犁百姓素來食用的是精河城北喀拉塔拉、額西柯淖爾所產之鹽,取攜十分便利;至于伊犁迤額魯特境內達布遜淖爾,現已分屬俄界邊境,蒙古民眾就近以皮張換取該處出產食鹽者,間或有之,俄方若橫加阻撓,則尚有精河之鹽可食;塔城食鹽,東半取于哈喇達布遜淖爾及愛里克淖爾,西半取于烏蘭達布遜淖爾。其次,察罕鄂博寬約三四十里,昔為布倫托海赴塔城的臺路所經,南山屬中國,北山屬俄國。當年分界,應于山下平原居中之地建立牌博;俄國此時強行將牌博建于南面山麓,以致臺路十分狹窄,通行難度較大。后參贊大臣使臺路改走哈屯山以南地方,取道木呼爾岱;該路雖然不如經由察罕鄂博近便,但只多行兩站而已,仍屬可走之路。“是其地容走不容走,于我無所損益。若因此而致巴爾魯克山不能收還,則太覺不值。”總之,“來示所慮各節,因已燭照靡遺,而此山實關伊、塔、新疆全局要害,久為俄哈盤踞,其害不可勝言。若稍涉游移,終必無索還之日。”[5]258-260
長庚還指出,如果到期后不能及時收回,那么巴爾魯克山就可能永遠落入俄國之手,“失地利、危疆域,為害甚大”[6]1597。具體來說:第一,從軍事上來說,巴爾魯克山為形勝之地、四通八達,東連烏魯木齊,西達伊犁,東北達塔爾巴哈臺,一旦邊境有事,則該處哈薩克民眾可能會成為俄國的向導。俄國若長期占據該地,可以分扼精河、老風口,或橫截庫城,伊、塔皆有斷絕糧餉之虞,新疆右翼就失去了安全。第二,從生計上來說,該處本為塔城額魯特牧地,嗣因俄屬哈薩克民眾借住,導致塔城當地的蒙古和哈薩克牧民無地游牧,不得不借科布多所屬烏梁海之阿爾泰山暫居。近年以來,烏梁海蒙古屢次向塔城索換,科、塔之間議定,自光緒十八年起,立限三年,無論巴爾魯克山能否收回,屆期即行交還所借之地。因此收回巴爾魯克山刻不容緩,否則塔屬蒙、哈民眾即無地放牧。第三,從治安上來說,租借之后,清方本應在當地設置卡倫,但由于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卡倫至今未設,哈薩克民眾可以任意出入,清朝毫無稽查之權力。俄屬哈薩克民眾頻繁行搶奪之事,清方屢次派兵追捕,但限于系租借之地無法進入;即使行文俄國,對方卻不嚴辦,旋即放哈薩克民眾復來,仍行搶奪,滋擾邊境。
長庚所言,極大地堅定了清廷如期收回的決心,但由于租借之時,“界上卡倫亦未安設,是名為借住,已與彼境連成一片,借之時遷就過多,現在辦理更為棘手”[5]255。光緒十九年四月,長庚再奏:現屆期滿,宜速派員會同俄方商辦收還事宜。新任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富勒銘額抵任后,立即著手準備,他派伊塔道英林與額魯特游牧領隊大臣圖瓦強阿代表中方前往商談收還事宜,俄方代表則是駐塔爾巴哈臺領事寶德林。
三、堅持“人隨地歸”的談判原則
談判開始,俄國領事寶德林“初猶狡執,既而再三爭辯,始允照約遷讓”[6]1615。但隨后他又提出附加條件,說俄屬哈薩克民眾還有1000余戶無地安插,可先交還一半土地,其余土地待尋好安置地點后再交還。長庚則指示英林:“中國重在收地,不重在得人,必于約內載明,限滿后俄哈不能遷移,即照同治三年人隨地歸之約統歸中國管轄”,“如不能載明此語,無論二年三年斷不可答應借地”[6]1641。告知英林必須堅持“人隨地歸”之原則,對于后續談判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收還日期將近,在向俄領事多次確認后,英林始允其在交還后,在山內暫借一地讓俄屬哈薩克民眾過冬,但要求至明年春天必須全部搬出,借居之地必須按時交還;而此前放回的俄屬哈薩克民眾600余戶,依照“人隨地歸”原則,劃歸中國管轄。俄方擬新借之地,約占巴爾魯克山總面積的3/10,北起瑪尼圖卡,南至察罕托海卡,東界喀喇布拉克河源,皆系山外無關緊要之處。不過,俄領事又提出將原定以明年春天為期限展至三年之后,即最遲于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將新借之地歸還。英林為避免談判決裂,只好再次允準俄方要求,但始終堅持“人隨地歸”原則,若在期滿前未能遷移,則俄屬哈薩克民眾即劃歸中國管轄。實際上,俄方的做法只是策略性的試探,見中方堅持“人隨地歸”原則,先是因續租十年的想法未能如愿,又擔心所屬哈薩克民眾被劃入中國,遂將再租三年之議作罷。
不過俄領事又稱,原議遷回俄境的哈薩克民眾內尚有數百戶居住于邊界附近,入冬之后氣候寒冷恐不能抵御,請求讓其暫于山內過冬,指給若干地方居住,明春則按時遷移。英林查驗后得知,此時確有哈薩克民眾數千人懇求借地過冬,“若盡拂其請,恐其不肯安心交山,轉致事機中變”[6]1640,因小失大,遂允準其請。而俄方也終于同意按期交還所有地方,收還行動的最后一個障礙也被掃除了。此后,中俄雙方簽訂了《中俄收回巴爾魯克山文約》,內容如下:
將巴爾魯克山、額敉勒河南岸各該處地方,于九月初三日,由俄國官員手內全行接收矣。至該處中俄兩國交界牌博,前經彼此派員會同前往查明,各該界牌鄂博均在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所分交界原立地方,中國界牌內有三處損壞,均于原立地方補修,已由該員等互換約結在案。自交收該地之日,中俄兩國各照光緒九年原定交界經管[6]1617。
光緒十九年八月,俄國開始依照約定陸續遷移哈薩克民眾。長庚敏銳地意識到,俄屬哈薩克民眾久苦俄國的苛政,此時難保無逃竄之虞,遂派兵駐扎在附近的梅利山一帶,以杜絕兩國哈薩克民眾私相往來,又嚴密巡查各處邊界,嚴禁俄屬哈薩克民眾私自竄入中國境內。并要求如有俄屬哈薩克民眾入境,拿獲后即刻解往塔城遣回俄國,避免給俄國以收留逃人之口實。通過這樣的嚴密部署,保證了收還行動的順利進行。九月初一,俄國將設在當地的哨所全部撤回,清方隨即派兵進駐。不愿遷移至俄境的哈薩克民眾有799戶,經俄領事柏勒滿造冊移送和清方查點之后,全部歸入中國管轄,仍舊安插在原地游牧。清朝嚴飭所有新歸附的哈薩克民眾:必須安分游牧,不得滋生事端。九月初三,將原先借牧于科布多的部分蒙古民眾移進山內,與哈薩克民眾一起安插。
租期之內,清朝未在巴爾魯克山設立卡倫,此時“業已收回,迤邐邊界,擇其要隘,亟宜安設卡倫,固我藩籬”[6]1642。長庚在派員勘察后,擇其險要之地設立了若干卡倫:塔城西南60里至瑪尼圖設卡,70里至薩爾布拉克設卡,50里至察罕托海設卡,70里至額爾克圖設卡,50里至尼楚渾巴爾魯克設卡;共計設立5卡,均與俄國哨卡位置相對。卡倫士兵均從當地額魯特、索倫營中抽調,每卡設官1員、兵20名,每三個月更換一次。長庚還向朝廷提出,巴爾魯克山西面綿亙七八百里,處處與俄境毗連,目前駐防士兵太少,恐怕難以發揮有效的防御作用;并請求命塔城額魯特領隊大臣移駐該山附近的布倫布拉克、伊犁察哈爾領隊大臣移駐博羅塔拉,如此則“彼此連為一氣,平時足資控馭,有警互為聲援,是新疆西北隱隱增一重鎮,而伊犁、塔爾巴哈臺后路皆可恃以無虞”[3]。
結 語
在同治年間中俄西北劃界之后,由于失去了大片領土,導致塔爾巴哈臺地方“蹙地千里,內附哈民不敷棲住,而俄人又有租借巴爾魯克山之約,牧地之分裂搶攘者,十有余年。加以俄哈闌入,蔓延遍天山南北,而牧界益淆”[4]1133。在十年租借期滿之后,清朝在外交談判中合理地利用了“人隨地歸”的原則,成功從俄國手中收回巴爾魯克山,重新控制了伊犁與塔爾巴哈臺之間的一處戰略要地,獲得了一塊水草豐美的牧場,從而得以安置暫時寄牧于科布多的蒙古和哈薩克牧民。對于在該事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伊犁將軍長庚,《清史稿·長庚傳》評價曰:
長庚詳陳利弊,謂此山關系重大,急應收回。隨遣員赴塔城與俄領事會商,堅持人隨地歸之約,卒收回[8]。
這是繼曾紀澤從俄國手中收回伊犁之后,晚清在外交上取得的又一項不小的成就。
俄國在交還巴爾魯克山之后,援引光緒十年簽訂的中俄《塔城哈薩克歸附條約》中第十條所載明的“若遇雪厚草枯不生之年,俄國所屬之哈薩克等,欲往中國所屬之地暫牲畜者,應稟由俄國領事官商請中國官員借給地址,應給地租,照中國人一律取給”[2]86一條,在光緒二十八年提出租借伊犁額魯特營的胡爾莫敦地方,并要求清朝“定界放牧,不取租,立約保護”[9]。次年,駐伊犁的俄領事發出照會,請照成案繼續借給冬牧場。時任伊犁將軍馬亮先是予以拒絕,“旋因該哈薩克馬群業已趕到過境,現在中俄邦交甚篤,勢難禁止,申請準其借牧前來”。他一面將情況上報外務部,一面通知伊塔道與厄魯特領隊大臣:“按照(光緒)二十八年借廠辦法,與該哈薩克等照舊書立合約十有一款,蓋戳簽名,驗明俄官執照所載人畜數目,制定借地界址,妥為保護。”[10]當年十一月,俄國牧民100人、馬1.5萬匹由那林郭勒卡倫入境,在胡爾莫敦放牧,至次年正月二十八日出境。放牧期間可謂相安無事,以后皆照此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