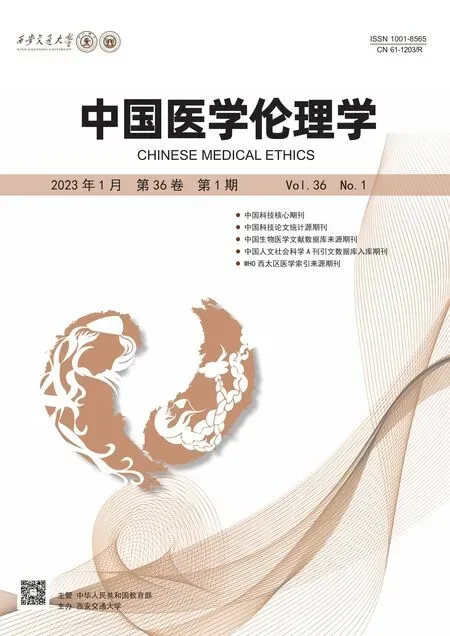“慈本論”基礎上的“良心認識論”
——兼論“立心”對道德教育的基礎作用
蔡 昱
(云南財經大學金融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21)
現代性帶給人類兩個根本的倫理困境是道德危機和外在導向的道德所致的人的工具化。具體而言,這種道德危機并不是多一些道德或少一些道德的問題,而是要不要道德的問題。根本上,這場道德危機就扎根于培根和霍布斯等現代性的早期籌劃者為人們指定的“自我保存”這一人之本性和根本的行為動機中。然而,他們卻沒有發現“自我保存”的本質是在“對生存安全感意義上的匱乏的恐懼”(即“生存性恐懼”或“畏死的恐懼”)逼迫下的盲目追逐或盲目屈從[1-4],它既使人失去了可以形成主體間性道德關系的道德的可能性[5-6],也失去了“選擇自己的自我”的自由的可能性。現實中,現代人仿佛全然接受了“經濟人”假設,即認為不擇手段地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是人性自然,這種被認為是人之本性的貪婪,當然也被認為是無法通過自律的道德得到拯救的。這在醫療領域體現為醫德的滑坡和醫德失范事件的發生。顯然,一旦人類被生存性恐懼下狹隘的功利蒙蔽了雙眼,忘記了良心和互為目的的真正的愛,喪失了發自內心的情感,就可能失去人性,而這如果發生在傳統上被認為是精神高貴并負有凈化和影響社會的責任的醫生身上,會令人更加難以接受。然而吊詭的是,當這類醫德失范的惡性事件被發現時,人們常想到的僅是法律的不完善,醫療管理和監督機制的不健全,卻很少考慮醫生的良心問題。也就是說,作為僅僅自我保存的經濟人,包括醫生在內的現代人的良心被認為已事先被喂下了“安眠藥”,他們的行為被認為只有通過外在于人的輿論、制度、規則和法律,甚至需要嚴刑峻法才能限制在安全限閾之內[7]。由此,服從外在于人的道德尺度也便成了現代人的所謂的“道德”。然而,現代性的籌劃中,這些外在導向的道德尺度的服務對象為外在于人的社會政治(如霍布斯的政治籌劃)、經濟(如資本主義的經濟籌劃)和科技(如培根的科技籌劃)的需要,這不可避免地將人工具化;于醫療中,醫生的工具化則體現為淪為資本的掙錢機器,進而,醫院對“好醫生”的評價標準也從治病救人扭曲為“給醫院帶來更多的效益”。由此可見,無論醫德的提升,還是醫生的自我實現意義上的自由,都要求內在導向的(即具有本然性的應然性的內在尺度的)自律的,并可以在感性世界中現實化的道德,即需要建立在(具有內在導向的道德尺度并具有道德力量的)作為道德基礎的良心之上的道德判斷和道德實踐,也即良知判斷和良知實踐。
近代以來的主體性哲學缺乏關于人在感性世界中本真存在的實體論的基礎(即“自我真理”,顯然,這里的“真理”意指普遍性,即非流變性和非相對性),由此,這種具有內在的普遍的道德尺度,并具有道德力量的“良心”及對它的認識的知識(即“良心認識論”)都是缺失的(下文將有詳細論述)。同時,人類歷史上曾有過一些關于此種“良心”及對其認識的隱性知識,是人類的思想寶庫,但因不究竟而不系統,也不能被大多數人所理解。因此,以普遍性的知識確立系統的“良心認識論”是急需開拓的道德哲學和道德教育的基礎領域。本文將在嶄新的存在論基礎上確認作為道德的價值基礎和力量來源,并內蘊了道德判斷和道德實踐的內在尺度的“良心”,進而,以普遍性的知識確立“良心認識論”,它是作為道德教育的基礎和關鍵環節的“立心”(即認識、激活、增強和擴充“良心”及其功能與表達)的前提和基礎。顯然,只有以普遍性的知識確立了“良心認識論”,并以之為指導幫助人們激活、強化與擴充良心,才能樹立具有獨立人格的道德主體,完成西方啟蒙未能完成的任務,即要使每個人都成為道德自覺的“主體”。同時,“立心”與外在制度的變革(即外在制度不再制造生存安全感意義上的對匱乏的恐懼)相輔相成,將可以實現對西方現代性的超越,實現真正屬人的世界,屬人的醫療。
1 阿倫特的疑惑——良知判斷的基礎和尺度是什么?
阿倫特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她曾震驚于二戰期間歐洲不同國家和不同的人對納粹驅逐猶太人的命令的不同反應,即只有少數國家和少數人沒有出現反猶主義,甚至主動拯救猶太人,與之相反,大部分國家和大部分人沒有提出對反猶主義的抗議,甚至積極配合。進而,正是這些少數的拯救者使她發現即便在文明的黑暗時期,即當時的輿論、制度、規則,甚至法律等道德判斷的外在尺度都變得黑白顛倒,仍有少數人保持著分辨善惡的道德判斷能力。進而,她認為這些少數人只是根據自己的判斷行事的人[8],并由此看到了希望——即便在最黑暗的時期,人類的自由仍是可能的[8]。顯然,阿倫特提到的“人們自己的分辨對錯的能力”是指人的內在導向的(即具有內在的本然性的應然性的尺度的)道德判斷能力,而無關那種盲從于習俗、輿論、舊有的規范和價值觀念等的外在尺度的外在導向的道德判斷(有趣的是,阿倫特曾以不斷變換的“餐桌禮儀”來比喻外在的道德尺度和外在導向的道德判斷的流變性和相對性),也就是說,阿倫特提到的道德判斷本質上便是“良知判斷”,它與人的“選擇自己的自我”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意義上的自由相關聯。進而,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的“后記”中,阿倫特提出了道德哲學和道德教育中的一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問題,即人類當以何辨別是非[8]?也就是說,那種在人類文明的黑暗時期仍能抵抗邪惡的力量的(也即使人獨立于惡的外在尺度的)道德判斷(即良知判斷)的基礎和其內在的具有普遍性的尺度是什么?
然而遺憾的是,阿倫特沒能就上述問題給出清晰的答案。究其原因,這是她受限于現代性的人性學說的體現,即現代性的人性學說并沒有支持她的理論資源。詳言之,“良知判斷”是人的具有本然性的應然性的內在尺度(顯然,內在導向的道德尺度是“作為自由的道德”的基礎。缺乏內在導向的道德尺度而造成的人的工具化是當代功利主義倫理學的顯著缺陷)和德性力量(顯然,這種德性力量是人類歷史上的那些道德典范們留給我們的顯著印象。缺乏道德力量而造成的“道德無力癥”是當代義務論倫理學和美德倫理學的顯著缺陷)的道德判斷,這意味著具有此種良知判斷能力的人是有力量和能力遵循內在于己的本然性的應然性的道德尺度的,也即是具有“選擇自己的自我”的力量和能力的在感性世界中本真存在的“存在者”,而非“虛無者”。然而,如前所述,現代性的早期籌劃者為人類指定的人性學說是將“自我保存”當作人的本性和行為的根本動機(我們可以將此種自我稱為“感性小我”),卻沒發現“自我保存”本質上是在“生存性恐懼”逼迫下的盲目追逐或盲目屈從[1-4],也就是說,專注于“自我保存”的現代人是已經喪失了“選擇自己的自我”的可能性的“虛無者”,他/她使內在導向的道德判斷(即良知判斷)和道德實踐(即良知實踐)成了無根之木和無源之水。與此同時,康德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的主體(我們可以稱之為“理性大我”)孤獨、空虛、無力,由于無法對抗感性的“生存性恐懼”而無法在感性世界中現實化,其實踐理性更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非但無法實現康德設想地對感性小我的支配和限制,還成為服務于感性小我的工具,也就是說,純粹實踐理性的主體在感性世界中是虛幻的。阿倫特以感性世界中的“虛無者”或“虛幻者”為理論前提,當然是無法完成對具有獨立人格的道德主體(他必須是感性世界中的存在者)才具有的“良知判斷”及其尺度的思考。同時可見,只有確立了人在感性世界中的本真存在的實體論的知識(即“自我真理”)后,才能對阿倫特所遺留的問題,即良知判斷的基礎和尺度進行討論。
2 “慈本論”的“自我真理”基礎上的良心及良知判斷的尺度
存在論在哲學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揭示“人如何存在”以及“人何以存在”(也即揭示人的“自我真理”)無論對道德哲學的建構,還是對道德教育都具有重要的基礎意義。筆者在《從生命需要看人之存在之謎——我們如何存在與何以存在》[9]一文中嘗試解答“人之存在之謎”。具體而言,一方面,上文嘗試解答“人如何存在”的問題,得到如下結論:在因果一體的作為人之存在基礎的“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即“慈”)-自由自覺的本真的生命實踐(即“互慈和創”)中,人之存在、道德與自由得以一體實現,人獲得了個體性與整全性的統一和有死性與永恒性的統一。同時,永恒處于當下,表達為與永恒相關的生命意義及其所帶來的勇氣和力量感所形塑的整全性的人格基礎上的精神維度指導下的生命態度、行為和情感方式與生命實踐,其根源是內在于生命需要的“生-生”(即一體兩面的“自我創生”和“相互/協同創生”)式的生命本真的存在方式這種超越性的結構。由此,揭示了“人如何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上文還通過“以超越畏死的恐懼為樞紐的生命面向的翻轉”揭示了“人何以存在”的問題。詳言之,“生存性恐懼”是人之存在、道德與自由在感性世界中現實化的障礙,也就是說,只有超越或遮擋了“生存性恐懼”(顯然,這里的“遮擋”意為使生存性恐懼不升起),人之存在、自由與道德才能在感性世界中一體實現,即人才能從“虛無”躍入“存在”。
綜上,筆者在上文中重塑了“人之自然”,即通過揭示人之存在的基礎(也即因果一體的“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自由自覺的本真的生命實踐)而揭示了人如何存在;進而,重塑了“自然法”,即內在于生命需要和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中的“生-生”的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它是“生命之道”,也便是“自然法”;同時,還重塑了人之存在的“第一因”,即具有內在自然法之導向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慈’)”,它是一種感性世界中的活的力量。顯然,上述關于“人之自然”“自然法”和人之存在的“第一因”的知識便是人之“自我真理”。同時,因“‘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慈’)”是人之存在的“第一因”,因此,我們也可將此理論稱為“慈本論”。
從上述“慈本論”的“自我真理”出發,我們首先可以確認的是,具有“‘生-生’的自然法”之內在導向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便是人的(作為“具有本然性的應然性的內在尺度,并可在感性世界中現實化的自律的道德”的基礎)“良心”,這表現為如下三方面:第一,“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和內在于它的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即“‘生-生’的自然法”)是人之存在的基礎和根據,也便是美德和規范具有真正的價值的基礎與根據;其次,內在于“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的作為生命本真存在方式的“‘生-生’的自然法”為道德行為、道德判斷和道德規范提供了內在的本然性的應然性的標準和尺度,這不僅使道德成為自律的和自由的,還以其普遍性驅散了困擾現代人的道德相對主義的迷霧;第二,“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是一種活的力量,它為人提供了使道德在感性世界中現實化的動力。顯然,在確認了“良心”之后,我們便可回答阿倫特所遺留的“人類當以何辨別是非”的問題,即人類的“良知判斷”的基礎和尺度是什么。具體而言,“良知判斷”是一種扎根于良心的,以內在于良心的“‘生-生’的自然法”為尺度的生命情感性判斷,如對道德行為可能產生“安寧、和諧與喜悅”等生命情感,對不道德的行為可能產生“不安、不忍、厭惡、羞愧和悔恨”等生命情感。由此可見,良知判斷的基礎便是作為良心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其尺度是內在于良心的“‘生-生’的自然法”,它使良知判斷具有普遍性。
3 “立心”和“良心認識論”在道德教育中的基礎作用
我們已知,“‘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慈’)”是人的具有內在自然法導向的“良心”,它為道德在感性世界中的現實化提供了動力,為良知判斷和良知實踐提供了本然性的應然性的普遍尺度,為美德和規范提供了價值基礎。由此,幫助人們認識、激發、擴充和強化“良心”,即“立心”,是道德教育的前提、基礎和關鍵性的環節之一。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道德教育僅強調幫助學生“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正確使用邏輯思辨工具和方法、理解知性的美德觀念與道德規范,卻無法幫助他/她們認識、激發和強化“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良心”這一具有內在自然法導向的活的力量,就會遭遇蘇格拉底的“精神接生術”在雅典城的失敗。顯然,這并不是說“精神接生術”式的和知性的道德教育是不對的或不必要的,與之相反,它們必須且重要,但同時,它們是很不充分的,是缺少“良心”這一道德價值的依據、良知判斷的尺度和良知實踐的動力的,是缺失“立心”這一道德教育的關鍵環節的。
顯然,幫助人們“立心”的前提是以普遍性的知識確立“良心認識論”。我們已知,西方近代以來的主體性哲學缺乏人在感性世界中本真存在的實體論的知識,由此,此種既具有內在自然法導向又具有道德力量的“良心”和“良心認識論”都是缺失的。同時,人類歷史上曾有過一些關于此種良心及其認識的隱性知識,是人類的思想寶庫(如發端于孟子,經王陽明達到頂峰的心學思想),但因不究竟而不系統,也不能被大多數人所理解。由此可見,以普遍性的知識確立系統的“良心認識論”是急需開拓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哲學的基礎領域。
4 以普遍性的知識揭示“良心認識論”
這一部分將以普遍性的知識揭示“良心認識論”,包括體認良心的前提條件、良心在感性世界中的表現(即良心之“相”)、“認知性的生命理性譜系”和“立心”的原理。由于這里的“良心”也便是人之存在的“第一因”,因此,這里的“良心認識論”也便是“本體認識論”。
4.1 體認“良心”的前提條件——遮擋或超越“生存性恐懼”
我們已知,“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便是人之良心,它是內在導向的具有普遍性的良知判斷和良知實踐的基礎和尺度,是可以使它們在感性世界中現實化的活的力量。然而,這里的疑惑是,既然“良心”是一種活的力量,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就應該可以經常體驗到它。顯然,這和我們的經驗并不相符。
實際上,我們于日常生活中難以體驗到“良心”的根本原因在于“生存性恐懼”的遮蔽。正如在之前的系列文章[1-6,9-15]中指出的,“生存安全感意義上的對匱乏的恐懼”(即“生存性恐懼”或“畏死的恐懼”)是人之弱點,如果被它“困”住,便會被封閉于“(盲目追逐生存性安全感意義上的)僅僅為了活著的目的”和“嚴格的私人性”中。前者表現為盲目追逐匱乏感所指向的對象,或盲目屈從于異化的權威或異化的社會力量,從而失去了“選擇自己的自我”的自由能力而成為“萎縮者”;后者表現為對其所有的遭遇都反射性地機械性地用“對小我的有用性”來衡量與歪曲,由此,便既無法通過有效的交流和溝通而與他人形成“生-生”式的道德關系(也即陷入“原子式個體”的封閉狀態),又會因“對小我的有用性”的“神秘參與”而仿佛戴上了“哈哈鏡”來看世界,即無法在感知和判斷中“看”到“真”。同樣地,在匱乏感與恐懼感的逼迫下,“對小我的有用性”的“神秘參與”(即以“對小我的有用性”對自己的遭遇進行衡量與歪曲)后產生的以焦慮和恐懼為底色的反射性的機械性的情緒反應也使得人們無法體驗到“良心”這種活的力量。
由上可知,“生存性恐懼”是人們可以切入良心這一事實從而產生對良心的覺知和體認的障礙,它也便是道德教育中“立心”的障礙。也就是說,“立心”的前提條件是超越或遮擋“生存性恐懼”而使作為一種活的力量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良心”得以顯現。
當然,人們在庸常生活中不能體驗到“良心”這種活的力量的另一個原因是“良心”的表現未曾被系統地以普遍性的知識揭示出來。顯然,只有當人們了解了“良心”在感性世界中的表現,在體驗到“良心”時,它才能被辨認出來。下文中,我們將以普遍性的知識揭示“良心”之表現,顯然,相對于被“生存性恐懼”遮蔽的庸常經驗,這些表現是“不同者”。
4.2 以普遍性的知識揭示“良心”之“相”——“不同者”
“良心”,即“‘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慈’)”是人之存在的“第一因”,它在感性世界有其表現。為了區別于人在“生存性恐懼”的遮蔽下,即在恐懼感和匱乏感的逼迫下的“虛無”(即存在之異化)在感性世界中的表現,我們將人之存在的“第一因”(即“良心”)和其所推動的“存在者”在感性世界中的表現稱為“相”,與之對應,將“生存性恐懼”和其所推動的“虛無者”在感性世界中的表現稱為“現象”。顯然,在感性世界中,“相”與“現象”是混雜的,但“相”相對于“現象”是“不同者”。由此,通過作為“不同者”的“相”,我們可以辨認“存在者”是否存在,即人之存在的“第一因”(也即“良心”)是否得以在感性世界中顯現,或者說,“良心”是否被“生存性恐懼”所遮蔽。
筆者在之前的系列論文[1,9-15]中根據是否受制于“生存性恐懼”而將人之生活境況區分為“片面的生存性境況”和“生命性境況”。其中,“片面的生存性境況”是被“恐懼感”和“匱乏感”封閉于前述的“僅僅為了活著的目的”和“嚴格的私人性”中的人之異化的狀況,也就是說,它所體現的是“生存性恐懼”和其所推動的“虛無者”(即前述作為“原子式個體”的“萎縮者”)在感性世界中的“現象”;與之相反,“生命性境況”是人超越了“生存性恐懼”從而擺脫了匱乏感和恐懼感的人之存在的狀態,其中的個體是作為感性世界中的本真存在的“存在者”的“超個體的個體”(也可被稱為“跨主體性的個體”[5-6]),這種既具有“選擇自己的自我”的自由能力,又具有結成“生-生”式的(即主體間性的)道德關系的道德能力的強壯的個體,也即是具有獨立人格的道德主體。也就是說,“生命性境況”所體現的是人之存在的“第一因”(也即“良心”)和其所推動的“存在者”(即“超個體的個體”)在感性世界中的“相”。顯然,對人來說,其具體的生活境況是非此即彼的,即以遮擋或超越“生存性恐懼”為樞紐,人或是處于“生命性境況”而使“存在者”顯現,或是處于“片面的生存性境況”而使“虛無者”顯現。我們可以將上述機制描述為以超越“生存性恐懼”為樞紐的“生命面向的翻轉”,即由“虛無”躍入“存在”。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于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情境下,生存性恐懼會被某些原因遮擋,也會發生生命面向的翻轉,此時,我們也會切入“‘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的事實,從而獲得對“良心”的體驗[9,15]。如在孟子的“乍見孺子入井”的故事中,因“乍見”而“生存性恐懼”尚未升起,因此,救人者在救人時處于“生命性境況”,即“良心”得以顯現;當人們被自然的大美和藝術的大美震撼而“忘我”時,或處于極度專注的狀態而“忘我”時,生存性恐懼同樣未能升起,人們同樣切入了“良心”的事實,此時他們所體驗的安寧、和諧與喜悅便是“存在者”存在,即“良心”突破遮蔽而顯現的有力證明。由此可知,即使在無超越生存性恐懼的自覺的情況下,人也可能在其一生中隨著是否受制于“生存性恐懼”而不斷變換著生活境況,即不斷切入“良心”的事實和對它的體驗。
然而,這里的問題是,既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會體驗到“良心”的,為什么我們沒有發現它?即為什么我們不能辨認它?實際上,人們曾經切入過“良心”事實卻不能辨認“良心”的原因是沒有關于“良心”的表現(即“相”)的知識,由此,便不能敏感于這些與庸常狀態(即被“生存性恐懼”遮蔽的“片面的生存性境況”)中的“現象”不同的“不同者”,由此,即使體驗到了“良心”,因不能辨認而將它忽略了。
由上可見,給出“良心”的“相”的普遍性的知識是“良心認識論”的重要部分,是作為道德教育的基礎和關鍵環節的“立心”的前提條件。可惜的是,由于沒有看到“‘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慈’)”是人之存在的基礎和“第一因”[9],同時,它便是人的作為一種活的力量的“良心”,之前的哲學或將“良心”觀念化(如康德的知性的善良意志)從而取消了它在感性世界中的“相”;或是僅以隱性知識(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道、本心、心即理、養浩然之氣、明明德等)給出包括“相”在內的人之存在的實體論的知識,但無法使大多數人理解;或是如近代以來居于政治和倫理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與功利主義一樣將內在導向的“良心”丟棄。因此,給出關于“良心”和其“相”的普遍性的知識(即常人可以理解的知識)不僅對推動道德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對推進道德哲學體系的重構和發展也有重要的作用。下面,我們將從生命態度和行為方式、情感或情緒模式兩個方面討論感性世界中的人之“存在”之相和“虛無”(即存在之異化)之現象的不同。
4.2.1 生命態度和行為方式的不同
在筆者之前的論文中區分了人的“生命性境況”(即“存在”)與“片面的生存性境況”(即“虛無”)中的人之生命態度和行為方式的不同,也即“相”與“現象”在生命態度和行為方式方面的不同。
具體而言,在“片面的生存性境況”中,人會被“匱乏感”和“恐懼感”封閉在(盲目追逐生存性安全感意義上的)“僅僅為了活著的目的”和“嚴格的私人性”(即“對小我的有用性”或“狹隘的私利”)中。其中,前者表現為盲目追逐匱乏感所指向之對象,或盲目屈從于異化的社會力量,從而喪失“選擇自己的自我”的獨立能力而成為“萎縮者”;而“嚴格的私人性”則表現為失去了相互通達的能力而陷入“原子式個體”的片面的個體性的狀態,即對其所遭遇的所有事物,包括他人的言行,都反射性地機械性地用“對生存性小我的有用性/狹隘的私利”來衡量與歪曲,便失去了相互間有效溝通的可能性。由此,這些作為原子式個體的萎縮者既喪失了使自由現實化的能力,也喪失了使道德現實化的能力。總之,“虛無者”被“生存性恐懼”逼迫著盲目追逐或盲目屈從,而這種“役于外物”或“役于外力”的外在導向的“(片面的生存性的)小我”(即作為“原子式個體”的“萎縮者”的)人格便是人之異化(或“生存性恐懼”及其所推動的“虛無者”)所表象的“現象”在生命態度和行為方式上的體現。
與“片面的生存性境況”中的“非存在”所表象的“現象”不同,“生命性境況”中的具有內在的自然法導向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慈’)”(即“良心”)和其所推動的“存在者”之“相”則體現為扎根于“良心”(即誠于“良心”)的“大我”人格下的生命態度和行為方式。正如筆者在之前的系列文章[9,15]中所揭示的,在人的“‘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慈’)”中,人實現了個體性和整全性的統一。具體而言,在作為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的“‘生-生’的自然法”下,人處于“整體關聯”中,而人之“整體關聯之在”,即“生-生”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擴展而成的開放的“人類生命共同體”是超越時間的,是永恒的,其中的每一個節點(即每一個人類個體)都可被看作是“永恒的人類生命共同體”的一環,即“潛在的人類生命共同體”。也就是說,人類個體既是個體化的她/他自己,又是“潛在的人類生命共同體”這一“永恒的大我”,即她/他處于個體性與整全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之中。顯然,對于人來說,“我是潛在的人類生命共同體”是可以被自覺認識的,進而,他/她對此的確認會帶給他/她與永恒相關的生命意義和由此獲得的勇氣和力量感所形塑的整全性的人格(即“大我”人格)基礎上的精神維度指導下的生命態度和行為方式。進而,此種“大我”人格的行為方式便是“生-生”式的生命實踐,在筆者之前的系列文章[3,6,9,11,13,15-16]中將它稱為“互慈和創”,即由“慈”推動的人與人之間肯定、成全與擴展雙方自我,肯定、成全與擴展雙方生命的,協同創生的有意識的生命實踐。它既使人獲得了“選擇自己的自我”意義上的自由的現實化,也獲得了道德的現實化,也就是說,這種大我人格便是具有獨立人格的道德主體。顯然,上述“大我”人格基礎上的精神維度指導下的生命態度(它以意義感、自由感、安全感和推開“生存性恐懼”后的勇氣和力量感為其特征)和“互慈和創”的生命實踐便是“良心”之“相”在生命態度和行為方式上的體現。
4.2.2 內在導向的生命理性情感與外在導向的盲目的生存性情緒
在“生命性境況”中,人之“良心”的“相”還體現為如下四個方面的具有內在自然法導向的情感,因它們內蘊了“生-生”的“自然法”,即具有內在的(互為目的意義上的)道德理性和(選擇自己的自我意義上的)自主(理)性,我們可以稱之為“生命理性情感”,簡稱“理性情感”或“生命性情感”。也就是說,“良心”具有如下四個方面的“生命理性情感”式的“言說”方式。具體而言,首先,是背景性的生命理性情感,即扎根于具有內在的“生-生”的自然法導向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慈’)”(即“良心”)的安寧感、安全感、喜悅感和和諧感,它們是貫穿于人之存在的情感“底色”;其次,是實踐判斷性生命理性情感,即扎根于“良心”的,可以以其內在的自然法為尺度而對自己或他人的行為作出善惡判斷的情感。如對道德的行為表現出安寧感、和諧感、贊同感和喜悅感,對不道德的行為表現出不安、不忍、不和諧、丑陋感、厭惡感、懊悔和羞恥感等;再次,是認知判斷性生命理性情感,即扎根于“良心”的,可以以其內在的自然法為尺度而對自然或藝術等精神作品等作出判斷的情感,如面對自然美的安寧感、和諧感和喜悅感,面對不好的作品的焦慮感、不和諧感、厭惡感、不適感和疏離感;最后,是動力性的生命理性情感,即扎根于“良心”的,具有內在的自然法導向的可以推動互慈和創的生命實踐(也即道德實踐)在感性世界中現實化的情感,如“惻隱”“同情”“不忍做……”或“不忍不做……”等。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后三種生命理性情感都是建立在背景性的生命理性情感的情感底色之上的。
與上述四類作為“良心”的“相”的“生命理性情感”相對應,被“生存安全感意義上的對匱乏的恐懼”(即“生存性恐懼”)封閉于“片面的生存性境況”中的“虛無者”具有與之不同的情緒性表象,即情緒“現象”,這體現為如下四個方面的外在導向的(即受制于匱乏感或恐懼感所指向的對象的)盲目的“生存性情緒”。具體而言,首先,是背景性的生存性情緒,即外在導向的(即受制于恐懼感或匱乏感所指向的對象的)以焦慮感、匱乏感、恐懼感和喪失安全感為主的背景性情緒,它們是貫穿于人之“虛無”的情緒“底色”;其次,是實踐性判斷性的生存性情緒,即對自己或他人的行為進行外在導向的(即受制于恐懼感或匱乏感所指向的對象的)善惡判斷時的情緒反應。我們已知,“片面的生存性境況”中的“虛無者”或是反射性地機械性地以“對小我的有用性”為尺度,或是盲從外在的道德尺度而對自己或他人的行為進行判斷,進而對所謂的“道德”行為產生占有感下的快適感(即占有性的滿足感,其中包括欣喜、狂喜、竊喜、舒適、短暫的安全感等快感,但其情緒底色仍然是焦慮感、恐懼感和匱乏感,且很快被追逐匱乏感指向的其他對象帶來的焦慮或痛苦等負面情緒取代),對所謂的“不道德”的行為產生損失感下的怨恨、憤恨或憤怒感、失望和痛苦感、煩悶感、不安感和絕望感等情緒。需要再次提醒的是,這種情緒反應受制于匱乏感所指向的對象或外在的被阿倫特比喻為“餐桌禮儀”的(即未經反思而盲從的)風俗習慣和規則規范,也就是說,這些判斷性的情緒都是外在導向的,是無根的和盲目的;再次,是外在導向的(即受制于匱乏感和恐懼感所指向的對象的)動力性的生存性情緒。我們已知,“片面的生存性境況”中的“虛無者”會盲目追逐匱乏感所指向的對象,由此會反射性地機械性地以“對小我的有用性”為尺度來衡量自己的“遭遇”,進而產生由占有的期待或損失感引發的可以推動行動的焦躁或焦慮感、快適感、厭惡、嫉妒、失望、痛苦、煩悶、怨恨與憤恨等情緒;最后,是認知判斷性生存性情緒,即對自然或藝術等精神產品做出外在導向的(即受制于恐懼感或匱乏感所指向的對象的)判斷的那些情緒,即反射性地機械性地以盲目內化的(即毫無反思的)規范為尺度衡量自然或藝術等精神產品,或反射性地機械性地以“對小我的有用性”為尺度來衡量與歪曲自然或藝術等精神產品,這些情緒包括占有感下的快適感(如對自己門派的作品產生的情緒反應)、喪失感下的嫉妒及因嫉妒而產生的絕望感、痛苦和憤恨感(如對非自己門派的作品產生的情緒反應)、盲目內化的規范評判下的無動于衷的無聊感與冷漠感等。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后三種情緒都是建立在焦慮感、匱乏感、恐懼感和失去安全感的情緒底色之上的。
綜上,因扎根于“‘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慈’)”,生命理性情感是相較于被(生存性恐懼遮蔽的)庸常狀態中的盲目的生存性情緒的“不同者”,其特征表現為:第一,如前所述,生命理性情感是理性的(既包括道德理性,也包括自主理性),由此,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統一;第二,由于內蘊了“生-生”的自然法,生命性情感是自由性與道德性的統一;第三,由于以人類共同的超越性的自然法為內在尺度,因此,生命理性情感是具有超越性的普遍性的情感,進而,根據它們所作的判斷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是自愛與公正的統一。
4.3 認知性的生命理性譜系
我們已經了解了作為良心的“相”的生命理性情感的譜系,它們可以被看作是“良心”或“生命需要”的“言說”,此種情感性的“言說”方式決定了認識良心所需要的理性與傳統的純粹理性和工具理性全然不同,作為區分,我們稱之為“認知性的生命理性”。認知性的生命理性是一個譜系,包括自我覺察力、自我覺察力之上的“具象性情感性的認知性生命理性”和“情感性的認知性生命理性”,在對良心的認識過程中,它們是相互配合的。
具體而言,首先,是自我覺察力,即保持對生命理性情感和生存性情緒的覺知,它對于感性世界中的人之存在的敞開和良心的認識具有基礎性的作用。具體而言,一方面,保持對生命理性情感的覺察力才能激活具有內在自然法導向的情感性的生命理性譜系(它不僅包括認知性的,還包括實踐性的。后者與本文相關度不大,因此不再贅述);另一方面,保持對生存性情緒的覺察力有助于打斷盲目的行為方式,進而為生命理性得以運用,從而使人回歸“選擇自己的自我”的自主性和自由,即回歸存在(也即“為其所是”)創造條件。總之,自我覺察力是生命理性得以運用的基礎和前提。
其次,是“具象性情感性的認知性生命理性”,它體現為三種能力,即建立在“具象性情感性的抽象能力”(顯然,這種抽象與不具有感性特征的與定義聯系在一起的“純粹抽象”不同,它是感性具體與抽象的結合)之上的“藝術性的創造能力”(也可稱為“具象性情感性的價值創造或凝固能力”)、 “藝術性的判斷能力”(也可稱為“具象性情感性的價值判斷能力”)、“藝術性的理解能力”(也可稱為“具象性情感性的價值融解能力”)。需要注意的是,這里所謂的“藝術性”是指具象性或意象性,比通常理解的“藝術”范圍更廣,如針對抗疫中的“最美逆行者”所進行的敘事雖然不屬于通常認為的“藝術”,但也是具象性的和意象性的,因此,我們也稱之為“藝術性的”;再如,中國古典的哲學經典(如《莊子》)通常也是文學作品,但習慣上并不將它們歸于藝術,這里,我們可以稱之為“藝術性的原初哲學”。其中,“藝術性的創造能力”是指將覺察到的具有內在自然法導向的生命理性情感以具象性情感性的抽象能力凝結成具有內在自然法之導向的音樂、美術、詩歌、小說、敘事、藝術性的原初哲學等的具象性的情感性的藝術性作品的能力。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因這些藝術性作品具有內在的自然法導向,因此,真正的藝術是具生命理性的,即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統一,而并非僅僅是感性的或非理性的。同時,真正的藝術性作品表達的必然是具有內在自然法之導向的具象性或意象性的價值觀念,是“良心-生命需要”的“言說”,而不是“片面的生存性需要”的表達;“藝術性的判斷能力”是指依據生命理性情感所內含的“生-生的自然法”對藝術性作品進行鑒別和判斷的能力。顯然,相較于以“對小我的有用性”為中介的感知判斷(即“感知為……”判斷)[5],這種以自然法為尺度的“藝術性判斷”是具有普遍性的;“藝術性的理解能力”則是指從“具象性情感性抽象”而成的藝術性作品中直覺或捕捉到生命性情感和價值的能力,即捕捉到“良心-生命需要”的“言說”的能力。
再次,是“情感性的認知性的生命理性”,它體現為三種能力,即建立在“情感性的抽象能力” (而非純粹抽象)之上的“情感性的原初哲學創造能力”(也可稱為“情感性的價值創造或凝固能力”)、“情感性的原初哲學判斷能力”(也可稱為“情感性的價值判斷能力”)和“情感性的原初哲學理解能力”(也可稱為“情感性的價值融解能力”)。具體而言,第一,是“情感性的原初哲學創造能力”,它是將覺察(這里既可能是對“良心-生命需要”的“言說”的直接的覺察,也可能是對藝術性作品中的意象性情感性抽象后的“良知-生命需要”的“言說”的覺察)到的具有內在自然法導向的生命性情感以情感性的抽象能力凝結成具有內在自然法之導向的情感性的價值觀念的能力,這是原初哲學家(如巴門尼德和蘇格拉底)所具有的一種“情感性的價值凝固能力”。顯然,在這些原初哲學家那里,價值觀念是和豐沛的具內在自然法導向的情感和力量聯系在一起的。如蘇格拉底就聲稱自己從小就可以聽到向他說話的內在的聲音,他稱之為“daimon”(神靈),這是希臘語中對一個干預自然和人類生活的非人格化的神的稱呼[17]。在“慈本論”的“自我真理”的視角下,我們可以合理推測,蘇格拉底內心的聲音便是他覺知到的作為一種活的力量的“生命需要-良心”的“言說”,因此,蘇格拉底在與雅典人的對話中雖然努力通過邏輯分析這種純粹抽象而思考一些已有的模糊概念,但在他自己那里,這些概念卻是與他所謂的“神靈”賦予的情感和力量聯系在一起的;第二,是“情感性的原初哲學判斷能力”,是指依據生命理性情感所內含的自然法對情感性的原初哲學作品進行判斷的能力;第三,是“情感性的原初哲學理解能力”,它是指從“情感性抽象”而成的情感性的原初哲學作品中覺知和捕捉到具有內在自然法之導向的生命性情感和價值的能力。

表1 存在者與虛無者的不同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經典經常也是文學作品,也就是說,中國傳統哲學是通過具象性情感性的認知性生命理性和情感性的認知性生命理性進行表達的,即它們是藝術性的原初哲學或情感性的原初哲學。
顯然,上述 “具象性的情感性的認知性生命理性”和“情感性的認知性生命理性”都超越了以“理性和情感之割裂”為前提的西方理性主義和情感主義,即實現了情感和理性的統一。同時,由于扎根于具內在自然法導向的人之“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良心”,它們也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學中的純粹理性(即剝離了情感的無力的理智)和工具理性(它服務于外在導向的役于外物或役于外力的“狹隘的自利/對小我的有用性”,它是將自我作為實現外在目的的工具的虛假的理性)。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純粹理性基礎上的理性主義所持的純粹抽象的價值概念只是藝術性或情感性的原初哲學中的具有內在自然法導向的意象性或情感性價值“干枯”之后的體現,它們既因缺乏價值根基而表現為無根性、形式化和支離化,也因無力而無法彌補知與行之間的裂隙。
4.4 “立心”的原理
我們已知,“良心”(也即作為人之存在的“第一因”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力”)一方面表達為具內在自然法導向的生命理性情感,另一方面表達為在對此種情感的自我覺察基礎上的生命理性。由于各種生命理性情感和生命理性具有共同的根基,即內蘊著“‘生-生’的自然法”的“良心”,因此,它們具有普遍性和相互促進性。
具體而言,一方面,各種生命理性情感和生命理性都以內在于“良心”的人類共同的“‘生-生’的自然法”為尺度和導向,因此,它們并非是因人而異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另一方面,因各種生命理性情感和生命理性都扎根于“良心”,因此,它們是相互促進的,即激發和強化任何一種生命理性情感或生命理性都可以通過激發和強化作為其基礎的“良心”,進而激發和強化其他的生命理性情感和生命理性。如通過覺察在自然大美中體驗的安寧喜悅的生命理性情感,便可以激活和強化“良心”(即“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驅動”),進而激發和強化認知判斷性的生命理性(如藝術鑒賞能力)、實踐判斷性的生命理性(如道德判斷能力)和動力性的生命理性情感(如作為道德實踐的動力的同情)等其他的生命理性和生命理性情感。總而言之,正是各種生命理性情感和生命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相互促進性使得認知、激活、擴充與強化良心及其功能與表達,即“立心”成為可能。
綜上,“立心”是道德教育的基礎和關鍵環節,進而,通過上述“良心認識論”,我們已知“立心”的前提條件是:①創造“生存性恐懼”被遮擋或超越從而可以切入“良心”之事實的機會;②確認關于“良心”在情感、人格、生命態度和行為方式等方面的“相”的普遍性的知識,即以大多數人可以理解的知識確認(那些相較于被困于“生存性恐懼”的“虛無者”所表象的“現象”的)“不同者”,從而使得人們在切入“良心”的事實時可以辨認對“良心”的體驗和辨認“存在者”的存在;③保持自我覺察力以激活具內在“自然法”導向的生命理性譜系和切斷盲目的行為方式。與此同時,“立心”的原理在于生命理性情感和生命性理性的普遍性和相互促進性。在此基礎上,我們便可以討論醫德教育中的“立心”的可能路徑了,它與外在制度的變革(即不制造生存性恐懼的外在制度)相輔相成,將使醫德狀況徹底改觀。關于“立心”的可能路徑,我們將另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