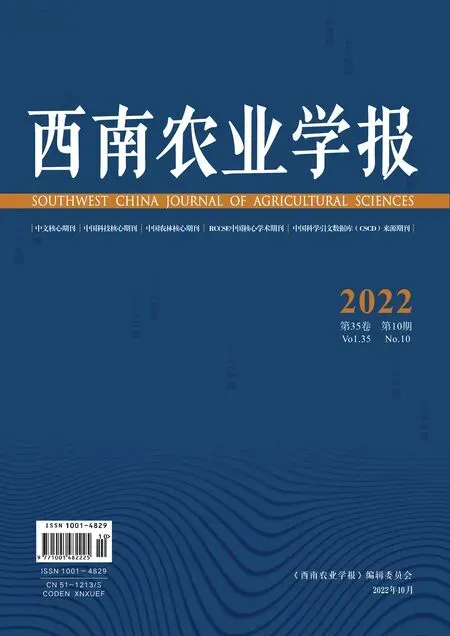滇東土壤重金屬高背景區不同農田利用方式對作物鎘砷含量的影響
楊 趙,和麗萍,姚紅勝,王 麗,李麗娜,楊濤明,唐 嫚,崔燦文
(云南省生態環境科學研究院,昆明 650034)
【研究意義】土壤重金屬含量關系到食物安全及人類和動物健康,其作為土壤質量的一個重要評價指標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1]。研究不同農田利用方式對農田土壤和作物重金屬的影響,對區域土壤重金屬污染的防控具有重要意義。【前人研究進展】中國區域農田土壤重金屬污染嚴重,以西南(云南、貴州等地)、華中(湖南、江西等地)、長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區較為突出[2]。云南地質構造復雜,金屬礦藏豐富,土壤母質重金屬背景值含量高,不合理的礦產資源開發和落后的處理技術,將大量含有重金屬的廢氣、廢渣、廢水排入土壤中,導致目前土壤重金屬污染問題較為嚴峻。云南省土壤重金屬污染面積大、種類多、副作用明顯,是重金屬污染最突出的地方之一[3]。張小敏等[4]通過Kriging插值得出,在云南農田土壤中Pb、Cu、Cr、Zn、Cd 出現高值區,其中云南省農田土壤中Pb和Zn的富集最高,是超出背景值最高的省份。滇東區域是云南典型的土壤重金屬高背景值分布區[5],也是云南受礦業活動影響的重點區域。云南省內滇東碳酸鹽巖發育區為最高,巖層形成的紅黏土Cd元素含量高達1.64×10-3~2.76×10-3mg/kg[6-7]。滇東土壤鎘的地球化學背景值不僅超過《土壤環境質量 農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試行)》(GB15618—2018)中的污染風險篩選值,有的甚至超過了污染風險管制值[8]。土地利用方式是人類活動的集中體現,它既能反映污染物的主要來源,又能反映影響重金屬移動和傳輸的土壤屬性[9-10]。土地利用類型和強度對土壤微量重金屬元素遷移富集具有強烈的影響[11]。國內學者對不同農用地利用方式土壤重金屬含量進行了調查研究[12-14],但研究區多為受工業污染的區域。【本研究切入點】在土壤重金屬高背景值區,排除工業源直接或間接污染外,因農田利用方式不同而帶來的農業投入品的差異是造成高背景值區農田土壤重金屬含量差異的主要原因之一[15]。【擬解決的關鍵問題】本研究針對滇東鎘、砷高背景區不同利用類型的農田土壤鎘、砷含量及農作物鎘、砷含量進行調查,研究不同農田利用類型對土壤鎘、砷的分布特征及對作物安全性的影響。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如圖1所示,研究區位于云南省東部(101.25°~106.87°E,22.5°~28.34°N)。該區域屬于亞熱帶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7.7~18.4 ℃,常年降雨量641~987 mm。土壤類型以磚紅壤、紅壤為主,成土母質主要以碳酸鹽類為主。地形地貌屬滇東喀斯特巖溶山區,山巒連綿起伏,河谷、溝壑縱橫交錯,地勢復雜性和緯度復合變化造成成土過程和土壤類型的多樣性。滇東農田利用類型以旱地、水-旱輪作、蔬菜地為主。
1.2 土壤樣品采集與處理
2020年4月20日至25日分2組進行采樣。采樣點位確定后,根據實際情況劃定采樣區域為20 m×20 m。以采樣點位為中心,避開田邊、路邊、溝邊和特殊地形的部位以及堆過肥料的地方,按照梅花布點法用不銹鋼土鉆采集5個小樣點0~20 cm的表層土壤,把各點采集的土壤混合均勻后用四分法處理,留取1 kg左右土壤作為該點樣品,裝入自封袋,并在袋口填寫標簽。土壤樣品在室內風干后,去除土樣中石子和動植物殘體等異物,用木杵研磨過2 mm尼龍篩,混合均勻后,取200 g土樣,用瑪瑙研缽研磨過100目篩,備用。
土壤樣品采用《土壤環境質量農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標準(試行)》(GB 15618—2018)中規定的方法測定,其中鎘采用石墨爐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16]、砷采用原子熒光法(GB/T 22105.2—2008)測定[17]、土壤pH采用電位法(HJ 962—2018)測定[18]、有機質采用滴定法(NY/T 1121.6—2006)測定[19]、土壤有效態鎘采用二乙烯三胺五乙酸浸提—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法(HJ 804—2016)測定[20]、有效態砷采用AB-DTPA浸提—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法測定[21]。
1.3 作物樣品處理及分析
采集土壤樣品時同步采集作物可食部分樣品,取回的植物樣品用自來水清洗表面粘附的土壤,新鮮蔬菜用去離子水淋洗3遍,晾干進行勻漿,小麥、水稻、玉米籽粒晾干后經粉碎機粉碎均勻。勻漿或粉碎均勻的樣品采用微波消解、ICP-MS 測定Cd、As含量[22]。
1.4 土壤污染評價方法
采用Hakanson[23]提出的潛在生態風險指數法評價重金屬污染及生態危害。其計算公式為:



表1 重金屬潛在生態風險評價指標與分級
1.5 統計分析
本研究中采樣點位分布圖采用ArcGIS 10.2繪制,利用SPSS 19.0統計分析軟件對原始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和方差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土壤pH和有機質含量特征
本次共調查162個點位,包括蔬菜地61個,水-旱輪作地26個,旱地75個。調查區域土壤pH范圍為4.85~8.49(表2),均值為7.15,pH 6.5以上的點位占76.5%,調查區域農用地土壤以中性偏堿為主。農田各類利用方式中,土壤pH由高到低依次為水-旱輪作地、蔬菜地、旱地,其中旱地土壤pH顯著低于蔬菜地和水-旱輪作地(P<0.05),且旱地土壤pH離散程度更大。

表2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下土壤pH和有機質含量
調查區域土壤有機質含量范圍為10.3~118.0 g/kg,區域土壤有機質含量變異程度較大。與中國第二次土壤普查養分分級標準比較,調查區域土壤有機質含量達到1級的點位占55%,土壤有機質含量總體較為豐富。農田各類利用方式中,土壤有機質含量由高到低依次為水-旱輪作地、旱地、蔬菜地(表3),但三者間均無顯著差異(P>0.05)。而農田各類利用方式中,土壤有機質含量的變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為蔬菜地、水-旱輪作地、旱地。
2.2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土壤鎘、砷含量特征
2.2.1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土壤鎘、砷含量及污染狀況 調查結果顯示,滇東區域農田土壤鎘含量分布為0.10~3.2 mg/kg,超篩選值比例為59.88%,超管制值比例為3.09%。農田各類利用方式中,土壤鎘含量由高到低依次為蔬菜地、水-旱輪作地、旱地(表3),但三者間均無顯著差異。各類利用方式的土壤鎘含量分布均表現為較大的變異,且變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為蔬菜地、水-旱輪作地、旱地。

表3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下土壤鎘、砷含量
滇東區域農田土壤砷含量分布為2.59~112.0 mg/kg,超篩選值比例為35.80%,超管制值比例為1.23%。農田各類利用方式中,土壤砷含量由高到低依次為旱地、蔬菜地、水-旱輪作地,且旱地土壤砷含量顯著高于水-旱輪作地。各類利用方式的土壤砷含量分布均表現為較大的變異,且變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為蔬菜地、旱地、水-旱輪作地。
滇東區域農田土壤鎘與砷相比,鎘超篩選值和管制值比例高于砷,同時土壤鎘含量的變異程度大于砷。
2.2.2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土壤鎘、砷有效態含量特征 調查區域農田土壤有效態鎘平均含量為0.061 mg/kg,表現為蔬菜地>水-旱輪作地>旱地(表4),有效態砷平均含量為0.212 mg/kg,表現為蔬菜地>旱地>水-旱輪作地,但不同農田利用方式間差異均不顯著。將土壤重金屬有效態含量除以重金屬全量值稱為重金屬的活化率[24]。分別計算各農田利用類型土壤鎘、砷的活化率,結果表明調查區土壤鎘、砷活化率區間分別為0.162%~0.231%和0.013%~0.041%,活化率均較低。蔬菜地土壤鎘、砷活化率均顯著高于旱地,旱地和水-旱輪作地、蔬菜地和水-旱輪作地間土壤鎘、砷活化率均無顯著差異。同一農田利用類型下,土壤鎘活化率均顯著高于砷活化率。

表4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土壤鎘、砷有效態含量及活化率
2.3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農作物鎘、砷含量特征
參照《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中食品類別分類方式,本次調查采集到稻谷、玉米、小麥、葉菜、蕓薹類蔬菜、塊根和塊莖蔬菜、瓜果類蔬菜、豆類8個類別的農作物可食部分樣品共計162個。調查作物鎘、砷含量均較低(表5),僅有2個樣品鎘含量超過GB 2762—2017限值,分別為茄子和辣椒。調查的各類作物中,鎘含量由高到低依次為小麥、瓜果類蔬菜、塊根和塊莖蔬菜、葉菜、稻谷、蕓薹類蔬菜、玉米、豆類;砷含量由高到低依次為稻谷、小麥、葉菜、玉米、塊根和塊莖蔬菜、瓜果類蔬菜、豆類、蕓薹類蔬菜。各類作物對鎘、砷的富集系數均較低,鎘富集系數由高到低分別為小麥、葉菜、塊根和塊莖蔬菜、稻谷、蕓薹類蔬菜、瓜果類蔬菜、玉米、豆類;砷富集系數由高到低依次為稻谷、葉菜、小麥、玉米、蕓薹類蔬菜、豆類、瓜果類蔬菜、塊根和塊莖蔬菜。

表5 農作物鎘、砷含量
按不同農田利用類型對所調查的農作物可食部分鎘、砷含量進行分析(表6)。結果表明,蔬菜地農作物可食部分的鎘含量顯著高于旱地農作物,而水-旱輪作地農作物可食部分鎘含量與旱地和蔬菜地的農作物鎘含量間均差異不顯著。但水-旱輪作地農作物可食部分砷含量顯著高于旱地和蔬菜地的農作物砷含量。蔬菜地農作物鎘富集系數顯著高于旱地農作物,而水-旱輪作地農作物的砷富集系數顯著高于蔬菜地和旱地。同一農田利用類型下,農作物的鎘富集系數均顯著高于砷富集系數。

表6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農作物鎘、砷含量
2.4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土壤鎘、砷的潛在生態風險評價
從表7可知,滇東區域3種農田利用方式下土壤鎘、砷潛在生態風險指數(Ri)由高到低為水-旱輪作地>早地>蔬菜地,分別為51.48、51.09和37.22,均小于150,屬輕微風險。從單元素角度分析可知,土壤鎘在蔬菜地中潛在生態風險最大(Ei=29.69),旱地中最小(Ei=16.55);土壤砷在旱地中潛在生態風險最大(Ei=34.54),水-旱輪作地中最小(Ei=18.47)。土壤鎘、砷在3種農地利用方式中潛在生態風險值均小于40,風險等級屬于輕微,潛在生態風險低。

表7 不同農田利用方式土壤鎘、砷潛在生態風險評價
3 討 論
關于土壤重金屬含量及分布特征的研究多集中于有明確污染源或人為影響較重的區域,如因礦業活動而導致重金屬污染的農田集中區或流域[25-28],而本研究選取滇東區域中無主要重金屬污染源輸入的農田作為研究對象。本次調查農田除人工耕作擾動外,無其他較大外源干擾,因此土壤母質、大氣的干濕沉降、農業灌溉、施肥、噴灑農藥和除草劑是不同農田利用類型土壤重金屬的主要來源,其結果是高背景區農田不同利用方式對土壤鎘、砷含量特征及生態風險的體現。調查結果表明,在旱地、蔬菜地、水-旱輪作地3種不同利用類型間土壤鎘、砷含量沒有顯著差異的情況下,土壤的有效態鎘、砷在3種利用類型間表現出差異性,且蔬菜地土壤鎘、砷含量變異程度最大,鎘、砷有效態含量和活化率均最高。這種差異可能是由于滇東區域蔬菜地與旱地和水-旱輪作地相比,具有更高的肥料、農藥投入和更多的翻耕頻次。研究表明滇東區域蔬菜地化肥施用量高于以糧食生產為主的旱地和水-旱輪作地[29]。周萍等[30]研究結果表明,施用肥料的質量和數量是影響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重金屬含量的主要因素。菜園隨著種植蔬菜時間的延長,土壤中Zn、Cu、Pb的全量含量和有效態含量均有明顯增高的趨勢[31]。耕作方式可通過影響土壤pH和有機質含量進而影響土壤重金屬的有效量,成為影響土壤重金屬含量、有效性及垂直分布的另一因素[32-33]。頻繁翻耕不利于土壤有機質的積累[34],頻繁翻耕蔬菜地導致有機質的降低,有機質對重金屬的吸附、鈍化作用也降低,進而導致蔬菜地相比水-旱輪作地、旱地有更高的土壤鎘、砷活性。
盡管本次調查中土壤樣品鎘含量超篩選值比例為59.88%,超管制值比例為3.09%,砷含量超篩選值比例為35.80%,超管制值比例為1.23%。但采集的162個農作物樣品中僅有2個作物超標。相關分析也表明作物鎘、砷含量與土壤鎘、砷含量和有效態含量均無顯著相關性。馬宏宏等[35]針對碳酸鹽巖母質重金屬地質高背景區的調查結果也表明土壤和水稻籽實中同一種重金屬含量之間沒有顯著相關性。王祖光等[36]對中國稻米產區土壤稻米一一對應采集的80 000個樣點數據統計結果表明,土壤Cd含量超過篩選值稻米Cd含量不超標和土壤Cd含量未超過篩選值稻米Cd含量超標的土壤環境風險誤判率在湖南長株潭地區,廣東北部與湖南接壤地區,四川綿竹、什邡市等區域為64%~79%。土壤重金屬含量及其有效態含量不能有效表征土壤環境風險的原因在于農產品對土壤重金屬的吸收主要由作物自身的內因和作物所處的環境外因共同決定。內因即作物自身對污染物脅迫的耐受能力。外因一方面取決于土壤污染物的含量和有效態含量,另一方面也取決于與污染物產生相互作用的物質含量。這些物質可以與污染物產生協同、拮抗、固持等作用。由于土壤環境復雜、各種因子交互作用,單純以土壤重金屬含量或其有效態含量難以精準評估農用地土壤環境的風險。農用地土壤污染的風險應綜合考慮污染物及其形態含量、土壤環境因子狀況、作物類別等因素。
4 結 論
(1)滇東區域農田土壤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鎘含量由高到低依次為蔬菜地>水-旱輪作地>旱地,土壤有效態鎘含量表現為蔬菜地>水-旱輪作地>旱地;土壤砷含量由高到低依次為旱地>蔬菜地>水-旱輪作地,且旱地土壤砷含量顯著高于水-旱輪作地,有效態砷含量表現為蔬菜地>旱地>水-旱輪作地。蔬菜地土壤鎘、砷活化率均顯著高于旱地。同一農田利用類型下,土壤鎘活化率均顯著高于砷活化率。
(2)滇東區域3種農田利用方式下,土壤鎘、砷潛在生態風險等級屬輕微風險,綜合潛在生態風險指數由高到低為蔬菜地>早地>水-旱輪作地,潛在生態風險低。
(3)調查的162個農作物可食部分鎘、砷含量均較低,僅有2個樣品鎘含量超過GB 2762—2017限值,分別為茄子和辣椒。相比較而言,蔬菜地農作物可食部分的鎘含量顯著高于旱地農作物;而水-旱輪作地農作物可食部分砷含量顯著高于旱地和蔬菜地的農作物砷含量。蔬菜地農作物鎘富集系數顯著高于旱地農作物,而水-旱輪作地農作物的砷富集系數顯著高于蔬菜地和旱地。同一農田利用類型下,農作物對鎘的富集系數均顯著高于砷富集系數。
(4)盡管滇東高背景區土壤鎘、砷含量超篩選值比例高,但其有效態含量和活化率均較低,農產品可食部分鎘、砷含量超標率也低,因此滇東高背景區綜合潛在生態風險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