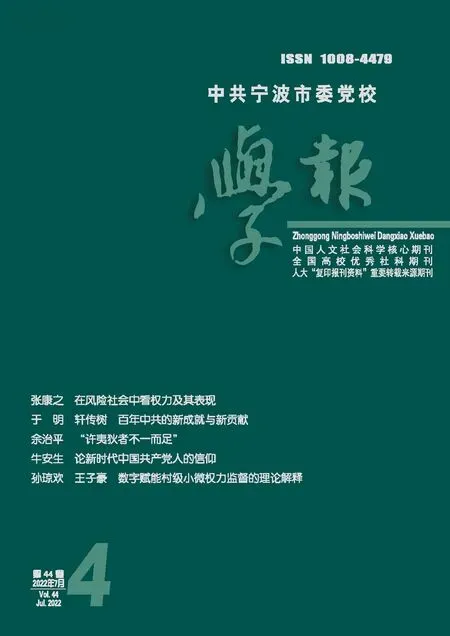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有效治理的基本策略
馬正立
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有效治理的基本策略
馬正立
(中國社會科學院 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北京 100732)
當前人類文明正在面臨著來自網絡虛擬化的重大挑戰與轉型,元宇宙作為網絡虛擬化進程的最終形態,成為人類文明演化進程的重要歷史性節點。元宇宙的可能未來所面臨的治理危機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重大問題。隨著元宇宙的形成與發展,人類未來發展的狀況將取決于預先政策引導也就是治理導向。尤其是在元宇宙的可能未來全球一體化進程不斷加深的背景下,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從而形成了一個“復合系統”。“復合系統”這一概念的提出為解決元宇宙可能面臨的一系列治理危機提供了新方法和新途徑。為更好地提升對“復合系統”治理的有效性,本文重新審視虛擬與現實這個“復合系統”的相互作用,系統分析“復合系統”轉型性變化,揭示出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的反應狀態與治理趨勢,并提出“復合系統”治理的有效戰略。在分析“復合系統”治理有效性的前提條件的基礎上,分析了“復合系統”有效治理的關鍵措施:通過提升“反應性”、“增強適應能力”、應對不確定性等一系列措施來應對治理危機,實現元宇宙可能未來的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目標。
元宇宙;“復合系統”;轉型性變化;治理戰略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中指出,“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1]。在國務院發布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2]。當下,網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技術,正在催生一個全新的數字社會形態——元宇宙(Metaverse)的產生。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歷史性節點,元宇宙在其誕生之始就獲得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在元宇宙的未來世界,人類社會將如何應對可能存在的一系列治理難題?如何加強虛擬與現實的嵌套耦合關系,避免成為完全虛擬的夢宇宙?如何使元宇宙成為現實社會的有益延伸和補充?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課題。
正如2002年拉斯金(Raskin)等人所揭示的那樣,“人類工程”已經遍及整個地球,形成了“這個驚人的‘復合系統’”[3]。在此之后,人類在一個日益復雜的系統中活動,實現這一系統可持續性發展的治理需求也日益增長。在這個“復合系統”之中,人類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治理系統不斷疊加,虛擬場景與現實社會相互作用,這決定了對“復合系統”治理的復雜性。例如,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愈演愈烈,人類開始從疫病、災難、國家治理、國家合作等層面展開對疫情的反思。人類是否有能力采取一些措施來切實維護“人類得以安全活動的空間”[4](p34)?尤其是面臨元宇宙的未來世界“復合系統”的轉型性變化趨勢,為通向人類文明發展的正確之路,更加迫切需要實施“復合系統”治理戰略。也就是面對一個非線性的、突然的、不可逆轉的變化系統,實施一系列有效的治理策略,確保元宇宙的治理堅持將虛擬場景嵌合在現實社會之中,形成共生的文明體的前置治理導向,從而確保元宇宙成為人類文明躍升的奇點。
一、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的轉型性變化
元宇宙(Metaverse)是“客觀存在的、開源的、動態演化的、以用戶需求為導向的,本質上是一個人造的虛擬平行世界”[5](p7)。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元宇宙既是平行于現實世界運行的人造空間,也是可以與現實世界交互的虛擬數字空間。在虛擬與現實的耦合系統(也就是“復合系統”)中,人類的力量變得日益重要,在許多情況下甚至變成了主導性的驅動因素[6]。元宇宙產生作用和影響的幾個重要方面涉及生產與創造、認知與經驗、身份與社群等。在元宇宙的可能未來,人類關系具有不同于此前的新情況,虛擬與現實這一耦合系統的動態變化使得“復合系統”具有若干與眾不同的特質,也就是轉型性變化趨勢:系統各組成部分的關聯度或緊密耦合關系;變化門檻、觸發機制;動態的發展過程;突發性和頻繁發生的意外狀況等。這些特質都增加了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的治理難度。對此,把握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的轉型性變化趨勢,對于理解治理危機發生的過程,以及應對可能性挑戰來實現人類文明躍升是至關重要的。
(一)“復合系統”的變化門檻與觸發機制
在元宇宙的未來世界,虛擬與現實這一“復合系統”具有非線性變化特征,會導致“臨界點”(tipping point)狀態,并伴隨“變化門檻”與“觸發機制”出現,這一狀態會使系統偏移既定運行軌道,而將系統彈射到一個完全不同的運行軌道之中[7]。臨界點是系統的一種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一個相對較小的事件或觸發因素可以突然引發系統的非線性變化。通常,這種非線性變化被視作不可逆轉的。一個系統一旦越過了無法返回的臨界點,就不再有回到原狀的可能性。一旦系統到達了變化門檻,觸發機制就會啟動并快速促成系統的轉型性變化。這一系統可能走向某種新的穩定平衡,但并不會恢復到原來狀態。也就是,這個變化過程的特點是,正向反饋回路和連鎖反應運行最終導致崩塌式的波動,將系統從一個運行軌道轉移到另一個通常完全不同的軌道。學術界關于“臨界點”狀態的研究大多涉及系統分析,并將越過臨界點與消極的或破壞性的危機聯系在一起。例如,經濟泡沫破裂、政治系統崩潰、公司破產、虛擬化陷阱等。對此,能否精確地識別系統的這種“臨界點”狀態、使可能發生的危機處于一個可控的范圍內,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學術界關于系統“臨界點”狀態的分析大多集中于生物系統或物理系統。實際上,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中這一狀態也會出現變化門檻和觸發機制。“復合系統”的變化門檻和觸發機制可以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爆炸型(explosions)、連鎖型(cascades)、失調型(inflections)。爆炸型指的是觸發事件僅以一個突然的步驟就將系統從一種狀態迅速切換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狀態。觸發事件實際上就是一個火花,當火花與極易燃燒物質接觸時,它就會點燃一次爆炸。連鎖型變化與爆炸型變化的不同之處在于,它不會在一夜之間或通過一個決定性的步驟實現狀態的變化。在連鎖型變化中,觸發事件引發正反饋過程,使系統在一段時間內從初始狀態一步步轉入某種性質不同的狀態,多米諾骨牌效應便屬于這種情況[8]。又例如,傳染型流行病可能引發一種連鎖型變化。在某些條件下,一個起初規模較小、相對局部性的疾病可以觸發一個加速過程,最后影響到世界各地的大量人口。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大約有4000萬至6000萬人因此死亡,這個事件一直是連鎖型變化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9]。此外,也有一些正向的連鎖型變化,類似現象也會發生在虛擬空間。比如科學知識的積累、蘋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大規模擴張。上述案例性質各不相同,但其發生的機制原理是一樣的。連鎖型變化是通過正反饋機制的驅動,以一系列步驟(有時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完成的。關于如何控制這個過程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辨別出啟動變化過程的觸發機制的性質,以及驅動變化從一個階段走向另一個階段的反饋過程的特性。而失調型變化則指的是關鍵變量的失衡變化,這些變量的變化將改變復合系統的動力,使系統隨著時間流逝經歷轉型式的變化。與連鎖型變化中的鏈式反應不同,當一個系統的某些關鍵元素的變化與其他元素的變化不匹配時,失調型變化就會發生。因此,失調型變化體現的是關鍵驅動因素之間的脫節,而不是正反饋過程。
事實上,以上三種“復合系統”的變化門檻和觸發機制都涉及不同的動態變化,可以從系統的動態變化過程分析入手來辨識出變化門檻和臨界點。還可以對那些可能導致非線性變化或引發這一變化的啟動過程的觸發機制進行辨識,分析一個系統究竟在什么條件下會經歷爆炸型轉變,并將這些條件與連鎖型變化以及失調型變化區分開來。上述過程涉及以下關鍵問題:哪些條件會導致“臨界點”狀態的產生?導致這種狀態發生的觸發機制的性質是什么?如何防止系統危機發生?如何促進系統良性發展?這些關鍵問題可以看作“有因果關系的復合體”(causal complexes)。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關鍵問題被視為與社會門檻和觸發機制相關聯的“社會反應”(societal responses)。比如轉型性變化的影響效果、伴隨轉型變革進程之后的調整等。
“復合系統”的變化并非總是線性和漸進的,而是存在轉型性變化。這種變化是非線性的、突然的、不可逆轉的,令人意外的是這種現象十分普遍。可以說,治理是指一種社會職能,其核心是努力引導“復合系統”走向人們所期待的正向轉型性變化,避免負向轉型性變化發生。由于人類對相關系統的脆弱性開展評估的能力有限,而且很難預測觸發事件的發生及其強度。在防止或鼓勵觸發事件發生方面,治理這項社會職能確實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解決集體行動問題(比如公共資源的枯竭),是滿足治理需求的范例。與“復合系統”的臨界點、觸發機制以及轉型性變化之后出現的情況有關的幾種治理職能是監測、評估和預警。對于“復合系統”來說,這三項治理職能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由于“復合系統”的脆弱性是很難計量的,因此觸發變革所需的時間也很難計量;另一方面,由于觸發機制中內在的不可預測性存在,因此觸發事件的發生及其強度無法預測。為避免“復合系統”的危機發生,早期預警被視為最高優先事項,同時要將更多精力集中于監測與評估。
觸發事件會推動“復合系統”跨越變化門檻,導致“復合系統”的轉型式變化發生。盡管觸發機制很難控制,但任何特定觸發事件所導致轉型式變化發生的可能性,取決于“復合系統”的脆弱性或強健性。在爆炸型變化中,“復合系統”的特點是從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突然的戲劇性轉變,因此最有效的策略是努力減少或增加相關系統的脆弱性。而在可能引發連鎖型變化或失調型變化的觸發事件初現端倪時,快速果斷的措施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因此,治理過程的關鍵是協調一致的行動,對以上進程進行監測與評估,并培養快速反應能力,以便在“復合系統”跨越臨界點時,能夠有效處理由此產生的各種問題。
(二)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的反應狀態與治理趨勢
從人類文明發展角度看,元宇宙的價值完全取決于虛擬與現實嵌合的緊密程度——嵌合的程度越強,其價值越高,反之亦然。那么,為實現元宇宙的正向價值最大化,就需要致力于從元宇宙發展之始就加強虛擬與現實的嵌合,也就是加強對虛擬與現實這一“復合系統”的有效性治理。治理的價值不只是形成有序的管理,還啟迪個體實現個人自由與群體秩序的統一。在這個過程中,理解“復合系統”的轉型性變化影響因素至關重要。“復合系統”的轉型性變化涉及兩組關鍵的影響因素。一組涉及使系統易受轉型式變化影響的條件,系統越脆弱,就越容易觸發轉型式變化;另一組是觸發機制的性質,觸發機制啟動轉型性變化進程,導致爆炸型、連鎖型和失調型變化。觸發事件影響強度越大,就越容易啟動轉型式變化。這兩組因素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當脆弱系統中發生影響強度大的觸發事件時,轉型式變化更可能發生;相反,穩定系統能夠經受住輕微的觸發事件[10]。在兩組因素強弱交織的狀況下,一個極其脆弱的系統,很容易發生爆炸型變化。能否以脆弱度的標尺在高度彈性到極度脆弱的區間內來為一些“復合系統”標定位置?能否對各種觸發事件帶來的沖擊強度進行估算?對此,制定一套用于評估社會制度脆弱性和觸發機制強度的標準,對于探討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的轉型性變化是非常有意義的。這不僅有利于更好地認識未來這一“復合系統”,還可以減少那些令人意外的危機發生的頻率。
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一旦達到轉型性變化的臨界點就無法返回原點。一旦一個系統跨過了這樣的變化門檻,隨后的變化就不可逆轉了,無法回到原先的狀態。一旦跨越了臨界點,轉型式變化并不會馬上使“復合系統”歸于穩定、均衡或平衡狀態。在“復合系統”的反應狀態中,一些動態特性會呈現出來,新系統與舊系統可能毫無相似之處,或者新系統會包含一些舊系統的特征。“復合系統”隨著時間的推移未必一定會變得穩定或具有彈性。無論如何,轉型性變化對“復合系統”中各種行為體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從積極的角度看,正向轉型性變化可以防止社會發展停滯。從消極的角度看,負向轉型性變化可能導致的系統狀態不具備合法性,容易導致社會信任度或群體認同感下降,而信任度或認同感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根據轉型性變化的性質不同,存在兩種傾向:防止“復合系統”越過導致負面轉型性變化的變化門檻;推動“復合系統”跨越變化門檻,以實現“復合系統”的正向轉型性變化。
在虛擬與現實的“復合系統”中,治理問題之所以非常難以解決,不僅與這一系統的自身規模相關,還與治理的“路徑依賴”有關,系統會沿著事先確定的路徑發展,而不受外部力量的影響。“復合系統”有效治理的一個主要功能是設法回避或克服“路徑依賴”的束縛。“路徑依賴”本身并不一定產生負面影響,但在某些情況下,“路徑依賴”可能使系統很難適應不斷變化的復雜環境。這也與“復合系統”的非線性變化特質所導致的面臨復雜環境的不確定性息息相關。一旦系統的內部變化過程越過了“變化門檻”或“臨界點”,系統運行軌跡就會發生偏移,這不僅會增加治理成本,更會帶來難以預期的治理難題。
隨著元宇宙的可能未來變得更加復雜,治理“復合系統”所面臨的挑戰也迅速增多。為實現對“復合系統”的有效治理,需要特別關注“復合系統”治理這一課題,進而創建并實施具有創新特征的治理方式,這與以往所熟知的治理方式是存在差異的。以往治理過程更多考慮規則制定與監管機制,重點關注與規則實施有關的問題,以及制定共同遵約性程序等。這并不意味著制定規則、頒布規定以及完善機制等規制性方法不再起作用,而是意味著需要更新“復合系統”治理的“工具箱”,添加一些新的方法來提升“復合系統”治理的有效性。“元宇宙將是一個具有三維深度的開放的數字空間體系”[11],這一空間體系最終能否繁榮取決于無數主體的參與和共建。“元宇宙的價值是讓人類的絕大多數活動能夠在元宇宙中復現,從而形成更為便捷的數字孿生體系。”[11]這就要求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能夠使無數主體參與其中共同治理。特別是在國際社會中,在沒有一個“復合系統”治理層面的共同體來承擔責任的情況下,往往面臨復雜的問題,即在面對“復合系統”非線性變化情況時,如何促進應對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的共同行動。這既需要國家的力量給予引導和治理,也需要全人類社會共同的覺醒和協作。為此,要實施“復合系統”治理戰略來設計一套獨特策略,引導共同行動。
二、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有效治理的前提條件
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治理如同大多數其他系統一樣,面臨集體行動的困境。正如謝林(Schelling)所概括的:當微觀層面的個體動因導致本可以避免的宏觀層面的集體行為后果發生,即產生了對大家都不利的結果時,問題就出現了[12](p67)。諸如“公地悲劇”[13](p34)與“搭便車”[14]系統中行動者有很強大的動因去忽視集體行動的需求,這可能歸因于行動者不愿意限制對公共資源的利用,或者拒絕承擔非排他性公共產品供給的成本。不僅小規模系統會面臨這種集體行動困境,“復合系統”亦如此。在元宇宙的可能未來,面臨虛擬與現實耦合的這一大規模系統,僅僅依靠一個行為體或者一個由多國組成的聯盟采取措施是遠遠不夠的,需要系統中所有行為體組成“復合系統”來協調一致并持久不懈地發揮作用。“復合系統”治理有效性的前提條件是全球治理共同目標的設定。
(一)理解共同目標設定的前提基礎
共同目標設定作為“復合系統”有效治理的關鍵條件,是構建有效的指導性治理機制的基礎。作為回應“復合系統”治理需求的一種策略,共同目標設定是應對挑戰的一種手段。共同目標設定通過以下四種方式指導集體行動:相互在競爭的目標之間分配注意力和稀缺資源,確定優先事項;激勵被分配到工作的人努力實現與優先事項有關的目標;確定目標,并提供用于跟蹤實現這些目標的進展的標準或基準;打擊短期欲望和沖動的傾向,這些傾向會分散分配給目標達標工作的注意力或資源。共同目標設定不同于規則制定與監管機制,規則制定與監管機制旨在通過闡明規定性規則(和實施規則)來指導關鍵參與者的行為。共同目標設定則是闡明要求和禁令,并制定旨在促使參與者依照要求調整其行為的遵約機制。
雖然共同目標設定的細節會根據情境不同而變化,但所有作為治理戰略的共同目標設定都擁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共同目標設定需要擁有明確優先事項的能力,并對這些明確的目標進行清晰表述。共同目標設定的要點就是選出有限數目(或者僅是一個)的目標,并在分配稀缺資源方面優先考慮它們。二是目標設定需要設計明確的指標,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根據這些指標追蹤取得的進展。跟蹤機制不僅在衡量目標實現的進展方面起關鍵作用,而且也是一種有效的手段,可以敦促所有參與方加倍努力,在預定截止日期前實現目標。
目標設定和規則制定可以且經常作為不同的應對治理需求的策略獨立運作。在特定情況下,它們可能是互補的。作為“復合系統”治理策略的共同目標設定,與規則制定的前提不同。規則制定的前提是制定行為規則(例如要求和禁令),并將關注點集中在遵守和執行的問題上,而共同目標設定的前提是愿望的表達,并關注在支持者中激發熱情,最大限度地發揮為實現共同目標所需的作用。此外,規則制定的目的是無限期地保持不變,它們往往會產生僵化的官僚機構,致力于執行規則而無視不斷變化的環境。反之,共同目標設定則通常以發起旨在特定的時間范圍內實現目標的運動為特征,規則制定則明確預期的行為將無限期地保持不變。在面對非線性的、突然的和令人意外的變化時,要應對不確定性、增強適應能力,需要促進目標設定和規則制定相結合。目標設定可以提供激勵,為參與者提供行動的指導原則。規則制定可以提供行動方案(要求和禁令),明確行為者如何行動才能在實現目標方面取得進展。沒有規則的共同目標容易退化成模糊的愿望,參與者原則上接受共同目標,但很難清楚在實踐中如何實現目標。沒有共同目標的規則容易退化為繁瑣的形式主義,參與者很難了解這些規則是實現共同目標所需的。為此,需要將共同目標設定與規則制定結合起來運用。
(二)破解共同目標實現的可能阻礙
在國際社會中實現共同目標設定這一策略仍面臨諸多阻礙。一是設定目標階段的阻礙。共同目標設定需要集體努力,涉及相對較多的利益參與者(比如國際社會中的各個國家)。參與者之間建立共識時會面臨如下阻礙:最終確定的目標太多,無法確定優先事項和分配稀缺資源;所選擇的目標以模糊的術語來界定,這些目標難以實施和監測;“一攬子方案”中的個別目標會是不兼容的,甚至是矛盾的。
二是跟蹤進度過程的阻礙。許多共同目標的實現程度是以難以短期衡量的,這導致跟蹤進度的難度增加。例如,在跟蹤改善人類福祉取得的進展時,有可能存在如下阻礙:過度強調操作性指標(比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估一些難以測量但非常關鍵的指標(比如人類文明發展),或在跟蹤實現目標過程中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或意見不一致性。
三是行動激勵機制的阻礙。促進目標實現的相關激勵機制可能不足以指導國際層面的集體行動,尤其是參與者在經濟、政治、社會領域面臨持續壓力或資源短缺的情況下,目標實現變得更加困難。可以說,作為“復合系統”治理的共同目標設定的有效性,取決于該策略是被用作解決治理問題的獨立工具,還是作為對其他工具的補充。
(三)把握共同目標實現的決定因素
共同目標設定并不是在所有條件下都發揮有效作用。在使用這一策略時,要明確促進這一策略發揮有效作用的決定因素。
一是危機性質。對于某些危機(比如元宇宙虛擬經濟的安全性、透明性、波動性等),實現一個特定目標某種程度可以解決這個危機。而對于連續性危機(比如人類欲望的虛擬化陷阱),共同目標設定可能會面臨復雜過程,因為無法對目標實現程度作出明確的評估。危機所涉及的規模和范圍也存在不同。總之,共同目標設定有效性取決于實現目標的程序與危機性質相匹配的程度。
二是參與者的行動邏輯。共同目標設定有效性還取決于參與者的行為是基于“結果性邏輯”或“適當性邏輯”的程度[15]。概括地講,在“結果性邏輯”占主導的情況下,策略需要在收益和成本方面對行為者有吸引力。這是因為對于參與者來說,實現共同目標在某些情況下需要以犧牲個體目標為代價。反之,在“適當性邏輯”占主導的情況下,共同目標設定與規則制定相結合可能是有效的。例如,在為共同利益作貢獻被主流文化所認同的情況下,實現共同目標可能比較容易。
三是場景特征。共同目標實現通常受到場景特征的影響,比如所涉及的參與者數量、參與者通過共同利益或文化親和力團結一起的程度、為實現共同目標作出貢獻的程度,以及可能有助于解決問題的技術創新的前景等。此外,還涉及社會、文化和歷史遺留問題。例如,如果參與者直接存在基于長期合作解決共同問題形成的信任,共同目標設定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常規方法。反之,長期存在的敵意會滋生不信任,合作則往往容易產生誤解,在這種情形下,共同目標實現的程度會大大降低。
(四)促進共同目標實現的有效方式
無論面對何種情況,簡單地闡明共同目標,并期望參與者作出協調一致的行動來實現這些目標,是遠遠不夠的。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治理策略的共同目標設定過程,需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集中力量,激勵參與者為實現共同目標作出持續努力。
一是為參與者提供履行承諾的強有力的激勵措施,強化參與者對共同目標的集體認同,來確保參與者的集體行為。為了確保承諾真實可信,參與者可能同意在未能履行的情況下承擔成本損失。此外,對于那些很難用收益成本衡量的目標說,為避免“搭便車”的情況發生,可以采用涉及榮譽、道德義務、群體團結感等因素的激勵機制。
二是為跟蹤機制制定明確的時間表。除了制定衡量目標實現進度的指標之外,制定明確的時間表通常是有效的,這樣可以通過時間表來評估目標實現進度,將總體目標細分,并設立節點,在必要時進行中期修正。特別是在總體目標實現周期較長的情況下,明確臨時目標的時間表是必要的。也就是,將實現臨時目標作為追求更高層次和更高價值目標的必要條件。在此基礎上,設計有效的程序來跟蹤目標實現進度。例如,在制定和實施人類文明發展目標時,建設一套有效的程序規劃,以配合每一個階段性目標的實現。
三是提升參與者協調一致行動的動力。由于參與者的行為動機不同,設定共同目標往往是有效的。在此情況下,應明確參與者的行動邏輯,對“結果性邏輯”和“適當性邏輯”進行區分。特別是在共同目標涉及集體行動的情況下,對于參與者來說,實現共同目標將有助于建立一個利于所有參與者的環境,要鼓勵參與者超越狹隘的自我利益,激勵所有參與者以促進共同利益的方式采取集體行動。
三、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有效治理的關鍵措施
人類所依賴的治理方法越來越有可能與需要解決的問題的性質不相配適。因此,實現人類文明發展目標,就需要滿足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中出現的治理需求[16],以提升“反應性”、“增強適應能力”、應對不確定性等一系列保障措施來應對治理危機,避免人類進化陷入漫長的虛擬化陷阱。
(一)提升“反應性”
“反應性”(reactive)一詞特指一種場景,在這一場景中,人的行動對相關系統的動態變化起著核心作用,其關鍵是對人類活動范疇的期望和預期反應。任何系統都存在“反應性”,非人類也有能力去感知變化的場景,并采取旨在應對預期變化(而不是觀察到的變化)的行動。然而,在討論對高度動態的“復合系統”的治理時,所涉及重點則是人類識別趨勢的能力、預測即將發生的變化的能力,以及在所涉及的變化實際發生之前或失去控制之前以恰當方式作出反應的能力。
從過去的情況來看,人類有時無法判斷趨勢,無法預見對他們有深遠影響的突然的和非線性的變化。在20世紀80年代,很少有學者預見到了西北大西洋鱈魚種群的衰退,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實際崩潰就發生了。大多數學者都對1991年末蘇聯急速解體并很快走向最終崩潰感到驚訝。即使人類認識到未來的變化并根據他們的預期采取行動,非線性變化的負面影響發生的可能性還是會增加。例如,銀行擠兌的事例,大量個體參與者的恐慌行為加速了人們普遍擔心事件的發生。
在“反應性”系統中,可以根據當前“復合系統”的發展趨勢來預期未來發展的趨勢,從而觸發導致預期發生的行為反應。“反應性”還可以成為在這種環境中努力建立有效治理系統的一個要素。關鍵在于設計一個負反饋機制,以便在“復合系統”的發展趨勢跨越臨界點之前轉換或改變整個“復合系統”的運行軌跡。因為一旦超過這個臨界點,非線性變化就不可避免了。例如,使用貨幣政策來防止經濟下滑引發衰退或蕭條(比如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下調利率的措施)。
可以說,提升“反應性”并將其作為避免“復合系統”內危機發生的一種手段,是非常有意義的。例如,我們不知道地球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達到何種數值就會導致地球氣候系統越過一個臨界點,并使地球氣候系統發生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轉的重大變化。但顯而易見的是,將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限制在百萬分之450至百萬分之500是有可能的,也有許多科學家認為,將目標定在百萬分之350會更加保險[17],這將足以避免啟動觸發機制。
如以上案例所示,三個關鍵條件決定著利用“反應性”來解決與人和環境互動相關的大規模問題是否成功。一是時間問題。人類認識到地球氣候系統發生不可逆轉變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隨著人類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更加深入,人類可以作出有效反應的能力也將會增強。那么,人類應該從何時開始對其進行干預?二是集體行動問題。我們如何才能確保應對地球氣候變化的措施是協調一致的行動?我們需要采取全球行動,但“搭便車”心理依然存在。三是機會成本問題,以及避免因采取行動而產生意外的、潛在的嚴重副作用。
“反應性”是“復合系統”的一個獨特特征,提升“反應性”是有效治理的關鍵。在一個充滿非線性的、突然的或不可逆轉的變化的廣泛的“復合系統”中,提升“反應性”可以提升人類應對危機的靈敏性和適應性,讓人類提前對危機的發生進行預測并作出有效反應,而不是等到危機降臨后再開始行動。因此,要提升快速反應能力以應付突發事件的負面影響。
(二)增強適應能力
不難發現,要應對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所具有的轉型性變化(非線性的、突然的、不可逆轉的和令人意外的),就需要具備發現和正確處理這種變化的能力,同時具備對觸發機制進行調整所需的靈活性,以將預期的變化后果考慮在內。因此,聚焦監測、早期預警和適應性管理是增強適應能力的關鍵環節。
首先,有效監測是至關重要的。越容易發生轉型性變化的“復合系統”,對高質量監測的需求就越大。聚焦監測過程,不僅需要對所涉“復合系統”的性質有透徹的認識,而且需要制定一套能夠很好地跟蹤該系統運轉的指標體系,這些指標應當被普遍認為是可信且合法的。在“復合系統”的觸發機制中,負反饋機制可以觸發反周期過程,正反饋機制則可能導致失控過程。因此,正反饋機制比負反饋機制需要更多的監測,包含數個維度的指數體系(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會更加有用。每年或甚至每隔多年所作的檢測可能足以追蹤同質系統,但對于具有高度多樣性的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來說是遠遠不夠的。在元宇宙的未來世界,設計用來預測突如其來變化的監測系統,將比監測緩慢變化的系統需要更頻繁的觀測,盡管這些緩慢變化可能是非線性的。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精密的、持續的實時監測。此外,監測范圍也是值得關注的。例如,金融系統是一個單一的、相互結合的整體,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監測。
其次,需要有效的預警系統,以此注意“復合系統”的變化門檻和觸發機制。從監測的角度來看,預警系統的價值在于可以預先確定導致發生非線性變化的條件,提供盡可能多的關于接近變化門檻和觸發機制的預警。當“復合系統”內發生線性的、漸進式的、可逆的變化時,便可以追蹤它們的軌跡。但是,沒有必要在早期預警方面進行大量投資。在實際情況中,即使是一些非線性變化也可能以慢動作發生,這給那些可能受到相關系統狀態變化影響的人足夠的時間去注意這些變化,并采取行動消除或至少減輕非線性變化對人類福祉的負面影響。但是在涉及突然變化的情況下,早期預警是非常重要的。監測過程應遵循如下準則:在所有情況下都監測系統的變化,但僅在這種變化有關事件可能對人類福祉產生重大影響的情況下才會啟動預警。
最后,需要有效的適應性管理。面對“復合系統”的變化,必須具有靈敏的調節能力,從而確保在三個不同的層級采取適應性管理。第一個層級是操作或微觀層面,管理者可以作出調整,不需要改變現行的治理模式,也不需要管理機構的批準。在第二層級也就是中觀層級,需要調整現行的治理模式,通常還涉及采用新的治理模式,但不改變現行治理模式的性質。在第三個層級也就是宏觀層級,就出現了為滿足日益增長的治理需要而改變現行治理模式及其性質的情況。針對特定的領域嘗試使用特定的政策工具是有意義的。
在面對“復合系統”的非線性的、突然的和不可逆轉的變化時,每一層級都需要有足夠的靈活性,以便作出調整,甚至改變現行規則。然而,就治理的有效性而言,這可能存在一種效應遞減。一方面,任何隨著問題性質或主體行為的每一個細微變化而改變的規則,都不能一勞永逸有效地調節“復合系統”中虛擬與現實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那些很難或甚至不可能根據不斷變化的環境進行調整的系統將變得脆弱,并因為虛擬世界的變化而最終崩潰。
適應性管理過程可以采取兩種調整措施:非正式的調整措施與正式的調整措施。非正式措施的優點是易于采用、快速實施,而且調整的爭議性更小。正式的或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措施則具有更大的規范性力量,可以對主體施加更大的壓力,迫使其遵守機制的要求或調整其行為,以滿足新的規則體系的要求。在變化是非線性的、特別是突然發生的情況下,依賴非正式的調整措施往往是必要的。這是因為正式的調整措施(比如相關法律制度的修改完善)涉及復雜的審議過程,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能倉促進行的。
(三)應對不確定性
在對元宇宙時代“復合系統”進行治理時,目前還無法避免不確定性的存在。不確定性涉及在“復合系統”內外部出現的未知因素。隨著我們不斷走進虛擬世界,這種不確定性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復合系統”中,治理機制必須能夠在或多或少存在嚴重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有效運作。可用于應對這些不確定性的策略包括采取預防措施,其中有保險計劃、開發探索式方法或經驗法則,以及進行有針對性的研究。
應對不確定性的有效方式是采取預防措施。在“復合系統”內的一些領域,比如在國家安全領域,在處理國家安全問題上,預防措施通常基于對某種形式的最壞場景的分析,對潛在對手的能力和意圖都作了最壞假設,然后根據這一假設撥出數千億美元用于每年的國防開支。依循這一邏輯,對虛擬世界變化可能產生的危機的分析越來越具有合理可信性。在這種情況下,一種預防性做法是側重于把握“元宇宙”這一虛擬世界和現實的邊界。從保險事業的發展可以看出人類應對不確定性的諸多嘗試。比如人壽保險的目的是避免低概率但災難性的事件造成的破壞。盡管這一策略在某些情況下是有效的,但對于虛擬世界變化來說,這一策略的局限性很明顯。因為用精確計算的方法來處理人類欲望這樣的危機幾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元宇宙的未來世界,與新經濟形態發展伴隨的潛在風險要予以防范,如通證的價格波動可能會讓創作者、消費者等主體的權益受到侵害;元宇宙的虛擬空間可能會滋生違法、違背公序良俗的行為;元宇宙可能被資本控制形成壟斷等。為此,可利用元宇宙與通證經濟的組合工具特點進行“法律+技術”規制。比如利用區塊鏈技術驗證數字身份與數字財產,審查參與者身份與活動內容,監管經營者壟斷行為并制定國家標準等[18]。應對“復合系統”中的不確定性的有效方式還涉及各式各樣的探索式方法或者遵循經驗法則[19]。探索式方法在涉及不確定因素的場景中被廣泛使用,特別是那些涉及公共政策議程的情況。面對許多問題(比如國防、宏觀經濟政策、醫療保健、公共教育)存在著測量上的困難,應對這種情況的有效方法之一是遵循經驗法則。經驗法則可能覆蓋從對主體遵守管制措施程度的預期到對實現各種目標的成本推測的各種情況。
在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場景進行預測時,情景設想也有作用。情景設想是對社會復合系統中可能出現的未來發展狀況進行的故事性敘述。它們不是對當前趨勢的簡單預測,也不具有預測價值。情景設想是有用的,它鼓勵分析家思考與通常情景有顯著差異的場景,并組織對這些場景日益相關的各種選項進行評估。有效的情景設想方案能引導關注一些具有可信性但與當前趨勢存在很大差異的場景,這可以確保決策者考慮可能出現的急劇的非線性變化趨勢。
(四)完善相關保障措施
在實現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歸納出一些有效的保障措施來應對“復合系統”可能發生的危機是可行的。元宇宙不是法外之地,在元宇宙出現的違法犯罪行為必須承擔與現實世界相應的法律責任。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保障措施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密切監測“復合系統”內互動行為,并完善提升調節能力以適應不斷變化情況的程序;充分利用各種形式的模擬和情景設想,以提高對“復合系統”的動態變化的預警;建造防火墻,在體制安排中儲備應急機制和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系統崩潰的可能性。
首先,密切監測“復合系統”的狀態和治理績效,并制定出一套程序便于進行調整或中期修正,以解決二者配適度的問題。投入所需資源來持續不斷地監測“復合系統”的狀態。一旦突然和潛在的破壞性變化發生,對監測的需求就會特別迫切,未能持續地開展監測的成本可能是極高的。“復合系統”中發生的非線性的、突然的、不可逆轉的危機,往往是可以避免的(例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應對以上危機失敗的原因在于未能監測到“復合系統”的變化趨勢,以及未能及時對現行治理模式進行重大改革。此外,即使監測到危機,路徑依賴的存在往往也會妨礙采取及時和適當的應對措施。因此,應致力于持續監測,制定相關程序,以便能夠靈敏地應對不斷變化的情況,確保“復合系統”不至于陷入那些拖延措施的復雜局面之中。
其次,充分利用各種治理方式,通過運用模擬、情景開發和其他管理程序,確保能夠深入了解復雜且不確定的“復合系統”的動態變化和突發性特質。模擬并不需要對“復合系統”作出變化趨勢分析,將大量時間和資源用于模擬,可以深入了解“復合系統”的變化門檻和觸發機制。在此基礎之上,可以運用情景開發來預測“復合系統”中可能出現的復雜狀況,隨后在就具體政策工具的使用作出決定時應考慮這些復雜狀況。
最后,一旦調適能力受到限制,治理機制安排中應設置防火墻或預留應急機制和措施,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系統層面突然崩潰的可能性。減輕發生非線性、突然的、不可逆轉和令人意外的變化之危險的方法之一就是將治理機制安排劃分成幾個獨立的部分,避免導致系統崩潰的連鎖反應。當然,這種策略會帶來很高的治理成本。正如關于多層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文獻所闡明的那樣,在這種機制安排下,協調很難實現,而且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即將某些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置于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之上。至少以這種方式來應對非線性、突然、不可逆轉和令人意外的變化將產生巨大的治理成本。這表明,當可能發生的變化是大規模的且通過關鍵的變化門檻的概率很高或未知時,這種解決方案將更有效。
①結果性邏輯是指行為選擇往往遵循結果性,即體現結果推動,根據某種行為所能帶來的結果來選擇最佳對策,利益最大化成為行為選擇的內在邏輯基礎。
②適當性邏輯是指行為選擇不是基于偏好、利益或效率等一元邏輯,而是在必要條件下的規則約束所衍生出的合價值與合正義的內在邏輯基礎。
[1] 習近平. 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J]. 求是, 2022(2).
[2] 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國發〔2021〕29號)[EB/OL]. 中國政府網, http: //www. gov. cn/zhengce/zhengceku/ 2022-01/12/content_5667817. htm, 2021-12-12.
[3] Paul J. Crutzen. Geology of Mankind——The Anthropocene[J]. Nature, 2002(415).
[4] 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M]. New York: Harper, 1968.
[5] [韓]崔享旭. 元宇宙指南:虛擬世界新機遇[M]. 宋茜, 朱宣, 闞梓文, 譯. 湖南: 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2.
[6] Peter M. Vitousek, et al. Human Domination of the Earth's Ecosystems[J]. Science, 1997(277).
[7] Danny Meadows-Klue. 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J]. Interactive Marketing, 2000, 5(4).
[8] 楊雪冬. 全球化、風險社會與復合治理[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2004(4).
[9] Nicholas P. Restifo. 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J]. Nature Medicine, 2000.
[10] Folke C. , et aL. Regime Shifts, Resilience, and Biodiversity in Ecosystem Management[J]. American Review of Ecology, Evolution and Systematic, 2004(35).
[11] 何哲. 虛擬化與元宇宙:人類文明演化的奇點與治理[J]. 電子政務, 2022(1).
[12] Thomas C. Schelling.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bavior[M]. New Haven: W. W. Norton, 1978.
[13]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14]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162).
[15] James G. March, Johan P. Olsen.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8(52).
[16] Robert B. Richardson. Book Review: Pursuing Sustainability: A Guide to the Science and Practic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7, 1(131).
[17] Will Steffen, et al. Planetary Boundari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on a Changing Planet[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5, 9(2).
[18] 李晶. 元宇宙中通證經濟發展的潛在風險與規制對策[J]. 電子政務, 2022(1).
[19] Amos Tversky,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J]. Science, 1974(185).
2022-02-17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時代我國基層干部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0CDJ010)階段性成果
馬正立(1989-),女,黑龍江哈爾濱人,法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執政黨建設理論、公共管理與領導科學。
F490
A
1008-4479(2022)04-0035-11
責任編輯 杜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