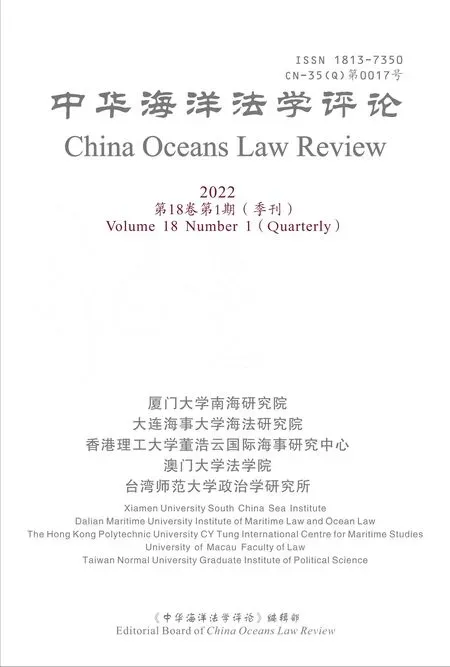海洋公共秩序基本原理研究
蔡從燕
一、導 言
就國際公法而言,公共秩序其實并不是什么新問題。如所周知,自然法觀念在18 世紀之前的近代國際法,尤其在15 世紀的國際法萌芽時期占據主導地位。從邏輯上說,公共秩序問題必然構成自然法觀念主導下的近代國際法之重要組成部分。考察國際法實踐史和思想史不難發現,諸如強行法之類的被人們公認構成公共秩序的現當代國際法律制度其實源于15、16 或17 世紀。比如,強行法就是源于瓦特爾愛默里赫·德·瓦特爾(Emerich de Vattel)的“必要的法”理論。不過,隨著19 世紀后實證法觀念在國際法理論與實踐中占據主導地位,人們較少討論國際公法中的公共秩序問題,而對于國際私法中的公共秩序問題的討論明顯增多。
20 世紀上半世紀連續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尤其在“一戰”結束后不到20 年再次爆發規模更大、損失更慘重的世界大戰使得自然法觀念再次被引入國際法理論與實踐,公共秩序問題再次受到關注。國際法理論方面,出現了以赫希·勞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為代表的新自然國際法學派。國際法實踐方面,諸如強行法等國際法概念、規則與制度相繼出現。不過,半個世紀的“冷戰”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國際公共秩序的理論研究與法律實踐。直到進入20 世紀90 年代,隨著傳統的東西方對抗的結束、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層出不窮,公共秩序的建立,尤其維護逐步成為國際法理論與實踐中一個日益重要的議題。
對于公共秩序的含義,在“未成年人監護公約案”中,時任國際法院法官的莫雷諾·昆塔納(Moreno Quintana)在其提交的單獨意見中做了比較詳細的闡述。他認為:
國際公共秩序是在國際公法范圍內適用的,它規定了諸如國際法的一般原則以及國家的基本權利之類的某些原則,尊重這些原則對于構成國際共同體的政治單位之間的法律上的共處是至關重要的。16 世紀時弗蘭西斯科·德·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ctoria)所指的國際社會、17 世紀時弗蘭西斯科·蘇茲(Francisco Suárez)所指的社會——它關系到一個普遍共同體內各完美共同體之間的共存、18 世紀時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所描繪的由所有國家在默示協定基礎上構成的世界社會(Civitas Maximas),以及19 世紀時由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界定的由國家組成并且受到要履行某些義務拘束的法律共同體都必然建立在這些原則與權利基礎之上。這些原則——因為它們的數量很少,因此我們都熟悉——具有強行性特征,是普遍適用的。一方面是海洋自由、打擊海盜、國家的國際持續性、管轄豁免,以及戰爭規則。另一面是條約神圣、國家獨立與法律上的平等。1Separate Opinion of Judge Moreno Quintana,ICJ Reports 1958,p.106-107.原 文 為:“International order public operates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system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when it lays down certain principles such a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e law of nations and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States,respect for which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legal coexistence of the political units which make up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The natural society of nations,to which Francisco de Vitoria looked forward,in the 16th century,the society which involved the CO-existence of perfect communities within a universal community as propounded by Francisco Suarez in the following century,the Civitas Maxima described by Christian Wolff in the 18th century,as constituted by al1 States on the basis of a tacit covenant,and the legal community of States bound by the performance of certain duties,as defined in the last century by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are al1 necessarily based on these principles and these rights.These principles– which we are al1 quite familiar with them because they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se rights,too,have a peremptory character and a universal scope.On the one hand,the freedom of the seas,the repression of piracy,the international continuity of the State,the immunity of jurisdiction and the rules governing warfare;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violability of treaties,the independence and legal equality of States.”
上述單獨意見表明:第一,公共秩序是一個法律概念,它包含著具體的權利義務內容;第二,海洋公共秩序是國際公共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根據下文的討論,2參見本文第三部分之(二)。純粹從實證法角度來描述包括海洋公共秩序在內的國際公共秩序是不充分的。進一步從社會或政治角度理解公共秩序有助于理解國際公共秩序的生成機理、運作現狀,進而確定其發展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西方國際法學者在討論國際公共秩序——包括海洋公共秩序——時往往使用“公共物”(global commons)或“公共物品”(public goods)概念。“公共物”原是經濟學中的概念,后來被引入國際關系研究,進而被一些國際法學者所使用。3關于全球公共物的代表性文獻,參見《歐洲國際法雜志》近期以“全球公共物與法律秩序的多元主義”為題刊發的專欄論文,如Fabrizio Cafaggi &David D.Caron,Global Public Goods amidst a Plurality of Legal Orders:A Symposium,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3,p.643-649 (2012);Daniel Bodansky,What’s in a Concept?Global Public Goods,International Law,and Legitimac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3,p.651-668 (2012);Gregory Shaffer,International Law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 a Legal Pluralist World,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3,p.669-693 (2012);Fabrizio Cafaggi,Transnational Private Regul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Private “Bad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3,p.695-718 (2012);Francesco Francioni,Public and Priv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Global Cultural Good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3,p.719-730 (2012);Petros C.Mavroidis,Free Lunches? WTO as Public Good,and the WTO’s View of Public Good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3,p.731-742 (2012);Elisa Morgera,Bilateralism at the Service of Community Interests? Non-Judicial Enforcement of Global Public Good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Law,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3,p.743-767 (2012);André Nollkaemper,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The Intersection of Substance and Procedur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3:3,p.769-791 (2012).又見Scott Jasper,Securing Freedom in the Global Common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這些國際法學者舍“公共秩序”而取“公共物”表明他們無意僵化地從實證法角度來理解包括海洋公共秩序在內的國際法上的公共秩序。筆者贊成這一術語選擇蘊含著的靈活性,但在本文中仍然使用“公共秩序”而非“公共物”。原因在于,筆者認為使用法律性的“公共秩序”表述可以揭示當前的海洋秩序與以往的海洋秩序之間的最大差別,并且可以揭示筆者認為的中國在應對海洋公共秩序問題面臨的深層次挑戰。
本文旨在從構成要素(第二部分)、觀念基礎(第三部分)、行為體結構(第四部分)、治理模式(第五部分)、法律形態(第六部分)以及規制方法(第七部分)為理解海洋公共秩序確立一種分析框架,揭示海洋公共秩序的復雜性,據此為我國的海洋事務提供理論支持。
二、海洋公共秩序的構成要素
就一般法理而言,法律追求實現的基本價值有二,即自由與安全(秩序)。誠然,不能認為自由與安全相互排斥或相對對立,但自由與安全之間客觀上存在著緊張關系。從根本上說,法律都應當追求自由與安全之間的平衡。盡管如此,在不同的情況下,自由與安全的觀念基礎、規制模式、行為體結構可能是不同的,因而達到平衡的過程可能是不同的。就國內法經驗而言,在私法范圍內,規范自由與安全遵循的基本模式是私法自治,據此由當事人自行約定有關交易自由與安全的安排,公權力機構原則上不應參與這些安排的約定過程。與此不同,在公法范圍內,公權力不僅有權力,而且有義務更加積極地制定并確保相關法律安排的實現。
(一)自由
從羅馬時期以來,自由就是海洋公共秩序的首要構成要素,對于維護國際交往至關重要。但應注意的是,自由的可欲性(desirability)是有條件的,它取決于自由的內部關系(不同自由之間的關系)與外部關系(自由與其它價值追求之間的關系)是否被準確地理解與善意地實踐。4關于海洋公共秩序的觀念基礎,參見本文第三部分。換言之,海洋自由訴求既可能是正當的,也可能是不正當的。
關于海洋自由,可以從主體與內容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從主體方面看,在古羅馬人看來,海洋和空氣都屬于“共有物”,而非“無主物”——后者可以適用“先到先得”原則,因而海洋對“任何人開放”。不過,由于羅馬帝國在地中海地區睥睨一切,其他歐洲小國在利用海洋方面根本無法與羅馬帝國相提并論,因此羅馬帝國所說的海洋自由“實際上服務于羅馬帝國的霸權主張”。5參見張小奕:《試論航行自由的歷史演進》,載《國際法研究》2014 年第4 期,第23 頁。直言之,這一時期的海洋自由其實是羅馬帝國一國的海洋自由,我們不妨稱之為“壟斷自由”。在經歷15、16 世紀的海洋割據運動后,6毋庸置疑,代表性的海洋割據行動有如1493 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發布敕令以及1494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締結條約完成對海洋的瓜分,據此,葡萄牙在印度洋、南大西洋,西班牙在西大西洋、墨西哥灣和太平洋擁有專屬航行權,有權對外國船只征收通行費,限制或禁止外國船只通行,以及限制或禁止外國漁船捕魚。隨著以17 世紀的荷蘭和18 世紀的英國為代表的新興海洋大國的崛起,尤其18 世紀始于歐洲并擴大到美國的工業革命,依賴于海洋運輸的國際貿易對于以英國為代表的少數國家——包括曾經因“閉海論”備受詬病的英國——逐步支持海洋自由。然而,直至20 世紀中期,廣大的亞非拉沿海國家——更遑論內陸國家——不僅遠不具備諸如英國那樣的利用海洋的能力,加之落后的經濟實力與封閉的經濟觀念使其不具備利用海洋的強烈的意愿或意識。直言之,這一時期的海洋自由其實是英國等少數國家的海洋自由,我們不妨稱之為“寡頭自由”。
20 世紀中期以來,一大批亞非拉新興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實現獨立或恢復獨立,并且日益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加上海洋觀念的更新,使它們逐步意識到海洋的重要性。誠然,發展中國家中的沿海國家是“二戰”后出現的新的“海洋圈地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但它們并沒有否定——事實上也不可能否定海洋自由,因為這與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趨勢以及它們追求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的主觀追求是相沖突的。由于發展中國家的“海洋圈地運動”客觀上損害了海洋自由,促使英國、美國等傳統海洋大國強化了對海洋自由的支持,這種支持固然是這些傳統海洋大國基于自身的利益計算,但客觀上有助于海洋自由的維護,盡管這一運動的始作俑者其實是美國,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只是追隨者而已。71945 年,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了第2668 號總統公告(即“杜魯門宣言”),據此設立了所謂的專屬經濟區。該公告指出:“美國有權保護美國海岸特定區域內的公海上的漁業資源;為養護與管理此類漁業資源,美國將在領海之外的鄰接公海內設立養護區,并行使養護與管理的權利”。受此影響,眾多沿海國家紛紛設立專屬經濟區。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中的內陸國家的海洋自由觀念也逐步萌生或強化,這些國家對于海洋自由的訴求經由《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部分“內陸國出入海洋的權利和過境自由”等獲得歷史性的確認。8應當強調的是,內陸國享有的海洋自由顯然不限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部分所說的“出入海洋的權利和過境自由”。這一權利既是內陸國之海洋自由權利的實體組成部分,也是這些國家行使其他海洋自由權利的手段。據此,第125 條第1 款規定:“為行使本公約規定的各項權利,包括行使與公海自由和人類共同繼承財產有關的權利的目的,內陸國應有權出入海洋。為此目的,內陸國應享有利用一切運輸工具通過過境國領土的過境自由。”直言之,20 世紀中期以來,尤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以來的海洋自由是所有國家的海洋自由,我們不妨稱之為“普遍自由”。
從“壟斷自由”到“寡頭自由”再到“普遍自由”對于海洋公共秩序的影響是豐富的。表面上看,它表明海洋自由權利主體規模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它對于海洋公共秩序的觀念基礎、治理模式、法律形態、規制方法等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而對于海洋公共秩序產生了整體性的重塑作用。
從內容上看,直到20 世紀中期,海洋只分為領海和公海兩個區域。領海被公認為屬于沿海國的領土,在這個海域內只存在很有限的公共秩序問題,即無害通過制度。直言之,海洋自由根本上等同于公海自由。不過,直到20 世紀中期,人們并沒有特別關注公海自由的確切含義,其原因不難理解:首先,在“壟斷自由”或“寡頭自由”時期,海洋足夠廣闊、豐富到允許那些壟斷國家或寡頭國家可以以其愜意的方式利用海洋;其次,受制于全球化的整體水平,壟斷國家或寡頭國家利用海洋的方式比較單一,甚至需求也是較為有限的。據此,海洋可以容忍各國“自由地”利用,以至于沒有多大必要界定海洋“自由”的含義。進而,海洋自由是否被善意地利用抑或被惡意地利用不會成為一個重要問題。
無論如何,20 世紀中期,尤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后,海洋自由的內容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由于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國際海底區域等制度的出現,基于海域或區域不同的海洋自由的多樣性進一步增強;第二,海洋自由在同一海域部分的含義或者特定的海洋自由的權利也在發生變化。以公海自由為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7 條的規定,公海自由是在該公約以及“其他國際法規則”規定的條件下行使的。顯然,無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還是“其他國際法規則”在實踐中都會發生變化,據此,公海自由的含義也會受到影響。
應當注意,就一般而言,自由不僅是主體追求的目標,并且也是主體主張、實現利益的手段,換言之,自由既具有本體性,也具有工具性。較之國內法語境中自由與利益的關系,9整體而言,較之西方法學界,深受唯物史觀影響的中國法學界尤其重視權利與利益之間的聯系,認為權利的基礎與目標是利益,換言之,權利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工具性的。海洋自由的工具性效用與特征更加明顯。原因是,海洋公共秩序特殊的觀念基礎、行為體結構以及規制模式,10參見本文第三、第四和第五部分。使得海洋自由有可能或有風險成為進行不均衡的利益分配的工具,比如在海洋大國與海洋小國之間、在沿海國家與內陸國家之間、在當代與后代之間。
(二)安全
安全是海洋公共秩序的另一個重要構成要素。如所前述,安全與自由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這揭示了自由實際上是誘發安全關切的重要因素。當然,自由與安全之間緊張關系的邏輯狀態與事實狀態是不同的,前者是潛在的,而后者是現實的。國際海洋法的歷史已經表明,在人類利用海洋的漫長進程中,影響海洋安全的因素主要是與海洋自由無關的因素,包括與人類活動無關的因素(比如颶風等天氣現象)以及涉及人類活動的因素(主要指海盜)。然而,隨著行使海洋自由權利的主體數量越來越多、能力越來越強,體現海洋自由的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形式越來越多樣、內容越來越復雜,由于行使海洋自由權利誘發的海洋安全問題也變得越來越突出。
相對而言,各國對于應對與海洋自由無關的因素誘發的海洋安全問題較為容易達成共識,并在此基礎上開展有力的合作。比如,針對索馬里海域日益猖獗的海盜活動,2008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以下簡稱“安理會”)第5902 次會議通過第1816(2008)號決議,規定在該決議通過后的六個月內,在索馬里過渡聯邦政府事先知會秘書長情況下,同過渡聯邦政府合作打擊索馬里沿海海盜和武裝搶劫行為的國家可以:
(a)進入索馬里領海,以制止海盜及海上武裝搶劫行為,但做法上應同相關國際法允許的在公海打擊海盜行為的此類行動相一致;(b)以同相關國際法允許的在公海打擊海盜行為的行動相一致的方式,在索馬里領海內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制止海盜及武裝搶劫行為。
此后,安理會又分別通過了第1838(2008)號決議、第1846(2008)號決議,以及第1851 號決議。這些決議強化、補充,乃至超越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關于遏制海盜行為的規定。11比較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00、105 條和安理會第1816(2008)號決議。事實上,反海盜幾乎是1999 年科索沃戰爭后安理會成員國開展有效合作的惟一領域。
與此不同,對于因行使海洋自由權利誘發的海洋安全問題,各國開展有效合作要難得多。原因是,應對此類海洋安全問題必然要重構既有的海洋自由權利,換言之,既有的海洋自由權利可能受到減損。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即便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被迫于1994 年接受《關于執行1982 年12 月10 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一部分的協定》——該協定實質性地修改了該公約第十一部分——之后也遲遲不愿意加入該公約的根本原因:美國可以主張享有習慣國際法項下的海洋自由,而無須受條約法對這些自由的限制。
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安全”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廣泛性。安全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不過,這些安全關切并未都有效地納入國際法的約束范圍,盡管它們可能是同等重要的。第二,關聯性。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際法實踐中的“議題聯結”問題顯得越來越重要。表現在安全問題方面,不同安全關切之間相互勾連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第三,時代性。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不僅新型的安全關切可能出現,并且傳統的安全關切可能也會發生變化,而由于國際法造法效率趨于降低等原因,國際法往往無法及時規范這些新的變化。第四,自判性。安全關切傳統上被認為屬于“高級政治”,即國際法,尤其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很大程度上尊重特定國家對于安全問題的判斷。在人類社會從工業社會進入風險社會——風險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是,風險往往被主觀地認知而非客觀地識別——的過程中,國際法實踐中的自判性問題顯得越來越突出。12關于風險社會理論,參見Ulrich Beck,World Risk Society,Polity Press,1998;Ulrich Beck,Risk Society:Towards a New Modernity,translated by Mark Ritter,SAGE Publications,1992;Ulrich Beck &Johannes Willms,Conversations with Ulrich Beck,translated by Michael Pollak,Polity Press,2004;Ulrich Beck,What Is Globalization?,translated by Patrick Camiller,Polity Press,2000.筆者把風險社會理論運用于國際法研究的嘗試,參見CAI Congyan,Regulation of Non-Traditional Investment Risks and Modern Investment Treaty Regime in the Era of Late Globalization,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Vol.7:3,p.457-506 (2010).其結果是,一方面,一些國家擔心由于接受特定國際法制度可能造成“義務外溢”,即被迫在沒有明確受到國際法約束的領域承擔國際法律義務;另一方面,一些國家則希望通過特定國際法尋求“權利外溢”,即在沒有明確受到國際法約束的領域主張國際法律權利。
具體就海洋安全而言,隨著全球化,尤其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持續推進,各國在資源、交通等方面越來越依賴于海洋,這必然滋生較之以往更多、更復雜的海洋安全關切,一些國家可能未能準確地理解海洋安全關切的廣泛性、關聯性、時代性以及自判性,而另一些國家則可能惡意地利用海洋安全關切的這些特征以追求實現本國利益。較之國際法已經針對各國間在陸地上的關系規定了較為明確、有效的法治框架,海洋的國際法治化程度顯然要低的多,因此國際法——不僅僅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應對海洋安全問題方面面臨著突出的挑戰:第一,國際法可能是無效的或者不夠的,因為相關國家對于特定的國際法規則的含義乃至存在有著不同的認識,因而它不足以被援引以有效應對新的海洋安全關切;第二,國際法可能是“有效的”,因為它可以被相關國家惡意利用以追求實現該國狹隘的國家利益。
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1條規定為例,該條的標題是“海洋的和平使用”,但該條并未規定“和平”的含義,其正文規定的是:“締約國在根據本公約行使其權利和履行其義務時,應不對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進行任何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與《聯合國憲章》所載國際法原則不符的方式進行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類似地,雖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三部分詳細規定了海洋科學研究(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問題,但并未規定“海洋科學研究”本身的含義。據此,在中美兩國關于專屬經濟區外國軍事活動的約束方面,中美兩國及多數學者對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1 條規定的和平目的以及外國軍艦、軍機等在專屬經濟區及其上空從事的情報收集等活動的性質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13比較可參見Raul (Pete) Pedrozo,Preserving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The Right to Conduct Military Activities in Chin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1,p.9-29 (2010);ZHANG Haiwen,Is It Safeguard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r Maritime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 Comments on Raul(Pete) Pedrozo’s Article o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1,p.31-47 (2010).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啟動之時恰值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漸入佳境”之際。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著力于通過海洋法會議改變舊的國際經濟秩序,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狀況,最終達成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也體現了這一時代訴求。14《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序言中規定:“考慮到達成這些目標將有助于實現公正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這種秩序將照顧到全人類的利益和需要,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利益和需要,不論其為沿海國或內陸國。”與此不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當時并不十分關注通過該公約有效應對美國等傳統海洋大國海上軍事力量對海洋自由的濫用問題,從而喪失了一次通過條約法更新習慣國際法的重要機遇。
三、海洋公共秩序的觀念基礎
在筆者看來,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包括作為新興海洋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面臨的最主要挑戰之一是如何應對國際公共秩序的不斷擴大與強化——包括海洋公共秩序的擴大與強化,以及進而由此導致的海洋治理模式的變遷。15參見本文第五部分的討論。直言之,作為傳統大國崛起之觀念基礎的個體主義越來越多地發展到共同體主義,中國將被迫更多地在共同體主義,而非在個體主義的基礎上進行相關的國際法實踐。準確地理解并且恰當地處理個體主義與共同體主義之間的關系對于中國等新興大國恰當地制定并有效地實施國際法戰略至關重要。在這方面,海洋公共秩序的變遷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
(一)個體主義
所謂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是指一國的對外關系行動以本國國家利益為主要甚至唯一考量。個體主義的本質是自由放任。著名國際法學家、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上訴庭長安東尼奧·卡塞斯(Antonio Cassese)正確地指出,傳統國際法,尤其“一戰”以前的國際法是個體主義的,根本上是建立在自由放任基礎之上的。16參見安東尼奧·卡塞斯:《國際法》,蔡從燕等譯,法律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41 頁。
從法律關系的角度看,在個體主義觀念基礎上形成與實施的國際法具有突出的雙邊性特征,即特定法律關系當事國以外的第三方不能干預該法律關系,即便該特定法律關系是基于某一多邊制度或機制發生的,比如都是某多邊協定的締約國。在卡塞斯看來,這些國際法規則是“雙務”的。值得注意的是,卡塞斯認為習慣國際法是向特定國家賦予針對所有其他國家的權利,因而是一種共同體意義上的權利,但他也認為此項權利在實施過程中被弱化為一種雙務意義上的權利,即缺乏一種相應的程序性權利。在他看來,公海自由就是此類國際法規則的典型。17同上注,第17 頁。類似地,在關于國家責任的第三份報告中,時任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特別報告員威廉·里普哈根(Willem Riphagen)指出,傳統國際法根本上是“雙邊傾向的(bilateral-minded)”,即國際法律義務存在且僅存在于單個的國家之間。18Willem Riphagen,Third Report on State Responsibility,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1982,Vol.2,Part 1,p.36.著名國際法學家、前國際法院法官布魯諾·西瑪(Bruno Simma)用“雙邊主義(bilateralism)”來描述傳統國際法的特征。19Bruno Simma,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Law,Recueil Des Cours,1994,VI,p.230.
僅就公海而言,公海自由意味著公海對國際社會的所有國家開放,據此“任何國家不得有效地聲稱將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權之下”,20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89 條。但這并不意味著國際社會已經在公海上確立了充分而公正的公共秩序,更遑論有效地維護這種公共秩序。在相當長的歷史期間內,海洋公共秩序是有限的和不公正的,是建立在個體主義觀念基礎之上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直至20 世紀中期,海洋自由尚處于“壟斷自由”時期或“寡頭自由”時期,而絕大多數國家由于不具備足夠的利用海洋的意識與能力,因而未能參與海洋秩序的構建,它們中的許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甚至被西方國家認為未能滿足“文明標準”而被拒絕承認主權國家的法律地位,因而未能成為國際共同體的成員。
個體主義觀念在海洋法的重要體現是,私法中的“先到先得”(first come,first serve)觀念長期以來深刻地影響著海洋利用。顯然,較之海洋小國來說,個體主義觀念更有利于海洋大國,因為后者擁有更強大的利用海洋和構建海洋法律制度的能力。盡管如此,海洋小國也在盡可能地利用個體主義觀念追求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如所周知,在20 世紀40 年代以來出現的以沿海國擴大領海范圍和設立專屬經濟區的“海洋圈地”運動中,既有諸如美國這樣的海洋大國,也有諸如馬耳他這樣的海洋小國。
(二)共同體主義
所謂共同體主義(communitarianism)是指一國的對外關系行動主觀上愿意或客觀上必須接受其所在的社群——它主動或被動地加入該社群——的制約,而無法純粹地追求本國國家利益。討論國際法中的共同體主義主要解決以下問題:第一,是否存在國際社會或國際共同體;第二,國際社會或國際共同體的含義;第三,國際社會或國際共同體的特征;第四,國際社會或國際共同體對包括海洋法在內的國際法的影響。雖然不能認為傳統國際法中全然沒有國際共同體觀念,21比如,19 世紀中期成立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及其開展的活動實際上就是基于國際共同體觀念的。但在20 世紀之前基本上可以說不存在普遍意義上的國際共同體觀念。沃爾夫岡·弗萊德曼(Wolfang Fridmann)提出的獲得廣泛接受的國際法發展分期說可以說明這一點。22晚近對于“共處法”與“合作法”之間區別的一項重要分析,參見George Abi-Saab,Whith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1998.在經典的《變動著的國際法結構》中,弗萊德曼把迄至當時為止的國際法分為“共處法”與“合作法”,“共處法”強調國家間關系的“消極不作為”,尤其不得侵害他國主權與領土完整,而“合作法”強調國家間關系的“積極作為”。23See Wolfang Fridmann,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4,p.60-63;Christian Tomuschat,International Law: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Mankind on the Eve of A New Century,Recueil Des Cours,Vol.281,p.56-63 (1999);《國際聯盟盟約》序言第1 段。中國學者也接受了這一分期說。例見李浩培:《國際法的概念與淵源》,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27 頁。顯然,“共處法”遵循的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邏輯,這正是一種缺乏共同體觀念的表現。雖然弗萊德曼沒有明確說明國際法從“共處法”邁向“合作法”的界限,但大致可以認為國際聯盟尤其聯合國的成立是“共處法”邁向“合作法”的分水嶺,因為《聯合國憲章》在歷史上首次把國際合作確立為一項國際法基本原則。24根據圖姆夏特的說法,國際聯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不依賴于傳統的主權平等理論而建立的法律架構。雖然國際聯盟失敗了,但它是邁向新的方向的一個重大步驟。Christian Tomuschat,International Law: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Mankind on the Eve of A New Century,Recueil Des Cours,Vol.281,p.59 (1999).誠然,在當前國際法中,合作從一般意義上說并不是主權國家的一項法律義務,但不可否認,不僅被國際法規定負有法律義務進行合作的領域不斷增多,被國際社會成員普遍認為負有政治義務或道德義務進行合作——這是邁向法律義務之合作的必要步驟——的領域也如此。這些領域之所以不斷增多,根本上是由于諸如國際金融危機、國際恐怖主義、國際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地出現,使得國際社會的成員之間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進而形成了日益堅實的共同體觀念,“相互依賴”這一措辭日益廣泛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種共同體觀念。
盡管如此,確實還有許多人否定國際共同體的存在。對此,前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Annan)批評道:
“一些人認為,國際社會只是一種幻覺。另外一些人認為,這個概念彈性太大,因而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還有一些有人聲稱,國際社會只是權宜之計,只在緊急情況下或需要為不作為尋找借口時才拿出來用。一些人認為,作為共同體存在之基礎的獲得國際公認的規范、目標和憂慮并不存在。”25Kofi Annan,The Mean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Address to 52nd DPI/NGO Conference,New York,15 Sep 1999.
安南不否認國際社會在許多問題上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但不應因此認為當前的國際共同體充其量只能稱之為“在制品”(work in progress),安南并不認為要建立一個完全和諧的世紀(an era of total harmony),所以也不應因國家間存在著利益與觀念沖突就否定了國際社會的存在。安南認為,隨著對相互依賴關系的日益體認,各國正在“重新制定規則、重新組織討論,以及重新安排工作”(rewriting the rules,reframing our debates and reshaping our work)。因而,安南堅定地指出:“我認為這些懷疑論者是錯誤的,國際社會的的確確是存在的。它有一個稱謂,它取得了值得贊賞的成就,它是我們邁向未來的惟一方向。”26Ibid.
對于國際共同體的存在與否,客觀的國際法實現顯然更具有意義。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3 條規定,國際強制性規范是指那些被“由國家構成的國際共同體”(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tates)接受并承認只能由以后具有同等性質之一般國際法規則始得修改的規范。克里斯蒂安·圖姆夏特(Christian Tomuschat)認為,從許多條約以及其他法律文件的規定中可以初步地認為,“國際共同體”的存在是沒有疑問的。27Christian Tomuschat,Obligations Arising for States Without or Against Their Will,Recueil Des Cours,Vol.241,IV,p.227 (1993).國際裁判機構也確認了國際社會或國際共同體的存在。比如,在“德黑蘭的美國外交和領事人員案”中,國際法院指出,其有義務提請“整個國際共同體注意”,并認為維護人類過去數百年來精心建造起來的法律大廈對于當今復雜的“國際共同體”的安全與福祉都是至關重要的;28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taff in Tehra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Iran),Judgment,ICJ Reports 1980,p.43.在“西南非洲案”中,國際法院指出,納米比亞作為受到損害的實體,有權利向“國際共同體”尋求援助;29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South West Afric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Advisory Opinion,ICJ Reports 1971,p.56.在“巴塞羅那電力公司案”中,國際法院指出對世義務(obligation ergaomnes)是對“作為整體的國際共同體”負有的義務。30Barcelona Traction,Light and Power Company,Limited (Belgium v. Spain),Second Phrase,Judgment,ICJ Reports 1970,p.3.當然,誠如安南承認的,國際共同體并非在所有問題上都有效地發揮了作用。
從法社會學的角度看,共同體的存在對于公共秩序的建立與維護至關重要。公共秩序事關特定群體所有成員,而非個別成員的利益。個別成員在建立與維護公共秩序方面不僅力有不逮,也可能“公器私用”,即以建立與維護公共秩序為名追求實現自己狹隘的利益。與此不同,共同體具有更強大的力量,并且更可能具有有效的“公意”機制,31參見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2003 年版,第37-41 頁。從而更有可能建立與維護公正的公共秩序。根本上說,沒有共同體,就不可能有公共秩序。就國內層面而言,國家就是人們建立的旨在建立與維護最低公共秩序的最重要的共同體。就國際層面而言,從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到1815 年維也納會議、從1919 年國際聯盟至1945 年聯合國的過程通過更有效的共同體形式以便更有效地建立與維護國際公共秩序。當然,主權國家與諸如聯合國之類的國際共同體表現形式在建立與維護公共秩序方面的能力是有差別的。
從規范性質的角度看,共同體邏輯地意味著某種公法性法律規范或機制——意味著針對整個共同體成員的權利或義務,而非私法性規范或機制——意味著只是針對特定共同體成員的權利或義務。從特定共同體成員的角度看,這不僅意味著它可以據此更有力地主張權利,同時也意味著它如若違反義務將經受更嚴格的評價、承擔更嚴厲的制裁。
從國內法經驗看,公共秩序的建立與維護依靠的是公法性規范,而非私法性規范,這是國內法公私法分立的重要理由。從國際法的角度,傳統國際法受到國內私法精神的強烈影響,它主要是建立在國家同意基礎之上的,由此國際法被認為“實際上屬于私法性質,或者甚至比國內私法還要私”,32參見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編譯:《國際公法》,知識出版社1981 年版,第77 頁。只是“更高級的私法”。33參見Hersch Lauterpacht,Private Law Sources and Analogies of International Law,Longmans,Green and Co.,1927,p.81.國際法大師勞特派特也認為,如果把私法看作是調整處于合作狀態中的法律實體之間的關系,而公法是調整處于服從狀態中的法律實體之間的關系,那么,國際法是屬于私法一類的。34同上注。新近,仍有國際法學者堅持“認為國際法規則與國內法律體系中的私法具有相同的特征并沒有錯”。35Teruo Komori,Introduction,in Teruo Komori &Karel Wellens eds.,Public Interest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Toward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Ashgate,2009,p.1.筆者把傳統國際法稱之為“私法性國際法”。然而,隨著國際共同體觀念在范圍上的擴大與程度上的增強,基于共同體權利或義務的規范或機制逐步增加,筆者把此類國際法規范稱之為“公法性國際法”。36關于“私法性國際法”和“公法性國際法”的系統論證,參見蔡從燕:《國際法律體系中的“公私法分立”》,載《北大法律評論》2011 年第1 期,第12-65 頁。載有此類規范——可能表現為條約規范,也可能表現為習慣規范——的條約往往被冠以“憲章”的名稱,比如《聯合國憲章》,或者被稱為所謂的“造法性條約”。根據一般的公法原理,共同體以及相應的公法性規范的基本價值取向是運用共同體權威保護弱者,遏制強者濫用優勢實力。不過,迄今為止關于共同體的最成功實踐是在已經實現國家化和法治化的國內社會,因而關于共同體和公法性規范的一般論斷是以相當成熟的國內法經驗為基礎的。如所周知,由于國際共同體在總體上不如國內社會成熟,因此關于國際共同體的法律安排在某些情況下可能被其成員,尤其是其中的強者“公器私用”,即以維護共同體利益之名行追求本國利益之實。37關于國際法上“公器私用”的風險,參見上注,第62-64 頁。如所周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被譽為“海洋憲章”。這意味著締約國基于該公約可以享有基于全球性共同體性質的權利,同時承擔基于全球性共同體的義務。38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有條款都具有此等性質。據此,諸如公海自由之類的習慣國際法規范改變了以往在“壟斷自由”和“寡頭自由”時期其實不可能成為公法性規范或機制的狀態——直言之,是一種實質上的私法性規范或機制,但在“普遍自由”時期成為了公法性規范或機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其提供了法律保障,而締約國對于利用海洋方面具有的普遍訴求及不斷提高的能力使之成為了可能。不僅如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還確立了作為公法性規范或機制的條約規范或機制,尤其是基于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原則建立的包括國際海底管理局在內的國際海底區域制度。39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一部分。顯然,較之一般意義上的私法性國際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締約國在該公約項下可以更切實地行使權利,但也會受到更有效的拘束。
通常來說,國際共同體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共同體被人們從兩種意義上使用,即社會學意義上的和法律意義上的。關于前者,在“希臘—保加利亞‘社區’案”中,常設國際法院做了頗為詳細的闡述。常設國際法院認為,社會是“生活在特定國家或地方的一群人,他們擁有自己的族群、宗教、語言以及傳統,并且由于這種族群、宗教、語言以及傳統而以一種休戚與共的情感團結在一起,而旨在保護他們的傳統,保持他們的崇拜習俗,確保根據他們族群的精神與傳統教導及撫育他們的子女,并且相互提供援助”。40Greco-Bulgarian “Communities”,PCIJ Series A,No.10,p.18;PCIJ Series B,No.17,p.21.一些國際法學者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國際社會的。比如,《奧本海國際法》認為,“一戰”之前,國際社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促使各國人民間可以經常交換思想和意見的“國際性的科學和藝術”,但最重要的是“農業、工業,尤其貿易”。41《奧本海國際法》上卷第一分冊,王鐵崖、陳體強譯,商務印書館1981 年版,第8-9 頁。
同時,一些國際法學者側重從法律的意義上理解國際社會。比如,托馬斯·弗蘭克(Thomas M.Franck)在其著名的《國家間正當性的力量》中指出,國際社會基本上只是國際法建構的“規則共同體(rule community)”,42Thomas M.Franck,The Power of Legitimacy Among N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02.即只是一種“法律共同體”。在弗蘭克看來,規則共同體是一種根據規則進行交往而形成的組織化體系,它超越了“烏合之眾式”的交往,43同上注,p.196-197.但他指出這一共同體“并無異于包含有社會學家或人類學家通過歸納或演繹提出的許多理論定義中的任何一種。這里使用共同體純粹只是表明規則結構——在這一結構中,一群行為體習慣地進行互動——的復雜性程度所達到的高度”。44同上注,p.201-202.換言之,弗蘭克認為,較之社會學意義上的共同體,法律意義上的共同體只是一種較低層次的共同體。不過,在著名的《國際法與制度中的公正》一書中,弗蘭克認為推動國際共同體出現的“不僅涉及權利與義務,而且涉及共同的道德律與價值”。45同上注,p.10.換言之,共同體成員相互之間不僅負有法律義務,而且負有道德義務,這就是公正(fairness)。46同上注,p.11.
弗蘭克認為,雖然我們尚未達到這種意義上的國際共同體,但隨著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國際法的發展,人類社會進入21 世紀后正在朝著這個方面邁進。47同上注。
弗蘭克關于法律意義上的國際共同體與社會意義上的國際共同體次遞發展的主張是不完全正確的。一方面,誠如西瑪所說的,許多國家同意進行談判或加入某些國際制度可能只是表面上的,48Bruno Simma,Consent:Strains in the Treaty System,in Ronald St.J.Macdonald &Douglas M.Johnson eds.,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aw,Martinus Nijhoff,1983,p.480–496.其未必真正認同特定的國際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弗蘭克的主張是正確的。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例,雖然特定國家締結了該公約,這并不當然地表明該國完全認同該公約,在該公約采取“一攬子交易”談判模式達成的情況下尤其如此。49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9 條。該條規定:“除非本公約其他條款明示許可,對本公約不得作出保留或例外。”晚近,這種“一攬子交易”的談判模式越來越多地被采納,比如WTO 談判。據此,雖然關于海洋的法律共同體已經形成,但還不能說關于海洋的社會共同體已經形成。其結果是,特定國家在某些情況下不會善意地履行該公約。另一方面,雖然利益集團等因素往往會干擾國內立法過程,但總體上國內立法機構能夠對特定的社會共識作出反應。與此不同的是,由于大國狹隘的利益計算以及小國對于大國此種利益計算的擔心,即便絕大多數國家對于特定議題已經形成基本共識,國際立法也往往難以進行或完成。以海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以下簡稱“WMD”)擴散為例,各國對于防止WMD 擴散,包括通過海洋發生的擴散無疑是有共識的,但主要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對于美國等海洋大國濫用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海洋力量懷有疑慮,從而阻礙了就此議題進行國際立法的進程,并且不愿加入美國在2003 年發起的“防擴散安全倡議”(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以下簡稱“PSI”)。50參見Michael A.Becker,The Shifting Public Order of the Oceans: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the Interdiction of Ships at Sea,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Vol.46:1,p.132-215 (2005).其結果是,雖然關于防止海上WMD 擴散的全球性社會共同體已經形成,但相應的全球性法律共同體尚未形成。換言之,其結果是,雖然特定國家由于不存在特定的全球性機制或者沒有加入特定的區域性或雙邊機制而不需要承擔國際法律義務,但會承擔政治、社會或道義方面的壓力,從而在事實上可能不得不做出讓步。以中國對待PSI 的態度為例,雖然中國拒絕加入PSI,但中國不得不表達對PSI 宗旨的贊同,51《外交部:中方贊成防擴散安全倡議(PSI)宗旨但也有所關切》,載環球網2009 年6 月2 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09-06/477588.html.據說中國在實踐中向美國等國家所采取的PSI 行動提供了配合。52同前注51,Michael A.Becker,p.166.
應該強調的是,較之法律共同體,特定國家應對來自社會共同體的影響可能更復雜。的確,特定國家尤其是大國可能可以采取阻止或妨礙全球性法律共同體——其成員無疑主要是主權國家——的形成與運作,或者采取不加入某一非全球性法律共同體,從而可以合法地避免本國承擔法律義務。與此不同,構成社會共同體的不僅僅是主權國家,甚至主要是非國家行為體,比如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些非國家行為體不僅數量龐大,而且影響力不可小覷。事實表明,它們對于某些重大國際法律議程的形成與處理產生了重大影響。53在這方面,被廣為援引的經典案例是“國際禁止地雷運動”對于《渥太華禁雷公約》獲得通過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
(三)海洋公共秩序中個體主義觀念與共同體主義觀念的結構性關系
鑒于海洋是“共有物”,因而對“任何人開放”在羅馬時期就已形成,尤其在18 世紀中期后獲得普遍承認并且簡潔地稱之為“公海自由”的觀念,似乎可以認為海洋公共秩序是久已存在的,進而可以認為全球性的海洋共同體和公法性的海洋法律規范或機制是存在的。然而,根據前文對于海洋自由分期的討論,在“壟斷自由”和“寡頭自由”時期,所謂的海洋公共秩序是建立在個體主義觀念基礎之上的,這與公共秩序的本質是不相符合的,因而這兩個時期的所謂海洋公共秩序很難說是真正意義上的海洋公共秩序。然而,鑒于海洋公共秩序、全球性海洋共同體以及公法性海洋法律規范或機制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這種特殊的海洋公共秩序對于海洋大國是極為有利的。不難發現,迄今為止的所有傳統海洋大國都是在這兩個時期確立其地位的。
在筆者看來,只有在“普遍自由時代”,即20 世紀中期以來,隨著各國海洋觀念的增強、與海洋相關的環境污染以及WMD 擴散等問題日益嚴重或者諸如海盜等問題死灰復燃,尤其《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以后,基于共同體主義的,因而是真正的海洋公共秩序的時代才可以說到來了,在法律上的主要體現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僅創設了一系列體現共同體觀念的制度,而且使得歷史久遠的公海自由規則具備了真正的共同體特征。可以認為,在個體主義與共同體主義的結構性關系中,重心已經朝著后者的方向發展。對于新興海洋大國來說,它們不得不經歷傳統海洋大國沒有經歷過的制約,因而如何理解并應對這些制約對于新興海洋大國能否順利實現崛起至關重要。
盡管如此,由于國際共同體的特殊性,54參見本文第四部分之(一)、(二)的討論。個體主義觀念仍然存在于海洋公共秩序的建立與維護過程中。其極端的例子是,美國通過不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拒絕該公約確立的基于共同體觀念的國際海底開發制度,企圖繼續運用在“壟斷自由”和“寡頭自由”時期的公海自由觀念來實現本國國家利益。
四、海洋公共秩序的行為體
(一)海洋大國與海洋小國
如同窮人與富翁、強者與弱者并存是國內社會結構的常態一樣,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并存也是國際社會結構的常態。同時,與國內法注重維護弱者不同的是,國際法似乎更重視維護大國的利益。其結果是,且不論包括中國在內的處于小國或者弱國地位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歷來批判西方大國操縱國際法,55例見周鯁生:《國際法》,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163-164、251-260 頁;J.H.W.Verzijl,International Law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pringer,1968,p.435-443.當代著名的一些西方國際法學者也認為國際法仍然屬于“霸權主義國際法”。56參見Detlev F.Vagts,Hegemonic International Law,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5:4,p.843-848 (2001);Jose E.Alvarez,Hegemonic International Law Revisited,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7:4,p.873-888 (2003);José E.Alvarez,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Law-Mak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99-217.盡管如此,由于利益與功能方面的考慮,在國際法實踐中賦予大國以特殊權利不僅對于大國,而且對于整個國際社會都是具有正當性的。與此同時,雖然大國是國際大家庭的領導者,但國際法的歷史表明,國際法中進步的提議往往是由小國提出的。57參見蔡從燕:《國際法上的大國問題》,載《法學研究》2012 年第6 期,第188-206 頁。
就海洋公共秩序而言,在“壟斷自由”和“寡頭自由”時期,海洋大國幾乎完全控制了海洋公共秩序的塑造,58當然,誠如前文所述,這兩個時期的海洋公共秩序很難說是真正意義上的海洋公共秩序。而海洋小國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當然這實際上是整個近代國際法的基本特征。59赫希·勞特派特認為,“就理論與實踐方面而言,這樣一種觀點,即基督教國家,尤其西方國家的文明對于17、18 以及19 世紀現代國際法的產生與發展所做的貢獻幾乎是全部的和決定性的,大體上是對歷史事實的準確反映”,參見Elihu Lauterpacht ed.,International Law:Being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Hersch Lauterpacht,Vol.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18.20 世紀中期以來,尤其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重要變化,海洋小國在塑造海洋公共秩序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大:
第一,一些海洋小國提出重要的海洋公共秩序主張,并且得到了在數量上已經遠遠超過發達國家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從而對海洋大國造成強大的政治、道德與法律壓力。在這方面,經典的例子是1970 年馬耳他常駐聯合國代表阿維德·帕多(Arvid Pardo)提出的“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如所周知,美國等發達國家曾經企圖把傳統的公海自由原則推及適用于國際海底資源的開發與利用。結果是,多數傳統海洋大國被迫接受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規定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原則以及據此構建的國際海底制度。雖然主導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美國即便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一部分被做了重大修改后仍然拒絕加入該公約,表現出其“強大”的一面,然而,從另一個意義上說,這恰恰表明海洋小國在塑造海洋公共秩序的作用較之以往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第二,海洋小國獲得更有效的實現其海洋公共秩序主張或權利的程序性機制,在其他與海洋大國的博弈中尤其如此。這些程序性主要指的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規定的爭端解決機制。該公約第286 條規定,除了特定的限制和例外,60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十五部分第一、三節。“有關本公約的解釋或適用的任何爭端”應任一爭端當事國請求“應當”提交給特定的具有管轄權的法院或法庭。換言之,該條規定了國際法院等國際裁判機構的強制管轄權。雖然此前或者同時期也存在著其他擁有強制管轄權的程序性機制,比如《聯合國憲章》第七章規定安理會代表全體會員國采取行動、61雖然《聯合國憲章》并未規定安理會作為爭端解決機構,而只是“執行”機構,但人們普遍承認安理會的裁判功能。根據《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解決》設立的國際投資仲裁機制,以及根據《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設立的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制,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可能是唯一的針對和平狀態下涉及所謂“高級政治”問題設立的具有強制管轄權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顯然,菲律賓就南海爭端把中國訴諸國際仲裁庭就體現了這一程序性機制的作用。
不難發現,該公約項下爭端解決機制處理的爭端事項主要涉及的正是海洋公共秩序,尤其航行自由、飛越自由以及鋪設海底電纜和管道等,62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7 條第1 款。但并非所有涉及海洋公共秩序的爭端都被納入強制管轄。63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7 條第2 款和第298 條。與此同時,與海洋公共秩序沒有直接關系的爭端,比如領土主權,被排除在強制管轄外。64參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298 條第1 款a 項。第三,國際關系實踐表明,小國往往會策略性地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以維護自己的利益,65參見August Schou &Aren Olav Brundtland eds.,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iley Interscience,1971;Davil Vital,The Survival of Small States:Studies in Small Power/Great Power Conflic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國際法上的中立國制度就是表現之一。如所周知,近年來中國與菲律賓等少數南海周邊國家圍繞南海資源利用等問題發生的紛爭很大程度上就是菲律賓等海洋小國利用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與新興大國的中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試圖利用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爭端解決機制在內的各種手段,以維護航行自由等海洋公共秩序為重要訴求,追求本國在南海區域的國家利益。
(二)既有海洋大國與新興海洋大國
在著名的《大國的興衰》中,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深刻分析了16 世紀以來五百年的大國興衰,認為經濟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大國興衰,經濟實力變化導致軍事實力變化,進而導致整體國家實力變遷。66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Vintage Books,1989.大國興衰的歷史表明,海洋實力的興衰構成大國興衰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大國興衰的主要標志。國際法的歷史表明,大國興衰對于國際法的變遷具有重大影響,據此國際法或是進入動蕩期,或是進入新的發展階段。67Wilhelm G.Grewe,The Epochs of International Law,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Michael Byers,Walter de Gruyter,2000.
既有海洋法的歷史表明,在特定國家成為海洋大國之前,該國在海洋公共秩序問題上很可能與既有海洋大國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立場,但其立場往往隨著該國海洋實力的增強而與既有海洋大國的立場趨于一致。從中國的角度看,前蘇聯在領海范圍內的無害通過是否包括外國軍艦可以未經沿海國事前批準通過問題上的立場變遷是一個極好的案例。20 世紀50 年代,前蘇聯的立場是,作為習慣國際法規則的領海范圍內無害通過只包括商船的無害通過,但不包括外國軍艦未經沿海國事先批準的通過。然而,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期間,前蘇聯的立場發生了逆轉,即認為領海的無害通過制度適用于外國軍艦。其重要原因是,雖然有漫長的海岸線,但在20 世紀60 年代前,前蘇聯主要是一個大陸型國家,其海上力量并不十分強大。1962 年古巴導彈危機的爆發促使前蘇聯著手大力發展海軍。進入20 世紀70 年代后,前蘇聯海軍實力大增。出于與美國對抗的需要,前蘇聯改變了其在無害通過問題上的立場。盡管如此,1983 年通過的《關于外國軍艦在蘇聯領水(領海)、內水和港口航行和逗留的規定》(Rules Concerning the Navigation and Sojourn of Foreign Vessels in the Territorial Waters [Territorial Sea] of the U.S.S.R.,the Intenal Waters and Ports of the U.S.S.R.)在采納這一新立場方面并不明確。其導致的結果是,1986 年美國軍艦“約克城”號和“卡隆”號進入前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領海,前蘇聯表示強烈抗議,但抗議的法律依據并不明確。1988 年2 月,當美國再次派軍艦進入前蘇聯領海時,前蘇聯的軍艦直接予以沖撞從而造成雙方軍艦都受有損害。此次,前蘇聯明確指出,根據其現行法,外國軍艦只能在其指定的用于國際航行的航道上通行,即位于白令海、鄂霍次克海以及日本海的航道,而黑海中不存在這樣的航道。不過,1989 年9 月,前蘇聯與美國簽署一份聯合聲明,其中包含《關于無害通過的國際法規則的統一解釋規則》(Uniform Intepretation of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ing Innocent Passage),該解釋根本上接受了美國的立場,即無害通過制度適用于軍艦通過。68參見Eric Franckx,Innocent Passage of Warships:Recent Developments in US-Soviet Relations,Marine Policy,Vol.14:6,p.484-490 (1990);William E.Butler,Innocent Passage and the 1982 Convention:The Influence of Soviet Law and Policy,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1,p.331-347 (1987);Anthony P.Allison,The Soviet Union and UNCLOS III:Pragmatism and Policy Evolution,Ocea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w,Vol.16,p.109 (1986).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聯盟行政院為舉行1930 年國際法法典化大會而成立的籌備委員會曾經就領海無害通過制度是否適用于軍艦問題征詢各國的意見,美國的答復是堅定的,即軍艦無權適用無害通過制度;與此相反,彼時前蘇聯向該籌備委員會解釋的立場是,無害通過制度應當適用于軍艦。69同上注,Eric Franckx,p.485.當時導致美蘇分歧的原因與20 世紀50、60 年代美蘇分歧的原因其實是一致的,只不過與美國的海上力量在20 世紀30 年代尚未能稱霸世界顯然有很大的關系,而當時的前蘇聯可能還擁有沙俄時期建設的強大海軍。
如所周知,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期間,在海洋公共秩序問題方面,彼時尚屬海洋弱國而當下正逐步成為新興海洋大國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印度、巴西、智利以及南非等與美國等既有海洋大國存在許多分歧。以專屬經濟區內的外國軍事活動為例,美國等既有海洋大國認為,專屬經濟區適用作為習慣國際法規則的傳統航行自由規則,因此外國軍艦有權在該區域內進行活動。與此不同,印度、巴西等國明確表示反對,并在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時做出了相關聲明,并且把這一立場體現于相關的國內法。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后,多個發展中國家對于美國軍艦在其專屬經濟區的活動表示抗議。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認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6 條對于沿海國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利的規定是窮盡的,并且多數國家并未對美國軍艦的活動提出抗議,因此印度、巴西等國的主張是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過度主張(excessive claims)。70參見J.Ashley Roach &Robert W.Smith,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Third Edition),Brill Nijhoff,2012,Chapter 7.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并未像印度等國那樣在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時做出類似的聲明,但中美因此爆發的沖突——從2001 年南海飛機相撞,到2009年“無暇”號事件,再到2014 年中國“遼寧”號航空母航與美國“考彭斯”號巡洋艦險些相撞——是美國在此問題上與他國發生類似沖突中最嚴重的。
如果遵循上述美國和前蘇聯的歷史經驗——更遑論英國從17 世紀的“閉海論”轉向18 世紀全面的海洋自由論,中國、印度等21 世紀的新興海洋大國在海洋公共秩序必將選擇與美國等既有海洋大國相類似的主張,因為直觀地看,傳統的海洋公共秩序觀念與制度對于海洋大國是有利的;即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了較之以往對廣大海洋弱國與內陸國家乃至整個國際共同體都較為有利的制度,但其中所存在的諸多模糊之處為海洋大國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釋提供了空間。因而,從法律技術上說,這一轉向對于中國、印度等國似乎并非難事。
筆者同樣認為國家利益在當代現實的國際關系狀態中仍然是一國行動的基本邏輯,但認為21 世紀的新興海洋大國在調整傳統的海洋公共秩序主張過程中可能會受到較之以往更為復雜的一系列因素的制約,比如海洋大國與海洋小國間關系的變遷、海洋公共秩序治理模式的變遷,以及特定海洋大國整體的國際法律戰略等。71參見本文第五部分。
(三)公共行為體與私人行為體
如所周知,在20 世紀90 年代全球化,尤其經濟全球化進程呈現快速發展之后,私人在國際法中的作用——不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才得到國際法學者的系統性關注,進而成為許多國家國際法實踐中的重要議題。但例外是存在的,那就是海盜對于國際法的影響。早在近代國際法出現時,海盜就已經廣泛存在,并且在17 世紀末期到18 世紀早期這一階段達到“黃金時期”,不過此后海盜的威脅總體上趨于下降。72David F.Marley,Modern Piracy:A Reference Book,ABC-CLIO,2010,p.6-7.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是作為公共行為體的國家的海上力量大幅提升。不僅如此,任何國家對海盜都享有普遍管轄被確立為習慣國際法規則。據此,在18世紀后的很長時間內,可以認為私人對于海洋法來說是不重要的。
與其它國際法領域一樣,“冷戰”結束后海洋公共秩序受到私人的威脅明顯增大,這表現在海盜威脅的重新出現、國際恐怖組織乃至主權國家利用私人從事威脅海洋公共秩序的行為,比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石油泄露等嚴重海洋污染等。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私人行動能力明顯提升。比如,海盜通過各種途徑獲得的高性能裝備擴大了其行動能力,從而對海洋公共秩序造成范圍更大、后果更嚴重的威脅;另一方面,主權國家行動能力相對失靈。比如進入20 世紀90 年代,索馬里由于長期的國內武裝沖突等原因,陷入無政府狀態,無法對其領海進行有效管轄,導致索馬里附近海域成為主要的海盜高風險區域;又如,隨著“冷戰”結束,美國和前蘇聯的海上力量退出印度洋,海盜死灰復燃;再如,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方便旗”制度被私人濫用。
在這種背景下,主權國家力量正在更多地“邁向”海洋或者“回歸”海洋。由于私人對海洋公共秩序的威脅基本上不存在“厚此薄彼”的問題,因而各國在遏制、懲治私人危害海洋公共秩序的行為比較容易達成一致并開展有效的合作。比如,各國在反海盜問題上進行了國際合作。73參見李文沛:《國際海洋法之海盜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第四章。
總體來看,國際法學者較多地關注公共行為體與私人行為體在海洋公共秩序中的沖突關系,而較少考慮它們之間可能的合作關系。根據筆者對于國際法中的公私關系理論與實踐的研究,74參見蔡從燕:《公私關系的認識論重建與國際法發展》,載《中國法學》2015 年第1 期,第187-206 頁。在維護海洋公共秩序方面強化公私合作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可能由于未能全面地理解國際法中的公私關系,國際海事組織新近針對在高風險海域使用私人海上安保公司應對海盜威脅開展的工作似乎未獲足夠的重視。75參見IMO,Interim Guidance to Private Maritime Security Companies Providing Privately Contracted Armed Security Personnel on Board Ships in the High Risk Area,MSC.1/Circ.1443,25 May 2012;Revised Interim Recommendations for Flag States regarding the use of Privately Contracted Armed Security Personnel on Board Ships in the High Risk Area,MSC.1/Circ.1408-Rev.1,25 May 2012;Revised Interim Recommendations for Flag States regarding the use of Privately Contracted Armed Security Personnel on Board Ships in the High Risk Area,MSC.1/Circ.1406-Rev.2,25 May 2012;Revised Interim Guidance to Ship Owners,Ship Operators and Ship Masters on the Use of Privately Contracted Armed Security Personnel on Board Ships in the High Risk Area,MSC.1/Circ.1405/Rev.2,25 May 2012.
五、海洋公共秩序的治理模式
即便彼時“冷戰”正酣,在1968 年首次出版的《國家如何行動》開篇中,著名國際法學家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仍然提出了一個被廣為引用并經實踐驗證日益準確的論斷:“在國家間關系中,文明的歷史可以被看作從武力到外交、從外交到法律的運動。”76Louis Henkin,How Nations Behav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1.總體而言,武力與外交均以國家實力為基礎,在此不妨從實力與法治兩個方面討論海洋公共秩序的規制模式。
(一)實力
較之陸地秩序而言,國家實力對于海洋秩序的建立與維護更為重要。原因是,隨著近代主權國家紛紛成立,地球的陸地部分率先并且主要通過條約方式被納入各主權國家的管轄范圍,據此基本上實現了陸地部分的“私域化”。與此不同的是,地球的海洋部分絕大部分適用公海自由而并未被納入各主權國家的管轄范圍,并且習慣國際法規則在規制公海秩序方面占據絕對主導地位,公海秩序的全球性條約化進程始于20 世紀50 年代召開的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如所周知,較之條約法實踐,習慣法實踐——無論是規制創制還是規則適用——一般來說都更仰賴于國家實力。
即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實現了海洋秩序的條約化,但至少存在四個因素使得國家實力在海洋公共秩序演進方面仍將扮演極為重要的作用:第一,雖然諸如公海自由等習慣國際法規則通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實現了成文化,但這些習慣國際法規則并未喪失其獨立的國際法淵源地位。尤其是對于諸如美國之類尚未加入該公約的國家來說,適用于它們的仍然是習慣國際法規則。顯然,對于諸如公海自由等形成于數百年前的習慣國際法規則來說,它們不可能完全“凝固”在歷史中,而可能甚至必須根據國際關系的發展發生變遷。在這一變遷中,國家實力無疑仍將發揮重要的作用;第二,從條約法的角度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還存在許多可謂“建設性模糊”的地方,比如“和平目的”的含義。在澄清這些模糊方面,國家實力也必然發揮重要的作用;第三,《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國際實施機制尚不足夠有效,甚至未必非常可靠,77參見本文第七部分的討論。因此特定國家,尤其海洋大國仍有可能運用國家實力以使海洋公共秩序朝著有利于該國的方向發展,這些行為并不總是具有正當性;第四,如前所述,中國等新興海洋大國正在崛起,這種崛起必然伴隨著運用國家實力建立或維護其主張的海洋公共秩序。
國家運用實力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由于傳統的武力使用在聯合國時代受到嚴格的限制,因而政治手段成為國家運用實力的主要方式。比如,鑒于談判比較有利于海洋大國發揮本國的實力優勢,海洋大國可以側重于通過談判處理海洋公共秩序,包括解決國際爭端。
從價值判斷角度看,國家實力在海洋公共秩序建立與維護中的運用既可能是正當的,也可能是不正當的。從本部分討論的主題看,筆者提請注意的是,國家實力的運用較之以往更多地受到法治的制約。直言之,法治是影響國家運用其實力最大的變量。
(二)法治
雖然亨金早在20 世紀60 年代時就提出了國際關系邁向法治的論斷,但在“冷戰”的背景下,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受到極大的制約,這也正是20 世紀50年代末期以后美國國際法學界出現所謂“政策定向學派(紐黑文學派)”的原因所在。然而,“冷戰”結束后,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有明顯提升。1989 年11月17 日,聯大通過了題為“聯合國國際法十年”的第44/23 號決議,該決議表達了國際社會追求實現法治化的普遍愿望。該決議指出,聯大深信“在國際關系中必須加強法治”。《2005 年世界首腦會議成果》明確指出,必須“在國家和國際兩級全面遵守和實行法治”。78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A/RES/60/1,16 September 2005,para.134.盡管國際法治在“冷戰”結束后仍多次受到重大挑戰,如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但應當承認,國際法治是一個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事實上,如現民主、人權一樣,法治——包括國際法治——已經成為普遍價值,因而否定或挑戰它對于任何國家來說都是不明智的。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海洋公共秩序的法治化對于新興海洋大國未必是好事,因為這使得其很難再像歷史上的海洋大國一般能夠更加自由地運用實力來追求本國國家利益。其他國家,尤其是海洋小國,可以利用甚至濫用國際法來阻止新興海洋大國的崛起。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府對有關國家“越權解釋和適用國際法,更不能罔顧客觀公正,借‘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國權益之實”的警告是正確的。79參見《王毅:中國是國際法治的堅定維護者和建設者》,載人民網2014 年10 月24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024/c1002-25903195.html;外交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于菲律賓共和國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轄權問題的立場文件》,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4 年12 月7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201412/t20141207_7948472.shtml。這一現象其實正是所謂的“全球法律主義的風險”。80參見Eric A.Posner,The Perils of Global Legal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無論如何,國際法治對于新興海洋大國來說將是一項長期挑戰。
六、海洋公共秩序的法律形態
從規范類型看,規制海洋公共秩序的法律可以分為國際法與國內法。
(一)國際法
鑒于主權國家只能對較小規模的海域主張領土主權(領海),或者主權權利(領海以外的毗連區、專屬經濟區等),國際法無疑應該在規制海洋公共秩序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被譽為“海洋憲章”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全球性和權威性更是必須得到尊重和維護。否則,其結果必然導致相關國家恣意擴大本國管轄權甚至主張領土主權,從而使海洋公共秩序受到極大損害。
顯然,國際法并不能完全有效、公正地規制海洋公共秩序,在許多情況下,國內法可以也必須發揮國內法的積極作用。
(二)國內法
之所以要積極發揮國內法在規制海洋公共秩序方面的作用,原因有二:
第一,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管是條約規定還是條約化的國際習慣——存在許多模糊或漏洞,有必要加以澄清或填補。除了進行國際立法,國內立法也是澄清這些模糊之處的一種手段,在國際立法未能進行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即便這些國內立法根據隨后的國際立法是不適當的,甚至被諸如國際法院、國際海洋法法庭之類的國際裁判機構認定違反國際法,也不能當然地認為這些國內立法行為就是惡意的。換言之,除非違反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中的確定規定,一國制定的國內法包括著這些國際法沒有規定的內容,或者對于存在模糊之處的內容予以明確化,不能簡單地認為此類國內立法就是惡意的,甚至違法的。
第二,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缺乏足夠全面、有效的實施機制,因而它們授權主權國家通過國內立法實施國際法的規定。比如,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58 條第3 款的規定,沿海國可以“按照本公約的規定和其他國際法規則所制定的與本部分不相抵觸的法律和規章”。
不難發現,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許多海洋國家掀起了國內海洋立法的浪潮,在進入21 世紀后國內立法或立法籌劃活動更加活躍。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國內立法既是行使《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所賦予的權利,也是履行其規定的義務;既是維護當前的國家利益,尤其對抗損害其國家利益或違反國際法的其它國家所通過的國內立法,也可以在未來的國際法立法過程中占據主動。從海洋公共秩序的角度看,國內立法可以為未來相關國際立法提供重要的國家實踐。從國際法研究的角度看,比較國際法研究是歐美國際法學界新興的一個研究方向,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國家對于特定國際法制度的不同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比較海洋法應該構成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七、海洋公共秩序的規制方法
(一)規則創制
隨著國際共同體成員的增加、國際關系民主化的推進,以及一國對外事務透明度的提高,多邊國際造法——無論是條約造法還是習慣造法——變得越來越困難。多邊貿易體制的演進便是極富說服力的例子。自1948 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以下簡稱“關貿總協定”)生效以來,關貿總協定及世貿組織已經進行了九輪談判。不難發現,隨著關貿總協定及世貿組織成員方數量的擴大和議題的增多,每輪談判的時間也隨之越來越長,而于2001 年啟動的最新一輪談判——多哈回合歷經13 年后仍未完成。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修改與此類似。根據該公約第312 條第1 款規定,在該公約生效之日起十年期間屆滿后,締約國可以書面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對該公約提出不涉及“區域”內活動的具體修正案并要求召開會議予以審議。如果在秘書長分送通知之日起十二月內有不少于半數的締約國回復贊成該要求,則秘書長應召開會議。但根據第313 條第2 款的規定,該期間內如果有任一締約方反對所提出的修正案,則該提案應視為未通過。然而,迄今為止,并未有任何修改該公約的行動。
較之多邊立法大都無法啟動或未能完成,區域層次的國際立法則要活躍得多。以國際貿易體制為例,雖然多邊貿易談判陷于僵局,但近十多年來區域貿易協定急劇增加,國際貿易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已從多邊造法轉向區域造法。事實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也規定了區域造法機制。該公約第311 條第3 款規定:“本公約兩個或兩個以上締約國可訂立僅在各該國相互關系上適用的、修改或暫停適用本公約的規定的協定,但須這種協定不涉及本公約中某項規定,如對該規定予以減損就與公約的目的及宗旨的有效執行不相符合,而且這種協定不應影響本公約所載各項基本原則的適用,同時這種協定的規定不影響其他締約國根據本公約享有其權利和履行其義務。”實踐表明,晚近區域性的海洋造法已經取得不少成果,比如區域的反海盜協定、漁業協定等。
值得注意的是,晚近國際理論與實踐表明,81參見Joost Pauwelyn,Ramses A.Wessel &Jan Wouters eds.,Informal International Lawmaki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Ayelet Berman,Sanderijn Duquet,Joost Pauwelyn,Ramses A.Wessel &Jan Wouters eds.,Informal International Lawmaking:Case Studies,Torkel Opsahl Academic Epublisher,2012.國際規則創制不僅僅指產生明確國際法律權利和義務的行為,尤其如締結條約,也更多地包括雖然不會產生明確法律權利義務但可以為相關國家提供明確行為指南與規范的行為。的確,這種可以被稱為“軟法”實踐的現象自20 世紀70 年代后期起就引發了人們的關注,但晚近這種基于功能主義而非形式主義的實踐明顯增多。除了上述晚近正式國際造法所面臨的困難,海洋公共秩序的極端復雜性也使得更多非正式國際造法被運用,比如美國并無意于使其發起的“防擴散安全倡議”成為一個正式的國際條約。
(二)規則解釋
從相當大的意義上說,在國際造法難度趨于提高、效率趨于降低的背景下,國際法實踐的重心正從造法轉向解釋。這正是前文提及的一些西方國際法學者當前進行“比較國際法”研究的重要原因。解釋不僅有助于澄清既有國際法規則尤其是習慣國際法規則的含義,也可能促成新的國際造法,甚至本身就構成事實上的國際造法。由于海洋公共秩序的極端復雜性,近期內進行新的國際造法尤其多邊造法的可能性并不大,解釋在有關海洋公共秩序的國際法規則演進過程中的作用尤其需要受到關注。
規則解釋可以由多種主體在多個機制內進行,包括主權國家和國際爭端解決機構。首先,主權國家可以通過國內立法的形式進行解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300 條有關締約國善意行使權利和履行權利的規定、第301 條有關和平使用海洋的規定,以及第310 條有關締約國使其國內法與該公約相協調的規定,主權國家可以對該公約進行非常廣泛的解釋工作。其次,國際爭端解決機構通過裁判爭端進行的解釋。如所周知,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包括國際法院、WTO 爭端解決機構、國際投資仲裁庭在內的國際爭端解決機構的裁判實踐整體上都呈現出“司法能動”的傾向,這些爭端解決機構不僅直接地裁判爭端,而且通過裁判過程的法律解釋在事實上發展了國際法,甚至引起了主權國家的警惕。82參見Ingo Venzke,How Interpretation Makes International Law:On Semantic Change and Normative Twis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就裁判海洋爭端的國際性爭端解決機構而言,諸如國際海洋法法庭的案例數量并不多,但近年來逐步增加,并且日益涉及海洋公共秩序問題。因此,應當對諸如國際海洋法法庭之類的國際性爭端解決機構的法律解釋及其之于海洋公共秩序的影響引起高度重視。相應地,新興海洋大國應當加大對此類國際爭端解決機構的參與或影響,而非任之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新近警告有關國際司法機構應該“防止越權解釋和適用國際法,更不能罔顧客觀公正,借‘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國權益之實”是正確的。83《王毅:中國是國際法治的堅定維護者和建設者》,載人民網2014 年10 月24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1024/c1002-25903195.html。
八、結 論
由于海洋及其治理秩序的特殊性,準確理解海洋公共秩序對于一國在海洋事務中確立、維護以及提高話語權至關重要,對于新興海洋大國而言尤其如此。準確地理解海洋公共秩序必須借助于一般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否則不僅可能在海洋公共秩序方面出現理解偏差,更可能在具體海洋公共秩序問題方面出現對策偏差。誘發海洋安全關切既可能與行使海洋權利自由有關,也可能與行使海洋權利無關,各國在應對前者方面較容易達成合作,但在后者方面則不太容易達成合作。
迄今為止,海洋自由經歷了“壟斷自由”到“寡頭自由”再到“普遍自由”的變遷,這種變遷對海洋公共秩序的構成要素、觀念基礎、行為體結構、治理模式、規制方法等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壟斷自由”和“寡頭自由”時期的海洋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或者說只是基于個體主義的海洋自由,“普遍自由”的出現強化了共同體觀念,進而促進了公法性國際法規范的出現。一般來說,個體主義的海洋公共秩序對海洋大國是有利的,而共同體主義的海洋公共秩序對海洋大國則是不利的。中國等新興海洋大國要努力引領海洋共同體的構建,避免被置于海洋共同體的對立面。
在海洋公共秩序日益進入共同體的時代,海洋公共秩序中的行為體(包括海洋大國與海洋小國、既有海洋大國與新興海洋大國、公共行為體與私行為體)之間的關系都發生了重要變化。因此,中國等新興海洋大國尤其要準確地理解這些變化。
從治理模式看,較之陸地領域,實力在形塑海洋公共秩序方面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盡管如此,國際關系已經不可避免地邁向法治化,法治已經成為海洋公共秩序新的治理模式。較之既有海洋大國,中國等21 世紀的新興海洋大國在實現海洋崛起過程中不得不受到國際法治更大的制約,盡管法治可能被濫用。
從法律形態看,國際法并不能完全有效、公正地規制海洋公共秩序,在許多情況下國內法可以也必須發揮積極的作用。國內立法既是行使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所賦予的權利,也是履行其規定的義務,是澄清《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重要途徑;既是維護當前的國家利益,尤其對抗損害其國家利益或違反國際法的其它國家通過的國內立法,也可以在未來的國際法立法過程中占據主動。從海洋公共秩序的角度看,國內立法可以為未來相關國際立法提供重要的國家實踐。因此,中國等新興海洋大國必須高度重視國內海洋立法。相應地,中國有必要開展系統性的比較海洋法研究。
從規制方法看,規則創制的難度趨于增大、效率趨于降低,因此必須創新地理解規則創制,即規則創制不僅包括狹義的國際造法形式(即條約和習慣),也包括規定明確行動指南與規范的非正式造法。盡管如此,較之多邊性國際造法,區域性國際造法更具有可能性。與此同時,應當對通過國內立法和國際爭端解決機構裁判活動等進行的規則解釋之于海洋公共秩序的影響引起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