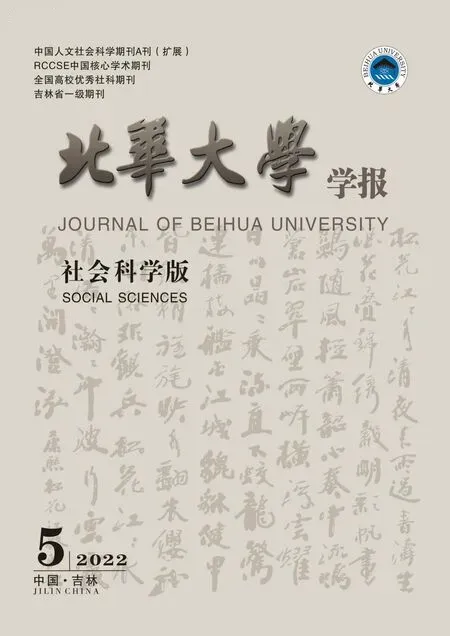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歷史與現實分析
許海云 尹 燦
眾所周知,自《北大西洋公約》訂立后,北約就一直被西方國家譽為全球最成功的集體防御組織,在維系歐美各國家團結協作、推動與華約軍事對抗等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北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提出,“與世界其他地區其他聯盟相比,北約極不平凡,《北大西洋公約》目前持續了半個多世紀,其成員國極為廣泛,在其存續期間幾乎所有成員國都給予廣泛的支持。”[1]到目前為止,北約擁有30個成員國,勢力范圍覆蓋了大半個歐洲,北約亦成為冷戰后世界最大的區域安全組織,并且還有向國際安全組織發展的趨勢。縱觀半個多世紀北約的發展歷程,該組織之所以在全世界為數眾多的聯合組織中脫穎而出,歷久彌新,其特殊之處就是北約擁有一套與眾不同的防御方針、安全戰略、聯盟架構以及指揮機制,確保其能夠在歐洲安全博弈中長久發揮作用,其中,又以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影響最為持久,因為北約所有的框架、戰略以及機制建設,無一不是在其集體防御方針的指導下完成。
深入研究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對于完整、系統了解冷戰時期的北約全貌,尤其是北約政治與安全戰略的特點與功用,可謂至關重要。“探究北大西洋公約的經歷并非只有歷史意義,人們也可以從北約的過去探知其可能出現的未來。”[2]雖然北約集體防御方針極為重要,但國內外學術界對這一課題的研究卻非常有限,目前并無專題性研究,只是在其他相關研究中對此有所涉及,缺乏系統性和完整性。(1)TUCKER R W,WRIGLEY L.The Atlantic alliance and its critics,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83;STEINBRUNER J D,SIGAL L V.Alliance security:NATO and the no-first-use question,Washington D C:Brookings Institution,1983;BAYLIS J.NATO Strategy:the case for a new strategic concept.International Affairs,1988,64(1);DUNN K A.In defense of NATO,The Alliance’s enduring value.Boulder,San Francisco & London:Westview Press,1990;MCINNES C.NATO’s changing strategic agenda,the conventional defense of Central Europe,London:Unwin Hyman Ltd,1990;YOST D S.NATO Transformed,The Alliance’s New Roles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1998。陳佩堯《北約戰略與態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朱立群《歐洲安全組織與安全結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邢驊、蘇惠民、王毅《新世紀北約的走向》(時事出版社,2004),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歐研究中心編《北約的命運》(時事出版社,2004),許海云《北約簡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陳宣圣《風云變幻看北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李海東《北約擴大研究(1948—1999)》(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高華《透視新北約:從軍事聯盟走向安全一政治聯盟》(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等。為此,本文將對冷戰時期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展開系統分析,總結并歸納集體防御方針的演進規律和特點,以此折射北約與歐洲安全態勢之間的互動。
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思想淵源及其塑造
1949年4月4日,歐美12個國家簽訂《北大西洋公約》。該條約第5條款宣稱:“各簽約國一致認可,對歐洲或者北美地區一國或多國的武裝攻擊,將會被認定是對所有簽約國的攻擊;這些簽約國一致同意,如果出現這種武裝攻擊,每一個國家將行使《聯合國憲章》第51條款所賦予的單個或集體自我防衛的權力;每個國家將單獨或與其他締約國一道采取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恢復并維持北大西洋地區安全。”[3]很明顯,上述內容雖不足以反映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全部,但卻反映了其中蘊含的諸多安全理念。
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并非成于天然,而是取自美國對戰后世界的安全認知,取自西歐國家的傳統安全理念,這些認知或理念有的源于歷史,有的則出于冷戰現實,互有交叉,相互影響,總體上可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第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取源于戰后初期西歐國家提出的集體防御原則,而這種集體防御原則直接源于歐洲歷史上的集體安全精神。眾所周知,歐洲除俄羅斯以外,大多數國家均規模較小,任何單一國家均無獨立建構歐洲安全秩序的綜合能力,歐洲在客觀上有奉行集體安全政策的基礎。從20世紀20年代起,伴隨德國法西斯主義興起,歐洲開始盛行集體安全理念,許多國家試圖通過多邊安全聯合確保歐洲和平。“集體安全是一個誘人的教條,但在20世紀30年代與并行不悖的共濟會夢想一起失敗了,這一夢想與值得贊美且理想化的、以廢棄戰爭為目標的‘凱洛格—白里安協定’有關。”[4]雖然二戰前歐洲集體安全實踐鮮有成功,但卻為戰后西歐各國推進集體安全聯合提供了寶貴經驗。
二戰后,歐洲集體安全思想回潮。由于西歐各國極度缺乏安全感,他們遂再度將實現集體安全視為謀求歐洲和平的一條重要途徑。1948年3月4日,西歐五國簽署《布魯塞爾條約》。該條約明確提出,“如果任何一個締約國成為歐洲武裝進攻的對象,根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款,其他締約國將向受攻擊的簽約國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軍事和其他援助”[5]。不僅如此,各簽約國還要在政治、經濟以及思想等領域保持一致,采取集體行動,共同威懾并挫敗針對西歐的任何軍事侵略或武力威脅。雖然西方聯盟的集體安全思想兼含防范德國東山再起、遏制蘇聯與東歐各國西來之意,但以集體防御來確保西歐安全這一思路卻為日后的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奠定了基礎。
第二,北約集體防御方針離不開戰后美國主導的區域安全原則,即區域性安全聯合以及“自助、他助與互助”安全模式。二戰后,美國成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憑借其超強國力在全球范圍內連續簽訂雙邊安全協定,包括各種相互援助協定、安全保障條約等,在全世界建立各種類型安全組織,北約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安全聯盟。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將許多區域安全理念訴諸實踐,將維護區域安全的路徑與設想貫穿其中,將其對戰后世界安全秩序的諸多考量融入其中,使美國能夠在各種區域安全協定與組織之上發揮引領作用。從表面看,北約似乎起步于西歐國家的倡議及其實踐,但在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醞釀中,美國實際上從始至終發揮著支柱作用。
因為早在1945年3月,美國就與其他美洲國家在墨西哥城查普泰皮克召開泛美會議,共同訂立“查普泰皮克議定書”(Chapultepec Protocol),加強美洲國家團結互助。該議定書強調,“對美洲任何一國的武裝進攻,將被視為是對其他國家的武裝攻擊。”[6]“查普泰皮克議定書”提出“一國即全部,全部即一國”(One is All,All is One)的安全理念,美國則將這一集體防御理念付諸實踐。1947年9月,以美國為首的美洲國家在里約熱內盧召開會議,訂立《美洲國家間互助條約》(泛美互助條約或里約條約)(Inter-American Treaty Reciprocal Assistance or Rio Pact)(2)《里約熱內盧條約》是美國與拉美18個國家訂立的集體安全條約。該條約規定,對任何一個美洲國家的侵犯,就是對所有國家的侵犯,每個締約國均有義務通過適當機構采取集體行動。該條約為美國在全世界推行區域集體防御提供了參照,為美國突破其現行法律與制度規定、參與歐洲集體安全建構提供了依據。。1948年3月,美洲國家在波哥大召開會議,正式建立“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簡稱OAS)。該組織同樣強調,“如果有簽約國遭受侵略,將采取共同行動;(簽約國)尋求政治、司法以及經濟途徑解決簽約國可能出現的問題,以相互合作來推動簽約國的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發展……”[7]美國雖然熱衷于建設泛美聯盟,但所屬意的美洲安全聯合卻不同以往,尤其強調區域安全組織內部平等,利益一致,共同擔責。美國的意圖就是突出區域安全組織在戰后國際安全秩序建構中的特殊作用,強調組織內部各成員國援助與被援助的關系。
第三,北約集體防御方針來源于戰后初期聯合國“大國一致”理念與區域自衛規則。眾所周知,美國在二戰期間設計聯合國(United Nations,簡稱UN),作為一戰后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簡稱LN)的替代,用于維持二戰后國際安全秩序,經美、英、蘇三大國協商,聯合國最終成為戰后國際安全權威機構。“美國公開提出,按照美國政府的觀點,聯合國表決程序包含兩個重要因素:第一,為了維護普遍和平,常任理事國必須全體一致;第二,對美國人民來說,非常重要的是,這一規定對本組織的所有成員國公平合理。”[8]顯而易見,聯合國在設立之初,就已確定一些基本安全理念,即大國在重大事項表決中必須保持一致立場;聯合國所有成員國一律平等,既要平等承擔聯合國的一切責任和義務,又要遵守聯合國的所有宗旨和規定。
1945年4月25日,來自51個國家的代表在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制憲會議,通過《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憲章明確設定聯合國的目標,即“保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聯合國將采取有效的集體措施,阻止和消除針對和平的威脅;制止侵略行為以及其他破壞和平的行為;以和平方式實現目標,按照司法原則與國際法,調整或解決可能破壞和平的國際爭端與情勢。”[9]聯合國將自身定位為國際集體安全組織,將集體安全政策與措施視為維持國際和平、解決爭端的主要手段。10月24日,聯合國正式成立,《聯合國憲章》各項安全理念得以訴諸實踐,開始得到越來越多國家或組織支持,最終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推崇的普遍規則。
不僅如此,在美國竭力主張下,聯合國還就區域自衛防御做了相關規定。《聯合國憲章》第51、第52、第53、第54條款明確提出,“如果出現針對聯合國成員國的武裝進攻,本憲章的任何規定都不會妨礙(成員國)單獨和集體實施集體防御的固有權利;在聯合國安理會采取必要措施、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前,成員國應將其在行使自衛權時所采取的諸多措施及時向安理會匯報;而且這些措施無論如何都不會影響安理會依據憲章而隨時采取行動時的權力與責任,此類行動注定對維持或者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是必要的。”[9]很顯然,美國對區域自衛權的種種設計,實際上是對《聯合國憲章》中區域安全理念的全面擴展,上述設計賦予各類區域安全組織以自由行動權,使其在遭遇安全危機時能夠及時實施“自衛權”。“第51條款帶有固有的自衛權,證明它與《聯合國憲章》相互兼容。”[10]事實上,北約正是通過這種安全理念的對接,在與聯合國保持政治和安全同步的同時,最大限度實現自身安全利益。
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思想內容極為豐富,并不止于某個具體的國家或組織,亦非局限于某種既定的思想框架,而是集多種思想要素于一身。除上文所提及的各種思想要素外,戰后初期美歐各國為適應美蘇冷戰而炮制的遏制思想,以及傳統的歐洲地緣政治理念,亦在北約集體防御方針逐漸凝聚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北約并不嘗試建立一個康德式或者威爾遜式的成熟集體安全體系,但北約支持源于集體安全傳統的各種觀念,特別是從18世紀起開始演變的傳統。”[11]21雖然所涉及的思想要素較多,參與者甚眾,但美國始終是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集大成者,因此一直對其擁有重大影響。
二、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基本內涵與表達
《北大西洋公約》簽署后,簽約國開始積極推動北約組織建設。1949年9月17日,各國在華盛頓召開峰會,正式建立北約政治與軍事架構。其中,頂層機構包括北大西洋理事會(North Atlantic Council,簡稱NAC)、防務委員會(Defense Committee,簡稱DC)、軍事委員會(Military Committee,簡稱MC),以及隸屬于軍委會的常設小組(Standing Group,簡稱SG)等,還有北歐區域計劃小組、西歐區域計劃小組、南歐—西地中海區域計劃小組、加拿大—美國區域計劃小組、北大西洋海域計劃小組等。[12]此后不久,北約還在軍事委員會下設立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簡稱SHAPE)、大西洋盟軍最高司令部(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Atlantic,簡稱SACLANT)、海峽司令部(Channel Command,簡稱CHANCOM)等,以及分屬于上述兩個指揮機構的次地區司令部與軍種司令部等。
正是通過這些機構,北約將多種安全概念、觀點與理論匯于一身,逐漸形成集體防御方針。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在表現形式上確實缺乏完整性和系統性,其基本理念大多體現在北約各項重大文件、政治決議與戰略方案中。概括而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第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強調戰略威懾與實力建設。軍事委員會在第14號文件第三稿修改案(MC 14/3)中強調,“北約防御概念的基礎建立在三個方面:一是采取聯合行動、保衛針對北大西洋區域免遭侵略的決心;二是擁有能夠有效反制任何層次侵略的公認的能力;三是擁有阻止潛在的侵略者的靈活性,使其預感到北約有信心對侵略行為做出特別回應,使其得出一個結論,即不管是何種性質的攻擊,都會招致無法接受的風險。”[13]作為北大西洋區域集體安全組織,北約既重視戰略安全威懾,又重視軍事實力建設,以此確使北大西洋區域避免遭受武力恐嚇或軍事入侵。軍事委員會在第48號文件中提出:“在未來北約武裝力量發展及系統化的計劃中,有一個重要且不能忽視的事實,即北約的主要目標是阻止戰爭,在這一目標中,北約在歐洲武裝力量中的作用就是必須實施有效威懾。”[14]對北約集體防御方針而言,戰略安全威懾與軍事實力建設是北約謀求北大西洋區域安全的兩個方向,對北約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同樣,北約亦強調“一國即全部,全部即一國”的安全理念,即所有侵略者都應了解,任何針對單個國家的武力威脅或攻擊,都會招致北約所有成員國的集體反制,侵略者將不得不承擔以一戰多、戰則必敗的結果。因此,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強調戰略安全威懾與軍事實力建設并重,實際上既是具備震懾各種威脅的一種能力,又是擁有應對現實武力威脅和侵略的一種有效手段。防務委員會在第6號文件(DC 6)中一再強調,“在和平時期協調我們的軍事與經濟力量,著眼對危及北大西洋組織各國和平、獨立以及穩定的任何單個國家或集團實施威懾;制定計劃,以備在戰時使用,使北約能夠組織各成員國聯合部署軍事力量,反擊敵方的威脅,保衛北大西洋組織各成員國的人民與疆土,保護北大西洋區域安全。”[15]
作為戰略威懾與實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核武器與常規武裝力量均在北約集體防御方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北約非常重視核力量建設與核戰略運用,目的是以最便捷的方式實現威懾效用最大化。“北約一直以核武器來阻止戰爭,并非在戰爭爆發時只以常規武裝為防御力量。”[16]與此同時,北約也非常重視常規武裝力量建設,通過不斷強化自身軍事戰略、常規武裝力量以及指揮架構,作為北約推進戰略威懾的重要依托。北約已經公開對外表示,對于可能的外來侵略,北約將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內的任何手段,削弱侵略國的力量,并對侵略國實施占領。[17]
第二,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強調在軍事上實施主動防御,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采取主動進攻。雖然北約名為防御組織,似乎只在北大西洋區域遭到武力威脅或侵略后才采取行動。美國新奧爾良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喬丹(Robert S.Jordan)持這種看法,“對北約的設計,并不是要使其成為一個維護和平的萬能機構,北約只是一個被設計用于抵抗或者挫敗侵略,以及追討戰爭責任的區域性聯盟。”[18]但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實際上強調攻防兼備,這種安全理念從北約防御部署中可窺一斑而見全豹。例如,北約一直強調,將在北約與華約邊界地區最大限度實施抵近式的戰略防御。“在區域計劃小組所設計的方案中,(北約的)目標是在德國盡可能最東邊地區阻止敵軍,在意大利盡可能最東邊地區、最北邊地區阻止敵軍,在北歐防御地區以外阻止敵軍。”[19]
這一前沿防御部署旨在形成某種步步為營態勢,在充分消耗入侵者綜合實力之后,再實施反攻。防務委員會在第13號文件(DC 13)中確定了防御、遲滯、反擊和擊潰華約入侵的階段性目標,提出分段、分級和分區實施從防御到反擊的應對之策,即“第一階段,抑制蘇聯最初的進攻,包括抑制最初的聯合空中進攻;第二階段,抑制蘇聯最初的進攻,共同采取重大進攻行動;第三階段,聯合采取重大進攻行動,直到蘇聯投降;第四階段,最終實現聯合戰爭目標。”[20]
北約在北大西洋區域采取軍事守勢的同時,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等領域則采取攻勢。其一,北約及其成員國在全世界大肆宣傳“民主與自由”理念、不遺余力推廣其道德觀與世界觀。例如,1969年,在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Nixon)提議下,北約成立“現代社會挑戰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Society,簡稱CCMS),應對全球危機,擴大自身影響。“‘安全共同體’的概念是:共同體的成員通過共同的價值觀和制度逐漸達到消弭成員之間戰爭的程度。由于北約的共同價值觀包括諸如個人自由、法治和文官治軍等民主價值觀,也可以認為北約成員國就是民主和平理論的例證。”[21]此外,北約還針對蘇聯與華約持續實施污名化,向東南歐各國施加影響,使之盡可能遠離蘇聯,不斷擴大華約內部嫌隙。其二,北約還利用經濟、金融、貿易以及科技等優勢,對華約及其成員國實施技術封鎖,經濟孤立,貿易限制,金融打壓等,以上述手段遲滯、削弱并且抵消華約實施軍事對抗的能力。很明顯,北約在軍事上強調積極防御,在非軍事領域實施主動進攻,兩者相輔相成,互相補充,這已成為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主旋律。
第三,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始終強調成員國團結協作。不論北約實施戰略威懾,追求強力威懾,還是實施主動防御,對入侵者后發制人,抑或推進實力建設,形成區域有效的防御力量,均離不開成員國的精誠合作。自《北大西洋公約》簽署后,北約就一直致力于維系聯盟內部團結,要求各成員國既要在軍事上相互配合、充分合作,又要在政治、經濟、思想以及意識形態上保持一致、共進共退,北約將推動各成員國協同與合作視為確保北大西洋區域安全的一項重要內容。“北約一直充當著保護傘,法國、德國和英國的政治—軍事以及經濟關系在其中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國家在300多年來一直是沖突的焦點,歐洲從1949年起一直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協同行動。”[22]2為此,北約為各成員國構建了一個全新的安全合作平臺,確保北約各成員國能夠按照統一的安全規則制定戰略、展開行動,并在其統一指導下開展合作。“一個盟國出于自身的個別原因,希望從(北約)特殊功能中撤出,但其他盟國可能會出于他們自身的原因而強化這一功能,不論這件事是否發生,這都可能是對(北約)‘安全共同體’的最好測試。”[23]
為了更好推進各成員國團結協作,北約一直致力于消除可能影響成員國合作的各種障礙。為此,北約特別強調各成員國平等互利,所有成員國共同分擔北大西洋區域防御責任,平等分享北約安全利益。即各成員國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分擔北約防務開支,確保各自的防務開支達到GDP2%的標準。當然,這只是北約及其成員國的理論考量,事實上大多數成員國始終未能達到防務開支規定的標準,美國一直承擔著北約的大部分開支,這種狀況一直延續至今。“美國為北約承擔了75%的防務開支,在冷戰時期承擔了50%以上。”[24]
與此同時,各成員國也須向北約派出武裝力量,由北約軍事指揮機構統一部署、訓練、演習和指揮。不僅如此,北約更致力于解決成員國之間的各種糾紛,以此加強內部團結。例如,北約參與解決希臘和土耳其對塞浦路斯的領土爭端,解決馬耳他的防御紛爭,協調各成員國對北約戰略決策權的不同要求,等等。此外,北約還通過各成員國共同承擔各種國際或區域安全危機的壓力,包括“柏林墻事件”“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等,統一各成員國的政治立場,協調其安全步調,以此顯示北約成員國的共同安全訴求。“北約以集體防御組織之名建立并且持續存在,就大國共識這個術語而言,北約被越來越多用于發揮集體安全職能。”[11]269
三、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特點與功用
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并非渾然天成,其思想內容伴隨著北約持續發展而不斷擴展、日漸豐富,其表現方式亦隨著歐洲軍事對峙局面日趨復雜化而不斷趨于多樣化。總體而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一直處于持續發展和變化中,這種變化和發展之勢幾乎貫穿整個冷戰時期,甚至一直延續到后冷戰時期。縱觀其發展全程,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變化并非隨意而行或者毫無章法,而是呈現出比較明顯的規律性特點,這些特點在整體上包括:
首先,北約集體防御方針是一種復合型而非單一化的指導方針,擁有多元化目標取向。這主要表現在,雖然北約在名義上一直致力于追求北大西洋區域安全,但其所設定的安全目標絕不僅限于保護成員國疆土安全,實際上也包括全力確保所有成員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以及意識形態等多領域安全。北大西洋理事會在其公報中公開提出:“我們的聯盟因而不能只關注北大西洋區域,也不能只關注軍事防御。北約必須按照相互依賴的原則組織其政治與軍事力量,必須考慮北大西洋區域以外地區的發展。”[25]就此而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看似目標單一,實則并未鎖定任何具體的軍事或者安全目標,而是指向一個極具冷戰意味的戰略目標。因此,北約所需防范的敵手并不止于華約或蘇聯,實際上還包括了所有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國家、制度、文化、思想以及意識形態,以及其他被北約視為背離或威脅其價值觀、政治與經濟理念的民族國家、思想觀念以及文化范式等。“北約的目標就是保護西方文明遠離外來力量,這些力量可能會挑戰其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價值。”[26]因此,這就決定了集體防御方針為北約及其成員國確立了一個漫無邊際的戰略目標,使北約的防御范圍覆蓋了包括北大西洋區域在內的更大區域,這一目標已經遠遠超出北約能力之外,導致北約長期深陷冷戰泥淖中無法自拔,使北約自身淹沒在東西方冷戰的漩渦中。
就此而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自身存在著某些無法疏解的邏輯矛盾與話語沖突,即北約雖一直以區域安全組織自居,但卻甘于承擔全球性冷戰責任;北約雖一直聲稱以防御安全為目標,卻行多方面挑釁和擴展之能事;北約雖一直致力于保衛北大西洋區域,但其武裝力量建設卻長期滯后;北約雖制定了多個防御安全方案,但卻從未有機會付諸實踐等。北約自己對此給出的解釋就是,“北約是一個防御聯盟,因此無需與華約展開槍對槍、炮對炮、飛機對飛機、坦克對坦克的對抗。北約必須保持一個足夠強大的態勢,這樣莫斯科就無法確定,憑借使用武力就能實現其政治目標。”[27]可以想見,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必然會受到上述矛盾的影響,其功用也必然為此大打折扣。
其次,北約集體防御方針是一種動態而非靜態的戰略指導方針。誠如上文所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在內容和形式上一直都處于發展變化中,這種變化不僅受到冷戰環境變化的影響,而且亦為北約自身發展規律所使然。前者源于戰后國際冷戰形勢的持續變化,北約為適應錯綜復雜的歐洲安全局面而不得不持續充實并擴展其防御思想,以此確保北約安全利益實現最大化。“(北約)已經證明將繼續發揮動態作用,即北約在歐洲安全治理中扮演一個關鍵組織的角色。”[28]后者則源于北約擁有一套比較穩固且系統的戰略思想、組織規則、運行模式以及利益表達方式,在安全戰略及其實踐中逐漸形成能夠自我修正、持續發展的內在規律,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實際上同樣為上述規律所驅動。總體而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呈現出某種正向發展態勢,即思想內容不斷豐富和深化,表現形式日趨復雜多樣,發揮功用的渠道不斷增多,其指導作用亦更具功效。
20世紀50年代,隨著美蘇冷戰趨于白熱化,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特別強調積極發展常規和非常規武裝力量,不斷發展并完善自身的軍事指揮體系。“(北約前歐洲盟軍最高司令)格倫瑟(Alfred M.Gruenther)將軍在1954年6月開列出處于不同程度戒備狀態的90個到100個師,他使這一計算數字和蘇聯武裝力量相比不會產生自卑感。”[22]61到了60年代,隨著東西方關系趨向緩和,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增加了緩和與對話等內容,雖然北約仍強調實力建設,但也強調合作與協商,甚至呼吁北約與華約實施均衡裁軍,美國與蘇聯建立軍備平衡,共同推動東西方緩和。
1967年12月,北大西洋理事會通過“哈默爾報告”(Hamel Report)。“北大西洋區域不能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區,北大西洋區域以外地區出現的危機與沖突,可能會通過直接方式或者通過掣肘全球平衡,損害北大西洋區域安全,因此北約盟國將會在聯合國內或者在其他國際組織內單獨為國際和平做出貢獻,或者為解決重大國際問題做出貢獻。”[29]由此可見,雖然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在基本方向上保持恒定,但是隨著國際安全環境的變化,該方針始終處于調整中。
再次,北約集體防御方針著眼于發揮長時段效用而非追求短期效應。北約集體防御方針融多種安全思想與理念于一體,集各成員國多方安全訴求于一身,所設定的安全目標也以戰略性和長時段的方向為主。因此,北約政治—軍事領導機構所做出的各項重大戰略決策,政治意義要大于軍事意義,理論意義要大于現實意義,這就決定了北約在集體防御方針指導下所設定的目標大多比較籠統,而且這些目標融合了政治、軍事、文化、思想以及意識形態等多方內容。北約前秘書長斯迪克(D.U.Stikker)曾對北約的目標做出描述:“北約并未威脅任何國家,它永遠不會實施侵略,它一直尋求消除戰爭以及戰爭理由。但是北約決心保衛其人民生活在自由中的權利,在當今世界,北約的團結與力量對于和平與自由生存極為重要。北約在道德與物質上的集體資源完全勝任這個任務,對其力量、人民意愿以及他們所堅持的理想滿懷信心,北約15個成員國決心重新投身于建立一個世界,可以遠離那個持續存在以及沖突不可避免的虛假教條。”[30]事實上,在集體防御方針的指導下,即使是北約軍事指揮機構所擬定的許多軍事防御計劃,也帶有相當多的非軍事因素。
北約對外須應對各種外來威脅與挑戰,確保北約在國際冷戰環境中占有一席之地;對內則須整合成員國力量,使之成為北約的綜合實力。很顯然,北約上述目標均非短期所能完成。正因如此,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功用最終大打折扣,不僅使北約在面對突發性危機時無法提出針對性較強的策略,而且也無法確保北約及其成員國全面發揮其安全戰略的應有功效。“共識是在幾個相關領域達成一致:(1)不論在公眾或者北約決策者看來,相對于大規模防御開支而言,華約對西歐發動蓄意軍事攻擊的威脅是一個靠不住的理由;(2)公眾仍支持北約保持其軍事力量,但相比對社會與經濟問題的支持要弱一些;(3)北約的長期規劃必須與降低武力層級相對應;(4)北約在未來十年的任務越來越多與對穩定的渴望、對政治變化的管控連在一起。”[31]由上可見,北約在整個冷戰時期一直在軍事上保持低調或者無所作為,其主要原因實際上更多出自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特性,而非北約及其成員國有意為之。
由上可知,北約集體防御方針所表現出的上述特點,預示著該集體防御方針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成效,只能放眼于長遠。在集體防御方針指導下,北約除制訂一系列軍事作戰方案外,還設計了一連串后勤支援計劃,例如,各成員國在維持穩定、實施軍演的行動中采取統一行動,全面實現情報與信息共享,就所有軍事物資與裝備制定統一的標準,針對武裝力量的維修設施與服務設施實施全面標準化,最大程度突破各成員國的法律制約以及行政限制等。另外,北約還動員各成員國按照其地理位置、工業能力、人口和軍事力量,將全部力量用于北大西洋區域防御。[32]由此可見,在北約集體防御方針指導下,其各項戰略、計劃以及方案大多著眼于對不同時段、地區以及領域發揮影響,其總體收效究竟如何,最終取決于北約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以及思想等領域的長期積累。
四、冷戰后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及其延續
縱觀整個冷戰時期,盡管北約曾在不同階段推出多個防御戰略,例如“前沿防御戰略”“大規模報復戰略”“靈活反應戰略”“劍與盾戰略”等,雖然這些防御戰略形式多樣、各具重點,但是它們所表達的政治與安全理念始終保持恒定,其基本目標與安全原則亦少有變化。“在北約的軍事安排中,雖然在戰術上、組織上以及其他領域均發生變化,但在1949年達成的基本認識卻從未變化。”[33]
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北大西洋區域傳統安全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大量非傳統安全危險風起云涌,恐怖主義、民粹主義、右翼政治、極端宗教運動等在全世界甚囂塵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擴散、國際海盜行為、全球能源安全、難民危機、非法移民、跨國走私、食品安全、氣候變化等層出不窮。與此同時,由于北約與俄羅斯競爭與對抗加劇,俄烏沖突持續升級,歐洲地緣政治沖突再起,包括北約在內,歐洲各個國家或組織都承受著巨大壓力。未來北約究竟應該走向何方?北約究竟會以何種方式確保其安全利益最大化?未來大西洋—歐洲能否確立積極有效的集體安全秩序?等等,這些問題已經成為北約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為此,北約大幅度調整其集體防御方針,以適應后冷戰時期國際安全形勢急劇變化的需要。1991年11月,北大西洋理事會在羅馬峰會提出“新戰略概念”(The Alliance’s Strategic Concept)。“北約繼續保持純粹的防御目標,確立其集體安全的基礎是統一的軍事結構、合作與協商協議,還有在不遠的將來實現常規力量與核力量適當搭配。使我們的軍事力量適應其新任務,規模變得更小,更具靈活性。”考慮到全球背景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及恐怖主義威脅,“北約將在更大范圍內推進合作”。[34]1999年4月,北約推出第二個“新戰略概念”,強調“北約的基本目標是維護歐洲—大西洋區域的安全環境,與盟國展開協商,對侵略威脅實施威懾和防御,其中包括危機處置、建立伙伴關系。”[35]2010年11月,北約推出第三個戰略新概念——“積極防御,現代防御”(Active Engagement,Modern Defense),即“北約將為實現統一和自由的歐洲而擴展,為應對各種威脅而與其他地區日漸連接在一起,北約將提高其應對挑戰的能力,并且為此實施結構改革,與外界展開合作,發展與伙伴國家的關系等。”[36]2020年11月,北約推出《北約2030:團結面對新時代》(NATO 2030:United for a New Era)。2022年6月,北約推出《北約2022戰略概念》(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這些戰略文件持續深化北約的戰略指導方針,不斷豐富集體防御方針的內涵。
此外,北約還提出其他許多新安全思想與理念,甚至包括許多非常具體的行動目標與方法,例如實施預防性危機處置、推動域外干預、發展綜合實力、構建伙伴關系等,這些思想與理念雖不足以構成一種新防御方針,但卻反映了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在冷戰后出現的新變化,亦折射出未來集體防御方針的發展趨勢,這些變化總體上可做如下概括:
第一,集體防御方針強調北約戰略轉型。冷戰結束,北約面臨政治與安全新變局。“隨著冷戰結束,整個歐洲—大西洋區域獲得一個能夠建立更完善安全架構的獨特機遇,此舉旨在向整個歐洲—大西洋區域提供更穩固的穩定與安全,并非重新制造分界線。北約將安全界定為一個廣義概念,包括政治、經濟、防御在內。新安全架構應以此廣義概念為基礎,通過歐洲現有多邊機制(歐盟、西歐聯盟、歐安組織)的相互作用而啟動統一與合作進程。”[37]為了掌控歐洲安全秩序建構的主導權,北約開始推進戰略轉型,由軍事防御組織向政治—軍事組織過渡。雖然北約并未放棄集體防御的基本職能,但其防范內容、范圍以及性質等均發生變化,北約不再發展單一軍事力量,而是著力發展綜合力量,特別是應急干預力量,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價值觀以及意識形態等在內。美國學者弗·阿恩·彼得森(Friis Arne Petersen)等人撰文指出,北約“綜合方法”包含了在危機與沖突處置中國際參與者的各個方面,當前安全挑戰要求在國家與國際層面展開合作,將民間與軍事資源結合起來,協調各種措施。[38]
盡管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在形式上多有變化,但其維護并擴展北約安全利益的根本目標始終沒有發生變化。在2014年9月威爾士峰會上,北約公開宣稱,“北約以團結、聯盟凝聚力、安全的不可分割性為基礎,為實現強大的集體防御而保持跨大西洋構架,為實現盟國的安全磋商和決策而扮演重要角色。”[39]在2022年6月北約馬德里峰會上,北約又重復了這一目標。可見,集體防御始終是推動北約政治與安全實踐的一面旗幟,是凝聚北約內部團結的一種粘合劑。
第二,集體防御方針強調東擴。1999年、2004年、2007年、2017年、2020年,北約連續五次東擴。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后,北約又公開宣布接納芬蘭、瑞典入盟,圖謀第六次東擴。在北約的東擴歷程中,北約確實考慮將格魯吉亞、烏克蘭等國納入其聯盟框架內,并且為此與兩國建立了密切聯系。很顯然,北約所追求的集體安全目標不僅是確保北約及其成員國的安全利益,而且是最大程度推廣其安全觀、價值觀以及世界觀。誠如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簡稱IISS)專家保羅·格布哈特(Paul Gebhard)所解釋的那樣,“為了滿足美國和西歐國家的重大利益,北約應該變成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聯盟,所擁有的能力不受地理與功能的限制。”[40]在北約看來,北約東擴就是要整合歐洲—大西洋區域力量,北約成員國的數量愈多,就意味著參與歐洲—大西洋區域集體安全目標的國家愈多,北約的集體安全也就會愈有保障。“北約東擴成為北約加強北大西洋區域政治統一與安全控制的一項重要內容。”[11]102-103
然而,東擴遇到俄羅斯持續抵制,俄烏沖突堪稱北約與俄羅斯對抗的最集中體現。很顯然,北約以東擴為導向的集體防御方針存在著巨大的邏輯矛盾。北約以犧牲俄羅斯戰略利益為前提,謀求北約成員國集體安全,這一方針不僅無助于歐洲—大西洋區域安全,還會直接將歐洲拉入地緣戰略沖突。
第三,集體防御方針強調預防性危機處置。鑒于后冷戰時期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普遍存在,尤其以歐洲為最甚,北約注重在歐洲安全秩序建構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再對各種安全威脅采取回避或忽視態度,而是選擇那些與北約具有重大利益關切的危機實施集體干預,介入的深度和廣度遠超以往。毋庸置疑,集體防御方針的歪曲,而是北約試圖在實踐層面進一步深化并擴大集體防御方針。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沙利卡什維利將軍(John Shalikashvili)曾很夸張地提到,“北約與波斯尼亞有重大關聯,如果我們不介入或軍事行動不堅決,北約就有可能垮掉,但北約通過采取行動終結了這些質疑。”[41]
事實上,北約在歐洲—大西洋區域內的干預行動體現了各成員國在政治立場、經濟力量、安全戰略上的統一,例如北約轟炸南聯盟。“北約仍然是全世界最能共同操作、最有效的多邊安全機構,即當危機來臨時,它能夠提供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和便利性。”[42]但是,北約針對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實施危機處置,并未得到所有成員國認可,這反映了北約集體安全目標與歐洲周邊危機處置之間尚存在較大距離,北約集體安全目標無法無限延伸,如果北約的集體防御方針施用得當,其凝聚力就會增強,反之亦然。“如果干涉行動得到認同,北約凝聚力就會強化;反過來,如果干預行動得不到認同,其凝聚力就會被削弱。”[28]
第四,集體防御方針強調伙伴關系和對外合作。北約在謀求東擴的同時,亦致力于構建伙伴關系。為此,北約連續推出“和平伙伴關系計劃”(Partnership for Peace,簡稱PfP)、“單獨伙伴行動計劃” (Individual Partnership Action Plans,簡稱IPAPs)、“地中海對話” (Mediterranean Dialogue,簡稱MD)、“伊斯坦布爾合作倡議” (Istanbul Cooperative Initiative,簡稱ICI)等,建立了為數眾多的合作國,按照不同層級推進雙邊安全合作或集體安全合作。
就像北約前副秘書長亞歷山大·弗什堡(Alexander Vershbow)所強調的,“北約盟國采取更強大的防御并非全部答案,如果我們想要聯盟安全,就必須使我們的鄰居更穩定。當前的問題是他們并不穩定,我們必須對伙伴國投入更多,支持他們有能力更好地保衛自己,限制極端勢力,給他們所在的地區帶來穩定。”[43]北約建立伙伴關系,目的就是進一步強化其集體安全目標。2008年4月,北約在布達佩斯峰會中宣稱,“北約單個行動無法成功應對今天的多種安全挑戰,北約將尋求與更寬泛的外部世界建立一種明確的伙伴關系……這種關系將建立在某種共識基礎上,即隨處可見的開放、合作和決心。”[44]
由上可見,集體防御方針已經變成冷戰后北約應對危機與挑戰、構建歐洲—大西洋區域安全秩序、穩固跨大西洋關系的一面旗幟,未來北約不僅不會放棄集體防御這面旗幟,而且還會繼續在集體防御的名義下強化其聯盟機制、組織功能、綜合能力、安全戰略等。非但如此,北約還會按照國際政治與安全形勢的需要,不斷充實和發展集體防御方針,使之更契合北約自身的新安全訴求。可以肯定,未來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在表現形式上將會更加靈活多樣,在內容上也會更加豐富和復雜,雖然許多安全理念或者政策會變得更細碎,但其對許多問題的指導也會更具體。
無可諱言,北約集體防御方針的功用在后冷戰時期會有所異化,北約將不再簡單恪守舊的集體安全傳統,包括實現集體安全的范圍、領域、對象以及屬性。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將會被進一步放大,單純的軍事功用將會下降,政治、社會、文化以及科技功用將會加強,尤其是其綜合功用會進一步凸顯。可以預見,未來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將會在注重短期效應的同時,也會重視長時段效應;在有效應對傳統安全威脅的同時,亦積極致力于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在重視歐洲—大西洋區域安全利益的同時,亦注重歐洲—大西洋區域以外地區的安全利益;既重視北約聯盟的內部合作,也重視北約與其他組織的對外合作;既注重發展北約的總體軍事實力,也注重發展北約及其成員國的綜合實力等。因此,未來北約集體防御方針將會持續發揮作用,繼續主導并推動歐洲—大西洋區域安全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