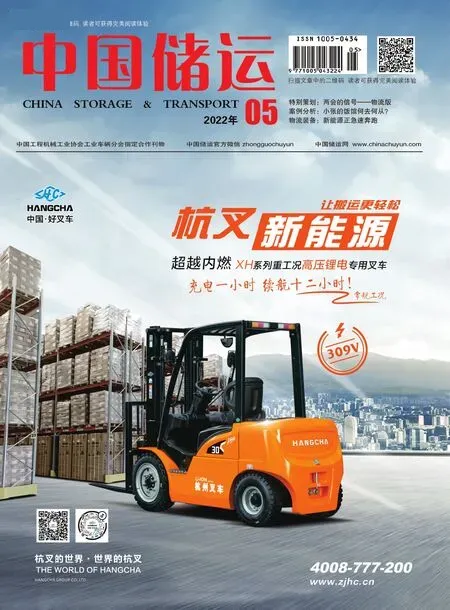大宗商品現貨交付中的貨權風險分析
文/毛靈超
大宗商品現貨交易有交易量大、交易金額大、流轉速度快的鮮明特點。交易過程中如未能嚴格了解并把控貨權風險,容易造成貨、款兩失,甚至對企業造成傷筋動骨的傷害。本文從法律規定及司法裁判角度,對大宗商品國內現貨貿易中比較主流的貨物交付方式進行分析,完善大宗商品貿易企業的現貨交易環節。
大宗商品通常指可進入流通領域,但非零售環節,具有商品屬性,用于工農業生產及消費使用的大批量買賣的物質商品,交易對象主要為原油、焦煤、鐵礦石、銅、棕櫚油、塑料粒子、液體化工等標準品。鑒于大宗商品體量大、兩端多為貿易商的行業特點,除直接進口、工廠直銷的情況外,一般均會涉及第三方倉庫,可以說大宗商品貿易流通離不開倉儲和物流環節。本文通過對大宗商品現貨交易主流的交付方式進行分析,以使大宗商品現貨交易模式滿足法律規定的各項要件,減少因貨權、風險轉移要件確實引發損失的風險。
一、大宗商品現貨交易中交付的主要類型
在大宗商品現貨的交易流通環節,根據進出口貿易和國內貿易兩種不同的交易類型,分成兩種完全不同的交付模式。進口貨物由于提單本身具有物權屬性,一般會通過提單的交付來完成物權轉移,而不是通過實體貨物的交割。國內貿易由于不存在提單這種代表物權的特別單據,其貨權和貨物實體一并轉移。國際貿易中的貨權一般跟隨提單流轉,其交付方式基本上與付款方式進行結合,常見的有信用證下的交單,銀行托收時的交單,直接寄付提單等。上述三種常見的提單交付方式中風險最大的為直接提單的寄付,這種交付方式對買賣的任何一方來說可能發生已付款但無法收到單據的風險,或提單已經寄出但無法收到貨款的風險,因此需要嚴格考察交易對手的自信情況。比較成熟且值得信賴的對手方才可采取此種交付方式。另外,還需注意無單放貨風險,這一風險的發生與貿易過程中的代理公司選擇、貿易術語、各國目的港政策、適用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相關,涉及風險因素多且復雜。因此了解目的地港口政策、考察國際貿易交易過程中各中間商,如貨代、船代的資信,完善整個交易流程的設計等都是風險控制的必要措施。大宗商品國內貿易中的交付,其交付主要存在自提、送到、轉貨權三種交付方式,同時還有相當一部分的見單付款、倉庫有條件放單、銀行有條件放貨等方式。對上述這些交付方式的風險控制,關鍵點在于控制錢與貨的關系,同時必須注意交付是否已經完全具備交付所需的全部要件。
二、國內現貨交易主要交付方式的風險分析
對買賣交易風險的分析與控制,首先需要區分貨物風險與貨權風險。貨權所指向的是貨物的所有權,權利人可以基于此權利提起物權請求或債權請求,而貨物風險所指向的是貨物毀損滅失風險,即需要解決的是標的物的毀損、滅失風險需要由誰承擔的問題。根據貨物風險承擔的一般原則,標的物的毀損、滅失的風險,在標的物交付之時發生轉移,即將貨物所有權與貨物本身作為一個共同體,貨權隨貨物轉移而發生轉移。這種合二為一的風險承擔原則為最常見的風險承擔和交付原則,適用于絕大多數國內的動產交易。
1.常規交付:自提與送到。自提和送到這兩種交付方式是根據交付節點進行區分的,均涉及到第三方運輸公司,其區別在于自提由買受人委托運輸公司至約定地點提取,送到為出賣人委托運輸公司送貨至買受人指定地點或約定的交貨地。以運輸方式交付的貨物,以交給第一承運人作為貨權及風險的轉移節點。若無其他約定,根據這一交付原則,自提模式下貨物交付應以貨物裝上運輸工具為節點,送貨模式下貨物交付以運輸工具到達交貨地點為節點。
2.返還請求讓與:轉貨權。如前所述,大宗商品現貨交易中倉儲公司是必不可少的參與者。除由生產商直發,國內的大宗商品流轉一般均在倉庫完成,且轉貨權是大宗商品現貨交易的主流交付模式。相較而言,自提和送到大多也涉及到倉儲環節,但由于貨物真實存在物理上的流轉,其所有權轉移的過程是比較明確的,而轉貨權是通過買賣雙方、倉儲公司之間一個單據流轉與確認的過程,對操作和文件完備性的要求更高。轉貨權,本質上來說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物權編第227條規定的指示交付,在第三人占有貨物情況下,負有交付義務的人通過轉讓請求第三人返還貨物的權利來代替交付。因此,轉貨權與簡易交付一樣,也是一種觀念上的交付,動產的實際占有并沒有發生轉移,仍由第三人實際占有和控制動產,出讓人與受讓人之間只是發生無形的返還請求權的轉移,即觀念上的轉移。返還請求權轉讓本身無法向外界展示物權的變動情況,物權的外在表征與真實狀態不相符合,因此其公示作用較弱,需要配合完善整套的交付要件才能防止出現因交付要件不完備引起的風險。中商華聯科貿有限公司與昌邑琨福紡織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表明,《貨權轉移證明》并不能起到轉移所有權的作用,買受人并不能憑《貨權轉移證明》實際提貨。該案事實為,買賣雙方簽訂了棉花購銷合同,交付方式為倉庫自提。買受人付款后,出賣人通過傳真將《貨權轉移證明》發送給買受人。此案中棉花所有權是否發生轉移,《貨權轉移證明》的效力認定成為關鍵。法院對于該份文件的效力認定中認為,根據雙方在購銷合同中約定的“辦理貨權轉移手續”、“買受人自行提貨”等表述,應理解為出賣人辦理完畢相關的貨權轉移手續后應將包括倉單、提貨單或者出庫單的權利憑證和相關手續交付給買受人,由其自行提貨。但結合出賣人與倉儲公司簽訂的《貨物儲運合同》,《貨權轉移證明》既非《貨物儲運合同》中所述的出庫單、提貨單,也并非法律規定的具有提取倉儲物性質的倉單,其不具有權利憑證的法律特征,因此認為《貨權轉移證明》不能實現轉移所有權的法律效力。該案說明,在轉貨權的貨物貿易中,出賣人履行交付義務,即其履行的擬制交付行為,一般為出賣人提供的交付文件,應當滿足權利受讓人可以自行提貨的全部必要條件,以完成交付貨物的合同義務。
3.指示交付是否需要通知實際占有人。在是指交付的情況下,其不以標的物的實際轉讓為要件。只要雙方約定生效,請求權發生轉讓,則物權不發生變動,便產生指示交付的效果。最高人民法院編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物權編的配套理解與適用,對于此問題的觀點為:雖然學界有不同的觀點,但是最高院認為,民法典雖然沒有明確規定讓與人通知第三人的義務,但在實際操作中,讓與人在讓與返還請求權之后,可以及時通知第三人,以防止第三人再將該動產返還給讓與人,導致交易過程復雜化;同時也便于受讓人向第三人主張權利時,第三人向受讓人履行義務。同時,通知第三人并非動產物權變動的生效要件,未通知第三人不影響動產物權變動的效力。如果第三人因未接到通知而將該動產返還讓與人的,讓與人應當將該動產及時交付受讓人。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實用版中對第227條項下的典型案例指引,所引用的肯考帝亞農產品貿易(上海)有限公司與廣東富虹油品有限公司、第三人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行所有權確認糾紛案中,法院裁判采用了間接占有財產出質時以書面通知占有人視為移交的精神,認為提貨單的交付,僅意味著轉移了提貨請求,在未將提貨請求轉移事實通知實際占有人時,提貨單的交付并不構成指示交付。上述案例的裁判觀點與最高院編寫的理解與適用存在相矛盾之處,但裁判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頒布生效之前,存在最高院司法裁判觀點的轉變可能。但企業在貿易過程中,出于謹慎和減少風險的考慮,對于指示交付,建議將通知占有人,也可以是請占有人確認作為交付完成的必備條件。另外,為完善轉貨權方式的完成,建議在合同中明確相關條款,比如以確認收到倉儲公司出具的入庫單,或者在倉儲公司的系統中確認貨主已經變更完成等作為貨權轉移完成的條件,而不是簡單地在合同中約定轉貨權,實際交付時只收到出賣人單方出具的提貨單、貨轉單等單據就視為交付已經完成。
三、結論:
貨權風險控制是大宗商品現貨交易的風險管理中最核心的風險之一,對其管理應通過交易對手管理、合同簽訂方式、條款審核管理、規范履行及出入庫管理等全套交易流程的規范化進行控制。大宗商品經營企業,在對貨權風險的控制中,應考量如何符合法定要求的交付。關注法條基本內涵和法院司法裁判方向是完善企業內部規范治理的重要途徑之一。
引用出處
[1]陳寰、林曉慧,《大宗商品貿易項下進口信用證業務的風險與控制——基于進口銀行的視野》
[2]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貫徹實施工作領導小組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物權編理解與適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50頁
[3(]2013)民提字第138號
[4]王利明《物權法研究》(上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57-358頁
[5](2010)民四終字第 2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