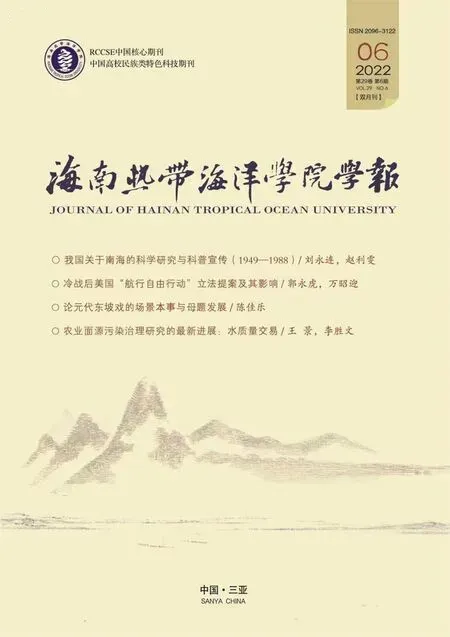元代東坡戲的場景本事與母題發展
陳佳樂,王 永
(中國傳媒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00)
元代產生一些以歷史真實人物為原型的雜劇,本文把蘇軾為主角的元雜劇稱為“東坡戲”,依據現存完整的三部東坡戲文本,探討場景本事與母題發展等問題。
一、 元雜劇東坡戲文本概觀
元雜劇中涉及蘇東坡的劇作共有六部:吳昌齡的《花間四友東坡夢》雜劇,費唐臣的《蘇子瞻風雪貶黃州》雜劇,無名氏的《蘇子瞻醉寫赤壁賦》雜劇,金仁杰的《蘇東坡夜宴西湖夢》雜劇,楊訥的《佛印烘豬待子瞻》雜劇,趙善慶的《蘇子瞻醉寫滿庭芳》雜劇。其中《花間四友東坡夢》《蘇子瞻風雪貶黃州》《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三部雜劇完整保存至今,其他皆已散佚。
《花間四友東坡夢》是元吳昌齡所寫的一部雜劇,共有四折一楔子,四折內容分別為:東坡誤入安石計,被貶黃州心不甘;東坡欲攜白牡丹,魔障佛印入紅塵;佛印巧設南柯夢,花間四友入夢來;夢醒方知一場空,東坡頓悟繁華世。蘇東坡因青苗法事件與王安石政見不合,王安石使計讓蘇東坡被貶黃州。東坡被貶之后心情低落,途經廬山,想起佛印在此處修佛,便想讓佛印還俗求取功名,二人一起在仕途上做出一番成就,于是便讓白牡丹誘惑佛印破色戒,結果反被佛印以夢化解,讓東坡頓悟塵世間的功名利祿,風花雪月皆為一場空。
《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乃元費唐臣所作雜劇,主要內容分為四個部分:政見不合引紛爭,介甫設局害東坡;東坡風雪貶黃州,正卿氣憤覺不值;虎落平陽被犬欺,生活拮據求太守;東坡拒絕圣上恩,愿做清閑自在人。蘇軾與王安石因青苗法政見不同,遭王安石忌恨,彈劾其賦詩訕謗,導致蘇軾最終被貶黃州。蘇軾風雪赴黃州,得馬正卿相迎,馬正卿惜其高才,處處關照。蘇軾攜家帶口生活拮據,上門求助楊太守,黃州楊太守乃王安石門客,不予幫忙反打其一頓,蘇軾看盡世態炎涼,后圣上回心轉意復召蘇軾回京,蘇軾拒絕皇恩最終歸隱。
《蘇子瞻醉寫赤壁賦》的作者不詳,雜劇共有四折一楔子,四折內容為:東坡醉寫滿庭芳,介甫一怒為紅顏;三相公長亭送別,東坡風雪赴黃州;蘇東坡夜游赤壁,與二友暢飲賦詩;邵雍辭世需碑文,東坡得借回朝堂。蘇軾與王安石為同窗好友,一日,蘇東坡應王安石之請前往參加宴會,在明知侍女之一為王安石夫人,依舊設計誆其露出手臂,席上醉寫《滿庭芳》調戲其夫人。王安石大怒,以東坡不知黃州菊花凋謝與調戲大臣妻子二事,奏請圣人將蘇軾貶上黃州。秦觀、賀鑄、邵雍長亭送別蘇軾,風雪日東坡艱赴黃州,被貶黃州期間與黃庭堅、佛印二位好友夜游赤壁,賦詩一首。后因邵雍辭世,圣人敕立碑文,因其家譜除了蘇軾無人知曉,蘇軾因此得借機會還朝再拜官。
二、 東坡戲場景本事考
《漢書·藝文志》載:“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1]本事最初是指原事,即某故事的原初事實。晚唐孟啟的《本事詩》序中則對本事的意義做了進一步的解釋:“抒懷佳作,諷刺雅言,著于群書。雖盈廚溢閣,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2]他認為,要想了解文本的真正意圖,就要了解其背后的故事。周裕鍇認為“本事”至少有兩個內涵:“一是指客觀上發生過的真實事件,一是指經人用文字記錄下來的事件。”[3]元雜劇現存的三部東坡戲,皆圍繞蘇軾被貶黃州這一核心事件展開創作并進行藝術加工和改編,其中還涉及蘇軾游赤壁、日常生活以及與佛印等人的交游事件。
(一)貶謫黃州及賦《滿庭芳》場景本事考
《花間四友東坡夢》中寫道:“安石將小官的滿庭芳奏與天子,道俺不合吟詩嘲戲大臣之妻。以此貶小官到黃州團練。就著俺去看菊花,誰想天下菊花不謝,唯有黃州菊花獨謝。”[4]349《蘇子瞻醉寫赤壁賦》第一折王安石云:“我到來日見了圣人說過,一者此人不知黃州菊花謝,二者趁此機會,將他貶上黃州,趁了小官之愿。”[5]741《蘇子瞻風雪貶黃州》第一折寫道:“〔駕云〕蘇軾,你職居近侍,何故托詩諷怨?本當處以重罪,張丞相再三申救,朕亦惜爾之才,赦爾死罪,謫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4]215三部雜劇所敘均為蘇軾被貶黃州事件。《宋史》記載: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并媒糵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鍛煉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筑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6]10809
《花間四友東坡夢》和《蘇子瞻醉寫赤壁賦》的第一折都提到了蘇軾在王安石舉辦的宴會上寫《滿庭芳》調戲其妻之事:
安石好生懷恨。一日朝罷,眾官聚于待漏院。……安石令俺為賦一詞。小官走筆賦滿庭芳一闋。誰想那女子就是安石的夫人。到次日安石將小官的滿庭芳奏與天子,道俺不合吟詩嘲戲大臣之妻,以此貶小官到黃州團練。(《花間四友東坡夢》)[4]349
此侍女中決有安石夫人。我著一個小伎倆,要賺出來。是好受用也呵。(唱)……(王云)蘇軾去了。叵耐此人無禮。某請你家宴,小官侍妾,淫詞戲卻,更待干罷。(《蘇子瞻醉寫赤壁賦》)[5]739-741
然而據史料記載,蘇軾寫《滿庭芳》一詞的契機并非在王安石舉辦的宴會上,而是在駙馬王詵舉辦的集會上。筆者考證發現,蘇軾于王安石所辦宴會上賦《滿庭芳》這一場景并未出現在具體的文字記載中,類似場景和事件卻在李公麟所繪的《西園雅集圖》中有所體現。李公麟的《西園雅集圖》中繪有蘇軾等16人聚會之景,劉克莊《西園雅集圖》跋云:
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世傳孫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釵墜之詞,想見一時風流醞藉,為世道太平極盛之候。未幾,而烏臺鞫詩案矣,賓主俱謫,而囀春鶯輩亦流落于他人矣。[7]
蘇軾所作《和王晉卿并引》云:“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功臣全斌之后也。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岡,而晉卿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晉卿亦還朝。”[8]1422《詞林紀事》:“西園雅集圖跋:此闋當在王都尉晉卿席上,為囀春鶯作也。”[9]因此,《滿庭芳》一詞應是蘇軾在西園集會上所作。元朝時期,除去這兩部雜劇中提及東坡寫《滿庭芳》之事,還有兩部雜劇中也曾提及此事。關漢卿《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雜劇第二折中〔賀新郎〕曲云:“呀,想東坡一曲〔滿庭芳〕,則道一個‘香靄雕盤’,可又早禍從天降,當時嘲撥無攔當,乞相公寬洪海量,怎不的仔細參詳?”[10]石君寶《諸宮調風月紫云亭》劇《雙調·新水令》曲云:“當日個為多情一曲《滿庭芳》,曾貶得蘇東坡也趁波逐浪。”[4]560關漢卿和石君寶都是元初期劇作家,也都曾提及蘇軾賦詞被貶黃州一事,這兩部雜劇雖未提及王安石夫人,卻又不約而同的提到蘇軾被貶乃是受宴會賦《滿庭芳》影響。可見,元代劇作家們并未采用《宋史》中的文字記載,反倒將蘇軾被貶黃州事件歸因于宴會賦《滿庭芳》一事中。因此筆者認為,元雜劇中涉及《滿庭芳》一事的內容,應都出自《詞林紀事》中西園集會典故,并受劉后村《西園雅集圖跋》和蘇軾所作《和王晉卿并引》的影響,而雜劇中蘇軾戲王安石妻之事,乃劇作家進一步虛構的結果。
(二)蘇軾夜游赤壁場景本事考
蘇軾夜游赤壁一事出自其所寫《赤壁賦》:“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11]5不過,《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蘇軾在寫《赤壁賦》時,全文并未提及陪同客者有幾人,直到清朝魏學洢的《核舟記》:“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為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12]才提到佛印與黃庭堅二人陪同蘇軾夜游赤壁,不過這也是魏學洢的一家之言。換言之,元以前,蘇軾《赤壁賦》中的客數仍有爭議,并無定論。此處應為作者虛構。
宋元之際的赤壁圖,最早出現的應是《東坡赤壁圖》,傳為王詵所作。元朝虞集的《道園遺稿》中錄有《王晉卿畫赤壁圖》一詩:“黃州江上霜月白,蘇子泛舟攜二客。”[13]根據此詩,可以推斷王詵所作的《東坡赤壁圖》中與蘇軾同游的有兩名友人。不過此圖已佚,未見真品。文伯仁曾說:“《赤壁后賦》,東坡真跡,舊傳吳匏翁家物。前王晉卿圖,后宋元人題跋甚多,今皆不存,豈轉徙散失故耶?東坡文筆固無容議,惟因此展玩,殊深慨嘆,后之收藏者,尤宜保惜。萬歷改元春三月,后進文伯仁書。”[14]628董其昌云:“東坡《赤壁》,余所見凡三本,與此而四矣。……文德承又謂此卷前有王晉卿畫,若得合并,不為延津之劍耶?用卿且藏此以俟。甲辰六月,觀于西湖上,因題。董其昌書。”[14]628從這些記載中可以得知,那個時期的王詵赤壁圖是有宋元人題跋的,應是當時比較知名的赤壁圖。
現存最早的赤壁圖實品是北宋喬仲常的《后赤壁賦圖》(見圖1),其中畫有蘇軾與三客和一船夫。

圖1 喬仲常《后赤壁賦圖》局部
南宋時期則以馬和之的《后赤壁賦圖》(見圖2)流傳較廣。圖中共有六人,船首尾應是船夫和侍童,中間有三人,畫的應是蘇軾及二客。

圖2 馬和之《后赤壁賦圖》局部
南宋楊士賢也有一幅《赤壁圖》(見圖3)傳世。畫中是以三人和一船夫為敘事中心。

圖3 楊士賢《赤壁圖》局部
南宋李嵩創作的《赤壁圖》(見圖4)是以團扇形制呈現,主要的內容也是蘇軾與客泛舟游赤壁場景。畫面中也是以三人和一船夫為敘事中心。

圖4 李嵩《赤壁圖》
金朝武元直也有一幅《赤壁圖》(見圖5)傳世,同樣也是三人一船夫的敘事場景。

圖5 武元直《赤壁圖》局部
明清之際亦有多幅《赤壁圖》傳世,由于本文以元雜劇的出現為作者認知終點,因此明清時期的《赤壁圖》不在本文討論范圍之內。
明朝胡應麟曾說:“前赤壁自白露橫江數語外皆議論,無可摹寫,后赤壁文簡于前而實景實情不啻十倍畫師,欲紆徐盈軸,自不能舍后而前也。”[15]這或許可以解釋畫家為何將畫中友人大多設置為二人。《后赤壁賦》云:“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11]8出于畫作的敘事需要,文人畫中的圖像應都參考了《后赤壁賦》中的設定。宋元之際,《赤壁圖》眾多,且流傳甚廣。元之前,只有南宋施元之曾提及與蘇軾游赤壁的友人:“先生為楊道士書一帖云:仆謫居黃岡,綿竹武都山道士楊世昌子京,自廬山來過余。……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東坡居士書。又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與楊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翅如車輪,嘎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不知其為何祥也。”[8]1115《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蘇軾所吟乃《前赤壁賦》,夜游赤壁時間為七月,此中提到的時間為十月十五日,所以此處記載應是《后赤壁賦》中的一客,而非《前赤壁賦》中的客人。宋元之際的赤壁圖,自南宋楊士賢的畫作之后,在描繪游赤壁一景時,主畫面已經形成一個固定范式,即船夫掌舵,蘇軾攜二友游赤壁。明清之際亦依照此范式進行創作,偶有改動,如仇英的《赤壁圖》中增添一侍童,但主畫面依舊沒有出“二客”范圍。因此,筆者認為無名氏的《蘇子瞻醉寫赤壁賦》雜劇中所設定為二友陪蘇軾夜游赤壁,應是受到《赤壁圖》的影響。
三、 東坡戲的母題發展
對于母題的定義,中國學術界多有爭議,并且出現了泛化現象。胡適將母題解釋為主題[16],樂黛云則認為母題是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人類基本行為、精神現象及周邊概念[17],張錯等人對于母題概念的解釋也更類似于主題或題材[18]。孫文憲在考察了相關母題理論后曾言:“母題必以類型化的結構或程式化的言說形態,反復出現于不同的文本之中;具有某種不變的、可以被人識別的結構形式或語言形式,是母題的重要特征。”[19]將母題當做題材之意已經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理論對母題概念的普遍性闡釋[20],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中國學者對于母題概念的本土重構。本文認為,母題是指不同文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某一要素,它可以是敘事文本中的某一人物,亦可以是某一程式化情節或事件。筆者提取三部東坡戲中所存在的母題,認為三部東坡戲中共有的母題有二:(1)以蘇軾為主角的人物母題;(2)貶謫事件母題。本文對于東坡戲母題方面的研究也緊緊圍繞這兩個母題進行探討。
東坡戲的母題發展經歷了一個原型重構的過程,劇作家對于蘇軾的人物形象和相關故事情節都進行了再創作,這種情節的取舍虛構和形象的變化也體現了雅俗文學融貫的動態過程和元代的時代精神。
(一)情節重構
三部雜劇中共有的貶謫情節,均圍繞王安石與蘇東坡的個人恩怨展開,其中《花間四友東坡夢》《蘇子瞻醉寫赤壁賦》兩本雜劇,又加入了蘇軾調戲王安石妻子的情節來加深王安石與蘇軾的矛盾,從而為后續蘇軾被貶黃州這一情節的發展作了充分鋪墊。略去劇中虛構的故事情節不提,筆者發現,元朝劇作家在撰寫東坡貶謫戲的過程中,刻意弱化了當時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將情節的主要矛盾歸結于王安石、蘇軾二人的私怨。
《花間四友東坡夢》第一折云:“王安石與俺為仇。……到次日安石將小官的滿庭芳奏與天子,道俺不合吟詩嘲戲大臣之妻。以此貶小官到黃州團練。”[4]349《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寫道:“我到來日見了圣人說過,一者此人不知黃州菊花謝,二者趁此機會,將他貶上黃州,趁了小官之愿。”[5]741《蘇子瞻風雪貶黃州》第一折寫道:“下官姓王名安石,字介甫。……獨翰林學士蘇軾,十分與我不合,昨日上疏說我奸邪,蠹政害民。我欲報復……我已著御史李定等劾他賦詩訕謗,必致主上震怒。置之死地,亦何難哉!計謀已定,且試看如何。”[4]211-212在這三本雜劇的第一折中,都將蘇軾被貶黃州事件歸結于王安石的私怨和推波助瀾,然而史料記載并非如此。當時王安石變法引起黨派之爭,王安石的改革遭到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蘇軾當時更偏向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一方,但這并不是其被貶黃州的直接原因。蘇軾是因御史李定、舒亶、王圭等欲置其于死地之人一手操辦的“烏臺詩案”才被貶黃州的,而此時的王安石已退居金陵,對蘇軾不僅沒有落井下石,而且還上書為蘇軾開解。
分開來看,《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情節重構較多,如:劇中邵雍告知蘇軾家譜一事,此事最終成為蘇軾還朝的契機;“東坡”名號出現在被貶黃州之前,王蘇二人的同窗關系,與黃庭堅、佛印夜游赤壁,皆為虛構。《花間四友東坡夢》中的東坡入夢以及勸佛印入世之事也是吳昌齡的再創作。《蘇子瞻風雪貶黃州》中蘇軾受到馬正卿的照顧和楊太守(王安石門客)的冷遇等,亦為作者加工創作的情節。
三部東坡戲中對蘇軾被貶黃州事件的重構更加注重敘事描寫,削減詩詞等傳統雅文學抒情的部分,文學作品趨向敘事功能。鐘嗣成在《錄鬼簿》中將元代文人共分為三類,其中“以文章為戲玩者”一類是他推尊的戲劇家,他說:“于學問之余,事務之暇,心機靈變,世法通疏,移宮換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為戲玩者,誠絕無而僅有者也。”[21]其中透露了一些信息:首先,開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元代文化為元雜劇的發展創新注入了新鮮活力,也誕生了新的創作群體;其次,元代科舉內容的“不平衡”性也導致了文人分流。“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22]2018元代尚實用而輕辭章的科舉偏好也影響了元代文人的文風。當仕途與學識已出現異途,文學開始回歸自身,文人創作傾向也逐漸世俗化,注重娛人,而蒙漢文化的沖突、交流、融合也進一步促進了元雜劇等俗文學的發展。
弗萊認為文學發展的動力源泉就在于文學原型的置換變形,文學原型會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受到當時的道德、藝術等時代因素而發生變形[23]。葉舒憲也根據弗萊的“置換變形”學說做出了推論:“文學的敘述層次是一個有規律可循的演變過程,文學內容的置換更新在很大程度取決于每一個社會和時代所特有的真善美標準。”[24]元代劇作家將一個擁有多重甚至復雜因素的事件簡化為個人恩怨的情節處理和虛構再創作歷史情節,筆者認為主要有兩點原因。其一,元雜劇雖盛行,然而當朝統治者并非毫不管制,任由其自然發展。《元史·刑法志》記載:“諸亂制詞曲,為譏議者,流。”[22]2685“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22]2651這種制度的出臺,迫使劇作家們不得不對史料進行加工創作和情節重構,以保證劇作能夠問世和出演,而這種做法也使得元雜劇更強調直觀的戲劇人物和情節的沖突。其次,元雜劇的目標群體是市民階層。李漁《閑情偶寄》云:“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不問而知為今曲,非元曲也。”[25]元雜劇的演出是一種面向市民群體的演出,如果想要吸引市民階層,或者說為了迎合市民階層的趣味,那么強烈直觀的戲劇沖突和生動形象的娛樂性則是必不可少的。
(二)形象重構
韋勒克、沃倫在《文學理論》中說:“一部文學作品的最明顯的起因,就是它的創造者,即作者。因此,從作者的個性和生平方面來解釋作品,是一種最古老和最有基礎的文學研究方法。”[26]榮格也認為“藝術實踐是一種心理活動,因而可以從心理學角度去考察”[27]。沃倫與榮格的觀念與中國本土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觀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強調作家、時代與作品之間的關系。
三部雜劇中蘇軾的形象各有千秋。《花間四友東坡夢》中蘇軾一心想要報國,認為登上仕途才是文人的出路。然而在佛印設計的南柯夢中與花間四友的歡情之景以及與其幾次三番的儒佛之辯中最終悟道出家,完成了從“俺如今領著白牡丹魔障此人還了俗,娶了牡丹,與小官同登仕路。量安石一人在朝,有何難處”[4]349到“蘇軾從今懺悔,情愿拜為佛家弟子”[4]371的轉變。《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蘇軾從一開始的輕狂,到被貶黃州游赤壁時的心態平和,再到最后還朝拜官的灑脫,人物形象是從狂到穩的轉變。《蘇子瞻風雪貶黃州》第一折中蘇軾的唱詞反映出其前期對于被貶黃州的憤懣:
【寄生草】臣則待居蠻貊,再誰想立廟堂。今日有曾參難免投梭誑。今日有周公難免流言講。有仲尼難免狐裘謗。本是個長門獻賦漢相如,怎做的東籬賞菊陶元亮?
【幺篇】臣折么流儋耳,臣折么貶夜郎。一個因書賈誼長沙放,一個因詩杜甫江邊葬,一個因文李白波心喪。臣覷屈原千載汨羅江,便是禹門三月桃花浪。
【金盞兒】不荒唐,不顛狂,折末云陽梟首高竿上,也要將碧天風月兩平章。拚著夢魂游故國,想像赴高堂。則今日傷心游海島,攜手上河梁。
【賺煞】則為不入虎狼群,躲離鯨鯢浪。直貶過淘淘大江,不信行人不斷腸。赤緊的接天隅煙水茫茫,助凄涼衰草斜陽。休想我筑起高臺望故鄉。這里有當途虎狼,那里有拍天風浪。我要過水云鄉,則是跳出是非場。(下)[4]215-216
到第四折,蘇軾的人物形象則從一個憤世嫉俗的文人轉變成了看透世態炎涼的隱士。《蘇子瞻風雪貶黃州》第四折寫道:
【雁兒落】臣寧可閑居原憲貧,不受夢筆江淹悶。樂陶陶三杯元亮酒,黑婁婁一枕陳摶困。
【得勝令】則愿做白發老參軍,怎消得天子重儒臣。那里顯騷客騷人俊,到不如農夫婦蠢。繞流水孤村,聽罷漁樵論。閉草戶柴門,做一個清閑自在人。[4]231
然而歷史上蘇軾被貶黃州并沒有元雜劇中所謂的出家、辭官或僅一載便還朝加官賜賞的結局。《宋史》記載:“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三年,權知禮部貢舉。”[6]10810-10812思想上,蘇軾雖然平生深受佛老思想浸染,但三次被貶期間依舊沒有放棄儒家思想研究,而是潛心修學繼承歐陽修未竟的事業,使“斯文有傳”[28]。蘇軾被貶黃州時期所寫的《定風波》,更彰顯了他不以時運為悲,不懼風雨,對人生厄運的斷喝[29],可見其并非會在被貶之后選擇隱退之人。仕途上,東坡在黃州待了四年之后才還朝,之后更是步步高升,甚至一度做到了翰林學士知制誥之位。
丹納認為種族、環境和時代是影響文學的三要素[30],作家在創作作品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時代和環境的影響。三本雜劇中的兩本都將蘇軾設定為最終出世的形象,僅有《蘇子瞻醉寫赤壁賦》中蘇軾最終重回官場。筆者認為這與元朝劇作家所處的時代有關系。元朝社會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將人分為四等,蒙古人地位最高,漢人、南人地位最低,并且元朝統治者極力打壓文人。《蘇平仲集》曾提到當時入仕文人的境遇:“例不過七品官,浮堪常調,遠者或二十年,近者猶十余年,然后改官。其改官而歷華要者,十不能四五;淹于常調不改官以沒身者十八九。”[31]《元史》也記載:“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22]2018而且元朝時期文人地位介于娼丐之間,地位非常低。《送方伯載歸三山序》記載:“‘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于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于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32]元朝文人地位低下,仕途無望,導致許多文人會產生一種心理落差和失落感,從而心態消極,厭世,不想與朝廷合作,轉而追求出世和隱逸。
結 語
吳昌齡的《花間四友東坡夢》、費唐臣的《蘇子瞻風雪貶黃州》、無名氏的《蘇子瞻醉寫赤壁賦》雜劇,是今存三本以蘇東坡題材為母題的元雜劇,皆來源于蘇軾被貶黃州這一歷史真實事件。其中宴會賦《滿庭芳》、東坡夜游赤壁,則分別源于李公麟《西園雅集圖》和諸多《赤壁圖》。筆者發現,宋元之際的文物圖像中,場景信息和元雜劇本事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系。宋元文人畫中的東坡場景,成為元雜劇這類戲劇中表現的場景。畫作本身帶有敘事和場景化的特質,元雜劇的場景本事所呈現的文學演變路徑為:雅文學——畫作——元雜劇,從中可以看出場景信息是連接傳統文學、繪畫與戲劇的橋梁。這種文圖遷移現象中,文學與繪畫作品所涉及的符號化場景,也為元雜劇本身的情節設置提供了來源。因此,元雜劇的文本內容會受到文學作品和繪畫作品的雙重影響。
元代劇作家基于貶謫這一母題展開創作,三位不同的劇作家對于蘇軾被貶事件的情節重構,主要基于玄幻和現實這兩個截然相反的色彩維度進行創作變形,一虛一實,殊途同歸。元以前的貶謫母題創作多集中于現實色彩的考量,直觀地抒發文人面對現實的無奈或不屈。至元,貶謫母題已從單一的現實色彩轉向多元的虛實結合。
《文心雕龍·體性》曰:“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33]不同的劇作家會對劇作中的內容進行不同的虛構和改動,切入視角和聚焦點亦不同。作品對事件的重構主要體現在弱化多重因素、強調單一線索、增強戲劇沖突以迎合市民階層的趣味。與此同時,作者虛構事件也強化了人物性格,增加了戲劇沖突,文本內容則從抒情轉向敘事。母題發展的多元性和戲劇性特征最終所體現的是元代雅俗文化的融會創新。對于人物形象的重構則體現出元代的時代風貌。作者基于對于元代社會現實的失望,而借用文本中的故事抨擊現實社會,追求一種超然、出世、灑脫的精神境界。三本雜劇從蘇軾被貶黃州事件切入,以夢幻、交游、世態三種不同的視角書寫,本質上還是為了反映社會現實,達到借古諷今的目的。有學者說:“正由于蘇東坡是這樣一位立體結構的偉大歷史人物,各個時期各個階層的各類人物似乎都可以在蘇東坡身上找到一個亮點,一個契合點,一種愉悅,一種慰藉。”[34]元代東坡戲也正是作者在東坡身上找到了某個亮點、契合點、愉悅、慰藉而結出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