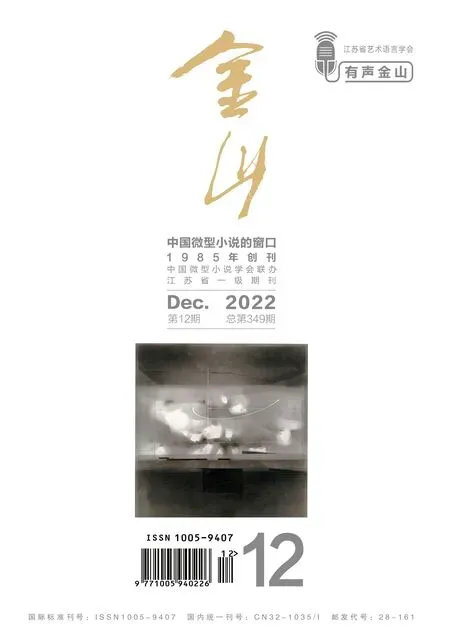二十年來常思君
——追憶“文學圣徒”高賢均
北京/李 昕
陶淵明曾作《挽歌》,詩中有云:“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說的是人去世了,會逐漸被友人淡忘,本是常情常理。但是,老友高賢均去世至今已整整20年,我對他的懷念卻有增無減,他的音容笑貌常在目前,以至我幾次在夢中與他對話。
當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文社”),高賢均是我最親密的伙伴。我們一同入職,一同成熟和成長。他擔任當代文學第一編輯室主任時,我是第二編輯室主任。他當總編輯助理時,我是社長助理。在人們眼中,他和我是陳早春社長兼總編輯的左膀右臂,是社里培養的兩個接班人,是“天生一對”,無法拆分。人們習慣地將我倆綁在一起,議論起來,基本是有高就有李,有李就有高。本來,我們應該是終生的“搭檔”,但后來我被調往香港工作,他留在社里擔任了“人文社”副總編輯。
記得那是2002年8月18日,我在香港接到“人文社”一位同事打來的電話,告訴我高賢均剛剛走了。他已罹患肺癌兩年,這消息并不突然,但我內心仍然深受打擊和震撼,悲痛至極。那位同事知我與高賢均相知甚深,便問我,社里委托他起草高賢均的生平,在遺體告別時使用,“你看最終應該怎樣評價他?”
我想,高賢均走時很年輕(55歲),從事編輯工作只有20年,這樣的編輯在老一代編輯心目中還只是年輕人。但是他論成就論貢獻,卻早已超過了許多老一代人。我覺得對他必須高度評價,所以說:“你一定要寫上,高賢均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新一代卓有成就的出版家和編輯家。”這句話后來成了官方定論,登在報紙上,令我欣慰。然而不久以后,我聽到陳忠實將高賢均評價為“文學圣徒”,感到這是文學家從另一個角度做出的點睛之論,可以和我的說法互補。
1982年,入職“人文社”的大學畢業生中有四個男生,高賢均、夏錦乾(后任《學術月刊》總編輯)、張國星(后任《文學評論》雜志社副社長)和我,曾被同在朝內大街166號大院里上班的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稱為“四大金剛”。但在這四個人中,高賢均是最出眾的。我們一同被送到校對科從學習圖書校對開始進入編輯角色,從最初接觸校樣那一刻我們就發現,高賢均對于編輯工作簡直就像有特異功能一樣。那時校對科實行評分制,逐月為每一位校對的“消滅錯誤率”(即查出排字或版式錯誤的百分比)打分,經過一段時間訓練,我和夏錦乾馬馬虎虎可以打上80分,張國星則是把心思用在給作者挑毛病上,校對只滿足于60~70分的成績。只有高賢均,校樣到他手里,好像錯誤會自動往出跳一樣,幾乎每次得分都在95分以上,令我們刮目相看。我那時就覺得,文化界喜歡把善于治學的人叫做“讀書的種子”,其實當編輯也有天生的種子,高賢均就是一個“編輯的種子”。
高賢均特別適合當文學編輯,也是因為懂創作。他在大學時期就發表過劇本和小說,而且閱讀涉獵極其廣泛。中外文學作品,凡是在國內有一點影響的,他幾乎沒有沒讀過的。這對他判斷文稿幫助極大。所以他審稿后給作者提修改意見,常令作者心服口服。這種能力使他在編輯部短短幾年就有很高威信。至于創作,他寫得的確不多,因為太忙,一年要看兩三千萬字書稿,平均一天七八萬字,實在顧不上寫。但他的中篇小說《七個大學生》在丁玲、牛漢主編的《中國》雜志發表以后,與我同在一個編輯室上班的文學評論家楊桂欣贊不絕口。他對我說:“從這篇作品可以看出高賢均背后的文學積累。在你們‘四大金剛’里面,數高賢均最有才能。”我說:“我們四個人的才能不是各有側重嗎?怎么能一概而論?”楊桂欣說:“你沒發現嗎?高賢均特別善于鉆研,他現在是搞當代文學創作,沒有進入其他領域,如果他搞別的,也一定成功。比如,他如果和你一樣搞文藝理論,恐怕就會比你強。”
楊桂欣這樣說,我是服氣的,相信他看人很準。因為我從一開始就發現高賢均身手不凡。他1978年考進北京大學時是四川省的文科狀元,當時他已經背過兩本詞典,即英漢詞典、俄漢詞典,上大學沒上過一天外語課。他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中學時代已經讀完《魯迅全集》。他的學識積累比我們都要早上很多年,他的文化修養著實讓我們佩服。我的直覺,他有條件成為一個很棒的作家或學者。
我很早就知道高賢均有一個作家夢。上世紀80年代中期,忽然有一天他說要寫長篇小說,腹稿都打好了。但是,他卻遲遲沒有動筆。因為他的時間和才華都用在編輯上了,“為人作嫁”,樂在其中,樂此不疲。后來他做過自我分析,說如果把編輯工作丟在一邊,自己埋頭寫作,他可以成為一個作家,但不會是很優秀的(這當然是自謙之語),但如果專心做編輯,他可以成為一個好編輯。他的結論是:“與其當三流作家,不如當一流編輯。”這后來就成了他給自己人生道路的定位。他很享受編輯工作,曾說:“我給作者提提意見和建議,幫助他們提高作品質量,其實也很有成就感。”
凡是與高賢均合作過的作者,對他的文學修養和編輯能力不僅認可,而且佩服。遠的不說,就拿我本人作例子吧。
我年輕的時候也喜歡寫些東西,曾經想嘗試各種創作。我不怕丟丑,寫了作品,總是第一個拿給高賢均看。我曾參考自己大學同學的一段經歷,寫了中篇小說《望盡天涯路》,描述一個既自卑又自負的青年人的心理悲劇。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說,寫的時候完全不知該如何落筆。高賢均看后,說情節很好,但是太平鋪直敘了。他提了兩條意見:一是要把結構打碎,把單線變為復線,把單向度時空變為交錯時空;二是告訴我,整部作品中,缺少幾個“彎”,就是可以調動讀者情緒的轉折性細節。“文似看山不喜平”,有幾個小小的轉折性細節,使讀者有出乎意外的感覺,就不平了。我按照他的意見修改了一遍,后來作品發表在《當代》雜志上,竟然還引起《新華文摘》重視,給予全文轉載。
后來我又寫了一個短篇名叫《七色光》,作品是寫一個經濟拮據的青年知識分子家庭,買不起彩色電視機,而當時北京電視臺天天播放的兒童節目名叫《七色光》,內容很好看,但這青年家五六歲的兒子不愿看自己家的黑白電視,天天往鄰居家跑看彩電,由此引起父親和兒子之間心理上的對抗。高賢均看了以后,認為故事的立意沒有問題,但是表達平庸。他對我說:“你和我是一樣的人,咱們的心理都太正常了,這樣是寫不出好小說的。你要把自己變成作品中的人物,他的性格中應該有一些怪異的因素,你就要把自己變得‘怪’一點,要發一些奇想才行。”他說,他自己寫小說,也常常需要“克服”自己心理過于“正常”的毛病。對此我極受啟發。后來這篇小說修改后,被臺灣作家郭楓看重,發表在臺灣的《新地》雜志上。
至于高賢均在編輯出版中發現好作品和幫助作者修改書稿的故事,那就實在太多了。他是一個永遠可以給我信心的人。我剛開始擔任編輯室主任的時候,他曾經是編輯室副主任,遇到長篇小說、報告文學作品,凡是拿不準的,我一定會問他。記得有過很多次,我和他一起同作者交流,只要有他在,我就以他的意見為主,因為他的意見總是更加專業,且更加系統。他曾經支持過很多別人并不看好的作品在“人文社”出版,這正是顯示他的眼光和水準的地方。例如麥天樞廣受贊譽的獲獎長篇報告文學《昨天——中英鴉片戰爭紀實》,最初由我交給一位曾經創作過報告文學的老編輯審讀,沒想到他提出完全否定的意見,主張退稿。這時我向高賢均求援,請他幫忙判斷。結果高賢均卻大聲叫好,認定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令此稿起死回生。后來我特地做了這本書的責任編輯,還為其作序并熱情推薦,實話說,我的底氣,一半來自高賢均。另一個例子是云南青年作家鄧賢的獲獎作品《大國之魂》,內容新穎、史料豐富,但因為作者沒有寫作經驗,書稿結構很不成型,題材也稍微敏感。接手書稿的《當代》雜志內部爭論很大,有人要用,有人要退,最后一直弄到社領導分出兩種意見。后來是社長找到高賢均和我,我們都寫了肯定性的意見,同意這本書做一些修改后出版。我清楚記得高賢均當時讀到鄧賢作品時滿臉興奮的神態。他對于鄧賢以微觀和宏觀相結合的視角描述抗戰時期滇緬戰場的情景是極為贊賞的,認為此書是填補當代文學空白的力作,并預言此書會引起很大社會反響。出版后的事實證明,他的判斷完全正確。
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是藏族青年作家阿來的《塵埃落定》。這部后來好評如潮并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品,投稿和出版之路卻極其曲折。1994年完稿以后,阿來四處投稿,卻經歷了多家出版社數次退稿。客氣的答復是給作者寄一封退稿信,那不客氣的,就是書稿石沉大海。退稿的原因,想必是出版社對這位無名作者沒有信心,不看好市場。直到四年后的1998年,“人文社”編輯腳印拿到了書稿,事情才有了轉機。腳印喜歡這部作品,但是她需要得到領導的首肯,于是把稿子轉給時任副總編輯的高賢均。高賢均當時正在患病休養中,但他很快看完稿子,情緒激動地打電話對腳印說:“我是真喜歡這部作品!我等了很多年,咱們四川終于等來了一個會寫小說的作家!(高賢均和腳印都是四川人)這本書咱們出版,你一定要好好編。”于是一錘定音。《塵埃落定》以急件安排出版,除了獲獎以外,還成了暢銷書。


“人文社”是出好書的地方,但是好書要有人識,有人編,有人拍板。好書的背后,總有人默默奉獻。高賢均是這家出版社當代長篇小說出版的重要參與者和決策者之一,堪稱幕后英雄。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大批有影響力的當代文學優秀作品的編輯出版,從《大國之魂》《中國知青夢》《活動變人形》《紀實和虛構》《南渡記》,到《白鹿原》《塵埃落定》《歷史的天空》《日出東方》《狂歡的季節》,以及風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等等,都與高賢均有關。關注中國當代文學的人會懂得,這一串書單的分量有多重,它意味著什么。有人對我說,高賢均就是在深夜審讀《哈利·波特》校樣的時候,吐出第一口血,從而被確診為肺癌的。原本作為副總編,他根本不必去理會什么校樣,但是他的責任心驅使他親力親為。在上述所有圖書中,高賢均有時是責編,有時是審稿人,有時參與出版策劃,有時是決策人。總之他作為幕后推手,時時顯示出獨具的眼光、魄力和膽識,以及豐富的編輯經驗。
我以為,高賢均能夠有這樣奪目的業績,不僅基于他的文藝修養,而且基于他對出版事業的摯愛,和他對編輯工作的一種燃燒的激情。
他去世后,大家懷念他,有很多同事和作者寫了文章,發表在《當代》雜志上。我把那本雜志找來看,發現大家想起高賢均總會回憶起同一個場景:大家都記得他每天中午端著盒飯這個屋聊一會兒,那個屋聊一會兒,聊的都是看稿子的事。他這個人,日復一日地看稿子還總是那么興奮,一有新發現馬上跟別人分享。我至今都記得他給我講的兩個細節。
有一次高賢均看了阿城的《樹王》,跑來告訴我說,阿城寫樹的細節是自己過去沒有觀察到的。作品描寫的是巨大的樹,寫風從左邊刮過來,樹葉就從左邊開始抖動,然后到中間,再漸漸波及到右邊,樹的抖動不是呼啦一下展開,而是有層次、有波浪的。高賢均說,阿誠的觀察多么細,他原來沒注意過,看了阿城的文章后才有意識地去看,果真如此。還有一次,高賢均讀了《白鹿原》書稿,很興奮地跟我說,你快去看看“黑娃吃糖”是怎么寫的。作品中黑娃是個苦孩子,長到十幾歲從沒有吃過糖,當有人給他一塊冰糖時,他不知是什么東西,以為是石子。當他把冰糖放進嘴里,他愣住了,從來沒想到世上還有這樣神奇的滋味,從眼珠到整個身體頓時就不會動了。這里,作品對黑娃表情的描寫簡直是一絕,寫他竟然渾身顫抖,繼而哇哇大哭。嚇得別人以為他的喉嚨被卡了,慌忙掐住他的腮幫,要幫他把糖向外摳,其實他那只是幸福的表現,他被那甜甜的味道震撼了。高賢均說,這個細節寫得太精彩了,從這個細節就可以看出陳忠實的功力。
那時,每天中午我們和高賢均一起吃飯,總是聽他講這些。我覺得他真是激情滿滿,沉迷于書稿,沉迷于文學作品,全情投入,入戲很深。
關于高賢均以激情編書的故事,有兩個很好的事例,我曾多次在高校和各大出版集團開設的編輯學課程中當作案例。
一是關于《白鹿原》,我要說說高賢均在這本書出版中的作用。《白鹿原》書稿,是“人文社”副總編何啟治早早約定的。他從上世紀70年代前期陳忠實剛剛寫過一兩個中短篇開始,就發現了這位作者的創作潛能,建議作者寫長篇。但陳忠實直到20年后才完成這部巨作。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天,陳忠實通知何啟治,可以交稿了。正好此時,高賢均和《當代》編輯洪清波要到成都出差,何啟治就說,請你們順路去一趟西安,陳忠實有稿子,你們先看看。于是高、洪二人去西安見陳忠實。
我看到當時情景的有關記錄是這樣:陳忠實拿出的書稿是手稿(那時沒有方便的打印條件),40萬字的書稿很厚,他把稿子包了又包,裹了又裹,里面是牛皮紙,外面是塑料袋,打成一包,很鄭重地交給高賢均和洪清波。然后他說:“我這是把多來年的心血托付給你們了。”高賢均當時要打開,陳忠實慌亂地說:“你不要打開,你不離開這里不能看。”我猜想,其實陳忠實是心里害怕,擔心用六年時間寫出的成果不被承認(作者在這種時候很緊張,像接受考試一樣,壓力山大,這是正常心態)。要知道,陳忠實在家里六年悶頭創作《白鹿原》,除了這本書稿以外,其他創作很少。他在此之前沒有寫過長篇,中短篇也沒有太大的反響,所以他老婆不斷譏笑他,說他還不如開養雞場,養雞還可以指望吃幾個雞蛋,而他這些年什么都沒有得到。所以陳忠實曾經跟老婆說,這部作品不成功他就開養雞場。他是把這輩子命運的寶,都押在這本書上了。
高賢均和洪清波拿到稿子后馬上坐上去成都的火車,一上火車就開始看稿。高賢均和洪清波一起輪著讀,到了成都又利用會議間隙讀,還沒回北京,兩人都把稿子讀完了,工作如此神速,顯示了編輯的激情和敬業。回到北京后,高賢均第一時間寫了一封信給陳忠實,說這是一本在中國當代文學歷史上注定要留下一筆的書,是他看過的中國當代長篇小說中最有分量的一本。陳忠實后來回憶說,高賢均拿到稿子只十天就給他來信,這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當時沒有電子郵件,也沒有快遞,一封信就要走幾天,而高賢均又要開會又要趕路,居然有這么高的效率!陳忠實也沒想到高賢均的評價這么高。收到信后他欣喜若狂,猛地翻身從沙發上跳起來。他對老婆說:“我不用開養雞場了!”后來高賢均和洪清波做了這本書的責任編輯,《白鹿原》獲得了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最高評價——茅盾文學獎。
另一個令人驚嘆的故事,就是徐貴祥的《歷史的天空》的出版。這部書稿在到達“人文社”之前,也曾被兩家出版社退稿。作者徐貴祥寫了一篇文章回憶此事,說他曾經想把這稿子一把火燒了,從此不寫了。結果就在心里很矛盾的時候,他見到了“人文社”《當代》雜志的編輯,提到了這部稿子,那位編輯說愿意拿回去看看。過了幾天,徐貴祥打電話問編輯:“你覺得怎么樣?”編輯說:“說不好,我一個人看怕判斷不準,轉給小說組編輯也看看吧。”于是稿子就被轉給“人文社”小說組另外一個編輯。這位編輯看完后,作者去電問:“你覺得怎么樣?”那位編輯也說:“拿不準,還是給領導看看吧。”這樣稿子才到了高賢均手里。高賢均在一周后直接給徐貴祥打電話說:“請你來,我要跟你面談。”
“人文社”副總編直接找他面談,把徐貴祥嚇了一跳,因為當時他還是沒什么名氣的作家。后來作者在回憶文章里描寫了他到高賢均辦公室后的情景:
高賢均高度評價這部書稿,他當著幾個編輯和作者,“激情澎湃、神采飛揚,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坐下去,雙手舞動著講了一個多小時”。這讓他感覺到自己幸運地遇到知音了。關于稿子里涉及的國共關系的敏感話題,就是前面說到有些人拿不準,有些出版社因此而退稿的那些內容,高賢均提出了一些具體修改意見,可以說是秘授機宜。作者說,其實高賢均提的都是些非常巧妙的處理方法,四兩撥千斤,操作起來一點不困難,作者當即表示完全接受。最后高賢均做了總結,對作者說:“你就照這個方法改,改完以后我給你做兩個預測:第一,這本書可以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第二,這本書參加‘茅盾文學獎’評獎很有競爭力。”后來的事實證明這兩個預測全都正確,這本書出版后一共獲得四個大獎:“解放軍文藝獎”“五個一工程獎”“茅盾文學獎”“人民文學獎”。試想一下,兩個出版社退稿,本社也有一些編輯拿不準的書稿,到高賢均手里變成這樣,不是化腐朽為神奇嗎?
“人民文學獎”評獎的時候高賢均已是肺癌晚期,距他去世只有兩三個月,但他作為評委,堅持從醫院趕來開會,上臺講了20分鐘話,介紹《歷史的天空》。后來作者提到這件事非常感動,他說一想起高賢均就流眼淚,還說對高賢均他無以報答。“人文社”的編輯就跟他說,你要想報答高賢均,今后有好稿子就都交給“人文社”吧。作者就承諾說:“好。”我以為,這純粹是高賢均以自己對文學事業和對作者的一片赤誠換來的。說他是“文學圣徒”,信然。
2012年8月18日,高賢均去世10周年時,作者們來到他的墓前。墓碑的題詞是作家阿來所擬:在人間編好書;去天堂聽妙音。特別要說明,高賢均是一位古典音樂超級愛好者。
高賢均去世20年了。“不思量,自難忘”。我今天在這里追憶他,因為我感到他的名字是值得出版界同仁永遠銘記的。他身上的那種執著、勤奮、充滿激情的敬業精神,理應得到后來者的繼承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