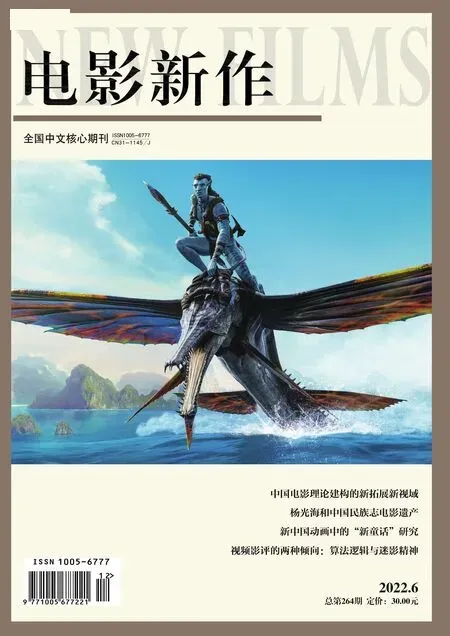心靈紀錄片:安諾斯·厄斯特高電影中的自我、認知與想象
伊卜·邦德比約/文 劉宇清 趙仁悅/譯
傳統的紀錄片理論傾向于認定(心靈紀錄片)這種類型屬于比爾·尼科爾斯所謂的“清醒話語”1,亦即,它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真實的直接呈現而非虛構,它是交流/傳播的一種修辭形式,是關于世界的理性論證。然而,盡管修辭結構、論證和直接運用來自非虛構空間的素材,都是區分紀錄片和虛構電影的重要依據,但大多數關于紀錄電影類型或模式的理論研究,包括尼科爾斯的《紀錄片導論》(2001),也承認其復雜性、變異性和創造性的維度。自尼科爾斯發表開創性的《再現現實:紀錄片中的問題與概念》(1991)以來,普遍的紀錄片研究不斷延伸到新的方向。盡管如此,關于紀錄片的認知理論仍然相對局限。筆者希望在本文中展示和證明,紀錄片如何深受情緒/情感結構和敘事結構的影響,它們如何給予我們現實的影像,我們具身的心靈和自我如何對紀錄片的制作和接受發揮作用。
認知電影理論對紀錄片的關注遠不及虛構電影,不過,卡爾·普蘭廷加(Carl Plantinga)的著作《非虛構電影中的修辭與表現》(Rhetoric and Representation in Nonfiction Film,1997)是一個關鍵的起點。他擴大了修辭的概念,使之涵蓋他所謂的“非虛構話語的豐富性、復雜性和表現力”。通過界定紀錄片的不同語氣(正式的、開放的和詩意的),并且引用約翰·格里爾遜對紀錄片的著名定義“對現實的創造性處理”,他開辟了一條道路,不再將紀錄片視為一種統一的話語或者再現現實的特定模式,而是一種呈現世界的方式,可以采取各種不同的形式。實質上,他的論證試圖將紀錄電影分析與經典理論區分開來,經典理論聲稱故事和想象是虛構作品的核心,而紀錄片僅僅是關于真實世界的修辭論證。2
然而,這種經典理論的基本問題根深蒂固。正如近年來的認知電影理論、情緒理論、敘事理論和隱喻理論所揭示那樣,在我們思考和體驗世界的各種方式中,情緒(感性)和理性是深刻關聯的。因此,敘事和想象不能簡化為虛構的元素;它們體現在人們對自我、他人和整個世界經驗之中。3情緒在推理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們對情緒的懷疑,或者對情緒不屑一顧的態度,加劇了神經學家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所謂的“笛卡爾的錯誤”,即西方思想中普遍存在的一種誤解(misconception)。4達馬西奧聲稱,我們的自我意識和解讀世界的能力都建基于情緒結構和敘事結構,正是這些結構搭建了自我的“舞臺”。因此,敘事結構不僅關聯到虛構的交流形式,而且是我們思維和想象的構成部分,是一種“內在福爾摩斯”的進化結構。5
喬治·萊考夫(G e o r g e Lakoff)和馬克·約翰遜(Mark Johnson)的研究,同樣動搖了人們對理性支配心理過程的信念。他們運用認知語言學來證明隱喻在語言和推理中的作用,認為思維創造的隱喻結構與身體和心靈都具有根本性的聯系。根據萊考夫和約翰遜的研究,隱喻屬于具體的范疇,思維的基礎是身體和心靈之間的神經連接。盡管他們的研究屬于語言學,但他們理論的重點是與我們說話方式和思考方式相關的意象圖式(image schemas)——感知世界并且將詞語和意義域關聯起來的具體方式。結果,具體的意象圖式,同樣影響了科學和哲學,影響了我們思考和論證的基本方式,駁斥了客觀性和主觀性對立的神話。6
因此,萊考夫和約翰遜的隱喻理論奠定在具體的認知定義之上。他們從三個方面描述了他們所謂的“原初隱喻”(primary metaphors):
1.它們是通過對世界的身體經驗體現的,身體經驗將感覺運動過程與主觀經驗相結合;
2.它們的源域邏輯來自感覺運動體驗的推理結構;
3.它們的神經實例是與神經連接相關的突觸權值(synaptic weights)。
兩位作者證明了整個初級的和復雜的隱喻系統如何構成了我們認知無意識的一部分,例如思考和談論“愛”,會產生豐富的認知經驗、情緒經驗和具身經驗,而這些經驗的產生,往往是下意識的。正如他們所言,“去掉那些將愛進行概念化的隱喻方式,就沒有什么了。”7
一、紀錄片與情緒社會學
最近,關于電影(尤其是紀錄片)的著作,常常提到“情緒的作用被輕視、甚至被埋沒”的情況。8例如,在尼科爾斯影響深遠的著作里,索引中沒有“情緒”(emotion)一詞,只是簡要提及“情緒的證明”(emotional p r o o f)和“情緒的現實主義”(emotional realism),將前者定義為對觀眾情緒傾向的訴求,后者則是指紀錄片可以嘗試在觀眾中創造特定情緒狀態的方式。9在紀錄片理論中,這兩個術語都被認為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理解紀錄片如何運作、紀錄片與現實以及觀眾心靈的關系時,情緒并未被賦予更大的作用。
對于處在認知領域之外的研究者而言,要揭示情緒在紀錄片中作用,最明顯的途徑莫過于通過精神分析和現象學,聚焦個人的、性別化的問題和主題。例如,邁克爾·雷諾夫(Michael Renov)的《紀錄片的主題》(The Subject of Documentary,2004),探討主觀紀錄片的發展歷史;貝琳達·斯梅爾(Belinda Smaill)的《紀錄片:政治、情緒與文化》(The Documentary: Politics,Emotions and Culture,2010),除了分析紀錄片中更主觀、更僭越的各種案例之外,還強調必須從理論上領會情緒在紀錄片中發揮的根本作用。斯梅爾反對理性和“清醒話語”在紀錄片理論中的支配地位,并且指出情緒在形成態度和社會規范時的重要性。然而,兩位學者對于激發-情緒(emotion-generation)的具體機制仍不明了。另一本對紀錄片理論具有重要貢獻的著作是伊麗莎白·考伊(Elisabeth Cowie)的《記錄現實,渴望真實》(Recording Reality,Desiring the Real,2011),該書將這種類型描述為“具體的故事講述”,“讓我們與社會角色的行為和情緒產生互動,就像小說里的人物”。“對真實的渴望”這概念源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論,結合了福柯、德勒茲以及德里達的現象學,但是沒有涉及認知理論。馬林·沃爾伯格(Malin Wahlberg)的《紀錄片時間:電影和現象學》(DocumentaryTime: Film and Phenomenology,2008)也是如此,他反對在分析紀錄片時忽視美學和情緒層面,并且致力于將關于時間和圖像的現象學理論延伸到紀錄片中。雖然提及具身(embodiment)和情緒,但是沒有深入闡發。
認知電影理論已經從認知的角度接受了挑戰,但大多是針對虛構電影的。達馬西奧強調的西方思想中的錯誤以及萊考夫和約翰遜在哲學和語言學中發現的理性與想象二元論,似乎仍然在影響紀錄片的理論方法。的確,正如筆者之前指出的,直到現在,電影中虛構與非虛構的區分主要是基于這種二元論:虛構電影被看做敘事、情緒和想象的類型,而紀錄片則被視為直接呈現現實、修辭和理性論證的類型。然而,盡管虛構與非虛構、“現實方式”與“假設方式”之間的這種二元區分,在我們的文化、社會以及交流方式中普遍存在,但是不管任何體裁和類型,都不會改變我們身心互動的基本方式。
二、自我、他人和想象
丹麥電影制作者安諾斯·厄斯特高(Anders ?stergaard)的紀錄片策略清晰地表明了將情緒視為“具體的知識的載體,從而認識自我,認識我們和世界之間的紐帶”,是多么有意思。10他在電影中運用情緒和自我來對社會、文化和歷史進行更加廣泛的表現,反映了人們對心靈活動方式的最新理解。例如,在《魔法師》(The Magus,1999)中,通過講述已故瑞典爵士音樂家揚·約翰松(Jan Johansson)的故事,通過音樂的情緒世界以及藝術家的生活與時代的抒情影像,厄斯特高激發了自我的具體層次,釋放了我們的個人記憶和經驗(以及我們對他人的記憶和經驗的認知),構成了我們的過去和現在。這部電影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有關爵士樂的歷史、斯堪的納維亞社會、約翰松的性格以及人際關系的信息,給我們帶來一種身臨其境的既視感和故事感,并且,這種感覺強化了實際知識。我們不僅把約翰松視為一位音樂家,而且把他看作生活在特定時空中的個人。盡管我們事先可能既不知道約翰松也不了解他的世界,但厄斯特高能夠使我們認同他,并且想象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
作為一個富有創造力的紀錄片制作人,厄斯特高并未受到現代心靈理論和情緒理論的直接啟發。然而,他使用紀錄片的方式,闡明了達馬西奧認為自我是一個過程而非實體的觀點以及他自己的看法——我們的大腦和身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稱之為“身體與大腦間的紐帶”。達馬西奧提供了三種不同的大腦-心靈視角:“個體的意識心靈”,我們只能主觀地進入;“旁觀他人的行為”,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對他人的意識心靈活動進行想象和理性思考;最后是“神經大腦”,可以在某種臨床狀態下進入。11前兩種狀態顯然是厄斯特高紀錄片策略中的決定性因素:他試圖以一種視覺的、敘事的方式來呈現他人的創造性思維/心靈,雖然通過電影來進入或記錄這個領域是極其困難的。他對想象、隱喻和情緒暗示的運用至關重要,因為它們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與共通的感受和經驗產生共鳴。
也許,就理解自我的運行方式而言,更重要的是達馬西奧對自我形成過程中的心靈和身體如何共同作用的描述。達馬西奧將自我區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原始自我”(protoself),是表現生命體原始的、自發的知覺/直覺(sensations)的最基本方面的場所——我們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并且知道我們還活著;第二層,“核心自我”(core self),涉及對“原始自我”的修改,通過有機體與自我之外的對象相互作用,從而在腦海中形成短暫而連貫的感覺、意象和敘事序列;第三層,“自傳自我”(autobiographical self),當原始自我中的對象被激活時,就會創造出新的、規模更大且更連貫的敘事序列模式,包括意象和感覺。總之,這個過程始于原始自我中自發的原始感覺,通過在核心自我中具有短暫意象和感覺模式的小規模敘事取得進展,最終在自傳自我中形成更連貫、持久和大規模的敘事、情緒和感覺/感觸的階段。達馬西奧的模型表明身體以及相關原始的和更高層次的感受在自我的構建和經驗中的重要性。在這方面,大腦和自我使用的主要“語言”包括意象和敘事序列。因此,從隱喻的角度來說,我們的心靈、我們的思考方式和經驗方式,都是由構成電影的東西構成的。
達馬西奧指出,對情緒(emotions)和感覺(feelings)進行區分,也同樣重要。情緒是發生在我們身體里的“復雜的、幾近于自動的行為”;感覺是在情緒實例和身體行動中“對我們身體里發生的情況的綜合感知”;它們都是大腦根據具體的情緒完成的意象或感知。12當然,敘事、情緒、感覺和想象并不能涵蓋整個心理過程。人類心靈也按照杰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所謂的理智、邏輯的思維和處理實際知識的“典型模式”運行。13盡管我們經常說到理性的爭論被情緒反應所破壞,但是必須強調,具體的情緒和理性并不是分離的,而是根本聯系的。正如他公開地運用詩學所表明的那樣,厄斯特高的紀錄片超越了理性與情緒的二元論。他的電影將真知灼見嵌入情緒結構和隱喻結構,小心翼翼地讓我們從自我的一層進入另一層。
三、厄斯特高、記憶和心靈的紀錄片
作為一名神經學家,達馬西奧也高度關注哲學和文化問題。事實上,他以一種近乎詩意的方式來界定記憶和想象的作用,尤其是指藝術的力量。他認為,藝術從基本的交流形式演變而來,逐漸成為在人群之間乃至在整個社會傳遞事實和情緒的特殊方式。因此,想象已經成為探索我們個人心靈和他人心靈的一種手段,并且進而影響我們更深層次的情緒以及我們表達和傳遞感覺的能力。達馬西奧聲稱:
“最偉大的人類屬性”是擁有在想象的海洋中駕馭未來的能力,引導自我航行到一個安全而且富有成效的港灣。最偉大的天賦再次取決于自我和記憶的交集。記憶,受個人的感受調節,使人們可以想象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福祉。14
厄斯特高曾將他的紀錄電影方法定義為“心靈的紀錄片”。15他試圖用一種表現性的和隱喻性的風格,進入主要人物的主觀心理世界,同時,讓主人公的藝術世界流淌在他的電影中,得以將自己的紀錄片置于身體、心靈、理智和情緒、自我與外部世界的交匯處。他以心靈和情緒作為切入點,把現實變成一種敘事和一種想象空間,這種方式揭示了紀錄片與兩種電影制作模式——理性電影和詩意電影——之間的關系。就本質而言,厄斯特高圍繞他的人物建立敘事的過程,清晰地證明了達馬西奧所謂的自我的三個維度,對記憶的強烈關注,以及自我的實際維度和歷史維度的不同層次。
開頭在所有的文字和影像傳播形式中都很重要,因為它們制訂了讀者/觀眾和文本之間的“契約”,并且介紹了作者/導演希望我們用來看待作品及其人物的角度。厄斯特高的紀錄片有一種獨特的開頭方式:他們邀請我們進入處于特定時間和地點的人物的敘事世界和想象世界。在他對約翰松的描繪中(這也是一個關于瑞典從20世紀30到60年代的詩意故事),開頭的段落激起我們的情緒和記憶,喚起對音樂的感覺。他們開頭用的是黑白影像資料,約翰松進入一間錄音室,開始演奏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將爵士樂和瑞典民間旋律融合起來。這條線索,直接觸及我們的歷史檔案思維,并且與一個當代科學實驗的彩色段落結合起來,強調他的音樂在不同的個體身上引發各種情緒。加上反映約翰松音樂的節拍和節奏的抽象動畫圖案,更添一層美感。
參與實驗的人是瑞典人口中頗具代表性的樣本。盡管他們的性別、年齡和種族背景大不相同,但是他們對音樂的反應卻相當普遍,從他們的面部表情和身體語言,足以證明這一點。他們也嘗試表達自己的感覺,反映自己在聆聽約翰松的音樂時體驗到的情緒。但是,當他們的評論提到喜悅、悲傷或者憂郁等常見的情緒時,參與者也表現出懷舊的沖動,重溫個人記憶,談論音樂表現的北歐/瑞典的特色。在這些反應之后,緊接著一位職業音樂家的鏡頭,他分析了約翰松音樂的特定形式和調性、他的獨創性以及他在爵士樂傳統中的地位。這些開場段落描繪了自我的不同層次。當影片中的普通瑞典人(以及電影觀眾)接觸到音樂時,原始自我的深層原始感受與核心自我更連貫的解釋維度開始產生互動:他們體會到被音樂喚醒的感覺,并且試圖定義它,將它與社會和文化背景聯系起來。當專家解釋約翰松的音樂并且將其置于一個連貫的歷史背景中時,這種互動會進一步加強。
看完這部電影的前五分鐘,沒有人會懷疑它是一部紀錄片,但是隨后觀眾被帶入沿著某種情緒路線展開的故事,表明該片是一部特殊類型的紀錄片。在影片的其余部分,約翰松的個人生活故事、他的音樂世界與更廣闊的歷史結合起來,既是線性敘事,也是視覺和音樂的蒙太奇。厄斯特高在2014年的一次采訪中描述自己的紀錄片方法和意圖時,將這部電影稱為一種“心靈紀錄主義”,并且解釋說“從視覺和美學角度講,我的人物電影(portrait films)的風格和形式……傾向于以詩意的態度面對作為一個人的藝術家及其藝術作品……我的目標是捕捉精神層面:心理方面,這個人的意識”。16
《魔法師》的開頭示例了厄斯特高的慣用手法。反復運用馬克·約翰遜所謂的“作為想象的理性的隱喻”,是影片其余部分的特征:用視覺和音樂的隱喻,支持更加理智的理解,直接談論我們對約翰松作為音樂家和歷史人物的看法。像許多紀錄片那樣,該片有效地利用來自專家、朋友和家庭成員的證詞,將約翰松置于一個人和一個藝術家的位置。但是它也使用了連續不斷的視覺隱喻和各種不同的組合鏡頭——有的有音樂,有的插入聲音,有的沒聲音,有的通過增加具有純粹象征功能的一組鏡頭、或者通過蒙太奇和動畫來建構或重現。這些鏡頭段落激發人們對敘事進行想象和情緒反應,造成將觀眾與文本連接起來的記憶網絡。這就意味著該片連接了自我的各個層面,從最基本的感覺和情緒,到我們自己的生活故事與更廣泛的文化語境相結合的地方。這類電影將感覺運動的具身經驗與主觀體驗聯系起來,比如利用音樂、風景和視覺暗示,創造出萊考夫和約翰遜所說的復雜隱喻。在我們的一生中,隱喻創造了影響我們認知的神經連接網絡。這些功能是一種具身的理解,一種電影所講述故事的現實的感覺。從這個意義上講,紀錄片就像是虛構電影,深度依賴敘事、想象、情緒和記憶,所有的這些(加上理性思考)使我們能夠理解現實。
四、埃爾熱的生命與心靈
厄斯特高的紀錄片《丁丁與我》(Tintin and I,2004)或許是他迄今為止最具創新性和實驗性的電影。該片的核心是在大多數聚焦于一個主要角色的人物紀錄片中發現的經典元素:1971年10月,埃爾熱(Hergé,George Remi的化名)的生命即將結束,一個在當時尚不知名的法國學生努瑪·薩杜爾(Numa Sadoul)對他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采訪。這次采訪讓我們親近地了解到這位著名漫畫家的工作、生活和時代——無論是臺前還是幕后——專家和評論家的證詞,也有助于對他的描繪。然而,厄斯特高選擇從美學角度來組織埃爾熱人生故事的方式相當獨特,并且突顯一個事實:真相不僅可以在第一人稱或第三人稱的事實陳述中找到,而且可以在某種中介的、情緒的現實中發現。厄斯特高圍繞埃爾熱及其世界建構的這種敘事,超越了一個具體的人和藝術家的故事。正如他所說的:“《丁丁與我》并不只是描繪具體的個人及其藝術世界:這部電影不僅關乎20世紀人的感受,也關乎這個世紀的歷史。”17厄斯特高在這里意思是,埃爾熱的生活以一種非常戲劇性的方式,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一些重要發展,而這一歷史時期也反映在他的漫畫中。起初,埃爾熱是一個非常保守的天主教男孩,他覺得需要改變,把自己從過去中解放出來。在經歷了一系列創傷事件之后,他在一段時間內慢慢地做了這些。同時,他在漫畫世界中呈現了他自己的生存困境以及他與世界的關系。

圖1.電影《丁丁與我》劇照
在呈現片名之前,開頭的場景說明了影片的內在結構。最初的電影畫面由漫畫構成,漫畫來自埃爾熱的作品《丁丁在西藏》(Tintin in Tibet,1959),描繪一架飛機在喜馬拉雅雪山墜毀的情景。利用攝影機的移動,搖拍和放大這個場景,再加上音軌上的風聲,漫畫圖片便活動起來。過了幾秒鐘,就聽到埃爾熱在畫外音中向杜薩爾承認:“你從我這里得到的秘密,我以前從未告訴過任何人。我不喜歡談論自己,我立即在自己周圍筑起高墻。”到這句話結束時,畫面變成了埃爾熱的工作室的鏡頭,窗臺邊擺放著來自《丁丁歷險記》的人物。移動攝影機,拍攝到房間里更多的物品,包括麥克風和磁帶錄音機。然后回到飛機墜毀的場景。人們聽到埃爾熱在說話:“它肯定傳遞了一個信息,我現在明白,這個故事是表達我自己的一種方式。”同時,他的臉出現了,被描繪成一個生動的漫畫形象,疊映在西藏的風景上。隨著動畫段落的繼續,埃爾熱的臉逐漸淡出觀眾的視線。
緊接著,厄斯特高引入一組新的鏡頭,薩杜爾(實時的現在)在這組鏡頭中回顧采訪的過程。就視覺而言,我們在磁帶正在轉動的錄音機、關于埃爾熱和采訪者的檔案照片和逐漸展開的隱喻視覺鏡頭之間來回變換。在這個過程中,埃爾熱書中所有的畫頁作為一個巨大的蒙太奇,生動地還原了丁丁的世界。(我們被告知)埃爾熱的23卷著作,代表了他47年的工作,已經被翻譯成58種語言,發行了數百萬冊。在無數書頁的意象之后,緊接著一段快速蒙太奇,畫面來自他的各種專輯;還有薩杜爾的表態:埃爾熱不僅在他的作品中萃取了50年的歷史、戰爭、政治和日常生活,而且讓我們得以了解他的內心生活和個人經歷。這也是通過視覺方式來表達的,即將作為漫畫人物的埃爾熱疊印在由全部23本專輯構成的背景上,說明用人物的疊印形象制作的銀幕動畫可以發揮具體的隱喻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埃爾熱就是他自己的漫畫(人物),他的漫畫(人物)就是他在現實生活中的形象。
《丁丁與我》的開場鏡頭帶有一個富有想象力的、詩意的、善用隱喻的電影制作人的印記。這部影片并非簡單地記錄或者解釋心靈、身體、情緒與我們的生活以及生活方式之間的緊密聯系,而是通過視覺策略來體現這種聯系,讓我們既能看到又能感受到被講述的內容。解釋與經驗、理性和情緒,都融合在敘事中;敘事既是歷史的和個人的現實故事,也是對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心靈和自我的視覺呈現。以一段長時間的采訪為基礎,這部“人物/肖像電影”也是一部關于記憶、關于三層自我的電影。面對自己的過往,同時面對自己作為歷史人物或者通過漫畫形象的解讀,人們見證了埃爾熱在原始記憶、核心自我的短暫情緒以及自傳自我的反思和變化之間徘徊。
當影片轉向比利時的社會/政治生活或者埃爾熱的童年時,使用的是檔案影像資料。厄斯特高將這種標志性/模擬性的檔案影像與更具隱喻性的畫面結合起來,讓觀眾體驗過去與現在、集體歷史與個人歷史之間的聯系。盡管采用了這些表現主義的技巧,但是該片仍然以闡釋的方式運用傳統紀錄片的基本元素,如采訪和檔案。這符合尼科爾斯在他的紀錄片類型學中所稱的“闡釋型紀錄片”18,這種類型立足于直接的修辭、理性的結構;或者普蘭廷加所稱的“正式的紀錄片”19,這種類型根據其認知的權威性及其對世界和觀眾的立場來定義。正如筆者在其他地方所討論的那樣,紀錄片的基本原型可以在尼科爾斯和普蘭廷加觀察的基礎上進行總結,如下表1所示:
考慮到這四種基本紀錄片模式的特點,很明顯,厄斯特高的影片幾乎運用了所有這些模式的元素,并且,他對權威型、戲劇型和詩意反身型紀錄片的投入是一樣的。這直接關系到他處理更復雜的隱喻結構和人物主體性的方式,同時,這些隱喻結構和人物主體性又與更廣泛的社會/歷史敘事聯系在一起。他經常在重構的形式以及不同影像的視覺和敘事活動中采用戲劇化,將敘事結構視為一種強有力的論證形式。正如老話所說的那樣:“只展示,不要說。”盡管厄斯特高尚未運用認知理論,但是作為紀錄片制作者,他似乎本能地了解,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敘事經驗,起碼與理性和抽象思維同等重要。事實上,在他的電影中,這些要素總是直接相連的,而不是被描繪成心靈二元分裂的離散部分。既然如此,那么,通過敘事來體驗,也即是通過認同和具身的理解來體驗。厄斯特高還利用紀錄片中更詩意和更隱喻的方面——他把握形象、形式和聲音的能力——作為進一步表達具身心靈(embodied mind)的方式。例如,在《魔法師》中,厄斯特高通過音樂、情緒以及其他人物對這個世界的反應和體驗,讓我們進入約翰森的世界,從而激活了身體和心靈的評判標準(qualitative dimensions),而不是那些通常與傳統的權威紀錄片相關的東西。
《丁丁與我》同樣如此,但是程度更深;它充滿想象力地將虛構的故事世界、埃爾熱的個人生活與歷史時代聯系起來。顯然,這部紀錄片沒有落入劃分內在與外在、主觀與客觀、情感與理性的陷阱。我們從某種個人的、視覺的和情緒的角度進入埃爾熱的世界、作品、生活以及他在社會歷史中的地位。從這種角度看,埃爾熱的自我與創作是融合在一起的。他采取開放的、坦白的方式,反思自我的各個方面。并且由此意識到,他的整個創作,離不開他自己、他與別人的關系以及他生活在其中并且深受其影響的時代。

表1.紀錄片的基本原型20
在影片中,視覺在敘事和想象力方面的運用,直接關系到處于核心的實際現實的基礎。然而,這種往往基于檔案影像的實際現實至少包括兩方面:它呈現埃爾熱的采訪者薩杜爾,以及兩位研究埃爾熱和丁丁的外國專家,他們不僅在鏡頭前面表達觀點,而且作為視覺蒙太奇的畫外音。視覺蒙太奇由檔案劇照、埃爾熱及其時代的影像資料、再現的鏡頭和照片構成。除了影片的真實性和典范性之外,厄斯特高還利用富有想象力的現實概念,將實際的知識嵌入某種情緒結構和敘事結構。
紀錄片檔案的第一個例子出現在影片的第四分鐘時,薩杜爾通過畫外音描述他如何采訪埃爾熱。當他說話時,我們看到的是1917年時布魯塞爾的黑白影像,人群坐火車和電車進入或者離開城市。緊接著,畫面切換到當前,薩杜爾在他的公寓里回憶這次采訪,然后,畫面又切換到正在轉動的錄音帶,正在接受采訪的埃爾熱以漫畫形象從錄音帶中疊化出來。由此,厄斯特高在電影的真實部分和想象部分之間建立起直接聯系。這種用一般的歷史檔案資料、薩杜爾的采訪影像、畫外音講述和埃爾熱富有想象力的漫畫圖像構成的蒙太奇貫穿全片;整個紀錄片的敘事都是以這種方式構建的,并且,不同的要素之間沒有明顯區別。例如,有一次,當埃爾熱和薩杜爾在討論丁丁以及其他漫畫人物(比如哈多克船長)多么像埃爾熱本人時,我們看到的是埃爾熱本人在舞臺上表演,而丁丁在模仿他的手勢和肢體語言。同樣的觀點,也可以通過分屏顯示的、漫畫風格的埃爾熱形象以及埃爾熱漫畫中的場景來說明;這些故事可能是虛構的童話故事,但是它們同樣描繪了埃爾熱的生活以及20世紀的歷史。
這種個人歷史與集體歷史交織的主題,也通過對埃爾熱生活故事的描繪呈現出來,例如他在極端的、右翼的天主教家庭和文化中成長,以及他同一位與法西斯運動有著可疑聯系的牧師的關系。這個殘酷的童年被一些接受采訪的專家描述為“灰暗”“平庸”和“殘酷”的,并且,正如電影清晰呈現的,埃爾熱一直在努力戰勝這段經歷,在他虛構的漫畫世界中尋求庇護,嘗試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形象。當他在晚年離開(由牧師“指派”給他的)妻子與另一個女人結婚時,埃爾熱的人生才達到情緒的頂峰。通過歷史檔案影像、埃爾熱的回憶與反思、專家的分析以及系統地利用埃爾熱的漫畫形象,厄斯特高將埃爾熱的個人解放的故事與20世紀充滿戲劇性的歷史故事融合成一個敘事整體。
隨著電影的推進,在不同的敘事和美學層面之間切換與融合,變得愈加復雜。隨著埃爾熱的自傳自我越來越充滿了反身性,并且意識到他的生活與工作的敘事層次及聯系時,不同元素的蒙太奇、對疊印、疊化和分屏的運用也變得更加強烈。影片中還有一種循環。當《丁丁在西藏》(開頭的影像)作為埃爾熱的事業和個人生活的轉折點時——他在這個時候向一位瑞士精神醫生尋求幫助——這種循環是顯而易見的。正如在厄斯特高所有的電影中一樣,這種情況不僅是被講述出來的,而且是被展示出來的:當我們在追尋有關埃爾熱的實際知識時,它會體現在所有的視覺敘事層面上。
結語
厄斯特高的紀錄片運用了敘事、想象和視覺隱喻的全部技巧,融合了新聞工作的經典修辭策略、傳播的科學模式、故事的講述、強烈的情緒以及視覺暗示。觀眾明顯感覺到它們是與實際的外部現實有著特殊關系的紀錄片,而與此同時,這些影片也像虛構電影一樣訴諸具身心靈的相同領域。厄斯特高以這樣的方式組織他對現實的呈現,讓觀眾從情緒上對他所描繪的歷史人物和時代予以更深刻的理解。他還在許多電影中把個人記憶作為切入點:在《魔法師》中,厄斯特高對20世紀60年代的情緒記憶彌漫全片;在《丁丁與我》中,影片結尾的一組鏡頭描寫一個男孩正在當地參觀他的圖書館,挑選了一些“丁丁”專輯,然后騎車回家,在穿過典型的丹麥郊區時,畫面中突然出現西藏的山地風光。主觀的、情緒的記憶并沒有偏離紀錄片的現實,實際上,它們是觀眾集體經驗和認同生活歷史的場所。
在自1990年以來丹麥收視率最高的紀錄片《加索林》(Gasolin,2006)中,厄斯特高利用20世紀70年代一個丹麥搖滾樂隊的故事來介入這個國家在戰后的歷史。他再次采取情緒、敘事和隱喻的路線,引導觀眾深入理解當時的文化沖突和社會趨勢。在影片的關鍵場景之一,他描繪樂隊音樂的雙重根源——典型的、流行的、民族民謠傳統和美國的搖滾風格——體現在樂隊中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物金·拉爾森(Kim Larsen)和弗蘭茨·貝克利(Franz Beckerlee)身上。拉爾森和貝克利的畫外音講述與生動的圖像和音樂視覺蒙太奇相結合,既展現了他們的個人故事,又呈現出20世紀70年代更廣泛的國家以及全球趨勢。厄斯特高在解釋他的視覺策略和敘事策略時聲稱,他特意為這部電影選擇了一個神話般的架構,將其嵌入根深蒂固的文學傳統和童話故事中。紀錄片最核心的想象力基礎體現在漢斯·克里斯汀·安徒生筆下的笨漢漢斯、《一千零一夜》故事中代表光明與黑暗的王子阿拉丁和努爾丁等人身上,以及后來的各種文學形式和大眾文化中。21
敘事、想象、情緒和不同層次的自我都在紀錄片里發揮作用,厄斯特高的紀錄片強有力地證明:如果我們認為感覺、情緒和敘事的配置不是紀錄片的核心,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它是我們所有思考和行動的基礎。達馬西奧認為,感覺“作為內部指南,幫助我們向別人傳遞同樣可以引導他們的信號……感覺和其他知覺一樣具有認知功能……它們是一種最具求知欲的生理安排的結果,這種安排將大腦變成被身體俘虜的聽眾”。22
【注釋】
1 Nichol s,B.Representing Reality: Issues and Concepts in Documentary[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3.
2 Plantinga,C.Rhetoric and Representation in Nonfiction Fil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3,84.
3 Bondebjerg,I.“Narratives of Reality: Documentary Film and Television in a Cognitive and Pragmatic Perspective,”[J].Nordicom Review,1994,1:65–85.Bondebjerg,I.Engaging with Reality: Documentary and Globalization[M].Bristol: Intellect Books,2014a.Bondebjerg,I."Documentary and Cognitive Theory: Narrative,Emotion and Memory,"[J].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14b,2(1):13–22.
4 Damasio,A.Descartes’Error: Emotion,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M].New York: Avon Books,1994.
5 Gottschall,J.The Storytelling Animal.How Stories Make Us Human[M].New York: Mariner Books,2012.
6 Johnson,M.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Imagination and Reason[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7.Lakoff,G.and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0.Lakoff,G.and 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 Basic Books,1999.
7 Lakoff,G.and 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 Basic Books,1999:72-73.
8 García,A.N.“Introduction,” in García,A.N.(ed.) Emotions in Contemporary TV Series[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6:3.
9同1,133.
10Martínez,A.G.and González,A.M."Emotional Culture and TV Narratives,"in García,A.N.(ed.) Emotions in Contemporary TV Series[M].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6:19.
11 Damasio,A.Self Comes to Mind.Constructing the Conscious Brain[M].Lond on:Vintage Books,2010:8,21,15.
12同11,109-110.
13Bruner,J.Actual Minds,Possible World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12.
14同11,296-297.
15 Hjort,M.,Bondebjerg,I.and Redvall,E.N.(eds.)The Danish Directors 3:Dialogues on the New Danish Documentary Cinema[M].Bristol:Intellect Books,2014:381.
16同15,389.
17同15,390.
18Nichols,B.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105.
19同2,110.
20 Bondebjerg,I.Engaging with Reality:Documentary and Globalization[M].Bristol:Intellect Books,2014a.
21同15,393.
22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