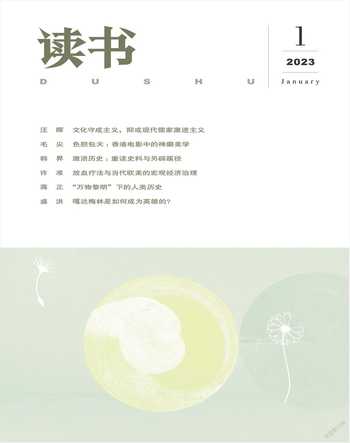“泰坦尼克號”:西方傳統建構與種族主義想象
劉益
二0二二年是“泰坦尼克號”巨輪沉沒的一百一十周年,也是卡梅隆導演的《泰坦尼克號》上映二十五周年。隨著美國海事歷史學家施萬克(Steven Schwankert)的紀錄片《六人》(The Six , 2021)以及同名著作《六人》([ 美] 施萬克著,中信出版社二0二二年版)的陸續上映和出版,電影《泰坦尼克號》的重新上映,與“泰坦尼克號”海難相關的問題被重新推回公眾視野。《六人》講述的是“泰坦尼克號”上六位中國幸存者的故事。
“泰坦尼克號”是二十世紀人類科技的象征,是“漂浮的社會縮影”(搭載了三十多個國家的乘客,他們被分成不同的等級),它的失事可以引出政治、法律、經濟方方面面的問題,而船上的華人在海難后的遭遇又可以引出美國的《排華法案》以及華人勞工、華人移民等問題。但一百一十年來,“泰坦尼克號”海難敘事的重點一直圍繞著愛、勇氣與命運展開。這種敘事的結果,在當時曾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幸存者的命運,參與到中國國民性話語的流傳中。今天,無論是《泰坦尼克號》還是《六人》,仍然延續著這一傳統,只是《六人》的敘述主角變成了中國人,但它骨子里仍然是有關命運、愛以及勇氣的敘述,這些都是西方傳統的延續和再次建構。“泰坦尼克號”海難是一個思想事件,既交織著西方傳統的自我建構,又若隱若現著種族主義,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施萬克的紀錄片和著作均命名為《六人》,但“命運”問題在著作中更為突出。施萬克說:“我們要呈現的這個故事并不是‘泰坦尼克號自身的故事, 而是關于這幾名中國乘客如何幸存以及他們最終的命運如何, 這才是這個故事格外突出之處。”這個說法讓我們意識到命運問題才是《六人》的命意所在。并非巧合的是,卡梅隆在本書序言中也對《六人》做出了有關命運、勇氣的解讀。他說:“那個中國男人求生的勇氣和決心,深深地打動了我,也激發了電影《泰坦尼克號》結尾的拍攝靈感,即眾所周知的杰克與露絲生離死別的情節。……《六人》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它不僅僅是一個關于‘泰坦尼克號的故事。它向我們展示了一群由于命運使然而最終登上這艘歷史上最著名巨輪的中國人所經歷的苦難和考驗, 它不只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決定命運的夜晚,也證明了對于像這六個中國人一樣堅韌和勇敢的人們來說,即使是一次如此巨大的海難也淹沒不了他們與命運抗爭的勇氣和追求夢想的決心。”卡梅隆不僅提示了《六人》這部書的主旨所在,也指明了《泰坦尼克號》與《六人》相通的精神內涵。由此可知,命運、勇氣是本書的主旨,而非海難本身。六名中國人的境遇—海難、二十世紀初艱難的世界政治與經濟局勢,西方人對“六人”的侮辱性指控、與家鄉親人的紐帶,都成為襯托他們與命運抗爭的背景。
這種有關勇氣與命運的敘述,表現的是人通過德性與命運和自然抗爭,這是西方傳統的主題。從荷馬的《奧德賽》、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到現代麥爾維爾的《白鯨》、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都貫穿著這一主題。同樣,“與命運抗爭”也貫穿于《六人》的敘述中。該書第一章“一塊木板”里,作者講述了方榮山落水時的所思所想,面對死亡的心境,以及他通過抓住木板堅持到救援到來,這不禁使人聯想到在茫茫大海中因為波塞冬懲罰而落水的奧德修斯,后來因為女神相助而得以幸存的故事。《六人》第六章“逃離”部分,再次講到方榮山在落水時如何憑借自身的智慧和堅強而獲救,這種感覺再次襲來,它提示我們,對“泰坦尼克號”的敘述已經慢慢被西方傳統吸納,成為其文化的一部分。現在,這種傳統在嘗試吸納其他民族或者他者的故事。方榮山等人雖是中國人,但“命運”明顯不是中國傳統的核心問題,或者說沒有占據如此核心的位置。在對這一“海難”的敘述中,西方的問題不斷涌現。
歷史敘述原本就承擔著教育民眾以及凝聚和塑造民族意識的功能。對于災難,除了鑒往知來外,最大的意義就是如何理解和消化它。亞里士多德《詩學》對“悲劇”的理解可以給我們提供一種理解的方式。他在該作品中曾經探討過“疏離”問題,即當自我親身經歷災難時,只會產生恐懼,如果災難沒有落在自己身上,“恐懼”就會轉化成“憐憫”,進而形成對“命運”的一種認識,并且達成對觀眾(聽眾)的教育或者凈化。面對一百年前的海難,任何敘述都不會僅僅停留在“災難”這個層面。當然可以去追問災難的原因,從而避免災難的再次發生,這些問題通常可以通過技術條件來解決,但更難的是在德性的層面理解海難。在“泰坦尼克號”海難之后,有關它的創作和研究一直是它思想的一部分,這百年來出版的相當多的回憶錄及相關的研究資料,都構成了英美歷史和西方傳統的一部分,美德、勇氣、愛情漸漸代替了苦難、災難等問題。
《六人》中,這一西方傳統的主題則是通過講述方榮山的故事突顯出來。這不僅因為方榮山的經歷在六位中國人中最完整可靠,更是由于方榮山的一生最艱難坎坷,他的品格更堅毅,他的故事最傳奇。總之,方榮山的一生非常契合《六人》的主旨:在艱難的社會背景和人生際遇下,為了生存而與命運抗爭的故事。這個故事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在開頭即表達了對方榮山與命運抗爭的智慧和勇氣的贊揚;二是六人在“泰坦尼克號”事件中的真相,包括“泰坦尼克號”海難和海難后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指控;三是六人在海難之后的生存和抗爭。這樣的結構所展現的視角是—正如施萬克在“前言”中所說—“中國乘客如何幸存及他們的最終命運如何”。也就是說,海難本身也是凸顯“命運”問題的一部分,并且是至關重要的部分。我們可以從施萬克講述的視角來論證對方榮山故事的建構在突顯《六人》主旨上發揮的作用。
首先,是《六人》的兩個“開頭”。作品中的開頭是“一塊木板”,這是方榮山人生最英勇的時刻。他沒有搭上救生艇,堅持到巨輪沉沒的最后時刻也不愿與同伴分離,他寧愿拼盡力氣游泳也不愿借力于浮尸,在冰冷的海水中堅持著,并不確定救援是否會到來。最終他贏得了命運的眷顧。另一個是方榮山人生的開頭。施萬克“想象”了方榮山的少年時代:他喜歡讀書,追求更好的生活。這一點與方榮山在美國只穿西裝、打領帶遙相呼應,代表一種體面、有尊嚴的生活。施萬克通過這個細節,勾勒(想象)出人物對自我的期待。這種對人物精神的“想象”貫穿于作品中,又主要體現在方榮山身上。比如海難發生前在船艙中暢想未來,海難發生后在海里掙扎的思想活動,等等。“想象”體現的是作者對人物的理解,同時也是作者思想的投影。
其次,施萬克極力講述了方榮山一生為了夢想與命運抗爭的過程。少年時,方榮山想要讀書,但家庭的貧困和社會環境逼迫他走向大海的旅途,夢想第一次破滅;方榮山在海難中幸存,但他到美國生活的夢想破滅,這是第二次失敗;他堅持了下來,再次等待機會,終于在一九二0年入境美國,不過離夢想仍然遙遠;一九四三年《排華法案》廢除,他也沒能如愿成為美國公民,直到一九五六年才終于如愿以償。長達五十年的時間里,他不僅沒有放棄,反而靠做餐館服務生支持家鄉親人,支持中國革命運動。用施萬克的話說,他“直面挑戰”“從未放棄”,他的一生就是傳奇和神話。
方榮山一生的經歷是真實的,但施萬克“發掘”了他,也“塑造”了他,并為之賦予了崇高的精神意義。如果說“泰坦尼克號”海難發生時,西方人極力淡化海難災難性的一面,突顯“盎格魯- 撒克遜”人英勇無畏的“騎士精神”;那么《六人》中,施萬克則通過海難、排華運動、歧視、戰爭等方面突顯了方榮山的堅韌、勇毅和決心。這也是《泰坦尼克號》杰克和露絲的最后時刻所要講述的精神。如果把方榮山成為美國公民的夢想比喻成奧德賽的“歸家”過程,也可以看到其中一脈相承之處。
但是中國學者程巍則提供了一個看待“泰坦尼克號”海難不同的視角。他是從中國人的問題出發,探討西方文化對中國人的污蔑在西方的思想根源及其在中國被接受的過程和文化背景,雖然,在面對的人物和問題上,他的《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種族主義想象力》(漓江出版社二0一二年版)與《六人》在許多方面有相似處:澄清中國人受到的誣蔑;對西方報章惡意指控的譴責;解釋事件發生的政治、經濟背景,特別是排華問題;以及為了說明這些問題所引述的材料,等等。且他們兩人都受到卡梅隆電影的啟發。卡梅隆拍攝《泰坦尼克號》時,曾經拍攝了有關中國人在船上的鏡頭和在海里趴在木板上的片段,但一九九七年的版本中只采用了部分且觀眾難以覺察,到二0一二年的3D增補版時又增加了一個明顯的華人鏡頭。程巍在“后記”中提到,他在電影中捕捉到一閃而過的中國人,從而形成了他的問題意識。而施萬克發現他要給英語國家讀者講述“海神號”時,讀者會想到《泰坦尼克號》,后來興趣便慢慢轉移到“泰坦尼克號”的沉沒,再到“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問題。施萬克的心路歷程也表明,“泰坦尼克號”已經嵌入西方人的歷史記憶,成為西方的文化符號。兩者的不同也很明顯,即在敘述的內涵和精神譜系上,《六人》與《泰坦尼克號》一脈相承。
程巍書中“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是西方的一個“他者”,折射了西方種族主義的偏見。也因此,程巍在《六人》的紀錄片中有三十幾秒的鏡頭,展示了他從“種族主義想象”的角度解釋“海難敘事”中對中國人的污蔑。程巍翻閱了大量的報章,分析了流傳于報章中的“海難敘事”的時間線索、演變過程,發現那些自相矛盾、不切實際的對中國人的指控幾乎都是“層累地造成”的。程巍的關注點在于,是哪些社會政治、思想背景導致了這些關于中國人的離奇的、破綻百出的侮辱性故事不斷被述說、編造和大量流行。他認為中國人的負面形象,是多種因素合謀的結果,包括:英美兩國政府及白星航運公司等直接利益集團將“海難敘事”往道德方面引導,這對幸存者的證言和敘述造成道德壓力;新聞媒體中“美式新聞”的泛濫,大量對盎格魯- 撒克遜英雄主義的宣揚和對華人的污蔑報道;契合了《排華法案》的實施;源于基督教的種族主義思想和英國人建構的“世界歷史- 地理模式”對他民族的仇視;等等。而這些因素中,“種族主義想象”又是最關鍵的一環。程巍相信,那些宣稱“目睹”了根本未曾發生的事件的西方人,正是“出于他們對華人的‘種族卑劣性的‘相信”。
但施萬克顯然不同意這種解釋。他雖然在紀錄片中引用了程巍的說法,但這毋寧說是為了澄清。因為施萬克和他的團隊通過復制C號折疊船得出結論:“沒有人捏造事實,只是他們的視線和角度讓他們產生了錯誤的判斷。”且幸存者小男孩弗蘭克的說法也證明,是由于中國人蹲在船尾,身著黑色長外套和圓帽子,才被誤當作女人。因此施萬克認為對中國人的惡意指控是“出于憤怒、激動的情緒和無知”。基于以上兩點,施萬克說那些“充滿惡意的謠言”“始終沒有得到認真的分析和理性的評價”。這里,施萬克實則隱晦地指出了程巍的評價是不理性的。但是,事實上《六人》所提供的證據也可以支撐程巍的論點。比如藏匿、假扮女人的行為原本發生在非中國人(如三名意大利、愛爾蘭或英國男子扮成女人,菲利普·贊尼趁船員不注意躲進六號船座板下)身上,而偷渡原本應在白星航運公司公布乘客名單后自動澄清,但這些罪名卻統統被加諸中國人身上。且施萬克自己也說“藏匿船底與假扮女人是相互矛盾的”,“一個人得跟中國人有什么深仇大恨,才會相信這樣一個完全荒謬的故事”。這些都不是簡單的“出于憤怒、激動的情緒和無知”可以解釋的。
由此,我們發現,程巍和施萬克面對類似的材料,卻是不同的處理方式,這折射出他們不同的出發點和立場。《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佬”》旨在理清謠言產生、傳播的機制,及其背后的思想基礎。程巍以中國人的身份,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除了澄清事實以外,還探討了這個“丑聞”在中國的接受和演化。恰逢民國初立,新文化運動前夕,在沒有辨偽的情況下,這一“丑聞”變成“國恥”,成為“國民劣根性”的一部分,參與了國民性批判話語。一方面,西方人借“他者”完成自身崇高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中國人自己不但對這一事實沒有質疑,反而接受了這種邪惡的形象,完成了自我矮化。這構成了強勢文化的一種權力的單向輸出,程巍的書就是要質疑這種單向蠻橫的權力關系。程巍既要澄清當時的事實,同時更重要的是要批判這種自我矮化的思想。
但“種族主義”沒有成為施萬克的核心關切,他在極力地,但很隱晦地澄清這個問題。《六人》既與以往的西方海難敘事構成對話關系,又與程巍的言說構成對話關系,由此體現了中國人和西方人對“泰坦尼克號上的中國人”的不同關注。在澄清了這一問題后,施萬克自然地將主題引向了六人(主要是方榮山)的命運,讓這部著作的核心旨趣悄然轉變。方榮山的故事成為書中的主線,敘述視角從他小時候在江門的生活,到香港,再到美國的生活,方榮山一生的經歷、命運和與命運抗爭的圖景逐漸向讀者敞開。這一敘述在使人物形象逐漸豐滿的同時,也將全書的重點落在了方榮山的“命運”問題上。因此,方榮山雖是一個中國人,但在《六人》中又變成一個“西方人”,一個追尋“美國夢”的新美國人,一個具有美國品質的華人。從這個角度,西方人巧妙地把中國人的故事講成了西方人的故事;巧妙地把中國人的個人歷史嵌入西方的大歷史中,悄無聲息地將中國人西方化。
綜上所述,《六人》的主角雖是中國人,但無論故事的歷史背景、人物形象,還是敘述中所要突顯的精神品質,都表明《六人》仍然是西方式的故事。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號海難敘事”將貧弱中國的子民當作“他者”,以襯托“盎格魯- 撒克遜人”的“騎士精神”,一百年后這個“他者”成為這種“英雄主義”話語的一部分。由《六人》反觀泰坦尼克號海難敘事的歷史,可以發現,種族主義實際上是西方自我建構的一個副產品。我們不必過于糾纏這種種族主義話語,但需要意識到《六人》雖然采用的是紀錄片這樣的紀實體裁,卻并非一個完全“客觀”的描述。今天,我們既要重新認識西方,也需要能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用中國人的傳統重新講述有關“泰坦尼克號”上中國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