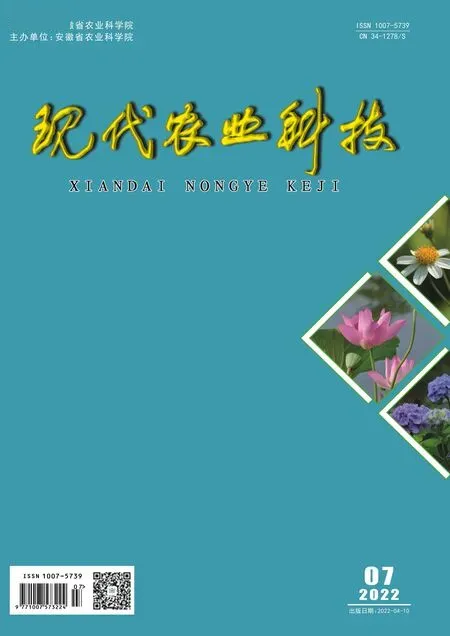國內“資本下鄉”的研究綜述
熊立芳
(南京大學金陵學院城市與土木工程學院,江蘇南京 210089)
“資本下鄉”指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和各地“城鄉統籌”建設的推進,政府財政資金大規模“反哺”農村,城市工商企業資本也大量涌向農村,進行土地整理、土地流轉和新農村建設,并從事農業經營[1]。2005年新農村建設系統工程在農村的展開,“部門下鄉”開始出現,各級政府以項目資金的形式對農村進行“反饋”。隨著一系列涉農政策的出臺,農村“資本下鄉”經歷了從以政府為主導的“項目下鄉”到以企業為主導的“工商資本下鄉”階段,并引起了“精英回流”。“資本下鄉”的熱潮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高度關注,“資本下鄉”也將是各界持續關注并重點研究的領域。
1 國內“資本下鄉”研究概況
基于筆者對知網、維普、萬方等中文數據庫的檢索結果,國內學者關于“資本下鄉”的研究最早出現在2005年,即學者馬國賢[2]提出的“工業反哺農業政策的核心是讓資本下鄉”。然而,明確以“資本下鄉”為主題的最早研究成果,是2006年學者田成川[3]認為的“辯證處理資本下鄉與農民進城的關系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關鍵”。
本文依托知網、維普等中文數據庫,以關鍵詞“資本下鄉”或相近概念,如工商資本、項目下鄉以及社會資本等詞組進行檢索,共選取了31篇研究成果。
2 我國“資本下鄉”的階段劃分
目前,國內“資本下鄉”的研究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分別為以政府為主導的“項目下鄉”、以企業為主導的“工商資本下鄉”以及以多元主體為主導的“資本下鄉”。
2.1 2005—2014年:以政府為主導的“項目下鄉”
這一階段的研究重點為傳統農業的轉型發展。2005年新農村建設系統工程在全國農村展開,“部門下鄉”出現,各級政府下達“條線”和執行對農村進行“反饋”,各涉農經濟技術部門開展涉農服務,推動農戶專業化、農村市場拓展和農村產業發展[4]。此外,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政府采取“工業反哺農業”這一特殊的農業政策,按市場經濟要求及國家農業政策要求,通過直接和間接投資,引入家庭農場制經營方式,將傳統農業改造成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產業[2-3]。這些針對農業的“資本下鄉”,按照產業化經營的方式發展農業,實現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經營,在此過程中,出現農村莊園經濟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而大多數高度分散的農民由于規模小、剩余少,難以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主體,逐漸成為資本下的農業工人,在分享社會平均利潤方面處于弱勢地位。此外,在后期發展中,大多數政府主導已經淪為部門利益主導,其追求的并非公共利益最大化,這也使得多數小農被“客體化”和“邊緣化”,這不僅導致“三農問題”日益嚴峻,在宏觀上也對國家糧食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5-6]。
2.2 2014—2018年:以企業為主導的“工商資本下鄉”
這一階段的“工商資本下鄉”由最開始注重農業向逐漸退出種植領域轉變。城鎮化的高速推進帶來了農民的普遍流動,農村因人地關系松散而產生了撂荒、老人農業及粗放式經營等問題[7]。在此背景下,國家政策倡導土地流轉,試圖通過地權流轉和資本投入來形成規模化、資本式經營。具體表現為政府通過推動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并以一定的稅收優惠和扶持政策引入工商資本進入村莊大規模流轉農村耕地,種植經濟作物或者發展高附加值的現代農業[8-9]。“資本下鄉”是嵌入在社會結構中受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的工商資本的理性選擇[4,10],其在有效激活傳統生產要素、培育和發展新型經營主體和經營方式的同時,也帶來了鄉村階層再造、村莊再造和村社重構。但是,由于資本的逐利本能和農業種植環節的“高風險、低收益”特征,企業逐漸退出生產種植環節而轉向中下游高利潤環節,公司流轉的土地只有少部分會繼續用于農業生產,絕大多數被轉換成其他用途[7-11]。
2.3 2018年至今:以多元主體為主導的“資本下鄉”
這一階段的研究重點主要為鄉村旅游及地產的發展。在工業化、城市化發展中期階段,城市產能過剩,大多行業領域僵化,獲利空間有限,導致資本退出城市,大量閑置的流動資本及積累的資金流向鄉村。在工商資本大規模下鄉背景下,一部分新精英抓住機會并采取行動積極返鄉,鄉村形成多元主體參與“資本下鄉”的局面[10,12]。工商資本最初只投入農業生產,這一階段逐漸拓展進入農業生產性服務業、休閑觀光循環農業領域,打造農業新業態[13]。此外,還有政企聯盟合力打造的鄉村旅游示范區[14]以及新精英攜輕資產進入鄉村從事餐飲、民宿等服務業。在“精英回流”的過程中不難發現,以旅游發展為主導產業的村莊會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和稅收補貼積極主動引入“新精英”,以激發鄉村活力,促進鄉村進一步發展。但筆者發現,由于我國地域發展差異較大,現階段關于發展鄉村旅游的研究更多集中于長三角地區。
3 研究重點
“資本下鄉”是我國鄉村發展的必然趨勢,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鄉村治理與村莊再造、農民權益保障、農業轉型發展、“資本下鄉”的邏輯機制及影響以及“資本下鄉”介入鄉村文旅產業發展都是國內學者關注的領域。
3.1 “資本下鄉”后的鄉村治理與村莊再造
有學者認為工商企業“資本下鄉”后大力推進“農民上樓”與“土地流轉”,構造了新的村莊治理結構,村莊和企業的關系日益緊密,這是地方政府依托彈性土地政策和財政專項資金,積極鼓勵和引導“資本下鄉”的結果[11]。在此過程中,地方政府和工商企業資本合作完成了對村莊整體性“再造”,形成“村企合一”模式以及鄉鎮企業改制后形成的“公司型村莊”“公司辦村”或“以廠帶村”的治理結構[13]。一方面,有學者認為“資本下鄉”也產生了階層再造,小農受高額地租收益誘導,將土地流轉給資本;中農因難以承擔高額租金,其經營規模和發展空間也受到限制。小農、中農被擠出農業經營領域,轉而成為資本勞動力市場的主力軍,最后出現階層再造的實踐結果[4]。另一方面,“資本下鄉”在經過土地流轉及村莊環境整治后,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鄉村的空間形態[14]。更有學者認為,“資本下鄉”也促進了無序的鄉土社會整治,形成了“資本主導型”和“精英主導型”的治理模式[12]。
3.2 “資本下鄉”后的農民權益保障
在推動鄉村發展的過程中,農民始終處于主體地位,對于“資本下鄉”后農民權益保障的研究就顯得很有必要。有些學者認為,“資本下鄉”能夠促進鄉村產業發展,利于農民增收就業[15],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對農民生活有總體改善作用[16]。也有學者認為“資本下鄉”導致農民缺乏依附性和主體性,擠壓小農生存空間[17]。“資本下鄉”擴大了村莊間的貧富差距,也使得鄰近村莊村民的相對剝奪感增強,這促使其通過一系列“阻攔”“破壞”“偷盜”等行動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18]。此外,資本進入農業生產后,原承包農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夠進入企業工作,其余多數都處于失業或隱性失業狀態,村莊的利益格局被改變,企業與農民間矛盾沖突頻繁[4]。基于此,學者也提出了要構建“資本下鄉”中農民權益保障機制,如建立基層政府的制度化管理機制、建立村民自治組織的利益保護機制及構建農民自主能力的培育機制[18-19]。
3.3 “資本下鄉”后的農業轉型發展
資本進入農村最開始投身于農業,以促進農業的轉型發展。學者認為傳統的小農經濟因各種閑置因素很難演化為大規模經營,因而招商引資形成規模經營是破解小農經營困境的唯一路徑[7]。“資本下鄉”能有效激活傳統生產要素、培育和發展新型經營主體和經營方式,促進農業規模經營,形成“農工商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等發展形式,推動小生產與大市場對接[9]。資本的逐利本能加之種植環節的“高風險、低效益”特征,資本只將很少一部分土地繼續用于農業經營,更多地轉向發展高利潤產業[7]。因此,有學者認為“資本下鄉”的規模效應在形式上完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務,化解了農業治理困境,但“資本下鄉”并未推動農業發展,其非生產性再分配活動反而進一步阻礙了農業現代化[20-21]。農業本身具有多重價值,而資本只強調其經濟價值,特別是土地價值。
3.4 “資本下鄉”的邏輯機制及影響
關于“資本下鄉”的邏輯機制,學者們普遍認為“資本下鄉”受內因和外因的共同驅使。對于內因,首先資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對于稀缺資源存在占有的沖動[22];其次,在政府政策扶持和鼓勵下,資本對農村發展優質農產品抱有良好的預期;此外,目前存在巨大的存量資本且城市發展空間有限,因而資本逐漸轉向農村地區。對于外因,存在政府政策的支持與鼓勵及農村社區經過村莊環境整治所形成的巨大拉力[4,9-10,19,23-26]。 對于“資本下鄉”所帶來的影響,學界褒貶不一。部分學者認為,一方面,“資本下鄉”為現代農業發展注入了先進的生產要素,推動了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養了新型職能農民,同時對于鄉村的空心化現象也起到一定的緩和作用;另一方面,“資本下鄉”也對農業生產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威脅我國糧食安全。此外,在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鄉村公共空間的私有化現象也越來越嚴重[6,13,26-27]。
3.5 “資本下鄉”介入鄉村文旅產業發展
鄉村振興背景下,市場化取向的土地制度改革為“資本下鄉”提供了體制通道,也為資本增值開辟了新空間[26]。隨著鄉村數量的減少,人們開始“消費”鄉村,尋找“鄉愁”的行為活動使自主性旅游快速興起[28],鄉村轉而發展旅游、地產等新興產業。“特色田園鄉村”“特色小鎮”建設也逐漸興起,吸引了大批城市中產階層前往鄉村進行消費。在此過程中,因文旅產業帶來的豐厚利潤,資本的主動參與性有所提高,“資本下鄉”的實踐操作從環境整治向多元業態并進。“資本下鄉”后,土地經營權從農業中“脫嵌”出來,由“農業+旅游”企業共同所有,其主導的規模農業生產和休閑旅游消費在空間上進行“聯動”開發,鄉村逐漸被“現代化”和“企業化”[26,29-30]。
4 結語
綜上所述,從學者們對于“資本下鄉”的大量研究中可發現,現有對“資本下鄉”的研究涉及鄉村治理與再造、農民權益機制保障、農業轉型發展、“資本下鄉”的邏輯機制及影響以及鄉村文旅產業發展等方面。在“資本下鄉”的發展過程中,也經歷了資本主體的變更,形成多元主體共存的局面。“資本下鄉”為鄉村帶來發展的同時,也對鄉村的生態環境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筆者認為鄉村發展要以“三農”問題為導向,“資本下鄉”應注重保障農民權益,合理促進傳統農業轉型升級,打造宜居、宜業的美麗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