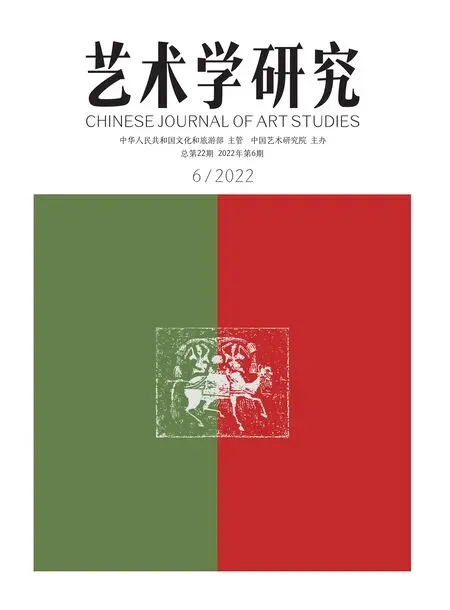銀幕的在場與生命的莊嚴
——媒介更迭時代重析電影本體的理論嘗試
李道新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
21世紀以來,隨著數字人文、人工智能與技術哲學、媒介考古學等研究領域的興起,電影研究也面臨著令人矚目的思維轉向、范式轉換與學術轉型。筆者曾在相關論文中,就這一數字時代的學術生產“趨勢”和“路徑”展開過相對具體的分析和探討[1]筆者相關論述,主要參見李道新:《數字時代中國電影研究的主要趨勢與拓展路徑》,《電影藝術》2020年第1期;李道新:《數字人文、影人年譜與電影研究新路徑》,《電影藝術》2020年第5期;李道新:《數字人文、媒介考古與中國電影“源代碼”》,《電影藝術》2022年第4期。,但在當下這種以跨媒介敘事與融合文化為主要特征的學術語境里,究竟應該如何有效定位,甚至重新定義“電影”,不得不說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
作為一種跟實體性的放映空間(茶館、咖啡廳、俱樂部或影院、劇場、露天)、機械性的放映裝置(發電機、放映機)與沉浸性的具身經歷(前后左右的其他觀眾、黑暗中投向銀幕的光影)不可分割的觀影體驗,“銀幕”不僅成為目光凝聚與身心所歸之焦點,由其衍生出的“儀式化”觀影方式更讓“生命”在此活動中獲得了超越凡俗的特殊表達,當人們從無所不在的影像中望向銀幕時,便獲得了一種同時屬于電影也屬于觀眾的凝視和聆聽。在當今短視頻盛行和流媒體主宰的時代,人們仍然需要電影,電影仍然需要銀幕。因此,想要探尋“電影”在今日的定位,就有必要在媒介考古學與中國電影“源代碼”的視野里,重新考察電影跟“銀幕”及其觀影者的內在關聯。
一
2006年,在討論新舊媒體沖突與融合文化話題時,美國媒介理論家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曾經提到,2004年12月,印度各地的影迷通過具有實時視頻流、支持EDGE(Enhanced Data Rate for GSM Evolution,增強型數據速率全球通演進技術)功能的手機,完整收看了一部觀眾正在熱切期盼的寶萊塢電影《停下,如果可能的話》(Rok sako To Rok Lo)。針對這一據說是人們首次通過手機完整觀看影片的行為,亨利·詹金斯表達了自己的疑惑:“這種電影發行方式究竟是否適合人們的生活還有待于觀察。它會取代人們去電影院看電影嗎?或者人們只是利用它來預覽以后可能會到其他場所觀看的電影的樣片?誰知道呢?”但他隨后也指出,“舊媒體”絕不會壽終正寢,甚至也不會逐漸削弱淡出,它們被迫跟“新媒體”共存;正如印刷文字沒有消滅口語交流,電視沒有消滅廣播,電影也不會消滅劇場和電影院[1][美]亨利·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體和舊媒體的沖突地帶》,杜永明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32—58頁。。
確實,在媒介迭代與知識成果跨學科結合的時代,計算機程序與虛擬攝影機已經將“電影”納入一種更為靈活自由的文化交互界面,所謂“電影式”的感知或“電影化”的體驗,隨著“銀幕”的缺席,已經演變為一個由算法控制面板與屏幕構成的博弈場。在國內,因疫情原因,徐崢導演并主演、歡喜傳媒出品的影片《囧媽》于2020年1月23日宣布撤出春節檔之后,隨即決定上線手機終端和智能電視,并以6.3億元賣給“信息流行業的產品和服務提供商”字節跳動(ByteDance),也因此在電影與娛樂、傳媒等領域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和討論。迄今為止,包括網飛(Netf lix)、愛奇藝在內的大型流媒體平臺,不僅積極介入原本屬于電影本身的生產與傳播環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一個多世紀以來“電影”必須依賴院線發行、在影院放映并通過銀幕呈現的“慣例”。當代的電影雖然沒有消滅劇場和影院,但銀幕的在場已不再必須,銀幕的缺席也不再令人驚奇。
這些現象也讓我們能夠理解,為何數字文化分析家列夫·馬諾維奇(Lev Manovich)在追溯電影銀幕與計算機屏幕各自不同的起源和演變,并對“觀看”與“身體”之間的關系展開歷史性辨析之后,會將電影銀幕歸結為一種必須變得更加動態、實時和交互的計算機屏幕,進而明確指出,幾個世紀以來,人們仍然在凝視著一個矩形平面,這一矩形平面存在于我們身處的真實空間中,作為通往另外一個空間的窗口[2]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MIT Press, 2001), 62-115.。在列夫·馬諾維奇看來,在我們目前所處的屏幕時代,銀幕只是我們“身處的真實空間”的一個側面。
二
然而,如果從最普遍而非最準確的意義上理解“電影”的話,相對不會引起太多爭議的說法是:“電影”仍然必須與“銀幕”聯系在一起。
事實上,當我們在討論“電影”的時候,無論在物質、技術的層面,還是在精神、文化的維度,有且只有“銀幕”能夠作為一種存在和存在的證據,用以表明“電影”曾經的樣貌和特性;也只有將這個現象作為基礎,“電影”才能在理論體系的構建上,跟1895年之前的“前電影”發起有效的對話;跟“電影”誕生以來,甚至遲至電視“熒屏”出現之后的多種視聽方式進行必要的溝通,尤其是跟以電腦“桌面”和手機“屏幕”等移動終端為表征的“后電影”展開辨析,或者分庭抗禮。
遺憾的是,一般電影史、電影理論與電影批評領域受到文本中心主義的深刻影響,在“經典”電影研究中的作者論、類型分析、藝術和美學觀照以及思想和文化闡釋的強大傳統影響下,電影心理學、精神分析學與電影觀眾研究層面的“觀看”“凝視”“夢幻”“意識”“認同”“縫合”等概念,已經受到廣泛關注和深入探討,成為現代電影理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與之相對的,作為電影裝置、觀影機制并直接作用于受眾身心的“銀幕”,以及與之相關的“影院”建筑、“影廳”設施、“觀影”人群、“放映” 實踐和“映片”過程等,乃至它們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至人類精神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問題,卻始終湮沒不彰,或者處在話語的邊緣位置。

“前電影”時期的有聲活動電影機(1895)與“后電影”時期的VR設備(2015),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中國,有關這一結論的顯著例證,可在洪深的《電影術語詞典》(1935)中找到某種“源代碼”。該著作以電影技術、電影機械與電影制作中的基本術語為中心,依序設立“活動影片”“攝影機,鏡箱,開麥拉”“鏡頭,透鏡”“攝影師,開麥拉曼”“隔光片,隔光網,及其他”“攝影場”“燈”“燈紗,反光板,及其他”“背景與布景”“膠片”“洗片”“印片”“制片部”“呆片,呆照,照相,相片”“技巧的鏡頭”“活動卡通”“彩色影片”“有聲電影”“聲帶開麥拉”“濾音器,橫棒桿,及其他”“放映機與銀幕”“編劇”“導演”“廣告,宣傳,及其他”和“科學電影”等詞條。盡管沒有忽略“放映機與銀幕”,但該書在解釋“銀幕(Screen)”時,幾乎完全基于其物質的和技術的維度,“銀幕是一個任何‘平面’,可以把那從放映機里射出來的光,‘混亂反射’入觀眾的眼簾”[1]洪深:《電影術語詞典》,天馬書店1935年版,第216—228頁。。或許正是為了改變這種固有的“銀幕”觀念,《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1991)在“銀幕(Projection Screen)”詞條中開始將其物質和技術維度的解釋內容壓縮,更多地從電影整體的“性能”“質量”和“效果”等角度展開討論,“接受電影放映機、幻燈機或投影器投射的光線,通過反射和透射,映出原拍攝畫面色光影像的屏幕。電影片的藝術效果和技術質量最后是通過銀幕表示出來的。銀幕光學性能和質量的優劣、運用和維護是否得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畫面放映的質量,進而也影響著影片的整體效果”[2]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電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頁。。但遺憾的是,在此后出版的《中國電影大辭典》(1995)里,“銀幕”一詞,又被從技術層面簡單地解釋為一種“放映電影用的白色幕布”[3]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3頁。。有趣的是,在大量的中文著述中,跟“銀幕”相關的表述,大約又等同于“電影”的代名詞。例如,1925年創刊于上海的小報《銀幕周刊》,1929年創刊于沈陽的刊物《銀幕雜志》,以及1981年起人民音樂出版社編輯出版的《銀幕歌聲》,還有臺灣皇冠雜志社1976年出版的論著《銀幕上下談》(魯稚子)、中國電影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文集《銀幕形象創造》(趙丹)等。
在西方,法國學者雅克·奧蒙(Jacques Aumont)與米歇爾·瑪利(Michel Marie)合著的《電影理論與批評辭典》(2002)也是“銀幕”在整體電影理論中“湮沒不彰或邊緣位置”的顯著例證。在這部由著者明確表示“僅僅提及那些創造了或激發了比較深入和系統的批評或理論思考的人物(導演、批評家和理論家)或歷史事件(尤其是類型片)”的辭典里,除了在“技術”一類中的“Projection”詞條里大約涉及跟“銀幕”相關的討論之外,“主題索引”中的其余12類,依次為“批評”“美學”“影片學”“類型;學派”“電影史”“機構”“敘事學”“哲學/人文科學”“精神分析學”“導演”“符號學/語言學”與“理論家”,均為無形的觀念層面的內容,跟電影的“技術”、裝置或任何物質實體無關;即便在“技術”這一類里,跟“蒙太奇”相關的詞條竟然多達6個,但只有“攝影機”和“膠片”等詞條接近于公認的“技術”或裝置、物質概念[4][法]雅克·奧蒙、米歇爾·瑪利:《電影理論與批評辭典》,崔君衍、胡玉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頁。。
值得注意的是,該辭典中的“Projection”詞條并沒有從技術、裝置或物質層面,說明并強調電影放映機(投影機)通過有史以來的各種發明裝置,將影像投射(即“放映”)到特定對象(即“銀幕”)的基本原理和具體過程,而是援引多米尼克·帕伊尼(Dominique Pa?ni)的觀點,將“Projection”解釋為“一個影像從一處傳至另一處的光亮現象,又是如此產生的影像的屬性,也是這一物理運動的想象性和虛構性結果”[5][法]雅克·奧蒙、米歇爾·瑪利:《電影理論與批評辭典》,崔君衍、胡玉龍譯,第182頁。。不得不說,這一解釋不僅模糊了“放映”本身的獨特機制,而且明確地避免了將“銀幕”當作“光亮現象”所傳達的“處所”,傾向于無視、解構甚至取消“放映”“影院”及“銀幕”之于“技術”“想像”和“虛構”的重要性。
其實,這種針對“放映”“影院”及“銀幕”的無視、解構和取消策略,既有“前電影”的歷史基因,又是“后電影”的必然結果。這也恰恰反證了“銀幕”的在場,不僅使“電影”成其為“電影”,而且使觀眾成其為“人”;正是通過“銀幕”,被定義的人性在暗黑的環境中得到了喚醒,生命的莊嚴也在隨時間而消逝的電流、光影與音聲里無限升騰。
在《詞語》(1963)一書中,58歲的哲學家薩特不厭其煩而又極為細膩地描述了7歲時的“我”被母親帶去電影院看電影的情景,這是半個世紀后薩特還能清楚地記得和反復回味的一切,是他自己跟電影在一起的“共同的童年”。結合薩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軌跡可以看出,如此精心的描述純屬作者的有意為之:
電影已經開演了。我們搖搖晃晃地跟著女引座員往前走,我覺得自己是個從事秘密工作的人,在我們的頭頂上,有一束白光穿過大廳,白光里塵土飛揚,煙霧繚繞。一架鋼琴發出馬的叫聲,紫色的梨狀燈泡在墻上閃閃發光,一股似消毒劑的油漆味道直嗆得我喉嚨難受。黑暗中到處是人,里面的氣味與梨狀燈泡已在我身上溶合在一起了,我吞食著太平門上的安全燈,飽嘗了它們的酸澀味道。我的背擦過別人的膝蓋,我在一只吱嘎作響的椅子上坐下,母親把一條折疊起來的毯子塞在我屁股下,讓我坐得更高些。我終于看見了銀幕,我發現了一支熒光粉筆和一幅幅閃動著的畫面,畫面被一陣大雨劃上了一條條的線,老是在下雨,不管是在陽光下還是在房間里。有時候,一顆熊熊燃燒的小行星穿過男爵夫人的客廳,可她似乎毫不驚慌。我喜歡這種雨,喜歡這種能穿透墻壁的無休止的擔憂。鋼琴家開始演奏《芬格爾洞》的序曲,大家都知道罪犯要出場了,男爵夫人驚恐萬狀,但她那被弄得污穢不堪的美麗的臉龐卻被一行淡紫色的字幕取代了,“第一部分劇終”。觀眾們突然從麻痹狀態中醒悟過來,燈打開了。我這是在哪里?在學校?在行政機關?沒有絲毫的裝飾,成行的折疊式座椅排列在那里,露出底部的彈簧,墻上亂七八糟地涂著赭色顏料,地板上滿是煙蒂和痰跡。大廳里一片嘈雜聲,人們重新創造了語言,女引座員在大聲叫賣英國糖果,母親也給我買了一些,我把它們塞進嘴里,就象在吮吸安全燈。人們揉著眼睛,這才發現坐在身邊的那些人,其中有士兵,有在附近幫傭的女仆,有一個瘦骨嶙峋的老頭在嚼著煙草,還有一些不帶帽子的女工在大聲笑著,所有這些人都不屬于我們那個階層,幸虧在正廳后排的觀眾里,不時出現一些在移動的大帽子,這才使人略微放心。[1][法]薩特:《詞語》,潘培慶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84—85頁。
在薩特的描述中,7歲的“我”喜歡看跟觀眾“更為接近”的電影,因為在1912年左右的地區電影院里,大家都“平等地”坐在“不舒服”的座位上。“這種新的藝術是屬于我的,就像它屬于所有人一樣。”為此,薩特表示:“就智力年齡來說,我和電影是同齡,我七歲,可我已會閱讀了,電影已十二歲了,可它還不會說話。人們說,它還在發展初期,它將會有很大的進步,我想我們將一塊長大。”[2][法]薩特:《詞語》,潘培慶譯,第86頁。
相信電影會跟自己一塊長大的薩特,最終仍然主要依靠文字的閱讀和寫作創造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但其在《影象論》及相關著述中,通過對胡塞爾的批判,從根本上區分了知覺材料(惰性的外在性)和影像材料(內在的自發性),進一步開鑿了通向想象意識現象學的道路,為影像研究帶來了重要的啟迪[1]參見[法]薩特:《影象論》,魏金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其實,宣稱文字“強暴了人”、認為文字文化“屬于非物質的、抽象的、理性的文化”并“把人的軀體變成了普遍的生物機器”的匈牙利電影理論家巴拉茲·貝拉,早在1924年出版的《可見的人——電影文化 電影精神》一書中就張開雙臂,熱情歡呼著電影攝影機這種“新機器”所創造的一種“根本改變人類文化性質”的新的“視覺文化”。按照巴拉茲·貝拉的理論,電影所展現的運動、人的面部表情和手勢等才是人類最早的母語,我們正在開始慢慢回憶并力求重新掌握這種母語。它還很粗糙、原始,與用文字表現的現代藝術相比還有很遠的距離;它雖然吃力而笨拙,卻經常表達出連語言學家都無法表達的東西。這是由于它比會說話的舌頭更早更深地在人類心中扎了根,同時它又是全新的事物。我們要從頭到腳用整個軀體(不只是用文字)表明我們是“人”,不要把自己的軀體當成某種陌生東西或實用工具搬來搬去。即將到來的新的動作語言,正是來源于我們這個痛苦的欲望,而這種欲望只有當已變為沉默的、被遺忘的、看不見的但卻有著血肉之軀的人被喚醒時才能產生。總之,電影藝術的魅力就在于:它將把人類從巴別塔的咒語中解救出來;當人最終變成完全“可見的人”時,盡管語言不同,他也能“辨認出自我”[2][匈]巴拉茲·貝拉:《可見的人——電影文化 電影精神》,安利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7頁。。迄今為止,在賦予電影以生命莊嚴的努力中,沒有人比巴拉茲·貝拉走得更遠。
三
顯然,是“電影”而非其他媒介建立了電影的放映機制,創造了區別于咖啡館和劇院的“影院”系統,并引入了迥異于舞臺空間的“銀幕”裝置。這一“經典”的電影放映機制,因流動放映的需要和露天電影的形式而弱化了“影院”系統的必要性,這也使“銀幕”成為這一放映機制中最顯要、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事實上,與發電機的電流、放映機的運轉和光線在暗黑環境中的投射一樣,“銀幕”不僅必須在場,而且具有不可觸摸的神秘性以及喚醒觀眾的儀式功能。
然而,媒介考古學與相應的“前電影”歷史研究表明,在“前電影”時代,無論是作為家庭娛樂的光學裝置,如立體成像鏡、留影盤、費納奇鏡、西洋鏡和活動視鏡,還是活動電影放映機、手搖電影放映機等指令性操作放映機器,大約都可以將其重新定位為一種“家庭娛樂設施”。按照德國學者旺達·斯特勞芬(Wanda Strauven)的觀點,與“電影”時代習慣于坐在標準化座位和銀幕對面的觀眾不同,19世紀亦即“前電影”時代的觀察者從不坐在座位上,也不會乖乖地只看放映機投射在銀幕上的畫面;與此相反,他們會親自操作放映機來直接控制畫面的播放和播放的畫面。通過僅供一人使用、需要雙手操作與自由調整手柄、隨時中斷放映等強調消費者身體與相關裝置互動的參與方式,“前電影”為人類提供了一種以身體接觸攝影機/放映機亦即“觸摸屏幕”的觀影模式。
旺達·斯特勞芬頗有意味地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家庭影院,再一次把觀影模式帶回其原初的形態亦即“前電影”時代。家庭影院強化了作為家庭設施的電影的潛在游戲功能,影院里的電影放映裝置被祛魅,“銀幕”相對縮小成下拉式的投影幕布、家具中的電視熒屏或個人擁有的電腦屏幕,包括投影出來的活動影像在內的所有一切都是觸手可及的。與在電影院不同,觀察者和電影觀眾不會因觸碰了銀幕而遭到懲罰,“觸摸或者不觸摸,將不再是個問題”[1][德]旺達·斯特勞芬:《觀察者困境:觸摸,還是不觸摸》,[美]埃爾基·胡塔莫、[芬蘭]尤西·帕里卡編《媒介考古學:方法、路徑與意涵》,唐海江主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159頁。。
正是在這一方面,“后電影”跟“前電影”殊途同歸。在短視頻盛行和流媒體主宰的“后電影”時代,電影和它的觀眾往往會因相對隨意的鏈接而產生不斷偶發的聯結。這是一種無需特別相約的,可以隨時暫停、偶爾慢放和經常快進的觀影模式。這種“個人化”與“隨意”讓電影放映以及“銀幕”本身曾經擁有的神秘魅力和儀式功能消失殆盡;觀察者和觀眾獨自操縱或者默默伴隨著身邊的遙控器和電腦鍵盤,在與“后電影”永無止境的互動中體驗著持續的落寞與永恒的孤獨。
如果說,電影的發明以及電影藝術的進步,曾如巴拉茲·貝拉所言“挑戰”了文字書寫的人類歷史,把人類從巴別塔的咒語中“解救”了出來,那么在“前電影”里并不真正存有,以及在“后電影”中已經缺席的電影放映機制及其“銀幕”的在場,仍將重新喚醒孤獨的人群,通過彼此之間身心的交流撫慰,共同抵抗各種媒介和海量數據所造成的熟視無睹或無動于衷,重新賦予電影內外的生命其應有的莊嚴。
跟哲學家薩特一樣,通過書寫放映機制及其“銀幕”記憶之于童年往事和人生經驗的重要性,幾乎在有史以來所有杰出的電影人那里都有所體現;這些杰出的電影人都對電影和“銀幕”表達了超出常態的“迷戀”和“狂熱”。英格瑪·伯格曼如此,弗朗索瓦·特呂弗如此,黑澤明也不例外。這將成為電影、電影人、電影放映和銀幕本身的記憶,在“后電影”的撲朔迷離中克服身份的迷惑,重建認同。
在1987年出版的自傳《魔燈》中,伯格曼曾經描述,童年時的自己不僅對擁有一臺電影放映機的渴望“勝過一切”,而且對第一次去電影院看電影的經歷記憶猶新:
影片在斯圖雷電影院放映,我坐在半圓形看臺的第一排。對于我,這就是開始。我沉浸在一股經久不息的熱情之中。無聲的人影轉過他們暗淡的面孔朝向我,用無聲的語言與我心中最神秘的感覺對話。六十年過去了,什么都沒有變,我依舊如此狂熱。[2][瑞典]英格瑪·伯格曼:《魔燈:英格瑪·伯格曼自傳》,張紅軍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頁。
同樣,特呂弗也在《影評人的夢想是什么?》中描述了自己逃學后不付錢偷偷溜進電影院看電影的經歷。隨著“看電影時引發的情感變得更加強烈”,特呂弗寫道:“我開始感覺到一種強烈的需要,想要‘進入’電影之中。我坐得離銀幕越來越近,為的是可以忽略電影院里其他的人和事的存在。……我常被別人問及,在與電影談的這場戀愛中,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想要成為導演或影評人的。說實話,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想離電影近一點,再近一點。”[3][法]弗朗索瓦·特呂弗:《我生命中的電影》,黃淵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頁。不得不說,特呂弗這種想要無限逼近銀幕并“進入”電影之中的強烈情感,跟黑澤明在其自傳《蛤蟆的油》(1990)中所表達的感情異曲同工。在自傳里,黑澤明表示:“從我身上減去電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1][日]黑澤明:《蛤蟆的油》,李正倫譯,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頁。
正因電影和“銀幕”跟人的生命之間始終存在著如此深切的關聯性,法國當代思想家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才會在電影人類學與人類電影學相互交織的視野中考察“電影”和“人”的命題。在《電影或想象的人:社會人類學評論》(1956)一書中,埃德加·莫蘭同樣回顧了自己作為“在成長過程中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的一代人,電影是如何以其“強大的幻覺力量”控制人們的身體、激發人們的情欲并帶來一生中“最強烈的震撼”的。對他來說,“銀幕上的陰影”就是一道“動人心魄的靈光”,電影把“化身”和“幽靈”的古老世界神奇地再現于銀幕,這些“化身”和“幽靈”使人癡迷陶醉,難以自拔;它嵌入人們的身體,向人們提供了未曾經歷的生活,并以夢想、欲望、向往和規范滋養著人們的生活。更加令人驚奇的,不僅是那些能夠捕捉和播放影像的“神奇機器”,還有人類神奇的“心理機器”;作為新生和整體的精靈,“電影”是一種“精神機器”“思想機器”或“機器人”;“電影”沒有雙腿、身體和頭顱,但每當光束投向“銀幕”,這臺“人類機器”便開始運作,“銀幕”便成了一種新目光,并取代了人們的目光[2][法]埃德加·莫蘭:《電影或想象的人:社會人類學評論》,馬勝利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頁。。
嵌入人類身體、取代人類目光并作為人類機器的“電影”,在獲得了人類文化的新維度之后,又獲得了人類與電影的二位一體,人類電影與電影人類合二為一。當人類把現實通過電流和光影投射到銀幕之上并展開自我想象的時候,銀幕之上的人類的自我想象也就被成功地納入人類的現實。
這種在想象與現實之間自由游走,并以幻為真、技進于道的文化技術實踐,在電影被放映到銀幕并獲得正式的命名之初,或者在19世紀末電影剛從歐美進入世界各地之際,便已經被世界各地的人們所體認;而在當今的“后電影”時代,數字電影和電影的數字化在摧毀電影放映裝置及其“銀幕”的時候,也在重建一種更大規模、更有深度的電影放映機制和一塊又一塊巨幅“銀幕”。如媒體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留聲機 電影 打字機》(1986)中所言,既然“象征界”已經真正變成了機器的世界,“數字”也就成了一切“生命”的關鍵[3][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聲機 電影 打字機》,邢春麗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頁。。在以數字技術為特征的、擁有巨幅“銀幕”的電影放映過程中,“生命”一如往昔,可以而且必須被“電影”喚醒、震撼并與其合為一體。
四
即便如此,在《技術圖像的宇宙》(1985)一書里,巴西哲學家威廉·弗盧塞爾(Vilém Flusser)也將電影歸為一類“特殊技術圖像”。與一般媒體理論家、影像論者或電影研究者不同,弗盧塞爾并不認為電影是一種必須在影院播映并投射到公共銀幕上的圖像,因為它仍舊依托于一種源自19世紀的技術,亦即接收者需要走到發送者那里才能收到信息,而這種技術已經不再適應數字技術及其社會結構。對于上文提到的在“后電影”時代重建電影院、電影放映與巨幅銀幕的事實,弗盧塞爾并不認為這種努力是值得的。在他看來,觀眾與銀幕之間存在一種共識,那是在銀幕與觀眾之間的反饋中建立起來的契約,但在技術圖像主導的信息社會中,核心問題是要中斷以往的反饋回路,將圖像轉變成人與人之間的媒介,在圖像與人類之間相互交流并使社會變得“人性化”[1][巴西]威廉·弗盧塞爾:《技術圖像的宇宙》,李一君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34—40頁。。也就是說,在信息社會,電影放映機制及“銀幕”是可以消失的。
我們知道,作為電影的物質基礎,膠片總在持續不斷地硝化和酸化之中,數字媒介也有自己的退降和衰竭形式;跟音樂演奏一樣,電影放映及面向銀幕的觀看,每一次都是獨一無二且不可復現的個人/個性體驗,并跟生命本身聯系在一起。正如2001年保羅·謝奇·烏塞(Paolo Cherchi Usai)在《電影之死:歷史、文化記憶與數碼黑暗時代》一書中所討論的相關問題,盡管每一種藝術都會遭到時間的蹂躪和空間的改變,但電影本質上更是一種“自動破壞”和“面向死亡”的媒體,通過放映機投射在銀幕上的動態影像/人類生命,總有太多變量能夠決定其觀賞品質和特定模式,并注入光源性質、放映設備、影像載體的物理結構以及觀影所在的建筑空間[2]參見 [澳]保羅·謝奇·烏塞:《電影之死:歷史、文化記憶與數碼黑暗時代》,李宏宇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因此,只要人們認為觀影體驗是可以無限次重復的,那么任何為避免活動影像受到環境和心理因素影響而致毀滅所做的努力,就注定是徒勞。
但無論如何,只要我們堅持從電影放映和觀影體驗的角度面對電影,而不是單從作者論、文本分析和類型研究的視野展開電影的藝術、美學觀照和思想、文化闡釋,那么“銀幕”的在場就是必需的,并且值得深入討論。也恰因此,我們可以回到中國儒道天地合氣、萬物自生,陰陽和合、生生不息的生命觀念與西方狄爾泰、伯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學,尤其以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現象學、海德格爾的詩意棲居之思等,構建一種以“銀幕”為核心的電影新本體論,這將是一種非常具有價值的理論嘗試。
法國作曲家、電影創作者和理論家米歇爾·希翁(Michel Chion)在《視聽:幻覺的構建》(1990)一書中,開門見山地描述了自己跟銀幕觀影聯系在一起的獨特體驗:
影院燈光暗下來,電影開始了。殘酷而神秘的影像出現在銀幕上:一臺電影放映機轉動著,電影的某個特寫畫面通過它,出現了嚇人的動物祭品的影像、一個釘子被釘入手掌。然后,在更為“正常”的時間里,出現了一個停尸房。我們看到一個男孩的尸體,像其他尸體一樣,但他忽然活了過來——他起身、讀書、他傾向銀幕前面,隨后,在他的手前面,看起來一張美麗的女人臉龐正在成形。[3][法]米歇爾·希翁:《視聽:幻覺的構建》,黃英俠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頁。
這是英格瑪·伯格曼影片《假面》(Persona,1966)的開場段落。為了通過銀幕真正地看到和聽到這樣的電影,米歇爾·希翁還寫過一本名為《洞穿銀幕》(La Toile trouée)的著作[4]Michel Chion, La Toile trouée: La Parole Au Cinema (Editions de l’Etoile, 1988).。
“洞穿銀幕”,正是生命獲得莊嚴的瞬間,也可看作生命向生命的一種崇高的致敬,電影和它的觀眾也組成了一對相約已久的,不可暫停、無法慢放和拒絕快進的生命共同體。銀幕是觀眾的身心在電影裝置和陌生人群中的定位,它的在場是電影的呼喚,電影的呼喚便是生命的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