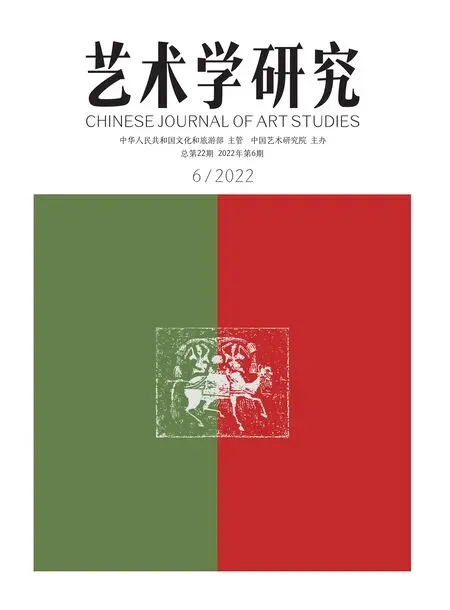“影游融合”的媒介視角:悖論、困境與關鍵問題
趙宜 賈天翔
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
引言
2022年上映的電影《神秘海域》(Uncharted)在全球獲得4.01億美元的票房收入,成為歷史上票房排名第4的游戲改編電影,市場成績僅次于《狂暴巨獸》(Rampage,2018年,4.28億美元)、《大偵探皮卡丘》(Detective Pikachu,2019年,4.33億美元)和《魔獸》(Warcraft,2016年,4.39億美元)[1]數據來源:https://www.boxoff icemojo.com,2022年7月14日。,并位列2022年全球電影票房市場的第10名。但相較于已邁入“15億美元俱樂部”的全球歷史票房前十的那些“頭部電影”,以及5.43億美元的全球歷史票房200名“準入門檻”[2]當前的全球電影歷史票房第10名是15.15億美元票房收入的好萊塢電影《速度與激情7》(Furious 7,2015),第200名則是5.43億美元票房收入的動畫電影《卑鄙的我》(Despicable Me,2010)。參見https://www.boxoff icemojo.com,2022年7月14日。,游戲改編電影在全球電影工業中的市場地位仍多少顯得無足輕重。
相比游戲改編電影不溫不火的市場表現,今天的電子游戲市場在體量上早已遠超電影,成為娛樂工業和媒體產業中最具經濟影響力的媒介。《大偵探皮卡丘》改編自風靡全球的任天堂公司游戲IP《精靈寶可夢》(Pokémon)。作為全球最暢銷的游戲系列,從1996年開始發售的《精靈寶可夢》在各類媒體和主機平臺上的銷售總成績已經突破100億美元[1]Katharina Buchholz, “The Pokémon Franchise Caught’ Em all,” accessed July 31, 2022,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4277/media-franchises-withmost-sales/.;《魔獸》改編自暴雪娛樂公司(Blizzard Entertainment)的同名游戲系列,該IP還包括多人在線角色扮演游戲《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和手機卡牌游戲《爐石傳說》(Hearthstone),全球綜合銷售成績已突破230億美元[2]Jonathan Leack, “World of Warcraft Leads Industry With Nearly $10 Billion In Revenue”, accessed July 31, 2022, https://www.gamerevolution.com/features/13510-world-of-warcraft-leads-industry-with-nearly-10-billionin-revenue#/slide/1.。
全球電子游戲產業與電影工業的市場地位,是我們在今天討論這兩種媒體藝術之間跨媒介生產的現實起點。但不難發現,當下以“影游融合”為代表的電子游戲與電影的跨媒介生產活動中,處于經濟效益下風的影視工業依舊占據主導地位并擁有更高的話語權。
在工業生產領域,好萊塢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圍繞電影產品展開特許經營權的跨媒介開發。彼時,以華納收購雅達利公司(Atari)為標志,剛剛立足家用主機市場、成為獨立媒體產業的電子游戲迅速被納入電影工業的整體版圖。近年來,中國文娛產業圍繞“IP開發”和“泛娛樂”等概念提出的“影游融合”觀念,則是在本質上延續了好萊塢圍繞特許經營權的跨媒介開發邏輯。在批評領域,電影與電子游戲兩種媒介的結合所產生的議題引起了近年來中文學術界,尤其是電影學界的廣泛興趣。在這些討論中,一方面,有觀點延續了文娛產業對“影游融合”概念的樂觀估計,并建構出了基于電影研究視角的“影游融合”批評話語[3]參見范志忠等:《影游融合:中國電影工業美學的新維度》,《藝術評論》2019年第7期;陳旭光等:《論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學與想象力消費》,《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饒曙光等:《“影游融合”與共同體美學》,《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等等。;另一方面,對電影未來感到憂慮的學者們則對兩種媒介的結合前景持更保守的態度[4]參見劉帆:《VR不是電影藝術的未來》,《文藝研究》2018年第9期;楊世真:《電子游戲改編電影的基因裂變與跨界風險》,《當代電影》2018年第10期。。
電影對電子游戲在媒介史上的“地位”優勢,構造了二者在當下合作中不平衡的產業鏈與評價體系。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和媒介,電影主導了自它發明以后的人類視覺文化慣例并影響了人類對世界圖景的想象模式。與之相對應的,電子游戲至今還未能有效申明自己獨立的藝術價值。然而今天的現實卻是,不僅全球電子游戲市場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有著遠超影視市場的體量,電子游戲自身也因其對實時屏幕、操作界面和算法邏輯的有效組織,而成為最能夠代表數字技術時代的媒介。可以說,以電影的命運為出發點的“影游融合”話語,遮蔽了對兩種媒介融合時面臨的重要問題——關于電子游戲蘊含的豐富文化與美學潛力及其作為新媒介的活躍生命力的討論。
在電子游戲對電影的產業、文本與美學產生持續影響的21世紀初,延續法國電影新浪潮與《電影手冊》傳統的理論家讓—米歇爾·傅東(Jean-Michel Frodon,又譯弗羅東)對電子游戲與電影的關系進行過評論,這些評論也常被后來的學者引用。傅東將電子游戲與電影的四種關系解釋為“引用”“評價”“改編”和“結合”,并給出基于兩種媒介語言結合的電影“改良”路徑。傅東討論的結合問題主要發生在敘事和電影語言層面,但今天,電子游戲與電影之間正發生更激進的結合,例如產生了以“引擎電影”(Machinima)為代表的全新電影制作方式。相比在敘事和電影語言層面的影響,由實時屏幕、操作界面和算法邏輯主導的自動化機制,正在對兩種媒介的未來產生更深刻的改寫:電子游戲正在生產電影。
一、電子游戲與電影:不平等的“融合”
2014年,國產網頁游戲開發公司游族網絡宣布拿到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系列的影視化改編權,并依托新成立的游族影業開展“F3模式”下的“影游聯動”規劃[1]《游族影業成立 影游聯動強化IP布局》,http://www.gamelook.com.cn/2014/11/191488,2022年6月28日。。盡管游族影業至今未能推出《三體》的電影版,但這部科幻文學“頂流”的IP影響力仍然讓這家新成立的影視公司賺足了關注,并且讓基于IP改編邏輯的“影游聯動”產業模式也成了明星概念。此后,好萊塢的游戲改編電影《魔獸》被引進國內后的不俗票房,進一步激發了文娛產業對電子游戲與電影相結合的開發興趣和市場信心。不久,萬達影業以26億元收購游戲公司“互愛互動”,并將“多元化定制IP”作為游戲開發戰略;而騰訊、網易、巨人等國產游戲頭部企業則相繼宣布成立獨立部門,以開發游戲版權改編影視劇。由此,電子游戲與影視行業形成了規模化的跨界聯動。
2015年,網劇《花千骨》收獲超高播放量,獲得IP授權的同名手游也借其熱度一炮而紅。之后,《瑯琊榜》(2015)、《三生三世十里桃花》(2017)、《慶余年》(2019)等“爆款”網絡劇紛紛推出同名手游并邀請劇中飾演過角色的明星做代言。于是,電子游戲與電影的跨界生產,成為影視產業“網文改編熱潮”之后的又一個新“風口”。在這股發展熱潮中,最初充滿商業口號意味的“影游聯動”概念也在越來越多的闡釋與討論中逐漸被確立為“影游融合”[2]張玉玲、滕華:《影游融合給我們什么啟示》,《光明日報》2016年8月4日第5版。這一更具探索性的話語,指向兩種產業之間更深層次的媒介融合理念與趨勢。但在這些被稱為“融合”的改編案例中,作為衍生品的游戲產品在影視劇熱度退去后,便迅速面臨玩家流失的經營困頓:《花千骨》手游的官網新聞活動停留在5年前[3]《〈花千骨正版〉年末新版今日上線 新增四大玩法》,http://hqg.sjwyx.com/news/506056.html,2022年6月28日。;而上線時間落后其3個月的《瑯琊榜》手游更是存活不足1年就宣布下架[4]《〈瑯琊榜〉手游停止運營公告》,https://www.936u.com/app/16/6468.html,2022年6月28日。;《慶余年》手游在上線首周進入IOS暢銷榜后又迅速跌出,1個月后甚至難以進入細分類型熱度排行前50。可以發現,在“影游融合”的話語下,影視劇對電子游戲產業的賦能卻是非持續性的。這暴露出了兩種媒介產業跨界融合時的困境:電子游戲始終扮演著影視產業鏈下游的、低附加值的衍生品角色。與兩者的市場地位不同,在媒介產業的價值鏈中,影視工業有著遠高于電子游戲的產業地位。
但這并非中國文娛產業的獨特困境,恰恰相反,這種產業地位的不平等不僅是全球性的,而且在電子游戲產業剛剛興起的時代便已經存在。1972年,新成立的雅達利公司依靠艾倫·奧爾康(Allan Alcorn)制作的《乓》(PONG)開啟了北美電子游戲的家用主機時代。與此同時,電影業務增長進入滯脹時期的華納公司看重電子游戲的消費潛力,豪擲2800萬美元并購雅達利,并向其追加1.2億美元的投資[1]Clare M. Reckert, “Warner Signs Pact to Purchase Atari,”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8, 1976, 51.。手握巨資的雅達利次年便推出劃時代主機——“雅達利2600”。作為今日家用游戲主機的起點,“雅達利2600”不僅以其搭載游戲的多樣性獲得消費者青睞,更為跨媒介改編產品提供了設計和消費載體。1982年,在《乓》問世10年后,“雅達利2600”成為世界銷量第一的家用游戲主機。
而此時,好萊塢也完成了由電影制片廠向跨國媒體集團和全產業鏈開發的轉型。不久,好萊塢內部的電子游戲“頭號玩家”斯皮爾伯格就指名設計師霍華德·斯科特·沃肖(Howard Scott Warshaw)為其電影《奪寶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1981)制作游戲版本。與大眾預想的相同,這位天才游戲設計師耗費10個月精心打造的《奪寶奇兵》“雅達利2600”版同樣斬獲超百萬銷量。為了延續《奪寶奇兵》的成功,不久之后,華納又向環球影業支付了2500萬美元的版權費用獲得斯皮爾伯格新片《E. T.外星人》(E. T. the Extra-Terrestrial,1982)的游戲開發權,并繼續邀請沃肖制作。但此時的華納和雅達利更愿意相信斯皮爾伯格和這部全球票房冠軍電影的IP價值,他們只給了沃肖5周的開發時間,卻投入巨資為這款簡陋的貼標游戲進行電視廣告營銷[2]Bruce Chadwick, “‘E. T.’ and Pals go Video—Game manufacturer Plunge into Film Business with Limited Success,” Times-Advocate, February 26, 1983, 85.(圖1)。于是,在銷售150萬份游戲卡帶后,游戲惡評如潮水般涌向雅達利公司,超百萬份無人問津的游戲卡帶被迫進入垃圾填埋場[3]“Searchers unearth grave of ‘E. T.,’ the video game Atari wanted us to forget,” accessed July 4, 2022, https://edition.cnn.com/2014/04/27/tech/gaming-gadgets/atari-et-video-game/index.html.。受版權費用、營銷推廣和超額生產共同造成的巨大虧損影響,在游戲行業素有聲望的雅達利公司瀕臨破產,這一事件也被稱為“雅達利大崩潰”(Atari Shock)。受該事件影響,整個北美游戲市場遭遇近3年的冰川期,市場規模由32億美元暴跌至1億美元,而在市場恢復后,雅達利在北美和全球的市場霸主地位也易位于來自日本的任天堂公司[1]Cassidy Ward, “Science Behind the Fiction: How Nintendo Saved and Redef ined the Game Industry,”accessed July 4, 2022, https://www.syfy.com/syfy-wire/science-behind-the-f iction-how-nintendo-saved-and-redef ined-thegame-industry.。

圖1 《E. T.外星人》的電影劇照(上)和雅達利版《E. T.外星人》的游戲界面(下)
這段“好萊塢往事”充分暴露出電子游戲與電影在跨界生產中的不平等地位,來自華納的行政命令和電影工業的評價體系輕易就掩埋了新生的電子游戲產業參與跨媒介生產的其他可能性。在電子游戲產業規模化發展的最初階段,它就如受到詛咒般被嵌入電影工業主導的跨媒介產業鏈當中。直到今天,在“影游融合”話語下的那些基于熱門影視IP衍生的游戲案例,依舊未能擺脫兩種媒介進行結合的先天性不足,因此也遠談不上實現兩者的融合。
二、銀幕:融合的界限
近兩年,擁有超高熱度的游戲IP也開始成為國產影視劇的改編素材:2021年上映的電影《侍神令》改編自手游《陰陽師》,后者在正式上線后日活躍玩家數迅速突破1000萬,是網易旗下的現象級游戲[2]網易游戲:《霸榜不止刷屏不息〈陰陽師〉DAU強勢突破1000萬》,https://yys.163.com/news/off icial/2016/10/24/22592_649780.html,2022年7月8日。;同年上映的《真·三國無雙》電影則改編自擁有21年歷史、至今仍在開發續作的日本同名動作游戲系列。但由游戲改編而來的電影頻頻遭遇市場與口碑失敗:制作成本逾6億元的《侍神令》僅獲得2.74億元的票房收入和5.3分的豆瓣評分;《真·三國無雙》不僅遭遇更嚴重的票房慘敗(1557.7萬),網絡口碑也在一片批評中跌至豆瓣3.9分。回過頭看,為中國“影游融合”目標注入市場信心的電影《魔獸》雖然在中國收獲2.21億美元,但全球總票房卻僅有4.3億美元。好萊塢票房分析師杰克·伯克(Jeff Bock)對此直言:“如果這部電影沒有在中國火起來的話,它就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品。”[3]Pamela Mcclintock, “Box-Office Analysis: ‘Warcraft’ Avoids ‘Utter Failure’ But Will Still Lose Money,” accessed July 8, 2022, 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box-office-analysis-warcraftavoids-910268/.事實上,比起文學、戲劇或漫畫改編作品,好萊塢主導的游戲改編電影不僅市場效果有限,而且歷來以“爛片”居多。
因此,即便從今天看來,傅東對電子游戲改編電影的判斷也沒有過時:“這一過程本身并沒有什么意義,只不過證實了,至今為止改編電子游戲所帶來的美學和經濟方面的影響都讓人失望。”[4][法]讓—米歇爾·弗羅東:《電影的不純性——電影和電子游戲》,楊添天譯,《世界電影》2005年第6期。比影視IP改編電子游戲的情況更糟糕的是電子游戲IP影視化的成果,其同樣很難符合我們對“影游融合”的產業預期。
相比改編,傅東認為兩者的“結合”更有討論的價值,他將這一過程理解為電子游戲對電影的“改良”,并將強調電影與電子游戲的媒介地位(而非市場或產業地位)作為其出發點。自然地,相比電影對電子游戲的影響,他更關注新媒介對舊媒介的激發,在《電影的不純性》一文開端,他就在注釋中強調了這一立場,“這里討論的只是電子游戲對電影的影響,至于電影對電子游戲的影響則為另一論題”[5][法]讓—米歇爾·弗羅東:《電影的不純性——電影和電子游戲》,楊添天譯,《世界電影》2005年第6期。。電子游戲與電影“結合”的觀點也更接近當下“影游融合”的問題意識,因此與傅東的出發點相似,今天討論“影游融合”的學術話語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依舊是關于電影命運的討論。
不過,即便傅東確實意識到了電子游戲所代表的數字媒介對電影的沖擊,因而試圖為電影尋求“退而求其次”的新地位,但這樣的出發點卻注定了其視野的保守性。作為新媒介代表的電子游戲,其歷史使命是為舊媒介的“改良”提供給養嗎?問題在于,一直以來,電影與電子游戲的進一步有效融合就面臨兩個困境:一方面,電影從電子游戲中獲取的靈感是極其有限的;另一方面,用電影藝術的理念和標準錨定電子游戲的思維也是長期和一貫的。
第一個困境不僅體現在電影在改編成功電子游戲文本時的糟糕表現,也體現在兩者難以兼容的語言系統中。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影史可以發現,許多帶有后現代反敘事色彩的影片都在通過借鑒電子游戲的敘事邏輯來解構經典戲劇結構[1]如《落水狗》(Reservoir Dogs,1992)、《低俗小說》(Pulp Fiction,1994)、《羅拉快跑》(Lola rennt,1998)、《記憶碎片》(Memento,2000)等。;《黑客帝國》(The Matrix,1999)系列中“子彈時間”“穿梭虛實”等時空表現,顯然與電子游戲的視聽體驗有直接的聯系;而今天以MCU系列和《頭號玩家》(Ready Player One,2018)等為代表的好萊塢“頭部電影”也幾乎都體現出了“時空設定游戲化、情節結構游戲化、視覺呈現游戲化”[2]施暢:《游戲化電影:數字游戲如何重塑當代電影》,《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1年第9期。的特征。但電子游戲最重要的特征:實時屏幕、交互性界面和基于算法生成的自動化邏輯,卻始終未能在主流的銀幕/熒屏作品中形成影響。
事實上,在“影游融合”概念誕生之初,就有國內學者指出“影游共生最大的障礙并非銀幕/屏幕的介質跨越,而是兩種不同的符碼象征體系之間的天然鴻溝”[3]聶偉、杜梁:《泛娛樂時代的影游產業互動融合》,《中國文藝評論》2016年第11期。。正因如此,即便雷蒙德·貝盧爾(Raymond Bellour)考察了電影《大象》(Elephant,2003)中呈現出的電子游戲式的互動性特征,并提出“同一互動性”的假設[4][法]雷蒙德·貝盧爾:《從現實生活中提取》,轉引自讓—米歇爾·弗羅東《電影的不純性——電影和電子游戲》,楊添天譯,《世界電影》2005年第6期。,傅東仍對這種“旨在人為地超越電影和電子游戲之間不可消除的差異性”持保留意見[5][法]讓—米歇爾·弗羅東:《電影的不純性——電影和電子游戲》,楊添天譯,《世界電影》2005年第6期。。在今天的討論中,學者們也傾向認為以“互動”為代表的媒介特性對電影的介入起到的作用更多是干擾而非助益[6]姜宇輝:《互動,界面與時間性——電影與游戲何以“融合”?》,《電影藝術》2019年第6期。,并認為電子游戲所追求的“高擬真”“沉浸/臨境感”和“交互性”擬真生態等美學目標均非電影的必要核心體驗,甚至是非電影的[7]劉帆:《VR不是電影藝術的未來》,《文藝研究》2018年第9期。。
不過,今天的使用者可以在微軟公司的游戲主機Xbox中訂閱HBO Max的流媒體影視服務,也可以在流媒體影視平臺網飛(Netf lix)上訂閱“云游戲”服務,這意味著“觀看”和“玩耍”的行為可以在一個終端上完成;并且如果我們不拘泥于“影游融合”中對影視媒介的保守視角,把“觀看到的一切”作為一種整體的“敘事”的話,那么在視頻網站中流行的游戲直播行業就是電子游戲和影視媒體融合的又一個成功案例——2022年,在中國游戲產業進入增速放緩的存量時代時,游戲直播卻以超10%的增速占據游戲市場逾三成份額[8]參見TalkingData:《2022年中國游戲直播行業白皮書——新平臺新機遇,千億游戲直播行業變道增長》,http://mi.talkingdata.com/reportdetail.html?id=1115,2022年7月14日。。相比傳統的影視劇產業對電子游戲市場的有限影響,互聯網視頻直播不僅在新的媒體環境中融入了游戲行業,且迅速成為影響電子游戲產業的經濟與文化力量。這些正在發生的變化拓寬了“影游融合”話語的邊界,也指出了一個事實:更為成功的融合案例,都是發生在新媒體界面上的。
由此看來,“銀幕的界限”主導了此前大部分討論的方向。為了保證電影藝術的“有效性”[1]“有效性”是指電影以一種相對獨立的狀態存在,進一步說,它應當被看作是一個獨立的領域。參見[法]讓—米歇爾·弗羅東《電影的不純性——電影和電子游戲》,楊添天譯,《世界電影》2005年第6期。,在電影銀幕上實驗電子游戲或任何新媒體藝術的語言時,即會遭遇這一邊界。作為電影藝術與觀眾之間的技術中介物,銀幕總是傾向于反對那些“人為”地消除其與新媒體界面之間差異的努力,這一技術傾向(或曰媒介的信息)構成了電子游戲與電影之間的“天然鴻溝”。但對于包括電子游戲界面在內的新媒體界面來說,跨越這條邊界卻不成問題。馬諾維奇(Manovich)就傾向認為新媒體交互界面之所以對用戶有效,正是因為其包含了電影、印刷和人機交互界面等語言慣例[2][俄]列夫·馬諾維奇:《新媒體的語言》,車琳譯,貴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2頁。。電影的慣例——它的“符碼象征體系”——早已蘊含在新媒體界面中了。
至此,電子游戲與電影融合的第一個困境和關鍵問題就變得清晰起來:兩者的媒介差異性,使電子游戲對電影的“改良”要么有限,要么無效;而進一步消除兩種符號象征體系之“鴻溝”的努力,則被電影銀幕的技術需求遮蔽了。
三、界面:融合的悖論
想要解決第一個困境,關鍵在于如何解放電子游戲新媒體界面的藝術潛能,為此學界與業界做了諸多嘗試,但剛剛踏上這個方向就馬上遭遇了第二種困境:電影在視聽文化層面的支配性影響,遮蔽了新媒體界面的價值和潛力。作為一種典范媒介,一個世紀以來在人類的視覺文化領域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電影,在面對同樣使用運動圖像和屏幕顯像的電子游戲時,必然會具有美學評價優勢。在電子游戲的發展歷程中,這種優勢主要表現為電子游戲在敘事上與語言上向電影形態的趨同趨勢[3][美]威爾·布魯克爾:《數字眼,CG眼:電子游戲與“電影化”》,于帆譯,《世界電影》2011年第1期。。
這就有必要重新考察被傅東懸置的問題——電影對電子游戲的影響及其結果。如今,游戲對光影效果和細節真實度的極致追求催生了游戲引擎技術的不斷發展。2012年,育碧(Ubisoft)制作的游戲《孤島驚魂3》(FAR CRY 3)正式發售,該作被IGN[4]IGN,即Imagine Games Network,是一家多媒體和評論網站,其主要對象為視頻游戲,現已發展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游戲娛樂媒體之一。評定為系列最佳,這主要得益于Dunia[5]在阿拉伯語中,Dunia含有“地球”“世界”,以及“生存”的含義,這款引擎是育碧為《孤島驚魂2》特意開發的新引擎,而升級版具有了動態天氣系統、動態火焰傳遞系統、非預設人工智能、輻射著色技術等新功能。引擎升級版所帶來的真實環境渲染——游戲中水面的粼粼微光、竹下斑駁葉影以及與場景交互的物理反饋等,該游戲的視覺效果深受玩家好評,這也使得光影表現能力逐漸成為游戲引擎評定的重要指標;2022年,Epic官方宣布正式推出虛幻5(UNREAL 5)游戲引擎,借助獨到的超分辨率升采樣算法、Nanite技術和Lumen技術[6]Nanite是一個虛擬化的幾何系統,可以在場景中加載高多邊形網格,用戶如果在導入幾何體時啟用此功能,它將自動準備網格,同時對其分析并創建分層集群。最后,Nanite將根據場景中所需的細節,自動改變這些三角集群簇的密度或細節,從而加載大型復雜程序資產和場景,并使之在游戲中運行良好;Lumen 是Unreal Engine 5的全動態全局照明和反射系統,可以實時自動模擬場景周圍的光線反射,根據不同反射體的特性選擇正確的光線照射路徑,并根據玩家位置和操作實時生成光影效果。,以虛幻5開發的電子游戲可以獲得影視級別的幾何體細節展現以及毫米級的光線追蹤效果(圖2)。游戲分辨率的變遷也印證著這一趨勢,20世紀游戲分辨率普遍低于320×240,至2008年仍有73%的游戲玩家的顯示設備為1680×1050及以下,但今天,已有49.8%的玩家采用影院標準分辨率(2560×1440)設備,甚至超過20%的玩家使用UHD 4K分辨率[1]“Umfrage-Auswertung: Welche Monitoraufl?sung steht für den Spielerechner zur Verfügung (2021),”accessed July 8, 2022, http://www.3dcenter.org/news/umfrage-auswertung-welchemonitoraufloesung-steht-fuer-denspielerechner-zur-verfuegung-2021.。“電影級畫面”成為生產者和玩家共同追求的美學效果——“更電影的”就是更好的。

圖2 基于虛幻5開發的《黑客帝國:矩陣覺醒(測試版)》(The Matrix Awakens:An Unreal Engine 5 Experience),被玩家討論最多的部分就是其宛如互動電影的視聽體驗,圖為游戲引擎對數字建模渲染后生成的“城市”
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以“一種媒介充當另一種媒介的‘內容’”[2][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1頁。來表述媒介技術的迭代關系,在電子游戲作為新媒介的發展過程中,作為典范媒介的電影逐漸成為其主要的內容——無論是“游戲電影化”的制作趨勢,還是基于電影工業IP改編的游戲產品。游戲研究者賈德·伊桑·魯格爾(Judd Ethan Ruggill)將電影化游戲的融合稱為“運動的、相互促進的、根本性的”,并且發出“融合,早已存在”的呼聲[3][美]賈德·伊桑·魯格爾、馬修·維斯、亨利·詹金斯等:《聚焦平臺之間的游移——電影、電視、游戲與媒介融合》,于帆譯,《世界電影》2011年第1期。,但他的樂觀態度卻因過于關注“內容”而顯得可疑。麥克盧漢提醒我們“任何媒介的‘內容’都使我們對媒介的性質熟視無睹”[4][加拿大] 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第19頁。,繼而喪失把握媒介技術傳遞“真正信息”的能力。
因此,讓電子游戲的界面僅僅呈現為電影銀幕的傾向是危險的,它調用過多的資源去完成文化與美學觀念的“向下兼容”。2019年,迪士尼推出3D翻拍版《獅子王》(The Lion King),這部以VR虛擬拍攝和真實的沉浸體驗為賣點的影片,其內核卻是不折不扣的游戲引擎產物。影片利用Unity游戲引擎實時渲染搭建虛擬拍攝場景,再通過動作捕捉技術將角色形構到虛擬場景中,從而完成整個拍攝過程[1]AMC Theaters, “How John Favreau Used VR Technology to Create The Lion King,” accessed July 9, 2022, https://www.amctheatres.com/amc-scene/how-jon-favreau-used-vr-technology-to-build-the-world-of-the-lion-king.。
Unity引擎原本的開發目的是打造一款能夠借助開放社區提供的大量素材插件,來支持個人游戲制作者和獨立游戲工作室開發工作的高易用性、低門檻游戲制作工具。馬諾維奇將常見于游戲中的“分支式(菜單式)交互性”與“用戶扮演了主動的角色”的邏輯稱為新媒體的“開放式交互”[2][俄]列夫·馬諾維奇:《新媒體的語言》,車琳譯,第40頁。。而用Unity翻拍《獅子王》(圖3)所帶來的悖論是,原本面向游戲開發者和玩家的技術,成了電影生產者的工具,并以銀幕體驗為其終極目的——“新”的電影不僅復刻了1994年動畫版本的分鏡頭劇本,并以復刻它的“語言”為目的。于是,電影成了游戲的“頭號玩家”,而銀幕的技術限制——運用特殊技巧創造出的“距離”[1][法]讓—米歇爾·弗羅東:《電影的不純性——電影和電子游戲》,楊添天譯,《世界電影》2005年第6期。——則掩蓋了電子游戲界面的交互性與游戲引擎技術的開放性[2]對引擎電影和好萊塢技術傾向的批評,參見趙宜:《交互崇拜:好萊塢電影工業的技術神話與未來景觀》,《文藝研究》2021年第1期。。由此帶來的潮流則是影視產業與引擎技術的進一步結盟:虛幻5游戲引擎在開發中便已內置虛擬拍攝需求,《勝利號》(Space Sweepers,2021)、《西部世界》(Westworld,2022)、《曼達洛人》(The Mandalorian,2023)等劇集均借助該系列引擎以降低視效費用,并達到比傳統綠幕特效更完整的視覺沉浸體驗[3]虛幻引擎:“影視 敘事新紀元”,https://www.unrealengine.com/zh-CN/solutions/f ilm-television,2022年7月9日。。

圖3 利用Unity引擎制作的新版《獅子王》(上圖)基本復刻了動畫版本(下圖)的電影語言
當下利用電子游戲制作影視劇的產業現實已經相當普遍,而且比起我們在此前討論過的任何一種電子游戲與電影的關系都更為“融合”,但界面賦予玩家的操控權卻在這個過程中被剝奪了。因此,最后的問題在于,如何在融合的過程中釋放新媒體/新技術的信息,由此更有力地激發包括電影在內的“舊媒介”新生?
四、持攝影機的“人”
前文提及的那部由游族影業制作并被看作是“國內影游融合話語起點”的《三體》電影至今未能在銀幕呈現,但同樣以小說《三體》為素材的自制劇集卻率先由游戲玩家完成了。《我的三體》是“嗶哩嗶哩”網站的視頻作者“神游八方”組織粉絲社群中的愛好者利用沙盒類電子游戲《我的世界》(Minecraft)[4]《我的世界》是馬克斯·泊松(Markus Persson)在2009年開發完成的沙盒類電子游戲,該游戲沒有設置主線劇情,也沒有設置強迫性的算法敘事,它以完全的自由和開放面對每一位玩家。玩家在游戲中可以選擇生存和創造兩種不同的模式,生存模式玩家所擁有的資源必須自己從游戲中獲得,而創造模式玩家則擁有無限量的所有方塊可以進行積木式的搭建游戲。的開放性引擎共同打造的一部動畫作品,改編自《三體》系列小說的第一部“地球往事”,全季共11集。相比國內外視頻網站中大量借助《我的世界》引擎自制的短視頻,《我的三體》因其擁有規律的更新周期、完整的故事鏈條以及巨大的受眾群體而得以登陸“嗶哩嗶哩”網站的“國創動畫”板塊,并收獲超3000萬次的播放,這足以說明這是一部被流媒體平臺和觀眾所認可的影視動畫作品[5]神游八方:《我的三體》,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ss1704?spm_id_from=333.337.0.0,2022年7月9日。。然而,不同于傳統的動畫制作流程,《我的三體》既沒有2D動畫的原畫草繪過程,也沒有3D動畫復雜的人物建模,其基本創作方式依賴于《我的世界》游戲中已有的游戲場景和道具素材。在整個創作過程中,無論是光線照射所產生的影調氛圍,還是人物的視覺形象,以及場面調度所產生的物理反饋,也均由引擎算法的自動化邏輯生成。但是,構成《我的三體》底層邏輯的還是玩家“玩游戲”的行為。以影片中主角葉文潔在“紅岸基地”擔任發報員的片段為例,在由玩家提前搭建好的雷達基站場景中,不同的玩家通過“扮演”(play)不同的角色緊密配合,共同完成了場面調度,實現了基地中的人們忙碌而有序的視覺和情節效果。由此,這部動畫的創作中體現出了“數字化呈現物理世界通信與協作”[6]Ruizhi Cheng, Nan Wu, Songqing Chen, Bo Han, “Will Metaverse be NextG Internet? Vision, Hype, and Reality,”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s://arxiv.org/abs/2201.12894.的特點,即在電子游戲交互界面的組織下,虛擬空間中玩家社會的協作性和自動化技術的生產性被充分地調用了起來。自動化的引擎算法降低了場景搭建的難度,而玩家協作的表演和調度則重構了電影生產的一般方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電子游戲界面的“開放式交互性”承諾被最大限度地釋放了出來,進而顛覆了電影工業所代表的、以相對技術優勢和制片人、精英藝術家的影響力為基礎的“機械復制時代”藝術的生產方式、敘事觀念與文化傳播邏輯。
與電影不同地方還在于,《我的三體》中承擔“攝影機”功能的是玩家的游戲視角(圖4)。整部劇集的第一個“鏡頭”,是對“某大學操場”的全景俯拍,細心的觀眾會馬上發現在畫面的下方,有一個跑動中的“人影”。這是一個典型的“穿幫鏡頭”,正是它從第一個畫面開始就主動暴露出這部電影的“攝影機”——一個在空中“跑動”的玩家。我們看到的“電影畫面”正是來自他的主觀游戲視角,這是新媒體的“電影眼睛”!在第1集的第二場戲中,玩家視角扮演的“攝影機”通過切換不同人稱來達到在“伐木”的過程中主觀鏡頭和客觀鏡頭的不同視覺效果。但在“鏡頭”切換的過程中,玩家界面的工具欄和地圖會出現在畫面中,這一影像中的“瑕疵”一方面聲明了“拍攝者”的玩家身份,另一方面也再次強調了生產《我的三體》的技術中介正是電子游戲的界面。

圖4 《我的三體》第一季第1集第15秒穿幫鏡頭,圖片引自神游八方:《我的三體》,https://www.bilibili.com/bangumi/play/ss1704?spm_id_from=333.337.0.0,2022年7月9日
相比《獅子王》用電影語言隱藏游戲引擎技術特點的傾向,《我的三體》選擇將它充分呈現出來。這指引我們在電影與電子游戲的融合關系中進一步“向后退”,越過“內容”的遮蔽,攻擊在這些討論中向來不可動搖的“拍電影”領域。如同維爾托夫(Вертов)在《持攝影機 的 人》(Человек с киноаппаратом,1929)中對拍攝者和剪輯臺的反復暴露一樣,《我的三體》通過相似的辦法,揭示出這一“影游融合”產物的技術基礎及其美學影響。
如果說維爾托夫的理論展現了作為20世紀的新媒體的電影機器相對人類眼睛所具有的技術超越性,那么我們有理由循著這樣一種思路,去尋找游戲引擎的相對進步優勢。由游戲角色視角帶來的主要畫面特點,便是服務于視線與敘事引導的“正反打”等鏡頭語言的無效化。實際上,如果用經典電影的景別、運動和調度關系看待這部動畫作品,會發現它通常傾向于在全景和主觀視角之間切換。這顯然是受限于算法本身所帶來的體積碰撞——為了避免“人物穿模”所造成的“穿幫”現象,因而需要保證包括充當攝影師的玩家在內的所有人物一定的安全距離。但這種對于電影來說堪稱重大缺陷的創作“限制”,卻比戈達爾和特呂弗們更激進地解構了經典電影敘事語法,它放棄了電影語言對觀眾的視線引導和意識形態“縫合”優勢,并鼓勵觀眾調動起玩家的身份認同,主動參與進影片的敘事當中。
借助電子游戲的新媒體特征,這一“影游融合”的“另類”產物在生產過程中體現出的遠程控制與社會協作的文化邏輯,在語言層面產生了交互性與沉浸性的接受體驗。電子游戲的技術因此得以解構電影的強大影響力——不論是對電子游戲等新媒介的持續性影響,還是20世紀以來的視覺文化對世界想象的慣有方式。這提醒著我們推動電子游戲與電影融合的真正目的——顯然,它既不是今天文娛產業的主流敘事所描繪的基于特許經營權的跨媒介改編潮流;也不應滿足于今天好萊塢在運用游戲引擎時的新傾向,即作為一種生產電影的更有效率的輔助工具。真正的融合產物,恰恰正處在新舊媒介的“斷裂界限”,這一“兩種媒介雜交或交會的時刻,是發現真相和給人啟示的時刻”[1][加拿大]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第53、74頁。,它提醒我們應以舊媒介為參照,去發現新媒介的豐富信息——它的技術與美學想象力,以及對藝術的觀念與語言的實踐進行結構性更新的潛力(圖5)。
結語
2021年以來,隨著“元宇宙”概念的不斷升級,全球技術資本和媒體產業的興趣也開始從電子游戲進一步走向了對VR、AR以及其他智能媒體技術的關注。不過,無論圍繞著“元宇宙”概念產生的諸如數字經濟、虛擬社群或遠程模擬等相關技術、文化問題如何發酵,一個不得不警惕的事實是:作為硅谷的技術商人代表,扎克伯格在向全球推銷他的“元宇宙”應用前景的時候,勾畫的是一個斯皮爾伯格的科幻電影《頭號玩家》般的未來世界圖景[1]Eddie Makuch, “Mark Zuckerberg Outlines His Vision For A Ready Player One-Like Metaverse And It Sounds Wild,” accessed July 10,2022, https:// https://www.gamespot.com/articles/mark-zuckerbergoutlines-his-vision-for-a-ready-player-one-like-metaverse-and-it-soundswild/1100-6494443/.(圖6)。如同宿命般,40年前斯皮爾伯格與電子游戲產業的故事再次重演,“雅達利的詛咒”依舊幽靈般盤旋在最前沿的技術想象上空。

圖6 電影《頭號玩家》中主角用被激光投影出的“身體”與他人在現實世界中交流的場景
未來技術的文化與美學想象力,被限制在電影銀幕及其語言系統內部,這是直到今天我們仍在面對的媒介文化現實。從這個意義上看,“用游戲拍電影”,作為對傅東有影響力的論述的補充,應該足以成為電子游戲與電影的結合過程中的另一種重要關系,并進而作為一種考察新舊媒介關系的方法和路徑。強調這一關系的意義在于,如果我們需要在今天的環境中通過“影游融合”的話語激活某種面向未來的、包括“元宇宙”在內的產業或文化技術格局,那么相比舊媒介的經濟與美學命運,新媒介技術的生產性和創造力,及其所帶來的對舊的媒體語言和文化的更新與重構,理應成為我們首先關注的對象。如此,才能避免陷入對舊產業體系和美學體系的迷戀,并進一步發現新舊媒介交疊時產生的巨大能量和未來技術蘊含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