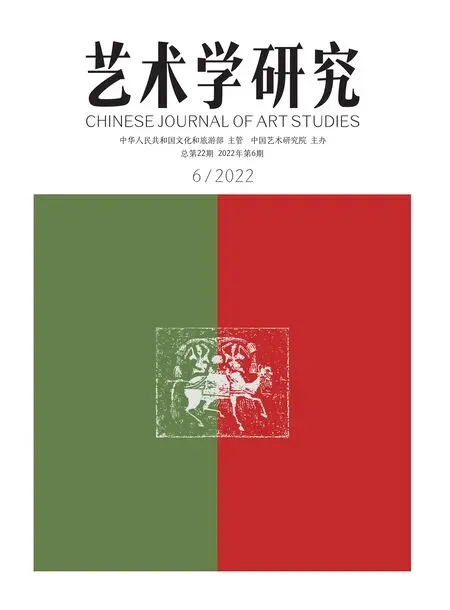揭示混雜“記憶”:后殖民語境下當代藝術家的種族影像再生產
鄧立峰
《中國藝術報》社
將矛頭指向種族主義,是西方當代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取向,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是對殖民歷史進行觀照與批判。在后現代思潮和后殖民話語方興未艾的當下,反思和批判殖民主義,重塑民族認同,成為那些出身于曾經被殖民、受歧視族群的藝術家進行創作的重要追求。
從某個層面來講,在追求批判和顛覆種族主義敘事的藝術創作中,訴諸過去的創作活動遠比只觀照當下的創作更有利于達成目的。正如印度裔美國學者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指出的,民族的存在并不是恒定不變的,也不只是一種橫向展開的架構,它是“歷史記憶與主體性臨場經驗”的結合,它在塑造民族性的過程中,基于歷史敘事和時間經驗發揮著重要作用[1][美]巴拔:《播撒民族:時間、敘事與現代民族的邊緣》,廖朝陽譯,《中外文學》2002年第12期。巴拔,即霍米·巴巴。。那些曾經是殖民地的地方,往往有著延綿不斷的歷史記憶——無論是由歌謠、故事等民間文學形式延續的或是由政府以權威話語書寫的內部記憶,還是“取材”于異域、由精英階層從西方引入當地后重新演繹生成的外部記憶,都影響著個體對主體身份的認知。因此,批判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需要直面記憶,重新返回歷史“現場”進行解構。基于此,面向“記憶”獲取批判的邏輯與素材,是種族主題藝術創作不可或缺的創作取向。
而在這一創作取向中,直接挪用由種族主義者拍攝制作的舊日影像,對其進行加工再創作,成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范式。這種范式重新喚醒傳統殖民影像,以立足于當下的道德邏輯加入現時展演,生產新的意義場域,以達到解構和批判的目的。本文即對這種創作范式進行考察,以當代藝術家對傳統殖民影像的再利用、再創作,分析后殖民語境下當代藝術家種族主題藝術創作的歷史原型、創作策略、方法意義以及所面臨的問題。
一、當代藝術中種族影像再生產的歷史原型
在挪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所生產的種族主義照片方面,當代藝術可以利用的資源異常豐富。早在現代攝影技術誕生之初,攝影實踐者的鏡頭就從他們熟悉的日常生活轉向了“他者”。19世紀是科學的世紀,也是誕生于科學思維的攝影的世紀,人們意識到攝影影像的機械生產是一種“沒有偏見、疲勞或推理的觀看”[1][英]凱利·懷爾德:《攝影與科學》,張悅譯,中國攝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頁。,攝影隨即被應用到科學觀察之中。
從19世紀中葉開始,攝影被納入生物學和早期民族志考察的工作之中。瑞士生物學家路易斯·阿加西(Louis Agassiz)于1865年前往巴西考察,為自己“多源人種論”的觀點尋求證據,他和助手對當地居民進行拍攝,將其視為對不同種族個體進行比較研究的“標本”。面對那些赤身裸體、一絲不掛的“未開化地區”的人,阿加西和他的助手從正面、側面、背面三個角度拍攝了影像[2]Louis Agassiz, A Journey in Brazil (Boston: Ticknor & Fields, 1868),529.,立體地展現這些人的身體,就像展示被固定在博物館中的動物標本那樣。阿加西拍攝人像的方式,在很多早期人類學照片中都能看到。1869年,大不列顛民族學會會長、生物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受殖民公署(Colonial Off ice)委托規劃了一套“大英帝國疆界內各個種族有系統的、一系列的照片”,赫胥黎所設想的“系統”,是要求被拍攝者“裸體站在一根丈量柱旁邊,各拍攝一幅全身、半身、正面、側面的照片”[3][美]約翰·普爾茲:《攝影與人體》,李文吉譯,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7頁。。類似將人類個體類比為動物進行存檔記錄的方式在當時的生物學和人類學影像中極為常見,正如凱利·懷爾德(Kelley Wilder)所說,此類基于“嚴格的科學標準”、用于歸檔的早期民族志學圖像,可以“將它們的對象從任何局部背景中摘出來并移植至一個‘科學’背景當中”[4][英]凱利·懷爾德:《攝影與科學》,張悅譯,第92頁。。它們既是訴求于科學研究的科學話語,也生產著西方拍攝者對“未開化地區”野蠻、原始、不發達等充滿偏見的敘事話語,兩種話語相互影響,體現了殖民主義的權力作用機制[5]鄧立峰:《早期民族志影像中的科學話語與敘事話語生產》,《百色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
除了用于早期民族志工作,攝影在19世紀還被廣泛應用于在遙遠的殖民地拍攝具有“異國情調”的商業照片,以及被傳教士、殖民官員用以拍攝個人影像。19世紀末,當法國畫家保羅·高更(Paul Gauguin)為了追求理想的藝術熱土而來到位于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島時,他看到的是一個具有原始美感、充滿情色幻想的人間天堂。“這殷勤好客、美不勝收的土地,這自由與美的國度!”他接著寫道:“這些野蠻人,這些無知的化外之民,教給我這個文明老頭的東西太多太多了。他們傳授給我的是關于生活的科學和關于幸福的藝術。”[1][法]保羅·高更:《諾阿·諾阿:芳香的土地》,郭安定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頁。在同一時期,從歐洲前往大洋洲傳教的喬治·布朗(George Brown)拍攝了大量太平洋島民的照片,這些不同于早期民族志影像的擺拍照片,更著重于塑造一種“太平洋風情”:皮膚黝黑、赤裸上身的男女,獨特的民族服裝,作為背景的高大樹木和寬大樹葉,這些元素都可以極大地滿足西方對太平洋島國美好伊甸園的想象。
無論是出于科學目的的人類學影像,還是在市場上流通的商業影像,都應和了西方世界用影像來塑造“他者”的實踐——拍攝者從拍攝元素的選取、拍攝對象的入鏡方式等方面,都試圖呈現作為“他者”的群體統一的、恒定的“本質化”形象,這掩蓋了“他者”群體中存在的差異性,種族被表現為單一集體經驗,也因此,傳統種族影像內含了“多合為一”的隱喻。
對于當代觀者來說,觀看這些拍攝于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的照片,很容易產生似曾相識的感受,當印度裔藝術家阿努·帕拉庫那蘇·馬修(Annu Palakunnathu Matthew)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印第安人的老照片時,他感覺到“印度人”與“印第安人”的重合——19世紀美國攝影師觀看“原始土著人”的目光與同一時期英國攝影師觀看印度的殖民目光相似[2]Annu Palakunnathu Matthew, “Perception and Projection: Dual Identity As an Indian Artist in the US,”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no. 2(2002): 68.。馬修所感覺到的“目光的重合”契合了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關于“他文化”認知的“套式說”:“當不同的文化相遇時,每種文化對其他文化形成的形象有可能成為套式……它往往會夸大事實中的某些特征,同時又抹殺其他一些特征。套式多多少少會有些粗糙和歪曲。然而,可以肯定地說,它缺乏細微的差別,因為它是將同一模式運用于相互之間差異很大的文化狀況。”[3][英]彼得·伯克:《圖像證史(第二版)》,楊豫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86—187頁。如伯克所說,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形象塑造致力于追求認知原型,這種認知原型有著固定的思考邏輯或表現范式,它有意無意地忽略不同群體間的差異,通過對種族群體元素的不恰當隱喻,抹平不同殖民地之間的差異,并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建構起現代啟蒙主義話語下“文明—未開化”的二元對立。19世紀,攝影機的出現為殖民者塑造“他者”形象提供了更具“客觀”色彩、便于存儲與傳播的條件,而通過種族照片的生產、傳播與再闡釋,對于“他者”的套式認知也一次次被確認。
二、生成混雜性的創作策略
打破認知套式及由其生成的“文明—未開化”二元對立關系,成為當代藝術家解構傳統殖民主義敘事的一個重要突破口。基于豐富的歷史素材,當代藝術家對傳統種族影像進行了挪用和戲仿,并在加入現時展演的過程中,創作了彰顯混雜性特征的圖像。
感受到“目光的重合”后,馬修借用19世紀初期美洲印第安人的照片,模仿其中印第安人的衣著、動作和神態表情進行了裝扮式表演,她在自己的照片中還原出同樣的衣著、動作和神態表情,然后將兩張看似相同的照片并置。在這兩張照片中,除了馬修本人的長相之外,觀者再也找不到另外的提示可以證明馬修的照片拍攝制作于當代,而另一張是19世紀印第安人的照片。馬修生產了一組如此兩兩相對的照片,取名為《來自印度的印度人》(An Indian from India)。之所以取這樣的名字,與她本人的經歷有關:馬修常常被問起是哪里人,每當碰到這樣的問題時,她總是在回答完自己是“Indian”后,再特別解釋自己是“印度人”,而不是“印第安人”,因為在英文中“Indian”可以同時指稱“印度人”和“印第安人”[1]Annu Palakunnathu Matthew, “Perception and Projection: Dual Identity As an Indian Artist in the US,”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no. 2(2002): 67.。通過《來自印度的印度人》中并置的照片,馬修將兩個完全不同的民族——19世紀的印第安人與她自己所屬的印度人——擺在了同一種族影像情境之中,彰顯了“相同又不同”的矛盾關系和其中內含的混雜性,也揭示了傳統種族影像生產的套式化特征。

阿努 帕拉庫那蘇 馬修,《來自印度的印度人》(部分),2001—2007年,圖片引自馬修官網:https://www.annumatthew.com/gallery/an-indian-from-india/
與馬修并置傳統種族影像和當代仿制照片不同,黑人藝術家凱莉·梅·維姆斯(Carrie Mae Weems)則以圖片搭配文字的方式,對拍攝于19世紀的早期民族志照片進行了再創作。維姆斯在《當我看到這一切時,我哭了》(From Here I Saw What Happened, I Cried)中,翻拍了阿加西及其助手在美國南部收集研究素材時拍攝的34幅黑奴照片。在阿加西那些原本打算用來證明黑人是劣等種族的照片中,作為被拍攝對象的黑奴的“尊嚴在裸身擺姿勢中被剝奪了……他們被當成某種概念上的‘種類’的標本,而不是個體”[2][美]約翰·普爾茲:《攝影與人體》,李文吉譯,第37頁。。維姆斯將這些照片翻洗放大,加入紅色濾鏡,并為每張照片都搭配了文字說明,諸如“你成為了科學研究的對象”“一個黑人樣本”“一次人類學論辯”等。這一系列作品對原始照片進行了紅色濾鏡的上色處理,使其失去了作為早期民族志照片所具有的歷史性情境——老舊照片因傳統影像工藝而具有的獨特色調,也關閉了觀者重新回到歷史“現場”的大門,這使得觀者對作品的凝視只能來自當下、來自外部。失掉了歷史聯系,人們只能在現代情境中重新認識傳統影像中的“他者”,也因此背上了基于當代準則的道德負擔。通過這組作品,維姆斯揭示了傳統種族主義內含的混雜性——當種族主義者將自己裝扮為“開化者”時,黑人卻成了被研究、被物化的對象,種族主義所依賴的道德借口蕩然無存。

凱莉 梅 維姆斯,《當我看到這一切時,我哭了》(部分),1995—1996年,圖片引自維姆斯官網:http://carriemaeweems.net/galleries/fromhere.html
“混雜”,是后殖民理論家對殖民主義特征的重要發現。1978年,愛德華·W. 薩義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學》(Orientalism)出版,之后,伴隨著后殖民主義研究的風生水起,薩義德理論的一些缺陷也被拎出來加以批判。其中一點是,雖然薩義德注意到了殖民話語內含的復雜關系,但他并未對此進行深入研究,而是強調一種“西方—東方”的二元對立關系,以突出東方主義的“再現”實踐。這種簡單的二元建構引起了一些后殖民主義理論家的不滿,他們指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不同種族之間的關系,都不是完全對立與涇渭分明的,按照霍米·巴巴的說法,其中蘊含著跨文化交融與協商(negotiate)的空間。
受法國作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文化含混”(ambivalence)觀念的影響,霍米·巴巴對殖民關系中的矛盾及交融狀態予以大量關注[1]參見廖炳惠:《后殖民與后現代——Homi K. Bhabha的訪談》,王德威主編《回顧現代——后現代與后殖民論文集》,臺灣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6—27頁。。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論致力于消除基于二元思維的文化或種族的對立分野,以及消解差異的邊界,同時也挑戰了文化或種族時間維度上的恒定性、同一性。其中,對混雜性的揭示是其重要的手段。他注意到,殖民主義中的模擬(mimicry)狀態最早產生了混雜——在早期的殖民統治中,為了迅速建立統治權威,殖民者將宗主國的政治制度及配套話語挪用到被殖民地,在被殖民地建立起相似但有差異的訓導體制。這一方面是殖民“教化”目的的外在實踐,另一方面又因為適應殖民地的不同需求而創造了一種差異性的模擬,加之越來越多的被殖民者對宗主國的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進行主動模仿,殖民話語模式的權威性也隨之受到了不確定性的沖擊:雖然“模擬”的形式是“一種改革、監管和訓導的復雜策略”,但模擬也內生出一種不合時宜的差異與反抗,它對“標準化”的知識和訓導權力形成了內在的威脅[1]Homi K.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 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85.。“混雜體”對權威的威脅是不可遏制的,因為它“打破了自我/他者、內部/外部的對稱性和二元性”,在權力的生產過程中,權威的邊界——它的現實影響——總是被固定存在的、如幻影般的“他者的注視”所圍困[2]Homi K.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 May 1817,”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116.。所以,西方殖民主義者、種族主義者和被殖民者、被歧視的群體之間從來沒有明顯的分界,他們彼此交融。
如前所述,宗主國在殖民地所塑造的權威話語,包含了影像話語,西方殖民者通過影像生產一次次加深對被殖民群體的歧視。不過,殖民國家和種族主義者所塑造的權威和“標準”,也因混雜性的現實而生成了全新的意義表達,內含著顛覆自我的種子。通過探尋現存殖民影像的蛛絲馬跡,當代藝術家完成了自己的解構工作。
也正是利用了殖民主義內在的混雜性特征,馬修和維姆斯的作品才具有明顯的顛覆意義。類似的創作還體現在薩摩亞裔藝術家木原重幸(Shigeyuki Kihara)的作品中。木原重幸的作品《第三性:宛如一個女性》(Fa’a faf ine: In a Manner of a Woman)[3]“Fa’a faf ine”是薩摩亞當地對第三性的指稱,指代具有男性生理特征卻以女性為性別認同的群體。值得一提的是,木原重幸本人就是跨性別者。利用太平洋島國傳統殖民影像,以三聯畫的形式展示了一個躺臥的太平洋島國女孩(由木原重幸本人所裝扮),她的臥姿讓人想起了高更筆下躺臥在土地上的塔希提女人的形象。在木原重幸的作品中,獨特形狀的熱帶樹葉和遮蔽女人身體的草葉,模擬了以大西洋島民為對象的傳統照片中所塑造的具有地域風情的人物形象,這使影像帶有明顯的辨識度。然而,木原重幸的三聯畫并不是單純的模仿,她通過在與前兩幅幾乎相同的第三幅照片中所展示的男性生理特征,完成了戲仿的過程。西方世界對太平洋島國過于情色的天堂式想象,被隨之而來的第三性現實打破。木原重幸的作品揭示了在殖民主義者所生產的、致力于構建種族和性別等二元對立的影像中,有著超越和諧穩定的混雜性元素——第三性群體的存在,而這使西方關于太平洋島國的想象性建構出現了縫隙。高更塑造了太平洋島國的兩性伊甸園,而木原重幸則以她的第三性主題作品宣告了伊甸園的消失。
當代藝術家在挪用傳統種族影像進行生產的過程中,善于將揭示其中所蘊含的混雜性作為自己的創作策略。我們可以從前述三位藝術家的作品中一窺這種解構手法的運作方式:當西方世界對“他者”的想象和呈現圖示(在此表現為:印第安人原始化、黑人種族標本化、太平洋島國情色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認知套式之外的元素,三位藝術家就用自己的作品揭示出西方傳統種族圖像致力于打造“他者”本質化形象的努力本身就是失敗的,而其失敗的標志就在于那些被遮蔽的混雜性元素——不同族群套式化想象背后的差異所在、“開化”“拯救”等“合法性”殖民敘事之中的道德危機、和諧“兩性天堂”內部的第三性群體——被揭露出來。
當代藝術家在重新審視殖民歷史時期由西方世界塑造的二元對立關系時,不僅追求不同種族間即時性的交流,還在歷史的時間軸上走入過去的緊張狀態,尋求當下與歷史的對談與交融。這樣的創作方式,是將歷史記憶與當下經驗相結合的有益嘗試,是回到種族主義在殖民時期的“起點”解構種族歧視,其真正起到了顛覆種族主義話語的作用。
三、雙重解構:當代藝術手法與后殖民話語策略的同構模式
按照霍米·巴巴的說法,被殖民者的模擬行為和殖民關系中的混雜狀態,表現出所有歧視和規訓場所的“必要變形和位移”,因此擾亂了殖民權力的模仿或自戀的要求,將身份認同的表達重新納入顛覆策略之中,而這種顛覆策略將受歧視者的凝視重新投回到權力掌控者的眼睛中[1]Homi K. Bhabha,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Questions of Ambivalence and Authority Under A Tree Outside Delhi, May 1817,”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112.。進一步講,它會使居于權威地位的“上位者”產生部分“變異”,進而影響其整個權威地位,可見,將殖民主義的“崇高理想”以模擬的方式戲劇性地表現出來,是應對殖民主義最有效的策略[2]Homi K. Bhabha, “Of Mimicry and Man:The Ambivalence of Colonial Discourse,” 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85.。如前所述,由模擬(在此為藝術生產視角下的“模擬”)生成混雜性的創作策略,使馬修、維姆斯和木原重幸的作品都充滿解構效力——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出現的跨文化狀態,在當代藝術創作中已成為常用的解構種族主義敘事的元素。
不過,當我們以更加宏觀的視角去審視,也可以在此類創作范式中發現一種雙重解構的模式:一方面,就像前述三位藝術家所做的,他們運用了后殖民理論所推崇的模擬和混雜的策略;另一方面,他們也利用了當代藝術創作中常用的挪用與戲仿的創作手法。
在當代藝術創作中,挪用、戲仿等藝術手法會首先設定一個在相關領域內具有導向意義的對象,它往往是某個領域的權威文本;在創作過程中,以這樣的對象為原型,創作者將新的話語元素滲入權威文本之中,使之產生與其同向或反向的聯系,從而產生批判或諷刺性效果。這與后殖民話語中的模擬、混雜策略的操作方式如出一轍:在當代藝術創作中,藝術家選定具有訓導權力的殖民話語或種族話語原型,然后將自我話語滲入其中,消解殖民論述的“合法性”。例如,在木原重幸的《第三性:宛如一個女性》中,挪用的對象為西方人于19世紀拍攝的太平洋島國影像,模擬策略的原型則為這些影像中伊甸園式的敘事話語;戲仿的手法為其加入了男性生理特征等元素,混雜的策略使西方世界對太平洋島國的兩性敘事生出了第三性的一端;通過原始影像套式與新影像中男性生理特征元素的沖突,最終形成了諷刺性的效果,而“兩性天堂”想象性敘事話語與第三性現實話語的對比,同樣顛覆了西方世界對于太平洋島民的傳統種族論述。
后殖民語境下當代藝術家的種族影像再生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代藝術手法與后殖民話語策略的同構性,兩者都向占主導地位的權威索取基于其意識形態所生產的文本,并以被主導者的身份向其中滲入自己的思想碎片,進而形成新的邏輯表現或情感表達。而在完成反叛和顛覆目標的同時,這樣的表達也會和當下西方社會中的主流種族論述、道德情境產生互動,生出新的意義場域。也因此,具有傳統被歧視種族身份、處于西方主流社會邊緣的藝術家,往往會借助于這種同構性的生產模式,在西方世界的藝術體系中發出更大的聲音。
聯結到后殖民話語和當代藝術準則的邏輯鏈條中,對傳統種族影像的再利用、再創作已成為當代藝術創作的重要范式。而近10年來,這種再利用與再創作也與當代藝術的各種創作方法全面對接,裝置化、數字化的趨向愈演愈烈——在大型裝置作品《展覽B》(Exhibit B)中,南非藝術家布雷特·貝利(Brett Bailey)以其令人震驚的裝置手法,讓黑人表演者一動不動地出現在特定情境中,復現19世紀白人將黑人作為觀賞對象的情景。其中,一名帶有鐵鏈的黑人女性坐在一面墻壁前,墻上掛著一面鏡子,鏡子里顯示出這名黑人女性呆滯的面容,而鏡子旁則擺著殖民時期以黑人為對象的歷史照片,這些照片成為這件作品中的情境性裝置,鏡子中的黑人面孔則通過在歷史性情境中加入現實展演而生成了混雜性元素。我們也可以從非洲裔數字藝術家芙拉薩德·阿德索(Folasade Adeoso)的作品中看出一種具有拼貼特征的數字化創作手法,阿德索以記錄非洲人生活的早期民族志攝影圖式為素材,以數字技術融入帶有時尚感的線條和圖案,在進行調色處理之后,百年前被作為凝視對象的黑人儼然成了“時尚大片”的主角。

野穆薩 馬庫布,“自畫像”系列作品之一,2007年—2013年,圖片引自達特茅斯藝術博物館官網:https://hoodmuseum.dartmouth.edu/objects/2014.58.10
在對傳統種族影像的再創作走向裝置化、數字化的同時,對影像語言的本體性探索則成為另一種取向。安哥拉裔藝術家德里奧·賈斯(Délio Jasse)通過傳統影像生產技藝——藍曬法生產具有復古情調的照片,他利用這種技法探索了傳統非洲圖像元素的再生產。南非藝術家野穆薩·馬庫布(Nomusa Makhubu)則用影像多重曝光的效果創作了“自畫像”系列作品(Self-Portrait series),將藝術家自己的照片和早期以非洲人為拍攝對象的照片加以重疊,凸顯黑人女性在殖民時期等級制度中受壓迫的地位。木原重幸也在2015年創作了作品《薩摩亞野蠻人研究》(A Study of a Samoan Savage),這是一組模仿人體測量學歷史影像的照片。在殖民時期,致力于人種考察的科學家將測量器具帶到“野蠻人”生活的地方,對他們的身體進行測量,然后用相機將土著和測量器具一起拍入鏡頭中,人體測量學照片也因此成為殖民視覺圖像的一個代表。在《薩摩亞野蠻人研究》中,一名薩摩亞男子站在鏡頭前,量尺正在分別測量他的身高、額頭寬度、鼻梁高度等。這本是對歷史影像的模仿,但站在鏡頭前的男子,并沒有殖民時期被拍攝的土著的弱態,而是以健碩的身體、自信的表情將嘲弄眼神投回給觀看者。在這組作品中,木原重幸并沒有像《第三性:宛如一個女性》那樣以幾幅作品之間的聯動產出意義,而是更注重對單幅作品中攝影本體語言的追求:她以用光和構圖來制造偽記錄效果,用關鍵細節的變化解構經典圖式,通過畫面元素對比(如赤裸的身體與素凈的白大褂)制造緊張感。

木原重幸,《薩摩亞野蠻人研究》(部分),2015年,圖片引自奧克蘭美術館官網:https://www.aucklandartgallery.com/explore-art-and-ideas/artwork/22711/a-study-of-asamoan-savage-nose-width-with-vernier-caliper
總之,在當代藝術手法和后殖民話語的共同影響下,一方面,藝術家對傳統種族影像的利用走向了裝置化,歷史照片和傳統圖像元素構成了藝術展演的情境;另一方面,藝術家則越來越關注影像本體語言的作用,對傳統種族影像進行剖析,其主題、內容、元素、技法、媒介等都被單獨提取出來,成為被挪用和戲仿的對象,進而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歷史加以解構。不過,無論創作手法和取向如何變化,揭示并展現殖民歷史中的混雜性,仍然是當下的主要創作策略。
四、反思:誰的創作?誰在批判?
近幾十年來,這些出身于曾經被殖民、受歧視族群的藝術家,以觀照和解構殖民歷史的方式來進行批判種族主義的藝術創作,逐漸產生了國際化的影響,并進入西方主流藝術體系之中。
不過,當我們深究這些藝術家的生活經歷、作品指向和創作方法時,會發現他們雖然多出身于曾經的殖民地,但他們的族裔身份卻并不“純粹”,他們的身份、作品的內容、所用的語言等大多是“混雜的”。例如,當我們深究前述藝術家們的身份時會發現,馬修和維姆斯長期生活在美國,木原重幸生活在新西蘭,貝利曾在歐洲系統學習過藝術課程,賈斯則在意大利工作……他們有著曾被西方世界凝視的種族身份,但在其藝術創作生涯中,有意無意地受到了西方文化和藝術理念的熏陶與影響。他們的創作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后殖民理論的直接影響,在敘述《來自印度的印度人》的創作理念時,馬修就引用了霍米·巴巴的觀點。
與之相契合的一個現象是,當今出現在國際視野中的那些具有后殖民追求的藝術作品,也多是由這些具有復雜身份或經歷的藝術家基于西方文化思維、利用來自西方的當代藝術語言所創作的,而那些以純粹的“原住民”藝術語言進行創作的作品,則還處在獵奇性的視野之下。對此,我們不禁要問,后殖民語境下當代藝術家種族主題的創作,到底是誰的創作?其所發出的批判,又是誰在批判?
如前所述,將自己的作品置入西方的社會環境、藝術觀念和道德邏輯中,當然可以更好地達到反思與批判的效果,通過對混雜性的揭示,也確實能解構殖民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基于本質化思維構建的二元論述。但是,類似的創作方式,能為曾經被殖民或受歧視的群體立足當下、形成新的民族認同探索出路徑嗎?能不能真正觸摸到這類群體的歷史癥結,從他們的角度去解構殖民主義,恐怕還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正如馬修所自問的,“對于居住在海外的藝術家來說,描繪我們的‘印度性’到底有多重要?甚至于說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當我創作作品時,會有其他考慮因素影響到我作品中的‘印度性’嗎?生活在離印度本土文化有距離感的僑民群體中,是否會讓我更具批判性?或失去客觀的立場”[1]Annu Palakunnathu Matthew, “Perception and Projection: Dual Identity As an Indian Artist in the US,” India International Centre Quarterly, no. 2(2002): 68.?
從當前的種族主題藝術創作來看,創作者多是基于個體的混雜經驗,利用產生于西方的藝術語言和后殖民話語,從西方社會內部的話語體系來理解他們對自己所屬族群的看法。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并不趨向于構建后殖民語境下種族或族群身份認同,而是要嘗試進入西方社會的主流藝術環境之中,在其內部爭取話語權。這種情況下,能不能在曾經的殖民者和原殖民地住民之間形成基于共同認知邏輯的溝通,是值得懷疑的。這一點,和當今主流后殖民話語的狀態極其相似。從這個角度來講,與其說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其所屬族群被殖民、受歧視的歷史,不如說這些作品表達了創作者基于個人流散身份對殖民關系的認知。
如何通過藝術創作的手段,在西方話語和曾被殖民、受歧視的族群之間達成有效溝通的效果?如何以原殖民地看待種族問題的內部邏輯瓦解種族主義話語,發出“原住民”的聲音?這是這些具有多重身份、在西方藝術體系內有一定話語權的藝術家應該致力解決的問題,也是當代所有關懷種族議題的藝術家應該正視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