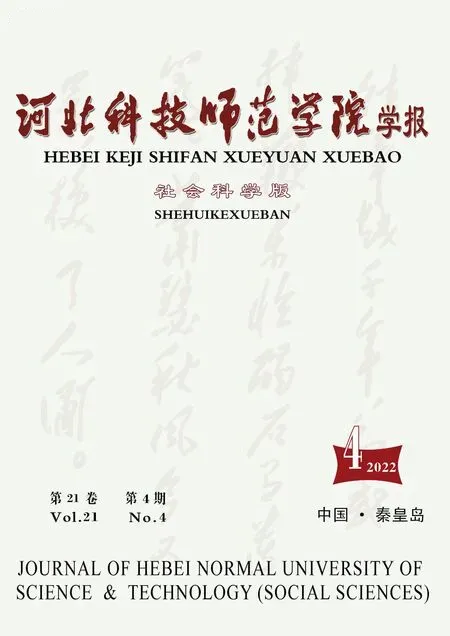“吃”的隱喻、邏輯與階級(jí)性
——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中飲食書(shū)寫(xiě)的歷史演變
郭劍敏
(浙江工商大學(xué) 人文與傳播學(xué)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談及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中“吃”,可先從魯迅談起。魯迅是浙江紹興人,他在作品中雖描寫(xiě)飲食不多,但每每談及卻頗能呈現(xiàn)出濃濃的紹興當(dāng)?shù)靥厣H缭凇渡鐟颉分袑?xiě)到了看戲歸來(lái)偷羅漢豆吃的情節(jié);《孔乙己》中的茴香豆;《在酒樓上》的“我”在名為“一石居”的酒樓上點(diǎn)了一斤紹酒、十個(gè)油豆腐,還點(diǎn)評(píng)到:“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來(lái)S城人是不懂得吃辣的。”[1]《幸福的家庭》里寫(xiě)到一道菜為“龍虎斗”,因著江浙人不吃蛇和貓,便將食材假設(shè)為蛙和鱔魚(yú)。可以看到,魯迅作品中談及飲食,不論是食材還是口味亦或是烹飪法,都具有著十分鮮明的浙東當(dāng)?shù)夭讼档纳省2贿^(guò)在魯迅作品中的飲食描寫(xiě)最具深度與魯迅?jìng)€(gè)人思想色彩的是以“吃”作比,即將“吃”作為一種頗具隱喻性和象征性?xún)?nèi)涵的行為,以此來(lái)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弊端進(jìn)行反思與批判。如《狂人日記》中魯迅便借狂人之口指出中國(guó)傳統(tǒng)禮教傳承的歷史也便是“吃人”的歷史。在小說(shuō)《藥》中,魯迅著重寫(xiě)了茶館老板華老栓為給兒子治病而去買(mǎi)人血饅頭,而這個(gè)“人血饅頭”顯然充滿(mǎn)了象征意蘊(yùn),揭示了早期民主革命運(yùn)動(dòng)中,革命與民眾的隔膜。在雜文名篇《燈下漫筆》中,魯迅更是以“人肉的筵宴”作比,批判所謂的中國(guó)文明。可以說(shuō),魯迅在其行文中以“吃”作比來(lái)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負(fù)面因子進(jìn)行批判,十分鮮明地體現(xiàn)了啟蒙時(shí)代的思想特質(zhì),飲食的日常性恰恰揭示出了封建思想毒害的廣泛與深入,由此才使得國(guó)民性的改造與精神病痛的療救顯得如此的迫切與需要。在現(xiàn)代作家中,以吃作比寫(xiě)得十分精彩的還有張愛(ài)玲和錢(qián)鐘書(shū),張愛(ài)玲以吃來(lái)比擬世情百態(tài),而錢(qián)鐘書(shū)則以吃來(lái)諷喻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的種種丑態(tài)。
在文學(xué)作品中深入而全面地展現(xiàn)一個(gè)城市的飲食文化特色的作家首推老舍。老舍在作品中對(duì)飲食的描寫(xiě)細(xì)致入微、繪聲繪色,把老北京的飲食文化特色呈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這其中又飽含著老舍對(duì)童年生活的記憶、對(duì)老北京市井風(fēng)情的深深留戀。老舍小說(shuō)的京味兒特色,也深深地體現(xiàn)在他作品中對(duì)北京飲食文化的生動(dòng)而傳神的呈現(xiàn),在這方面小說(shuō)《四世同堂》最為突出。小說(shuō)寫(xiě)的是北平淪陷后的歷史情景,但作品中不斷寫(xiě)到淪陷前北平的市民生活和市井生活情景,從而形成鮮明的對(duì)照。而追憶往昔生活情景時(shí),飲食是老舍著重描寫(xiě)的對(duì)象。如老舍用在小說(shuō)中用杏來(lái)串起有著老北京夏天的記憶,“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很可愛(ài)的。從十三陵的櫻桃下市到棗子稍微掛了紅色,這是一段果子的歷史——看吧,青杏子連核每每教小兒女們口中饞出酸水,而老人們只好摸一摸已經(jīng)活動(dòng)了的牙齒,慘笑一下。不久,掛著紅色的半青半紅的‘土’杏兒下了市。而吆喝的聲音開(kāi)始音樂(lè)化,好象果皮的紅美給了小販們以靈感似的。而后,各種的杏子都到市上來(lái)競(jìng)賽:有的大而深黃,有的小而紅艷,有的皮兒粗而味重,有的核小而爽口——連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馳名的‘白杏’用綿紙遮護(hù)著下了市,好象大器晚成似的結(jié)束了杏的季節(jié)。”[2]老舍在這里用一個(gè)杏來(lái)串起一整個(gè)老北京夏天的記憶,色彩豐富,有色有聲,深深的市井氣息,無(wú)限的故土情懷。老舍筆下的老北京飲食已成為呈現(xiàn)舊是北京民情風(fēng)俗的重要方面,也成為沉淀著這座特殊城市歷史記憶的重要所在。老舍出身北京市井,在這飲食敘述中,有著老舍對(duì)童年、對(duì)家鄉(xiāng)、對(duì)親朋鄰里的深情。
在現(xiàn)代作家中,對(duì)中國(guó)的飲食文化有著深入而全面的書(shū)寫(xiě)的是梁實(shí)秋,其代表作是《雅舍談吃》。梁實(shí)秋是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著名的散文家、學(xué)者與翻譯家,是20世紀(jì)30年代新月派的重要代表,其小品文,堪稱(chēng)中國(guó)現(xiàn)代散文中的精品,舉凡琴棋書(shū)畫(huà)、衣食住行盡收筆端,溫婉平和的敘述中,把一種典雅而精細(xì)的生活情趣展示得淋漓盡致,同時(shí)也體現(xiàn)出了一種適閑、淡泊寧?kù)o的人生姿態(tài)。散文集《雅舍談吃》集中收錄了梁實(shí)秋談美食的近百篇文章,《燒鴨》《鍋燒雞》《爆雙脆》《烏魚(yú)錢(qián)》《滿(mǎn)漢細(xì)點(diǎn)》《佛跳墻》《西施舌》等等,寫(xiě)的舌尖上的味道,呈現(xiàn)出的是數(shù)千的中國(guó)文化的底蘊(yùn),同時(shí)也把作家濃濃的故鄉(xiāng)情意及家國(guó)情懷書(shū)寫(xiě)了出來(lái)。現(xiàn)代文壇上另一位小品文大家周作人也曾有多篇文章專(zhuān)述飲食,《故鄉(xiāng)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窩窩頭的歷史》《吃茶》等等都是其論及飲食的名篇,也有著與梁實(shí)秋文章一樣的文化意蘊(yùn)與人生情趣。
從飲食的視角來(lái)審視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最后要談及的是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一個(gè)因喜吃喜聚而形成的一個(gè)著名的文人圈,這便是“二流堂”文人群落。“二流堂”是抗戰(zhàn)時(shí)期在重慶形成的一個(gè)別具一格的文人群落。這是一個(gè)由性情相投的文藝界人士在交往過(guò)程中聚合而成的朋友圈,主要成員有:唐瑜、吳祖光、丁聰、黃苗子、郁風(fēng)、盛家倫、馮亦代等。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這個(gè)文人群落在不斷地?cái)U(kuò)大,成員主要來(lái)自美術(shù)、音樂(lè)、戲劇、書(shū)法、電影、文學(xué)等領(lǐng)域。可以說(shuō),這是一個(gè)由文藝、新聞、演藝界人士組成的一個(gè)朋友圈,大家彼此因意氣相投聚合到了一起,在這個(gè)文人圈子里散發(fā)出一種自由主義文人散淡自在的氣息。
“二流堂”文人的一個(gè)特點(diǎn)便是喜聚、喜吃。“二流堂”文人在一起時(shí)常聚餐,無(wú)拘無(wú)束,灑脫不羈,而且重義輕利。當(dāng)年在重慶時(shí),他們便是有苦一起吃,有錢(qián)一起花,不分彼此。這種交往風(fēng)格在他們后來(lái)的歲月中也繼承了下來(lái),成為一種傳統(tǒng)。夏衍當(dāng)年在重慶時(shí)便與“二流堂”文人有過(guò)密切的交往,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后,時(shí)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zhǎng)的夏衍每去北京必去“二流堂”文人所聚居的棲鳳樓,據(jù)說(shuō)有一次為了和好友自在聚會(huì),路上還故意甩掉了自己的警衛(wèi)人員。進(jìn)入新時(shí)期,飽經(jīng)風(fēng)霜的“二流堂”文人們又聚到了一起,而且?guī)缀趺看味际且跃鄄偷男问秸偌!岸魈谩蔽娜藗円虿艢舛郏蛄x氣而聚,也因性情相投而聚,聚會(huì)既是一種交往的方式,同時(shí)也是情義的表現(xiàn),尤其是共同歷經(jīng)坎坷,這種聚集更具有一種見(jiàn)證歷史、見(jiàn)證情義的意味,這在現(xiàn)代以來(lái)知識(shí)分子群體中也有些十分獨(dú)特的意味,而且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更多的情投義合者走到了一起,“二流堂”的交往成員也有了更廣泛的聯(lián)系,正如李輝在《亦奇亦悲二流堂》一書(shū)中所寫(xiě):“‘二流堂’就不再僅僅是原有的那批人的圈子,而是在更加廣泛意義上的‘物以類(lèi)聚’。從王世襄、楊憲益、范用、黃永玉,到稍微年輕一些的姜德明、邵燕祥等,這些不同領(lǐng)域的人士,也都不時(shí)出現(xiàn)在‘二流堂’的聚會(huì)上。維系他們的當(dāng)然依舊是綿綿不絕的文化情懷。”[3]
二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后的50~70年代的文學(xué)作品中,有關(guān)“吃”的描寫(xiě)被賦予了鮮明的政治色彩。在這一時(shí)期的作品中,一方面吃香喝辣成為對(duì)反面人物的形象化描繪;另一方面,憶苦思甜成為正面人物的一種革命性的表現(xiàn)。可以看到,在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藝術(shù)作品中,不論是小說(shuō)、電影、戲劇等,飲食具有了階級(jí)性。好吃、貪吃、吃好的等等思想和行為被視為是落后的、反動(dòng)的、丑陋的、罪惡的。趙樹(shù)里小說(shuō)《“鍛煉鍛煉”》中諷刺一個(gè)貪吃的落后農(nóng)村婦女,給她起的綽號(hào)叫“吃不飽”;當(dāng)年有關(guān)地主劉文采的故事敘述中,他在吃的方面的講究和奢靡,成為表現(xiàn)他反動(dòng)性的重要證據(jù);而在小說(shuō)《林海雪原》中,土匪首領(lǐng)坐山雕于除夕時(shí)大擺百雞宴,眾土匪齊聚一堂,成為整部作品敘事的高潮,當(dāng)然最終被楊子榮帶領(lǐng)解放軍一網(wǎng)打盡。
可以說(shuō),在50~70年代的文學(xué)作品中,“吃”具有著鮮明的階級(jí)屬性與內(nèi)涵,對(duì)飲食的喜好具有了劃分階級(jí)陣線(xiàn)的意義。所以,在這一時(shí)期的革命歷史題材文藝作品中,推杯換盞、大魚(yú)大肉常常成為描繪反面人物生活的典型場(chǎng)景,而吃糠咽菜、忍饑挨餓則成為描繪革命戰(zhàn)士與革命群眾日常生活景象的常態(tài)。這其中暗含著一條成規(guī),要成為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要能戰(zhàn)勝肉身的欲望,能徹底地抵制美食、美色的誘惑,這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相反,則會(huì)有著經(jīng)不起誘惑而導(dǎo)致背叛革命的危險(xiǎn)。
與此同時(shí),在這一時(shí)期的文學(xué)作品中,粗菜淡飯、省吃?xún)€用成為一種革命的、高尚的品質(zhì)和境界。如柳青的小說(shuō)《創(chuàng)業(yè)史》中寫(xiě)梁生寶進(jìn)城買(mǎi)種子時(shí),著重寫(xiě)了他為了給大家節(jié)約開(kāi)支,舍不得進(jìn)城里的小飯館吃飯,一路上全靠自己帶的干糧充饑。“吃苦”的革命性的形成來(lái)自于紅色革命敘事的打造,在對(duì)革命戰(zhàn)爭(zhēng)歷史的敘述中,“吃的苦”“吃的粗而簡(jiǎn)” 不僅是筆下革命者們的日常生活場(chǎng)景,同時(shí)也是一種革命品質(zhì)的體現(xiàn)。在有關(guān)長(zhǎng)征故事的敘述中,吃野菜、剝樹(shù)皮,煮皮帶成為十分典型的細(xì)節(jié)和場(chǎng)景,由此,“吃苦”成為一種革命傳統(tǒng),成為一種高尚的品質(zhì),相反,貪吃、好吃等沉溺于肉身欲望的行為被看作是一種品行不端或思想反動(dòng)的表現(xiàn),而只有超越肉身欲望才能成為真正的英雄。憶苦思甜也便成為這一時(shí)期對(duì)民眾進(jìn)行思想教育、革命教育的一種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對(duì)省吃?xún)€用的提倡,一方面來(lái)自于優(yōu)良革命傳統(tǒng)的繼承,另一方面也緣于這一時(shí)期整個(gè)社會(huì)生活水平較低、物質(zhì)供應(yīng)匱乏的事實(shí)。為何愛(ài)吃、講究吃成為了革命的對(duì)立面,這其中包含著意志品行的考驗(yàn),意味著沉溺肉身欲望有著導(dǎo)致意志不堅(jiān)定的危險(xiǎn),反之則會(huì)成為革命意志堅(jiān)定的有力保障。所以在革命歷史敘事中,“吃得苦”成為革命者的重要品行。
進(jìn)入新時(shí)期以來(lái),文學(xué)中的飲食書(shū)寫(xiě)終于褪去了階級(jí)的色彩,回歸其本色,談吃、談美食又成為了作家可以正面書(shū)寫(xiě)的題材與內(nèi)容。具有展現(xiàn)新時(shí)期農(nóng)民新變化和新面貌標(biāo)志性意義的高曉聲的小說(shuō)《陳奐生上城》,正是從“吃”入筆,通過(guò)敘述農(nóng)民陳奐生進(jìn)城賣(mài)油食的經(jīng)歷,寫(xiě)出了進(jìn)入新時(shí)期中國(guó)農(nóng)民的物質(zhì)生活及精神面貌上的變化與特征。而陸文夫的《美食家》堪稱(chēng)是20世紀(jì)80年代小說(shuō)中書(shū)寫(xiě)飲食文化的經(jīng)典之作。小說(shu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后50~80年代的時(shí)間背景下,講述資本家出身的朱自冶的“吃”的故事,在風(fēng)云變幻的政治斗爭(zhēng)年代里,貫穿著的是主人公朱自冶對(duì)美食的始終不變的執(zhí)著,美食沉淀著蘇州這座城市的歷史記憶,美食也承載著一種往昔歲月里上層社會(huì)生活的某種蘊(yùn)味。朱自冶以對(duì)美食的沉醉,游離于五六十年代的社會(huì)主義改造之外,也終在進(jìn)入新時(shí)期以后的社會(huì)變革中找到了安放自己美食情懷的天地。小說(shuō)一方面是有關(guān)飲食文化歷史的呈現(xiàn),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80年代中國(guó)文學(xué)終于從那種政治化的寫(xiě)作中擺脫了出來(lái),在一種充滿(mǎn)歷史文化底蘊(yùn)的寫(xiě)作中而傳遞出新的審美走向。汪曾祺也寫(xiě)有談飲食的散文《五味》《故鄉(xiāng)的食物》《家常酒菜》《蘿卜》《豆腐》等,其中體現(xiàn)出的不僅是作家對(duì)于飲食的特殊記憶,更重要的是透露出了進(jìn)入新時(shí)期之后,曾經(jīng)承受政治風(fēng)云的一代作家走出陰霾后的那種輕松愉悅的心境。
三
民以食為天,也許是經(jīng)歷過(guò)很長(zhǎng)時(shí)間的食物短缺,饑餓成為很長(zhǎng)一個(gè)時(shí)期里人們的一種深刻的記憶。長(zhǎng)時(shí)期的物質(zhì)匱乏、生活用品和日常食物的限量供應(yīng),都使得關(guān)于吃成為一個(gè)頭等大事,也許正因如此,在一段時(shí)間里,“吃了沒(méi)?”成為人們?nèi)粘I钪信雒鏁r(shí)的問(wèn)候語(yǔ)。也正因此,有關(guān)饑餓的敘述成為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中國(guó)文學(xué)中的一個(gè)重要的寫(xiě)作命題。80年代的文學(xué)作品中直面描寫(xiě)糧食短缺年代情形的代表性作品有高曉聲的《“漏斗戶(hù)”主》、劉恒的《狗日的糧食》以及張賢亮的《綠化樹(shù)》《邢老漢和狗的故事》等,這些作品聚焦于底層小人物于饑荒年代里的艱難生存的本相。這種關(guān)于饑餓、饑荒的敘述,進(jìn)入90年代以后,逐漸匯聚而成所謂的苦難敘事,代表性的作品便是余華的三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即《在細(xì)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guān)賣(mài)血記》。
張賢亮的小說(shuō)《邢老漢和狗的故事》中,圍繞以邢老漢討老婆成家過(guò)日子為線(xiàn)索,串連起的是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一個(gè)底層農(nóng)民艱難生活的歷史。小說(shuō)中的一個(gè)場(chǎng)景是講述了大半輩子沒(méi)有討到老婆的邢老漢,卻在饑荒年代意外地因收留一個(gè)逃荒要飯的外鄉(xiāng)女子而終于有了一個(gè)可以搭伙過(guò)日子的人。這種女子在饑荒年代通過(guò)委身他人而度過(guò)災(zāi)年的情景在其他作家的筆下也多有述及。劉恒的小說(shuō)《狗日的糧食》發(fā)表于1986年第9期的《中國(guó)》,小說(shuō)開(kāi)篇即寫(xiě)村里的老光棍楊天寬在饑荒年代里用二百斤谷子換來(lái)個(gè)脖子上長(zhǎng)著癭袋的女人當(dāng)了自己的老婆。癭袋女人長(zhǎng)得很丑,卻在楊天寬面前逐漸變得十分強(qiáng)勢(shì),這強(qiáng)勢(shì)主要來(lái)自于女人的兩大本領(lǐng),一是能生娃,二是能弄來(lái)吃的,這在饑荒連連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里,幾乎就是天大的事了,而癭袋女人卻有本事把這兩樣都做得無(wú)話(huà)可說(shuō),也因此而在楊天寬面前變得霸道。女人因能弄來(lái)糊口的糧食而變得強(qiáng)勢(shì),卻也最終因弄丟了購(gòu)糧的糧本而自覺(jué)顏面盡失,最終吃有毒的杏仁兒而自殺身亡,咽氣前那一句“狗日的糧食”也成了女人命如草芥的卑微人生的一種詮釋。小說(shuō)《綠化樹(shù)》里的章永璘在饑荒的年代里,練就了一身覓食、討食的本領(lǐng),讀書(shū)人的所有智慧都轉(zhuǎn)化為如何能夠獲取多一口的食物,一個(gè)窩頭,一勺野菜湯,不餓死成為人生最大的追求。余華的長(zhǎng)篇小說(shuō)《在細(xì)雨中呼喊》中以孫光明為視角,書(shū)寫(xiě)出了一個(gè)底層家庭在饑荒年代里,因物質(zhì)的極度匱乏而導(dǎo)致的家庭成員之間親情關(guān)系的極度惡化與極度冷漠。而在小說(shuō)《許三觀(guān)賣(mài)血記》中,余華以一個(gè)普通的中國(guó)工人為養(yǎng)家而不斷地賣(mài)血求生的故事的敘述,呈現(xiàn)出了50~70年代底層家庭辛酸的生活史。
在20世紀(jì)80年代眾多講述饑荒的作品中,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有著特殊的意義。小說(shuō)最初發(fā)表于 1980 年第1期的《收獲》,后于1981年獲全國(guó)第一屆中篇小說(shuō)評(píng)獎(jiǎng)一等獎(jiǎng)。小說(shuō)講述1960年春李家寨的四百九十多口人陷入了饑荒,李家寨的黨支部書(shū)記李銅鐘冒著風(fēng)險(xiǎn),在昔日戰(zhàn)友、現(xiàn)今為縣糧店主任的幫助下,從糧庫(kù)里“借”出了五萬(wàn)斤的糧食,村民得救,自己卻被作為煽動(dòng)不明真相的群眾而搶劫?lài)?guó)家糧食倉(cāng)庫(kù)的首犯而被捕。這部小說(shuō)可以說(shuō)是新時(shí)期文學(xué)作品中較早的一篇直接對(duì)當(dāng)代特定的歷史事件進(jìn)行書(shū)寫(xiě)的作品。作品開(kāi)篇從1960年春的饑荒開(kāi)始寫(xiě)起的,“黨支部書(shū)記李銅鐘變成搶劫犯李銅鐘,是在公元1960年春天。這個(gè)該詛咒的春天,是跟罕見(jiàn)的饑荒一起,來(lái)到李家寨的。自從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攪到那口裝了五擔(dān)水的大鍋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經(jīng)吃了三天清水煮蘿卜。”[4]5而這時(shí)的十里鋪公社的黨委書(shū)記楊文秀則熱衷于搞浮夸風(fēng),熱衷于“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級(jí)意圖”[4]6。當(dāng)村民開(kāi)始因糧食短缺而鬧饑荒時(shí),有關(guān)上級(jí)卻弄出所謂的“化學(xué)食品”來(lái)邀功請(qǐng)賞,以期糊弄百姓。上級(jí)動(dòng)員缺糧的公社、大隊(duì)搞代食品,楊文秀很快組織人搞出了所謂的新的食物品種,有稱(chēng)為“一口酥”的玉米皮淀粉虛糕、“扯不斷”紅薯秧淀粉粉條、“將軍盔”麥秸淀粉窩頭等等,但其實(shí)這些號(hào)稱(chēng)用玉米皮、紅薯秧、麥秸做出的“化學(xué)食物”,其實(shí)純粹是弄虛作假的產(chǎn)物。瞞干、亂干、高指標(biāo),加重了饑荒,作品對(duì)這樣的一段歷史有著深刻的表現(xiàn),也正因如此,該作成為新時(shí)期初期反思文學(xué)中的一部力作。
1980年第2期的《新觀(guān)察》發(fā)表了汪曾祺的一篇題為《黃油烙餅》的小說(shuō)。小說(shuō)主要是從一個(gè)兒童的視角展開(kāi)敘事,講的是蕭勝的爸爸媽媽都是科研人員,在口外沽源縣的一個(gè)馬玲薯研究站工作,因條件所限,在蕭勝三歲那年,爸爸只好把他送回到家鄉(xiāng)農(nóng)村與奶奶一起生活。蕭勝七歲時(shí),奶奶于饑荒中去世,但她到死也沒(méi)舍得去吃蕭勝爸爸早些時(shí)候帶給她的那瓶牛奶煉的黃油。奶奶去世后,蕭勝被接到了爸爸媽媽工作的馬玲薯研究所一起生活。小說(shuō)中令人觸動(dòng)的是作家講述那種艱辛生活時(shí)的淡然,雖然命運(yùn)很是不公,但這對(duì)普通的科研工作者沒(méi)有抱怨,不論是面對(duì)親人的去世,還是自身處境的不公,還是基層社會(huì)中的不平等,他們都淡然處之,不抱怨,認(rèn)認(rèn)真真地生活,認(rèn)認(rèn)真真地工作,只有在兒子不解鄉(xiāng)下三級(jí)干部開(kāi)會(huì)時(shí)所吃的黃油烙餅是何物時(shí),正咽著紅高梁餅子的媽媽下狠心取出那瓶奶奶一直沒(méi)舍得動(dòng)過(guò)的黃油,給蕭勝做了一張黃油烙餅。“蕭勝一邊流著一串一串的眼淚,一邊吃黃油烙餅。他的眼淚流進(jìn)了嘴里。黃油烙餅是甜的,眼淚是咸的。”[5]79這是汪曾祺復(fù)出后發(fā)表的較早的一篇小說(shuō),書(shū)寫(xiě)的正是有關(guān)過(guò)往歲月里的饑荒經(jīng)歷留給人的一種記憶。不久之后,汪曾祺又在1981年第5期的《收獲》上發(fā)表了小說(shuō)《七里茶坊》,這篇小說(shuō)中所講述的故事與汪曾祺劃為右派后的勞動(dòng)改造經(jīng)歷有關(guān)。小說(shuō)中的七里茶坊因在張家口東南七里地而得名。小說(shuō)講“我”在一家農(nóng)業(yè)科研所下放勞動(dòng),在生產(chǎn)隊(duì)長(zhǎng)的安排下,拿著介紹信、帶著三個(gè)人去張家口的公廁掏大糞。那是1960年,天寒地凍,白天掏糞,晚上回到車(chē)馬大店睡大炕。“掏公共廁所,實(shí)際上不是掏,而是鑿。天這么冷,糞池里的糞都凍得實(shí)實(shí)的,得用冰镩鑿開(kāi),破成一二尺見(jiàn)方大小不等的冰塊,用鐵鍬起出來(lái),裝在單套車(chē)上,運(yùn)到七里茶坊,堆積在街外的空?qǐng)錾稀!盵5]167住在車(chē)馬大店,一早一晚都是店掌柜來(lái)給做手推莜面窩窩,莜面是自己帶來(lái)的,做熟了蘸著自己帶來(lái)的麥麩子做的大醬吃。吃得是粗飯,“沒(méi)有油,沒(méi)有醋,尤其是沒(méi)有辣椒!可是你相信我說(shuō)的是真話(huà):我一輩子很少吃過(guò)這么好吃的東西。那是什么時(shí)候呀?——一九六〇年!”[5]168勞動(dòng)的臟和累,吃的粗,住得簡(jiǎn)陋,但作者恰恰是要寫(xiě)出這種天寒地凍的時(shí)節(jié),在這車(chē)馬大店所感受的溫暖和香甜。不管是一起勞作的同事,勞動(dòng)中互不計(jì)較,互有照顧。車(chē)馬大店的掌柜,一早一晚生火做飯,即使碰上的同住一個(gè)在炕的趕牲口的壩上人。人與人之間,無(wú)戒備,無(wú)妨犯,坦誠(chéng)相待,即使一碗水,一袋煙,一塊咸菜,見(jiàn)得真情真義,汪曾祺把社會(huì)底層的真性情寫(xiě)了出來(lái)。汪曾祺的作品述及了六十年代初歲月的艱辛,但他卻把這種艱辛講述得很淡然而寧?kù)o,他更多呈現(xiàn)的是艱難歲月里所顯示出的那種人間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