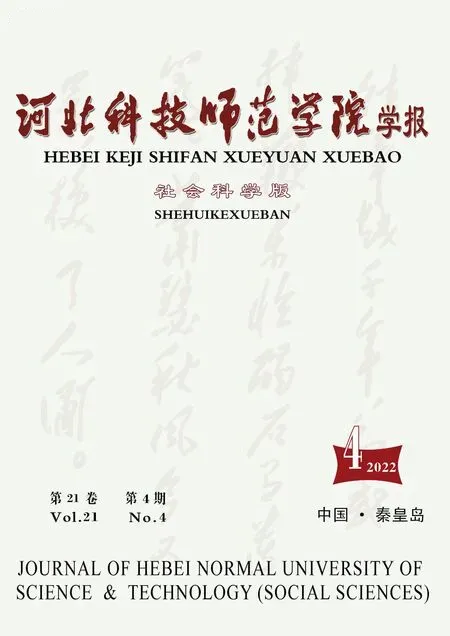“安大簡”《詩經》研究動態*
韓宏韜,婁翔宇
(河南科技大學 人文學院,河南 洛陽 4710233)
從簡牘的產生時間來看,安大簡《詩經》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詩經》版本,比傳世《毛詩》的產生還要早。在簡本《詩經》的內容上,安大簡《詩經》雖僅存六國“國風”57篇,但出現了大量的異文、異體字,甚至部分篇章章句的字數也存在不同。在編排體例上,各國“國風”篇外的編排次序、篇內章次的編排次序也存在著異于傳世《毛詩》的現象。深入研究安大簡《詩經》,不僅有助于窺探早期《詩經》的原始面貌,還有助于對照研究傳世《毛詩》文本的流傳演變。
關于安大簡《詩經》,2015年安徽大學入藏該批簡牘,2019年安大簡簡牘整理小組將相關《詩經》整理成果匯集并出版為《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1]一書。時至今日,已有諸多研究者發表不少相關研究成果,且研究綜述也已發表兩篇,分別是:湯漳平的《近百年來出土文獻與楚辭研究綜述》[2]和李丹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研究綜述》[3],而涉及對安大簡《詩經》相關研究進行匯總的僅《<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研究綜述》一篇,湯漳平的文章只是將安大簡作為一種出土材料與上博簡、清華簡等出土簡牘并列敘說。李丹則主要從“文字考釋”和“詩文文本的訓釋”兩大部分,對已有的安大簡《詩經》研究成果進行梳理。上述研究存在以下問題:其一,隨著時間的變化,新的研究成果迅猛遞增。其二,該篇研究綜述所涉及的研究論文數量略有不足,李丹歸納的研究文章總數為45篇。迄今為止,安大簡《詩經》相關研究成果已多達80余篇。其三,該篇綜述的分類范圍有嫌粗略,“文字考釋”和“詩文文本的訓釋”的分類方式,實際上遺漏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諸如安大簡《詩經》文本結構研究、韻讀研究、文本性質研究、價值研究等。這樣看來,根據上述的綜述研究,近年來安大簡的整體研究動態仍然無法向學界全面呈現。因此,對于安大簡的研究現狀,有重新反思和梳理撰寫的必要。
一、常識性介紹
2015年安徽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該批竹簡數量眾多、內容豐富,包含了《詩經》在內的大量珍貴文獻。經“安大簡”整理小組整理后,共計發現《詩經》篇目57篇(含殘簡),涉及六國《國風》:有《周南》10篇、《召南》14篇、《秦》10篇、《矦》6篇、《鄘》9篇,《魏》(唐)10篇。關于已整理簡本《詩經》篇目的基本情況,黃德寬道:“值得注意的是,出現了《侯風》,所屬六篇詩《毛詩》則歸《魏風》,而《魏風》除首篇《葛屨》外,其余九篇則是《毛詩》之《唐風》。各國風內部所屬詩篇排序和數量也與《毛詩》略有差異。”[4]另有研究者根據簡文內容推測簡本《詩經》為58篇,應為七國國風。馬銀琴認為:“這部《詩經》抄本的基本特征: 總共包括七國國風,其中《周南》10 篇、《召南》14 篇、《秦》10 篇、《侯》6 篇、《鄘》9 篇、《魏》10 篇,介于《秦》《侯》之間完整遺失的‘某’……《鄘》9 篇,不包括《載馳》。”[5]此外,簡本與傳世毛詩本相比,還存在大量異文現象,或是通假,或是訛誤。這些異文的出現使得人們在一些傳統看法和觀念上有了新的理解。
二、字詞研究
因與傳世毛詩本的內容相比存在較大差異,安大簡《詩經》一經出土,在文本字詞方面便引起眾多學者的關注。目前對簡本字詞的研究性論文大致可細分為兩類:其一,對字詞的考釋;其二,對簡本字詞偏旁省略的解讀,且以第一種研究居多。
(一)字詞考釋
在安大簡《詩經》中,對字詞考釋的研究成果眾多。
1.《秦風》相關篇章
對《詩經·秦風》字詞考釋的有:曾富城從同源詞的角度分別對《鄘風·君子偕老》《秦風·小戎》《魏風·陟岵》中的“玼”“俴”“岵”字進行新的訓釋,認為“玼”字義當為“玉色白”,“俴”字義為“馬無著甲”,“岵”字義為“山無草木”[6]。董露露認為,訓簡本“蒙伐有苑”為“盾上的雜色文飾華美繁盛”[7]。同樣對《秦風·小戎》一篇進行訓釋的,還有周翔,他認為,《秦風·小戎》中的“駕我騏馵”的“馵”與簡本中的“馺”有別,二者并非異體、通假或古今字關系;同時訓“馺”當為千里馬義的 “驥”字初文,簡本“馺”字的出現有可能為文本傳抄過程中出現的訛誤[8]。郝士宏則對同屬秦風中的多篇異文進行了考釋,他認為:“《毛詩·秦風》中‘駟驖’本應作‘四牡’,‘溯洄’‘溯游’應讀作‘溯違’,‘有條有梅’應讀作‘有柚有梅’。”[9]在《詩經·君子皆壽》篇的相關研究中,徐在國對“蒙彼縐絺”的“縐”進行考釋,認為簡本中的“縐”字形當訓為從“玉”,“翛”聲,與今本“縐”音近可通[10]。
在與《毛詩》本的對比研究中,汪梅枝通過對比毛詩本,對“於”字的詞性進行了探討,認為在此處把“於”看作介詞更加合理[11]。同樣是與《毛詩》本的對照,鄭婧、王化平則從詞義訓釋、字形字音等方面,將“羔羊之縫”“于嗟乎騶虞”“四驖孔阜、四馬既閑”“於我乎”和“誰之永號”等五處異文進行了詳細訓釋[12]。
在簡本《秦風·晨風》篇的研究中,劉剛對“鴥彼晨風,郁彼北林”之“郁”字,以及在簡本中寫作“炊(吹)字的現象作了探討,他認為,《毛詩》中的“郁”可能是誤字[13]。高中華則對簡本異文“息、思”進行了論述,他認為,“息”是“思”字的假借[14]。禤健聰對“夨”字體偏旁戰國文字作出訓釋,認為簡本“ ”字與今本《卷耳》篇“不盈傾筐”之“傾”對應[15]。陳偉武則依據簡本,訓釋今本中的“樛木”在簡本中應假借為“流木”[16]。
2.《魏風》相關篇章
在《魏風·碩鼠》篇的研究中,朱彥民對“碩鼠”一詞作了訓釋,他認為,傳本《詩經·碩鼠》篇中的“碩鼠”在簡本中寫為“石鼠”,“石鼠”實則是“鼫鼠”的一種異體寫法,在古代也存有“石鼠”“鼫鼠”的別稱,所以《詩經》“碩鼠”應該是指昆蟲螻蛄一類[17]。
3.《周南》相關篇章
關于《詩經·葛覃》篇的字詞研究也有不少。徐在國對《葛覃》中的“刈、濩”二字重新訓釋,認為《詩》中“刈、濩”屬于同義互換[18]。姚小鷗則對整理者徐在國先生已論定的“濩”字進行重新訓釋訂正,認為《毛傳》以“煮”訓“濩”并無不當[19]。同樣,耿可可從《詩經》中的“是A是B”句式分析和“穫”字所存文例分析,認為“濩”也當讀作“鑊”,訓為“煮”[20]。
在字詞的訓釋中,《詩經·關雎》篇也引起了研究者的較大關注,如杜澤遜談到,“要翟”二字,應訓釋為“姣好之貌”[21];徐在國則以為,簡本中的“要翟”應讀作“腰嬥”,即細而長的腰身,“腰嬥淑女”,就是指身材勻稱美好的女子[22];孫可寒從異文、構詞與語境等角度對該詞的訓釋進行了考察,認為“要翟”應該是“窈窕”的異文[23]。在簡本《關雎》字詞訓釋研究中,除對“要翟”的訓釋外,還有對“寤寐”二字的關注,徐在國從字形分析,認為早期《詩經》版本“寤寐”作“寤寢”,是出于“寐、寢”二字同義互訓,后因秦時戰火,文本僅得口口相傳,漢時學者可能因形體相近,故將“寤寢”寫作“寤寐”[24]。華學誠認為,毛詩本《關雎》篇中“左右芼之”的“芼”同簡本中“左右教之”的“教”不應解釋為通假,教可訓釋為“解釋”[25]。相宇劍認為,今本《關雎》中的“悠哉游哉”在安大簡中作“舀才舀才”,“舀”和“悠”通假,“哉”“才”可通用[26]。同時,相宇劍對“關關雎鳩”的異體作了訓釋[27]。此外,周翔、邵鄭先則對簡本中出現的“專字”進行了考釋[28]。
4.其他篇章
夏大兆對傳統命題“言”當“我”講的使用狀況進行了確證,“《詩經》中‘言’可當‘我’講可能是方言成分的遺留。”[29]
(二)字詞偏旁省略
除上述對字詞的訓釋外,還有研究者關注到了簡本字詞的偏旁省略現象。如俞紹宏、張青松訓釋“人”為“飤”的省去“食”的寫法,認為:“省去偏旁現象在楚簡等戰國文字中大量存在”,同時,他們將這種省略現象的現象歸結于是古文字偏旁的漏抄[30]。
三、韻讀研究
在安大簡《詩經》的研究中,關注《詩經》韻讀研究的研究者也有數位。如俞紹宏、宋麗璇從韻讀的角度將毛本的韻讀和簡本《詩經》的韻讀進行對照,認為在韻讀上的一致性表明二者的親緣關系很近,可能都來源于孔子整理過的本子[31]。程燕則關注到了毛詩本和簡本用韻的不同之處:“雖然安大簡《詩經》大部分詩的韻例和所押韻部與《毛詩》相同,但韻腳部分用字的不同必然會導致其余用韻的不同。”[32]俞紹宏對《陟岵》一篇的用韻作了探討,認為“行役夙夜無寐”之句原本可能不入韻[33]。
四、文本性質研究
在現存的安大簡《詩經》研究中,對簡本文本性質研究的也有不少。如張樹國對簡本《詩經》的原型做出探討,認為其產生與歷史上身為魏文侯講師的子夏西河有關[34]。馬銀琴則認為安大簡《詩經》是流傳到楚地的抄本,極有可能與早年魏文侯推行霸業有關,而且簡本《詩經》的編排或為魏國早年改制《詩》樂、強化本國影響力的反映[35]。夏大兆對簡本“矦”風篇詩的文本產生進行了討論,認為矦即是晉,矦六篇均為晉詩[36]。他后來又進一步對簡本《詩經》的產生進行考證,認為“安大簡《詩經》底本可能是晉國的一個抄本或摘編本”[37]。除上述研究外,沈培從句讀入手,對簡本重新斷讀,并以簡本為對照,揭示毛詩本在詩旨、斷讀及字詞方面的不同,了解古人主注釋的正誤及其產生原因,把握古代文本流傳的復雜性[38]。
五、文本結構研究
在目前的眾多研究成果中,對安大簡《詩經》文本結構的研究也占了不小的比重,主要包括簡本《詩經》的句式研究和編次研究,其中編次研究又可細分為章序研究和篇序研究。
(一)句式研究
截至目前為止,單純對安大簡《詩經》的句式進行研究的僅李林芳,他認為簡本句式的整齊性要高于《毛詩》,推測《毛詩》雖產生于漢代,但其版本來源可能更加古老[39]。
(二)編次研究
1.章序
對簡本《詩經》章次的研究如下:楊玲、尚小雨對57篇簡文《詩經》中出現的8篇章次不同的異文成因和價值進行研究,認為互易的章次均發生在使用了復沓章法的詩篇中,而異文章次在文學表現力上多遜于今本《詩經》[40]。不同的是,鄭婧通過對比,發現,簡本《詩經》與《毛詩》共有14篇在章次方面存在差異,大多篇章的不同章次變化,對詩旨表達、詩意理解并無影響,但《駟驖》《綢繆》兩詩的章次互換后,在表達上或許更合理[41]。趙海麗則對《螽斯》的章次互易問題進行了單獨的探討,認為互易后的章次對以祝禱子孫眾多為主題的《螽斯》而言,更能形成邏輯和詩意上的層層遞進[42]。可見,對章次的互易現象,學者們大都持有不同的意見。
2.篇序
簡本《詩經》所涉國風的篇目編排,與傳統毛詩本相比,也不盡相同,因而也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關注。如,陳民鎮著重探討了“侯”“魏”“唐”之間的次序及關系問題,認為,“侯”即是“唐”,安大簡抄寫者因誤抄,故將“侯(唐)”“魏”的風名分別安到《魏》和《侯(唐)》之上[43]。王化平對安大簡《詩經》中“侯風”“魏風”的篇目編排歸屬進行了探析[44]。此外,還有徐在國從整體上對簡中異文和編排次序進行了概述[45]。
六、價值研究
首先,從簡本產生的時間上來看,安大簡《詩經》作為目前發現最早的《詩經》抄本,其本身的存在就具有極大意義;其次,從內容上而言,簡本《詩經》出現了大量不同于《毛詩》本的異文和編排現象,這對現有的《詩經》研究,無疑具有新的啟發意義。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對安大簡《詩經》的價值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其一,關注簡本異文的解題價值以及對詩旨的重新闡釋;其二,以安大簡《詩經》為對照材料,從其間異文看毛詩本中的訛誤及毛詩本文本的流變;其三,分析安大簡《詩經》中的女性本位意識;其四,關注安大簡的補證價值。
(一)異文的解題價值和詩旨揭示
在安大簡《詩經》的研究成果中,有部分研究者根據簡本異文新釋詩旨及分析解題價值。如,趙培依據簡中出現的“騶虞”字形,對《詩經·騶虞》篇中“騶虞”的幾種傳解進行新的分析和界定,他認為,“從安大簡《騶虞》的主旨可能與狩獵縱生及其所喻指的弭兵止殺相關。”[46]程燕對“茨”字重新訓釋,認為:“用居于墻上、活動于夜間、丑惡的蜈蚣起興,引起夫妻夜間枕邊所說之言辭,于詩意更為吻合。”[47]寧登國、王作順則將關注點放在了該篇異文的解題價值上,認為,該篇有“增字、減字、章次互換”三種異文現象,并探究該異文現象生成背后的原因,確證《江有汜》為單純的“美媵”詩[48]。
(二)從安大簡異文看毛詩本中的訛誤及毛詩本文本流變
作為與《毛詩》不同體系的安大簡《詩經》,對傳世毛詩本的文本流變及訛誤的訂正,具有極大的價值和意義,因而有不少研究者以安大簡《詩經》為參照材料,對這兩方面內容進行研究。如,徐在國以安大簡《小戎》為訂正材料,對《毛詩·小戎》的“亂我心曲”句重新訓釋,認為毛詩本中的“亂”字應當為“撓”字[49]。劉澤敏則認為,簡本《小戎》的 (亂)我心曲之 ,可能是“亂”的訛字[50]。在《秦風·終南》篇的研究中,徐在國從字形字音角度分析,認為《毛詩》本之“丹”在安大簡中寫作“庶”,應當是毛詩出現了訛寫[51]。同樣,徐在國還對毛詩《摽有梅》篇進行了訂正,認為“摽”應為“囿”,《毛詩》中的“囿”應為流傳中的誤寫[52]。劉剛對《魏風·葛屨》《秦風·晨風》兩篇進行訂正,認為《詩·魏風·葛屨》的“宛然左辟”本作“俛然左倪”,是描寫新婦行為特點的句子,《毛詩》作“宛然左辟”,可能因轉寫錯訛所致;而《詩·秦風·晨風》的“軟彼晨風,郁彼北林”,本作“軟彼晨風,吹彼北林”,意為“早上迅疾的風啊,在北林里呼呼地吹著”,且最早對“鴃彼晨風”做出正確解讀的是宋代的戴侗[53]。王挺斌對《小星》篇進行訓釋,認為毛詩本中的“嘒、喵”字對應簡本中的“季、李”,前者為假借關系,后者是訛誤關系[54]。趙敏俐則對簡本訛誤的原因做出推測,他認為簡本訛誤現象如此嚴重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底本本身存在問題;其二,抄寫者不夠嚴謹,從而出現抄寫之誤[55]。此外,吳洋對簡本八篇異文進行分析,從中管窺毛詩文本的流變[56]。趙敏俐再次對安大簡《詩經》出現的文本諸多問題做出探討,最終認為簡本《詩經》并非善本,對其中的一些文字上存在的問題,不宜作過高的評價[57]。
(三)從安大簡《詩經》看女性本位意識
除上述價值研究外,還有研究者將安大簡《詩經》和女性聯系起來,張瀚文關注到簡本《詩經·卷耳》“維以永傷”和《毛詩》本中“維以不永傷”的差異,認為古代文學作品中正面描寫女性多為堅貞不屈、舍己為人等“悲壯、崇高”的價值觀和形象,而簡本《卷耳》卻折射出不同的意境和思想,它站在女性的角度去同情思考女性的處境和命運,顯示出簡本《詩經·卷耳》所蘊有的濃厚的女性本位意識[58]。
(四)補證價值
安大簡《詩經》作為新出土的戰國文字材料,對現有的先秦楚地文字研究具有極大的補正價值。目前將安大簡《詩經》作為補證材料,用于補證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類:其一,補證《清華簡》;其二,補證《書》;其三,補證《世本》;其四,補證《孔子詩論》;其五,補證字詞。下面將逐一對上述五種補正進行闡釋。
1.補證《清華簡》
作為同屬戰國時期楚地的出土簡牘材料,安大簡《詩經》的出土無疑極大地豐富了戰國楚字研究的資料庫。因二者在產出時間和地點上的相近,因而可以互相補證。如,侯瑞華以安大簡《詩經》為材料,補論上博簡、清華簡等楚簡牘中的“刈”字,認為,楚文字中的疑難字 為“刈”的異體字[59]。馮聰根據安大簡《詩經·小戎》篇的 字,對清華簡 字進行考釋,認為,該字是 的異體字,應讀作“載”,訓為動詞“重”[60]。蔣偉男認為,安大簡《詩經·殷其雷》中的 字即清華簡《成人》中“ ”的異體字[61]。張樹國通過安大簡《詩經》,補證清華簡《耆夜》組詩為子夏所造的魏國歌詩[62]。此外,黃錫全將安大簡《詩經》中的“ ”考釋為“髡”的異文,進而論證《清華簡》中推測的“淋郢”,有可能就是楚國位于今紀南城遺址或附近的“南郢”地區[63]。
2.補證《書》
作為先秦出土材料的安大簡《詩經》,還有研究者將其用來補證《書》。寧鎮疆認為《毛詩》中的“之子”在安大簡中寫作“寺子”,其中的“寺”讀為“時”,理解為指代詞“是”,與“之子”的“之”相同,這一現象在清華簡的《書》類文獻中均有所見[64]。
3.補證《世本》
在現有的安大簡《詩經》研究成果中,還有研究者利用安大簡《詩經》補證《世本》。原昊對《世本》楚世系遠追顓頊得到印證,同時借助安大簡出土簡牘,將《世本》中楚康王、楚考烈王世系名號也得以確證[65]。
4.補證《孔子詩論》
季旭升通過比較《毛詩·鄘風·柏舟》中“母也天只”、《安大簡(一)·柏舟》“母可天氏”的語氣詞“也、只”及其固有句式,認為,《上博一·孔子詩論》中的“……溺志,既曰天也,猶有怨言”評的應是《鄘風·君子偕老》,而非《鄘風·柏舟》。[66]
5.補證字詞
借助安大簡《詩經》補證楚字的研究也較為豐富。如,夏大兆對安大簡72號簡中的“焚”字進行補論訓釋,他認為,安大簡《詩經》中的“苂”字雖在金文和已公布的楚簡文字材料未見,但上承接甲骨文,應釋為“焚”字,讀作“汾”,揭示了安大簡具有早期性的特點[67]。徐在國依據安大簡《詩經》出土材料,對楚文字“ ”進行新釋,認為,該字當釋為“兕”[68]。程燕則對簡文“古、希”字進行訓釋,認為安大簡“纟谷” 之異文可作 “希卩”[69]。徐在國以安大簡《詩經》為補證材料,對“傾”和“矛”及從“矛”的一些字進行論證[70-71],依據安大簡《詩經·周南·卷耳》中“不盈傾筐”之“傾”字,釋楚帛書中“ ”字為“傾”的異體。此外,李松儒以安大簡為材料,將之與清華、上博等簡牘放在一起進行對讀[72]。
七、余論
從目前研究成果的整理結果來看,學界對安大簡《詩經》的研究漸趨成熟,研究成績的突出點在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研究角度多樣化。在安大簡《詩經》的現有研究中,許多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簡本《詩經》作了研究:從文字學的角度,對簡牘文字的訓釋;從文獻學的角度,對文本的生成、性質、編排現象的研究;從音韻學的角度,對簡本《詩經》的用韻做出探討;從考據學的角度,對文本文字的訛誤進行訂正等。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注重采用對比研究。安大簡《詩經》作為截止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較為完整的《詩經》抄本,其內部的編排體系和文本內容與傳世《毛詩》本相比,都存在極大不同,因而不少研究者將目光聚焦在這一方面,將簡本《詩經》與《毛詩》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拓展了《詩經》研究的途徑和內容。第三,注重安大簡《詩經》與楚文化研究的結合。簡本《詩經》產生于戰國末期的楚地,因而保留了大量的先秦古楚文化的痕跡,安大簡《詩經》的出土,豐富了楚文化的研究資料,因而有部分研究者利用簡本《詩經》對涉及楚文化的疑難問題進行補證。多角度的切入,對照研究方法的使用,拓寬了《詩經》研究的視角和范圍,使得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安大簡《詩經》。
目前,安大簡《詩經》的研究不足之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研究內容占比不均衡。在安大簡《詩經》相關研究中,其中對字詞研究、價值研究的比重較大,對簡本文本性質、文本結構、韻讀等方面的研究比重較小,研究數量略顯不足,原因或許在于安大簡《詩經》異文大量出現,研究材料較為豐富。第二,對安大簡《詩經》地位的探討不足,安大簡《詩經》雖然作為迄今為止發現最早的《詩經》抄本,但其在文本質量似乎低于《毛詩》,因而在今后的《詩經》研究中,應賦予它怎樣的地位,是遵從《毛詩》本,還是遵從簡本,亦或是二者兼從,哪些方面從《毛詩》,哪些方面從簡本。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者深入討論。第三,對簡文的異文現象成因探究不足,截至目前,有大部分學者認為簡文異文的出現是出于抄寫者的不認真,從而導致訛誤的出現,可是試想,在近60篇簡文《詩經》中,若僅有三五處訛誤出現也可說正常,但目前發現的大量成因不同的異文,都歸結于訛誤,難免缺乏說服力。是以往的解讀出了問題,亦或是簡本《詩經》所展現的是另一種文字現象,亦或是其他原因。這些都值得反復思考。
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繼續加強對簡牘文本的考據和釋讀。文本是研究的基礎,還原文本的本來面貌、提高文本質量,是產生優秀研究成果的前提。安大簡《詩經》作為最早的《詩經》抄本,本身的存在對于《詩經》研究就具有極大意義,只是礙于本身展現出的不少訛誤,嚴重損害了它應有的價值和地位。如果將訛誤內容一一訂正,那么不僅將有助于還原先秦《詩經》的本來面貌,還能為此后的《詩經》研究提供一個可靠的善本。第二,繼續拓寬研究視角,加大對比研究。其一,將安大簡《詩經》與上博簡、清華簡等同類材料放置一起,進行同類比較,更容易發現其中的異同;其二,將安大簡《詩經》與傳世《毛詩》等“三家詩”放在一起進行比較,關注其中的變化,這樣不僅有助于對安大簡《詩經》的了解,還有助于研究傳本《詩經》文本的生成流變。第三,加強對已整理安大簡《詩經》的二次訓釋。安大簡整理小組雖已對安大簡《詩經》進行了詳細而嚴謹的訓釋,但人力有窮盡,安大簡《詩經》出土文本近60篇,數量較大,且受學術領域的限制,整理者對簡文的釋讀難免有所遺漏和偏失,因而研究者在使用該材料時,應謹慎地對待已整理的材料,重新審視已整理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