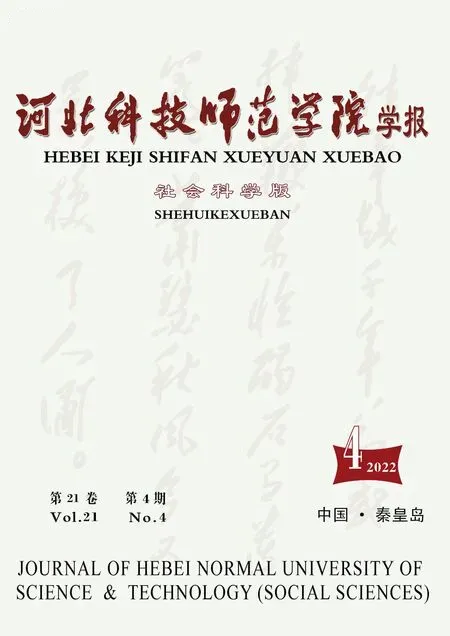論路內小說形象的“代際差異”與“身份認同”
林玉妹
(福建師范大學 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007年,作家路內發表長篇小說《少年巴比倫》,后來,又陸續創作了《追隨她的旅程》《云中人》《花街往事》《天使墜落在哪里》《慈悲》等五部長篇小說以及《在屋頂上牧云》《十七歲的輕騎兵》兩部短篇小說集。雖然路內獲得了不少獎項,但路內在當下的讀者群中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路內的轉型之作《慈悲》,路內憑該作獲得第14屆華語文學傳媒盛典年度小說家獎后,才算真正地走進了更多讀者的視野。后來,隨著路內小說的同名電影《少年巴比倫》和《十七歲的輕騎兵》的上映,作家路內借助影視媒體的宣傳力量,才慢慢地提升在年輕讀者群中的關注度與影響力,后來,才逐漸有不少碩士研究生以其為研究對象撰寫碩士論文。
目前雖然有不少研究關注到路內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成長與追尋主題,但是較少關注到不同代際的工人形象差異,對水生這個青年工人形象的分析也不夠深入。筆者以市場經濟浪潮下,國企改革中工人的身份認同的變化對師徒傳承危機的影響為主要的考察路徑,著重關注在工廠的“規訓”中,不同“代際”的工人成長經驗對工人的影響,深入闡釋師徒制度的傳承危機和新時代“出走”的誘惑和可能。
一、不同“代際”的工人成長經驗
阿爾弗雷德·格羅塞在《身份認同的困境》中提到了“代際”的涵義,“它指的是在某些重要歷史事件發生時,擁有大致相同年齡段的男人和女人。然而,不應當僅依靠某種共同經歷就演繹出一種共同記憶。在類似經歷中,個人身份的多樣性會導致記憶內在化的不同,繼而導致在日后對記憶的應用也不盡相同。”[1]34在格羅塞關于“代際”定義中可以看出身份認同與“代際”、個人身份的多樣性、共同的經歷之間的關系。同一“代際”的人,總是攜帶著昔日的生存體驗繼續生活。因此,個人身份的多樣性會導致同一年齡段的人即使面對同樣的經歷,也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如果按照傳統的概念劃分,以路內的《慈悲》和“追隨三部曲”為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代際”。從代際的角度出發,水生的父親和師傅對水生的一生都起著思想引導作用;在“追隨三部曲”中,綽號“老牛逼”的路小路的師傅、堂叔、父親也都是父輩的代表,他們的處事原則是遵循;水生、根生、玉生等是被啟蒙的一代,長頸鹿、廣口瓶、路小路、楊一、楊遲、長腳、小蘇屬于新一代年輕工人,他們更加強調自我,具有反叛意識;復生則是“重建”希望的第三代。
汪民安在《文化研究關鍵詞》中寫到:“在當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評中,‘identity’一詞具有兩種基本含義:一是指某個個人或群體依據確認自己在一個社會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確的、具有顯著特征的依據或尺度,如性別、階級、種族等等,在這種意義上,可以用‘身份’這個詞語來表示。在另一方面,當某個人或群體試圖追尋、確證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時,‘identity’也被稱為‘認同’。”[2]283路內筆下的文學典型主要是側重于前者。從這個角度出發,水生的父親、師傅都是幫助水生建立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傳遞生存哲學的重要人物,他們和水生共同塑造了一個父親的形象[3]124-129。正是父親的逃生策略和師傅的肯定,使得水生逐漸具備身份認同的顯著特征,這也造就了他的沉穩和慈悲,彌補了他與師傅之間的“代際”差異。從而構成了水生夾雜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復雜形象。而對于同一“代際”的根生而言,面對共同記憶,不同代際所造成生存體驗差異使得他與師傅具有不同的應對方式,“記憶”對他們所起的作用大相徑庭,比如他們面對工廠的“規訓”所做出的選擇,是二元對立的遵守與反抗。
作為父輩的傳統工人們,擁有穩定的物質生活和“工人當家做主”帶來的身份認同感。傳統的工人身份在他們心中,是光榮感和穩定的代名詞,在肖克凡的《生鐵開花》中,王云亭曾說道:“當了工人多好啊,走到哪兒都受人尊重!進工廠多好啊……”[4]29在《慈悲》中,按照水生嬸嬸的說法,工人的顯著特點就是“不會餓著了。”水生師傅剛收水生為徒的時候,就告訴他要穿代表工人階級的勞動皮鞋以防被欺負。車間領導還得讓工人三分,在《少年巴比倫》中,路小路的師傅,綽號“老牛逼”的工人,他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曾用煙灰缸在車間主任的腦袋上敲了三下,事后不僅沒有遭到任何處罰,反倒是被打的主任托人給他送了一條香煙,最后才談妥。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工人因為不滿被工廠領導克扣獎金而拉下電閘這件事沒有被當作車間重大的生產事故,工廠領導卻由于擔心他做出諸如炸廠長辦公室這樣的事情而不了了之。這其實都是傳統技術工人的身份所提供的保障。此外,他們還有民間組織為其提供經濟支援。民間的捐會或者稱作互助會,互助會建立在在人與人之間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沒有法律條文的監督,形成了屬于獨特的人際關系圈。在《慈悲》中,水生師傅帶領水生參加捐會,目的除了幫助其購買大件生活物品之外,還在于讓他融入工廠的互助圈,使其逐漸認識到工人身份帶來的認同感。除了自發組織的捐會,每個車間都有申請補助的權利,雖然常常是以犧牲個人的利益來換取,未能確保公平,但是卻是老工人們解決燃眉之急的一條途徑。比如水生師傅在得知水生不能及時通過捐會的錢買自行車后,又替他找李鐵牛要補助,師徒之間的感情非常濃厚。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到了不同于中國傳統社會的行會學徒特征:“對師傅的依附關系即是個人性的又是絕對的;法定的訓練期限,結束于一次資格考試,完全按照嚴格的計劃而不可更改;在師傅與學徒之間有一種全面的交換,師傅應該傳授知識,學徒應該提供服務,做輔助工作,往往還要支付一些費用。這種私人服務形式是與知識的轉讓混合在一起的。”[5]168在路內的“追隨三部曲”中,路小路與“老牛逼”師傅、水生和水生師傅,不僅是單線的“教與學”的交換關系;資格考試的結束也不是按照嚴格的計劃不可更改,而是由各師傅根據所帶的徒弟的表現來決定其出師時間。《慈悲》中的水生,跟著師傅做了一年,一級成品率達到了和師傅一樣的水平,既勤奮刻苦,又遵守車間的規章制度,所以不用多久就出師了。在中國的傳統“師徒關系”中,資格考試的完成往往是師徒之間萌發更為深厚的情感的起點,而不是終點。除了技術上的指導,師傅對徒弟在思想觀念上的引導更為重要。工人社群中的師承關系可以為每個新入職、新進入社會的年輕工人提供一些建議,降低他們因缺乏閱歷而造成的犯錯率,因此,師徒關系在工廠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作為被啟蒙的一代的水生、根生等工人,除了具備自己特定的“代際”特征之外,還受到了不同的生存體驗的影響。不同代際的生存體驗差異,是“師徒之間”發生思想碰撞和磨合的源泉。根生與水生面對同樣的規章制度和教育,卻具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水生的早慧,是因為他具有區別于同代人的父輩生存體驗。水生十二歲時,一家集體逃難,最終的結局是爸爸和弟弟音訊全無,媽媽也在尋找家人的途中喪生。而且,在水生的記憶深處,一直有一個骨頭像一根剝了皮的枯樹枝的人在向父親揮手的畫面,父親遠遠地喊道:水生,走過去!不要看他!”[6]7-8面對親人的離世、職位的下調、下崗的風潮,水生都有“走過去”的勇氣和選擇。此外,水生的叔叔也是重要的引導者,吃飯的三成饑和穿衣的三分寒是叔叔所傳授的“家底”。水生到了廠里以后,工廠里的毒,也成為他眼中的“家底”[6]10。在水生看來,“家底”是一種不完美的東西,“跨過死亡”“饑寒”“毒”都是普通人們的生存考驗,但是一旦能夠忍受并接受它,就說明少年在“成長”,他不再橫沖直撞、過于貪婪,而是保持善良,深諳工廠的生活哲學。正如阿爾弗雷德·格羅塞在《身份認同的困境》中所言:“個體行為受到群體內部的制約,也許先受到外界的制約,伊曼紐爾·列維納斯徒然呼吁個體“表里如一,成為自我,去內在認同自身。”[1]7人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通過自身的行為所帶來的自我認同感受到了外在環境的制約。水生試圖通過工作帶來的內在認同,擺脫外界的制約。家人喪生和生存困境切斷了水生的身份認同感,師傅的溫情治愈了他,使其具有擺脫外界制約的信心。“‘集體記憶’是后天的習得和傳承,它通過家庭、階層、學校和媒體來傳承。”[1]34家庭、學校是水生的“集體記憶”習得的重要媒介,而水生師傅是其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人。在技術上,師傅對他十分滿意,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給予了水生信心和鼓勵。師傅在認真考察以后,把承載著自己的期待的人生經驗教給水生:“是根槍就要立起來。”[6]2-3這是水生一直以來的精神動力。從前,在師傅的“幫、傳、帶”模式下,水生曾經在工廠獲得了家庭般的溫暖,他也將自己所獲得的溫情傳遞給徒弟林福先。在生活上,師傅幫水生領取了兩雙具有工人階級標志的勞動皮鞋,不僅傳授給他技術,而且為他買自行車申請補助,教他適應工廠生存環境的方法和給予他追尋理想的動力。因此,早慧的水生擁有父輩的獨特的生存體驗,在師傅的敦敦教導之下,他深諳老一輩工人的生存之本和力量之源,懂得了處理好工廠中人際關系的重要性。后來,面對經濟和社會關系的瓦解,師傅因為申請補助和喪葬費失去了一直以來最為看重的自尊。甚至在患了骨癌,還親自到苯酚廠要自己的喪葬費。師傅的離世帶走了水生在工廠中逐漸建起來的身份認同感和歸屬感,當然,也強化了水生的自我保護意識,讓水生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工廠的嚴酷秩序,改變了以往對工廠所存的依賴意識,深刻地明白了工廠給不了一個普通工人真正的尊嚴。水生是工廠裝置中早慧的“清醒者”,他和父親、師傅一樣經歷過“生死的抉擇”,選擇了在制度的“規訓”中周旋,獨特的個體生存經驗使得他和根生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像水生這樣的子輩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像根生這樣的人。既不滿足于當前的生活環境,但是又被困在工廠所安排的軌道中。在《慈悲》中,根生的個性與工廠的規訓是格格不入的,他幾乎得罪了工廠里的所有人。在統一的資源配置之下,水生的行為是侵犯到其他人的公共利益的。比如他因為食堂的飯缺斤少兩而和食堂的人打架;也曾經順手牽羊偷過紗手套。逃出獄以后,他依然會因為水生的小孩被白孔雀欺負而拆掉托兒所的秋千架[6]38-40。同時,根生又是一個不甘平凡的時代新人,他不滿足于看管廢品倉庫的工作,提前二十分鐘溜出廠偷擺地攤賺錢的行為了。正是內心的貪戀使其掉進了金錢的漩渦,最終因為走私香煙,賠掉了全部的本錢。水生是一個處于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的復雜性人物,與父輩的共同記憶令其深諳工廠的生活哲學,但是長期以來,子輩工人的社會體驗使得他缺乏父輩工人的身份認同感。水生是時代的“早慧者”,但是早慧代替不了經歷,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動,他和父輩工人具有完成不同的應對方式,比如他用不同于以往的理由替工友們申請補助,在“下崗潮”中外出辦廠,適應了時代的轉向,創造了第二代工人“出走”的可能性。
此外,青工長頸鹿和廣口瓶則是更年輕的第二代工人代表,他們更加敢于反叛和“突圍”。廣口瓶比“叛逆”的根生更為大膽,不顧眾人的反對,把朱建華用來記工人們的“私語”的小本子放在茶缸里點火燒了,苯酚車間是禁火的,他這么干是非常危險的。等火燒成灰燼以后,廣口瓶往茶缸里澆水,命令朱建華吃紙灰[6]77-78。他們是未被工廠制度徹底“規訓”的青春叛逆者,會因為利益,不惜鋌而走險,當走私煙的中間人。《少年巴比倫》中的管工班的長腳想要參加成人高考,暗地里復習功課,及時被發現后,班里其他人四處抓他,不讓他復習,甚至燒了他的復習資料,還派兩個師傅看著他干活。白藍擔心檔案被廠里卡住,瞞著廠里考上了研究生,最終選擇先辭職再上學。廠干部們四處堵莊小雅,不讓她去美國,她攔卡車直接去上海。
綜上,“代際”、身份認同和生存體驗之間互相建構,從水生師傅到復生,不同的“代際”所發生的“沖突”和碰撞是我們回看身份認同的重要意義的基礎。筆者在該部分也通過了對路內筆下的典型形象進行較為深入的分析,發現他們同樣都有存在之思和個體救贖情懷。無論是水生還是路小路,都不只是傳統敘事中“高大全”的工人形象,更是對身份認同感具有強烈期待的追夢者和具有人文情懷的青年工人,這其實也體現了作者將日常生活審美化的寫法。“代際差異”不只是社會現象的普遍描述,還是打開多代人之間情感交流的閥門。結合典型工人形象水生的分析,逃生經歷帶給了自己和師傅一樣的共鳴體驗,這使得他能夠領悟到生存本身的真諦,深諳工廠的生存哲學,即使自己逐步探索到通往光明的未來的路徑,依舊還是保持初心,盡量為他人申請補助,在國企改革的時代巨浪中躲過一遭,并依靠自己的技術探索新時代的可能。當然,水生這個文學典型形象也不是完美的,他也沒有做到阻止鄧思賢出賣根生,他也會為了幫工人申請到補助而“編造”理由,但是他主動幫助出獄后的根生,在自己本身就很艱難的情況下,還愿意幫助段興旺,最后還把自己曾經獲得的溫情傳遞給徒弟林福先,是以“慈悲”為內核的個體救贖情懷的詮釋者。
二、遵守與挑戰:工廠的“規訓”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提到:“紀律的歷史環境是,當時產生了一種支配人體的技術,其目標不是增加人體的技能,也不是強化對人體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種關系,要通過這種機制本身來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而變得更有用。”[5]148在工廠中,“不能用腳踢門閥”的廠規、補助申請條件、青年工人的性壓抑以及時刻潛伏著的告密人是管理者規訓工人的重要載體,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和“馴服”工人。而且,工廠中的工人也有明確的等級劃分,技術工種比操作工種地位高和體面,操作工要倒三班,從白天干到深夜,從日落干到日出,甚至吸入有毒的氣體,患上各種癌癥,每個人都要遵守森嚴的等級制度,在自己的位置上規規矩矩工作。
在《慈悲》中,“不準用腳踢門閥”是工廠對工人的身體和欲望進行壓制的重要方式,這種“規訓”和“秩序”主要體現在在“不能用腳踢門閥”的廠規和“申請補助”的條件上。地上的閥門必須用手關,一旦用腳踢,就會以破壞生產罪遭到嚴厲懲罰。因此,工人們必須彎下腰去關門閥。而且罪的輕重和判罰的刑期不是根據實際的情況,而是根據服從的態度,這也是制定工廠紀律的目的。在這里,“門閥”是領導用來規訓工人的載體,遵守“不能用腳踢門閥”的廠規也就意味著服從管理,在工人們的互相監督中,實現“不會有混亂、盜竊、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質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現象的目的[5]216,在這個以生產效益為工廠盈利的空間里創造更大的收益。
面對工廠的“規訓”,不同“代際”的工人具有不同的態度。老一輩往往是傳統制度的遵守者,在他們的記憶之中,“規訓”的背后是穩定的經濟來源和工人身份的光榮感。對于他們來說,廠規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觸犯的,這也是他們在剛招收徒弟的時候,第一時間要交代的事情。當然,規訓的對立面是被懲罰的后果,一旦同時觸犯“不準用腳踢門閥”的廠規和不尋常的“性關系”,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于是,工人對工廠“規訓”的不滿只有在退休以后才會去發泄。對于《少年巴比倫》中的王德發而言,忍耐和檢舉他人是其生存哲學;但是退休以后,他會因為藥全都不能報銷,到廠里的醫務室出氣;也會因為退休工人拿不到補助,把口水全都噴在魏慶功的臉上。在這短暫的發泄中,王德發找到自己真的年輕和解放的感覺[8]152。在路小路的印象中,宋書記不會關注工人的身體情況和告密被抓,直到退休后,他才說出工廠的規訓與懲罰的不合理性。
鄧思賢和根生同樣是門閥制度的挑戰者,根生是一直被打到小腿失禁才慘叫,即使是這樣,還是不低頭。而鄧思賢被抓住,還沒審就主動承認錯誤了。因此,他們所受到的懲罰是大相徑庭的。而且,王德發落井下石,揭發根生與汪興妹不尋常的關系,這加重了他的刑罰。一旦“用腳踢門閥”的違規行為和“性事”相關聯,根生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這一切的背后,是“檢舉有功”的獎懲機制在背后操縱著。補助的申請也是工廠管理者用來規訓工人的重要方式。在水生師傅那一輩工人看來,工廠補助是國家給工人的經濟保障。如果工人在生活方面有困難,可以向廠里提交補助申請,在考察核實后會通過,根生和石寶都曾經得到過廠里的補助。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雖然摻雜著人情等因素,但卻得到了老一輩工人的長期遵循。后來,宋百成規定,“第一,申請人得足夠窮、足夠困難;第二,提交人得足夠有口才、足夠有水平。”[6]82水生憑借著口才,以沒有夫妻生活為理由,替段興旺申請補助,打破了工人們原有的認知;他甚至將工傷說成是烈士,從兩代工人申請補助的對比視角,可看出子輩的工人對傳統的工廠“規訓”制度的反抗。
相對于遵守“規訓”的老一輩工人,路小路這一輩人是沒有歷史的一代。在他們人生中重要的抉擇期,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先的平衡狀態被打破了。青年工人們認識到整個工廠的規章制度存在著不少不合理的制度,他們更在意個人的感受。所以,面對工段長朱建華不合理的“監督”,廣口瓶和長頸鹿敢于不顧眾人的反對和苯酚車間禁火的規定,把朱建華用來記工人們的“私語”的小本子放在茶缸里點火燒了;等火燒成灰燼以后,廣口瓶往茶缸里澆水,命令朱建華吃紙灰[6]77-78。此外,路小路、廠醫白藍、小蘇、長腳、于小齊、寶珠等人依舊敢于反抗工廠心照不宣的“規訓”,選擇偷偷備考等方式,不斷地靠近自己心目中的“黃金海岸”。
工廠的“規訓”在本質上就是對身體和欲望加以克制的一種手段。隨著工業文明的發展,廠規成為了規訓工人的重要媒介,領導者以嚴苛的處罰方式來警醒一代代的工人,傳遞“不得反抗權威”的觀念,但是他們卻忽視了最為重要的一點,先入為主的管理方式,使得他們忽視了工人的主體性,忽視了人性的特點。恰如《審美現代性》中關于審美的現代性與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的相關論述,或許可以說,“工廠的規訓就是阿多諾所認為的資本主義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法則對日常生活的廣泛滲透,體現為他為的原則和可替代原則,而藝術本質上是自為的存在,它是不可替代的自律存在。因此,現代主義藝術的審美現代性,就呈現為一種對日常生活的否定功能。阿多諾認為,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啟蒙的工具理性發展到極端的產物,理性壓制感性,道德約束自由,工具理性反過來統治主體自身,啟蒙走向了它的反面,其最極端的后果乃是法西斯主義乃其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阿多諾看來,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嚴峻現實,破除工具理性壓制的有效手段之一乃是藝術,因為藝術是一種世俗的救贖。所以,現代主義藝術必然拋棄傳統藝術的模仿原則而走向抽象性。”[7]43因此,文學作為藝術的一種方式,也承載著對極度理性化的啟蒙工具加以消解的責任,路內從對工廠的“規訓”方式到子輩工人的反抗,到“慈悲”為懷的救贖母題,都在詮釋藝術作為一種世俗得勁救贖方式所起的作用。
三、出走:時代變動下的失落與反抗
在計劃經濟時代,工人具有一個穩定的生活空間。在20世紀80年代初,單位里造的公房,分配到職工手里,交一點房租就能住進去……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單位的名稱來定的[8]8。工廠提供一系列的配套設施,工人的生活完全可以在工人新村的范圍中自給自足。因此,在以往的低風險環境中,從未面臨下崗與再就業問題的工人階級普遍缺乏思想與技能上應對風險的準備。這一隱患最終導致工人們在失去國有企業的庇護后,喪失了尋求新時代出路時可以憑借的自身力量[9]。
20世紀90年代以后,正處于大下崗時代,沒有人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龍套的[10]19。職工與工廠的關系在發生變化,終身制和工人階級的優越感被現實所挫敗。在以往,勞動皮鞋對工人來說是身份的象征,而對于路小路來說,那種勞動皮鞋穿在腳上,一天的工夫,就把襪子磨得前穿后破。在《慈悲》中,“苯酚廠實行股份制以后,宿小東廠長是大股東,其他干部是小股東,工人要出錢,買廠里的股份,做散戶。城里的工廠都在關停并轉,工人除了要掏錢買股份,還要買下已經分配到手、住了十幾年的房子[6]161-163。人們失去了穩定的住房保障,不少人甚至被迫下崗。水生為了不下崗,只能返回做操作工。段興旺和妻子在時代的沖擊之下雙雙下崗,因為沒有錢治癌而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導致死亡[6]170。
此外,廠長為了節省開支,較多地招農民工,正式工都下崗了。因為以往發給正式工的那份錢,現在可以雇兩個農民工,余額還能給正式工發下崗工資[10]54。工廠在供求關系失衡的壓力下,為了‘減績增效’,增加了農民工的就業機會,而城市工人時刻處于下崗的壓力之中。“在技術的總體效果范圍內,自動化和半自動化反應充斥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工作時間的機械化勞動……因為機械化加快了勞動速度,控制了機器操作者(而不是產品)并把工人們相互隔離起來。”[11]24-25機器和先進技術替代了工人成為了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工人之間被相互隔離起來也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淡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傳幫帶”的傳統師徒模式存在的必要性,一頁密密麻麻的機器使用說明替代了傳統師徒模式中的“言傳身教”。而且,自動化的否定特征十分顯著:加速、技術性失業、管理層地位的提高、工人無能為力和聽天由命思想的增長。由于管理層更需要工程師和大學畢業生,晉升的機會逐漸減少。工廠面臨倒閉的壓力,技術創新迫在眉睫。工廠提供給工人的,不僅是工資和福利,更是一種競爭力[12]230。工廠的自動化發展帶來的否定特征使得老技術工人師傅不再一心一意地教徒弟,甚至形成了“教會了徒弟,餓死師傅”的心理。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便工廠不衰落,師徒之間的傳承關系同樣也會逐漸弱化。《慈悲》中的鄧思賢到車間偷冷凝塔的設計圖紙,發現老工人們不約而同地把自己以前設計的圖紙銷毀了。就像鄧思賢所說的,“宿小東找了很多外地民工來頂崗,他們工資低,又找了新畢業的大學生來做技術員,他們服從管教,理論水平比他們還高,而且會電腦。如果不銷毀圖紙,作為老技術員和老工人,用不了三天就會被清退。”[6]186這些年輕的大學生和復生一樣,都是新一代的希望。隨著工業化生產的發展,傳統的“師徒”模式在新時代發生裂變,隨著技術傳承的消失,社會關系也逐漸瓦解,師傅在時代變革的挑戰之下呈現出了“衰敗”的形象。路小路的父親,自尊自愛的工程師,在被偷走兩輛自行車后也撬開了別人的車鎖[10]19。這些下崗工人曾經的自豪感和優越感已經被現實的困境磨盡,他們在社會上成為了被拋棄的無用階層。在《少年巴比倫》中,路小路的堂叔也下崗了,靠一個小車攤維持著全家的生計。他也成為了靠把玻璃渣子灑在路邊來獲得賺錢機會的人了[8]33。“老牛逼”等師傅們在上班期間下圍棋,顧不上干活,凡有管道泄漏,都讓徒弟去處理[8]174。當然,路內并沒有停留在對老一輩工人“衰敗”形象的平面化敘述,而是關注個體的主體性,深入傳統工人的內心世界,關注工廠自動化的否定特征所帶來的影響和工人階級身份的失落感,傳遞了老一輩工人在面對變革的精神失落和緊張情緒。
在黨圣元和陳定家編選的《審美現代性》提到,“現代性的批判性反思總是奇怪地包含著對現實強烈不滿的情緒,它的社會理想也不只是單純地朝前看。現代性反思傳統中,就有不少思想家懷著對傳統的溫情脈脈的眷戀,帶著美化傳統的想象來批判現實。盧梭以及整個浪漫派的哲學和文學都是以回歸傳統對抗工業主義來表達批判性反思的。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性是一種自己批判自己的態度,是一種反對自身的致思趨向。如果把現代性看成一個思想運動,當然其中始終包含著正面建構現代社會的各種思想理念,但那種批判性反思始終占據主導地位。這正是現代性社會得以不斷更新變異發展的精神動力。如果一個社會、一種制度喪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它的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也就極為有限。”[7]74在他看來,雖然現代性的批判性反思包含著對現實強烈的不滿情緒,但我們還應該看到它所包含的正面建構現代社會的思想理念,這是現代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這也對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戰。一旦處理不好工廠傳統的運營模式與新的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將會造成人才流失和工人消極怠工的后果,這是屬于兩代人的共同困境,父輩工人失去了技術精湛帶來的成就感;子輩工人既失去了工廠內部晉升通道,又時刻處于下崗的壓力之中。比如苯酚廠搞技術革新,水生和鄧思賢合作改進了原料管道,廠里只發了二十元獎金,兩人各得一半[6]33。此外,糖精廠在考察新工人技術評職稱的時候,考察鉗工的內容不是修理水泵,而是考核他能不能把一個鐵塊銼成一個立方體;結果不行的時候,師傅和干部叫板,干部妥協稱反正鉗工也只是擰擰螺絲而已就通過了[8]49-50。在工廠里干部和工人都知道的潛在的問題,但沒有人愿意去反映和改變。這一系列的變化導致工廠的生產效益低下,缺乏市場競爭力。
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之下,國營經濟走向衰落和傳統老工人靠“消極怠工”等待退休時間的到來。他們用自己的“無能為力”告訴自己的子女,工人的身份伴隨的是漂泊、不穩定、恥辱等詞匯,是失意者的選項,當工人是不肯學習或者成績不理想的學生才會選擇的道路。“在黎明的職工子弟中學,老師時刻會用嘲諷的語氣說,你們不好好學習,就只能回黎明廠做工人。在有著二百多萬產業工人的沈陽仿佛有一個共識:做工人是可恥的。”[12]230在這樣的教育之下,父輩所面臨的時代劇變所造成的精神失落也間接影響了子輩的價值觀念的形成。所以,即使他們成為了工人,也缺乏父輩工人的身份認同感。最大的變化是,有一度下崗這個國家調控措施變成了糖精廠的行政處罰手段。在《天使墜落在哪里》中,廠里的標語也換成了“服從大局,爭創先進”,還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之類的話[10]284。而且,工廠不再是提供各方面保障的場所,路小路曾經希望得到工廠的關心,后來在見到那些被機器切掉手指的人和被硫酸噴到臉上的人之后,認識到頭上的紗布只會引來嘲笑,而不會帶來任何希望[10]73。子一輩工人的希望的喪失,也意味著工廠不再是工人們的精神之源。
面對“出走”的誘惑和可能,水生和鄧思賢合作造新廠,他們開始“外出”試車,逐漸適應這突然的時代轉向。路小路等工人們重復做著“簡單的工作”,在技能方面沒有多大的提升,在工廠內部也難以獲得提升的機會。雖然工廠用各種方式對主動離開工廠的工人設置障礙,但是路小路、長腳等子輩工人依舊選擇通過成人高考、考研和出國來獲得提升自身的身份認同感。比如廠里得知莊小雅要去美國,廠干部們四處堵她,她最終只好攔卡車直接去上海;部隊面向工廠征召青年入伍時,廠里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希望技術骨干、優秀青年入伍,比如不讓比較符合要求的工人,電工班的小李,去參加征兵選拔等等。
此外,在路內的“追隨三部曲”中,路小路講述了自己青年時代的故事,采用了倒敘或者說回憶模式的敘事手法,而不是按照時間順序記錄其成長軌跡。這樣的處理方式更加容易帶領讀者回到文學現場,回到路小路的時空中一同成長。路內的回憶敘事與當代文學的人性敘事相互交叉,如“鐵西三劍客”——雙雪濤、班宇、鄭執的作品也離不來以追憶的姿態記錄往昔歲月的模式。“記憶一直都是一種重要的文學載體,在路內的小說創作中,從江南小城鎮圖景的建構到對于城鎮人的生存反思,都是出于對過去城鎮記憶和工廠記憶重構與再現的渴望。通過對于往昔生活的追憶,也逐漸拉開了屬于一代人的小城鎮序幕。回憶性敘事令路內的文本里始終隱匿著一種感傷而又深情的追憶目光,但同時又插入理性的現代性審視,這也成就了路內獨特的文本風格。”[13]
結 語
綜上所述,通過探究不同“代際”的工人成長經驗,以水生的復雜性形象為考察路徑,分析個人身份的多樣性、代際與集體記憶之間的關系,通過對比兩代工人的身份認同感差異,闡釋他們在面對工廠的“規訓”時的不同態度。同時,以水生師傅和段興旺申請補助的理由和態度的對比,闡釋九十年代國有企業改革對父輩工人的理想主義情懷的顛覆,展現“衰敗”的師傅形象和勇于接受挑戰的徒弟形象。此外,探討時代變動之下的父輩的失落與子輩的反抗,在對比探析中強調工人身份認同感的重要性。當然,作品也通過水生與水生師傅、路小路與“老牛逼”師傅的師徒關系對比,探討新時代背景之下“師徒之間”的傳承危機,同時也展現了九十年代市場化浪潮和國企改革對工廠工人的影響,探討新時代工人“出走”的誘惑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