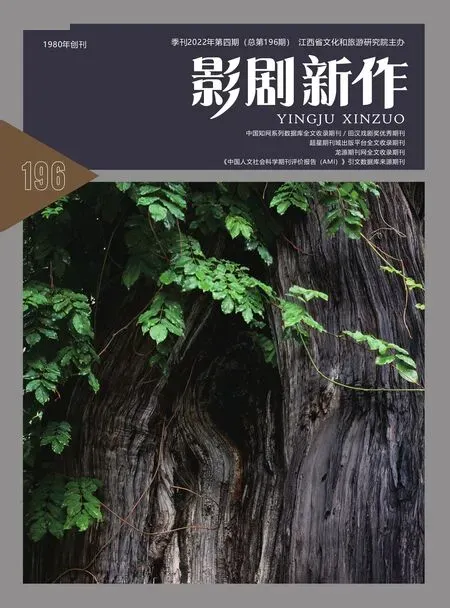試論張庚與格羅遂藝術、戲劇觀點的異同
李夢希
張庚先生是“前海學派”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主要創立者之一,主持完成的《中國戲曲通史》《中國戲曲通論》《中國戲曲志》《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卷》等著作早已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可,在戲曲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方面居功至偉。張庚先生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績,與他豐富的實踐經歷與廣博的學習積累密不可分。他自青年時期起即廣泛學習外國經典藝術著作,格羅遂(即格羅塞,張庚先生慣稱為格羅遂,今從)之理論與方法便是他頗為推崇與積極踐行之一種。1932年,張庚先生就曾于武漢翻譯、發表格羅遂《藝術的起源》之第二章《藝術學的方法》。同年,在反駁一自稱“門外漢”者“個性等于精神生命”的立論時,他借《藝術的起源》中對《哈姆雷特》與《荷馬史詩》作者的議論,認為社會對于作品的影響更甚于某一作家。[1]126-127上世紀40年代,他在《戲劇藝術引論》中大量引用《藝術的起源》中的例證和觀點,完成了自己對于“各種藝術在戲劇中的綜合”之論述。[2]63-661990年,在全國藝術研究工作座談會上,他稱贊格羅遂是個“很好的研究家”,用格羅遂以調查研究得學問的做法舉例,駁斥了彼時一些人在外國搞點資料就寫本書當研究的不良風氣。[3]331
從上世紀30年代到90年代,格羅遂及其《藝術的起源》反復出現于張庚先生筆下和口中,可見其學說確乎對于張庚先生產生了一定影響。此外,張庚先生高足吳乾浩在回憶自己的學術歷程時也提到過,正是因為張庚先生“常說外國有一個搞藝術史的格羅塞到原始部落去田野考察后”“寫出了有價值的《藝術的起源》”,才促成他產生了對戲曲現狀進行調查以嘗試解決戲曲安危與前途的思路。[4]134彼時,集成志書編纂工作正在全國如火如荼開展,調查研究的方法在這一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參與調查的許多人都曾和吳乾浩一樣,受過張庚先生教導。可以說,格羅遂的學說與方法不僅直接影響了張庚,更由于張庚藝術教育家及領導者的身份加持,間接影響到了“前海學派”及與之相關的各地方藝術研究單位。比較、把握張庚與格羅遂的藝術見解異同,能夠捕捉到一些格羅遂對張庚的具微影響,看到張庚對外國藝術理論的揚棄借鑒,有助于我們更好認識張庚先生的學術淵源與成長動因,也有助于我們今天在戲劇領域更好地借鑒、學習格羅遂、藝術人類學與國外藝術界的理論成果與實踐經驗。
一、如何認識藝術、戲劇?
格羅遂說“最初期的藝術”和“其他一切時代的藝術”在“主要動機、手法和目的”上是一致的,“原始的和高級的藝術形式之間的差別是量的方面多過質的方面”,他以為“戲劇是詩的最古的形式”。[5]236、202類似的,張庚先生也認為“我們現代的戲曲,一定的意義上只不過是史前時期的東西”。[6]83-84后來,還有人進一步就此闡發出了張庚先生的“史前戲劇說”。[7]512-516格羅遂與張庚均主張回到歷史原點審視藝術或作為藝術種類之一的戲劇。格羅遂說,“音樂在文化的最低階段上顯見得跟舞蹈、詩歌結連得極密切”。[5]214張庚先生在著述中也多次提及詩、樂、舞之間關系,“前海學派”在《中國戲曲通論》中更是用一整節闡述了詩、樂、舞的混合、綜合與戲曲形式的形成,可看作格羅遂詩、歌、舞接連密切的中國化說法。[8]99-113詩、樂、舞緊密結合是中國戲曲同其他民族的戲劇形式一樣自起源萌發以來即擁有的共通性鮮明特質,載歌載舞地對文學進行舞臺重塑至今仍是中國戲曲的基本呈現形式。今天的中國戲曲,雖然在詩、樂、舞的結合上有了更為復雜化、多樣化的創造性更設,但實際仍只是量的增加而未有質的變化,仍屬于格羅遂所說的“文化的最低階段”與張庚先生所說的“史前時期”。
“初期藝術”與“史前時期”是所謂高級藝術與現代時期的源頭與根本,因此格羅遂主張獲得藝術的科學知識應研究藝術的原始樣態,且應從歷史學與考古學走向人種學,他認為“藝術學的研究應當及于一切民族,而且應當特別對于那些不被注意的民族去盡力研究”。[9]168張庚先生亦大力提倡進行少數民族藝術研究,主張將少數民族戲曲作為中國戲曲的重要組成部分予以關注。張庚先生不僅主持成立了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少數民族戲曲研究室,還多次出席少數民族戲曲相關活動,對少數民族戲曲研究人才予以親切關懷,主張在重要戲曲史論中加入少數民族戲曲內容,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于病床上還心心念念著少數民族戲曲……[10]156-162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僅反對部分人“原始民族和文化比較落后的民族,他們的任何東西都覺得是不可理解的”之錯誤觀點,還能夠保持“不要把它當作落后寶貝,不要將它神秘化”的理性思考與高度警惕,顯示出了成熟學者應有的沉穩與睿智。[11]406
張庚先生曾說“西方人的傳統看法,劇作也是一種詩”,格羅遂就認為戲劇是詩的最古的形式。[12]283格羅遂反對“多數的文學史家和美學家都以為戲劇是詩的最新的形式”,[5]201而張庚先生卻認為“戲曲是詩的高級階段”,“是一種新體詩”,并將之作為其“劇詩”理論的核心觀點之一,二者藝術觀點差異折射出的是二者思維理念的不同。[13]2、3格羅遂以為,從人類“不以口說事跡為滿足”而“還要靠適當的聲調和姿勢”“來輔助他所說的言辭”開始,戲劇便已誕生。[5]202張庚先生也曾多次引用《毛詩序》“詩言志,歌永言。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記載。[14]370戲劇元素的原始因子正悸萌于古人渴望表達時的模仿、表演本能,二者此段所論何止類似相仿,簡直如出一轍。但格羅遂選擇了止步于此、刻舟求劍,而張庚先生卻選擇了動態考察、歷史看待,對格羅遂的理論作出了有益補充與合理修正。他從“詩言志”而深入到中國詩的抒情傳統,將戲劇的誕生與戲曲的形成分別審視,認為從前者到后者實現了從“九九表”到“高等數學的問題”之演變。[9]168張庚先生不滿足于只把戲曲看作是“史前時期的東西”,他更飽含著文化自信地指出“真正的戲曲的歷史還是在將來”,呈現出了用唯物辯證法的發展觀點看問題,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超長歷史刻度中審視戲劇藝術的鮮明特色。[6]84
二、如何研究藝術、戲劇?
格羅遂的藝術理論山系由“藝術史”與“藝術哲學”雙峰并峙,二者既相互勾連又彼此獨立。一作為“記述部門”“考究各個特質的實際情形”,一作為“解釋部門”“把它們來歸成一般的法則”,史與論兩個部門“互相依賴,互相聯系”,“藝術史和藝術哲學合起來,就成為現在的所謂藝術科學”。[5]1-2張庚先生的戲劇理論構建與格羅遂的藝術理論構建高度相似。在他看來,沒有系統的史論建設是不可能真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15]214為此,他提出要搞收集資料、編輯志書、寫就歷史、研究理論、從事批評的多維藝術體系建設,從而把史與論有機結合、高度統一。[3]330-341在他看來,雖然“史、論單純從內涵、外延來看差別很大,似乎是學術研究領域兩門截然不同的學問”,史之研究旨在認識它為什么是這樣的,論之研究旨在找到它的規律性的東西,但“社會發展到現代”,“界限有所打開,治學方法有所模糊”,不妨“試著開始史論結合的探索工作”。[16]424基于張庚先生以上高遠見地,“前海學派”形成了極具啟發與借鑒意義的中國化藝術研究模式。
張庚先生與“前海學派”在史論建設方面身體力行,有許多卓有成就的著述。先生《戲劇概論》《戲劇藝術引論》《戲曲藝術論》等個人著作,均能做到對史信手拈來,《戲劇藝術引論》在論述各種藝術在戲劇中的綜合時,就部分引用了《藝術的起源》中關于原始民族的情況。[2]63-66張庚、郭漢城二位先生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與《中國戲曲通論》分別主要對藝術史、藝術哲學進行深入探討,但內容并不拘泥書名,常常互相深研對方。《通史》能以史帶論,如介紹關漢卿時,大量篇幅用于論述“本色”“當行”的北雜劇語言特色,借關漢卿劇作闡發了劇作語言應自然、真切、質樸及能夠刻畫人物的觀點。[17]141-144《通論》能論從史出,開篇論自成體系的中國戲曲,先由印度梵劇歷史回顧引入,在中、印兩國對比中突出了中國戲曲的特殊道路。[8]2-5在張庚先生直接、間接影響下,中國藝術研究院曲藝學科之《中國曲藝通史》《中國曲藝通論》,舞蹈學科之《中國舞蹈通史》《舞蹈藝術概論》,影視學科之《中國電影史》《電影學論稿》等學科成果,均呈現出了鮮明的史、論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特色。
格羅遂的藝術哲學包涵“那些通常稱為藝術評論而不稱為哲學的研究”,張庚先生與“前海學派”也素來將理論與批評相互聯結。[5]3不過,格羅遂對于藝術評論似乎頗有微詞,以為它“標榜”出“那樣十全十美的儼乎其然的樣子”,“想蒙上科學的獅子皮”來“遮住了自己的狐貍尾巴”。[5]3-4張庚先生卻以為“在文藝里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評論,如果一個人能把評論寫好,寫出的評論被創作藝術的人承認,那你就是把藝術理論真正搞通了”,為此他還寫了多篇文章強調評論的作用與要求評論的質量。[3]339格羅遂對于藝術評論的批評,完全建立在他以為藝術評論“那些意見和定理”缺乏“客觀的科學的研究和觀察做基礎”而只是“以飄忽無定的、主觀的、在根據上同純科學的要素完全異趣的想象做基礎”的片面看法之上。[5]3而張庚先生與“前海學派”、兄弟院所卻在藝術評論之前,用唯物辯證法的聯系觀點看問題,通過資料、志、史、論的前期鋪墊建立起了整套、完善的藝術研究體系,形成了諸多具有開拓性意義的理論與實踐標準。以理論而言,張庚先生關于“劇詩”“物感”“神似”等有益探討越來越得到戲劇研究者的認可。以實踐而言,張庚先生對戲曲調查的重視在當代得到了越來越多回響,戲曲人類學、戲曲社會學正在蓬勃生發。有此理論、實踐雙重保障,“前海學派”的藝術評論方才真正做到了言之有物、言出必響。
三、如何應用藝術、戲劇?
格羅遂通過對原始藝術進行田野考察與理論分析,認為原始藝術除了它直接的審美意義外,對于狩獵民族也有一種實際的重要性,原始藝術之最高的社會職能是統一,它可以充實并提高我們的感情生活,他還進一步指出,雖然“我們的確有權利要求藝術去致力于社會功效的方面”,“但是我們倘使要求藝術成為道德的,或者正確一點說,成為道德化的,那我們就不對了”。[5]239、240在格羅遂看來,藝術本來就具有實用主義色彩,但必須最大化確保它的藝術性,才能最大化實現它的社會性。張庚先生同樣深切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將“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改成“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意義重大,因為從過去的戰爭時代轉入經濟建設階段,文藝的任務重點也要從全民總動員狀態下的隨著政治號召走轉向對人民的心靈起潛移默化作用。[18]363在他看來,全民總動員狀態下的延安戲劇改革能取得一定成功,正在于藝術家們開始摸索到了一點戲曲規律的門徑,經濟建設階段的“樣板戲”沒有生命力,正在于其“高大全”“三突出”的政治教條違背了“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的藝術原則。[18]360-363
從延安時期到新世紀,張庚先生一直走在讓戲曲實現現代化進而服務社會與民眾的改革道路上。擔任魯藝戲劇系主任時,他參與了新秧歌運動與平劇改革,新中國成立后,他又與田漢等人共同領導了“改人、改戲、改制”的戲曲改革運動。張庚先生與中國戲曲研究院的同僚們通過開辦演員講習會、召開劇目討論會、開展調查研究與教育教學等工作,很好配合了彼時的戲曲實踐發展需要。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他提出了“舊劇現代化”的重要命題,認為要以創造“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戲曲”作為改革目標,“把傳統的文化和社會主義聯系起來,使之適應社會主義”,使戲曲“能為社會主義服務”與“表現社會主義的新生活”。[19]28在張庚先生等一批先行者的領導和影響下,新中國的傳統戲曲整理在“推陳出新”中實現了淬煉升華,新編歷史劇創作在“古為今用”中孕育了累累碩果,現代戲發展更是質、量雙收,涌現出了一大批為群眾喜聞樂見,兼具社會與藝術雙重功用的精品佳作。今天戲曲研究領域對“現代戲”“現代性”“現代戲曲”等議題不絕如縷的討論,仍可看作是張庚先生“舊劇現代化”理論的回響。
格羅遂認為,藝術科學(藝術史與藝術哲學)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應用而是為了支配藝術生命和發展的法則的知識”,這一點與張庚先生的主張無疑存在著較大的分歧。[5]5郭漢城先生說,張庚先生“寫了大量戲曲理論方面的文章,對指導戲曲改革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理論聯系實際”是以張庚先生為代表的所謂“前海學派”的第一個特點。[15]212-213漢城先生進一步解釋稱,所謂“理論聯系實際”,“從狹義方面看,它密切聯系戲曲歷史、戲曲實際”,而“從比較廣義的方面看,就是聯系我們的時代,聯系我們的國家”,[15]213并稱“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研究方法”是他與張庚先生“實現戲曲現代化”與“戲曲為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共同目標”的學術合作基礎。[20]73在格羅遂那里,理論只是純粹的知識探索,不僅經常會被“形式和關系的內在的本質問題”和“藝術歷史的過程中所顯現的動力問題”質問而“不能答復”,還與自己藝術(藝術科學當然也屬于藝術一部分)具有社會功效的判斷相背離,其設想固然不失為一種美好的期待,但實際上往往曲高和寡、難以達成。[5]6在實踐這一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首要基本觀點指導下,張庚先生與“前海學派”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理論研究有了更強的指向性,工作實踐有了更強的方向性,有的放矢,對癥下藥,互利共贏,成果豐碩,有效實現了他們文藝為人民和為社會服務的初衷。
余 論
一位理論家的學術淵源和成長動因固然是多種多樣的,但憑借張庚先生本人對格羅遂跨越幾十年的的推崇,我們依舊有理由相信格羅遂的見解確乎對他多少曾有一定啟發。張庚先生曾批評有的人“沒有真正完全把外國的東西學懂”而“到處抄些東西湊成一篇來唬我們”,他對格羅遂的研究卻絕非如此。[3]331在如何看待藝術、戲劇上,張庚先生與格羅遂均主張回到歷史原點審視藝術,但張庚先生能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區別對待戲劇不同發展階段。在如何研究藝術、戲劇上,張庚先生與格羅遂均主張史論并重,但張庚先生能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把資料、志、史、論與批評相關系。在如何應用藝術、戲劇上,張庚先生與格羅遂均主張通過發揮藝術審美性來實現藝術社會性,但張庚先生能用實踐的觀點看問題,主張把藝術理論與藝術實踐相結合。通過以上三方面異同比較能夠看出,張庚先生對格羅遂高度重視卻并不盲從,融合各家、結合實際地對其觀點做了揚棄式、中國化處理,形成了自己既具有理論說服力,又具有現實操作性的藝術主張。由此啟發我們,一方面我們需要保持對國外藝術學相關理論的求知欲與敏感度,用豐富的閱讀開拓視野與增強能力,內化于心,為己所用。另一方面,我們要辨別良莠、分清是非,善于使用發展、聯系、實踐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應對和處理紛繁復雜的多樣學說。唯有如此,我們方能真正貫徹“‘二為’方向、‘雙百’方針、推陳出新、古為中用、洋為中用這一整套方針政策”來對待、處理我們的民族文化遺產。[15]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