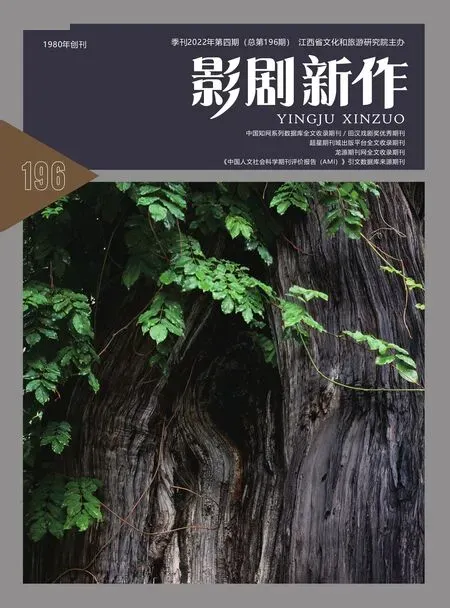非線性時間與疏離空間下的遺忘與共情
——評《困在時間里的父親》
童一凡
“我感覺我的葉子好像要掉光了。”這是罹患阿茲海默癥的安東尼在混亂的時空、衰老的生命里無助的自白。當生命的嚴寒襲來,面對至親的離去、記憶的撕裂、死亡的恐懼時——困在時間里的人們又該何去何從?電影《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以患有阿爾茲海默癥的安東尼為全片的主要敘事視?,為我們展現了一個混沌、迷茫而又令人心碎的世界。影片的敘事把情節安排得如同迷宮般交互切換,使得現實與臆想交錯并行,建構了獨具一格的影像時空。
一、無序的時空:拼湊與重塑
時間和空間是電影藝術構造文本的依憑,一個優秀的導演總是能夠出人意料地在時間和空間的雙重維度中,將一個真切的故事以一種全然陌生化的方式講述出來。電影的時間敘事通常指的是,把時間(及其對時間的操控)作為電影敘事和表達的主要手段。[1]時間作為一種敘事手法時,意味著線性或非線性時間的縮放、畸變、折疊、復原進入了電影的敘事和表達的每一個過程;而空間敘事則意味著電影通過對于空間的使用來組織和敘述整個故事,即“一是導演對空間的選擇、表現和組合等工作;二是指電影敘事空間本身的敘事性以及敘事空間的選擇和處理對故事中的人物、情節與敘事結構等的影響或制約”。[2]《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中充分使用了時間和空間的雙重敘述方式,用拼湊和重塑的方式,再造了一個無序的時空,安東尼置身于這個時空中,便如同被困于永恒困境之中。
《困在時間里的父親》本來是佛羅萊恩·澤勒自編自導的舞臺劇,在從舞臺藝術到電影藝術的媒介轉換過程中,導演佛羅萊恩·澤勒對視?進行了巧妙的設計與安排,采取了特殊的時空構造方法。電影以一種含混而令人迷醉的方式講述了日漸蒼老而又不幸身患阿爾茨海默病的安東尼在記憶與妄想的雙重糾纏下,開始懷疑他所愛之人、他的信念、他的存在,甚至現實的故事。導演從安東尼的主觀視點出發進行敘事,使得整部影片中所有的影像存在都帶上了老人所特有的主觀色彩,呈現出一種極不可靠的印象主義破碎感。在這種強烈的個人化綱領下,進行了空間感與時間感的營造。
在空間?度上,導演通過對安東尼的公寓、安妮的公寓、醫院、養老院等地點的組合和選擇,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空間狀態。在這個失衡、混亂、破碎的空間中,隨時切換、變化,使得觀眾在觀影中會產生對于影像世界認知的無序感——觀眾的這種心理與阿爾茲海默癥患者間的內心失序,跨越了屏幕,形成了一種同構關系。此外,導演對于空間的使用不僅停留在直觀的感官層面——使習慣于生活中穩定空間的觀眾感受阿茲海默病人混亂的空間,進而基于人類相似的心理結構產生共情;空間還在這里承擔了重要的敘事功能,需要在情節的推進和觀眾的思考下緩緩呈現與還原。這些不同的空間呈現出了高度相似的布局、陳設,導演有意識地混淆故事發生的不同場景,但在這些場景之中,導演穿插了暗示故事發展和人物心理狀態的大量線索。譬如,在以藍色為基調的養老院中,安東尼房間的構造與兩處公寓房間是幾乎相同的——鏡子,衣柜,窗戶,床等家具的位置,這一空間構造便暗示了安東尼將養老院這一空間在記憶中與曾經居住過的公寓進行相似部分的疊加重組;除此之外還有懸掛在墻壁上的小女兒畫作,鋼琴,壁爐,黃色和藍色的塑料椅子等等線索,每個線索都隱喻著影像世界里正在發生的空間的拼湊與重塑。這種構造空間的方法,不僅讓觀眾被卷入迷亂的敘事中,迷失在安東尼的碎片記憶之海里,更能夠以不同空間里的他人視?(女兒安妮、養老院的客觀視?)來最終還原真相,讓作為觀者的觀眾得以逾越虛幻與真實的鴻溝,梳理出故事本來的樣貌。
觀看《困在時間里的父親》,是一場觀眾跟隨主人公的視?,接受著看似合理但時序拼接錯亂畫面的奇妙之旅。導演時間重塑的敘事手法在護工勞拉來訪、安東尼與女兒女婿共進晚餐的那一天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這一天里,不同于普通人默認的“早 - 中 - 晚”時間發展的規律線性,影片為我們展現的是“早 - 晚 - 下午 - 晚”的被重組的非線性時間。電影拍攝安東尼早上見到護工勞拉,緊接著的便是晚餐前安妮向丈夫說明父親病情嚴重的情節,安東尼與女婿進行了不愉快的對話之后,下午安東尼外出前往醫院看病,隨之而來的是晚餐間隙,安東尼聽到女兒和女婿關于養老院的爭執。這樣巧妙的時間顛倒完成了一個敘事上的詭計,讓觀眾和安東尼腦海中認為的相一致——安妮妥協于丈夫的要求,送父親去了養老院;而直到影片最后的敘述,我們才知道故事的真相。
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在患病的安東尼眼中,這都是真實的;然而對于觀眾來說,觀眾可以有意識地感受到這是導演有意地對現實進行扭曲,拼接與重構后展現的景象。屏幕內,安東尼置于困境;屏幕外,觀眾努力獲得失序里的真實。時間與空間的重構同等地對劇中人和劇外人發生作用,而這種神奇的體驗,最終將會指向水落石出之后眾人的驚奇與感動。
二、豐富的意象:受困與遺忘
除了精心打造的亂序場景,電影中的諸多意象,以不同的方式賦予了影片更為深刻的意義和直擊靈魂的穿透力。在概念表述的層面上,影片選擇了“手表”“家”等意象,來表現阿爾茲海默病人安東尼身上的永恒困境。在具體的視聽語言層面上,影片精心設計了具有豐富意蘊的音樂,進行對情節的暗示與情感的抒發。
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指出:“要更好地理解一部電影的傾向如何,最好先理解該影片是如何表現其傾向的。”《困在時間里的父親》中展現“影片的傾向”的方式便是使用物象。例如,影片的主要線索是“困在時間中”,而時間這一意象最直觀的表達就是手表的使用。一開始是父女對話引入“懷疑護工偷拿手表”這一猜測,以致于到了父親、女兒、女婿的三人晚餐前場景,父親與女婿的矛盾日益凸顯:父親懷疑女婿的手表是自己的。而在“女兒找到父親的手表”這一情節發生之后,這些敏感、猜疑、囈語被證實為是安東尼記憶缺失、心靈錯亂的表征,對于“手表”這一物象的反復尋求意味著安東尼對于時間的遺忘和內心的孤獨。影片的末尾,身處養老院中的安東尼沒能找到手表,表明他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時間的掌控,被徹底困于時間之中。“手表”不僅串聯起了情節,成為了人物沖突的線索,更肩負了隱喻和象征的作用,手表的丟失、尋找、徹底消失正對應著安東尼晚年時期記憶和自我的丟失、尋找、徹底消失。
“房間”與“公寓”同樣是一組重要的意象,暗示了本片的母題之一“家庭”。它充分地展現了外在空間的遼闊、時間的變動與人物內心的孤獨。銘記的終會被遺忘,遺忘的幻影般再度出現,使得電影蒙上一層超現實主義色彩。
影片大量拍攝了客廳、廚房、走廊等空間感極強的場景,還常常使用空鏡頭來捕捉公寓內飾細節的調整,進而營造時間上的錯亂感。很多鏡頭的內容都在講述安東尼的狀態,即:在明亮與幽暗交織的房間里,孤獨的安東尼徘徊著、踟躕著、尋找著,無助又彷徨,原本處處熟悉的家庭在老去的安東尼的視?下變得陌生且詭異,錯亂的空間、非線性的時間,使得不論是劇中的安東尼還是觀影的觀眾,都無法確定,在原本為“家”的公寓里行走時,沿著走廊、推開那扇門,出現的會是無助呼喊的小女兒露西?還是平淡無奇的雜物間?這種陌生化的“家”是影片講述的“家”這一意象的表層,暗示、渲染了壓抑的情緒。而在第二層,“家”這個概念參與了敘事,并且不斷變化:安東尼在女婿家里被驅逐時,我們會對“家”的概念產生質疑;在安東尼身處療養院時,“家”在他心里已然變成了一種遙遠和無法抵達的狀態。在故事的推進過程中,安東尼由尋找家園,到被家園拋棄,最終永遠無法返回家園。他不存在于家中,他的真實的生活空間只在一個被幻象扭曲了的、衰老的心里,安東尼的悲劇性正在于此。影片意象的選用參與了敘事和抒情的進程之中,成為推動情節發展所不可或缺的脈絡,也成為人物狀態、心理、命運的外化,在影片中與主題相互應和。
“人的視覺會受到影像呈現形式的限定,而電影聲音作為觀眾感知電影世界的本體存在,則是一種無形的物質現實呈現形式。”[3]除去“手表”“家”意象的使用,影片還成功地選用了大量的具有豐富意蘊的音樂。音樂同樣成為了理解電影的一把鑰匙,音樂本身的使用在片子里成為了一種意象。如片頭的古典音樂,便來自于普賽爾《亞瑟王》的選段《冷之歌》,是掌管嚴寒的精靈被丘比特喚醒后唱的一首詠嘆調,象征了“冬”和“冷”的意象。空靈縹緲的長段音樂一開始就為電影增添了幾分厚重感,步履匆匆的女兒,戴著耳機白發蒼蒼的父親,內飾華麗的公寓,故事的大幕拉開,音樂戛然而止,而屬于父親和女兒的寒冬,才剛剛開始。在影片接近尾聲,女兒走出養老院的大門,她背后矗立著破碎的面具雕像,配合比才的歌劇《采珠人》的詠嘆調之《她在花叢中》—“我仿佛聽見她的聲音”,于美夢里最熟悉不過的場景。這里音樂的使用象征了“夢”和“幻”的意象,無限飄渺夢幻,無限孤獨寂寥。
三、深刻的共情:凋零與落幕
“電影中的大部分重要內容本質上都與情緒有關,對于敘事藝術而言,情緒居于中心地位。”[4]這是普蘭丁格所秉持的觀點。一部優秀的電影能夠帶來巨大的感染力,其通過塑造?色、講述事件所引導、形成的情緒會觸發廣泛的觀眾的情緒,從而指向人類內心最深層的情感。
在觀看《困在時間里的父親》的過程中,我們透過迷亂的時空、變換的意象、抒情的音樂,進入了安東尼的精神世界。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杰斯將共情定義為“個體體驗他人的精神世界,如同體驗自己的精神世界一樣的能力。”可以說,整部電影中處處蘊含著安東尼的個人感受,從每一個鏡頭、每一處配樂中,我們都能夠身臨其境地感受安東尼晚年的精神圖景。例如,導演多次拍攝了安東尼的窗戶——透過這扇窗戶,我們見證了安妮的離去、孩童的玩樂、郁郁蔥蔥的樹木年年歲歲、枯榮相生。這些畫面里,我們能夠切切實實地感受到安東尼面對安妮的離開,心中無限的傷心和不舍;面對充滿活力的孩童,他又懷有一種對于旺盛生命力的強烈羨慕之情;在安東尼感覺自己的生命力如同像樹葉一樣掉光了的時候,我們也同樣能夠體會到晚景降至、不知道還能看多久窗外世界的無限悲哀——“我的葉子好像要掉光了......風雨裹挾著我的枝葉,我已經搞不明白發生的一切,你知道發生了什么嗎......我再也沒有棲身之處了。”
患上阿爾茲海默癥對于一個老人來說就像是來到另一維度的時空,在這個時空里,患者把自己與原本熟悉的生活與人割裂開來,在虛幻的破碎中,只有生命的流逝最為真實。子女離開、家庭消逝、自我消逝,我們目擊了一位老人的瀕臨死亡;而《困在時間里的父親》恰恰把這種個體從外至內的緩慢的死亡過程刻畫地細致入微。安妮的贍養困境、進入養老院中的情節是安東尼外在部分的逐漸死亡——無法養活自己,無法獲取和社會的連接,無法獲得生命的主體性,無法回到自己的家園之中,被永恒放逐;影片中多次出現的安東尼自我否定的細節則暗示著安東尼內在的死去,即人自我認同的錯亂乃至消逝。安東尼的職業是工程師,但是在罹患阿茲海默癥之后,卻不斷否定著自己的身份,堅持自己是一位在馬戲團工作的踢踏舞者;他最常飲用的飲料是咖啡,然而卻不斷抗拒這個說法,堅稱自己愛喝茶水。當自我的認知混亂,一個人便徹底地處于了無助之中,走向不可逆轉的在世間的消逝——這種消逝的最后,安東尼徹底忘記了自己是誰,只記得自己的名字是媽媽取的;他想要媽媽帶他回家,帶他離開這里;溫柔的護工凱瑟琳安慰像嬰兒一樣無助痛哭的他……生命的循環終將回到原點,陽光、空氣和水對于一個人來說都變得毫無意義,就如同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的前一刻,離去永不止息地來臨。在《困在時間里的父親》帶領觀眾走完的這段旅程里,我們看到了安東尼自我的凋零與落幕,他的慟哭與悲鳴也是我們的慟哭與悲鳴。安東尼的嘆息何嘗不是每一個觀眾,無論年齡、性別、地域、種族、國家,面對人類所無法避免的死亡的嘆息!
安東尼呆在養老院中,回溯著錯亂的過去,看不到任何可能的未來。他活在自己的時間里,而真實的時間又決不為他停留片刻,于是只能走向必然的消逝。我們為這樣的故事而惋惜悲痛,在阿爾茲海默式錯亂的敘事中,我們仿佛也是同樣的病人,在風燭殘年坐在養老院的房間,默默地守護著殘缺的記憶。在影片放映的每一刻里,我們都感受著生命的凋落,共情著生命消逝下人的孤獨。
四、結語
《困在時間里的父親》嘗試了對于電影敘事空間的拓展。它采用了非線性的時間來參與敘述,同時以空間敘事的方式,把人們日常所習慣的穩定空間進行扭曲和再造。此外,《困在時間里的父親》設置了大量的意象與細節,為觀眾提供了沉浸式的觀影體驗,使得觀眾深切地共情安東尼的命運。
一部電影最閃閃發光的,不僅是精彩的故事呈現,不僅是多樣的敘述方式,不僅是充滿延伸意義的象征符號,更是那在看似平靜的湖面上擲出的圈圈漣漪——真正情感內核的浮現。我們期待著更多具有人文關懷的電影的出現,也由衷希望除了對藝術作品的共情外,加速老齡化的社會對于阿爾茲海默癥患者及其家庭的更多關注,能減少哪怕一丁點遺忘帶來的痛苦,能夠讓每一個人帶著歡欣降臨、伴隨著尊嚴與親情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