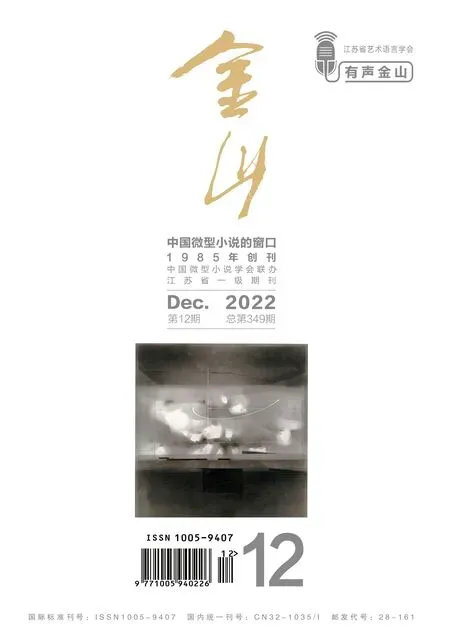人物與細節:寫食譜其實是寫人物(點評)
——點評張大愚食譜系列微型小說
浙江/謝志強
《九轉大腸》這一篇寫得很成功,是一篇好小說。“九轉大腸”這個題目——或者說以這個菜譜名作題目——是有意味的。主人公老甄做九轉大腸,追求外表光鮮,這是性格使然。因此也引出了他獨特的婚姻。九轉大腸,可引申為回腸九轉,暗指老甄婚姻的不順利不如意,事實上他的婚姻是很糾結的(準確地講,還算不上真正的婚姻,不過是為了顏面自導自演,做一場交易罷了)。這一點上,兩者暗合。結尾處,老甄告訴“我”做九轉大腸這個菜的訣竅時,嘴里蹦出“砂仁”兩個字,諧音“殺人”,這個細節很巧妙,有代入感,讓讀者讀了心頭震了那么一下子。
另外,文中取的名字也很含意,比如說老甄和老賈,老甄做菜注重表面,老“真”(甄)其實不一定真;而老賈做菜卻追求味道,老“假”(賈)倒未必假,其中很有諷刺意味。結尾寫“我”按老甄所傳授的“訣竅”做出九轉大腸,外表的樣子很像了,那味道怎樣呢?到底正不正宗?沒有完全交代出來,這成了“我”的疑惑,也是讀者的疑問。由此就引發出思考,有余味。這個留白是要得的。
《布袋全雞》這一篇,“布袋”這個物件,或者說這個細節,運用得很妙。布袋雞塞得太滿烹制時就會爆裂,這句話很有內涵,就像小小說,不要塞得東西太多,要留有余地。
本文敘事也有特色,巧妙而自然。先寫主人公老譚的肚子(這個不怕燙的胃,可理解為一個大布袋),由肚子(大布袋)引出布袋雞這個“小布袋”,此段末尾,寥寥一筆,又帶出老譚的家庭情況,由此又寫出老譚為什么貪吃。筆很順,自然妥當。另外,整篇作品當中,“布袋”是一個核心細節,大肚子,布袋雞,帆布包,都可以理解為“布袋”,三者很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講,它們都是相通的,都統一到老譚這個人物身上了。看似漫不經心的敘述,一步一步地寫,到最后都聚攏到一起了。
特別是最后的情節(細節),老譚因為吃了太多撒在地上的東西,引發病癥,從而不得不做了胃切除。但出院后第一個念頭,就是想吃自己做的布袋全雞,可惜卻只能看不能吃了。于是摸著自己的肚子感慨:“唉,袋子破了,袋子小了。”這些處理都很好,和主題扣合得很好。給主人公起名“老譚”,我想是經過考慮設計的,老“譚”不就是老“貪”嘛。
《太白鴨子》這一篇,主人公董哥揣著錢睡覺的細節很好,很巧妙。還有“沒吃過太白鴨子,那些冠軍明星能飛得起來嗎?”一句寫得也好,把董哥的心態刻畫出來了。結尾處,董哥親手做了一只太白鴨,看著兒子吃,兒子撕下個翅膀遞過來,但董哥搖搖頭,齜齜牙,突然讓兒子叫他一聲爸爸。兒子叫了一聲爸爸,董哥響亮地應了一聲,說,吃吧。然后看著兒子吃鴨翅膀。這段描寫很出彩,寫出董哥與兒子關系(不是親生兒子)的同時,也把董哥的心態寫出來了。讀者也感覺很溫暖。
我喜歡張大愚這一路扎實的寫作,他設計的這種系列寫作方式(前面帶個菜譜,后面講個故事)很新穎,很別致,緊扣細節,寫出人物關系,塑造出人物形象,從而形成一種緊密的邏輯關系,這一點很難得。
這幾篇作品總的特點是扎實、幽默,還很空靈——好的小小說就應該空靈。乍一看小說本身似乎比較“實”,但加上前面的菜譜,就形成一種映照,一下子產生出空靈的效果,有意味了,可以“多解”。讀者對照菜譜,會讀出另一番意思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