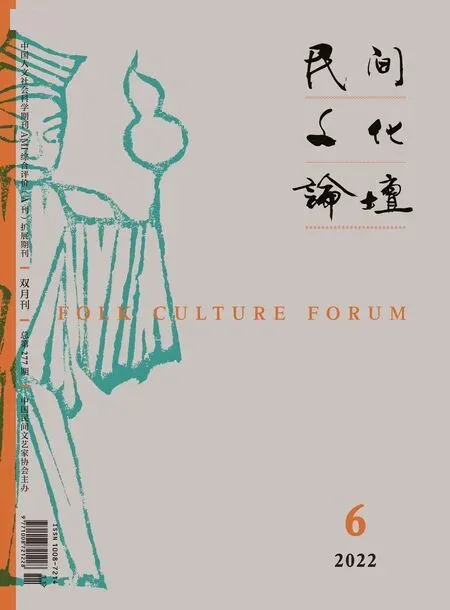商品、游藝與人流
—— 北京丫髻山廟市的商業地景
鄧 苗
引 言:神圣之路上的眾聲喧嘩
交換在鄉村生活和民眾交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種交換有時是通過固定地點周期性的以商品的流通為主要內容的集市買賣,有時是通過融合了包括敬拜、娛樂、商品交易等內涵在內的廟會。廟會作為一種疊合了多種需求與功能在內的文化現象,既與地方社會的經濟關系聯結在一起,同時又與鄉村民眾的信仰需要結合在一起。廟市以其特有的附著性、獨立性和神圣性①小田:《廟市特征小議》,《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1期。,不但擔負著一般的經濟交換的功能,也承擔著為信仰需要的交換提供物質依托的功能。
廟會的商業屬性歷來受到人們的高度關注。早在民國時期,著名經濟史研究學者全漢昇就發表了對于廟市發展歷史的考察②全漢昇:《中國廟市之史的考察》,《食貨》,1934年第2期。,此后,施堅雅探討以四川為中心的中國地方社會的空間體系的過程中,提出包括廟會在內的社會體系是整個市場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人們圍繞廟會形成了一個與基層市場體系相疊合的信仰圈。③[美]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與社會結構》,史建云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48—49頁。趙世瑜詳細考察了明清時期城市廟會和鄉村廟會在商業貿易上的差異,他發現城市廟會商品以日用百貨為多,而鄉村廟會則以生產生活必需品為多,實用性較強;同時,城市廟會擔當著向鄉村提供貨源的作用。除此之外,通邑大都的廟會文化娛樂色彩較濃,而鄉村小鎮的廟會則商業貿易色彩更重。④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第171—175,198—204頁。
從物質性的商品買賣到精神性的宮觀敬拜實踐,廟市從單純的商品交易之地進入各種聲音共同激蕩的聲音之所。盡管不同的論者對于廟市、廟會和集市這三個概念之間是否有差異以及差異的程度具有不同的理解①包括全漢昇、1979年版《辭海》編者、北平民國學院王宜昌先生等論者將集市、廟市和廟會三個概念所指代的現象歸為一類,或者說認為這三個概念是一種社會現象,而更多的包括施堅雅、楊慶堃、楊懋春等論者在內的學者則將集市與廟會區分開來。見岳永逸:《精神性存在的讓渡:舊京的廟會與廟市》,《民俗研究》,2017年第2期。,但不論怎樣,這三個概念都代表著一種群體的目的性聚合,或者是以經濟為目的的交易聚合或者是以信仰為目的的敬拜聚合。從以商品買賣為主的廟市景觀到宮觀中以求神拜神、許愿還愿為主的信仰之場,來自不同地方的人們,以不同的目的在廟會期間聚集到了廟宇所在的地區。個體性的私人經濟、私人信仰與廟宇所在的地域社會聯系起來。雖然位于山下的廟市和身處山上的敬拜實踐是一體兩面、互相聯系的一個整體,但是在這兩個場所,人們發出的聲音是不同的。山下的廟市中的聲音是以商品和服務的買賣為媒介,人們在交易的過程中發出自己求財、求樂、求新和求異的聲音,現實的嘈雜聲和人們實現自己價值訴求的聲音交合在一起。而地方政府作為廟會活動主辦者,他們也通過這種眾聲喧嘩、人潮洶涌的消費、玩樂實現了自己所追求的發展旅游業、擴大地方特產銷售、擴大就業、擴大農民增收渠道、擴大地域文化影響力的訴求。②劉鐵梁主編:《中國民俗文化志·北京·平谷區卷》,北京: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65—66,83—85頁。廟市中的商品種類,相當一部分是日常生活并不多見的非生活必需品,這些商品是在廟會這樣一個特殊的時空領域獨有的。
如果說山下的以商品銷售為主要內容的廟市更多聚集在經濟的一面,那么,山上的敬拜實踐則更多的是信仰的一面,在這個場域中,一方面每一個香客都有自己的信仰訴求,通過直接的敬拜實踐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另一方面,大家又通過一些共同、共享、合作的行為,例如相似的敬拜、求神許愿、組織花會、整修宮觀等行為,發出統一的聲音,希望廟會的神靈對于國家、民眾有一個整體上的護佑。對于這種聲音,趙世瑜和劉曉春更多的是從其文化內涵來探討,聚焦于這類聲音的文化本質或特點——狂歡性③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第98—119頁。與非狂歡性④劉曉春:《非狂歡的廟會》,《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岳永逸認為,廟市和廟會之間并非沒有貫通的可能性,近現代以來中國廟會的發展特點之一恰恰在于“廟會的廟市化”⑤岳永逸:《精神性存在的讓渡:舊京的廟會與廟市》,《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但是問題在于,廟會和廟市之間這種信仰性和經濟性的分野是否那樣差異分明?恰如前述,廟市總是依托于一定的廟會,廟市的發展與廟會息息相關,因此,山上和山下的聲音實際上在一個更深的層次上互相交織在一起。在一系列論文中,岳永逸關注到廟市和廟會之間的差異,并且特別注意到國家/政府對于當代鄉村廟會,尤其是具有較大影響力的鄉村廟會所施加的影響,使得當代廟會發生了一種“圣山景區化”和“景區圣山化”的變化。⑥岳永逸:《民族國家、承包制與香火經濟:景區化圣山廟會的政治—經濟學》,《中國鄉村研究》,2016年。
從廟市到廟會,包括民眾自身、地方政府、民間精英、體制精英(包括文化方面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都在其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作為一種公共文化,每一個有自己價值訴求的社會主體都能夠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從而參與到對于丫髻山廟市和廟會的建構當中。這實際上也就是一種文化的共謀。
一、從幕后到臺前:丫髻山廟市的發生史
丫髻山位于北京市東北部的平谷區劉家店鎮境內,原屬懷柔區管轄,1946年,由于行政區劃調整,隨所在地原劉家店鎮劉家店村一并劃歸平谷縣。丫髻山既是京東一處著名的風景名勝區,景色秀美,風光旖旎,又是一處以碧霞元君信仰聞名于華北的著名道教圣山,每年農歷四月初一到四月十八舉行廟會,是北京地區與妙峰山齊名的“(五頂)二山”之一①徐天基:《明清時期北京丫髻山的進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14年第10期。。
丫髻山宮觀及其信仰體系始于元代,興盛于明清,為華北地區四大廟會之一②王新蕊:《元明以來北京丫髻山道觀文化的歷史考察》,《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目前有關丫髻山宮觀的實物資料,最早的是近年出土的“敕賜護國天仙宮匾額”,該牌匾為明朝嘉靖皇帝所賜。這說明最晚在明朝嘉靖年間,丫髻山的碧霞元君信仰就已經得到了官府的認可和褒獎,且當時廟會的規模已經十分宏大。
在文獻記載方面,目前所見相對較早的是明朝萬歷年間的《懷柔縣志》,該書記載:“丫髻山,在縣東九十里,……上有天仙圣母宮,靈應如響,四方之人,于每歲四月十八日大會五日致祈云。”③周仲士纂:《懷柔縣志》,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刻三十四年(1608)增刻本。可見,最晚在萬歷年間,丫髻山已經成為當地一個民間信仰的中心,且舉行長達五天的廟會。雖然有廟會并不一定就會有銷售包括香裱紙錢等各種祭祀用品在內的商業市場存在,但是,這種以供應香客進香為目的的祭祀用品的買賣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而且就長達五天的會期來說,廟會規模必然很大,人流量也必然很多,因此,我們可以推斷,丫髻山碧霞元君祠的廟市很可能早在明朝萬歷年間以前就已經存在了。
這段時期,丫髻山廟會雖然受到官方的注意,并得到褒獎,但是其香火主要還是來自于民間。④徐天基:《北京丫髻山的進香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4期,2014年6月。對此,康熙《懷柔縣志》對于丫髻山王奶奶發愿修殿的記載可以略觀一二。明代廣泛流行的《靈應泰山娘娘寶卷》將丫髻山列為泰山娘娘的行宮之“北頂”,說明丫髻山在北方碧霞元君信仰中的重要性。
清代,有關丫髻山廟會的資料開始翔實起來,各種碑文、志書層出不窮。這一時期最早的資料為康熙三十五年(1696)京都地安門白米斜街的三頂崇善老會所立的《丫髻山進香碑記》和來自北京東城鄭村口北馬房的《新建丫髻山圣母娘娘行宮普義門勒碑序》。這些碑文記載了當時北京民間進香組織的朝頂活動。⑤同上。
丫髻山進香的高潮應該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康熙駕臨和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萬壽道場在丫髻山的舉行。皇家壽誕在丫髻山舉行,使丫髻山廟會的規模達到了頂點。此后,一直到道光年間,丫髻山宮觀建筑群不斷得到重修和擴展。這些來自官方的褒獎和支持,促進了丫髻山廟會規模的擴大和影響力向周邊地區的擴張。
對于雍正、乾隆時期丫髻山的繁盛狀況,潘榮陛的《帝京歲時紀勝》做了詳細的描述:“京師香會之勝,惟碧霞元君為最。……又有涿州北關、懷柔縣之丫髻山,俱為行宮祠祀。圣祖御題丫髻山天仙殿匾曰敷錫廣生,玉帝殿匾曰清虛真宰。每歲之四月朔至十八日,為元君誕辰。男女奔趨,香會絡繹,素稱最勝。”⑥潘榮陛、富察敦崇:《帝京歲時紀勝 燕京歲時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19頁。
清乾隆時期,隨著香稅的廢除,丫髻山廟會有組織的進香團體更加發達,香會的組織結構更加完善,分工明確、各司其職,這說明當時的進香活動規模相比以前更加盛大,因為這種結構完整的民間香會組織一定是來源于進香中復雜事務的實際需要,是進香活動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這個時期的丫髻山廟會,不但有乾隆皇帝的親自駕臨和賞賜,也有內務府的派員,以及皇子、郡王等皇室貴胄,還有各種普通旗人、漢民百姓、職業道士、文人士大夫。其盛大的規模也受到了眾多文人的關注,他們在《夜譚隨錄》《新齊諧》《夢廠雜著》等筆記小說中留下了對丫髻山的聞知。①徐天基:《北京丫髻山的進香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4期,2014年6月。
清嘉慶、咸豐時期,由于各種教派動亂,丫髻山廟會開始逐漸衰落。此后,王(二)奶奶②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王奶奶是京津地區聲名顯赫的神明。她以多種形象出現,并有多種稱呼,如王奶奶、王二奶奶、王三奶奶,在丫髻山稱為王二奶奶,在妙峰山稱為王三奶奶。民間對于王(二/三)奶奶的具體所指有時名稱不同,指代的具體神明相同,有時又同名不同指,但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論名稱和神明指向如何,這些地區王(二/三)奶奶的事跡和信仰內涵是基本一致的。參見徐天基:《北京丫髻山的進香史》,《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4期,第89—91頁。信仰的崛起,逐漸使丫髻山的進香主體從北京當地居民變為順天府東路的香河和武清二縣居民,北京當地居民在進香事務中的地位退居二線,只在捐助丫髻山香火錢等方面發揮作用。清同治以后,香河、三河、寶坻、武清等各縣逐漸成為丫髻山共同的主人,他們以王(二)奶奶信仰為號召,將四大門信仰的信奉者聚合在一起③李俊領、丁芮:《近代北京的四大門信仰三題》,《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共同建構了丫髻山廟會的又一盛景。
根據林玉軍和岳升陽的研究,明代至民國,在北京東部形成了一個以丫髻山為中心,包括大興、宛平、懷柔、密云、平谷、順義、通州、三河、香河、武清、薊、寶坻等州縣在內以這些地區的碧霞元君廟為次級中心的碧霞元君朝拜圈。④林玉軍、岳升陽:《明至民國北京東部碧霞元君朝拜圈研究》,《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顯然,這些存在碧霞元君廟的地區不但共同構成了丫髻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勢力范圍,而且也是丫髻山廟會期間廟市的顧客分布范圍。在這些次級中心中,值得關注的是香河縣,因為香河縣是丫髻山神靈體系中除碧霞元君之外另一位十分重要的神靈——王二奶奶——的娘家所在地。⑤劉鐵梁主編:《中國民俗文化志·北京·平谷區卷》,第68頁。因此,除了大批奉碧霞元君、王奶奶為更高級神靈⑥李慰祖著,周星補編:《四大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3—65頁。,并將其納入信仰體系的四大門信仰者之外,還有一群固定的來自香河縣的,主要以王(二)奶奶為信仰對象的信眾群體。實際上,他們也構成了丫髻山廟市的顧客群體。由此可見,丫髻山的廟市和丫髻山廟會,或者更嚴格地說,丫髻山廟市的顧客群體和丫髻山廟會的信眾群體具有十分重要的連帶關系。
晚清以降,直到新中國成立,由于社會的動蕩,丫髻山的廟會和進香活動整體上處于衰敗狀態,官方的資助逐漸停止,廟會活動只能依靠民眾自身的財力勉強維持。雖然這導致廟會的規模大大縮小,但是仍有一些民眾自發組織的進香活動。這種進香活動之所以能夠持續下去,是因為民眾將當地免于戰禍的原因和人們的進香聯系起來,認為是民眾進香的誠心感動了神靈,從而獲得神靈保佑。據存于丫髻山的《寶坻縣城南如意老會碑》記載:“吾儕弟子,每歲四月初八日護駕來朝丫髻山頂,蓋四十有余載矣。凡在會諸家,天災不染,人害不侵,耄耋康強,髫齡精壯,轉禍為福,易危為安,雖庚子大劫兵燹,均未及焉。”
新中國成立之后,1953年,劉家店鄉政府籌劃恢復丫髻山廟會。據時任劉家店鄉鄉長回憶,當時的廟市,“本縣的供銷社大部分都來了,大街上放著戲匣子,大家都覺得稀奇新鮮,…五里長街兩側搭著布棚,彩旗招展,賣日用品的、農產品的應有盡有,個體賣絹花、小食品、日用雜貨齊全。在戲樓青睞文藝團體唱大戲,變戲法、雜技、拉洋片,耍蛇的也都來了。”⑦北京市平谷區文化委員會編:《畿冬泰岱——丫髻山》,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125頁。1958年,丫髻山舉辦了以“物資交流大會”為名的廟會,商品的買賣在當時這屆廟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后,丫髻山廟市伴隨著丫髻山廟會的停滯而暫停。1987年恢復丫髻山廟會,廟市也隨之得以復興。恢復之后的第一屆丫髻山廟會,“四月初一那天,丫髻山上鑼鼓喧天、旌旗招展、香煙裊裊。山下各種雜耍、馬戲、賣山貨、賣日用品的小攤販,熱鬧非凡。”①劉鐵梁主編:《中國民俗文化志·北京·平谷區卷》,第64—65頁。
伴隨著丫髻山廟會在各個歷史階段的興衰,廟市也會發生相應的興衰。需要指出的是,丫髻山廟市和廟會之間的伴隨關系并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說可能曾經出現過有廟會而不一定有廟市存在的情況。同時,丫髻山廟會的信眾也并不一定都是廟市的顧客,他們可能只是純粹的進香群體。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許多來自香河的信眾群體都自備香裱紙錢和各類祭祀用品,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去山上進香,很少在廟市逗留游玩。
丫髻山廟會的一個重要參與群體是各類的民間花會組織,他們為廟會的所有參與人提供各類服務和表演,同時他們也上山進香,也會光顧廟市,是丫髻山廟市的重要顧客來源。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北京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們旅游休閑觀念的改變,丫髻山地區的旅游業逐步發展起來,政府投入大量資金對丫髻山景區進行相應的景觀改造。②張振江:《發展道教特色溝域經濟,打造京都旅游文化大鎮——劉家店鎮丫髻山道教養生谷溝域經濟建設情況調查》,《北京農業職業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包括丫髻山道教文化節、平谷桃花節和丫髻山廟會在內的地方旅游品牌互相融合借力,從而帶來了當地旅游業的大發展。丫髻山逐漸成為京東地區一個著名的文化旅游景點,許多旅游者來丫髻山參加政府舉辦的上述各種文化旅游活動。農歷四月中上旬,丫髻山廟會和其他文化旅游活動的開展,吸引了大批來自北京城區和包括順義、懷柔等平谷鄰近區縣的普通民眾。他們是純粹的旅游者,以逛廟會、參加道教文化節和桃花節為目的,但同時又遵循當地習俗,和普通碧霞元君信眾一起上山進香。
二、娛樂與嘗鮮:丫髻山廟市的商業地景
對于廟市的商販而言,日復一日的商品買賣既是他們謀生的工作或職業,同時又是他們的日常生活。這種日常性表現在這些活動一方面是平常的、習慣性的,另一方面卻是每天都必須進行的,是每日生活的主要內容。對于他們而言,廟會只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做生意的機會而已,這種機會與集市所帶來的有限時間內大量的人流所帶來的商業機會是一樣的。丫髻山廟會所帶來的人流量遠遠超過了大部分商販平時進行商品買賣的場所的人流量,因此他們暫時放棄了原來的貿易地點而聚集到丫髻山。
如果說一般集市當中的商品類型主要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如蔬菜瓜果、衣服鞋帽、五金日雜,那么在廟市當中,大部分的商品就是非日常生活必需品。廟市中的商品更具趣味性和休閑性,如各種玩具商品或游戲道具、特色小吃和祭祀商品。當然,在一般集市中也會有玩具商品和特色小吃,但是數量遠遠比不上廟市。人們趕集的主要目的在于補充家庭生活的基本所需,所以大宗的商品是人們生活中的剛性商品——瓜果蔬菜、衣服鞋襪。小吃和食攤是為了滿足路途較遠的人們無法及時趕回家吃飯的需要,同時地方小吃在日常生活中的罕見性也對人們有一定的吸引力。玩具和游戲則是滿足同長輩一起趕集的小孩或者留在家中的小孩的玩樂需要的。人們逛廟會,就普通信眾來說固然是為了進香,但同時也是為了娛樂休閑。在當代社會,人們以休閑娛樂為目的來逛廟會,因而并不能稱為神靈信眾的游客在廟會參與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大。雖然水果、帽子等商品也能夠在廟市中看到,但并不是廟市的主流,廟市的商品種類更多樣、更繁雜。廟市因廟而生,伴隨著神廟的節期性廟會活動而舉行,同時,廟市也因廟而盛,廟會的規模決定了廟市規模的大小。①樊鏵:《民國年間北京城廟市與城市市場結構》,《經濟地理》,2001年第1期。正是由于廟市的存在,廟會才不僅是一種信仰的盛會,同時也成為集敬神祈福、娛樂、旅游休閑和商品交易于一體的公眾活動。②寧欣:《鄉村的廟會與廟市》,《文史知識》,2007年第1期。
丫髻山廟市中,有很大一片區域是集中經營兒童玩具或者游戲娛樂設施的商販。這些商販是專門的趕會者,他們的生計來自于這些游戲設施的門票或玩具銷售的收入。根據各地廟會舉行的不同時間,他們形成自己固定的流動路線。玩具大部分是小玩意兒,如塑料制作的變形金剛頭盔、喇叭、長翎悟空帽等。游戲娛樂設施分兩種,一種是路邊攤,和其他商販混雜在一起,占地相對較小,如打氣球、打彩蛋、投球獲獎、投圈獲獎等,另一種是占地較大的娛樂設施,以收取門票,獲得刺激性體驗為內容,如內景設計了多條道路的迷宮樣式、大地震的地動山搖、深山老林的吸血蜘蛛精、恐怖陰森的陰間地獄,以及世外桃源的浪漫之地、鬼屋,彈簧制作的固定蹦床,碰碰車、軌道小火車、飛天輪,用充氣塑料膜做的“兒童世界”“鯊魚大滑梯”。還有面向一般民眾的“雙龍7D電影院”等。除了這些有固定攤位和場所的坐商,也有一些挑著裝滿各種玩具的擔子、扛著插滿小玩具的玩具柱、自行車上掛滿一大團五顏六色形態各異的氣球的流動小販。
廟市當中的特色小吃和飲食也是廟市吸引香客和游人的一大亮點。這些小吃種類繁多,味道各異。有的是北京本地的糕點和特色小吃,如老北京鹵煮火燒、炸灌腸、驢打滾、艾窩窩、扒糕、炒肝、炸丸子,也有的是外地特色美食,如朝鮮族打糕、蒙古烤肉、長沙臭豆腐等。當然也有經營一般飲食的,如面攤、涼皮攤、烤玉米紅薯攤、干果攤,還有一些賣干貨的,如蘋果干、干薯條、堅果。這些小吃和食攤一方面滿足了香客和游人對于地方特色小吃的喜好,另一方面也解決了遠道而來的香客饑餓的問題。
廟市中有不少專門經營香攤的商販,這些香攤售賣進香所需的一切物品,如不同規格的香、紙錢、紙元寶、鞭炮。這些香攤有的是長期在此經營以售賣進香用品為生的當地村民,有的是借著廟會臨時售賣香燭紙錢的當地人或者外鄉人。由于平時過來進香的民眾較多,丫髻山所在的北吉山村也建了香廠,專門生產各種規格的香。香廠的香不但大規模向外批發,也向村民零售。丫髻山廟會期間,有很多香攤的香就是從北吉山村香廠拿的貨。同時,由于香廠規模不大,香的種類有限,比較粗大的香也產量較小,因此也有許多商販從外地進貨以滿足香客的多樣化需求。
在丫髻山廟市中還有一類人,他們并不是專業的商販,但也是廟市的一部分,他們有的身著道袍和僧服,以道士與和尚的名義為進香敬神、觀光旅游的各方來客看相測字、占卜命運。有的則沒有特殊的打扮,依靠一些特殊的道具作為非人自然力的象征,例如小鳥,通過小鳥翻開的紙簽來求占者的命運或未來。他們和那些經營游樂設施的商販一樣,隨著各地廟會的節期而四處轉場。對他們而言,算命是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他們的日常生活就是在不同廟會的流轉中度過,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除此之外,丫髻山廟市還有許多與一般集市無二的商攤,售賣時鮮水果、鞋帽衣服、手串核桃、手串原木。這些經營不同商品的攤販來自于四面八方,有丫髻山周邊的村民,也有來自北京其他區縣的鄉民,還有許多來自于外省專門趕廟會生意的小販。正是這些經營不同商品的攤販共同構成了丫髻山熱鬧興旺的廟市空間。
丫髻山廟會所帶來的大量貿易機會并不僅僅是外地人和丫髻山之外的其他群體獨享的盛宴,同時也是丫髻山所在地區民眾增加收入的機會。一方面,通往丫髻山的北吉山村的街道兩側房屋和場地的出租為當地民眾帶來了租金收入,另一方面,當地民眾也實實在在地收獲了大量游客所帶來的商業機會。丫髻山的所在地劉家店鎮是大桃之鄉,蟠桃的收入在當地民眾的收入結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對于當地民眾來說,蟠桃的銷售不僅依靠當地建立的許多蟠桃銷售市場,如胡店大桃市場、劉店大桃市場、北宮大桃市場,以及胡家營大桃市場,同時也依靠許多客商的上門收購。但是并不是農戶收獲的所有桃子都能夠在市場和收購中得以銷售。因此,當地農戶除了到專業市場銷售大桃,還用桃子做成罐頭向客人銷售。這種罐頭作為當地的一種地方特產,一方面成為民眾互相送禮的對象,另一方面也將多余的桃子以這種制作罐頭的方式進行加工銷售。每年農歷四月初的丫髻山廟會,也成為當地民眾銷售大桃罐頭的一個機會。事實上,當地政府也在著力利用丫髻山廟會向外地客人宣傳和推廣當地的大桃。當地政府將丫髻山廟會和桃花節結合起來,在丫髻山廟會期間推出賞桃花、觀民藝、品名吃、購特產等活動①馬春江、于雷鳴:《平谷桃花節旅游有望出現“井噴”》,《中國現代企業報》,2009年4月10日,第B04版。,從而促進蟠桃的銷售,增加農民收入。
三、守護繁華:廟市賣者的多樣與艱辛
作為嵌入丫髻山廟會整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廟市不但為前來丫髻山進香祈福的信眾和參觀游覽的游客提供了一個品嘗當地特色小吃、購買當地特色商品和敬神所需要的香燭紙錢的機會,同時,也為諸多以從事這類商品買賣為主業的商販提供了一個增加收入的機會。這熙熙攘攘的人流和琳瑯滿目的商品,都是丫髻山廟會所積聚起來的神靈經濟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這種神靈經濟借著拜神的名義,將神圣和世俗勾連起來,將文化和經濟串聯起來,同時也將地方社會與區域、國家聯系起來。
根據與廟市的關系,丫髻山廟市的賣者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以廟市、物資交流會等年節性的集會活動為商品交易的主要場所的賣者。這類賣者在全國各地轉場,他們熟知全國各地大型廟會或者物資交流會的時間或者會期,根據不同地區廟會或物資交流會的時間安排自己一年的轉場路線。這類賣者在丫髻山廟市中主要經營游樂設施、贏獎游戲和來自各地的特色小吃,如蒙古烤肉、朝鮮族打糕、長沙臭豆腐、氣槍打氣球、打彩蛋、投球贏獎品等,還有到各地廟會替人算命的人。
第二類是以北京各地鄉鎮集市為商品買賣的主要場所的賣者。廟市只是集市的補充,因為廟會期間的人流量遠遠大于一般的廟市,因此逢廟市的時候他們就放棄自己平時固定經營的集市攤位來趕廟會,以獲得更多的銷售機會和收入,這類商販多經營一般的日常商品,如水果、衣服、帽子等。
第三類是在丫髻山所在的平谷縣城等地有固定的門店。平時依靠門店經營,家里有充足的幫手和方便可用的車輛,在鄉鎮的集日以及附近的大型廟會舉行的時候也過來趕集或者趕廟會。這類賣者的動機和前一類賣者是相同的,都是為了抓住廟會所帶來的大量人流及隨之而來的貿易機會。在丫髻山廟市,這類賣者大多是那些經營水果、衣服、玩具的商販。
第四類是丫髻山下的固定擺攤或開店經營者。他們長年累月在丫髻山下擺攤或者經營自己的門店,不逢廟會的時候他們依靠平時、特別是周末向前來爬山游覽丫髻山勝景的游客銷售飲料、日常飲食、野營用品等商品,逢廟會的時候也正好利用廟會,只不過比平時擴大了攤位的規模。這類賣者銷售的商品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上山進香所用的香燭、花炮、紙元寶等,另一類是普通游山玩水的游客所需要的飲料、雪糕、瓜果等。
對于大多數賣者來說,不論其屬于上述四類商販中的哪一種,長期的還是短期的,有固定攤位的還是沒有的,他們在廟市中的日常生活大體上來說都是相似的——招徠買者銷售商品。盡管每一個具體的買賣過程,發生在每一次買賣當中的故事是不同的,但是對于每一個具體的賣者來說,集市不但是一個工作的空間、收入的來源,同時也是嵌入自己生命歷程和生活軌跡中的一種文化結構,潛在地建構自己的生活模式和思維圖景。
丫髻山所在的平谷區,和密云區緊鄰,有不少密云區的人過來趕廟會賣東西。這些人一大早開著車來到丫髻山,占好攤位,將自己的商品擺出來,等待顧客的光顧。有的是夫妻合作,不光在廟市中有攤位,同時還用小推車推著商品在廟市中轉悠,這樣能最大限度地彌補固定攤位可能失去的客源。
我們在上面所講的第二類商販是廟市中最普遍的一種商販類型。他們以每日到各個鄉鎮的集市售賣商品為生,起早備貨,有的人為了省去一筆固定的攤位費,就經常臨時去占攤位,所以不得不在天還未亮,大多數集市賣者還未到場時就早早地來到集市賣場。每天賣到中午十二點,甚至下午一兩點鐘,顧不得吃飯和休息,期間的艱辛難以言盡。在這種日復一日的生活中,他們經歷著生活的艱辛,同時也收獲了辛苦的成果。在他們背后站著的是自己的整個家庭,他們通過趕集或趕廟會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買賣的好壞直接關系著一家人的收入和生活狀況的好壞。因此,對于他們而言,廟市不僅僅是一個銷售的地點,更是生活的希望所在,重要的不是在哪里賣,而是賣得怎么樣以及如何才能賣得更多。
對于廟市而言,廟會期間眾多賣者每日在丫髻山下同無數的買者所發生無數次商品交易就是廟市日常景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交易生活是平淡無奇的,從數量、質量和認同上來說,也是最經常、平常和正常①康敏:《“習以為常”之蔽:一個馬來村莊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的活動。正是由于他們這種“過日子的平常、通常的過程與狀態”②高丙中:《日常生活的后現代遭遇:中國民俗學發展的機遇與路向》,《民間文化論壇》,2006年第3期。,才使得丫髻山廟市和廟會活動能夠順利地在每一年的這個時間不斷舉行下去,也才使得包括廟市在內的丫髻山廟會能夠成為平谷地區的一個地域標志。③劉鐵梁:《“標志性文化統領式”民俗志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廟市上每一個賣者正常而不斷的交易使得丫髻山廟會最終得以達成。但是,這種賣者的日常性和作為整體的丫髻山廟市和廟會的日常性又是相對的。因為丫髻山廟會之所以有魅力,能夠吸引信眾和游客,恰恰在于其本身的“非日常性”。廟市中琳瑯滿目的地方商品和特色小吃,廟會中熙熙攘攘的人流和丫髻山信仰文化的“非日常性”才是真正吸引所有參與者的核心所在。這也就是“日常生活的相對性”,這牽扯到的就是廟會的指涉對象問題。對于商販以及廟會的主辦者來說,這是最“日常的”,他們追求的目標也正在于這種“日常性”,但是對于廟市和廟會吸引或者面向的他者來說,又是“非日常的”,他們追求的目標又恰在于這種“非日常性”。因此,這種“日常性”和“非日常性”的共謀或者說平衡才最終達成了丫髻山廟會的現實。
四、北京地域社會中的丫髻山廟市
丫髻山廟市是附著于丫髻山的碧霞元君廟會和丫髻山所在的區域貿易體系的,因此,丫髻山廟市一方面作為丫髻山廟會文化的一部分被納入了地域社會乃至更廣范圍的信仰體系當中,另一方面作為地方社會貿易體系的一部分被納入了區域貿易系統當中。因此,對于丫髻山廟市的理解就要從神靈信仰和商業貿易兩個方面來審視。
丫髻山廟市首先是要納入丫髻山廟會的年度性祭祀的時間制度當中來的。因此,廟市舉行的時間和規模就直接和廟會聯系在一起。丫髻山廟會的會期及其所帶來的人流量從根本上決定了丫髻山廟市規模的大小。丫髻山作為京東地區碧霞元君信仰的一個重要信仰中心,其影響擴展到了北京、天津和河北乃至華北的許多地區,其長達近二十天的會期帶來了大量進香的信眾和游玩的游客。這一方面為丫髻山廟市帶來數量可觀的買者,另一方面也使得丫髻山廟市的規模相當可觀,從而不但吸引了周邊地區商販的加入,也吸引了許多外地賣者的參與。除此之外,由于同屬碧霞元君信仰,共享同一系統的神靈,前來丫髻山廟會進香的香客以及由他們所組成的香會也是包括妙峰山、“五頂”在內的諸多其他廟會的香客。①張青仁:《行香走會——北京香會的譜系與生態》,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87—193頁。丫髻山廟市實際上也被納入了京津地區的碧霞元君信仰體系當中,成為碧霞元君信仰中與香會表演、施粥施茶等香客服務活動聯結在一起的文化共同體。②王曉莉:《明清時期北京碧霞元君信仰與廟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5期。
對于鄉村社會來說,由集市所勾連起來的集期制度是一種重要的時間制度。這種時間制度有效地滿足了鄉村社會內部產品交換的需要和補充外部產品的需要。雖然這種集期制度和丫髻山廟會所依賴的神靈信仰的年度周期制度之間并未發生直接的關聯,但是如同上文所述,集市的賣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廟市的買賣,而且從另一方面來說,廟市和集市互相補充。集市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大宗農產品和外來工業品,廟市提供特色小吃、信仰商品和娛樂商品,共同滿足了人們對商品交換和娛樂的需要。
丫髻山廟市還處于更廣范圍內的區域性廟會制度中。在這種制度中,不同區域的大型廟會由于舉行時間的差異,從而能夠根據先后次序相互銜接起來。這就為一大批專門以趕廟會為生的商販提供了穩定的銷售機會,也正因此,廟會才以其集中的大規模的人流養活了一批專門性的廟會商販。這些商販就是我們前文所提到的專門經營游樂設施、各地特色小吃的商販。這些人根據自己熟知的全國各地廟會的會期和廟市規模情況,在長年累月的轉場中積累了豐富的關于廟市的知識,從而形成了自己固定的趕廟會的路線。他們是廟市中不可或缺的一群人,而且他們售賣的部分商品和提供的服務也是地方商販沒辦法提供的。同時,各地的特色小吃在地方上也并不多見,或者說,規模太小不成氣候,只有許多特色小吃集中在一起,為人們提供多種選擇,才能最大限度吸引人流。
廟市中發生的大大小小的故事或者事件從“人”的角度來看固然是個體性的,但從地域社會的角度出發來看,它們也是社會性、實踐性的,是“北京”這一概念所包含的地理、文化和社會意義在現實世界的物化映照。通過對這種以具體的商品買賣和人際交往為基礎的社會細節的觀察和體驗,我們對于“北京”的理解也就不再停留于虛無縹緲的想象,而進入到民眾生活的現實當中。那么,丫髻山廟市是否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北京”,如果能,它又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北京”一詞所具有的真正內涵?或者換個說法,丫髻山廟市能夠在什么樣的一種層面上促進我們對于“北京”這一概念內涵的理解?我們如何經由對丫髻山廟市的觀察,通達“北京”這一概念指涉的核心內涵?
一方面,作為“北京”這一概念所包括內容的一部分,丫髻山廟市和其他種種包括物態實體和非物態景觀在內的文化形貌共同構成了人們對于“北京”一詞的文化認知;另一方面,丫髻山廟市又不單純是一種普通的民間商業文化,而是一種既與傳統廟會文化、道觀文化、小吃文化聯系在一起,同時又與當代新興的旅游休閑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多元文化形式。它在承載傳統所賦予它的進香祈福的文化內涵的同時,也擔當宣傳地方文化、提高當地知名度、增加農民收入、繁榮地方經濟的重任。因此,對于地方社會而言,丫髻山廟市和廟會不但具有某種作為文化傳統而存在的象征意義,更具有許多實實在在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丫髻山是平谷地區乃至京東地區的標志性文化。①劉鐵梁:《“標志性文化統領式”民俗志的理論與實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它具有獨特的歷史和較高的區域知名度,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當地的社會、歷史的變遷,以及當地民眾對于社會和自己生活的認知與思考,因而成為當地政府著力利用以實現自己的經濟抱負的文化資源。
因此,丫髻山廟市和廟會文化從內容上構成了我們上面所說的“北京”內涵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同時,作為當地的標志性文化,丫髻山廟市和廟會文化又能夠代表其所在的地區,與北京其他地區進行對話,或者代表北京地區的民間文化與其他種類的文化形式進行互動,甚至作為北京文化的一個代表與更廣范圍內其他地區的文化形式進行溝通和比較。更重要的是,丫髻山廟市和廟會文化既融合了一般的民間文化如廟會進香祈福、花會表演、廟市買賣等,也融合了道教的宮觀建筑文化、宗教文化,還有皇家文化的孑遺。其歷史比較久遠,有具體的物化傳承形態和文字記載,因此就更加能夠體現北京文化中所特有的歷史感和傳承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說丫髻山廟市和廟會文化能夠反映“北京”一詞的真正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