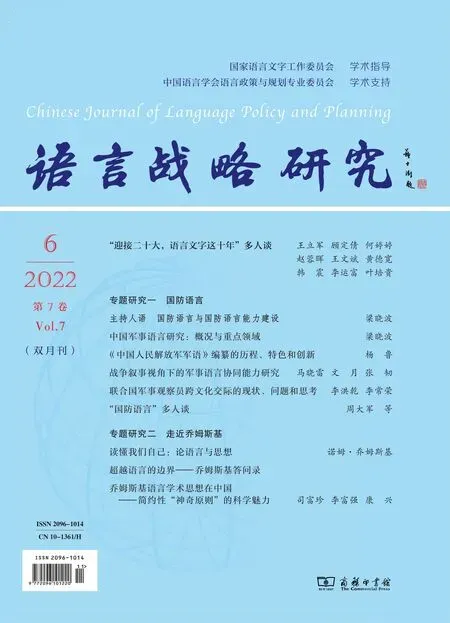超越語言的邊界
——喬姆斯基答問錄
封 葉,田英慧,閆玉萌,董澤揚(譯)
(北京語言大學 語言學系 北京 100083)
【問答一:李宇明(北京語言大學教授)vs.諾姆·喬姆斯基】
問:讀您的著作,比如您與豪瑟(Hauser)和費奇(Fitch)2002年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語言能力:它是什么,誰擁有它,它是如何進化的?》一文,以及《我們是何種生物》的系列講座,使我們認識到人類的語言能力是由遺傳因素決定的,是人類大腦中先天存在的“普遍語法”在起作用。我想請教您:(1)聾人因聽力受損而不能習得自然語言,聾人手語是否也受“普遍語法”的制約?(2)人到老年,外顯的語言交際能力退化,那么老年人的內在語言能力是否會發生相應改變?
答:非常好的問題,十分符合我現在的情況。如你們所見,我現在就有點耳背,聽得不是很清楚。我在讀由中文轉錄來的英文翻譯,當它試圖轉錄中文時會有點問題,很好玩。
關于第一個問題。大約在30或40年前,人們首次對手語進行了非常認真的研究,這些研究結果令人振奮。事實表明,手語就其結構而言與口語幾乎是完全一樣的,或者說非常相似。也就是說,聾啞嬰兒和正常嬰兒,從發育的早期階段開始,都以相同的速度和方式習得語言。有過育兒經驗的人可能比較清楚,有一個特定的時期,一般是6個月左右,嬰兒咿呀學語,也就是開始發聲。這對嬰兒可能是有意義的,盡管在我們看來沒有任何意義。同一時期,聾啞嬰兒也開始咿呀學語,他們用的是手勢。還有一個時期,在15個月左右,孩子容易混淆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他們將母親稱為“我”,將自己稱為“你”。這比較容易理解,因為這和他們聽到的指稱有關,他們后期會自行改過來。事實上,聾啞孩子用手勢時也會發生同樣的事情。他們稱他們的母親是“我”,稱自己為“你”,這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因為他們用于指代人稱的手勢與他們用于指向的手勢相同,而在用于指向時,他們用的都是正確的。單純指向母親時用的是對的,而用于語言表達時,對面的母親變成了“我”。在整個語言發展階段中,聾啞孩子和正常發展的孩子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此外,還有大量研究發現,盲人孩子對和視覺有關的詞匯有著驚人的理解,如glare(瞪)、gleam(閃爍)、gloom(幽暗)、look(看)see(看見)等,他們可以區分得非常清楚。不知為何,生物的內部系統似乎完全相同。所以語言就好比一臺電腦,它內部有一個程序,它并不關心它所連接的打印機是怎樣的,甚至可以連接到任何打印機上。就語言本身而言,接什么樣的“打印機”(聲音系統,手語,甚至是觸覺)外化這個語言程序,都不影響語言本身。對于盲人也是一樣,幾乎不需要外部刺激。
關于第二個問題。的確,語言的使用能力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年紀大了的人都熟悉這種感覺。話到嘴邊了,但是卻表達不出來。類似這種情況很多。關于內在語言能力是否退化很難說,我們甚至不知道如何研究。因為我們只能研究外在語言表現,而外在語言使用能力確實在退化。但是內在語言是否也會退化就不得而知了。今天我們還沒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這個答案。也許如果我們對大腦的編碼方式有更深入的了解,就能得到答案。大多數機能都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衰退,這并不奇怪。
【問答二:邢心藝(北京語言大學本科生)vs.諾姆·喬姆斯基】
問:按照您的觀點,LAD(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是人類特有的,它自然有別于其他動物的交流系統。您是否認為可能存在一個人類和其他動物認知能力的連續統,而非兩者在根本上處于對立的系統呢?
答:我們應該始終對這些問題保持開放的態度。目前來看,我們只能說,這個鴻溝看起來是無法跨越的。其他有機體中都不存在類似(人類)可以產生無數遞歸結構的語言系統,所以遠沒有可比性。人們曾試圖推測二者間的聯系,但都沒有什么結果。人類的語言概念,哪怕是最基本的語言單元,也與動物的交流系統完全不同。正如我提到的,動物的(交流)概念似乎是與物理上可識別的事件一對一地聯系在一起的,這與很多哲學家對人類語言的錯誤推斷一樣。但事實上人類語言并非如此。我也提到過,語言的設計似乎并不利于交流。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果你看一下進化的方式,我們假設科學研究中的“神奇原則”有效,那么這就是你所預期的。那么你所說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呢?我認為現有的證據是不支持這種說法的。
【問答三: 封葉(北京語言大學講師)vs.諾姆·喬姆斯基】
問:語言的內在性是否必然意味著領域特異性?語言能力的某些方面是否有可能通過領域一般學習機制獲得?
答:同樣地,這是有可能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問的是:什么是領域一般學習機制?事實上,就目前所知,基本上沒有這樣的機制,更不存在學習機制。大約六七十年前,有觀點認為學習就是條件反射作用的結果。以英語國家中領軍式語言哲學家蒯因(W.V.O.Quine)為例,他認為語言只是由操作性條件反射作用所形成的一種綜合性配置系統。這是沒有依據的,一點根據都沒有。事實上,你們問問自己:學習和生長的區別是什么?人類胚胎并不是通過學習成為人類的,而是生長為人類。但是這種生長需要環境輸入,就像養分之于胚胎。所以我們處于這樣一種情況:有某種輸入系統,輸出的是人類。即輸入養分,輸出人類,此謂生長。那么,我們再來看什么叫學習。事實上它是同樣的,只不過它相比內在的東西更強調外在的環境。但是如果一個孩子學習一些介于二者之間的事物,我們甚至不知道該如何定義。什么叫學習走路或者學習騎自行車?它既是學習也是生長。什么叫學習一個單詞?一樣的。就像我給出的例子中,內在結構、自然環境、單詞,他們本來就在那兒。所以我們有一個頻譜,這個頻譜是所有的輸入輸出關系。輸入總是先天結構和環境的結合,輸出是這個有機體產生的任何結果。如果你仔細觀察,在某些情況下,先天的作用更多,環境的作用更少,我們傾向于稱這些為生長。而在其他某些時候,我們則傾向于稱它為學習。但是不存在所謂的學習機制。只有生長的生物學機制以不同的方式運作。任何一種生長都是需要一些經驗的,其中一個已經被深入研究過的主題是視覺。通過視覺的研究,我們對視覺了解了很多。因為還有其他生物和我們具有相似的視覺系統,比如貓,我們就允許自己用貓做一些無法用人類做的實驗,不管這樣做是否正確。研究發現,如果你在小貓出生后的幾周內帶走它,并且沒有讓它得到圖案刺激,那么它就永遠看不到。此外,圖案必須是線條,水平線和垂直線。如果垂直線更多,它的垂直辨別能力就會更強。那么我們的視覺系統是我們通過學習得到的,還是自己生長出來的?兩者都是。關于學習的每一個例子,都是一樣的。就像實驗心理學家訓練鴿子打乒乓球,之所以可以做到,是因為鴿子會啄。由于鴿子會啄,它們可以啄球,于是心理學家自欺欺人地陷入了思維循環。鴿子打乒乓球,其實就是啄球,是一種稍加修改的本能。因此,不存在所謂的領域一般學習機制。在有人能解釋它具體是什么之前,恐怕無法真正提出這個問題。
【問答四:雷晨(北京語言大學碩士研究生)vs.諾姆·喬姆斯基】
問:目前有很多神經語言學的研究結果證明語言和音樂的加工腦區存在重疊;同時,二者的加工腦區也存在非重疊區域。您認為二者具有相同的大腦激活區域,是否意味著擁有相同的加工處理機制呢?
答: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近年來人們對它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正像很多人所了解的那樣,50年前,偉大的音樂家萊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在哈佛的諾頓講座中真正提出了這個問題,他提出調性音樂(他沒有研究其他類別,僅限于古典調性音樂)和語言之間是否存在相似之處(結構上的相似之處),這引發了大量的相關研究。目前已有很好的證據表明,至少調性音樂的大部分基本結構似乎與語言具有共同的屬性,這意味著它們可能來源相同。關于算術也有類似的觀點。這可以追溯到達爾文(Darwin)和華萊士(Wallace),在進化生物學中有一個嚴肅問題,這就是,為什么每個人都會算術。它在人類歷史上幾乎從未使用過,幾乎不可能是由自然選擇而來。達爾文和華萊士為此提出了這個著名的爭議性問題。它很可能是語言官能的一個衍生物。如果做內部合并,再加上一個由算術的基本要素所構成的心理詞典,你基本上可以得到基本的算法(比如后繼函數和加法,非常接近算術運算)。這很可能就是語言的衍生物,或者就是和語言從相同的起始要素發展而來。這其中有著非常非常有趣的問題。關于來自大腦的證據,我們對大腦還不是很了解,只是非常粗淺地了解一些大腦皮層的功能定位,而即使是這些也都是懸而未決的問題。你選擇的證據可能正說明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
【問答五:龔銳(北京語言大學博士研究生)vs.諾姆·喬姆斯基】
問:首先,您2014年的著作中將遞歸定義為“可計算的有限過程產生的離散對象的集合”。那么,您是否認為遞歸在動物交流系統中也存在呢?如果遞歸是人類語言與動物交流共有的特性,那人類語言的遞歸機制有什么獨特之處嗎?其次,依您目前的觀點,生成語法作為遞歸過程的一個特殊案例,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最簡遞歸呢?在接口的邊界條件下這樣的遞歸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答:我們雖然不完全排除這一可能,但目前還沒有證據證明(遞歸存在于動物交流中)。而且,文獻中存在很多對這個概念混淆不清的狀況。人們總是把遞歸單純地混同于重復的、嵌套的,或是有層級的結構。這不是遞歸。遞歸是數字上的無限性。任何已知的動物系統都不具有能與數字無限性媲美的性質。我們必須仔細研讀相關文獻,因為大家都對這個話題感到困惑。但如果真的在動物系統中發現了遞歸性,便可以證明語言特性有更深的起源。那么我們必須要問,如果語言的屬性真的能被動物所用,為何動物一直沒有發展出語言?它們為何將這種能力拒之門外?正是這種語言的特殊屬性引發了人類非凡的進化,促使了人類族群的成功。因此如果這個性質在動物身上被發現,這將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奇跡。這就好比在某些島嶼找到了一種鳥類,它們本來有著出色的飛行潛能,但自己卻從未意識到這一點,還得等到有人類來嘗試教會它們飛行。我的意思是,雖說從邏輯上講并非不可能,但果真那樣,那真是一個生物學奇跡了。然而恐怕還沒有什么理由指望真的存在這樣的奇跡。
【問答六:陸儉明(北京大學教授)vs.諾姆·喬姆斯基】
問:上個世紀90年代末,語言學界逐漸認識到語言的句法結構實際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核心結構,一類是邊緣結構。核心結構,譬如說“約翰喝了一杯咖啡”;邊緣結構,譬如說菲爾墨(Fillmore)所研究的“let alone”以及“what’s X doing Y”不表疑問的這種句子。那么我請問喬姆斯基先生,怎么來解釋這些邊緣結構,因為我感覺您的理論好像主要是來解釋分析核心結構的,對邊緣結構怎么來解釋?
答:首先,我們應當認識到,相較于其他科學,語言學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初級階段。自伽利略開始的科學領域里,大家都認識到,理解一個復雜現象需要對觀察結果進行高度的抽象。如果從伽利略的角度來考慮,我們想要尋找運動定律的話,是不可能去觀察風中飄動的樹葉的,因為這樣做根本無法發現運動定律。我們必須從中進行抽象,這就是所謂的實驗。實驗就是對現象的高度抽象。科學不斷發展,我們身邊的現象都成為了科學研究的對象,但這些現象都太過復雜,其中涵蓋的變量太多,并發的事件也太多。因此我們應當研究高度抽象的情景。這在科學研究中早已成為習慣,沒人會去刻意提及。在語言學中卻并非如此,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通俗地稱語言為一種“復雜的混沌”。以我自己的語言為例,如果仔細研究的話,會發現我的語言源自費城北部的一種當地口音,同時與我父母的移民口音進行了某種程度上的混雜。隨著時間推移,到了我上大學的時候,又摻雜進了一些所謂的牛津標準英語。而當我移居波士頓后,我的語言又發生了變化,因為我又遇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這就是一種“復雜的混沌”,世界上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如果我們要對它進行研究,就要找到它的核心成分,正是這些核心成分為它提供了一套普適的基本原則。我認為這個道理對于核心-邊緣結構來說也是適用的。那么我們來看一個邊緣結構的經典例子。比如,在構式語法中,“the bigger he is,the harder he falls”這樣一個表達并不是由普通的規則所生成的,如果仔細考察這個結構,就會發現它實際上是由數條生成規則復合而成。你還可以用“the taller he was”“the more he likes potatoes”等等來代替“the bigger he is”,能用來替代它的東西還可以很多。因此,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都各有一個生成能力無限的規則支持,而這兩條生成語法規則又非常相似。這樣一來,構式語法中就需要3條生成語法規則來解釋它,一條生成前半部分,一條生成后半部分,第三條則把這兩個部分組合起來。它們之間高度重合,甚至可以說它們實際上本來就是同一個語法規則。所以,如果這么來看語法的生成,那就太復雜了。照這樣把它們以特定的方式組合在一起,你會發現語言中有很多這樣的東西。以習語為例,比如“he spilled the beans”,真正意思卻是“他泄露了秘密”。實際上,語言中的任何句子都可以變成習語。比如對于“you enter the store”這句話,我們可以編造一個語境讓它可以用來表達“他沒寫作業”的意思。一旦我們開始這么用,它就能成為一句習語。因此,任何句子、任何結構都能成為習語。研究習語也就是研究語言本身,只是依據慣例從中選取了一部分并賦予了特殊的意義。如果完整地研究語言所有的混沌狀況,必定會出現這種現象的大雜燴。這就好像為了解釋樹葉在風中飄動的現象而研究運動定律,得到的必定是一團糟,研究者們是不會這樣研究物理現象的。所以,我認為抽象化才是我們應當學習的語言研究方法。我們首先要找出那些基本原則的來源,再嘗試在更復雜的情境中運用它們。
【問答七:何雨殷(北京語言大學副教授)vs.諾姆·喬姆斯基】
問:在分析語言數據的結構派生時,語言學家如何確定某一操作是否屬于第三因素操作呢?您可否具體來說一下,第一因素操作(如合并)與第三因素操作(如Chomsky 2021提出的控制結構中的拷貝形成)之間的界線是什么?區別這兩種操作的證據是什么?
答:其實,它們之間存在一個非常清晰的邏輯區別,但在實證科學中,想要確認這一區別可能并不容易。普遍語法是先天的,作為基因稟賦的一部分編碼在大腦中,它與計算復雜性原則(如最小搜索或者其他簡約性原則)這類自然的普遍規律之間存在概念上非常清晰的區別,但要證實某一操作屬于哪一種可能不那么容易。這就是實證研究的特質,也是可預見的難題。所以你要在研究中考察最合理的理論會產生什么推論。如果你認為某個操作是出于普遍的計算原則,那么要去考察它是否適用于語言之外的其他情況。如果你認為某個操作是語言特有的,則要證明它不適用于其他情況,這就是實證研究。所以你提問中的兩類操作存在明確的概念上和事實上的區別,但要甄別這一差異的運作過程可能并不容易。這也是實證研究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