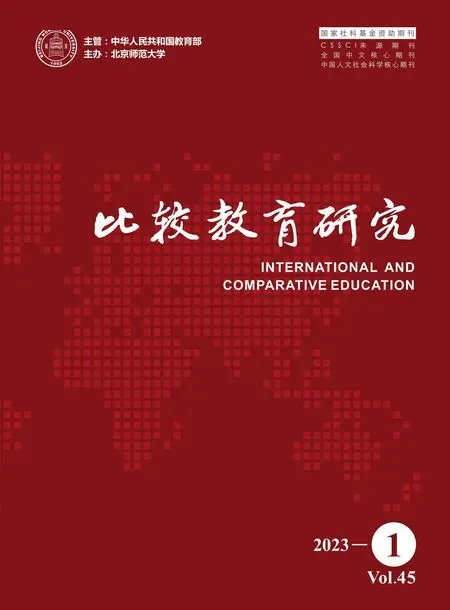荷蘭企業助推0~3歲兒童托育服務發展責任與行動分析
杜麗靜
(紹興文理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浙江紹興 312000)
當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對發展托育服務的重要性已經達成共識,[1]采取各種舉措推動0~3歲兒童的托育服務發展,其中歐洲的托育服務在遭遇“低生育率陷阱”的境況下仍然保持穩步發展的態勢,荷蘭是典型代表之一。2014年,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和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受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委托,對27個成員國的托育服務情況分析發現,荷蘭的學齡前兒童(0~4歲兒童,4歲兒童進入基礎教育階段)享受托育服務的比例遠遠高于“巴塞羅那目標”(Barcelona Targets)①2002年,歐洲委員會在巴塞羅那召開了一次會議,鼓勵會員國消除對女性在職場的不利因素,為3歲以下兒童以及3歲至法定學齡兒童提供正式早期教育與照護服務。會議宗旨為預計在2010年各個成員國實現至少為33%的3歲以下兒童提供托育服務,為至少90%的3歲到法定學齡的兒童提供正式早期教育與照護服務。,即0~3歲兒童接受正式托育服務的比例已達50%,3~4歲兒童接受學前教育服務的比例超過90%,位居歐盟成員國前列。[2]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調查,截至2017年,荷蘭有56%的0~2歲兒童參加了正式托育機構提供的優質服務,遠超經合組織國家38%的平均值。[3]荷蘭0~3歲兒童托育服務的發展與其長期形成的“圩田模式”(Polder Model)密不可分。[4]“圩田模式”是荷蘭企業雇主、工會和政府以共識為基礎合力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一種模式[5],解決托育服務問題便是其中之一。2018年,世界銀行女性、商業與法律小組(Women, Business and The Law 2018)對全球189個經濟體的調查顯示,荷蘭政府率先立法,要求企業必須負擔員工子女的托育責任(其他國家包括巴西、智利、厄瓜多爾、印度、荷蘭、伊拉克、日本、約旦、土耳其、烏克蘭、越南)。[6]政府配套了一系列政策引領企業雇主充分關注兒童發展,從機構設置、托育津貼、休假安排等幾個層面多維并舉地推動0~3歲兒童托育服務發展。
一、荷蘭企業承擔托育責任的背景深描:生育悖論隱藏的間接方式
近些年來,荷蘭女性平均生育率經常維持在接近世代更替水平①世代更替水平是一個國家或區域出生與死亡達到某種相對平衡的情況,生育率只有超過死亡率,才能實現人口增長。,需要強調的是,該國有超過60%的國民沒有宗教信仰,政府并未實施直接的生育政策,[7]卻造就了一種“荷蘭生育悖論”(dutch fertility paradox)的奇觀,這種奇觀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逐漸形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荷蘭人口數量雖然一直呈現出穩定增長的態勢,生育率卻跌宕起伏,經歷了由高峰滑向低谷,觸及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警戒狀態,再由低谷緩慢回升的波折。20世紀60年代,荷蘭每位婦女的平均生育率為0.312%[8],遠遠超過當時歐洲0.166%的世代更替水平,且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創造了荷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輝煌的“嬰兒潮”(baby boom)奇跡。但從20世紀70—80年代,荷蘭經歷了嚴重的生育下滑,生育率由0.257%降到了0.160%,[9]低于當時國際生育替代率0.18%~0.21%的水平。[10]20世紀90年代,荷蘭的生育率長期穩定在0.16%左右, 直至1995年略有小幅回升,且這一趨勢延續到2000年后,當時荷蘭婦女的平均生育率上升到0.172%,在2010年甚至升至0.179%,也就是每位婦女平均生育 1.5 ~1.8 個孩子。[11]荷蘭的生育率在經歷了一段劇烈下滑之后有所反彈,這種現象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12]
2015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United Nations)公布的人口政策調查結果顯示②2015年之后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的報告沒有涉及不同國家政府對生育水平的態度與干預。,從2011年至2015年,荷蘭政府對全國整體的生育水平展現出了由滿意到不明的態度變化,盡管沒有對生育政策做出任何干預(自1976年以來一直采取不干預的方式),但采用了間接的方式支持家庭計劃(見表1)。③家庭計劃包括婚姻、伴侶關系、懷孕、育兒等。也就是說,荷蘭政府已經意識到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和結構的問題[13],但由于歐洲民眾普遍信奉“個人決策自由”的價值觀,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和影響個人及其伴侶對生育與家庭組成的重要私人決定,[14]促使政府不得不采用間接方式,即企業雇主與政府、家庭共擔員工子女托育服務的責任來影響家庭決策。

表1 荷蘭政府對生育態度與生育政策的情況一覽表
間接方式的應用植根于荷蘭這個國家持久而獨特的歷史文化。17世紀以來,荷蘭因人口多元、文化豐富而逐漸形成一種新的以利益為基礎的自治社會團體形式。[15]各個社會團體通過“集中協商、尋求共識”[16]的獨特方式進行社會決策。1982年,政府與企業、工會等社會團體簽署了《瓦森納協定》(Wassenaar Arrangement),催生了“圩田模式”的廣泛應用。需要強調的是,政府鼓勵企業雇主、政府與家庭承擔起員工子女的托育服務責任,并非直接指向促進婦女生育率,而是為了給婦女提供平等、多元的就業機會。長期以來,荷蘭男性外出工作,女性照顧家庭,由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與普遍度越來越高,適齡女性生育孩子后不得不權衡家庭與工作的關系。[17]為此,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做了一些性別平等的改革,[18]鼓勵企業采取多項積極措施,為女性提供平等、多元的就業機會,支持每個年輕家庭有更雄厚和豐沛的能力兼顧工作與育兒,緩解員工難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的緊張狀態。這些舉措雖然意在刺激女性就業與經濟發展,卻意外成為國家托育發展和生育更替的一股重要力量。
二、荷蘭企業承擔托育責任的政策轉變:要求企業從自愿參與到強制參與
20世紀90年代,荷蘭政府著手調整一些就業政策,幫助企業員工協調工作與生活的關系,涉及休假安排、托育服務及鼓勵婦女兼職就業的內容。2000年,荷蘭社會事務與就業部(Ministerie van Sociale Zakenen Werkgelegenheid)頒布了《工作和照護法》(Work and Care Act),構建了企業雇主與工會協調家庭友好措施的法律框架,規定了雇主需承擔為員工提供照護兒童的休假計劃、資助計劃及限定工作時長的責任[19],但對于企業到底要支付多少費用等細節問題并未明確,尚需各州議員深入討論。2001年,荷蘭社會事務與就業部頒布了《工作時間調整法》(Working Times Adjustment Act),要求企業為員工提供更為彈性的工作時間,確保員工可以滿足日常照護兒童的需求。[20]
2005年,荷蘭政府開始在全國范圍實施《兒童保育法》(Childcare Act),建議政府、雇主和父母共同分擔托育責任。最初,該法案并未對企業雇主產生直接的約束作用,只是敦促雇主自愿參加,結果多數雇主不愿擔責。2006年荷蘭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企業主動配合的比例只有65%,很難在2008年達到預期90%的比例。[21]由于成效不彰,2007年荷蘭政府重新修訂《兒童保育法》,強制要求政府、企業雇主和家庭必須共同承擔員工子女的托育責任,雇主需負擔員工家庭育兒費用的三分之一,每年須繳納一定比例的托育稅。同年,芬蘭社會事務與就業部頒布了《商業登記法》(Commercial Register Act),要求凡是雇傭5人以上的各類企事業單位或機構雇主均需為員工子女提供托育服務,且行業覆蓋面廣,涵括生產制造業、農業、建筑業、商業、醫藥、交通、政府部門、健康福利、教育機構等。[22]后續,為了統一規范托育品質,荷蘭政府于2010年修訂了《兒童保育法》,更名為《兒童保育與托兒所的質量標準法》(Wet kinderopvang en kwaliteitseisen peuterspeelzalen),對企業開辦托育機構的品質、管理、收費補助等更細致的內容進行了系統規范。[23]2017年,政府再次頒布了《兒童保育的創新質量法案》(het akkoord Innovatie en kwaliteit kinderopvang),該法案的宗旨是借助規范企業舉辦的各類托育機構的教育質量、游戲質量,促進兒童的全面和諧發展。
縱覽上述內容,有兩個重要取向日趨明顯。第一個是政策的約束力由低到高。初始時期,荷蘭政府頒布的相關政策僅僅是鼓勵企業自愿參與員工子女的托育責任。后續,政府強制要求各類企事業單位或機構雇主必須承擔起支持員工子女托育服務的責任,而且把雇員人數確定在5名以上,這就對大部分企業雇主提出了強制要求。第二個是政策約束的內容日漸豐富,前期政策涉及企業雇主為員工提供休假計劃、托育服務、資助計劃、工作時長調整計劃,后續的政策更側重企業開辦托育機構的責任、品質、管理、收費補貼、服務等。這些看起來貌似無關企業經濟發展的條款,實則是政府對企業員工心聲的深度洞察,唯有企業雇主為員工解決了后顧之憂,才有可能刺激就業與生產。
三、荷蘭企業承擔托育責任的立場奠基:充分關注兒童發展
對于從事各行各業的企業雇主而言,若想為員工子女提供優質的托育服務,首先必須奠基科學的兒童發展立場。兒童發展立場是促使雇主將關切點從商業盈利回歸“人”的根本站位與態度,具有引導思想走向與行動落實的重要作用。在荷蘭,雇主逐步樹立兒童發展的專業立場深受兩個層面的影響。
第一,長久以來,荷蘭不同社會團體在“圩田模式”的廣泛應用中尋求解決各類棘手問題的策略,逐漸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國家治理特色,即多主體“共擔責任”。不同社會團體在這種文化浸潤下鐫刻了共同的特質,即寬松、協商、妥協,這就不難理解為何企業雇主更容易接受承擔員工子女托育服務的新責任。與此同時,雇員擁有的主導政治觀點亦是社會伙伴與政府、家庭應該肩負同樣的責任。荷蘭經濟政策分析局(Netherlands Bureau for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企業雇主與國家共同分擔責任才能確保員工平衡工作和家庭。[24]不要小看民眾擁有的這種普遍的、相似的、篤定的價值觀,它猶如一縷看不見的線,牽引著荷蘭這個國家的政策走向,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為員工子女承擔部分托育服務責任而秉持的兒童發展專業立場。
第二,荷蘭社會事務與就業部修訂了一系列兒童保教的相關政策,引領雇主從兒童發展的專業立場提供優質托育服務。這些政策主要圍繞四個核心要義展開。其一,雇主要切實關注兒童的發展。[25]雇主是否具有兒童發展的立場,對兒童發展的價值理解與施行程度蘊含在所提供的托育服務水準之中,若兒童立場科學而堅定,則其托育服務質量高,員工的滿意程度也隨之提高。其二,雇主要關注托育機構的健康與安全。[26]健康與安全是所有兒童最重要、最基礎的權利之一,[27]雇主在申請開辦托育機構之前,必須為本機構細致規劃一套成熟的健康與安全手冊,在托育機構創辦三個月后及時更新內容。此外,雇主有責任帶領教學人員、志愿者學習如何發現機構內外可能潛藏的風險、如何規避風險、如何應對小風險等。其三,雇主要創設穩定的、富有教學意義的托育環境。[28]在托育機構中,熟悉的面孔、相對固定的空間和日常節奏有助于給予兒童安全感與秩序感,雇主要熟知兒童發展的秘密,為兒童營造穩定的物質環境和人文環境。其四,雇主要將育兒視為一種專業性極高的職業。[29]其品質取決于教育教學人員的資質與素質,雇主需要支持教學人員持續學習兒童發展所需的情感、知識、能力。
在文化浸潤與政策引領之下,一些企業雇主將員工子女的托育服務與兒童健康發展奉為分內之事,甚至有一些獨具優勢的企業充分發揮行業所長,為更多兒童提供更優質的支持。例如,阿斯麥公司是世界級半導體行業的創新領導者,為芯片制造商提供光刻機的硬件、軟件及相關服務,在荷蘭總部的員工超過1.4萬人。[30]該公司不僅為員工提供專業的托育機構,而且成立了基金會,招募兒童教育研究人員,開展非營利性教育項目,設計科學、技術、工程、數學(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Mathematics,STEM)教育與語言教育等課程,為國際處境不利的2~16歲兒童提供教育支持,惠及16個國家60個城市的兒童。
四、荷蘭企業承擔托育責任的行動落實:多維并舉的積極舉措
(一)設置專業化、規范化的合格托育機構
荷蘭政府鼓勵企業雇主為員工子女提供優質的托育服務,部分雇員較少的企業采用與正式托育機構簽訂合作協議的方式①荷蘭托育服務分為正式和非正式兩類,正式的托育機構包括日托中心、學校照護(4~12歲的課前和課后照護機構)、保姆照護機構和公共托兒所。非正式的托育服務包括幼兒游戲小組(2~4歲)、學校午休托管、親友協助和賓客家長團體。正式托育機構是遵照《兒童保育法》的規范,有國家托兒所的合格注冊。,讓員工子女享受優質托育服務,也有一些較大規模的企業采用獨立或共同設置托育機構的方式提供服務。荷蘭的正式托育機構包括日托中心(childcare centres)、托兒所(childminding agencies)、校外護理中心(out-of -school care centres)、家長參與的托兒中心(parent participation childcare centres)。荷蘭經濟部(Ministerie van Economische Zaken)為企業提供了翔實清晰的托育機構設置清單,涉及如何建設托育機構、如何管理托育機構、招募托育人員的數量與資質等,還給企業配備專業人員協同處理上述專業事宜。[31]以托育機構選址為例,政府建議企業雇主在選擇托育機構地址時應符合所在城市的分區計劃(位于本轄區內,方便員工接送小孩),符合當地政府的環境管理規范(在安全、健康、可用、綠色能源等方面要達到相應標準)。[32]若符合上述條件,雇主需要在全國兒童保育與托兒所注冊機構(National Childcare and Playgroup Register)進行登記,依據清單提供安全計劃、風險預防計劃、教學計劃、教學人員資質方案以及教學空間與家具配備計劃。
托育機構的園所選址、空間配置、計劃研議僅是舉辦托育機構的初始一步,后續的專業經營和規范管理才是真正體現雇主為員工子女提供優質托育服務的核心所在,也最能體現雇主“關注兒童發展”的意識與情懷。荷蘭政府特意提供了經營托育機構的一系列建議,包括如何調控合適的師幼比例,如何提供有品質的兒童教育與照護,如何提升教學人員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如何保證教育品質,甚至為托育機構提供了發生各類糾紛的處理策略。[33]承辦者可自行參照服務清單了解每個步驟的做法。以師幼比為例,依據“熟悉面孔原則”(Familiar Face Criterion)①“熟悉面孔原則”是《兒童保育的創新質量法案》中規定的師幼比例,熟悉面孔是0~4歲兒童所在機構經常看到的兒童照護者,有助于兒童發展社會情緒、安全感。每個年齡段的兒童所需要的熟悉面孔數量不一。,熟悉的面孔有助于幼小兒童形成安全感,0~1歲、1~2歲兒童每天在機構內需要見到2張熟悉的面孔,3歲以上兒童則需要見到3張熟悉的面孔。[34]若1~2歲的兒童所在的活動室有4位保教人員,最好保證有2位保教人員是兒童熟悉的,唯有如此,兒童緊張的情緒才會有所緩解。此類教育建議具體而翔實,不僅告知承辦者要怎么做,而且解釋了這些做法背后的兒童發展原理。
(二)提供因人而異的托育服務津貼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Keynesian economic policy)的盛行催生荷蘭蛻變為一個高福利國家,政府成為民眾家庭生活的重要支持力量。2005年,荷蘭社會事務與就業部施行《兒童保育法》,明確規定了托育費由家長、雇主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擔,每一方各付三分之一。雇主支付托育服務費用有兩種渠道,一種是通過稅務渠道按比例繳納。依據荷蘭政府發布的《工作成本計劃》(Work Expenses Scheme)的規定②2015年荷蘭社會事務與就業部頒布本計劃,對企業雇主具有較強的約束力,計劃中的條款和內容必須強制執行。,雇主參照員工的稅前工資總額,抽取一部分用于支付員工的托育津貼或其他福利(無論該員工是否有子女,子女是否享受托育服務),比例占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一,此部分雇主無須繳稅。[35]由于每年經濟發展情況不同,員工的職位薪酬不同,所享有的托育津貼各不相同。以2020年為例,雇主必須為每位員工支付工資總額的1.2%作為托育津貼,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這個比例增至40萬歐元之內為3%,40萬歐元以上為1.18%,且持續到2022年。[36]第二種則是通過繳納保險費的方式支付。依據《社會保險基金法》(Social Security Fund Law)的規定,每位長期工作或生活在荷蘭的人必須參加《國家保險計劃》(National Insurance Schemes),其中一個就是兒童福利保險。雇主從雇員的工資中依據投保薪資總額扣繳固定比例的稅金,繳納給荷蘭稅務和海關總署,作為兒童福利保險資金,比例從2007年的0.28%上調到2012年的0.5%。[37]
托育津貼的額度一方面與員工薪資總額的固定比例相關;另一方面,具體數額依據員工子女在正式托育機構享受服務的時間及每小時補助的上限確定。2008年,荷蘭政府發放的托育津貼為每小時最高6.10歐元;到了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托育津貼增至每小時8.17歐元[38],支持員工家庭加強應對疫情的經濟能力,保證其子女享受優質托育服務。員工(全職與兼職均可)以季度為時間單位在社會保險銀行(Sociale Verzekeringsbank)申請托育津貼,[39]政府會依據每位員工的收入狀況,以及子女在正式注冊的托育機構享受服務的時間長短(每月最多申請的托育照護時間不能超過230個小時),[40]核算每位員工可以領取的托育津貼數額,再經由稅務部門把這筆錢匯入員工賬戶。
(三)賦予父母平等的育兒休假權利
多數家庭需要夫妻雙方肩負“工作”與“家庭”兩項重擔,然而,工作與家庭往往會互相競爭個人的時間和心力,形成工作與家庭的沖突(work and family conflict),[41]工作與家庭中任何一種角色的過度都會給人帶來壓力。荷蘭政府一直將平衡家庭和工作視為一種重要的社會價值,并通過制定法規保障父母的各類育兒休假權利。1991年,荷蘭政府要求企業為孩子未滿8歲的員工提供3個月的育兒假(parental leave),主要用于兒童的保育與養育,但僅限于從事兼職工作的員工使用,[42]且企業無須支付員工假期期間的薪資。1992年,歐盟委員會通過了一項兒童保育的建議(92/241/EEC),鼓勵成員國盡可能讓男性和女性都享有從事職業與照顧家庭的責任。1996年,歐盟委員會要求成員國立法確保每位家長能夠享有充足的育兒假,一年達到3個月。[43]在歐盟委員會的倡導下,荷蘭政府頒布了《工作與照護法》,明確規定員工享有育兒假,每位員工(不論男女)均可休息13周用來照護孩子,2001年后每年增加10天的短期照護假(care leave),用于短暫照護生病的孩子,同時享有七成薪資。至2005年,政府再次修訂了《工作與照護法》,增加了長期護理假(long-term care leave),要求企業給予員工每年6周的無薪假期,用于照護生重病的親屬(包括孩子)。[44]如果員工生了雙胞胎,則可以獲得兩倍的育兒假。
企業雇主為員工提供的育兒假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是男女平等。荷蘭統計局(Centraal Bureau voor de Statistiek)的調查顯示,父親與母親享有數量相近的休假時間,分別是一年享有310小時和312小時,而且育兒假是每位父母的個體權利,不可以互相轉移。第二個特點是休假期間因工作而導致的收入損失可獲得部分補償,由政府、企業雇主和員工共同承擔,但這種補償僅限于短期休假,員工享有七成薪資,部分費用可以獲得稅收減免,長期休假則無法享有薪資。
五、荷蘭企業承擔托育責任的成效分析:由直接效益轉向間接效益
隨著世界各國的競爭與日俱增,企業處于最為激烈的“前線”地帶,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狀況的“晴雨表”。在一般人的認知結構中,企業可能會與盈利或創新產生直接聯系,鮮少將企業和托育責任對接起來。而荷蘭政府在特有的“共享責任”的濃郁文化下,倡導各類企業與政府、家庭共同承擔員工子女的托育責任,由政策保障到多維舉措,可謂事無巨細,滲透到員工子女能夠享受托育服務的各個層面。此舉讓企業獲得的最直接效益則是解放了被家庭束縛的女性,給予女性平等獲得就業機會的權利。美國佐治亞州立大學內文·瓦列夫(Neven Valev)引領的經濟學家團隊對全球200個國家的經濟調查顯示,截至2021年,荷蘭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達到59%,超越了世界平均水平51.96%,[45]60%的就業女性是兼職勞動者,[46]有效協調了家庭與工作的矛盾。與此同時,承擔員工子女托育服務的企業,用解決員工后顧之憂的策略吸引了大量優質人才的目光,得以匯聚更多人才長期駐守。
企業承擔員工子女的托育責任,不僅是給予員工的必要福利,而且更是一種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使命擔當,是對社會公共托育的長效投資,最終將會回報公共社會。社會學領域的知名學者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曾提出“宏觀-微觀-宏觀模型”理論(macro-micromacro model)(見圖1),[47]強調某個時期宏觀層面的政策、制度會形成獨特的背景機制,對微觀層面的個人做出“那時那地”的決策具有一定影響,而個體的決策會引發后續的相應行動。當某個時代多數個體都做出某種行動后,會向上傳遞信號,影響國家在某個領域的發展。展開來說,荷蘭政府規約企業必須負擔員工子女托育服務責任的法案或政策,以及多主體“共擔責任”的國家治理特色,凝練成一種無形但無處不在的文化或風氣,影響雇主積極筑造婦女友善的職場,并提供“幼有所育”的福利,“潤物無聲”地傳遞給微觀層面的個人,影響了員工家庭的生育意圖和決策。在友善氛圍中工作的員工有較高自由度進行選擇,更愿意生育、養育孩子并做出相應行動。若社會中較多微觀個體愿意做出生育與養育的決策和行動,則會增多新生嬰兒的數量,提高每名適齡女性的平均生育率,進而影響國家的生育趨勢和人口發展取向。

圖1 宏觀-微觀-宏觀模型圖
六、結語
荷蘭政府要求企業承擔員工子女0~3歲兒童托育服務的一系列舉措是全方位的、深層次的改革,在政策設計、責任歸屬、專業支持、行動落實層面均有引領和規范,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獨特性。一是企業愿意與政府、家庭共同承擔員工子女的托育服務,得益于荷蘭具備多方“共擔責任”的深厚土壤,企業雇主在長期采用“圩田模式”合力解決社會難題的歷程中,自然而然地認同承擔員工子女托育服務的“三分之一”責任。二是荷蘭政府各個部門通力合作,頒布了一系列法規和政策,并經常修訂與調整內文,以期達到引領企業雇主逐漸融入責任方的角色,從兒童發展的專業立場考慮各種問題,為員工子女提供優質的托育服務。三是荷蘭企業在政府引領下,從機構設置、托育津貼、休假安排三個層面給予員工子女享受托育服務的必要支持,切實解決了員工的后顧之憂。從成效來看,不僅提升了女性的平等就業權利,影響整體勞動力在質與量上的發展趨勢,更擴大了0~3歲兒童托育服務的范圍,為提升托育服務質量水平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