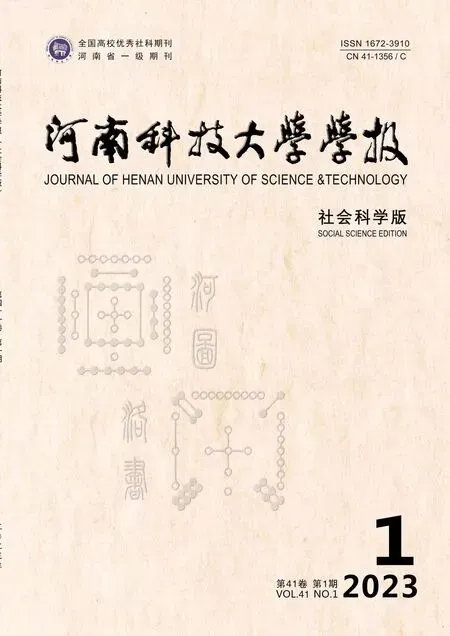從摩崖石刻看明代的鄉(xiāng)村敘事
——以上甘棠村為例
徐 紅
(湖南科技大學(xué) 人文學(xué)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摩崖石刻是一種古老的敘事方式,在傳承民間文化傳統(tǒng)、記錄普通民眾歷史等方面有重要意義。今湖南江永上甘棠村保存有明代摩崖石刻11方,時間自洪武三年(1370)至天啟七年(1627),涵蓋明初到明后期各個階段(1)據(jù)筆者實地考察并參閱湖南科技學(xué)院圖書館藏“古籍與碑刻”圖片、曹學(xué)群《江永上甘棠村月陂亭石刻》(載《湖南省博物館館刊》第1期,《船山學(xué)刊》雜志社2004年7月),確定位于上甘棠村月陂亭的明代摩崖石刻包括洪武三年1方、天順?biāo)哪?方、天順五年2方、成化七年1方、成化八年1方、嘉靖十年1方、隆慶三年1方、萬歷三年1方、天啟三年1方、天啟七年1方。文中凡述及11方石刻具體內(nèi)容的引文,未標(biāo)注出處者,皆出于此。。上甘棠村所在的江永即明代永明縣,隸屬湖廣承宣布政使司永州府[1]1091,是一個默默無聞、地處內(nèi)陸的小地方,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方面均不占優(yōu)勢;明代也沒有出現(xiàn)過對朝廷產(chǎn)生影響的重要人物。雖然上甘棠村周姓村民的先祖與宋代大儒周敦頤同族同宗,但那已是距明代300余年的事了。明王朝的基層社會正是由這些湮沒無聞的縣城和鄉(xiāng)村構(gòu)成的,生活于此的百姓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因此上甘棠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石刻基本能夠反映明代鄉(xiāng)村石刻的敘事情況。這些摩崖石刻均鐫刻于上甘棠村西南月陂亭一側(cè)的天然石壁上,瀟賀古道穿亭而過。石刻內(nèi)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稱頌與該村生存和延續(xù)密切相關(guān)的地方官功績,二是歌詠該村的自然風(fēng)光和人文景觀,三是記錄和贊譽該村的公共性工程及捐助題名。摩崖石刻因其材質(zhì)和位置而具有永久性、開放性特征,這就決定了其并非隨意為之,而是有意識地選取與本村有關(guān)聯(lián)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勒石為記,傳之久遠(yuǎn)。
一、對本地地方官的稱頌
知縣是明代的基層官員,知縣之上有知府、承宣布政使等多個層級的權(quán)力網(wǎng)絡(luò),受到各種政策法規(guī)、官德倫理的制約。但知縣掌管著一縣的行政、財政、司法等各項事務(wù),對于縣境內(nèi)的鄉(xiāng)村而言,是擁有生殺大權(quán)的官員,其言行及政策、舉措很有可能影響到鄉(xiāng)村的興衰。因此,如果知縣曾經(jīng)做過有益于某個鄉(xiāng)村的事,本村的鄉(xiāng)紳就會以各種方式記錄此知縣之功德,摩崖石刻即其一,對于資料有限的明代鄉(xiāng)村而言,這些留存至今的摩崖石刻就顯得彌足珍貴。
上甘棠村明代摩崖石刻中,有兩方涉及有功于上甘棠村的永明知縣。其一是鐫刻于洪武三年的“邑侯謙齋彭公大丞平滅賊首鄧四功績歌詩”,由永明縣儒學(xué)教諭王懷寶撰文:
……功不補(bǔ)患致遺患,壬辰鄧四踵構(gòu)亂。狐嗥鼠嘯蕃有徒,獍食鸮噬肆無憚。吞沒七鄉(xiāng)限郡城,黨周伯顏攻湘酃。甲午甄帥進(jìn)殲削,鄧四暫降旋不庭。黃簽院軍全府起,鄧右丞師發(fā)二水。倡義向?qū)叻グ丝四苋 Jッ魍硬拍懞狄用娓镄内ゎB。大丞彭公既蒞政,深謀遠(yuǎn)慮禍本芟。鄧四將然舊面逆,公奮決策神掩襲。父子授首巢穴傾,洪武二年夏六月。不動官儲煩郡兵,靡驚婦織妨農(nóng)耕。十有八載大難息,我公功烈誰能成。書生目瞽傷蕩柝,業(yè)復(fù)青氈公盛德。歌頌盛德垂無窮,千古甘棠崖上石。(2)《光緒永明縣志》卷三○《職官志二·列傳》亦載有此方石刻,可與摩崖石刻相對照。《縣志》與石刻文獻(xiàn)的內(nèi)容僅有個別字詞的差異,意思基本相同。
上甘棠村之所以將彭公之事鐫刻于石壁上,是因其平定以鄧四為首的少數(shù)民族民變有功。據(jù)《光緒永明縣志》載,彭公名彭德謙,字謙齋,洪武初年,“丞永明,兼知縣事。初至,即平土賊鄧四之亂”[2]448。彭德謙的平叛讓永明恢復(fù)了往日的太平,故后人將其事跡載于縣志中,但為何上甘棠村為彭德謙鐫刻此“功績歌詩”石刻,王懷寶未能明言。檢《光緒永明縣志》可知,在鄧四作亂時,上甘棠村曾有周翠嫦、周翠娥姊妹,因不愿順從鄧四而跳崖身亡[2]576。此一事件說明,鄧四率領(lǐng)的軍隊在劫掠永明縣城時,上甘棠村亦未能幸免,且很可能還遭受重創(chuàng),所以上甘棠村才會對平定鄧四之亂的彭德謙充滿感激之情,以至于請王懷寶撰文歌頌彭公,并刻于摩崖之上。
第2方石刻為永明縣令何守拙的功德碑,萬歷三年(1575)由前永明縣令、成都府通判何朝佩撰文(3)此方摩崖石刻末記其撰者為“四川城都府通判何□□”,后二字漫漶不清。《光緒永明縣志》卷三○《職官志二·列傳》載,前縣令何朝佩撰有“治績守拙志,而刊于甘棠之石”,又載何朝佩曾在何守拙前任永明縣令六年,因無私公正、治理有方而升任成都府通判,據(jù)此可知撰寫此方石刻者應(yīng)為何朝佩。。碑文如圖1[3]。
此石刻先是贊頌何守拙在任縣令三年間“政通人和,遠(yuǎn)邇稱頌”,然后借周氏族人周秉直之口,言為何公立石原因有三:一是何公“律己以廉,馭下以寬。均里甲以便民,興學(xué)校以造士,撫猺夷以靖亂。實心實政,歷歷可紀(jì),而于吾族尤有厚恩焉”。二是何公為周氏家譜撰擬譜序,為周氏祠堂題寫匾額,“發(fā)先世之光,為將來之勸,厥賜渥矣”。三是何公準(zhǔn)許保留上甘棠村的寺廟,使其“香火載續(xù)”。其后,何朝佩又特別申明何守拙之善行并非獨私上甘棠村,而是“顧甘棠本同濂溪公之派,侯于濂之學(xué),方尊而仰之,故因濂以及其族胤,又安得不屬意于周氏之譜牒與其祠堂耶”;至于上甘棠村的寺廟,則因其“在祠堂之左,先人建置,非曰崇尚虛無,實蔭祠堂靈秀。侯知其然,故為祠堂以存是寺也”。上甘棠村民感念“侯之惠政,被于周族”,于是請文于何朝佩,刻石為記。

圖1 邑侯何公惠政之記
何守拙是四川簡州人,“少從大學(xué)士趙貞吉講學(xué)”[2]449。趙貞吉亦為四川人,號大洲,“以博洽名。最善王守仁學(xué)”[1]5122。他是王陽明心學(xué)泰州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贄認(rèn)為,“心齋之后為徐波石,為顏山農(nóng)……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為趙大洲,大洲之后為鄧豁渠”[4],即泰州學(xué)派的創(chuàng)立者心齋(王艮)之后,有徐波石(徐樾)和顏山農(nóng)(顏均)繼承其思想,波石之后的傳承者則為趙貞吉,可見李贄給予趙貞吉較高的評價。不過,趙貞吉的思想又有自身的特點,比如他對于禪學(xué)的態(tài)度較為寬容,當(dāng)他言及世人對其留意禪學(xué)的非議時,有這樣一段話:“夫仆之為禪,自弱冠以來矣,敢欺人哉!公試觀仆之行事立身,于名教有悖謬者乎!則禪之不足以害人明矣。仆蓋以身證之,非世儒徒以口說諍論比也。”[5]以此說明禪學(xué)并非如某些儒學(xué)家所認(rèn)為的那樣是異端邪說。何守拙雖曾學(xué)于趙貞吉,卻“頗斥釋老”[2]450,其思想更偏重于理學(xué),故才有“侯于濂之學(xué),方尊而仰之”的情況。何守拙還曾因永明有周敦頤族裔,“又有先生所常游覽之處”,感嘆永明無專門祭祀周敦頤的祠堂,恰好 “邑庠之旁,有浮屠氏廢宮”,于是利用其地“建仰濂祠,以系邑人之思”,并請時任都御史趙賢撰《仰濂祠記》[2]652-653。可見,上甘棠村鄉(xiāng)紳之所以刻石稱頌何守拙,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對周氏先祖之一周敦頤的景仰之情及與之相關(guān)的行為,如修建仰濂祠、為周氏家譜寫序、為周氏祠堂題匾,甚至上甘棠村的寺廟也因位于周氏祠堂之側(cè)而得以保存。
此兩方摩崖石刻的敘事帶有非常明顯的地域特征,所記主角及其事件皆與上甘棠村有直接而密切的關(guān)聯(lián),對于本村的生存、延續(xù)亦有重要意義。由于上甘棠村所屬永明縣地處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交錯的特殊位置,因此這里發(fā)生的戰(zhàn)亂多為少數(shù)民族民變,有的甚至威脅到鄉(xiāng)村的存亡,如石刻中所記元末明初鄧四之叛即是如此。從歷史上看,當(dāng)中央王朝對少數(shù)民族的約束力下降,或者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的矛盾突出時,少數(shù)民族民變就會發(fā)生,如南宋度宗咸淳年間,廣西秦孟四率少數(shù)民族反抗,“破永明,殺縣令并尉及學(xué)官,劫縣印,屠掠其城而去”。且秦孟四軍所到之處“屠戮居民,擄婦女,掠財物”[2]469,破壞力極大。有的民變持續(xù)時間較長,波及富川、賀州、永明等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雜居區(qū),對如上甘棠村一樣身處此地的漢族村落而言影響巨大。正是因為這樣的民變關(guān)涉村子的存亡,所以村中有識之士才會在摩崖石刻中敘述此類事件。但是,上甘棠周氏自唐代遷居至此,到明代已有500余年的歷史,其間遭遇的艱難曲折自不待言。從史料記載看,數(shù)百年間的少數(shù)民族民變次數(shù)眾多,為什么單單在摩崖石刻中敘述平定鄧四之亂一事?這應(yīng)該與上甘棠村鄉(xiāng)紳的現(xiàn)實政治考量有關(guān)。盡管中央機(jī)構(gòu)、承宣布政使司及州府的官員,地位更高,政治權(quán)力更大,但對于普通鄉(xiāng)村及村民來說,這些官員畢竟太過遙遠(yuǎn),大多數(shù)百姓甚至終其一生都沒有機(jī)會見到他們,更不用說與他們發(fā)生關(guān)聯(lián)了。縣府官員則不一樣,他們雖屬官僚階層的底端,看似權(quán)力不大,卻是百姓能夠直接接觸的朝廷命官,且擁有與百姓關(guān)系密切的經(jīng)濟(jì)、刑罰等權(quán)力,因而百姓往往對縣府官員天然地懷有畏懼之心。永明縣地處偏遠(yuǎn),這一特征就更加突出。縣府官員,尤其是縣令,直接掌管著縣境內(nèi)各項事務(wù)。因此,摩崖石刻才會選擇與永明縣令相關(guān)的平叛之事作為敘事對象,希望以此獲得保障本村存續(xù)的良好外部環(huán)境。
同時,明代先后擔(dān)任永明縣令的官員不少,若縣境內(nèi)發(fā)生少數(shù)民族民變及爭斗,一般皆由縣令出面平息事端,但在上甘棠村摩崖石刻中僅提及彭德謙一事,可見,鄉(xiāng)紳選擇敘事對象時,還會考慮到是否與本村命運直接相關(guān),若沒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哪怕縣令所做之事影響再大,也不太可能進(jìn)入本村的石刻敘事中,以避阿諛奉承之嫌。依循此一原則,何守拙是因有顧念上甘棠周氏之舉,才被鄉(xiāng)紳刻石記之。此外,何朝佩所撰石刻文字還一再申明何公對周敦頤即濂溪先生的仰慕之情,這里又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即上甘棠村鄉(xiāng)紳非常關(guān)注承載著本村文脈的人物及其事件。理學(xué)鼻祖周敦頤與上甘棠周氏同族同宗,也是上甘棠村得以長期延續(xù)的文化記憶。因此,鄉(xiāng)紳極為認(rèn)同何守拙以周敦頤之名建祠、題文、題匾的行為,并將其看作與彭德謙平定民變一樣,關(guān)系到上甘棠村的延續(xù),于是才刻石紀(jì)念。
上甘棠村摩崖石刻處于瀟賀古道必經(jīng)之地,又有便于旅途勞頓之人稍作休憩的月陂亭,湖廣西南部各地與廣西之間往來的游宦、商賈、小民等在此小憩時,很自然就會抬頭仰望石壁上的文字,且有可能隨著他們的行跡,將石刻所敘之人和事傳布到遠(yuǎn)方。上甘棠村鄉(xiāng)紳以公開勒石為記、傳播久遠(yuǎn)的方式稱頌于本村有恩的永明縣令,用意非常明確,一方面表達(dá)報恩之意,樹立上甘棠村知恩圖報的有德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希冀借助縣令權(quán)威,防范盜匪的襲擾,護(hù)佑上甘棠村安寧。
二、對鄉(xiāng)村景色的歌詠
上甘棠村明代摩崖石刻文字還有一類是歌詠鄉(xiāng)村景色的七言詩,即“甘棠八景”“八景詩一”“八景詩二”3方,凡10首,刊刻時間皆在明代中期。明英宗于正統(tǒng)八年(1443)親政后,雖有土木堡之變、奪門之變等事件發(fā)生,但遠(yuǎn)離京城的百姓所感知的則可能是秩序安定、經(jīng)濟(jì)繁榮。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題詠身邊美景、贊嘆農(nóng)耕生活就成
為鄉(xiāng)紳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流,鄉(xiāng)村石刻即是如此。鄉(xiāng)紳具備撰文、作詩、填詞等中國古代文人素養(yǎng),他們將村民非常熟悉的自然景色和勞動場景進(jìn)行提煉、加工,以詩文的形式予以呈現(xiàn),鐫刻于摩崖上,村民對詩文所描繪的鄉(xiāng)村景色倍感親切,自然也就會受此影響生發(fā)出對本村的熱愛之情。
上甘棠村歌詠鄉(xiāng)村景色石刻詩文的作者或刊述者,大體包括兩類人。一是村中鄉(xiāng)紳,包括周欽、周新、周顯等數(shù)人,他們擁有文化知識,有的還有官方身份。如周欽在成化年間“以歲貢入監(jiān),吏部尚書王恕薦授順天府通判。九載考滿,升治中……以任職稱,公事外無私交,貴戚豪家憚其嚴(yán)正,勿敢干以私也”[2]508。周新、周顯亦是歲貢出身,分別官至云南巨津知州、山東即墨縣丞[2]490。他們是鄉(xiāng)村的文化精英,只要德行純正,均能受到村民的尊敬,由他們撰寫或刊述詩文也是理所應(yīng)當(dāng)?shù)氖隆5诙愂怯芍苄兆迦苏埼牡钠渌聦庸賳T,如翰林檢討劉俊等(4)從甘棠八景詩石刻看,每首詩均有“翰林檢討劉俊作,周新述”之類的落款,即翰林院、國子監(jiān)官員作詩之后,由上甘棠某位周姓族人敘述。可見這些詩均為邀約之作,有可能是應(yīng)述者之請而作,也可能是周姓族人輾轉(zhuǎn)他人請文。由于史料闕載,具體細(xì)節(jié)已不得而知。,作詩者的官職主要有翰林檢討、國子博士、國子學(xué)正、國子助教,均屬學(xué)識淵博、文才出眾、品行端方的職位。翰林檢討為翰林院史官之一,從七品,“由一甲進(jìn)士除授及庶吉士留館授職”,無論是一甲進(jìn)士,還是庶吉士,皆為“進(jìn)士文學(xué)優(yōu)等及善書者”[1]1788。國子博士、國子學(xué)正、國子助教均為國子監(jiān)官員,從八品或正九品,國子博士“掌分經(jīng)講授”,即承擔(dān)為國子生講授儒學(xué)五經(jīng)的工作,學(xué)正、助教負(fù)責(zé)國子監(jiān)的管理,同時也有講授之責(zé),“掌六堂之訓(xùn)誨,士子肄業(yè)本堂,則為講說經(jīng)義文字,導(dǎo)約之以規(guī)矩”[1]1789。由此可知,這些國子監(jiān)官員亦為博學(xué)、有才之士。在中國古代民間社會,學(xué)問是權(quán)力的表現(xiàn)之一,尤其是宋代科舉制度完善后,學(xué)識淵博之人更是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上甘棠村摩崖石刻的作者和刊述者群體非常符合中國古代社會的這一傳統(tǒng),表現(xiàn)出民間對“文”的尊崇。另外,考慮到上甘棠村在明代并無有影響的人物,周姓族人即使身居官位,也處于當(dāng)時官僚體系的中下層,一般很少有機(jī)會結(jié)識上層官員,交游范圍基本限于和他們的政治地位相當(dāng)?shù)膶蛹墸虼耍麄兡軌蛘埼牡膶ο笠蔡幱谶@一階層內(nèi)。從作詩者的身份看,雖然官品不高,但皆為中央文翰之地或最高官學(xué)的任職者,這應(yīng)該是周姓族人竭盡全力拓展人脈的結(jié)果,甚至可以認(rèn)為與周敦頤的余蔭庇護(hù)密切相關(guān)。質(zhì)言之,如果上甘棠村周姓沒有與周敦頤的同族同宗關(guān)系,以他們的身份,不一定能夠邀約到這些處于政治中心、未來可期的官員作詩。
從形式和內(nèi)容看,這些石刻詩均屬中國古代典型的田園山水詩,且?guī)缀跞繃@“甘棠八景”展開,其中最詳細(xì)者是天順?biāo)哪?1460)的石刻(圖2)[3]。

圖2 甘棠八景
上述石刻有詩8首,以命名的方式建構(gòu)了上甘棠村的八處景觀,即“昂山毓秀”“清澗漁翁”“甘棠曉讀”“獨石時耕”“山亭隱士”“龜山夕照”“西嶺晴雨”“芳寺鐘聲”,以四字語詞概括出景觀的主要特點,言簡意賅而又充滿詩意。為永州山水命名始于唐代元結(jié)[6],又有柳宗元的“永州八記”記述永州城郊的八處景觀,后人在此基礎(chǔ)上衍生出“永州八景”,即“朝陽旭日”“回龍夕照”“萍洲春漲”“香零煙雨”“恩院風(fēng)荷”“愚溪眺雪”“綠天蕉影”“山寺晚鐘”。《光緒永明縣志》還記有“永明八景”,命名方式大同小異,如“層巖疊翠”“古剎臨風(fēng)”等[2]679。可見,“八景”已經(jīng)成為古代文人建構(gòu)地方景觀的主要方式之一。從名稱看,這些八景與“甘棠八景”一樣,均為南方鄉(xiāng)村常見的景象,但經(jīng)由詩文的方式予以命名和吟詠之后,則使其具有了豐富的人文內(nèi)涵。
“甘棠八景”的名稱顯示,這些景觀大體包括兩類,一類體現(xiàn)了自然風(fēng)光之美,如“昂山毓秀”:
混沌分來秀氣鐘,半天削出翠芙蓉。縈回上國三千里,壯觀鄰藩十二峰。樹色瞑時晴復(fù)雨,嵐光多處淡還濃。巋然壓斷群山景,風(fēng)月無邊知幾重。
此詩以“削出”形容昂山之奇麗,以“壯觀”“巋然”描繪昂山之壯美,高大而又不失南方山峰的濃淡總相宜,表現(xiàn)出詩情畫意的鄉(xiāng)村風(fēng)光。
第二類是渲染人文景觀之雅,如“清澗漁翁”:
源通活水碧潺湲,一葉扁舟任往還。青笠謾追青瑣貴,綠蓑猶勝綠袍閑。世情榮辱全無念,人事升沉總不關(guān)。笑彼紅塵車馬客,何如詩酒老溪山。
這是一幅非常典型的南方鄉(xiāng)土生活畫。作者有著敏銳的色彩觀察能力和審美感受,善于采用繪畫的方法創(chuàng)作詩歌,從而形成中國古代詩歌典型的“詩中有畫”的藝術(shù)意境,這也是中國古代文人作詩的特征之一。詩中最具特色的是色彩的描繪,首聯(lián)以“碧”字寫出南方河湖水的內(nèi)斂之美,頷聯(lián)更是以“青笠”對“綠蓑”,以“青瑣”對“綠袍”,既有同一色彩的和諧堆疊,又有江湖閑雅之情勝于廟堂枯坐之威的對照,頸聯(lián)和尾聯(lián)則進(jìn)一步表達(dá)了作者對于隱逸生活的向往。全詩雖未直白描述漁翁的形象,卻句句關(guān)涉漁翁,南方鄉(xiāng)村百姓常見的漁翁形象,在古代文人看來則是寄情山水、隱居江湖的隱喻者。據(jù)石刻文字,此詩的作者是明英宗時國子博士鄒鳳,遺憾的是,未見關(guān)于鄒鳳的更多記載,不過,以其國子博士的身份,一定知曉柳宗元謫居永州時作有《漁翁》(5)《柳宗元集》卷四三載有其《漁翁》一詩:“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淥。回看天際中下流,巖上無心云相逐。”一詩,很可能鄒鳳就是受其啟發(fā),為上甘棠村寫下了“清澗漁翁”的詩作。
10首描寫甘棠八景的田園山水詩,結(jié)構(gòu)、寫法均較為簡潔,詩意流暢,這就使得詩所蘊含的信息明確而清晰,營造出一種單純的詩味。比如“清澗漁翁”一詩的主旨就是圍繞漁翁進(jìn)行描寫,無旁支逸出,再加清遠(yuǎn)、飄渺的遠(yuǎn)景意境,以及活水、扁舟的動態(tài)意象,反映出作者向往心靈自由的旨趣,這些詩既是對鄉(xiāng)村田園生活的贊美,亦是作者真實心聲的流露。詩文的撰寫者多為進(jìn)士出身,文才出眾,又精通儒學(xué)經(jīng)典,可謂文化精英,卻屈居于官僚體系下層,這難免使他們生發(fā)出懷才不遇的落寞感,很自然地借詩寄情,表露出不如歸隱山林的心態(tài)。當(dāng)然,上甘棠村民不可能理解這些官員希望棲隱江湖的情感及其背后強(qiáng)烈的功名心,他們一方面對寫詩者的身份感到崇敬,畢竟這些官員在京城任職,帶有中央王朝的光環(huán),而大部分身居“上國三千里”的上甘棠村民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走出過永明,況且寫詩者又多為進(jìn)士,屬于占有知識的群體,被朝廷賦予了強(qiáng)大的文化權(quán)力。另一方面,詩中描寫的山、水、亭、寺等,皆為村民日常生活和勞作中時時見到的景觀,即使他們不懂田園山水詩的意境美,熟悉而親切的景觀還是能使他們感知到這種美的影響力和穿透力,不知不覺中激起超越功利的情感追求。因此,甘棠八景詩雖非名家之作,敘述的也只是南方鄉(xiāng)村常見的景觀,卻能引起村民的共鳴,且為上甘棠村增添了濃厚的文化氣息。
三、對公共性工程的記錄和贊譽
由于古代王朝的社會救濟(jì)往往難以惠及鄉(xiāng)村,像上甘棠村這樣距離京城數(shù)千里之遙的地方,更是不太可能受到朝廷的關(guān)注,于是普通鄉(xiāng)村一般采取鄉(xiāng)紳牽頭、村民捐資的方式進(jìn)行公共性工程的修建和維護(hù)。上甘棠村明代摩崖石刻中,有5方敘及本村的公共性工程,即天順五年(1461)“云歸觀重塑圣像舍錢題名記”,成化七年(1471)“前芳寺重建梵宇題名記”,成化八年(1472)“重建壽隆橋記”,嘉靖十年(1531)“修砌澗下洞路記”,天啟七年(1627)“建觀年月記”,此外還有1方為天啟三年的“詠始祖詩”。這些工程可分為宗教、路橋兩類,一般皆由鄉(xiāng)紳主持進(jìn)行。
上甘棠村的鄉(xiāng)紳對于佛、道之類的宗教從內(nèi)心深處而言并無排斥之心,更不會有視佛教、道教為異端邪說的想法,因此他們主持的公共性工程多與宗教有關(guān),如重塑圣像、重建寺觀等,摩崖石刻對此有明確記載。以“前芳寺重建梵宇題名記”
為例,此類石刻文獻(xiàn)的主要內(nèi)容大體包括五個方面:一是言及佛教在中國“其來遠(yuǎn)矣,始于晉,盛于唐,而相沿于近代”,之所以有如此久遠(yuǎn)的傳播歷史,皆“以其能覺悟群生而陰翊王度也”。二是以簡潔的語言敘述前芳寺始建于宋,之后歷代皆有修葺,至明代成化年間又出現(xiàn)“棟宇傾頹,弗稱瞻仰”的現(xiàn)象。三是周氏族人謀劃、組織重修事宜,他們“相與謀議,圖惟更張,度力計費,立為干首,率先題疏,不惟坊團(tuán)之人樂于施舍,而四方賢達(dá)亦與同植福田也”;在眾人的通力合作下,前芳寺煥然一新,“佛靈有妥,暨凡獲持神物,與夫坐禪、說法、齋居、寢食,亦各有所”。四是稱頌眾人重修寺廟的行為,“原其用心,無非為福生民、翊王度”,于是要“就山亭之崖”刻石為記,存之久遠(yuǎn)。五是捐資者題名及捐資數(shù)。
石刻敘事中,值得關(guān)注的是關(guān)于佛教教化功能的內(nèi)容。朱元璋建立政權(quán)后,對于宗教采取嚴(yán)格管理、充分利用的策略,他認(rèn)為,古今圣賢遵從的“不易之道”為三綱五常,而“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圣人于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頑聞之,如流之趨下,漸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圣人之道而同焉”[7]。一方面極力推崇儒學(xué)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觀,一方面認(rèn)可佛教的功用符合儒學(xué)倫理觀的要求,與中國傳統(tǒng)的“圣人之道”相同,均是統(tǒng)治者治理天下、鞏固統(tǒng)治的思想基礎(chǔ),即所謂“陰翊王度”(6)“陰翊王度”出自《柳宗元集》卷六《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也就是說,明太祖看重的是佛教世俗化、功利化后的勸善功能,尤其是其教化功能,這樣的態(tài)度深刻影響到了明代的鄉(xiāng)紳階層。從上甘棠村石刻可以看出,鄉(xiāng)紳在主導(dǎo)和促成與宗教相關(guān)的鄉(xiāng)村公共事務(wù)時,基本秉持著這一觀念,極力宣揚宗教的教化功能。
上甘棠村的鄉(xiāng)紳雖然熟讀儒學(xué)經(jīng)典,有時還會成為官方的代言人,但他們出生、成長于上甘棠村,是本村的一分子,必須為本村的利益考慮,加之生活于上甘棠村的經(jīng)歷,使他們更了解本村的實際情況,更便于尋找到儒學(xué)與宗教的最佳結(jié)合點。因此,他們既重視儒學(xué)的倫理道德,也對村民崇奉的佛、道之神表現(xiàn)出認(rèn)同,并通過帶頭捐資、組織管理的方式重修寺廟、道觀,促使村民參與此類活動,從而將這些宗教納入教化村民的范疇。可見,越是在遠(yuǎn)離中央王朝統(tǒng)治中心的地區(qū),佛教、道教這樣的民間非儒學(xué)文化的作用就越強(qiáng)大,鄉(xiāng)紳往往也會在儒學(xué)文化和官府允許的范圍內(nèi),整合這些非儒學(xué)因素,使其與儒學(xué)一樣,成為安定鄉(xiāng)村秩序、教化普通百姓的方式。
修砌路橋更是鄉(xiāng)村的重要公共性工程。明王朝統(tǒng)治下的鄉(xiāng)村眾多,地方官府公用經(jīng)費有限,不可能有資金支持普通鄉(xiāng)村的路橋建設(shè)和維護(hù),于是這些公共性工程一般皆由鄉(xiāng)紳帶領(lǐng)村民共同出資,組織修砌。為紀(jì)念這樣的善舉,往往勒石記之,如上甘棠村石刻文獻(xiàn)“重建壽隆橋記”就有較為詳細(xì)的記載,如圖3[3]。

圖3 重建壽隆橋記
重建壽隆橋是上甘棠村信奉佛教之人的行為。這是鄉(xiāng)村公共事務(wù)的特征之一,即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此類石刻基本皆有相似的敘事范式,與前揭“前芳寺重建梵宇題名記”一樣,首先闡述勒石紀(jì)事的必要性;其次申明壽隆橋因年代久遠(yuǎn)而破損,已不足堪用,所以要重修;再次是記述主持重修者的姓名及其具體操作;然后又再次重申修橋善行雖小,但必須記之以利于子孫后代;最后是撰書者、捐資者姓名及捐資數(shù)額。可見,在村里鄉(xiāng)紳看來,重修壽隆橋這一善舉便利了百姓日常生活,所以要以石刻的方式贊頌此事,同時亦褒揚其勸善之功及福澤子孫之德。
修砌路橋是帶有普遍性的鄉(xiāng)村公共性工程,受益者以本村村民為主,同時也包括途經(jīng)鄉(xiāng)村交通古道上的旅行者。推動此項公益事務(wù)的鄉(xiāng)紳,既是出資最多者,也是組織者,他們這樣做一方面是出于對本村族人的關(guān)心和同鄉(xiāng)情誼,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了他們提高自身社會聲望、樹立有德形象的訴求。這些鄉(xiāng)紳憑依自己的身份和能力,出資出力,積極參與公共事務(wù),造福地方,為村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表現(xiàn)出一定的責(zé)任擔(dān)當(dāng),也使他們在鄉(xiāng)間的社會聲望和地位得到提高。將修砌公共性工程之事鐫刻于交通路線一側(cè)的摩崖上,傳之久遠(yuǎn),不僅使本村村民世代知曉,也使途經(jīng)上甘棠村的游宦、商賈、小民等皆能看到這些石刻,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公共性工程除了方便百姓,還具有了更重要的道德標(biāo)識作用。也就是說,因致力于鄉(xiāng)村義事而獲得社會聲望的鄉(xiāng)紳,經(jīng)由摩崖石刻這樣具體的物化形態(tài)敘述出來,就使得他們成為當(dāng)?shù)匕傩兆鹁础⑿Хǖ膶ο螅瑥亩欣谛纬沙绲隆裆频拿耧L(fēng),這也是中國古代鄉(xiāng)村宗族得以長期延續(xù)的重要精神內(nèi)核。
四、結(jié)語
上甘棠村的石刻敘事展現(xiàn)了明代鄉(xiāng)村的諸多特征,使我們看到內(nèi)陸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對于明代目不識丁、生活范圍狹窄的鄉(xiāng)村百姓而言,生存永遠(yuǎn)是第一要義,其次才是精神追求。因此,鄉(xiāng)紳必須以滿足村民現(xiàn)實利益需求的行為引領(lǐng)百姓,比如保障村民安全重修靈驗的寺廟和道觀,修筑道路和橋梁等,這樣才能獲得村民的認(rèn)同和尊敬。從鄉(xiāng)紳的角度看,僅止于此顯然是不夠的,他們需要以勒石記之永存的敘事方式,稱頌有功于本村的地方官,歌詠鄉(xiāng)村美景,贊譽公共性工程的修砌。這些人物和事件本身所包含的知恩圖報、崇尚文教、仁愛至善、造福鄉(xiāng)里等道德條目,是儒釋道三家合流在民間的表現(xiàn),也是鄉(xiāng)紳著意倡導(dǎo)的鄉(xiāng)村精神生活的主要內(nèi)容。村民在崇祀神祇、行路過橋、耕種田里等日常生活和勞作中,在吟詠石刻文獻(xiàn)的行為中,不知不覺就會受到摩崖石刻敘述的人物和事件的影響,自覺將這些道德條目融入日常言行。總之,摩崖石刻敘事將有形的人物、景觀、事件轉(zhuǎn)化為鄉(xiāng)村的精神內(nèi)核,正是由于有了這些精神內(nèi)核,如上甘棠村一樣的古代鄉(xiāng)村,才有可能存在數(shù)百年乃至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