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的詩藝之環:走向《四個四重奏》
談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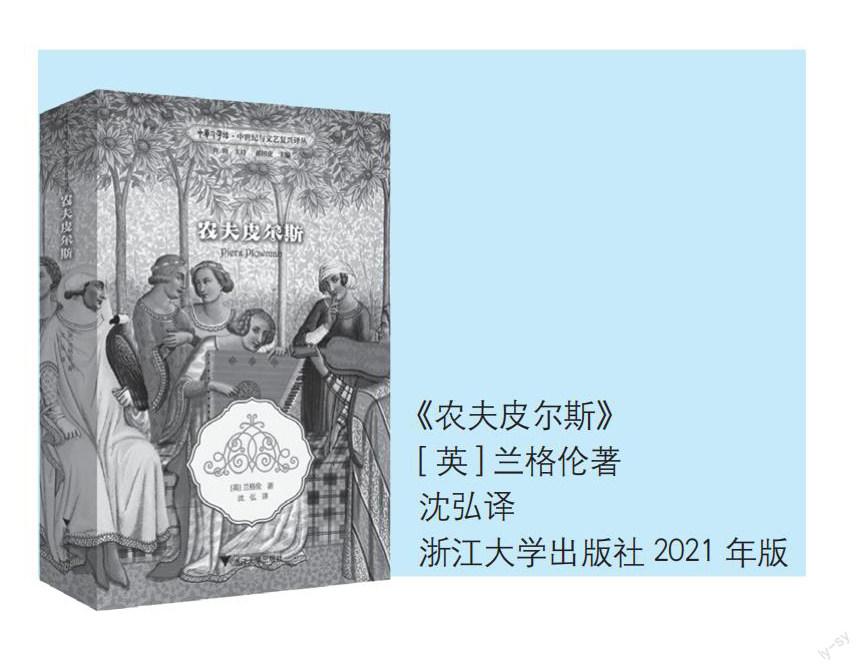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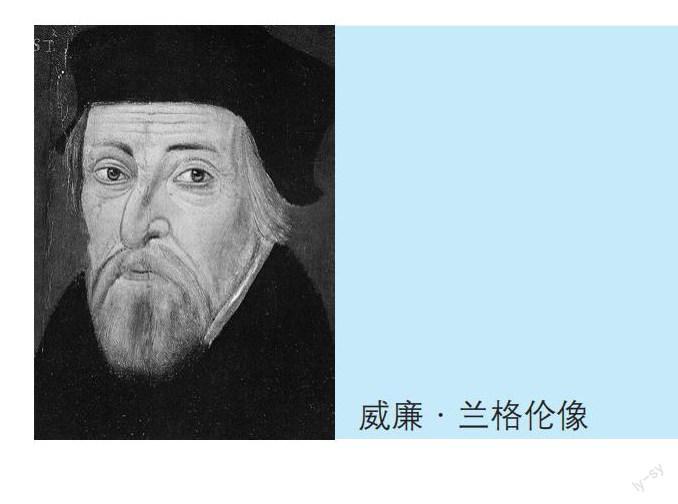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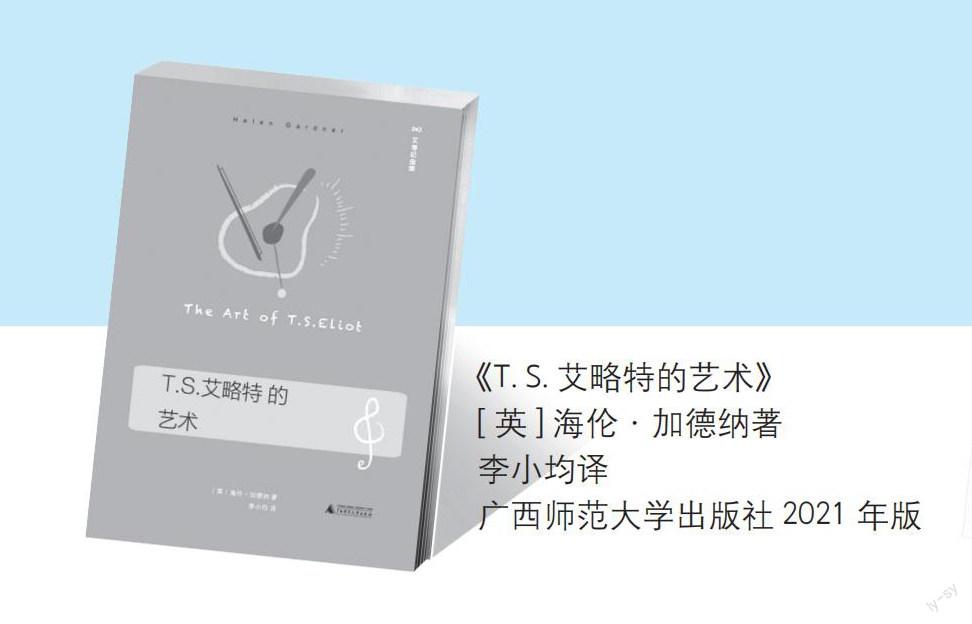
無疑,T. S. 艾略特(1888-1965)其詩其文,在英語現代詩的發展中,占據著極為關鍵的位置。他之于英語現代詩的重要性,在于他總是能發現一種清晰的理論公式,并將它貫徹到自己的寫作中去:他的評論打碎了喬治時代失去革命性的浪漫主義綿軟如肥皂泡的風格,又引入了一種嶄新的、知覺化的感受力,取代慵懶而模糊的無身體的韻律。《荒原》《傳統與個人才能》,客觀對應物、感性的分離,他的詩歌與理論被迅速納入經典化的過程,并造成現代文學評價標準的板塊漂移:由于玄學派板塊的擠壓,鄧恩從枯燥、抽象的詩歌盆地隆起為難度等級極高的山峰,雪萊、彌爾頓卻經歷著一次次地震,成為一種需要被克服的痼疾。而關于艾略特的詩歌與理論的論述,又仿佛形成了新的、伸出文學大陸的“半島”,逐漸有了自己的水系、地勢與氣候。在艾略特的第二故鄉英國,他的受歡迎程度僅次于莎士比亞。
同時代性的書寫
英國文學評論家海倫·加德納(Helen Gardner,1908-1986)所著《T. S. 艾略特的藝術》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對艾略特詩歌的即時觀察。該書初版于一九四九年,其淵源則是作者于一九四二年寫作的《艾略特最近的詩歌》一文。不同于大多數此類著作,加德納是以《四個四重奏》為論述中心的。
評論同時代的文本是大概最適用于新批評的方法,把文本當成一種完善的晶狀結構,而不借助外部的歷史、社會與傳記材料來稀釋它的文學性。此書出版時,距離艾略特完成最后一首四重奏《小吉丁》不過七年(其余三首,《燃毀的諾頓》1935年,《東庫克》1940年,《干塞爾維其斯》1941年)。《四個四重奏》所書寫的內容,還沒有徹底地熔鑄成某種公共經驗,它依然把那些個人性的書寫附在詞的羽翼下,它所提及的事物依然是當下的,所以既鮮活,又常被忽視。人們傾向于認為當代的文本是松軟的、浸過水又沾上現實塵埃的海綿拖把,只有當它被閑置已久,現實的塵埃逐漸讓它變硬、難以使用時,讀者與評論家們才愿意反復地擠壓文本的海綿柱,以恢復它在歷史中原本的柔韌與自然。但同時代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產生一種深刻的“同時代性”,正是因為它完全是“不合時宜的”。讀者常常會把同時代性理解為書寫新聞事件,這些看似合時宜的作品,就像報紙上尋常的新聞攝影,是將信息壓縮在圖像的連接、斷裂與皺褶中的,而圖像本身卻并沒有從其中流溢出來。我們只是在讀,把圖像讀成另一種文字,但我們的眼睛與耳朵并沒有為它打開。詩歌不服從于一般新聞寫作所要求的純粹工具性,它要求全部知覺的介入,可以成為圖像,那非文字的圖像。在艾略特那里,詩歌在文字成為非文字的地方成立。
例如他在《小吉丁》中寫到德軍對英國的轟炸,便是把歷史事件上升為關于本質經驗的沉思。他的升華沒有讓詩喪失具體性,當他將德國轟炸機比作“黑色的鴿子吐著閃亮的舌頭”“俯沖的鴿子以白熾的/恐懼之焰劃破天空”,他并沒有取消這一事件的復雜性;相反,他勾勒出它令我們恐懼的地方,即在絕對惡的籠罩下,人類之言說的艱難。轟炸機作為“現代圣靈”,是那種技術力量的象征。與之對應的,在《干塞爾維其斯》中,密蘇里河成了“強壯的、棕色的神”,不論圣靈還是神,它們都有超出于人性之上的權能。但人正是因為自信于可以把控機器非人性的破壞力,才會崇拜作為絕對的進步神話之具象化的機器。圣靈可以與人相切磋,它落到你的肩膀上,是這樣的一個時刻:你感到自己強烈地與世界聯系在一起,就像電路板上一個小小的電路,因為共同的電的通過而震顫,你看到太陽的第一束光,啄破了地平線,你的皮膚上有露水的味道。但我們的現代圣靈絕非如此,一旦它與你發生聯系,你必須伏臥于地如一條被曬干的蚯蚓。
艾略特用鴿子象征圣靈,這個意象第一次出現在《小吉丁》的第八十到一百五十一行。這一大段詩歌模仿了但丁的《神曲》,無論形式上還是內容上。詩句以三行作為一個單位向前緩步推進,空襲過后,黎明之前,詩人在巡邏路上走著,他遇到了逝去詩人(主要指葉芝與喬納森·斯威夫特)的鬼魂,那些大師教導他“既然我們的關注是言語,言語逼迫我們/使部落的方言純凈”,而在災異之中,灰燼之下,保持語言的純凈幾乎成為一種英雄主義。加德納認為,在《四個四重奏》中,艾略特成功地抵制了把這首長詩寫成自傳的誘惑。他為英語發明了真正的頌詩,英語讀者無法適應品達式的精致韻律的甜膩,也無法容忍布滿水密隔艙的日記體長詩,這種長詩結構松散,每一段都可以被淹沒、被舍棄。頌詩對當下經驗的處理不同于日記或自傳:“日記可以給我們進步感和成長感,但沒有內含于開始之中的終結感,而是必然的成長感;日記有敘事的興趣,卻沒有情節帶來的深層次愉悅。”每一段日記都是攀著海藻、裝載著貨品的水密隔艙,它沉入我們海水一般苦澀的日常,在其中遲緩而猶疑地移動。日記依照一個給定的航線行走,這航線像珍珠項鏈一樣把一個個終點串在一起,因為它隨時可以停下,所以在這條線上,每個點都是將來時的終點,這樣的書寫也無所謂頌詩需要的嚴謹結構了。
身體的語言
或許我們可以想象一位活在十四世紀的艾略特。他必定要在一個鄉村小教堂,用結結巴巴的羽毛筆蘸上失聰的黑色,一絲不茍地勾勒那些堅固如羅馬柱的花體字。那個世界被同一種語言、同一種知識型聯結在一起。我們所設想的這個不為人知的神父艾略特,可以用詩人艾略特的幾句即興詩來描述:“遇到艾略特多不愉快!/他的容貌是一副教士氣派,/他的額角這樣肅穆嚴峻,/他的嘴巴這樣一本正經”。如果神父艾略特為了緩解一下抄經的疲倦,或許想要反芻自己的經院哲學作些詩的話,他會發現拉丁語是一件稱手的工具,而他所使用的詞語與象征早已盡善盡美,仿佛一張嚴謹的密碼表,可以將思想轉寫為圖像與韻律。他也不必考慮讀者,因為所有能讀懂拉丁文的讀者都欣然接受這一套語言系統。
但正如詩人艾略詩在《宗教和文學》一文中論述的,對于現代讀者,宗教詩歌是次要的:“宗教詩人并不是用宗教精神來處理全部詩歌題材的一位詩人,而是只處理全部詩歌題材中一個有局限性的部分的一位詩人:這位詩人排除了人們通常認為是人類特性的一些主要激情,因此也就承認了他對這些激情的無知。”艾略特不相信在剝離其使用價值后,文字可以單獨獲得價值。當然,他并不認為我們不能純粹欣賞一部科學或哲學著作的文風,但對語言欣賞的濫用會磨損我們對這些經典作品真正力量的感受。如果欽定本《圣經》僅僅被當成英語散文作品,它就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的象征系統,且對英國文學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欽定本《圣經》就像金礦,有的人找到了礦脈,于是成為經典的一部分,有的人覓得一身灰塵,讓語言也布滿了灰塵。但這一切悲喜劇的源頭都在于這文本被當成了金礦,當成神的話語本身。現代文學的語言危機就在于—依艾略特之見—當《圣經》被當成文學討論后,就像我們把金礦當成了一座布滿了鉆孔的白蟻巢,那些金子,那些神圣的光輝消逝了,其文學影響也就此終結。
作為宗教信徒和保守主義者的艾略特,顯然不欣賞現代文學批評分食《圣經》的倒影的嘗試。一九二七年,艾略特加入英國國教,并入了英國籍。三年后他發表的《灰星期三》便因為宗教體驗的進入而體現出與包括《荒原》在內的前期詩歌在風格上的差異。加德納注意到,艾略特前期詩歌晦澀、濃縮,緊繃如鍛煉過度的肌肉。《灰星期三》卻有著咒語一樣的節奏,圍繞著個別詩句不停打轉。艾略特的前期詩歌習慣于編織嗅覺與味覺體驗。與視覺不同,嗅覺與味覺較少被詩人們注意到。因為相比視覺,嗅覺與味覺更加切近身體,它們有著綿密的連續感與厚度,仿佛充盈于我們血液的一種氣息。視覺可以直接榨出意義,納入思維的過程,嗅覺與味覺除了表征它們自己以外,并不與形而上直接相關。當我們說“森林”,我們看到的是一派濃稠得無法進入的綠色,聽到的是風撥動牙刷軟毛的錚錚,是搖落的水珠與落葉,是鳥從齒輪般咬合在一起的陰影中沖出,這幅景象可以輕易地上升為象征:在人生的森林中我們總是迷惘。但當我們以嗅覺與味覺的方式去感受一片“森林”,我們聞到松林與露珠的清香,落葉發酵后的臭味,我們想象著我們如何咀嚼森林中淡藍色的氧氣。這樣的感覺幾乎完全服從外在環境,我們的知性難以為嗅覺與味覺披掛上一身意義的勛章。正因如此,艾略特前期詩歌中的嗅覺意象,完全不追求意義上的升華,他采用這些意象,旨在拓下陳腐而令人厭煩的世界的一個碎片。譬如《序曲》中的這些句子,“走廊里一股炸牛排的味兒”“早晨開始意識到/踩滿鋸屑的街上傳來的/微微走了氣的啤酒味兒”。這些嗅覺意象是人造的、庸常的,它同時關聯著味覺,但也只喚起某種乏味的味覺。
《T. S. 艾略特的藝術》引述了艾略特對阿諾德“沒人能否認詩人的特權是書寫一個美的世界”這一言論的評價。在艾略特看來,詩人本質上的特權,不在于那個被意識形態的糖漿層層包裹的“美”,而是“能夠看到美與丑的底層,在于看到厭煩,以及恐怖,以及光榮”。加德納認為正是“厭煩、恐怖以及光榮”構成了前期艾略特與基督徒艾略特的統一性。嗅覺與味覺的意象當然不可能變成那種尖銳的恐怖,它們四處彌散,給人以溫水煮青蛙的窒息感。但恐怖要求一種對生活本質的洞察,厭煩至多是恐怖所垂下的陰影。從前期詩歌到《荒原》,恐怖逐漸成為他詩中的主角,隨著那個皈依時刻的到來,恐怖背后的光榮遂構成了《四個四重奏》。
詩劇與戲劇詩
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中完成了他在《灰星期三》里開啟的探索。這位時刻需要為自己的晦澀辯護的詩人,想要找到一種具有普適的可理解性,可以穿透階級隔膜發揮其效用的語言:在拉丁中世紀曾經有過這樣的語言,它如同連接作者與讀者的臍帶,不倦地溝通彼此。海倫·加德納將《灰星期三》與《四個四重奏》和蘭格倫的《農夫皮爾斯》對比。威廉·蘭格倫(William Langland,1330-1400)生活在十四世紀,生前是一名默默無聞的小牧師(甚至由于位階較低,無法享受圣俸)。研究者認為蘭格倫可能在大馬爾文修道院接受了完整的神學教育。加德納在《T. S. 艾略特的藝術》中多處提及蘭格倫:盡管與喬叟相比,蘭格倫沿用了舊的頭韻詩形式,他的語言也沒有在英語文學中留下持久的印記;從一五六一年到一八一三年,他的作品再沒有重印,關于他的研究也停滯不前,但他的《農夫皮爾斯》仍是英語詩歌中最富想象力的作品之一。如果我們想象中的神父艾略特學會了寫詩,他也許就會成為語言更強勁的威廉·蘭格倫;如果蘭格倫生活在艾略特的時代,他或許也會寫出《灰星期三》那樣的作品。
在《灰星期三》中,艾略特幾乎完全置換了自己的意象系統:玫瑰、花園、珍珠獨角獸、白色的蜥蜴取代了頭發中的紙帶子、阿伽門農尸體上的鳥糞。他依然熱衷于用典,只不過這次集中于《圣經》與《神曲》。在這首詩中,更多時候艾略特并不停留在特定的意象上,與其讓讀者沉溺于對意象美學質感的咀嚼,不如讓意象服從于主題,因為對于皈依者艾略特來說,這主題具有極端的重要性。不過,《灰星期三》并不是一次成功的嘗試。但這對于蘭格倫,則是一種慣習的手法:用《圣經》語言標示思維的路徑,直接使用宗教意象表達思想。這在艾略特的時代已經失去了理解基礎,而蘭格倫由于被迫下沉至生活的底部—他與妻女居住在康希爾的小木屋,靠為贊助人祈禱賺取報酬—所以他的語言在他所生活的年代擁有了艾略特追求的普適性。他不像宮廷詩人,為少數幾個王公貴族寫作,他的讀者是那些布道文的聽眾,其中既有小商小販,又有馬夫農民。所以《農夫皮爾斯》采用了一種混雜的語體風格,其中既有粗淺的俗詞俚語,又有文雅的雄辯,既有琥珀般散發神圣光澤的詩句,又有鄉野村夫們泥濘的口音。
對普適性語言的追求把艾略特導向了詩劇的創作。他的前期詩歌有戲劇詩的特點,即他會通過一些人格面具來說話,并且會有一個極為精巧的舞臺背景內嵌于詩行中。譬如《杰·阿爾弗萊特·普魯弗洛克的情歌》(以下簡稱《情歌》)這首名詩,雖然是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述的,但這聲音非常明確地屬于一個異于作者的說話人,作者與說話人保持著反諷的距離,類似于劇作家與劇中角色的距離。我們跟隨普魯弗洛克穿行于黃昏的城市中,《情歌》展開的背景,對于一首中等篇幅的詩來說,是一個非常廣闊的背景:從廉價小客店到上流社會的沙龍,從黃昏到夜晚。《情歌》不僅在現實空間中展開,它還打開了一個經典與神話的空間:普魯弗洛克將自己與《圣經》中的先知約翰、哈姆雷特王子等對照,以一種否定的方式確定自己的位置—“盡管我已經看見我的頭顱(稍微有點禿了)給放在盤子里端了進來”“不!我不是哈姆雷特王子,也不想成為王子;/我是侍從大臣,一個適合給帝王公侯出游/炫耀威風的人,發一兩次脾氣,/向王子提點忠告;毫無疑問,是個隨和的爪牙”。
但詩劇與戲劇詩的文體特質畢竟大不相同。在現代,詩歌常常被當成一種案頭文學;而詩劇,它既是詩的,也是戲劇的。如果詩劇中的句子因過度的典故、修辭而板滯,就像沒有蓋蓋子的液體膠,滲出來的過多的意義凝固住了,使得它不再可以被使用,那么它就不是戲劇的;同樣,如果它沒有像飛過水面的瓦片一樣在觀眾的心靈上輕輕點上幾下,那么它就不是詩的。而要打出最多的水漂,語言的瓦片就不能太厚重,同時,劇作者讓語言打向我們心靈的水面時的角度以及他與水面的距離也很重要。戲劇語言需要即時讓觀眾理解:它必須產生意義。
這里,我們應該審思一下戲劇中的意義與詩歌中的意義的差別。一個詞,它連接了聲音與符號,我們把聲音與符號這些語言的外殼稱為能指,把詞所指的概念稱為所指。所指與能指并非嚴絲合縫地一一對應,而是系于一長串永無休止的能指鏈條:它可以根據聯想的原則無限延伸。譬如,說到“衣架”時,我們由它聯想到“衣服”,由“衣服”到“洗衣機”,由“洗衣機”到“洗衣液”,由“洗衣液”到生產洗衣液的“車間”,由“車間”到“勞資關系”,由“勞資關系”到“資本論”,所以,“衣架”這個所指上不僅能掛衣服,也能掛上整個世界。不存在固定的意義,意義是我們觀察能指鏈條時所處的位置。在一則軼事中,當有人問起艾略特他的幾行詩的意思時,他把這幾行詩又讀了一遍。我們大概會覺得艾略特在刻意地沉默,逃避對詩的闡釋,事實上,他更有可能是在提醒讀者詩歌在能指層面的效用。詩歌有時會處在德里達式的“延異”中;戲劇,卻要更逼近所指,它必須對觀眾有所表達,也對觀眾的回應有所期待。戲劇正是在觀看與被觀看中產生的一系列動作與言語的扭結。
走向《四個四重奏》
在《T. S. 艾略特的藝術》出版時的一九四九年,艾略特才剛剛開始了他的戲劇實驗,完成了《斗士斯威尼》的兩個片段,以及《大教堂兇殺案》和《家庭團聚》。很難從舞臺的角度考慮這些戲劇,加德納羅列了這些戲劇在技術上的缺陷:“提示部分過于笨拙,動機不足或不可信,明顯依靠巧合。”但她堅持認為,這些作品是“十七世紀以降最好的英語戲劇詩”。當然這里我們主要把這些戲劇當成以對話形式寫作的詩歌。
《大教堂兇殺案》中并不存在人物,存在的只是觀念的器皿。這出戲劇幾乎是靜態的,艾略特以埃斯庫羅斯早期戲劇為模板,觀眾看不出謀殺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的那些騎士的心態變化。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與互動造成的戲劇性讓位于人與觀念的聯系。這出戲劇真正動人的地方在于合唱曲的運用。合唱消解了“我”的存在,只留下“我們”這樣一個單一的巨大聲部,它需要配合既定的音樂,用語詞填充音樂的存在,隨著音樂的起降而改變它的銳度與亮度。艾略特為《磐石》劇本(《磐石》由倫敦主教區下轄四十五教堂基金會委托創作,1934年5月28日至6月9日于馬具匠之井劇院演出)所寫的合唱詞,是他第一次嘗試這種言說方式。與《大教堂兇殺案》一樣,這些合唱詞有強烈的應制色彩,磐石的典故出自耶穌登山寶訓中的磐石之喻,所以,這出劇與《大教堂兇殺案》一樣,是一出宗教劇,是以舞臺的形式進行布道的嘗試。
一九六八年,《T. S. 艾略特的藝術》第六次重印時,海倫·加德納介紹了艾略特創作《四個四重奏》的因緣—在接受作者訪談時,艾略特以他慣常的謙遜談到了自己創作《燃毀的諾頓》的經過:“《燃毀的諾頓》取自《大教堂兇殺案》的‘一點兒余料’,他覺得‘浪費了太可惜’,于是就把這‘一點兒余料’和《愛麗絲漫游奇境記》的開頭以及一個周日去燃毀的諾頓的一處花園閑觀‘攪拌在一起’。”因為其強大的語言能量,《大教堂兇殺案》沒有成為一出真正的現代詩劇,古典戲劇強調情節,現代戲劇更強調劇場的存在,艾略特的詩劇不在這兩者的行列。但也正因為創作詩劇的嘗試,艾略特真正地找到了一種有普適效應的語言,不再依賴神話的構型,不再要求讀者諳習諸多潛文本。他直接與他的讀者對話,不臣服于自傳性的書寫,以自傳性稀釋理解的難度。可以被自傳性稀釋的難度,本身就是可疑的,就像濃霧,當我們置身其中時,就會發現它們只是一些稀疏的水珠。《四個四重奏》本身是有難度的,它的難度不是作者刻意制造的難度,而是因為語言的鞘中,那把觀念的劍有時鋒利,有時銹跡斑斑,有時甚至在懷疑論中打結。
但《四個四重奏》最終完成了艾略特的詩歌創作:不僅僅在于它完全擺脫了英語詩中“英雄詩體”的強力傳統,還在于它重新找回了那種充滿可能性的語言—一種超越階級的現代經驗可以在這語言中棲居。與蘭格倫不同,《四個四重奏》不再能依賴于一個固定的象征系統與知識、教育體系。它只能在自反性中反復提純語言本身的存在,語言有時徑直變成音樂,有時變成一種即將到來的東西:“每首詩都是一則墓志銘。”它拓下我們生命中的一部分,當拓包在石碑上敲擊,我們看到那些筆畫:時間的一小塊碎骨,在我們的注視下成型。承載這些詞語的紙,常常是過于脆薄了,它會在陽光照射下破裂,變成一地語言的皮屑。制作一張詞的拓片需要耐心、柔韌與持久的練習。但我們拓印下來的詞語從來不是那鏤在石頭上的永恒的詞語本身,只是復本。就算大詩人,也僅僅是在拓印永恒,他們每個人都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一塊石碑。可惜的是,更多的詩人,或者說絕大多數詩人,只是把大詩人制作的拓片拍攝下來而已。
在完成了《四個四重奏》后,沉默成了艾略特的最后一首詩。《T. S. 艾略特的藝術》再版時,加德納也沒有再往書中加入關于艾略特新作的內容。這本書呈現的那個大詩人已在《四個四重奏》中達到頂峰,而這本書同樣以《四個四重奏》為討論的起點和終點。因著這一份即時的批評,文學界得以把握艾略特詩藝的環狀結構,仿佛他在《四個四重奏》開頭所引述的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上升的路與下降的路是同一條路。”我們走完了那上升的路,我們看到《四個四重奏》成為語言指環上的那顆鉆石,后世的詩人一遍遍地擦亮它,回到它,乞求那純凈的語言與對語言的意識重臨于我們的詩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