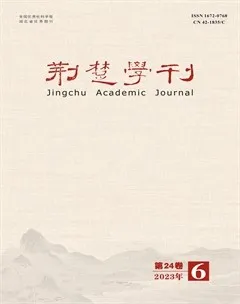北朝時期民居綠化探析
趙延旭
(河北工程大學 文法學院,河北 邯鄲 056038)
《周易·系辭下》載:“上古穴居而野處,后世圣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1]610自古以來,人類對于居處環(huán)境改善的步伐從未停止,除居住地點、建筑規(guī)模、空間格局的調整外,綠化美觀也是重要方面。北朝時期民居綠化現(xiàn)象極為盛行,對于隋唐及后世民居建設具有重要的影響, 與此同時,民居綠化的流行,與時人的信仰觀念、林業(yè)技術、社會生活等密切相關。 因此,研究北朝時期民居綠化的類型、原因及影響等相關問題,對于深入了解此時的建筑史、思想史、技術史與社會史等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長期以來, 關于古代綠化問題的研究多側重于城市綠化,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馬軍山《中國古代城市綠化概況及手法初探》、司艷宇《淺析北宋東京城綠化成就與特色》、祁昭《揚州歷史城市綠化與格局》等,或從宏觀層面對古代城市綠化的發(fā)展狀況進行系統(tǒng)闡述,或立足特定時期、特定城市,從微觀層面對其綠化問題展開論述, 而針對北朝時期民居綠化問題尚無系統(tǒng)和深入的研究。 有鑒于此, 本文擬從北朝時期民居綠化的基本類型、 綠化流行的主要原因及其產(chǎn)生的積極影響等方面展開論述, 以期對相關問題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民居綠化的基本類型
關于“民居“一詞的定義,學界尚無統(tǒng)一的界定。陸錫興《中國古代器物大詞典·建筑》將其定義為“平民居住之所,不包括王府、官邸等”[2]334,是在居住群體的層面對民居進行限定,而閻瑛《傳統(tǒng)民居藝術》指出民居包括“民宅、聚落及周圍環(huán)境(村鎮(zhèn)、街坊、里巷)、橋、亭牌坊、寺廟、祠堂、陵墓、塔和店鋪等”[3]1,則是對民居空間范圍的劃分。 綜合諸說,本文所述民居可以概括為民眾所居,包含住宅以及由其延伸的居住環(huán)境的特定空間。因此,依據(jù)北朝時期民居綠化的地點、 形式以及栽植樹種的差異,可具體劃分為庭院綠化、園林綠化、公共綠化等基本類型。
(一)庭院綠化
傳統(tǒng)民居大體可以劃分為院落式、 樓居式和穴居式三類,其中,院落式民居興起于秦漢,是古代最為常見的民居形態(tài),在“漢民族聚集的地區(qū)以及漢文化交流密切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 少數(shù)民族中比較發(fā)達的部分地區(qū)、 與漢民族混雜而居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 都普遍采用院落式民居”[4]4。北魏道武帝立國之初,即頒行“分土定居,不聽遷徙”[5]1812詔令,鮮卑部民開始定居生活,一改逐水草而居的流徙狀態(tài),及至孝文帝時期,積極實行漢化改革,除政治經(jīng)濟制度外,衣服、飲食,爰及居室等亦效仿漢人之法,自此,院落式民居成為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民居形態(tài)。
庭院作為院落式民居的主體, 其內(nèi)部綠化也成為民居綠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即所謂“庭樹”,早在漢代便有“庭中有奇樹,綠葉發(fā)華滋”[6]20之語,可知庭樹栽植的傳統(tǒng)由來已久, 北朝時期關于此類樹木栽植的記載屢見不鮮。 《魏書·崔光附崔鴻傳》載:“(延昌)四年,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5]1502,《北齊書·方伎傳》亦載“武衛(wèi)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于庭樹”[7]680,可見庭院綠化較為盛行。 具體而言,此時庭院內(nèi)部樹木的栽植,主要分布區(qū)域為庭前與屋舍周圍。
北朝時期,庭前所植樹木有桐、梨、槐等。 據(jù)《齊民要術》所載,青桐“明年三月中,移植于廳齋之前,華凈妍雅,極為可愛”[8]356,即桐樹在幼齡期移植到庭前,造型雅致可愛。 梨樹“園中者,用旁枝;庭前者,中心。 旁枝,樹下易收;中心,上聳不妨。”[8]288梨樹嫁接庭前時,應選擇中心枝條,以利其挺拔高聳, 可見外形和高度是庭前綠化樹種選擇的主要標準,因此,其他樹形優(yōu)美、姿態(tài)挺拔的樹木也常見于庭前,庾信所言“槐庭垂綠穗,蓮浦落紅衣”[9]200,槐樹亦為庭前綠化樹種。 相較而言,屋舍周圍所植樹木則較為整齊一致,正如《齊民要術》引《雜五行書》所載:“舍南種棗九株”[8]264,“舍東 種 白 楊、 茱 萸 三 根”[8]312,“舍 西 種 梓 楸 各 五根”[8]354,對于屋舍南、東、西三個方位所宜植樹木及數(shù)量均有詳細記載, 看似刻板, 然而成書于當時,且以“采捃經(jīng)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8]18著稱的《齊民要術》,其中關于民居綠化的相關記述當較為可信。
(二)園林綠化
北朝時期是中國古典園林發(fā)展的重要階段,在社會物質財富增加、隱逸文化發(fā)展、渴望親近自然等多重因素的推動下,私家園林大量出現(xiàn),史載其時“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饒,爭修園宅,互相夸競。 崇門豐室,洞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樹,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桃李夏綠,竹柏冬青。”[10]206此種競奢之風逐漸在社會蔓延開來,漸及漢族官僚、富商乃至平民,也多熱衷于住宅內(nèi)外修筑私園,且均在植物景觀的布置上頗為留意, 如京兆人杜子休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疏”[10]89,夏侯道遷之園“殖列蔬果”[5]158。 因此,園林綠化亦為民居綠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主要包括園內(nèi)林木栽植與園籬構置。
北朝時期,園林內(nèi)部所植樹木品種繁多,涵蓋了果木、喬木、竹等諸多類型。 果木是園林之中最為常見的植物,庾信小園之中“梨桃百余樹”[9]22,及至收獲“棗酸梨酢,桃榹李薁”[9]25,可見其間果木之豐。除果木外,庾信之園亦有“榆柳三兩行”[9]22,不惟如此,通過“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9]22的描述,足見小園之中的植物綠化儼然已經(jīng)超越建筑,成為其中最為顯著的景觀。 此外,桐、竹等亦多見于園林之中,即所謂“舊竹侵行徑,新桐亦幾圍。 ”[9]189與此同時,園林綠化植物的栽種方位也相對固定,例如榆“種者,宜于園地北畔”[8]338,竹“于園內(nèi)東北角種之”[8]359,這種綠化布局與植物的自然習性密切相關,“榆性扇地, 其陰下五谷不植”[8]338,因而將其栽植于園林北側,“竹性愛向西南引,故于園東北角種之”[8]359,如此布局,則“數(shù)歲之后,自當滿園。 ”[8]359利用竹的自然習性,達到事半功倍的園林綠化效果。
除此之外, 園籬也是北朝時期園林綠化一道獨特的風景。《釋名》:“籬,離也,以柴竹作之,疏離離也。 ”[11]403藩籬最初當為柴竹制作、用于分隔的屏障,《詩經(jīng)》有“折柳樊圃”之語,柳樹亦可為園圃藩籬。北朝時期“園”“籬”始合二為一,“園籬”一詞最早便出現(xiàn)于《齊民要術》之中,并將其置于“栽樹”一卷之首,可見當時對于園籬的重視以及其與園林綠化的關系。北朝時期,柳樹依然是重要的園籬樹種,制作方法較為簡單,“種柳作之者,一尺一樹,初即斜插,插時即編”[8]254。 此外,酸棗樹亦被用于制作園籬,“秋上酸棗熟時, 收, 于壟中穊種之。……至明年春,剶去橫枝,剶必留距。……剶訖,即編為巴籬。 ”[8]254對于構置園籬所植酸棗樹的播種時間、 株距以及編織方法等都有詳細的規(guī)定,除單一樹種的園籬外,此時還出現(xiàn)了榆、柳共同編織而成的園籬,“如其栽榆,與柳斜植,高共人等,然后編之”[8]254,可見當時園籬制作工藝的進步,至于樹種的選擇,多“具有枝葉繁茂、耐修剪、適于在密植條件下生長、 容易繁殖、 耐移植等特點。 ”[12]
(三)公共綠化
公共綠化即居住區(qū)內(nèi)由住宅延伸而來,“供平民百姓活動的區(qū)域,包括城中街道、居住區(qū)的戶外場地、廣場等,也包括可供百姓自由出入寺院”[13]等空間的綠化。 北魏宣武帝“發(fā)畿內(nèi)夫五萬人筑京師三百二十三坊”[5]194,里坊成為城市民眾居住和生活的主要空間, 也是公共空間的主要組成部分,其間除庭院、園林外,亦包括道路與寺院等民眾自由出入的空間,因此,北朝時期公共綠化主要包括道路綠化與寺院綠化。
《國語·周語》載:“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14]76我國行道樹栽植歷史悠久,周朝已注重道路綠化,后世歷代承襲此制,如秦之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 ”[15]2328此后,道路綠化由官修馳道漸及城市內(nèi)部民居區(qū)域的道路,史載前秦時期“長安大街,夾樹楊槐。”[16]2895北朝時期居住區(qū)內(nèi)道路綠化亦十分盛行,以北魏洛陽為例,永寧寺之“四門外,樹以青槐”[10]4,義井里北門外亦“有桑樹數(shù)株,枝條繁茂”[10]52,永和里內(nèi)“楸槐蔭途,桐楊夾植”[10]60,受其影響,遷居北魏的少數(shù)民族和南朝民眾,其所居之處也多重視綠化,如洛陽之歸正、歸德、慕化、慕義四里,其間“附化之民,萬有余家,門巷修列,閶闔填列,青槐蔭途,綠樹垂庭。 ”[10]161里坊之內(nèi)當是一片綠植繁茂、生機盎然的景象,道路綠化樹種多選用桑、槐、楸、桐、楊等高大的喬木。
北朝時期佛教盛行, 寺院作為信徒禮佛的重要場所,其營造也迎來興盛期,史載此時僅洛陽城內(nèi)“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10]349,且多建于里坊之中,如建陽里內(nèi)“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圣、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 ”[10]78寺院成為里坊在空間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故而其間綠化亦為民居綠化的重要形式。 “伽藍之內(nèi),花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披庭”[10]201,綠植繁茂之景可以想見。果木是寺院綠化最為常見的樹種,史載此時“京師寺皆種雜果”[10]158,且其間不乏珍稀品種,報德寺“周回有園,珍果出焉。 有大谷含消梨,重十斤,從樹著地,盡化為水。 ”[10]146白馬寺“柰林葡萄,異于余處,枝葉繁衍,子實甚大。 柰林實重七斤,葡萄實偉于棗,味并殊美,冠于京師。 ”[10]196除此之外,寺院亦多栽植挺拔高大松、竹等,正始寺“眾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 ”[10]99景明寺“房檐之外,皆是山池,竹松蘭芷,垂列階墀。 ”[10]132寶光寺“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 ”[10]199足見寺院綠化極為普遍,植物景觀引人注目。
北朝時期,不僅城市之中民居綠化盛行,即便是遠離城市的村落,亦重視民居的綠化,多有樹木栽植。 庾信《望野》詩中有載“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9]285,可知此時村落周圍有無樹木栽植成為辨識其新舊與否的重要標志, 足以佐證北朝時期村落綠化的盛行。
二、民居綠化流行的原因
通過前文論述可知,北朝時期民居之庭院、園林及公共空間的綠化現(xiàn)象極為盛行, 除民居綠化可帶來直接的經(jīng)濟效益外,究其原因,還緣于以下因素的推動作用。
(一)國家政令
《孟子·梁惠王上》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17]5可知宅地栽植經(jīng)濟林木的傳統(tǒng)由來已久,鑒于宅地植樹的經(jīng)濟效益,歷代帝王多以政令推進其實施,《漢書·食貨志下》 載:“《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15]1180并且對宅地無樹者施以經(jīng)濟處罰。 漢文帝時“詔書數(shù)下,歲勸民種樹”[15]124,景帝亦頒發(fā)詔令,“令郡國務勸農(nóng)桑,益種樹”[15]152,由于此時“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谷”[15]1120,故而樹木栽植多分布于農(nóng)田之外,民居周圍即主要區(qū)域之一。基于此種施政的理念,民居樹木繁盛與否也成為衡量地方官員政績的標準之一,孔子稱贊子路,其三善之一即“入其邑,墻屋完固, 樹木甚茂”[18], 西漢潁川太守黃霸也因“及務耕桑,節(jié)用殖財,種樹畜養(yǎng)”[15]3629,得以列位循吏。宅地樹木的栽植,最初雖緣于經(jīng)濟層面的考量,但客觀上也起到綠化居住環(huán)境的作用。
綜上所述,中藥補腎活血湯聯(lián)合西藥治療早期糖尿病腎病療效確切,促進患者臨床癥狀緩解,控制炎癥反應,減少尿蛋白,值得推廣。
北魏立國, 拓跋鮮卑作為草原部族,“統(tǒng)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yè)”[5]1,其生存和發(fā)展本就與森林草原環(huán)境有著更加密切的聯(lián)系,上自君王,下迄民眾,習于地域遼闊、水草豐美的居住環(huán)境,十分注重綠化,并且,伴隨勢力深入中原地區(qū),逐漸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紛紛效仿中原王朝,重視農(nóng)桑生產(chǎn),因此,北朝帝王也多有保護樹木的詔令頒行,《魏書·道武帝紀》載:“兵之所行,不得傷民桑棗”[5]28,周武帝時亦詔“禁伐樹踐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 ”[19]93此類詔令對于民居綠化起到了積極的保護作用。不惟如此,鼓勵植樹的詔令亦屢見不鮮,如周文帝時“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19]538,提倡和推廣行道樹栽植。國家政令的頒布與實施,成為此時民居綠化盛行重要的外在動力。
(二)林業(yè)技術
民居綠化的盛行也與林業(yè)技術的發(fā)展密不可分。 北朝時期,農(nóng)業(yè)技術集大成之作——《齊民要術》纂輯而成,計十卷,九十二篇,其中第四卷和第五卷主要闡述此時的林業(yè)技術, 占據(jù)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一,可見其時對于林業(yè)生產(chǎn)的重視,通過相關記載可一窺此時林業(yè)技術的發(fā)展全貌。
北朝時期,林業(yè)技術主要涵蓋了樹木的繁殖、撫育、副產(chǎn)品加工,以及氣候災害和生物災害的預防技術等。 這一時期,繼承前人智慧的基礎上,勞動人民在生產(chǎn)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 并將其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 能夠依據(jù)樹木的自然習性和繁殖方式的特點, 確定樹木繁殖過程中具體采用有性方式,抑或扦插、嫁接、壓條、分株等無性方式,借助于最適宜的繁殖方式,加之樹木移栽時機、地點、密度等逐漸科學化,此時樹木的繁殖效率和幼苗成活率得以極大地提高。 此外,樹木的增產(chǎn)、延壽技術也取得了進步,“侯大蠶入簇, 以杖擊其枝間,振去狂花,不打,花繁,不實不成”[8]263,首創(chuàng)了人工疏花技術,以此提高果樹產(chǎn)量。 同時,針對北朝時期氣候寒冷的特點, 為減少霜凍害對樹木的破壞,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明了“熏煙法”,即“常預于園中,往往貯惡草生糞。天雨新晴,北風寒切,是夜必霜。此時放火作禿,少得煙氣,則免于霜矣。”[8]257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科學的管理方法既保證了樹木的成活率, 同時也提高了林副產(chǎn)品的產(chǎn)量, 為民居綠化的盛行提供了充分的技術支持。
(三)傳統(tǒng)觀念
北朝時期民居綠化的盛行也與時人的傳統(tǒng)居住觀念存在關聯(lián)。眾所周知,古代社會的傳統(tǒng)居住觀念對于民居建設具有一定的影響,其中對“植樹方法也非常講究,于種植密度、高度、方位和樹種的選擇等方面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 ”[20]前文所述北朝時期對于屋舍東、南、西三面適宜栽植的樹木品種及數(shù)量的詳細規(guī)定, 恰恰體現(xiàn)了時人在綠化布局方面所受傳統(tǒng)居住觀念的影響。 依據(jù)《齊民要術》所引《雜五行書》的記載,舍東栽植三根白楊和茱萸,可以“增年益壽,除患害也”[8]312,舍南栽植九株棗樹,能夠“辟縣官,宜蠶桑”[8]264,舍西栽植梓樹和楸樹各五根,則起到“子孫孝順,口舌消滅”[8]354的效果。此外,《齊民要術》又引《術》所載:“北方種榆九根,宜蠶桑,田谷好”[8]342,此時屋舍周圍栽植樹木的品種和數(shù)量與個人身體健康、家庭和睦興旺以及農(nóng)桑收成緊密聯(lián)系起來, 時人的傳統(tǒng)居住觀念中, 合理的民居綠化具有趨利避害的特殊功用,所以說,傳統(tǒng)居住觀念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居綠化的實施和規(guī)范。
三、民居綠化的積極影響
北朝時期民居綠化的盛行對于時人生活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具體而言,主要體現(xiàn)在民居綠化不僅改善了時人的生活環(huán)境,同時,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們的物質生活。
(一)生活環(huán)境的改善
北朝時期庭院和園林綠化對于改善時人的居住環(huán)境發(fā)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如前文所述,此時桐、槐等樹形優(yōu)美、姿態(tài)挺拔的樹木栽植于庭前,屋舍周圍環(huán)以桑、梓、楸等高大的喬木,園林之中遍栽果木、喬木、竹等綠植,構成了園林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加之由樹木編織而成的綠籬,“共相蹙迫,交柯錯葉,特似房籠。既圖龍蛇之形,復寫鳥獸之狀,緣勢嵚崎,其貌非一”[8]254,形態(tài)優(yōu)美且富于變化,“非直奸人愆笑而回,狐狼亦自息望而徊。行人見者,莫不嗟嘆,不覺白日西移,遂忘前途尚遠,盤桓瞻矚,久而不能去。”[8]254兼具隔離保衛(wèi)和藝術觀賞的雙重價值, 成為一道獨特、 靚麗的風景, 這些客觀上都起到綠化和美化居住環(huán)境的作用, 展現(xiàn)出一幅充滿生機活力且生活氣息濃郁的場景。
與之相應, 寺院綠化也為時人休閑娛樂活動的開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此時的佛寺日常或定期對公眾開放,其“開放性兼顧園林公共性的功能”[21],寺院成為時人禮佛和休閑的主要場所, 豐富的植物景觀是吸引游人的因素之一,并在此基礎上,催生了一系列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 欣賞寺院美景之余進行創(chuàng)作以抒發(fā)情感,如寶光寺,“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征友命朋,來游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 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為興適。 ”[10]200凝圓寺,“竹柏成林,實是凈行息心之所也。 王公卿士來游觀為五言者,不可勝數(shù)。 ”[10]249足見寺院綠化對于時人休閑娛樂活動的影響。
(二)物質生活的豐富
民居綠化對于時人物質生活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林副產(chǎn)品不僅可以充當代糧食物,同時,也為制作各類生活用具提供了基本原料。 《管子·權修》載:“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 ”[22]14可見栽植樹木的經(jīng)濟效益遠超糧食作物。 北朝時期氣候寒冷,水、旱、霜、雪、凍等氣候災害頻繁爆發(fā),加之與南朝政權及北方民族戰(zhàn)爭連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遭受打擊,糧食作物產(chǎn)量極不穩(wěn)定,饑饉薦臻。 相較于糧食作物,樹木對于土壤和災害的適應性更強,如棗樹,“其阜勞之地, 不任耕稼者, 歷落種棗則任矣”[8]263,榆樹,“唯須一人守護、指揮、處分,既無牛、犁、種子、人功之費,不慮水、旱、風、蟲之災,比之谷田,勞逸萬倍。”[8]342用力少而收效大,樹木成為“五谷”之外重要的栽植對象,林副產(chǎn)品也由此成為糧食的重要補充。 前文所述庭院、園林及道路所植桑樹, 不僅具備美化生活環(huán)境的功能,同時,桑葉可以飼蠶,桑葚“兇年粟少,可以當食”[8]318,至 于 民 居 所 植 的 果 木,果 實 亦 可 成為災年助糧之物, 如杏實 “可賑貧窮, 救饑饉”[8]282,其間部分珍稀品種,如白馬寺之柰實、葡萄,“宮人得之,轉餉親戚,以為奇味,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shù)家。 ”[10]196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時人的飲食生活。
民居綠化也為時人制作各類生活用具提供了基本的原料,小自杯、盤、碗、盞,以及各類家具、樂器,大到房屋、車輛、棺槨,其制作均離不開木制原料。 以園林所植榆樹為例,“十年之后,魁、碗、瓶、榼,器皿,無所不任”[8]342,即成年后枝干砍伐可用于制作各類生活器皿。又如楸樹,“十年后,一樹千錢,柴在外。 車板、盤合、樂器,所在任用。 以為棺材,勝於柏松。”[8]354除用作燃料外,亦可用于制作各類器具,兼具實用價值與經(jīng)濟價值。再如園籬所植各類樹木,“數(shù)年成長,若值巧人,隨便采用,則無事不成,尤宜作機”[8]254,同樣也可作為器具用木。正如《齊民要術》所載“凡為家具者,前件木,皆所宜種。”[8]358足見樹木在時人物質生活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民居綠化則是木料重要來源之一。
北朝時期民居綠化的盛行, 對后世民居建設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及至隋唐時期,沿襲北朝傳統(tǒng), 帝王頒發(fā)詔令鼓勵綠化, 玄宗詔令“兩京道路并種果樹”[23]1346,代宗亦詔“種城內(nèi)六街樹”[24]125, 直接推動了民居區(qū)域的道路綠化,同時更是將樹木保護寫入律法之中,《唐律疏議·雜律》載:“毀伐樹木、稼穡者,準盜論。 ”[25]440在這種政治背景下,唐人多熱衷于民居綠化,這在其時的詩作中多有體現(xiàn),如白居易“栽松滿后院,種柳蔭前墀”,杜甫“平生憩息地,必種數(shù)竿竹”等正是唐人民居綠化盛行的真實寫照。 北朝與隋唐時期民居綠化的盛行, 恰可佐證陳寅恪先生關于隋唐制度淵源之(北)魏、(北)齊一源之論斷,“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fā)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摩仿采用, 傳至北齊成一大集結者是也。 ”[26]4
綜上所述,北朝時期民居綠化極為盛行,樹木栽植遍及庭院、園林及公共空間等區(qū)域,展現(xiàn)了一幅生機勃勃且富于生活氣息的圖景。 此時民居綠化的盛行, 離不開國家政令的頒行與林業(yè)技術的支持,同時,傳統(tǒng)的建筑觀念亦有鼓勵栽植樹木的元素,也對民居綠化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北朝時期民居綠化,不僅改善了時人居住、出行以及休閑娛樂等生活環(huán)境, 而且林副產(chǎn)品也豐富了人們的飲食生活,為各類器物的制作提供了基本的原料。北朝時期民居綠化對后世民居建設產(chǎn)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及至隋唐,民居綠化亦普遍流行,樹木保護和栽植被寫入詔令與律法之中。近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的建設, 提出了建設“美麗鄉(xiāng)村”的發(fā)展理念,村容整潔作為最為外在的展現(xiàn)形式, 如何樹立和打造社會主義新農(nóng)村良好的整體形象,除道路建設及房屋改造外,傳統(tǒng)民居的綠化配置或可為我們打開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