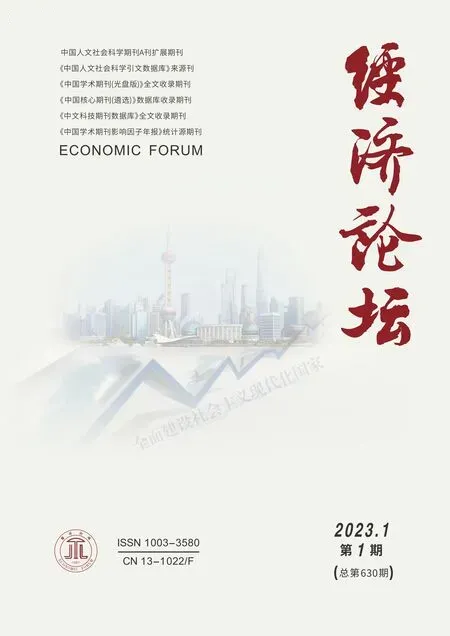異質性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與生態福利績效
——基于中介效應模型的實證檢驗
郭炳南,唐利
(江蘇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江蘇 鎮江 21210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歷經30年的高速增長,已成為全球經濟總量第二的國家。然而,長期傳統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所引發的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嚴重污染,威脅著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生態福利績效是指單位自然消耗所帶來的福利水平提升,用以衡量自然消耗轉化為福利水平的能力,提升生態福利績效有助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污染防治攻堅戰等重大國家戰略的實現,也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福利提升。與此同時,中國正在采取日益嚴格的環境規制政策,并且利用多種政策組合工具,試圖改善環境嚴重污染、資源過度利用等問題,那么,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種影響又是否通過綠色技術創新進行傳導?綠色技術創新在環境規制與生態福利績效之間起著怎樣的中介效應?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對于制定適宜的環境規制政策,誘致綠色技術創新,提升生態福利績效,加快生態文明建設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文獻綜述
隨著經濟增長、民生福祉、生態環境保護之間不協調發展問題的日益突出,眾多學者越來越重視生態福利績效。當前,關于生態福利績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生態福利績效的衡量與測度,Daly(2005)最早采用單位自然消耗所帶來的福祉評估國家可持續發展狀況[1];諸大建等(2014)將生態福利績效表示為人類發展指數與生態足跡的比值[2];付偉等(2014)將生態福利績效表示為人類發展指數與人均生態足跡的比值[3];肖黎明等(2018)采用SFA模型對生態福利績效進行測定[4];龍亮軍(2019)運用兩階段Super-NSBM和DEA模型測度了中國35個主要城市的生態福利績效[5]。二是生態福利績效影響因素及時空特征分析。馮吉芳等(2016)采用LMDI法剖析了省市生態福利績效的影響因素[6];杜成宇等(2019)研究發現影響中國省際生態福利績效的因素有技術進步、綠化程度、社會性支出、醫療水平、城鎮化、產業結構和環境規制等[7];徐昱東等(2017)研究發現中國各省及地區生態福利績效水平在空間上呈現出空間相關性[8];方時嬌等(2020)分析了中國生態福利績效的空間效應[9];郭炳南等(2022)研究了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升級對生態福利績效的影響[10]。
伴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增長,環境污染問題的日益嚴重,環境規制作為保護環境的關鍵手段,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們關于環境規制與經濟績效的關系探討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類觀點支持“波特假說”,認為適當的環境規制能倒逼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并提升生產效率,產生創新補償效應。隨后Jaffe和Palmer(1997)[11]、Hamamoto(2006)[12]、Yang(2012)[13]、李 小 平 等(2017)[14]等學者研究發現環境規制通過創新補償效應,促進了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與擴散。第二類觀點支持“遵循成本假說”,認為環境規制將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成本內部化,增加了企業的研發成本,抑制了企業生產率的提升,不利于企業的創新發展。Collop(1983)研究發現環境規制抑制了企業生產率提升[15];Lanoie等(2011)指出嚴格的環境規制對企業績效產生負面效應[16];蔣伏心等(2013)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增加企業生產成本,抑制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發展[17]。第三類觀點認為環境規制與經濟績效的影響作用存在不確定性。在不同的環境規制工具與強度下,“創新補償”效應和“遵循成本”效應所產生的強度不同。沈能(2012)[18]、原毅軍等(2015)[19]、周海華等(2016)[20]、Yuan(2017)[21]從不同角度研究發現,環境規制對經濟績效的促進作用存在門檻效應。以上文獻主要研究了環境規制對經濟績效的直接影響,少量文獻研究了環境規制如何通過技術創新對綠色經濟產生影響。范丹等(2020)研究發現,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通過激發綠色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綠色經濟發展[22];魏巍等(2020)研究發現環境規制會通過清潔型結構對工業環境效率產生間接影響[23];史敦友(2021)研究發現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工業綠色化的影響存在部分中介效應,通過技術創新“擠出效應”抑制工業綠色化,公眾參與型環境規制對工業綠色化存在中介效應,通過技術創新“激勵效應”促進工業綠色化[24]。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對環境規制以及生態福利績效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尚有以下不足:一是已有文獻重點關注了環境規制與經濟績效的關系研究,缺乏綠色技術創新在環境規制與經濟績效之間的中介銜接作用的研究。二是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作用可能存在差異,但已有文獻缺乏對異質性環境規制的深入分析。在已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一是將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與生態福利績效納入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并基于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效應模型檢驗,考察環境規制如何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對生態福利績效產生影響;二是探究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工具對生態福利績效的差異性影響。
二、研究設計
(一)計量模型
1.面板模型。為檢驗異質性環境規制與生態福利績效的關系,本文首先構建異質性環境規制與生態福利績效的計量模型:

其中,epit為第i個省份在t年的生態福利績效;zyssit和kybtit分別為第i個省份在t年的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Xit代表控制變量集;μ為個體效應,δ為時間效應,ε為隨機擾動項。
2.中介模型。本文基于中介效應模型,引入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中介變量,分析其在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傳導作用。首先分析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影響,如式(1)所示。其次,考慮綠色技術創新、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影響,如式(2)所示。最后分析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考慮到綠色技術創新存在一定的滯后性,本文選擇系統GMM方法進行分析。具體設定方程如下:

將式(1)(2)(3)聯合,形成綠色技術創新作為中介變量關于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影響的檢驗方程組。在該方程組中,ai為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總效應,βi為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直接影響,bi×c為環境規制通過綠色技術進步對生態福利績效的影響效應。若經檢驗中介效應存在,則中介效應等于bi×c,且bi×c ai為中介效應的權重系數。
(二)變量與數據
1.被解釋變量。生態福利績效(ep):本文采用Super-SBM模型,選取9個指標來衡量生態福利績效。其中,投入指標3個(人均用水量、人均建成區面積和人均消耗標準煤);產出指標6個,包括意合產出(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預期壽命和人均GDP)和非意合產出(人均廢水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以及人均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Super-SBM模型如下:
其中,ep為生態福利績效值;sg表示期望產出不足;s-表示投入過多;sb表示非期望產出過度;λ是權重向量。
綠色技術創新(gt):本文借鑒陳曉等(2019)[25]的方法,使用綠色產品創新來衡量綠色技術創新,因為綠色產品創新主要體現在資源節約、能耗降低、污染減少等方面,綠色產品創新指標以新產品單位生產耗能衡量,即能源消耗總量與新產品產值比,對其取對數后再取倒數,即其值越大,綠色技術創新能力越強。
2.解釋變量。資源稅收環境規制工具(zyss)是指在經濟利益刺激下,通過市場的力量影響當事人的環境行為,主要有排污費、稅收、排污權交易等,本文采用資源稅占地方財政收入比衡量;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工具(kybt)采用單位研發補貼比重來衡量,單位研發補貼指RD研發經費中政府補貼額與GDP之比。
3.控制變量。對外開放水平(open),采用進出口總值占GDP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ind),利用第三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pgdp),利用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來衡量;城市綠化水平(gee),利用城市綠化率來衡量。
4.數據來源。本文的樣本區間為2005—2019年間我國30個省、自治區、市(不包含港澳臺地區和西藏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以上所有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年鑒》及EPS數據庫。
(三)描述性統計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從表1中可以看出,樣本期間我國生態福利績效水平較低,均值為0.663;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等變量的標準差反映不同省份之間存在較大差異。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分析
(一)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為了解決異方差和內生性問題,在模型中加入了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從表2回歸結果可知,由于AR(1)、AR(2)和Sargan檢驗均顯著,表明無法拒絕原假設,即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影響的GMM估計結果有效。

表2 異質性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影響的回歸結果
從表2的回歸結果來看,上一期生態福利績效水平對本期生態福利績效的影響顯著為正,表明上一期生態福利績效累積效應可以促進本期生態福利績效。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能促進生態福利績效提升,其中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每增加1單位,促進生態福利績效水平提升0.005個單位,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每增加1單位,促進生態福利績效水平提升0.069單位,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促進作用強于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
(二)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促進作用可能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激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從而作用于生態福利績效。參考溫忠麟等(2004)[26]提出的中介效應檢驗程序,本文進一步檢驗綠色技術創新在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中介傳導作用。
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從總效應來看,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顯著促進了生態福利績效的提升,說明在控制了產業結構、城市綠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等變量后,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總體上促進了生態福利績效水平的提升。從直接效應回歸結果可知,綠色技術創新和資源稅收型以及綠色技術創新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均存在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從間接效應回歸結果可知,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且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大于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

表3 基于綠色技術創新中介效應的回歸結果
從表3的直接效應模型結果可知,可證實中介效應的存在性。基于中介效應檢驗與劃分標準,可計算出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驅動生態福利績效的中介效應,如表4。從綠色技術創新中介效應檢驗結果可知:經Bootstrap法直接檢驗H0:ab=0,檢驗結果顯示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總效應、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顯著為正,說明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存在中介效應,即綠色技術創新“激勵效應”。且中介效應分別占總效應的68.78%和34.54%,說明資源稅收制型環境規制受污染稅和排污比例的影響,在污染排放范圍內,資源稅收制型環境規制通過促進綠色技術進步提升生態福利績效;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受研發補貼的影響,在一定補貼范圍內,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通過促進綠色技術進步提升生態福利績效。

表4 綠色技術創新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異質性環境規制通過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生態福利績效的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對綠色技術創新指標進行替代。借鑒齊紹洲等(2018)研究[27],將替代能源生產類、廢棄物管理類、能源節約類專利作為綠色專利的具體項目,利用每個樣本的上述三項專利申請數相加,并加1后取自然對數,從而作為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度量指標,該值越大,企業綠色創新水平越高。通過中介效應模型可知,總效應與綠色技術創新無關,因此,回歸結果不變,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與綠色技術創新相關,回歸結果見表5。

表5 穩健性檢驗結果
由表5結果可知,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等核心變量顯著性及相關性與上文基本一致。如表6可知,對其進行Bootstrap檢驗,再次驗證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存在中介效應,會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效應”促進生態福利績效,且中介效應占總效應比值分別為34.32%和19.24%,與上述結果無顯著差別。綜上所述,將綠色技術創新進行替代后,異質性環境規制通過綠色技術創新驅動生態福利績效上升的研究結論沒有變化,因此,本文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表6 綠色技術創新中介效應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探討了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影響,并檢驗了綠色技術創新的中介傳導效應。主要研究結論如下:(1)不同類型環境規制工具均促進了生態福利績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的促進作用大于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2)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效應”可以推動生態福利績效提升,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的中介效應大于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3)從間接效應來看,資源稅收型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均激勵了綠色技術創新,且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更強;(4)對綠色技術創新變量進行相關替代之后,上述結論基本沒有變化,即本文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1)充分發揮不同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驅動作用。根據研究結論可知,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和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均促進了生態福利績效的提升,但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生態福利績效的促進作用更強。因此,一方面要發揮財政補貼等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工具的作用,充分激發社會主體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實現綠色技術創新產品數量增加和質量升級;另一方面提供綠色專利資金支持,促進專利數量和質量的同步增長,充分發揮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工具對生態福利績效的促進作用。同時,加強資源稅的執法力度,充分發揮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工具的“倒逼”效應。(2)發揮不同環境規制工具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鑒于科研補貼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更大,政府應合理規劃,監管落實到位,推動通過企業技術創新發揮其學習效應。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激勵作用相對較小,政府應著力完善和落實資源稅收型環境規制政策,通過環境稅、資源稅等手段充分發揮其外部效應。(3)加強對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支持。綠色技術創新對生態福利績效的提升具有“激勵效應”,應加強對綠色技術創新活動的扶持,尤其在財稅政策、政府補貼、研發投入等方面加大對綠色技術創新的支持及投入,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福利增加、環境保護的“三重紅利”,以促進生態福利績效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