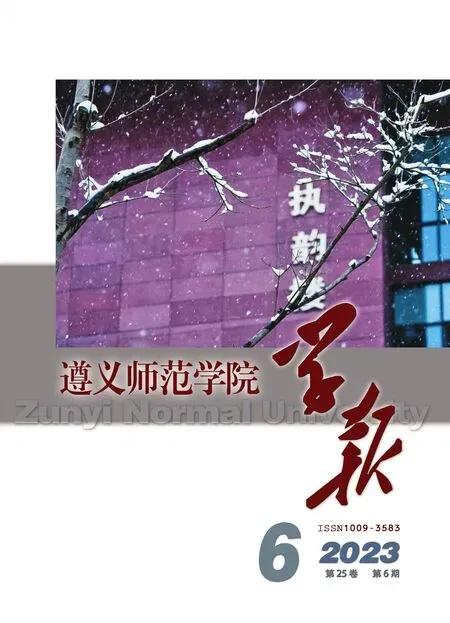《百川東到海》的“文化”書寫
孫建芳,蒲 實(shí)
(1.遵義師范學(xué)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貴州 遵義 563006;2.重慶外語外事學(xué)院,重慶 401120)
鄭欣的長篇小說《百川東到海》以42 萬字的鴻篇巨制,展示了從1919 年至1949 年的歷史畫卷。三十年的風(fēng)云際會,作者借助全能視角,結(jié)合時代背景與地域特色,通過五四運(yùn)動、北伐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重大歷史事件的背景描繪,形象勾勒出那段波瀾壯闊、波詭云譎的歷史煙云。仔細(xì)品讀作品,不但可以了解世紀(jì)風(fēng)云的滄桑巨變、領(lǐng)略鄉(xiāng)風(fēng)民俗的淳樸厚重、感受傳統(tǒng)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可以進(jìn)一步探索“百川東流”的歷史淵源和文化根源,尋求在“大浪淘沙”沖刷中的民族性格與精神品質(zhì)的文化基因及心理動因。
文化是一個多元概念,內(nèi)涵豐富且廣博深邃。作為一部數(shù)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百川東到海》以廣闊的歷史背景、曲折的故事情節(jié)、生動的人物形象,優(yōu)美的語言文字,為我們徐徐開啟了一個勤勞智慧卻災(zāi)難深重民族的“文化”大幕:大氣磅礴的歷史文化、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詩情畫意的語言文化。展卷細(xì)讀,精彩紛呈——櫛風(fēng)沐雨的革命斗爭、大浪淘沙的改朝換代、出生入死的英雄傳奇、一波三折的浪漫愛情、婚喪嫁娶的煙火市井、琴棋書畫的唯美風(fēng)情……濃濃的“文化”氣息撲面而來,如和風(fēng)穿柳、春雨潤物,讓人不知不覺陶醉其中。
一、大氣磅礴的歷史畫卷
《百川東到海》的封底,以高度凝練的文字概括道:“這是一部浪漫、傳奇的革命史詩,以1919-1949年為時間坐標(biāo)建構(gòu)宏大的敘事框架,腐朽黑暗的軍閥統(tǒng)治,風(fēng)雨飄搖的社會時局,人物命運(yùn)一朝顛覆,眾生百相波詭云譎……波瀾壯闊的革命歷史,畫卷徐徐展開。”
都說歷史是一面鏡子,可以透視過去,也可以照見未來。《百川東到海》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二十世紀(jì)上半葉的生動歷史畫卷,幾乎所有的時代重大事件,都被作者款款敘述、娓娓道來。這是大手筆書寫的大時代,正如《人民日報(bào)》的精準(zhǔn)評價:“書寫大時代,需要練就通達(dá)古今、直抵人心的蒼勁筆力。只有守住人民這個‘根’,筆下的人物形象才能是真實(shí)的、現(xiàn)實(shí)的、樸實(shí)的,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真實(shí)鮮活的質(zhì)感。”[1]
江河奔流,泥沙俱下,但是,百川東到海,一路浪淘沙。“身在大潮流中,卻企圖獨(dú)善其身,生在亂世卻期待開辟桃源凈土,又怎么可能,這些年來,中國有識之士堅(jiān)持的各種主義與犧牲,為的早已經(jīng)不是讓哪一股勢力占上風(fēng),最源頭最根本的是為國家和民族的走向和道路。歷史給我們以警示,而只有未來才能證明一切。就好像無論是哪一條河流,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得泥沙俱下。向東流,入大海,才能從入海口的匯入和消失中,獲得真正的永恒的安全。因?yàn)橹挥写蠛2攀怯篮愦嬖诘摹!盵2]P292小說中這段議論兼抒情的文字,可以看作題旨,既點(diǎn)明了作者的創(chuàng)作目的,也概括了作品的主題。
沒有任何文學(xué)作品可以脫離時代而不朽。《百川東到海》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下,精心安排了幾對復(fù)雜的“愛情”線索——羅丹與王中南從激情幼稚到分道揚(yáng)鑣,最終與淳袏志同道合而成為同志愛人;敏之與淳祐從一見傾心到血濃于水的生死相隨;淳袏與惠茗始而甜蜜濃稠終究道不同不相與謀的一拍兩散;蕙茗與王中南彼此貪歡各有所圖利益失衡后的勞燕分飛;當(dāng)然,還有唐炳銓夫婦、孟學(xué)士夫婦舉案齊眉的夫唱婦隨;淳衷與端芬舊式婚姻的貌合神離;淳衷與翠仙、翠仙與奎栗各懷心事的一廂情愿;山口醫(yī)生“男主外女主內(nèi)”嫁雞隨雞的日式婚姻;桃葉“女大三抱金磚”的“小丈夫”婚姻……這些或隱或顯、或詳或略的婚戀關(guān)系,并不局限于才子佳人恩怨情仇的情感糾葛,而是借助個人命運(yùn)的沉浮榮辱展現(xiàn)時代浪潮,否則,小說就會淪為無病呻吟的失敗之作。畢竟,歷史上這類鴛鴦蝴蝶、風(fēng)花雪月的娛人故事數(shù)不勝數(shù),但終究湮沒于時間的洪流,了然無痕。
網(wǎng)上有句被高贊的流行語:時代的一粒灰,壓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沒人可以脫離時代而獨(dú)活,即便是逃進(jìn)深山不食周粟的商朝遺臣伯夷、叔齊,到底也做了時代的犧牲品。滾滾洪流泥沙俱下,革命就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選擇過程,只有烈火才能煉得真金,就如小說主人公之一的羅丹所說:“創(chuàng)造一個新世界,必須打碎這個舊世界,這個過程必是一個流血的過程。這就是我們的道路,為之付出一切而不悔的道路!”[2]P233
可是,動蕩不安的時局,變幻莫測的社會,理想的實(shí)現(xiàn)任重道遠(yuǎn):征途遙遙、歧路漫漫、荊棘密布、暗流洶涌。在某些特殊的歷史關(guān)頭,信仰的坍塌使人類精神大廈土崩瓦解,群體的迷茫和個體的異化,成為一種焦灼不安的時代情緒,同時也成為小說藝術(shù)集中展示的深刻主題。這充分體現(xiàn)在作品的人物形象上:普通群眾、革命者、進(jìn)步者、觀望者、投機(jī)者、叛敵者、隨波逐流者,等等。非常典型的人物有羅丹——集富家小姐、進(jìn)步學(xué)生、時髦青年、頑強(qiáng)戰(zhàn)士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革命者;敏之——看似弱不禁風(fēng)、隱忍退讓的大家閨秀,實(shí)則剛強(qiáng)嫻淑、通情達(dá)理的賢妻良母;惠茗、王中南——一對叛節(jié)蛻變的“精致利己主義者”;淳祐、淳袏兄弟的成長成熟……時代大潮中,此起彼伏的波峰浪谷,清濁難分中的渾水摸魚,縱良莠不齊,神鬼莫測,經(jīng)自然選擇與淘汰,終究大浪淘沙,百煉成鋼。
歷史不容假設(shè)。作為一部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百川東到海》強(qiáng)烈的歷史感撲面而來,其最可寶貴之處,在于它的真實(shí)性。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jì)慈在他的名篇《希臘古甕頌》中有句名言:“美即是真,真即是美。”[3]P126小說除細(xì)節(jié)、環(huán)境、氛圍等的真實(shí)外,還有一種更高的真實(shí),那就是說真話,并用最大熱情描繪心中的理想,人類的共同夢想。
羅曼·羅蘭說:這世界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熱愛生活。敏之與惠茗這對表姊妹的不同人生道路,是個體的選擇,也是時代的選擇,更是命運(yùn)的選擇。羅丹、敏之、淳祐、淳袏兄弟,順境中善待他人,逆境中善待自己,在時代的滾滾洪流中,在革命的烈火淬煉中,堅(jiān)守信仰,堅(jiān)持目標(biāo),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也成就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
二、豐富生動的民俗文化
常言道:十里不同風(fēng),百里不同俗;又說,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民俗的形成有一個漫長的約定俗成的過程,背后是悠遠(yuǎn)的歷史沉積和日漸趨同的民族文化心理。民俗經(jīng)地域切割和時間發(fā)酵,逐漸演化為絢麗多姿且獨(dú)一無二的地方性與民族性,沉淀在語言、藝術(shù)、飲食、服飾、建筑、節(jié)慶、信仰、心理等各個方面,種子般被時間風(fēng)干、窖藏、傳播,成為一種柔韌的文化基因,嵌入群落骨血并一脈刻錄傳承,鍛造出專屬的集體記憶和民族性格。
中國古典文化中落葉歸根、認(rèn)祖歸宗等民間俗信,就是安土重遷、故土難離的集體心態(tài)的外化、固化和物化。不計(jì)其數(shù)的詩詞歌賦都在書寫描述天涯海角的游子和浪跡江湖的俠客,終不甘背井離鄉(xiāng)的漂泊,沖破凄風(fēng)苦雨的羈絆,“宦海沉浮終是客,解甲歸田養(yǎng)天年”,說到底,他鄉(xiāng)再好難為家,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這是漢民族對“故土”的一種普遍認(rèn)知,也是走遍世界都難忘家園的強(qiáng)大心理動因。
從時間維度和地理范疇來看,《百川東到海》長達(dá)半個世紀(jì),橫跨半個中國,時空縱橫交錯,勾勒出一幀幀浩大的動態(tài)歷史畫面,也描摹著一幅幅鮮活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圖景。鄭欣說:“在故事之外,為寫出每一座城市、每一個鄉(xiāng)村的歷史文化特色,我鋪陳了很多文化場景,比如市井街頭、園林建筑、書法繪畫、戲曲歌舞等等,以此增加時代質(zhì)感。當(dāng)掌握了豐富的資料,諳熟文化背景及諸多細(xì)節(jié)后,我感到‘下筆如有神’,虛構(gòu)的人物置入真實(shí)的歷史畫卷,別具一格的故事場面呼之欲出。”[4]
作者所言非虛,她的筆下的的確確“鋪陳了很多文化場景”:豪門望族轟動一時的世紀(jì)婚禮,軍閥權(quán)貴雕梁畫棟的山水園藝,八旗子弟玩物喪志的文玩煙酒,貴族小姐描金繪彩的鳳冠霞帔,花街柳巷倚門賣笑的吹拉彈唱,文人雅士夸才斗藝的琴棋書畫……從鐘鳴鼎食的侯門大戶,到引壺賣漿的販夫走卒,無論富貴錦繡還是頹敗破舊,都有一股濃濃的藝術(shù)質(zhì)感,都是無可替代的民族文化。例如,小說開篇即讓人不能小覷、必須高看一眼的“三希堂青蓮詩文銘白羊脂玉方壺”“兩盅桂花蓮子銀耳湯”,那是富貴之家的鐘鳴鼎食、風(fēng)雅閑適,而“鋦盆鋦碗鋦大缸的營生”,無非是平民百姓的養(yǎng)家糊口,雖也衍生為不可或缺的生存技能,但“技”與“藝”終究是卑賤與高貴的分野,有一道難以逾越的“質(zhì)”的天壤之別。
小說中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唐太太自殺一節(jié)的細(xì)微描寫。比之前文高朋滿座的熱鬧婚禮、車水馬龍的盛大葬禮,唐府盛極而衰的凋零頹敗、墻倒眾人推的分崩離析,更讓人過目難忘,唏噓不已。曾經(jīng)呼風(fēng)喚雨的豪門權(quán)閥,被時代的驚濤駭浪擊碎,瞬間四分五裂,眾叛親離,“忽喇喇似大廈傾”“好一個飛鳥各投林”,恍惚間,樹倒猢猻散的悲涼感油然而生,很有點(diǎn)讀黛玉葬花、焚稿時情不自禁地潸然淚下。強(qiáng)烈的共情產(chǎn)生強(qiáng)烈的共鳴,悲劇的震撼力就在于此。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浪潮洶涌滔滔,沒有誰能阻止歷史前進(jìn)的腳步,無論是指點(diǎn)江山的一代帝王,還是改朝換代的一眾英雄。
就傳統(tǒng)觀念而言,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應(yīng)當(dāng)最大程度地深入淺出,因?yàn)椤吧钊搿币住ⅰ皽\出”難,這需要極高的寫作功力,包括觀察想象的能力、邏輯思維的能力、語言組織的能力和文字表達(dá)的能力。也就是說,真正好的小說,并不是把故事編造得多么離奇驚悚,把背景渲染得多么緊張神秘,也不是把人物刻畫得多么神出鬼沒,把語言鋪排得多么漂亮華麗,而是能夠以小見大,小中見大——繁瑣細(xì)碎的衣食住行,一日三餐的油鹽柴米,酸甜苦辣的婚喪嫁娶,生離死別的愛恨情仇……這些日常生活的庸常瑣細(xì),其實(shí)就是一個又一個的尋常日子,是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yuǎn)也不會忘記的人間煙火。
社會在發(fā)展,歷史在前進(jìn),隨著各民族不斷地交流融合,民俗文化也在悄然變化;而從民俗文化到民族文化,呈現(xiàn)為螺旋上升的發(fā)展態(tài)勢。但銘刻在集體記憶深處的歷史和文化,卻愈加鮮活生動。歷史不能忘記,文化不會忘記。只有以史為鑒,才能面向未來。尼采說:“我們必須知道什么時候該遺忘,什么時候該記憶,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時候該歷史地感覺,什么時候該非歷史地感覺。這就是要請讀者來考慮的問題:對于一個人、一個社會和一個文化體系的健康而言,非歷史的感覺和歷史的感覺都是同樣必需的。”[5]P4
文化附著于歷史長河的每一朵浪花,光華灼灼、熠熠生輝。那么,關(guān)于民族歷史、民族文化的“記憶”與“遺忘”,特別是兩者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以及尋找歷史、當(dāng)下與未來三者恰當(dāng)合理的精神坐標(biāo),便是一個值得深刻反思的問題。沒有過去就難以擁有未來,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今天,無數(shù)精彩紛呈的文化遺產(chǎn),承載著曾經(jīng)輝煌的遙遠(yuǎn)記憶,張揚(yáng)著不斷進(jìn)取、永遠(yuǎn)超越的理想和自信。
三、詩情畫意的語言風(fēng)格
語言的書寫與思想的傳達(dá),是考驗(yàn)一位作家真實(shí)水平的“硬功夫”。《百川東到海》特別突出的一個特點(diǎn),就是語言的詩化。細(xì)膩傳神的描寫,古樸優(yōu)雅的表達(dá),靈動有趣的思維和活潑浪漫的想象,都仿佛在與讀者進(jìn)行情智對話。這也可以看作是對生活的審美化,即主體脫離理性判斷和功利目的,對世界有一種無聲的鑒賞和審美,表現(xiàn)為透視的質(zhì)感、非理性的邏輯、令人舒適的比例和恰到好處的比喻。此所謂“文筆”,往往為學(xué)者型作者所偏愛。
毋庸置疑,鄭欣的古典文學(xué)修養(yǎng)深厚,根基扎實(shí),體現(xiàn)在小說的語言上,就是妙筆生花,古意盎然,特別是修飾語的兩兩對應(yīng),頗得駢文神韻,不僅節(jié)奏上抑揚(yáng)頓挫、朗朗上口,行文也是排列有序、美觀整齊。
《百川東到海》的語言之美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名字、句子、文字。
1.唯美名字
名字是人或物的指稱性符號,多數(shù)還兼具象征意義或文化意義。作為一部背景廣闊、結(jié)構(gòu)宏大的長篇小說,眾多個性鮮明、關(guān)系復(fù)雜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一個辨識度高、又有特定含義的名字來稱謂。這是一個基礎(chǔ)性同時又具有一定挑戰(zhàn)性的工作,不能太隨意,也不能太刻意,就像年輕父母給孩子取名,寄托著全部的愛和夢想,包含了無限的祝福和心愿。
不難看出,《百川東到海》的取名頗為巧妙,特別是女性名,用字考究,寓意美好,無不彰顯其主人的蕙質(zhì)蘭心:敏之、蕙茗、桃葉、菊香、梅箏、素琴、錦瑟、紅珠、晚柳、宛淇、宛漪、續(xù)春花……梅蘭竹菊,琴棋書畫,桃紅柳綠,花團(tuán)錦簇,唯美畫面呼之欲出,仿佛一個個詩詞中的古典美人,一路款款行來,儀態(tài)萬方、風(fēng)華絕代。作者借人物之口向讀者解釋這番良苦用心:“素琴,錦瑟,都是前一個字是顏色,后一個字是從玉的,那么還是從玉紅珠。紅色最辟邪;珍珠,又是圓滿和富貴的意義。”[2]P401
書寫新時代,怎能缺席新女性?羅丹,便連名字也透著幾分“洋派”:一身衣著“斑斕得像一只蝴蝶”,象征著人物不拘一格、特立獨(dú)行的爽朗率性,“一位時髦女郎,一身青翠色西裝與玫紅洋綢旗袍中西合璧式服裝引人側(cè)目,大紅大綠在她身上倒也雜糅出一些別樣的味道。”[2]P17年齡、身份、教養(yǎng)、語言都在不動聲色地配合著這個“洋氣”的名字,彰顯其熱情洋溢的活潑性格和熱烈如火的革命激情。
至于其他名字,也都各具特色,如淳衷、淳祐、淳袏三兄弟,左中右顯然煞費(fèi)苦心;項(xiàng)伯亦、方可為,透著幾分書卷氣;山口醫(yī)生、菲堤醫(yī)生,充滿異域氣息;小滴答、段大挑,顯出俏皮勁兒;還有喚作“蕉雨軒”的餐館、“裊晴絲”的煙館、“止遠(yuǎn)堂”的書畫店、“辰軒榭”的方亭水榭,頓時讓人對“文化”心生敬意;“小花枝胡同”里出現(xiàn)妓院“浮光美”,有個名妓叫“翠仙”,似乎也都再貼切不過;而正正經(jīng)經(jīng)的“坪林山莊”,則是大戶人家看似低調(diào)實(shí)則篤定的四平八穩(wěn)、成竹在胸。
總之,這些人名地名,既可以“雅”得高山流水、仙氣飄飄,也可以“俗”得市井煙火、“痞氣”十足。這不能不看作是作者的十分功力和百分用心。
2.對稱句子
對稱是形式美學(xué)的一個基本法則,也是中國古典藝術(shù)特別重要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突出地體現(xiàn)在中國獨(dú)有的楹聯(lián)藝術(shù)以及詩文中的對偶、對仗,基本要求是字?jǐn)?shù)相等、結(jié)構(gòu)相同、詞性相對、詞義相反等等。
《百川東到海》非常明顯地運(yùn)用了對稱原則,許多句子都是兩兩相對:“多愁多病的身,憐香惜玉的心。”“檢查一下人口,核對一下良民。”“千萬不能有閑雜人等混進(jìn)來,也不能有吃里扒外的混出去。”“朗朗世界,母子不得相聚,夫妻不得團(tuán)圓。”“列位的馬褂長袍,西裝革履,珠環(huán)翠繞,云鬢香影,一幅人間富貴繁華的景象。”“戲臺上出將入相,仙魔畢至,絲竹盈耳,鑼鼓喧天。”“什么主義,什么名分,一切不過都是夢幻泡影,惟有聲色犬馬和真金白銀,才是世上最穩(wěn)妥的安身立命之所。惠茗一面揮汗,一面揮淚。”
還有大量耳熟能詳?shù)某烧Z俗語:天光水影,碧波蕩漾;郎才女貌、佳偶天成;應(yīng)對合宜、大方得體;宦海沉浮,飄搖不定;皓月高升、月華如練;放馬歸田,安享晚年;喧囂熙攘、高朋滿座;凄風(fēng)苦雨、陰陽相隔;紅燭照影,喜字高懸;紅燭美人,挽發(fā)梳妝;艷若桃李、冷若冰霜;亭臺樓榭、花草樹木;湖光山影、水禽飛鶴;風(fēng)云變幻、詭譎莫測。
慣常的四字結(jié)構(gòu),語義明確,節(jié)奏鏗鏘,雅俗共賞,為小說一大亮點(diǎn)。而眾多詩文的高頻次現(xiàn)身,既言簡意賅又畫龍點(diǎn)睛,亦為小說增色不少。
3.詩性文字
傳承數(shù)千年的方塊漢字自帶詩性,形音義三者的完美結(jié)合,仿佛詩樂舞的三位一體,靈動、柔媚、唯美,動感十足、魔力無限。《百川東到海》語言的詩性特質(zhì),在小說中不用刻意尋找,隨時隨地就“跳”將出來:
“浮光美那間熟悉的小閣樓里,奎栗靜默地坐在一把圈椅上,手里拈著一把小小的紫砂壺,待喝待不喝地舉著,微微瞇著雙眼,在想著什么心事。翠仙也是沒有話,靜靜地撮了一爐香點(diǎn)上。片刻過后,香氣似松柏林中掃過的清風(fēng)一樣,若有若無地飄浮在房間里。翠仙端端地坐在琴凳邊,調(diào)了一下弦子。剎那間,十指蘭花初綻,那樂音也就恰似那新鶯出谷、銀瓶乍裂。”[2]P32
“紅霞白塔,桃花流水,霞光中天空慢慢轉(zhuǎn)成靛藍(lán)色,湖水沉淀成青藍(lán)色,北海公園里也一下子安靜了許多。西仔在水邊桌臺點(diǎn)燃了盞盞油燈,燭火隱約搖曳著,湖水慢慢變成深藍(lán)。”[2]P20
例子太多,不勝枚舉。“單看這戲樓,卻是說不出的金碧輝煌,正中寫著‘盛世和聲’四個大字,兩側(cè)聯(lián)對‘演悲歡離合當(dāng)代豈無前代事,觀抑揚(yáng)褒貶座中常有劇中人’。”[2]P7-8簡簡單單幾十個字,現(xiàn)實(shí)中有虛幻,虛幻中有現(xiàn)實(shí),存在與虛無,在聯(lián)中彼此映照,這恰好就是語言文字難以言喻又不言而喻的絕妙之處。
通讀小說,單就語言來說,也不難看出作者的溫婉氣質(zhì)。即便表現(xiàn)血雨腥風(fēng)的軍閥混戰(zhàn)、表現(xiàn)生離死別的愛恨情仇,都難見文字的氣急敗壞、咆哮吶喊,而是一如既往的平心靜氣、典雅端麗,在交代背景、敘述故事、塑造形象、烘托氣氛的從容淡定中,歷史大潮的“剛”與詩化語言的“柔”相互映襯又彼此中和,剛?cè)岵?jì),詩畫一體。這種“魔性”貴在日常修為的“定力”,恰如白居易詩:一勤天下無難事,一靜天下無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