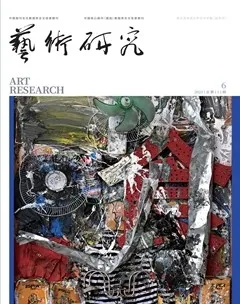《狙擊手》:群像敘事、符號表達與類型敘事
江蘇師范大學/李 想 新鄉學院/曹耀辰
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尹鴻教授在談到新主流電影時說道:“新主流電影以正劇題材、精良制作、低起點人物、個體視角、國族情懷、認同想象為核心特征,達成主流價值觀、大眾國族認同想象的融合,成為重要的電影和文化現象。”縱觀中國電影理論的發展,始終存在一條主線,就是特色鮮明的主旋律電影創造,那么從主旋律電影到新主流電影,這些獨具中國特色的影視理論體系正隨著時代的變遷進行著革新,從電影《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中所構建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形象,到《中國機長》《烈火英雄》中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價值表達,再到《我不是藥神》《我和我的父輩》中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新時代公民話語權體現,不難看出,當下中國的新主流電影發展,其題材更多的是與新時代社會所弘揚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高度契合,這種被大眾所接受的主流文化,體現的是創作者們積極迎合時代,主動的創作出反映時代、歌頌時代的電影作品。
一、用群像敘事塑造英雄
“新中國成立以后,電影不再被視為特殊的文化商品,而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治宣傳的工具”。電影從敘事的手段成為了保衛意識形態的武器和工具,從主旋律電影電影到新主流電影,唯一不變的就是英雄人物形象的背后承載著的一直是家國情懷。從《戰狼》《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再到《長津湖》《長津湖之水門橋》《懸崖之上》《狙擊手》,電影的敘事基本上都呈現出多線多點交叉的表征,必然要依托形形色色的人物進行串聯,推動故事向前發展。而英雄主義電影的核心就是對集體主義的描摹,集體主義就必然要對特定的英勇群體進行塑造,《紅海行動》中前往伊維亞執行撤僑任務的海軍小分隊,《懸崖之上》中的中共地下黨和敵特分子的明爭暗斗,這種群體的影像化表達都是在個人—集體—國家中對民族形象和英雄群體進行塑造。
(一)啟用新演員群體
在電影《狙擊手》中,對新人演員的使用更好的契合了張藝謀導演的小切口敘事,在五班這樣一個戰斗集體中,只有演員章宇被觀眾所熟知,其余的戰士們都是銀幕首秀,帶著一副生澀的面孔更加貼近史實,同時也給觀眾一種新鮮的觀感。在以往的戰爭史詩題材電影中,導演們更多熱衷的是“數星星”的人物堆砌,各種老戲骨和流量明星輪番上陣,也許是出于吸引更多群體觀看以獲得高票房,總體來講,在粉絲經濟大行其道的中國電影當下,使用新人演員對英雄人物進行新的詮釋,更是技高一籌。抗美援朝戰爭是青春的戰爭,電影《狙擊手》也為了更好的凸顯“青春的戰場”。新人演員的加入帶來的生動感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正當年少,將這種純粹感融入到電影敘事和人物刻畫中,帶來了普通真實的志愿軍戰士最壯烈的犧牲,這種雙重概念的“無名”,卻滿是力量,雖是新人,但演技卻不新,為塑造真實的中國志愿軍狙擊戰士形象,飾演“狙擊五班”的年輕演員們提前半年進行封閉訓練,從體能、格斗、射擊等軍事素質各方面嚴格訓練,進行體質、心智與意志的多重磨煉。
(二)沖突雙方的群像刻畫
藝術來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真實感人的人物形象需要真實的故事來支撐。在《狙擊手》中,五班戰士拯救戰友的故事就是根據抗美援朝戰爭中“冷槍冷炮”的神槍手群體事跡改編而來。狙擊手五班奉命執行解救前線情報員亮亮的任務,班長劉文武帶領他的同鄉娃兒們即刻奔赴戰場,導演將鏡頭對準敵我雙方,在冰天雪地里冷靜克制的呈現一場廝殺,作為我國第一部專注描摹抗美援朝戰爭中狙擊手的電影,對每位狙擊手的形象刻畫是決定影片成敗的關鍵因素,在后續展開阻擊戰中,每一個狙擊手的犧牲,都有一定的道理和章法,以人換人的班長劉文武,在死去的最后一刻還在向敵人扔著手榴彈,背著鐵板搭救亮亮,在犧牲時還在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起名字的胖墩,遭敵人槍擊還不忘提醒戰友莫暴露的高軍,張藝謀將每一位犧牲的英雄們遇難的過程直觀地表達出來,目的就在于讓后輩們記住,只有這樣,我們更能體會到在抗美援朝中戰士們把青春獻給祖國的精神。
不同于以往電影中對英雄人物“臉譜化”的描摹,《狙擊手》中對戰士們的形象塑造則盡顯平民化,班長劉文武和戰士們更多的是平等的交流對話,扮演的是一種引導的角色,而不是發號施令的導師形象,這就有利于打造一個團結向上的英雄群體,縱觀近些年來新主流電影的發展,這種導師的形象設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一主多從,在《懸崖之上》中,為了秘密執行“烏特拉行動”,在由共產黨特工組成的人物小隊中,分成了兩個行動小組,經驗豐富的張憲臣自然就成為了決策者,帶著王郁、小蘭、楚良進行營救任務。由于經驗的問題,在一個團隊里面更多擔當的是決策者和領導者的形象,其他的成員只有執行權利,另一個就是組織領導,《1921》《革命者》中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黨組織的刻畫,甚至可以回溯到《戰狼》《紅海行動》中對營救任務的安排和領導,但是在《狙擊手》這部電影中刻畫的更多是整個群體,導演敘事的視角就是單一場景——戰場,固定時間——必須要在規定時間完成任務,所以在圍繞如何突圍,如何撤退等重大問題上都是班長和戰士們進行溝通交流完成任務。而在對于美軍陣營的刻畫上,導演并沒有刻意丑化、妖魔化美軍,有別于早期中國的戰爭電影中對于敵對勢力的夸張的丑化,近年來的新主流軍事電影中,更多采用了客觀的表達,從人物刻畫到整體形象,從純粹的殘酷無情的侵略者,喪失人性的殺人狂到有血有肉、有家庭有夢想的敵對陣營中的“普通人”形象,相比于直接扁平化的設定,這樣的形象刻畫使得新主流電影中的“反派”更加圓滿。
二、用符號表達建構意象
“對于電影作品來說,所有的細節、節奏、畫面都應該指向一個統一的整體,這個整體既是電影敘事的整體,也是指電影美學的統一性,好的隱喻式敘事與電影本身一定是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機構整體”。在張藝謀導演的作品中,這種電影敘事和電影美學的統一性體現的尤為明顯,運用某種特殊的符號作為影片的意象建構方式,以便傳達出導演的特定思想,符號化的表達也可以使得電影的故事講述增加更多語義的延伸,但是導演的具體的創作過程中也不能過于強調隱喻式符號的塑造形式,更應該有一種“以小見大”的觀念來引導電影的創作。
(一)物象符號
隨著電影符號學的誕生,電影理論由經典電影理論時期進入到現代電影理論時期的新階段,在符號學家建構的符號化的世界體系中,基本上所有的物象都有著一定的指示意義。真正意義上的電影是由代表價值意義的敘事和代表功能效用的物象構成。物象是真正具有電影化的表意元素,也是電影區別于其他藝術的重要特征。在《狙擊手》中,雪和望遠鏡這兩個最具代表性的物象符號體現的就是這個含義。
1.雪
白色的雪和灰黃的土、鮮紅的血構成了凄涼殘酷的美學風格,在戰場上,雪是覆蓋在灰黃的土地之上,在彈坑和地道,這些所有戰斗過的痕跡。《懸崖之上》是四個字:雪一直下。很有詩意的感覺。這次我覺得不要下雪,地上有雪就夠了。在影片表達青年狙擊手們犧牲的場景時,地上的雪就顯得更為純潔,導演將雪的“無生氣”和血的“有生氣”進行有機結合,巧妙的隱喻了在寒冷的朝鮮戰場上,五班狙擊手營救任務的無比艱辛和戰勝對面戰壕中的美軍力量的來之不易。
2.望遠鏡
在電影《狙擊手》中,破舊的望遠鏡既是用來偵探敵情的唯一工具,在電影中出現了很多次,也是在影片最后承擔起使命與擔當的重要意象。“其意義指涉而言,它們既可以是電影中的背景、陪襯,也可以是影片發展的線索,甚至可以是電影的主要表現對象。出現在電影文本中的物象符號,以各種方式或多或少地參與了電影的表意”在影片的開頭,兩名小戰士討論全班唯一一個望遠鏡給誰的問題,這個時候,望遠鏡作為的是一種情感的紐帶,去串聯起戰友之間的情誼,而在影片后半段解救被俘的亮亮的時候,班長劉文武選擇以人換人,將唯一的望遠鏡送給小徐,這是任務的交接,是英雄之間的犧牲和成長。
(二)色彩符號
縱觀張藝謀所導演的電影,視覺奇觀一直是張藝謀的拿手好戲,其在色彩方面表現出一種獨特的張藝謀式的美學藝術,無論是《大紅燈籠高高掛》《我的父親母親》還是《影》《英雄》等影片,無不展現出了張藝謀突破傳統電影對色彩的局限,敢于尋求色彩帶來的視覺沖擊力從而進行藝術表達的魄力。在《狙擊手》這部電影中,張藝謀用國畫的風格描繪了一幅蕭瑟慘白的戰場畫卷,以血紅和雪白的強烈對比,凸顯出戰場上的無情,在這樣一個具體的戰場之上,兩方勢力進行角逐,導演沒有用更多的篇幅去具體呈現所在具體的場景,而是通過人物的交鋒和事件的具體發展來展示。其多表達出來的美學意蘊也自然更為深刻。電影的色調使用不僅營造了肅殺的氛圍,強化了敘事風格,同時作為圖像符號隱喻化的表達,也使得整個影片立意高遠。
“符號文本的表意不僅與發送者相關,也與接受者相關”。張藝謀導演之所以選取了一個不同于《長津湖》《長津湖之水門橋》的宏大敘事,而是選取一個小切入口去對朝鮮戰場上的狙擊手形象進行刻畫,也是著眼于受眾的接受域,2020 年是抗美援朝戰爭70 周年,以反映抗美援朝精神為主題的一大批影片紛紛上線,而張藝謀導演卻能夠從千篇一律的敘事體系中跳脫出來,敢為人先,使得《狙擊手》可以達到一葉知秋的高度,也是充分考慮了當下受眾的審美疲勞,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張藝謀在影片的符號文本設置中下足了功夫,青年群體的狙擊手英雄,勢均力敵的兩方勢力,單一事件的完整描述,戰爭題材的技術化表達,將藝術思想、精神追求和市場表達進行有機融合,讓當下的中國觀眾對英雄主義,對抗美援朝精神有一個新的體會。
三、用犧牲與成長來加強類型
作為一部戰爭片,唯一的主題就是反戰,在生與死之間展示勢均力敵或者敵強我弱的較量,通過對人物美的描寫,再在之后進行摧殘來體現戰爭的殘酷無情,從而達到宣傳名族英雄,發揚名族氣節和反戰的目的。不同的是,在此之前的抗美援朝題材電影,大多都把滿足意識形態的需要作為最主要的主題表達,往往或忽略了個人情感的流露,在《狙擊手》中,我們可以看到是保家衛國的民族大義,導演將五班戰士們的家國情懷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觀眾面前。而在對五班這個小集體進行具體人物畫像時,導演用一種類型加強的策略進行藝術化的塑造,青年狙擊手們在犧牲和成長之間完成任務的交接以及靈魂的洗禮。
(一)老英雄的犧牲
在《狙擊手》中,電影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就是老英雄的犧牲,另一個就是新英雄的成長,在對班長劉文武的人物塑造上,導演通過兩個側面進行描摹,這個側面是通過敵我雙方的角度,一個是對面戰壕中的美軍力量,主要策劃者將亮亮作為人質的目的也是為了生擒劉文武,在美軍看來,劉文武是一個戰無不勝的神槍手,從一開始,劉文武就是作為一個完美的人出現在銀幕中,這也為在后續的影片發展中掌握話語權作了鋪墊,而這種話語權的掌握不是一種絕對命令,而是和五班的戰士們在面對復雜多變的戰局和生死攸關的戰斗中進行體現,而劉文武也更多地以長兄的形象出現,不同于以往領導者的訓誡和指揮,班長的話語以一種趣味的“調侃”進行表達,在戰士小徐被炸掉下半身將要犧牲時,班長為了讓他減少痛苦,說:“震麻了,腳板還在,雀雀還在,還雄得起”,在教大永用勺子的反光面測距時,更多的也是鼓勵和肯定,在最后的犧牲段,班長為了成功營救亮亮和減少五班成員的傷亡,毅然用自己和人質進行交換,在交換之前還在教大永如何突圍,這種教導是一種任務的交接,是身份的傳遞,這種傳遞是一種力量,是愛國主義的高揚。
(二)新英雄的成長
《狙擊手》打破常規的挑戰源于劇作的創意和穩健,按照導演張藝謀和編劇陳宇的設想和追求,即在一個幾乎封閉的時空中,不依靠外力,只通過故事的內部矛盾形成的張力推動故事敘事。導演對于大永的人物設定就是作為這個內部矛盾存在的,全片觀眾對大永的印象就是由一個愛哭鼻子的小戰士成長為能夠擔當大任的新英雄,得知同鄉的亮亮被俘會哭、戰友犧牲會哭、班長批評會哭,而大永的成長正是在這種哭泣中完成性格的塑造和縫合主題的表達,作為一個四川娃兒,在班長的帶領下到戰場上和美軍進行廝殺,這種成長具有雙向性,一個是班長劉文武的指導,一個是大永自身的領悟,在集體與個人之間,我們看到的是在一個簡約的空間里,大永憑借著一個勺勺完成班長交付的營救任務,成功地將亮亮用生命換來的情報交給上級,成全了集體同時也塑造了個人的成長。
班長的犧牲和大永的成長,在生與死之間,完成主題的升華,時間固定,劇情集中,將這種成長敘述的主題巧妙的串聯起來,導演用“點名”的方式將五班的精神永固,開始的班長點名,五班全在,后面的點名,只有大永一人,但其他士兵的喊到,真正的將這種縫合主題所呈現出來的集體主義精神完美地表達出來,儀式性的營造升華主題——五班精神永在,老英雄的犧牲和新英雄的成長,在短短一個半小時的影片長度中,給觀眾帶來的是具有“中層工業美學”的視聽盛宴,以及對前仆后繼,英雄殺敵的志愿軍戰士們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的感慨。
四、結語
在電影《狙擊手》中,導演張藝謀擯棄宏大敘事體系,淡化背景,著重對“人”的描述,為我國的戰爭題材影片提供了新的思路。通過群像敘事和成功的電影符號學的運用,在滿足了商業性的同時也不失獨特的藝術表達,邁出了新主流電影成熟化和走出形式固化的重要一步。在這樣一個電影工業穩步發展、藝術與商業融合逐漸走向成熟的時代,中國新主流電影從國內市場的成功走向國際,在國內導演積極探索、勇敢嘗試和黨中央大力支持下,也許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