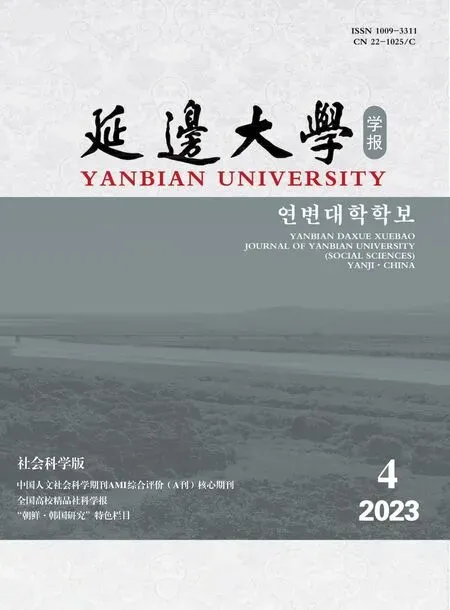韓國“印太戰略”對印太地區秩序的影響
——基于建構主義體系結構的分析視角
劉 芳 王靖林
2022年12月28日,韓國總統府發布了一篇題為《自由·和平·繁榮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以下簡稱韓國《印太戰略》)的外交政策文件,這是韓國政府首次單獨制定的地區外交戰略,也是其將政策重心從朝鮮半島轉移到印太地區的重要標志,一度被國內外學者稱為“韓國外交史上的分水嶺”。“印太戰略”構想最初是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1)學界普遍認為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繼承了先前日本高層的“泛亞主義”精神,并于在任期間積極推進“印太”構想,是當今世界“印太戰略”的核心推動者。后成功宣傳給美國特朗普政府,在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加盟下,美日印澳四國重啟了“四邊對話機制”,逐漸形成以美國為主導的印太同盟體系。“印太戰略”表面上強調要共同加強國際多邊合作、維護地區安全等目標,但深層目的則是擴大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勢力范圍,營造遏制中國發展的國際聯盟“小圈子”。而韓國政府近期出臺的韓版“印太戰略”,在向美日印澳四國同盟示好和靠攏的同時,卻將中國納入戰略的合作角色,這無疑表現出了尹錫悅政府在對華關系方面強烈的矛盾心態。
韓國《印太戰略》最終版文件從經貿、安全、國防、外交和國際合作等領域進行全面布局,揭示了韓國政府未來一段時期在印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制定方向。目前,國內學界雖對美日等國的“印太戰略”及其印太同盟體系研究甚為豐富,但對韓國政府新近出臺的“印太戰略”還暫未涉及。鑒于此,本文將以建構主義體系結構理論為分析視角,以韓國“印太戰略”為研究對象,分析其生成動因、主要架構與預期目標,進而從物質、利益和觀念三個維度探究韓國“印太戰略”及其與“印太同盟體系”的互動關系對印太地區秩序構建的影響。
一、施動者與地區秩序:一種因果和建構關系
國際體系主要國家間的實力變化以及互動進程(施動性)影響著體系權力、制度和觀念分配結構轉變的進程和方向,進而塑造了國際(地區)秩序的架構、模式與形態。(2)孫通:《美日印澳戰略互動對地區秩序的影響——基于體系結構視角的分析》,《東北亞論壇》2021年第6期,第94頁。同時,地區秩序作為一種相對穩定的國際體系結構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又會建構處于體系文化中施動者(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因此,施動者互動與地區秩序之間既互為因果又相互建構,并共同在動態的塑造中發展和演變。
(一)國際關系學界的“體系結構”之辨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體系結構”一直是西方國際體系理論研究的重要議題,并成為國際關系學派“第三次辯論”的主要內容。結構現實主義學派的開創者肯尼思·沃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指出,“如果人們在研究方法上既注重單位層次,又注意結構層次,他們就能夠全面把握國際體系的變化和延續”。(3)[美]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胡少華、王紅纓譯,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3頁。在國際體系的單位內涵方面,他認為,在以無政府狀態為特征的國際體系中,同類的、功能相似的國家是國際體系中最重要的體系單元。(4)[美]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信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4-129頁。建構主義代表人物亞歷山大·溫特認為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基本組成單位,也是其建構主義研究的主要層面。(5)[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4-195頁。不論是體系單元、國際體系研究單位,還是施動者,皆指向當前我們所理解的主權民族國家,以其作為最主要和最小的研究單元,并主動忽略國內復雜因素對國際體系的影響,西方各學派基本對此達成了默契。在國際體系結構的內涵界定方面,溫特結合結構化理論和符號互動理論,強調體系單元與體系結構之間“相互建構且互為因果”的邏輯關聯,將單元互動所形成的共有觀念和體系文化(觀念結構)看作國際體系中重要的社會性結構和特征,并能夠影響體系結構的各個因素。(6)[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4-175頁。這些國際體系單元和結構相關觀點都為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建構主義視角下單元互動對地區秩序的塑造路徑
地區秩序是國際體系中施動者物質分配、利益構建和觀念塑造的結果,其主要表現為地區的制度與格局發展。西方建構主義學派認為施動者與地區結構存在兩條并行的相互構建路徑。從一個層面上來講,地區結構是一種外部結構性因素,會在國際體系中對體系單元產生影響,使施動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受到激勵或是抑制,從而在自我與他者的審視中對施動者身份、利益的構建造成影響。在另一個層面上,體系單元互動與地區結構之間是雙線雙向構建的。溫特反對將身份和利益看作既定的常量,而認為國際體系中施動者的身份與利益處于不斷變化的進程中,并且約束施動者的互動行為,使之影響體系結構或地區結構,整個過程系統是同時進行且時刻運作的。(7)[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0-228頁。簡言之,體系單元、地區結構和地區秩序三者存在一種理論邏輯,即體系單元的互動與地區結構存在互相構建且互為因果的邏輯關聯,地區結構又直接作用于地區秩序的格局,因而地區體系單元的互動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地區秩序的塑造進程與方向,同樣也會受到地區秩序塑造結果的制約,逐漸形成了一條國際體系單元互動對地區秩序的塑造路徑,印太地區秩序的塑造過程也是如此。
二、韓國“印太戰略”的生成動因、主要架構與預期目標
早在出臺韓國《印太戰略》前,韓國官方就對美國“印太戰略”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8)2019年11月2日,時任韓國外交部次官補的尹淳九與時任美國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史達偉舉行了會晤,并達成了一項關于“韓美將繼續為新南方政策和印太戰略相互合作而共同努力”的共同聲明,這一聲明為韓國參與美國印太同盟體系埋下了種子。尹錫悅總統上臺后,一改文在寅政府的溫和外交政策,多次在國際公開場合表示擬定韓版“印太戰略”的意愿,并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2022年12月28日,韓國《印太戰略》一經公布,就迅速在國際社會引起了廣泛關注與討論。
(一)韓國“印太戰略”的生成動因
韓國政府出臺“印太戰略”,既表現出韓國尹錫悅政府對印太地區的重視,又代表了韓國在處理印太事務中的親美立場,其生成動因可以從印太地區戰略價值、中韓關系和韓美同盟關系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第一,從印太地區的價值方面來說,韓國政府制定“印太戰略”是必然選擇。冷戰結束之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開始重建,印太地區逐漸成為世界經濟重心,其戰略地位愈發凸顯。以2021年為例,印太地區約占韓國總出口額的78%,總進口額的67%,韓國有超過半數的重要合作伙伴國家都位于印太地區。(9)數據來源于韓國《自由·和平·繁榮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政策文件第5頁,https://www.mofa.go.kr/www/brd/m_4080/view.do?seq=373216。由此看來,印太地區對于韓國價值斐然。作為具有區位優勢的“橋梁國家”,韓國此前一直將對外政策的重點置于朝鮮半島和亞太地區,這不僅約束了其發展空間,還會錯失本國經濟發展機遇和利益。因此,韓國政府必須在轉移對外政策重心之前制定一套詳盡的印太地區戰略方針,使韓國能在所處的有限地緣條件下獲取最大程度的國家利益。
第二,從中韓關系來看,韓版“印太戰略”是韓國政府意圖推動漸進式對華脫鉤所采取的政策選擇。在地區秩序建構中,經濟一體化常常被視為地區合作的基石,(10)門洪華:《地區秩序建構的邏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7期,第19頁。國家間經貿合作、協調和相互妥協行為促生了地區穩定的軟性法則。中韓兩國關系在長期經貿合作的促進下保持穩定發展態勢,培育和拓展了雙方共同利益。然而韓國總統尹錫悅上臺后,中韓關系似乎面臨著走下坡路的趨勢,部分韓國政府高層認為,雖然中國是重要的“戰略合作伙伴”,但是對中國各領域的高度依賴會成為阻礙韓國發展的桎梏,必須擴大對外交往的戰略布局,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程度。(11)《韓新政府經貿政策前瞻:加深與美合作降低對華依賴》,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52434。因此對韓國而言,融入“唯一同盟國”所主導的印太同盟體系是最優選擇。
第三,在韓美同盟關系方面,韓版“印太戰略”是韓國鞏固同盟關系,尋求廣泛合作的應有之義。韓美同盟是韓國外交戰略的核心,長期以來韓美兩國在印太地區就一直都有密切的合作。文在寅政府時期的“新南方政策”原則是圍繞繁榮、人、和平三大領域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這一政策就與美國“印太戰略”的前身“印太經濟愿景”有契合之處,而后兩國在印太地區的外交政策則是圍繞這些基本主題展開的。美國總統拜登自上臺以來,將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轉為“聯盟優先”政策,全面提升在全球范圍內的同盟關系,并將韓國和日本視為其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前沿”。韓國大選之后,尹錫悅政府更是抓住發展“機遇”,開始轉向價值觀外交,并積極修復和提升韓美同盟關系,力推兩國在外交安全方面的戰略轉型。再加上美國和日本的極力拉攏,韓國政府出臺“印太戰略”已經成為必然。
(二)韓國“印太戰略”的主要架構與預期目標
韓國《印太戰略》全文共37頁,由推進背景、“印太戰略”的原則、重點推進事項和總結四個章節組成。在推進背景部分,文件主要圍繞印度-太平洋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展開,介紹了印太地區的人口與經濟價值,并對印太地區與韓國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指出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直接影響到韓國的國家利益。在第二部分,文件對韓國“印太戰略”的愿景、合作原則及地域范圍進行了說明。韓國政府在文件中提出,作為印太地區的重要成員,韓國有意愿和能力為實現印太地區的自由、和平和繁榮貢獻力量,以包容、信賴和互惠的合作原則實施“印太戰略”,并加強與中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印太地區國家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第三部分是具體內容部分,這部分詳細闡述了韓國為實現“印太戰略”的愿景而提出的9個推進主題,具體包括:1.構建基于制度與規則的印太地區秩序;2.促進法治主義與人權合作;3.加強核不擴散與反恐合作;4.擴大全面的安全合作;5.完善經濟安全網絡;6.強化高新科技領域合作和消除地區內數字鴻溝;7.主導氣候變化與能源安全相關的區域合作;8.有針對性地發展合作伙伴關系,為地區發展作出貢獻;9.增進相互了解和交流。在最后一個部分中,文件重申了韓國政府“印太戰略”的愿景與原則,并明確了此戰略性文件在韓國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指導地位。
在韓國《印太戰略》中,除了經濟合作、地區安全、氣候和生態保護等常規話語之外,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方面:一是文件中體現出的對華態度,出于對本國經濟利益的考量,韓國《印太戰略》主動將中國納入互惠互利的印太合作構想中,表現出對中國的模糊態度;二是文件中多次提到“捍衛和增進普世價值”,這是韓國首次將“普世價值”公開寫進對外戰略中,意味著韓國將與共享相同價值觀的國家攜手,積極推行價值觀外交。兩個方面看似矛盾,卻表現出了韓國政府對外戰略的謀劃和目標: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成為“全球中樞國”。要達成這一目標,韓國必須在中美“新冷戰”中審慎定位。中韓兩國在地緣、經濟、歷史、文化等領域聯系密切,韓國對中國的依賴度較高,難以在對外戰略中排斥中國而快速發展,因而韓國政府從維護國家利益出發,既需要借助盟國的力量,也需要保持與中國的交流合作關系。在文件中,雖然多次提出要建立自由、和平和繁榮的印太地區秩序的愿景,但是韓國政府為本國發展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的目的則更為顯著,其對外戰略重心從朝鮮半島擴大至印太地區也恰好證實了這一點。
三、韓國“印太戰略”對印太地區秩序的多維影響
亞歷山大·溫特認為,任何結構都包括物質結構、利益結構、觀念結構三個要素,三者之間存在緊密的邏輯關聯且以觀念作為基礎。(12)[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9-140頁。因此,在國際關系中地區結構同樣存在物質、利益和觀念要素,并且共同影響地區秩序的塑造與重構。韓國政府出臺“印太戰略”,是韓國積極融入美日印澳同盟、抑制中國崛起的合作型互動,此舉也勢必會引發中國作出反應的競爭性互動。在多種體系單元互動的交織下,東亞甚至印太地區的物質力量和觀念力量的分配將會受到一定沖擊,地區秩序也會受此影響而加快重塑進程。
(一)韓國“印太戰略”對印太地區物質結構的影響
雖然溫特對沃爾茲的“物質結構說”抱有批判態度,但其并不否認物質在國際體系結構中的存在價值。國際體系的物質力量是一種權力形式,包含軍事、經濟等,是最易發現和捕捉到的結構因素,正是這些物質因素的調整與流動決定了地區物質結構的樣態。美國從“亞太再平衡戰略”到“印太戰略”,拜登政府對地區的干預意圖再次升級,但其實際干預能力還遠不能擔任單獨主導的角色,需要借助同盟的力量共同整合印太地區秩序。而作為原本“印太戰略”體系先鋒國的韓國政府深知:長期被動卷入大國爭端極易成為國際政治旋渦中的犧牲品,必須在印太事務中掌握更多主動權。韓版“印太戰略”的發布表明,韓國正成為印太同盟體系的新力量,并積極謀求更高層次的身份定位,這種區域性力量整合在短期內將會對印太地區的物質結構產生一定影響。
印太地區面積廣闊,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65%,域內國家GDP之和占世界總額的半數以上,(13)數據來源于韓國《自由·和平·繁榮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政策文件第5頁,https://www.mofa.go.kr/www/brd/m_4080/view.do?seq=373216。且具有成熟的國際貿易體系和海上運輸通道,從地緣屬性來看,“印太”具有政治、經濟和戰略等方面的多重價值。構建和諧穩定的印太地區秩序固然是域內多數國家的利益所在,但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卻借正義之名,行霸權之實,通過打造和參與區域性的地緣政治“小圈子”,強化國家軍事威懾力、經濟控制力和同盟關系。在韓國《印太戰略》中,韓國政府計劃積極開展印太地區的安保和經濟合作,擴大多邊聯合演習與軍事伙伴關系,在深度融入印太經濟框架的基礎上繼續堅持自由貿易原則,并大力推進高新技術的研發與合作。2022年底韓國《印太戰略》剛剛發布,韓政府就積極著手“戰略”的推進事宜。2023年2月3日,韓國外交部“印太戰略”實施工作組正式啟動。同年4月,韓國多個中央政府機構向工作組提交了具體執行計劃,這也標志著韓國“印太戰略”早期部署階段揭開了序幕。(14)《韓國外交部召開實施“印太戰略”第二次檢查會議》,https://www.mofa.go.kr/www/brd/m_25840/view.do?seq=7&page=1。韓國“印太戰略”出臺后,在美國的協調下韓國尹錫悅政府與日本的外交關系似乎變得親近,并受邀出席2023年5月在日本廣島舉辦的七國首腦峰會。韓國的“戰略互動”舉措有助于國家短期物質力量的增長,并且會對國際體系內更多國家產生連鎖反應,使之進行對外政策調整或是產生新的戰略目標。韓國的定位從美日印澳等國家“印太戰略”的從屬國和協助國逐漸向全球中樞國轉變,在與美日等國家加強地區多領域合作的同時,將其自由、和平、安全等印太理念在國際社會傳播,必然會導致地區經濟、軍事和影響力等物質因素逐漸向韓國傾斜。受此影響,印太地區原有的物質結構會發生相應的改變,印太地區秩序也隨之會受到來自韓國對外戰略調整而產生的沖擊。
(二)韓國“印太戰略”對印太地區利益結構的影響
國際體系的利益結構是體系內各單元相互關聯而形成的動態結構網絡,是由物質和觀念共同定義的產物。按照建構主義的理論觀點,印太地區利益結構是區域內單元互動建構的結果,是以共有觀念為主導的施動者互動而產生的利益結構塑造,韓國“印太戰略”的出臺影響了這一進程。
首先,國際體系單元間的互動是在身份和利益的指引下進行的,每個國家都是多重身份的集結體。東盟區域性合作體系和亞太經合組織原是印太地區的中心制度架構,美國和日本等西方國家提出“印太戰略”后,積極在印太地區布局,邀請東盟和APEC主要成員加入其合作框架,與原有的地區體系產生了碰撞。韓國作為東盟合作伙伴和亞太經合組織成員,深入參與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印太同盟體系,身份的重疊必然對國家利益產生重塑,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他相關國家的身份和利益。其次,當前國際體系結構的利益因素更多體現的是經濟與安全利益。中國的快速崛起使印太地區部分國家享受到了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合作紅利,也有一些國家認為這是一種威脅,韓國政府同時存在這兩種政治考量。韓版“印太戰略”明確表示韓國此后的外交政策制定原則和方向,即積極融入印太同盟體系的同時,對中國采取包容的態度。此舉不僅會對中國的國家利益產生影響,還會使美國及其“印太戰略”同盟的利益受到來自內部的張力。此外,地區體系的變化會直接影響體系單元的身份和利益塑造。由于國際經濟重心東移和全球新冠病毒流行的影響,印太地區的體系重塑進程加快,國家利益沖突的調和復雜性增加。
美國和日本主導的“印太戰略”機制與合作同盟原本是為了“遏制中國”而形成的排他性“小多邊”合作機制,(15)徐金金、嚴湘:《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印太戰略”的延續與調整》,《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第24-25頁。如美日澳三國聯合發起的“藍點網絡”計劃、日本和印度提出的共建“亞非增長走廊”計劃等都是在“印太戰略”的原則上擠占中國的發展空間,而韓國政府為參與這一體系而制定的“印太戰略”雖然內容明晰,但是在對華政策上卻存在矛盾性與模糊性。韓國在地緣和文化上與中國聯系甚密,因此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其在“印太戰略”中必須對中國的態度有所保留,這一微妙變化或許會對印太同盟體系原有的競爭和對立局面產生一定的緩沖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戰略目標與事實行為都會存在錯位的可能,即便在韓國《印太戰略》中將中國作為主要合作國家,近期韓國政府的“抱團”行徑卻在明示其在中美“新冷戰”旋渦中的“傾斜”立場。在近期對外活動中,韓國外長樸振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重點宣傳其“印太戰略”,(16)《樸振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印度-太平洋小組討論》,https://www.mofa.go.kr/www/brd/m_25840/view.do?seq=5&page=1。韓國政府也積極與美澳等國家開展多邊對話,(17)《韓美澳首開司局級地區戰略對話共商印太戰略》,https://cn.yna.co.kr/view/ACK20230329005300881。意圖在印太地區尋得廣泛支持并為“印太戰略”的持續推進造勢。2023年5月21日,韓國總統尹錫悅在日本廣島出席七國集團(G7)峰會期間,與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了韓美日峰會,決定通過加強三國安全合作,助力“遏制來自印太地區的威脅”。(18)《韓美日首腦商定將三邊合作提升至全新水平》,https://cn.yna.co.kr/view/ACK20230521001800881?section=search。在印太地區的利益競爭中,韓國“印太戰略”的模糊態度與清晰行為表現出了明顯的差距。
(三)韓國“印太戰略”對印太地區觀念結構的影響
亞歷山大·溫特等建構主義學者認為,觀念決定了國家身份、國家利益和國家行為,因而國際體系中的共有觀念對體系結構塑造至關重要。(19)[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3-115頁。國家行為體之間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處于間歇性或不間斷的互動進程中,互動層次現象產生共有知識,建構主義稱之為“主體際共識”,即行為體相互之間關于對方理性程度、戰略、偏好、信念以及外部世界狀態的認知,(20)張建新:《建構主義國際體系理論及其社會結構觀》,《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12期,第13頁。成為國際體系最深層次的結構。
“印太”既是地緣概念,也是地區秩序和地區愿景的集合,存在著地區體系的自有知識、共有知識和集體知識而構成的觀念結構,并持續深入地塑造地區秩序。美日等國家在印太地區倡導“民主、自由、人權、開放”等價值理念、秩序主張和愿景,與印太地區原有的多元觀念存在分歧并對其進行抨擊和打壓,使印太地區陷入了以競爭為主導的“洛克文化”結構。在韓國《印太戰略》中,全篇多次重點強調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計劃為西方“普世價值”深入至印太地區貢獻力量,意圖強化美國在“印太”以排斥差異價值為主要途徑的“反華同盟”。“普世價值”這一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與印度-太平洋地區原有的包容共生價值主張以及聯合國以國際法為中心的和平發展理念存在著根本差異,因此美日韓等國家的極力推行會對印太地區現存的觀念結構造成快速沖擊,地區秩序的構建將會變得更為復雜和困難。而美國及其同盟國似乎認識到了這一點,韓版“印太戰略”在宣傳“普世價值”的同時將“包容”理念列為戰略原則,這是印太同盟體系主動與其他印太價值觀念融合的表現,韓國的這一舉措是印太同盟體系主動與印太地區價值觀念拉近距離的重要一步,反映了韓國等西方國家對其“普世價值”在印太地區獲得更大范圍認同的迫切愿望。此外,韓國政府的外交策略從“亞太”轉為“印太”概念,外交范圍也從傳統的周邊外交向全球外交延伸,韓國“印太戰略”政策文件中使用的概念和語言主動與美國“印太戰略”接軌,這些觀念變化在潛移默化中會對印太地區的觀念結構產生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以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同盟對該地區的塑造能力,并對印太地區秩序造成影響。
四、結語
在國際體系中,物質、利益和觀念需要進行整體分析,沒有觀念也就不會有身份和利益,沒有身份和利益也就沒有了具體的物質因素,沒有具體的物質因素就沒有客觀事實存在。(21)[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9頁。本文在寫作中并不否認制度分配和權力分配對地區秩序的影響,僅是以建構主義體系結構的視角對地區秩序塑造進行分析,因而在其他影響因素所用筆墨較少。國際體系單元對地區秩序的塑造是一個動態過程,施動者行為主動調整的同時,必然會牽動著與國際體系的互動行為。韓國“印太戰略”對印太地區秩序的塑造主要體現在共有觀念方面,直接體現在主題所推崇的“普世價值”與“印太”原有的價值觀念進行結合的企圖,這必然會導致印太地區物質結構、利益結構和觀念結構的相應調整,從而動態構建著印太地區新秩序。美國及其同盟國也會對此進程起到助推作用,以此來維護美國在印太地區秩序的主導地位和影響力,由此產生的地區結構調整需要國內外學者持續關注。
一股“印太”洋流來勢洶涌。截至2023年2月,全球已有14個國家和地區出臺了“印太戰略”和設想,其中11個國家和地區根據身份和利益對中國進行了戰略定位。(22)[韓]金藝京、金道熙等:《韓國的印太戰略:特點和未來挑戰》,《焦點與展望》2023年總第2061期,第3-4頁。韓版“印太戰略”雖然將中國視為“主要合作國家”,主動將我國納入其在印太地區發展的合作體系,但是不能忽視韓國政府真正的戰略動機。韓國“印太戰略”的施行已然表明了其對于中國的競爭和遏制態度,積極宣傳“普世價值”也是聯合西方國家以降低對中國依賴程度的重要體現。尤其是2023年5月的G7峰會,以美日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涉華消極議題異常關注,公然渲染“中國威脅論”,大有借助同盟勢力排華的勢頭。因此,中國政府需要繼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主張和“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持續拓寬和深化我國與印太地區國家的交流交往合作,主動參與和支持在東盟和APEC框架下產生的多邊經濟、科技和安全合作機制,以此消除和應對印太地區持續的風險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