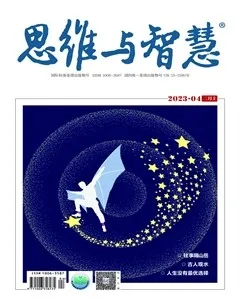思如絮
馬浩

一個故事,如何展開,似乎并不取決于故事本身,一如盲人摸象,故事的脈絡或許簡單,品味故事,卻五味雜陳。
春天里,有人看到一樹繁華,有人看到了滿地落英,有人看到風卷枯葉,有人看到葉放枝頭……這無疑都是真實的,沒有對錯,每人有著吹面不寒的微風追隨呼應。就拿“春風吹又生”的詩句來說,從詩句的字面上來看,春風是生的大前提,往往會忽略詩句中的“又”,其實,又字方是詩句的靈魂,令人遐思。
多年前,讀過一文——《河的第三條岸》。一位父親,為自己打造一條船,以船為岸,漂泊在生活的河流之上。躺在大地上的河流,僅有彼此兩岸可以選擇,生活卻有無數種選擇,可惜生活之中,世俗力量太過強大,常常會左右著人們的判斷力,只有少數清醒者,披衣夜讀,借著如豆的燈火,在白紙黑字間尋找驚世駭俗的發現,往往卻是命運多舛。
在春天,看到花紅柳綠似乎更容易。
閑時,我喜歡散步。那種喜歡非常純粹,沒有任何目的性,比如有人為了養生散步,每天需走多遠,步伐是快是慢,走姿如何,都有要求。人做事一旦有目的性,注意力就會集中在目標上,趣味便會大減。我散步往往隨心所欲,漫無目的,腳走在路上,眼睛便開始四處撒歡,一任思緒飄飛。看到草叢中小花,便會快走兩步,蹲下身來,仔細觀瞧。若小花有知,心底會不會暗罵我輕浮孟浪呢?花顏不會是因為我肆無忌憚地端詳,變得緋紅吧。對于那些野花,知名的,不知名的,我都心生歡喜,無以言表地歡喜,莫名其妙地歡喜,拿起手機,變換著角度以定格它們的美。野花的姿態、花色各有不同,或高或矮,或壯或弱,或白或黃或藍或紫或紅……無不一派天然,絕無矯揉做作,取媚于人。若要說取媚的話,大約亦是為了蜂蝶,這是大自然賦予它們的天性,人不免自作多情。
那些野花之中,我能認識的極少,便是通過科技手段,勉強知道它們的芳名,也就是知道而已,無法連接到我的記憶庫存的故事,以后再見,或許就會有了聯絡,能為我打開多年前的情景,相遇成故友。想到這些,頓覺生活又多了幾分趣味,多了幾多欣喜,多了幾分期待。野花中,我對蒲公英最為熟知,蒲公英花好看,黃燦燦的,無端地讓人想到嬰兒的笑臉,花褪之后,如絲的飛絮,一蓬蓬的,隨風飄舞,看得人心癢。俗稱婆婆丁的蒲公英,是一道清鮮的美味,亦可制茶,供人啜飲。
有時,散步到河邊,看著悠悠的河流,望著水中的倒影,倒影隨著水紋波動,影子如同一根彈簧,被波浪這只手牽拉著,有趣又好玩,人是真實的,影子是不是真實的?若否認了影子的真實,是否意味著否定了人的真實?一些無來由的思緒在頭腦里打轉,不禁莞爾。干脆坐在河堤上,看著水中幽藍的天。水中的天,經過河流這面鏡子,似乎比它的原貌更加迷人,河流居然有美顏功能。藍天總會有白云相伴,沒有白云的藍天是貧乏的。誰說白云千載空悠悠,白云是來成就藍天的,或者說,它們相互成就。
天高云淡,望斷南飛雁。藍天亦是飛鳥的舞臺,天高任鳥飛。世間似乎就是一個大舞臺,花草樹木,泥土是舞臺;游魚水草,江河是舞臺……人的舞臺似乎就更大了,其實,說大也大,說小也小,大小取乎一心。
世間的故事,每時每刻都在上演,無論人是否感知。人都會有自己的認知局限,就像沒有人能夠拎起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人世間,做一名看客容易,品味故事的意蘊就不那么簡單了。人生如夢,夢里不知身是客,醒來卻似在夢中。
(編輯 余從/圖 雨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