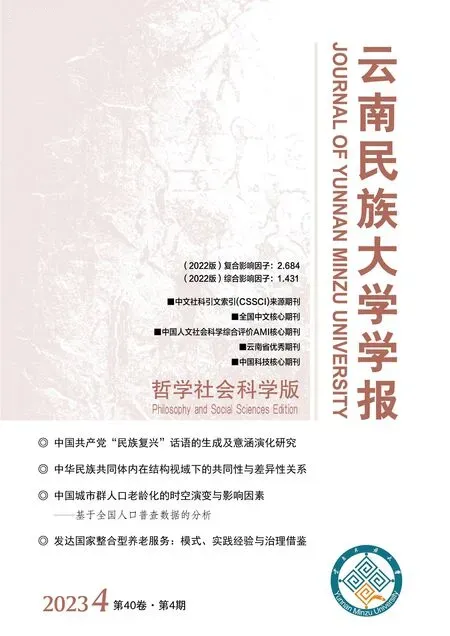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的擴張與中國的策略選擇
李姍姍
(云南財經大學 法政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1)
國際商事仲裁中的“可仲裁性”是指,按照應當適用的法律,哪些爭議可以通過仲裁來解決。(1)寇麗:《現代國際商事仲裁法律適用問題研究》,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頁。一國法律允許仲裁解決的爭議事項即為該國劃定了仲裁范圍,仲裁范圍外的爭議不得提交仲裁解決。爭議事項不可仲裁性反映出國家對于用司法而非仲裁解決該爭議所具有的特別利益。(2)Albert Jan van den Berg:The New York Arbitration Convention of 1958,the Hague: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81,p.367.如果仲裁所涉爭議按照一國法律不可仲裁,仲裁裁決就會被撤銷或被拒絕承認與執行。但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以來,很多法域的仲裁法改革,要么對可仲裁性不作規定,要么以“可以自由處分”作為判斷可仲裁性的標準,要么將不可仲裁性限定在“公共政策”或“法律明確禁止仲裁”的范圍內。這些法域的法院在司法實踐中亦對不可仲裁性持更加謙抑的態度,特別是對于國際仲裁,不輕易以爭議事項不可仲裁為由否定仲裁裁決。立法和司法的雙重協奏,促使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范圍不斷擴張。傳統上因涉及強行法適用和公共政策而不可仲裁的爭議,如與競爭、破產、證券、知識產權、侵權、消費合同、特許權、稅收、貿易制裁、腐敗賄賂等有關的爭議,現在在許多法域都已經可以仲裁。
可仲裁事項不斷擴張是國際商事仲裁發展的趨勢,已經引起國內學界關注研究,但研究成果基本都集中于介紹特定種類的爭議在其他法域由不可仲裁到可以仲裁的轉變,論證其具有可仲裁性的理論基礎,主張我國應當承認或明確這些爭議的可仲裁性。例如,有學者從公力救濟替代理論、成本收益理論之視角論證了反壟斷糾紛的可仲裁性,提出了反壟斷爭議可仲裁性的判斷標準及我國反壟斷糾紛仲裁機制的構建。(3)胡程航:《論反壟斷糾紛的可仲裁性判斷及實施機制》,載《國際經濟法學刊》2023年第1期。有學者分析了知識產權效力爭議可以仲裁的理論基礎和域外實踐,提出了我國推進知識產權效力爭議仲裁的基本路徑。(4)孫子涵:《我國知識產權效力爭議仲裁的理論基礎與實現路徑》,載《現代法學》2023年第1期。這些研究局限于探討特定種類爭議的可仲裁性,難免存在“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虞。在構建完善“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之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以下簡稱《仲裁法》)修訂在爭議事項可仲裁性問題上面臨或維持或擴張之選擇。要作出科學合理的選擇,必須首先澄清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的制度機理,慎思其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與危害。但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付闕如,本文意在以更加宏觀的視角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研究,冀對修訂《仲裁法》相關條文有所裨益。
一、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的主要原因
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不斷擴張是既成事實,必然有其原因和合理性。對于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的理據或原因這一重要問題,國內外僅有極個別學者在相關論著中附帶提及和粗略論證,且不同學者的觀點大相徑庭。有論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的發展和新經濟現象的涌現。(5)趙健:《國際商事仲裁的司法監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189頁。有論者認為,原因在于國家整體利益考慮、承擔《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紐約公約》)規定的責任、對國家仲裁制度和仲裁員水平的信任、減輕國家法院的過度擁擠等。(6)楊良宜等:《仲裁法:從1996年英國仲裁法到國際商務仲裁》,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14頁。有論者認為,原因在于市場經濟的深化與拓展、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深化與拓展、全球化時代的交互影響和對仲裁本質的理性認識。(7)歐明生:《民商事糾紛可仲裁性問題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139頁。基于對國際商事仲裁理論與實踐的理性認知,筆者以為,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是如下四個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結果。
(一)擴張內因: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拓展
國際商事仲裁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產物。(8)Julian D.M. Lew,Loukas A. Mistelis &Stefan M. Kr?ll: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3,p.244.國際商事仲裁之所以成為解決國際商事爭議最常用的方式,根本原因在于其充分體現和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當事人在自主自愿基礎上達成仲裁協議。有效仲裁協議的要素之一,就是要明確界定提交仲裁解決的爭議事項。當事人在約定提交仲裁的爭議事項時,可能會有意無意突破法律規定的可仲裁事項范圍,將法律規定的不可仲裁的爭議提交仲裁。這就會出現當事人意思自治與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及其體現的公共政策的沖突與協調問題。
對此,著名國際貿易法專家施米托夫曾經指出:“仲裁條款是合同中的一個特殊類型的條款,應該首先考慮的總是實施當事人關于通過仲裁解決他們之間的爭議的意圖。……對該規則的唯一限制只能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要求。”(9)[英]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趙秀文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626頁。也就是說,只要不涉及公共政策或者雖然涉及但不會損害公共政策,就應當認可仲裁協議的有效性,滿足和實現當事人仲裁解決爭議之意圖。是故,仲裁庭和法院一般都不會輕易否定仲裁協議的有效性。特別是在國際商事仲裁中,面對當事人提交的按照特定國家法律不可仲裁解決的爭議事項,仲裁庭和有關國家法院往往會基于仲裁的國際性、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爭議事項與本國沒有實質聯系因而不會損害本國公共政策等因素之考量,傾向于認定仲裁協議有效,默認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由此一來,公共政策的適用范圍受到嚴格限制,意思自治原則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大。(10)張艾清:《國際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事項的可仲裁性問題研究》,載《法學評論》2007年第6期。實踐表明,特定種類的爭議由不可仲裁到可以仲裁,都始于當事人約定的推動。如果當事人不充分行使意思自治的權利,嚴格依法只將法律規定的可以仲裁的爭議提交仲裁,就不可能出現可仲裁事項擴張的現象。可以認為,當事人行使意思自治的權利以及仲裁庭和法院對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是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不斷擴張的內在原因。
(二)擴張外因:國際商事仲裁的競爭優勢
與訴訟及其他替代爭議解決機制相比,仲裁具有終局性、快捷性、程序靈活性、保密性和專業性等比較優勢。相較于國際民事訴訟和國際商事調解,國際商事仲裁具有兩大核心競爭力。一是更高程度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如果不選擇仲裁,發生爭議后又不能達成妥協或和解,就只能到一方當事人所在國法院進行訴訟。在訴訟中,法院地一方當事人相較于外國當事人,他們更加熟悉本國的司法制度和訴訟程序,能夠獲得更加充分的信息,享有更多的便利,總體上處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任何國家的法官事實上都會偏向于其本國當事人,這一現象普遍存在,在有些案件中還有很好的理由。(11)Peter Cornell &Arwen Handley,Himpurna and Hub: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port, Sept. 2000.故法院訴訟不適合于解決國際商事爭議。而如果選擇仲裁,基于意思自治原則,當事人有權選擇中立的仲裁地和中立的仲裁員,可以選擇適用于案件的程序規范和實體規范,從而保證仲裁裁決更加公平公正。(12)Mahmood Bagheri:International Contracts and National Economic Regulation:Dispute Resolu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0,p.105.二是裁決具有更強的全球可執行性。無論是訴訟還是仲裁,最終目的都在于維護和實現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國際商事爭議的顯著特點是其國際性,由此決定了判決或裁決往往需要他國承認與執行。國際社會至今沒有承認與執行外國法院判決的全球性多邊國際公約,一國法院作出的判決往往只能在該國得到強制執行。法院判決難以跨國承認與執行,是國際商事交易當事人不愿意選擇訴訟的又一重要原因。仲裁的圖景則完全不同。現今已有172個國家加入了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紐約公約》,在任一締約國作出的仲裁裁決,其他171個締約國的法院都有義務承認與執行,除非存在公約第五條明確列舉的可以拒絕承認與執行的七種有限情形。
正是由于具有中立性、公正性和裁決可全球執行性,國際商事仲裁被譽為“唯一適合于解決國際商事交易中產生的或與此相聯系的爭議的程序”(13)[英]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趙秀文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頁。。也正是由于國際商事仲裁具有的競爭優勢,商人們總是希望用仲裁方式解決其全部跨國爭議,而不管特定國家法律有何禁止或限制。當有關國家法律出于公共政策等考慮而禁止或限制將某種爭議提交仲裁解決時,他們也總是試圖突破這些禁止或限制。如果沒有這些獨特優點和競爭優勢,商人們只會拋棄國際商事仲裁,就不可能出現可仲裁事項不斷擴張的現象。因此可以認為,國際商事仲裁的競爭優勢是催生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的外在原因。
(三)擴張推力:國家支持仲裁的政策
可仲裁事項的范圍同一個國家的司法對仲裁的態度密切相關。仲裁與訴訟是相互競爭的關系,各國法律在承認仲裁的同時又賦予法院對仲裁的監督權。在仲裁發展史上的很長時期,各國法院在行使司法監督職能時,對仲裁普遍持不信任甚至敵視態度。例如,英國法院在司法實踐中長期對仲裁不信任,認為法院的管轄權不容當事人以任何方式予以剝奪。(14)王小莉:《英國仲裁制度研究(上)——兼論我國仲裁制度的發展完善》,載《仲裁研究》2007年第3期。美國法院在歷史上也長期認為仲裁協議不具有可執行性,法院可以以仲裁協議剝奪了法院管轄權且有悖公共政策而撤銷仲裁協議。(15)高曉力:《國際私法上公共政策的運用》,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頁。由于對仲裁不信任,法院對爭議事項是否可以仲裁的認定嚴加管控和嚴格解釋。在如此生態環境中,仲裁受到司法嚴重打壓,不可仲裁性原則被各國法院頻繁援引,(16)[美]加里.B.博恩:《國際仲裁:法律與實踐》,白麟,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09頁。可仲裁事項被嚴格限定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不可能擴張。
但近幾十年來,隨著仲裁日益常態化、規范化和制度化,特別是在“訴訟爆炸”時代為了減輕法院自身負荷與壓力,各國法院對仲裁的態度逐漸轉向信任、接納,甚至支持。仲裁不再被認為是對司法和司法權的侵犯,而被視為一種能夠公平解決爭議的機制。(17)張艾清:《國際商事仲裁中反壟斷爭議的可仲裁性問題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頁。在這種理念支配下,越來越多的法院認為,應當尊重當事人選擇仲裁的自由,應當保障當事人仲裁意圖的實現。在對待可仲裁性問題的態度上,傾向于弱化司法干預和監督,不再輕易支持一方當事人提出的爭議事項不可仲裁的抗辯。自《紐約公約》生效以來,以爭議事項不可仲裁為由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情形極其少見。(18)Herbert Kronke,Patricia Nacimiento,Dirk Otto &Nicola Christine Port: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A Glob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1,p.305.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以爭議事項不可仲裁作為抗辯理由的案件,抗辯成功率僅為15%。(19)Roger P. Alford,Crina Baltag,Matthew E.K. Hall &Monique Sasson:Empirical Analysis of National Courts Vacatur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wards,J. INT’L ARB, 2022(39).
法律服務市場競爭是現代國家間競爭的重要內容,建設國際爭議解決中心是一些國家或地區確立的競爭目標。為此,美國、英國、法國、瑞典、瑞士、新加坡、香港等國家和地區都轉向奉行支持仲裁的政策。要支持仲裁和建設國際仲裁中心,就必須弱化司法對仲裁的干預,放寬“不可仲裁性”限制。在那些爭取構建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的國家和地區,其仲裁法或相關立法中不再有“可仲裁”或“不可仲裁”的爭議清單,只是籠統地規定涉及公共政策的爭議不可仲裁。不難設想,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限制可仲裁的爭議事項范圍,某類爭議在該國或該地區不可仲裁而在其他國家可以仲裁,勢必將該類爭議的仲裁推向其他國家或地區,從而失去競爭優勢。恰如有論者指出,國家基于成為國際仲裁中心的目的,轉而站在支持仲裁的立場上,其結果是可仲裁事項范圍日益擴張。(20)杜新麗:《國際商事仲裁理論與實踐專題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頁。
(四)擴張引力:域外立法的影響
國際語境下的“可仲裁性”問題取決于法律選擇與適用。在國際商事仲裁的不同階段,都可能提出爭議事項是否可以仲裁的問題。在不同階段,法院或仲裁庭適用的法律可能是不同的。在訴訟階段,受理訴訟的法院會適用法院地法判定爭議事項是否可以仲裁;在仲裁階段,仲裁庭或法院通常會適用仲裁地法;在裁決撤銷階段,法院會適用裁決作出地法(通常但不必然是仲裁地法);在承認與執行階段,法院會適用承認與執行地法。例如來自A、B兩國的當事人約定在C國適用D國法律進行仲裁,仲裁庭在E國作出裁決,勝訴方到F國或更多國家去申請承認與執行。由于不同國家的法院在不同階段通常都會適用其本國法律,故上述國家的法律都有可能得到適用。如果其中一些國家認為爭議事項可以仲裁,而另外一些國家認為爭議事項不可仲裁,就會出現相互矛盾或沖突的結果。
為了避免出現矛盾和沖突,一些國家的立法,特別是司法實踐,會考慮該爭議在其他相關國家是否可以仲裁,會區分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加以不同對待。特別是,與國內仲裁案件相比,國際仲裁案件與法院地國聯系較為松散甚至沒有聯系,對法院地國的影響較小甚至沒有,故法院對國際爭議的可仲裁性往往持更加寬松的態度,不輕易以國內法規定否定國際性質的同類爭議的可仲裁性。(21)張艾清:《國際商事仲裁中反壟斷爭議的可仲裁性問題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66頁。美國法院的實踐最為典型。在一系列案件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主張在國際爭議領域中適用國際禮讓原則,不能把國內不可仲裁的觀念機械地適用于國際仲裁;他們認為,狹隘的國家利益應當服從于日益增長的國際貿易的廣泛利益,任何具有國際商事性質的仲裁協議或裁決都可以得到執行,而不管其是否與傳統的可仲裁性標準或公共政策標準相一致。(22)Jay R. Sever:The Relaxation of Inarbitrability and Public Policy Checks on U.S. and Foreign Arbitration:Arbitration out of Control?Tulane Law Review, 1991(6).法國、英國、瑞士等國的立法或司法實踐還主張,不應當適用特定國家的法律來判定國際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出現了認定爭議事項可仲裁性的國際統一實體規范。(23)石現明:《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獨立性新解》,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劉曉紅:《國際商事仲裁專題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5頁。在很多國家,某類爭議由不可仲裁到可以仲裁大都是從國際仲裁開始的,涉及反壟斷、知識產權、破產、腐敗賄賂的國內爭議不可仲裁的,而同樣涉及這些問題的國際爭議則可以仲裁。故可認為,是不同國家立法的相互影響,進一步刺激了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的擴張。
二、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的消極效應
雖然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既有立法和司法實踐基礎,又有內在外在原因和動力,總體上亦符合國際商事仲裁發展和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之需要。但由于可仲裁事項與公共政策、可自由處分等概念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起,對這些模糊概念采取不同立場予以彈性解釋,就會對爭議事項可仲裁性得出不同結論。善意的擴大解釋,可能成全相關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反之,則會限縮可仲裁的爭議事項范圍和仲裁的存在空間。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不斷擴張,由國際商事仲裁庭裁決關涉公共政策或強行法適用的爭議,可能會產生一系列消極后果。這是其辯證效應。
(一)侵蝕國家司法主權
司法主權是國家主權獨立的重要表征,司法也是公正的最后防線,故國家有義務設立和維持法院等司法機構為民眾提供爭議解決服務。另一方面,在純粹私法領域,國家應當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允許當事人將其有權自由處分的爭議提交仲裁等替代性、民間性爭議解決機制解決,在一定程度上讓渡司法管轄權和司法主權。仲裁之民間性和私人性,決定了它只能裁決私人之間當事人可以自由處分的爭議,不得介入公法和強行私法領域。為了保證本國公法和強行私法規范得到一體遵循,國家將這些爭議確定為法院專屬管轄范圍,不允許仲裁介入。
爭議事項的可仲裁性“是一國法律在可仲裁與不可仲裁的爭議事項之間劃出的一條明確的界限”(24)劉想樹:《中國涉外仲裁裁決制度與學理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頁。,“界定了契約自由之終點和司法公權之起點”(25)Thomas E. Carbonneau &Francois Janson:Cartesian Logic and Frontier Politics:French and American Concepts of Arbitrability,Tul J Int’l &Comp L, 1994(2).。可仲裁事項的范圍與國家司法管轄權的范圍呈此消彼長的關系。可仲裁事項不斷擴張,及于公法和強行私法爭議,必然會限縮國家法院的專屬司法管轄權范圍,侵蝕國家司法主權,破壞公法和強行私法的統一實施。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及于公法爭議,還會壓縮有關國家根據實際情況制定或調整管控市場經濟的政策和法律的空間,危及國家經濟管理主權。
(二)損害國家公共政策
商人的目標追求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置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于不顧。為了維護市場交易秩序,調整規制商事交易行為,防止當事人將交易成本外部化進而對公共政策造成損害,許多國家制定了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證券法等法律,介入私人商事交易活動。這些公法的公開、統一、有效實施,對于維護一國的市場經濟秩序和公共政策至關重要。
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及于涉及公法和強行私法適用的爭議,可能會損害有關國家的公共政策。國際商事仲裁都是保密的,對于這類公法爭議的整個仲裁程序甚至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社會公眾難以及時知曉,國家及其監管部門難以有效監督。國際商事交易當事人為了實現私人利益最大化,有可能利用仲裁來規避對其不利的強制性公法規范的適用。國際商事仲裁庭和仲裁員不是國家機構和國家公職人員,不像法院和法官那樣負有保證國家法律統一實施的義務,他們可能根本不熟悉,因而難以正確適用特定國家的強制性公法規范,也可能為了迎合當事人或尊重當事人選擇的實體法而拒絕適用本應適用的有關國家的公法規范。這樣一來,就會使那些旨在防止交易成本向外轉移給第三人的強制性法律規范得不到有效實施。如果第三人能夠利用這種方式規避強制性規范,商業規制的全部圖景就會改變,因為所有規范都將變成任意性規范,當事人就能夠將許多被強制內部化的成本外部化。這種伎倆破壞了旨在使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協調一致的強制性法律,可能減損社會福利。(26)Andrew T. Guzman:Arbitrator Liability:Reconciling Arbitration and Mandatory Rules, Duke Law Journal, 2000(5).這是反對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的主要原因,也是各國對“可仲裁事項”施以“公共政策”限制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
(三)減損仲裁裁決的合法性
如果可仲裁事項擴展到涉及公法和強行私法適用的爭議,仲裁裁決的合法性將可能難以得到保證。公法和強行私法是任何人都必須遵守的,必須得到有效和統一執行。但在國際商事仲裁中,當事人享有極大的法律選擇自主權。如果涉及公法和強行私法適用的爭議也可以仲裁,當事人出于規避法律之目的,完全可能不選擇適用本應適用的較為嚴厲的公法和強行私法。如上所述,即使當事人沒有進行法律選擇,出于迎合當事人以便獲得更多被指定的機會,仲裁員也愿意而且能夠選擇適用對雙方當事人均更加有利的法律。
在一項調查中,90%的仲裁員相信他們可以輕松自由地忽略或忽視有關國家的公法和強行私法規范。(27)張圣翠:《國際商事仲裁強行規則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頁。也就是說,當今的國際商事仲裁活動實際上是處于非法化或規范性不足的狀態。由此,本應適用的公法和強行私法會因為當事人的選擇或仲裁庭的利益平衡而被排除適用,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不合理的法律適用,裁決結果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國際投資仲裁是仲裁介入公法爭議的典型例子,近年來引起一些國家政府質疑和國內外學術界熱議,進而推動ICSID仲裁改革的國際投資仲裁合理性、合法性危機就是最好例證。
(四)降低爭議處理結果的確定性
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及于涉及公法和強制性私法的爭議,會增大爭議處理結果的不確定性。首先,仲裁裁決不一定能得到其他國家承認與執行。前述涉及公法和強行私法的爭議只在少數仲裁大國或主要國際商事仲裁中心所在國可以仲裁,而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不可仲裁。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當事人,出于規避本國強行法或者看重國際商事仲裁優點之考慮,會選擇到允許將這些爭議提交仲裁的國家仲裁,而仲裁裁決又可能需要向一方當事人本國或其他不允許將該類爭議提交仲裁的國家申請承認與執行。按照《紐約公約》的規定,承認與執行地國法院會依據其本國法律認定該爭議事項是否可以仲裁,極有可能最終判決或裁定拒絕承認與執行該仲裁裁決,致使爭議處理結果難以預測。
其次,可能會導致爭議處理結果不一致。在不具有可仲裁性之前,公法爭議和強行私法爭議只能由制定這些法律的國家法院管轄和裁判,不會出現挑選法院的情況,判決結果總體上是一致的。而當這些爭議可以仲裁后,由于國際仲裁庭在作出裁決時可能不適用或不嚴格適用這些公法和強行私法,就會出現法院判決與仲裁裁決結果不一致的情形,還會出現不同仲裁庭作出不一致的仲裁裁決的情形,導致爭議解決結果缺乏確定性和可預見性。
三、我國應對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的策略選擇
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是雙刃劍。合理把握和界定可仲裁事項和不可仲裁事項的界限,實現二者的協調與平衡是關鍵,既不能固守傳統的不可仲裁性標準,也不能無限制地擴張可仲裁事項范圍。在構建“一帶一路”爭議解決機制和修訂《仲裁法》背景下,我國應當理性看待其他國家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的擴張,作出恰當的策略選擇和合理的制度安排。
(一)適度擴大涉外商事仲裁的可仲裁事項范圍
“一帶一路”倡議贏得了沿線國家的積極支持和高度贊譽,但“一帶一路”經貿合作必將催生大量國際經貿爭議,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爭議解決機制。2018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通過的《關于建立“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和機構的意見》,提出積極培育并完善訴訟、仲裁、調解有機銜接的爭端解決服務保障機制,切實滿足中外當事人多元化糾紛解決需求。“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市場化運作,公司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主體,“一帶一路”建設爭議主要是不同國家私人主體之間的商事爭議。仲裁是解決國際商事爭議的最佳方法和常用方式。筆者以為,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的重點和關鍵應是改革完善我國涉外商事仲裁制度,提升我國涉外商事仲裁的國際競爭力。
要提升我國涉外商事仲裁的國際競爭力,一個重要舉措就是確立和奉行支持仲裁的政策,擴大涉外仲裁可仲裁事項的范圍。我國現行《仲裁法》第2條和第3條采用正向和反向列舉方式嚴格限定了可仲裁事項范圍,這些規定同樣適用于在我國進行的涉外商事仲裁。我國在加入《紐約公約》時作出了“商事保留”,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紐約公約》的通知也以列舉方式界定了可以仲裁的商事爭議的范圍。按照我國現行法律和司法實踐,前述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可以仲裁的涉及強行法適用或公共政策的很多爭議在我國是不可仲裁的,或者可否仲裁在立法上是不明確的。例如,在我國法院2015-2021年受理的6個與反壟斷有關的仲裁案件中,當事人之間均有仲裁協議,但法院判決認定反壟斷糾紛不可仲裁的就有4個,反壟斷糾紛仲裁存在法律障礙。(28)胡程航:《論反壟斷糾紛的可仲裁性判斷及實施機制》,載《國際經濟法學刊》2023年第1期。“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了許多創新性的經貿合作模式和構想,“一帶一路”經貿合作呈現出異型化、多樣化、復雜化特征,“一帶一路”建設中必將出現許多新型爭議,依據我國現行《仲裁法》,有些爭議可能是不可仲裁的。如果當事人希望通過仲裁而不是訴訟來解決這些爭議,他們就只能選擇到那些認可這些爭議的可仲裁性的國家或地區去仲裁,我國涉外商事仲裁將因此失去競爭優勢。為促進我國涉外商事仲裁的發展,為滿足當事人將“一帶一路”建設爭議提交仲裁解決的需要和追求,筆者主張適度擴大我國涉外商事仲裁的可仲裁事項范圍。
一是《仲裁法》修訂應當改變涉外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的立法模式,概括性地規定當事人可自由處分的爭議,包括附帶涉及強行法適用和公共政策的爭議,均可仲裁。(29)《仲裁法(修訂)》(征求意見稿)第二條規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下列糾紛不能仲裁:(一)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二)法律規定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的,從其規定。”該條規定與現行《仲裁法》第二條和第三條相比,僅有個別文字表述差異,并無實質性修訂。就“一帶一路”建設爭議而言,只要是商事主體之間的爭議,無論是否是商事爭議,無論是否具有經濟內容,無論是否關涉有關國家強行法適用和公共政策,都應可以仲裁,并應鼓勵當事人通過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立法還應當以某種方式明確規定,商事主體之間附帶涉及競爭法、破產法、知識產權法、證券法、侵權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特定類型的復合型爭議均可仲裁。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應當樹立支持信任仲裁的理念,對在我國進行的涉外商事仲裁,如對所涉爭議事項是否可以仲裁存在疑義,則應盡可能推定其可以仲裁;對在我國法院尋求承認與執行的外國仲裁裁決,只要不損害我國公共政策,均應承認所涉爭議的可仲裁性,不輕易支持被申請人提出的爭議事項不可仲裁的抗辯。
二是適時撤回加入《紐約公約》時所作的“商事保留”。雖然《紐約公約》允許締約國作出“商事保留”,但公約本身沒有對“商事”作出界定,不同國家對“商事”的理解差異較大,故172個締約國中只有57個作出了“商事保留”,大多數主要國際商事仲裁中心所在地國,如英國、法國、瑞士、瑞典、新加坡等,都沒有作出“商事保留”。即使在那些已經作出“商事保留”的國家,絕大多數法院也都對“商事”做寬泛解釋。(30)Herbert Kronke,Patricia Nacimiento,Dirk Otto &Nicola Christine Port: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A Glob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York Convention,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11,p.13.我國最高法院關于執行《紐約公約》的通知也只是采用概括定性加不完全列舉的方式來界定“商事”的范圍,所列舉的商事爭議范圍本身也已經突破了“商事”這一概念的傳統外延。基于此,為彰顯我國對涉外和國際仲裁的包容態度和支持立場,吸引外國當事人選擇到我國仲裁,便利外國仲裁裁決在我國的承認與執行,以及我國涉外仲裁裁決在外國的承認與執行,筆者建議適時撤回我國對《紐約公約》所作的“商事保留”,進一步放寬對可仲裁事項的限制。撤回“商事保留”后,如果在其他締約國作出的非商事爭議的仲裁裁決在我國的承認與執行會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法治等產生負面影響或損害,我國法院仍然可以動用公約第5條第2款第2項之“公共政策”理由拒絕承認與執行該仲裁裁決。
(二)堅守涉外商事仲裁不可仲裁事項的邊際
盡管各國法律規定不同,但均認為國際商事仲裁應以當事人合意為前提,而當事人意思自治又總會受到各種限制,如“當事人雙方談判實力對等”“不侵犯第三方或國家利益”“不違反公共政策”“不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等。當事人約定將爭議提交仲裁的自由也應當受到必要限制。筆者主張,我國在適度擴大涉外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范圍的同時,也應當明確規定和堅持下列爭議,包括“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下列爭議不可仲裁,只能訴訟解決。
一是單純涉及政府管理的爭議。商事性是國際商事仲裁的根本屬性,爭議的商事性,或所涉權利義務的可自由處分性,是爭議具有可仲裁性的前提條件。國際商事交易,包括貿易、投資、融資、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等,大多受有關國家,特別是東道國法律的嚴格監管。國際商事領域的爭議既有平等主體之間的交易爭議,又有國家或政府與交易當事人之間的管理爭議。附帶涉及政府監管的國際商事交易爭議在本質上仍然是商事爭議,仍然可以仲裁解決,但以仲裁及其裁決不違反有關國家的強制性法律規范和不侵犯有關國家的監管主權為前提。單純因為政府對國際商事交易活動的監管而引發的政府與私人之間的爭議本質上屬于行政爭議,涉及國家主權及其行使,理當不可仲裁解決。事實上,即使在那些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不斷擴張的國家,單純涉及政府管理的爭議迄今為止仍不可仲裁解決。為維護我國國家主權,確保我國對涉外經貿活動實施有效監管,我國應當繼續堅持單純涉及我國政府管理行為的爭議不可仲裁之原則和底線。
二是單純涉及強行法適用的爭議。強行法包括公法和強行私法。公法和強行私法關涉一國的基本社會經濟秩序、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體現一國的重大公共政策,不允許當事人私自處分。單純涉及公法,如憲法、刑法、行政法和經濟管理法等適用的爭議,在任何國家都不可以仲裁。涉及諸如婚姻、家庭、繼承、監護和撫養等領域的強行法適用的民事爭議,由于當事人不能自由處分,通常也是不可仲裁的。但對于國際商事交易爭議,即使涉及強行法的適用,如涉及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商業賄賂法、知識產權法和破產法等的適用,只要仲裁庭能夠準確解釋和正確適用應當適用的有關國家的強行法,保證不影響或損害有關國家的公共政策,則可以仲裁。實際上,所謂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主要指的就是后一類爭議以前不可仲裁而現在可以仲裁。我國應當堅持單純涉及我國強行法適用的爭議不可仲裁。但如果爭議只是附帶涉及我國強行法適用,或者單純涉及外國強行法適用而該外國允許仲裁,則該爭議仍可仲裁解決。
三是其他單純涉及公共政策的爭議。盡管“可仲裁性”與“公共政策”是不同概念,具有不同指向和旨趣,但“公共政策”是判斷爭議“可仲裁性”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標準。涉及公共政策的爭議當事人無權自由處分,當然不能由民間仲裁庭仲裁解決。正因為如此,任何國家都不允許將涉及本國公共政策的爭議提交仲裁解決。即使在那些可仲裁事項不斷擴張的國家,不管法律是否明確列舉可仲裁事項的范圍,實踐中都將爭議涉及“公共政策”作為“可仲裁”的例外。我國應當堅持涉及我國公共政策的爭議不可仲裁。當然,對于“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商事爭議和其他國際商事爭議,我們不應僅僅因為該爭議按照我國法律涉及公共政策,但事實上爭議處理結果并不關涉我國公共政策,而否定其可仲裁性。
(三)嚴格對公共政策和強行法適用的司法審查
如前所述,如果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擴張及于涉及強行法適用和公共政策的爭議事項,國際商事仲裁當事人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可能會通過選擇仲裁地或實體問題準據法之方式規避本應適用的有關國家的強行法,仲裁庭也可能出于迎合當事人之目的而不適用本應適用的有關國家的強行法。由此一來,有關國家制定強行法的目的就會落空,強行法所體現的公共政策將會受阻。司法是公正的最后防線,也是保證法律統一實施和維護公共政策的最后手段。可仲裁事項擴張帶來的這些消極后果,只能由司法予以控制和補救。有論者在主張反壟斷糾紛可以仲裁的同時,強調需要對仲裁裁決進行司法審查,使超越糾紛法律性質的社會公共利益得到保護。(31)童肖安圖:《社會公共利益視角下壟斷糾紛可仲裁性研究》,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通過司法審查確保反壟斷糾紛中的消費者權益、社會公共利益未招致損害,實現仲裁解決反壟斷糾紛的有效性和公正性。(32)胡程航:《論反壟斷糾紛的可仲裁性判斷及實施機制》,載《國際經濟法學刊》2023年第1期。筆者同樣認為,我國在擴大可仲裁事項范圍的同時,必須強化司法審查監督。
為了防止當事人利用國際商事仲裁規避強制性法律規范和損害公共政策,美國和歐盟等在承認競爭法爭議可仲裁性的同時,強調對仲裁裁決進行后續司法審查,保留法院對仲裁員是否適用競爭法進行“二次審查”(second look)的機會。(33)Gary B. Born: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9,pp.796~797.美國和歐盟法院的這一做法同樣適用于其他涉及強行法適用和公共政策的仲裁裁決。其他許多國家在允許可仲裁事項范圍擴張的同時,也都強化司法審查監督。如果仲裁裁決沒有正確適用本應適用的本國強行規范或損害了本國公共政策,裁決作出地國法院往往會撤銷仲裁裁決,承認執行地國法院也都會拒絕承認與執行該仲裁裁決。
筆者因此主張,我國在擴大涉外仲裁可仲裁事項范圍,允許當事人將附帶涉及公共政策和強行法適用的爭議提交仲裁解決的同時,為了保證我國的強行法得到有效實施,切實維護我國的公共政策,我國法院應當在仲裁裁決撤銷程序和外國仲裁裁決承認與執行程序中,強化司法監督,嚴格審查仲裁程序和仲裁裁決是否正確地解釋和適用了應當適用的我國強行法,是否損害我國的社會公共利益,并給予相應司法補救。對于在我國進行的“一帶一路”建設爭議仲裁,我國法院還應當強化對仲裁裁決是否符合我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的政策立場的審查,確保仲裁裁決符合“一帶一路”倡議的宗旨、目標和原則等政策主張。為保障“一帶一路”建設項目東道國國家主權,維護項目東道國公共政策,確保東道國法律實施,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和推動者,我國司法機關也應當在撤銷程序和承認執行程序中加強對“一帶一路”爭議仲裁裁決是否遵守和適用應當適用的“一帶一路”國家的強行法以及是否符合有關國家的公共政策的審查監督,合理審慎地把握其中的可仲裁性標準,維護沿線國家在可仲裁性中所寄托的公共政策,尊重沿線國在可仲裁事項上的關切和基本立場。
四、結語
爭議事項可否仲裁是國家劃定的司法管轄權和仲裁管轄權的界限,可仲裁事項的范圍設定了仲裁庭管轄權的最大邊界,逾越該界線的仲裁裁決是無效的。但可仲裁事項的邊界不是天然的,也不是確定不變的,而是立法選擇的結果。隨著人們對仲裁認識的發展和態度的轉變,出于尊重當事人用仲裁方式解決爭議之愿望與需求,出于提升本國仲裁服務的國際競爭力之考量,在許多國家,特別是在主要國際商事仲裁中心所在地國,至少在國際商事仲裁中,先前基于保障強行法實施和維護公共政策之目的而不可仲裁解決的爭議逐步變得可以仲裁,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的范圍不斷擴張。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的擴張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正當性,我國應當順應可仲裁事項擴張之國際趨勢,適當擴大涉外仲裁和國際仲裁的可仲裁事項范圍,凡是當事人有權自由處分的爭議都應可以仲裁解決。這在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之當下尤應如此。
任何事物有利必有其弊,國際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項的擴張亦有其消極作用和負面效應。我國在擴大涉外仲裁可仲裁事項范圍,允許將附帶涉及強行法適用和公共政策的爭議提交仲裁解決的同時,應當堅守單純涉及政府行政管理、單純涉及強行法適用及其他單純涉及公共政策的爭議不可仲裁之底線原則,將這些爭議列入法院專屬管轄的范圍。對于那些附帶涉及強行法適用和公共政策的仲裁及其裁決,應當強化和嚴格司法監督,授權法院對這些仲裁裁決進行“二次審查”,確保仲裁裁決正確適用我國的強行法,符合我國的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