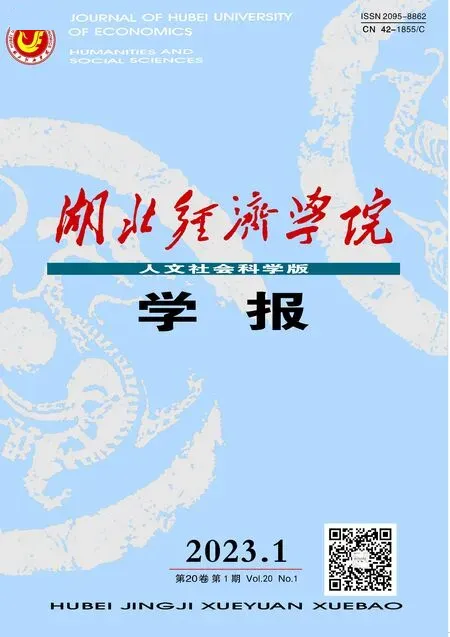英語戲劇中隱喻漢譯策略對比研究
——以朱生豪和許淵沖的《第十二夜》漢譯本為例
張子龍,何明霞(湖北經濟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一、引語
戲劇是一門獨特的綜合藝術,其文本兼具語言學及翻譯學方面的極大研究價值。而論及英語戲劇,便不得不提到被譽為“英國戲劇之父”的莎士比亞,其一生共著有三十七部戲劇作品,每部作品都令人拍案叫絕。而莎劇當中無論是精妙的遣詞造句,還是生動的修辭格律,都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文學影響。這些學術價值跨越時空,歷久彌新,不斷吸引著不同時代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譯者立志化用不同的語言文字,將之進行二次演繹。也因此,戲劇翻譯逐漸成為國內外近現代文學翻譯學者研究的一大思路。
戲劇的文本相比其他常見文學作品類型具有更為復雜的特征,其文學價值是劇作的文學表意和表演實踐兩大要素的復合。誠如英國翻譯理論家蘇姍·巴斯內特(Bassnett,1985)的觀點,戲劇文本的翻譯實踐過程應當不僅僅只是源語言文本到目的語文本的單純轉移,還涉及語言學層面之外[2]。莫娜·貝克(Baker,1998)也認為戲劇藝術是具有雙重性的,因而要求翻譯過程中需要體現語言同視象、音效的有機結合[1]。
由于不同譯者所處歷史背景及所持翻譯理念存有一定差異,也在各自的英語戲劇漢譯實踐中,對于諸如直譯與意譯、選詞歸化與異化、文化調整與適應等翻譯思想加以選擇應用,從而產生了各具特色的理論與思路。本文將通過對比研究的方式,依托認知語言學中概念隱喻的理論架構,以戲劇翻譯界中主流認可的文學表意性和表演實踐性作為兩大衡量指標為評價標準,比較分析朱生豪和許淵沖兩位翻譯獨具風格的學者譯本,研討英語戲劇中隱喻漢譯的恰當策略,并借此擴大認知語言學理論在文學翻譯過程的交叉運用實踐。
二、隱喻修辭和概念隱喻的相關研究
在文學作品當中,隱喻不單單在文學修辭方面起著畫龍點睛的作用,同時也極為精妙地推動著情節發展、反映著角色心理。盡管多數人認為“隱喻僅是文學作品中的一種常見修辭手段,常用于加強描寫、深化表意”,但隨著語言學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有關隱喻的研究前景也得以不斷擴展。認知理論的研究表明,隱喻實際也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并不局限在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文字編排之中。因此,要從認知語言學層面探討文學作品中的隱喻,就需要聯系到概念隱喻的理論。
(一)隱喻研究的伊始和發展
關于隱喻的早期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修辭學》(Rhetoric)中表述的相關觀點。亞里士多德認為隱喻同其他修辭一樣,具有語言的說服功能,自此修辭也首次與論辯聯系起來,這為后世有關隱喻的諸多理論,如“對比論”“類比論”“互動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有國內學者認為,隱喻修辭在我國最早能追溯至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作品,并與《詩經》中常用的“賦比興”手法中的“比”相鄰近[6]。但有關隱喻較成系統的理論性研究可以認為是在近五十年才漸成規模。
至20世紀,美國學者喬治·萊考夫與馬克·約翰遜在二人共著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1980)一書中,將原先隱喻在修辭學、語義學視野上的研究拓展,并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概念隱喻”的理論。該理論的誕生與發展使得隱喻的研究基準自文學修辭與語言現象層面,拓寬到了認知手段和思維方式層面,并進一步連貫了隱喻中的文學涵意與思維表達。自此,迎來了各界學者爭相通過多視角從認知層面對隱喻開展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全新局面。可以認為,當把概念隱喻理論引入至翻譯研究時,就應當多角度地思考隱喻在文學翻譯過程可能產生的多樣影響。
(二)概念隱喻的本質及分類
萊考夫與約翰遜(1980)建立的概念隱喻理論認為,隱喻不僅僅是一種修辭手段或是詩學表達,應將其放諸語言層面外研究,結合人類的基本認知機制,使目標讀者能夠通過相對熟知的事物來認識、理解、甚至體驗相對陌生的事物[3],即在始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標域(Target Domain)兩個概念域范疇之間能夠建立一定的跨域映射(Mapping)。因此隱喻在認知層面表現出了諸如普遍性、概念性、系統性和體驗性等特征。同時也可以通過始源域的差異,可以將概念隱喻分為本體隱喻、方位隱喻和結構隱喻三大類型。
其中,本體隱喻(Ontological Metaphor)是指借助了有形的物質和實體來呈現概念化的抽象事件、經歷、情感等的隱喻表達,具有指稱、量化等功能。容器隱喻(Container Metaphor)則是該類隱喻中一種常見子類,主要特征在于往往選用有邊界的容器來完成上述抽象概念的表達。同理,文學語言中常見的擬人手法亦屬于本體隱喻的范疇。
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則是通過組織構建一個具有空間性質的概念系統,從而使非空間概念在空間結構上得到映射,并就此具有一定的空間方位,最終完成表意的隱喻類型。故其往往會表現出具有相對意味的關聯性。
而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是用一個結構清晰、簡單而具體的熟悉概念來構建另一個結構模糊、復雜而抽象的陌生概念,特征在于其對于概念域的凸顯(Highlighting)和隱藏(Hiding)。故對于同一概念的結構隱喻,會因其始源概念的描述角度存在差異,產生關于多種目標概念的映射,從而得到更為豐富的表達。
三、莎士比亞、朱生豪、許淵沖與《第十二夜》
莎士比亞(1564—1616)的作品被譽為英國文學創作史上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可謂英語文學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莎翁傳奇的創作人生及其浪漫的詩意語言至今仍廣受學術關注,不少學者尚在爭相研究莎式語言的整體風格以及劇中角色的舞臺塑造。
《第十二夜》[4]作為莎士比亞創作的經典四大喜劇之一,講述了Viola和Sebastian兩兄妹因遇船難分離,在伊利里亞與公爵Orsino和Olivia小姐上演的諸多機緣巧合和陰差陽錯交織的愛情故事。但通過文獻檢索不難發現,該劇所受到的學術研究關注稍遜于其他三部同列為“四大喜劇”的莎劇,更是遠不及《麥克白》《哈姆雷特》等更具莎翁特色的悲劇作品。而《第十二夜》的相關研究,也是隨著不斷貼合時代進行改編的登臺演繹,主要研討其劇作主題,而在戲劇藝術表現以及其修辭語言內涵兩方面的研究,仍有一片廣袤天地值得探索。
(一)朱生豪翻譯風格概述
朱生豪(1912—1944),浙江嘉興人,一生為譯莎劇“功績奇絕”,共譯莎劇三十一部半。朱老翻譯態度嚴肅認真,將“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圍內,保持原作之神韻”立為自己翻譯的主要宗旨。其譯筆流暢,文詞華麗,多采用極為自由的散文體,使之譯本成為漢譯莎劇領域中最為流通,覆蓋讀者最廣的譯本之一。
朱生豪翻譯戲劇的思路同國外相關研究中注重戲劇藝術的兩重性的觀點不謀而合,同樣認可應從讀者與觀眾兩個角度去進行翻譯實踐。也因朱老深厚的文學造詣,其翻譯思想常為后人用“神韻說”這種中國古典詩學觀來加以概括,稱其譯作為“‘神韻說’之余音”,所以可以認為朱譯本不僅譯出了莎劇中固有的文學色彩與美感,還能再現出原作的“神韻”[5]。但與此同時,朱譯本雖竭力做到了“明白曉暢”,但也多有原句重組,損益原文之嫌,甚至在這個“再現”的過程中存有任意漏譯、諸多誤譯、強加詮釋的不足之處。故可以認為,朱譯本始終以漢語文化為基礎,是相當典型的“漢化”譯本,而有學者則認為此種譯法過于強調“中國化”且稍欠分寸。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由于朱生豪先生在忠實與準確層面的諸多考量,其譯本仍是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符合“優選法”的絕佳譯本。
(二)許淵沖翻譯風格概述
許淵沖(1921—2021),江西南昌人,從事翻譯七十余年的他,被譽為“詩譯英法唯一人”。相比在英漢互譯早期占據重要地位的“對等論”,許老提出了翻譯應是“美化之藝術,創優似競賽”的觀點,表露出中西語言間自有存在不對等之處,故應當以“優化論”的視角發揮譯語優勢予以彌補。同時進一步強調文學翻譯過程中應當不斷追求的“美”,故在其結合自身大量翻譯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歸納得出“三美論”(“意美、音美、形美”)的翻譯指導思想。
在許淵沖先生的翻譯生涯中,其譯作的源語文本多選用文學作品,且對中國傳統古典詩歌有明顯傾向,這是中國文化外宣時代背景的相當體現,故有眾多學術研究者對許老獨具特色的詩詞英譯格外關注。但亦有學者就此展開論證,認為許氏譯論所闡述的“三美”可以作為文學翻譯中審美批評層面的衡量標準。也點明當下多數研究仍囿于許老的詩詞英譯作品,而忽略了諸如許譯散文、許譯小說以及許譯戲劇,或是許老譯筆之下的漢譯作品同樣蘊藏著極富詩意的文學價值,同樣能夠展現其文學翻譯的較高造詣[10]。許淵沖先生獨樹一幟的文學翻譯理論具有較強的創新性和前瞻性,甚至從一定角度上對傳統翻譯理論的諸多局限有所突破,這對當下文學翻譯理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9]。
四、案例分析
莎士比亞所著劇作語言特征明顯,用詞豐富多樣,不難發現《第十二夜》的文本語言(在下文案例中記作ST)中有近百處隱喻性概念。隨著認知語言學界對于概念隱喻研究的深入,萊考夫與約翰遜所劃分的結構隱喻、本體隱喻、方位隱喻三類隱喻類型,在實際應用中必然存有一定交融,并無明顯界限劃分。本文將選取各類隱喻在《第十二夜》原作中最為明顯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譯例展開論述,同時聯系情節概要,以文學表達和演繹實踐為兩大主要評判標準,對朱譯本(記作TT1)和許譯本(記作TT2)展開比較。此外,在下文的分析當中,使用粗體句式“甲是乙”(同英語完全大寫的“A IS/ARE B”形式)作為概念隱喻解構后的基本形式,其中的 “是”(“IS/ARE”)應視作無特殊意義的表述標記。
(一)朱、許譯本中有關結構隱喻的翻譯
如前所述,結構隱喻的主要特征在于通過一定的凸顯和隱藏,構建起兩個概念的跨域映射,即:目標域雖不與始源域中概念一一對應,但在文本語境中仍存有一定共性關聯,并通過隱喻化的表達得以強化。由于結構性是概念隱喻的一大特征,故結構隱喻所涵蓋范圍廣于本體隱喻、方位隱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與此兩者有所重合。但實際上,結構隱喻強調的是概念進行跨域映射過程中存有的邏輯聯系。以下是一些典型譯例。
例1:

?
評析:當Sir Andrew用盡辛酸之辭打算向Viola宣戰時,Fabian對此深表懷疑,懷疑其挑戰信是否確有那么尖酸潑辣。此處運用結構隱喻“詞句是味道”(WORDS ARE FLAVOURS),凸顯出語言能附帶情感色彩的特征。顯然語句本身無臭無味,但通過這樣的隱喻表達,我們也能理解刻薄的語言正如醋般尖酸,帶有怒氣的話語也似辣椒一般潑辣,所以尖酸潑辣的句段自然會帶給讀者五味雜陳的感覺,能夠領略到其中滋味。正如前文分析中的用詞,可以認為此處結構隱喻之所以能建立這樣的映射,是因為該經驗基礎在中西方文化均存在。朱譯本中,選擇直譯Sir Andrew的臺詞而意譯Fabian的詞,可以認為是為了補充解釋此處隱喻,便于讀者和觀眾都能迅速理解其中涵義,也不易產生誤解。但相比之下,許譯則選擇保留了所有的隱喻性表達,是更加貼合原文的譯法。
例2:

?
評析:Antonio使用“善良是美貌”(VIRTUE IS BEAUTY)這一隱喻的延伸,來責備“忘恩負義的Sebastian”(實為喬裝后的Viola,只因兄妹二人長相極其相似)。顯然,美貌只要有了一處細小的瑕疵就會變得丑陋,而純潔心靈一旦有了瑕疵也自會誕生奸邪的品格。所以案例表達了不友善(unkind)者是“deformed”(畸形的),也就是丑陋的這一觀點。同理,在日常漢語表達中也會使用諸如“美德”“丑惡”的詞語出現,可見該隱喻誕生的經驗基礎在中西方文化中可以共享。另一方面,單獨研討案例中另一處隱喻“邪惡是箱子”(EVIL IS TRUNK)時,或可視其為典型的本體隱喻表達,這將會在下文中詳細探討。但若能理解此處的trunk是指莎士比亞時代用作家具的木箱,且其往往會有精美的雕刻裝飾,不難發現話語核心仍在闡述“品德好壞”與“內外美丑”之間的關系。在案例中,朱譯本比許譯本更好地接納了源語中這一含義及其文學表意,譯出了外美心惡的人正如虛有其表的家具間的聯系。而許譯本中,則是選取了trunk一詞的另一解,譯為“軀殼”,但回歸源語會發現或與“flourished”難以搭配,故此譯法仍待斟酌。此外,朱譯和許譯中均體現了源語文本中存在的韻律,實在精彩。
(二)朱、許譯本中有關本體隱喻的翻譯
正如例2中提及的隱喻“邪惡是箱子”(EVIL IS TRUNK),本體隱喻最主要的目的便是要實現指稱、量化等功能,同時也會賦予作為始源概念的抽象體一定的個人感受,從而將之具化為目標概念的有形物。因此本體隱喻在實際表達中往往附帶一定感情色彩,并具有獨特性。其常見子類容器隱喻則是需要通過構建有邊界的容器實體,來表述始源概念本體的某一特性。另外,在當下的相關研究中,普遍接受將傳統文學領域中的隱喻、擬人修辭手法歸為本體隱喻的范疇中。以下枚舉部分相關譯例。
例3:

?
評析:該段節選自《第十二夜》開篇經典場景。通過隱喻“音樂是食物”(MUSIC IS FOOD)和“愛情是人”(LOVE IS PERSON)的連環套用,公爵Orsino聽曲享樂而飽受相思之苦的形象得以巧妙展現。至此,人格化的“愛情”有了“食欲”,不僅能以“音樂”為食,還有可能“生病”(sicken)甚至“死亡”(die)。朱譯本當中,使用漢語中的“是”字結構,以最直白的方式還原隱喻,同時保留了原文擬人化的“愛情”這一概念。許譯本中則將該本體隱喻糅雜,將“音樂”同樣擬人化,而在后文放棄抽象表達“愛情”這一概念,直接具化為“多情人”。相較而言,朱譯顯得更為頓挫,長短參差的話語使得臺詞更有節奏,從而使劇本的表演實踐性優于更顯文氣的許譯。
例4:

?
評析:在與喬裝后的Viola溝通后,Olivia對眼前這位交流不深的青年怦然心動,卻全然不知她實際上也是女兒身。除開“優點是人”(PERFECTIONS ARE PEOPLE)和“眼睛是視覺”(EYES ARE SEEING)這兩組明顯的隱喻,源語中的介詞“in”和“at”展現出了一定的空間性,同時把“視野”作為一個有界容器,表現出了“內外的分別”,因此構成了容器隱喻。在兩種譯本當中,分別使用“進入”或“溜入”來幫助讀者和觀眾認同此種認知層面的容器,再次可見此認知經驗基礎在中西文化中共有。而與朱譯本相比,許譯本中再次進行增譯,使得臺詞表達更為清晰直白,相對更優。
(三)朱、許譯本中有關方位隱喻的翻譯
方位隱喻的建構與結構隱喻不同,因其無需借助另一種概念,而是通過組織一套相互關聯的概念系統來進行構建的。雖然方位隱喻是與空間方位相關聯的一類隱喻,但其產生的隱喻性方向并非是任意的,相反是必須要基于一定的自然及文化經驗來確定的。由于概念隱喻具有系統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或是在不同的經驗基礎上,方位隱喻的表述都會有所差異。下面將列舉一些譯例。
例5:

?
例6:

?
評析:在例5當中,小丑Feste的情歌中“hereafter”點明了隱喻“未來是后方”(FUTURE IS BACK)。而在例6中,公爵Orsino忿忿的訣別中卻表達的是“未來是前方”(FUTURE IS FRNOT)。有關時間的方位隱喻常常會出現這樣看似“自相矛盾”之處,但誠如前敘,一切隱喻表達都是基于經驗來構建的,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同一始源域概念可以對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目標域。因此分析應置于同一語境范圍中展開。在例5中,兩種譯本規避了源語中的隱喻化表達,緩解了由于文化差異可能導致的文本難以對等的問題;而在例6中,兩種漢譯本都選擇了進行文化調整的方式,在譯文中基于漢語語言習慣譯為“以后”,雖然看似與“henceforth”對立,但源語中的隱喻表達得以保留。
例7:

?

五、結語
在上述案例的對比分析過程中,不難發現,由于戲劇藝術本質上所獨具的雙重性,英語戲劇漢譯無疑是一個復雜的過程。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最早的莎劇譯者大家之一的朱生豪先生,還是21世紀以翻譯中的以詩意語言著稱的許淵沖先生,都能從他們的譯本中體會到極具個人特色的翻譯風格,因此就完整譯本的質量而言的確難分伯仲。但仍能大致總結出三條有關英語戲劇中隱喻的漢譯策略:(1)對于具有相同經驗基礎或共同思維模式的隱喻表達,可以采用直譯和文化適應的方式;(2)雖然目的語中存在類似與源語的隱喻概念,但難以完美實現跨域映射的相似概念隱喻表達,應當采用歸化和意譯的方式;(3)而對于那些帶有強烈文學表意和表演特征的隱喻表達,異化和文化調整則是更合適的翻譯策略。
此外還需注意,翻譯的發展過程必將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完善的,因為譯者要準確把握不同文化下的所有隱喻表達實屬不易。因此,英語戲劇的優秀漢譯本需要隨時代變化不斷接受打磨和重譯,而且應當將讀者和觀眾同時作為譯文的目標受眾,并始終以其中的文學表意和表演實踐作為考量標準。一方面,明確英語和漢語都是隱喻表達能力很強的語言。尤其是當戲劇等文學作品中的隱喻研究超脫于修辭層面,而從認知思維的角度去研究時,很有可能會有關于同一案例的不同理解。另一方面,若能在后續研究中建立語料庫來進行定量的實證研究,必將為學者帶來更多實質性的幫助。期待后繼學者能夠進一步將認知語言學視角應用在文學翻譯的研究當中,從而能夠更為恰當地理解和認識英語戲劇的漢譯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