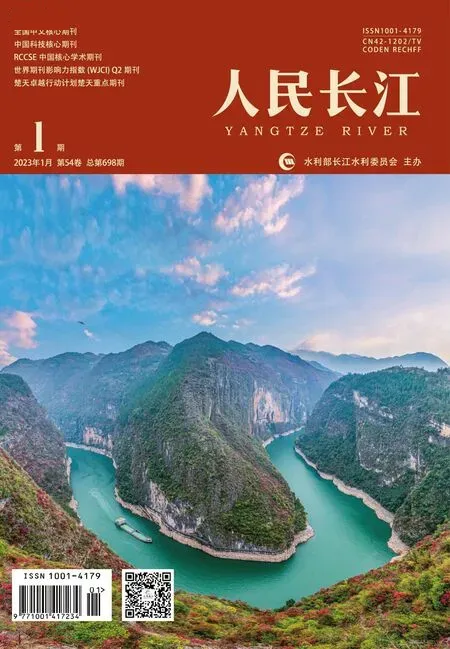基于人工神經網絡的隧道斷層帶突涌水風險評估
袁 青,于 錦,熊 齊 歡,張 子 平,陳 世 豪
(1.中交第二航務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北 武漢 430040; 2.中交公路長大橋建設國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 100088; 3.交通運輸行業交通基礎設施智能制造技術研發中心,湖北 武漢 430040; 4.長大橋梁建設施工技術交通行業重點實驗室,湖北 武漢 430040)
0 引 言
隨著基礎設施建設向地質條件更加復雜、深度更大的地層推進,更多的工程地質問題亟待解決。深長隧道作為中國公路、高鐵線路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然成為整個路線的控制性工程。但由于工程地質、水文地質條件復雜,當隧道穿越富水斷層時,發生隧道涌水事故風險急劇增大,對施工安全造成重大影響。開展涌水風險評估已成為隧道穿越富水斷層時的必備措施。
國內外學者在開展隧道涌水風險評估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相比國外,國內工程風險管理起步較晚,但近年來發展迅猛。2007年《鐵路隧道風險管理評估與管理暫行規定》《地鐵及地下工程建設風險管理指南》以及2011年《城市軌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設風險管理規范》相繼頒布,標志著中國地下工程建設風險管理日趨規范。眾多學者從多方面開展了工程風險管理研究。黃宏偉等[1]從工程建設的規劃、設計、施工等多個階段總結了隧道及地下工程風險管理。李利平等[2]以多個國內巖溶隧道突涌水案例為數據源,基于模糊層次評估法和綜合賦權法建立了隧道勘察、設計、施工3個階段的風險評估模型,并驗證了基于風險評價的施工許可機制的可行性。蔣國云[3]在調查誘發深部巖溶隧道突水災害誘因的基礎上,采用層次分析法與專家調查法,建立了各風險因子比較矩陣,基于模糊數學理論建立了隧道巖溶突水安全性評價模型及評判標準。朱珍等[4]基于地層巖性、不良地質、地下水位、地形地貌、巖層產狀及層間裂隙等6個影響因子,采用加權平均法建立了巖溶隧道突涌水風險評估模型。此外,許多學者基于傳統分析方法,各取其長處進行了融合,建立了風險評估模型。侯東賽等[5]基于綜合賦權TOPSIS,毛正君等[6]基于F-AHP法,侯守江[7]基于G1-GPR(灰度關聯分析)模型,劉敦文等[8]基于云模型,周宗青等[9]基于改進的屬性區間識別方法分別開展了巖溶隧道涌水風險評估研究。
從上述研究可知,目前隧道涌水風險評估研究主要是圍繞巖溶地質隧道,以其他特殊地質環境為背景的隧道涌水風險評估研究比較有限。隧道穿越斷層帶不良地質體時,涌水風險的研究則更少。而且,對風險因子在總風險評級中的權重占比均未進行較深入的研究,主要采用專家調查法、事故樹分析法等主觀方法確定權重值,但主觀方法受到經驗判斷的影響,對風險評估結果客觀性影響較大。因此,本研究基于人工神經網絡開展了隧道穿越斷層帶突涌水風險評估。該方法可有效評估斷層涌水風險等級,克服人為賦權、主觀判斷影響等問題,進而提高評估結果的客觀性、科學性。
1 人工神經網絡原理及訓練流程
1.1 神經網絡原理概述
神經網絡種類繁多,其中以人工神經網絡應用最為廣泛。人工神經網絡是非線性映射方法的體現,在數據訓練的基礎上,通過設置的若干個非線性映射層即神經網絡層,獲得輸入數據與輸出數據之間的非線性映射關系[10]。通常所述神經網絡為前饋型人工神經網絡,采用誤差反向傳播算法進行訓練,主要包括輸入層、隱含層和輸出層,層與層之間通過網絡連接,其內涵是為輸入數據配以權重值后的自動運算。應用實際數據進行網絡訓練,根據輸出數據與標簽數據之間的誤差,采用誤差反向傳播算法不斷調整層間權重值,直至輸出數據的精度滿足要求。通常根據特征因子的數量及數據復雜程度,設置一定數量的隱含層,使神經網絡模型具有相適應的學習能力。
1.2 人工神經網絡結構及訓練流程
以單隱含層神經網絡為例介紹神經網絡的正向運算和誤差反傳算法,如圖1所示。

圖1 人工神經網絡Fig.1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數據正向傳輸時,數據經過輸入層到輸出層輸出,經過如下計算:
yj=f1[(wij)T×xi+bj]
(1)

隱含層至輸出層的網絡間計算過程與上述類似,如式(2)所示:
ok=f2[(wjk)T×yj+bk]
(2)

上述傳遞函數分別采用tanh函數和線性函數,如式(3)~(4)所示:
(3)
f2(x)=x
(4)
經過上述計算,即可得到網絡輸出值,再采用誤差反向傳播算法計算并傳遞誤差,以動態調整各網絡層之間的權重值和閾值,直至輸出值與標準值之間的誤差滿足精度要求。誤差計算函數,如公式(5) 所示:
(5)

輸出層神經元誤差項δk計算公式為

(6)
式中:zk為輸出層凈輸入值。輸入層與隱含層的誤差項δj計算公式為
δj=f′(zj)⊙[(wk)T]δk
(7)
式中:zj為輸出層凈輸入值。輸出層與隱含層之間的連接權值與閾值更新計算公式為
wjk(n+1)=wjk(n)+ηδk(yj)T
(8)
bjk(n+1)=bjk(n)+ηδk
(9)
輸入層與隱含層之間的連接權值與閾值更新計算公式為
wij(n+1)=wij(n)+ηδj(xi)T
(10)
bij(n+1)=bij(n)+ηδj
(11)
搭建及訓練本文所述花崗巖斷層涌水風險評估神經網絡流程如圖2所示。

圖2 神經網絡訓練流程Fig.2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neural network
2 隧道斷層帶涌水風險評估指標體系
2.1 評價指標體系
隧道發生涌水事故通常與工程地質、水文地質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在眾多研究中,多數研究者主要基于水文地質、工程地質所包含的地質因素開展隧道涌水研究。楊卓等[11]基于不良地質、地層巖性、地下水位、地形地貌、巖層傾角、圍巖裂隙5方面因素,應用神經網絡開展了巖溶隧道涌水風險評估研究。所述因素中,不良地質因素表述不夠具體,而且僅采用5個風險因素難以具有足夠說服力。隧道施工時,合理有效的施工處置措施對施工安全具有重大意義,因此施工設計因素應當考慮其中。廣泛閱讀相關文獻[8,12-13]和綜合取舍后,本研究考慮工程地質、水文地質、施工設計3方面致災因素,即斷層巖性、斷層充填物、斷層性質、斷層寬度、年均降雨量、地表水量、地下水量、含水層透水性、斷層含水量、施工工法、隧道埋深、超前注漿、超前支護共13個獨立風險評估指標,構建隧道斷層帶涌水風險評估指標體系。
參閱《鐵路隧道風險管理評估與管理暫行規定》《地鐵及地下工程建設風險管理指南》及《城市軌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設風險管理規范》,劃分上述13個評估指標致險評分,如表1所列。

表1 隧道斷層帶涌水風險評估指標評價標準
2.2 風險等級評估準則
基于上述規范、研究文獻、專家評分、工程經驗,建立綜合考慮13個風險因子影響的隧道斷層帶涌水風險評估準則,如表2所列。
參考鐵路隧道、城市軌道交通等領域關于風險評估與管理的規范與指南,本文所述4級風險具有如表2所列的工程指導意義。

表2 隧道斷層帶涌水風險評估準則
3 風險評估人工神經網絡構建
本研究從董奉山隧道、新疆某隧道、各碩博論文案例實際工程中收集了97個樣本,并根據表1所述特征狀態評分方式,對所有樣本進行了評分處理,建立了神經網絡訓練、測試數據集,隨機摘取了部分樣本,如表3所列。
根據風險因子數量,初設神經網絡中三類網絡層數均為一個,其中輸入層神經元、隱含層神經元、輸出層神經元分別為13,5,1,應用程序構建如圖3所示的神經網絡。值得指出的是,網絡結構、訓練數據等并非一成不變,在實際應用過程中,還可根據項目數據特點,調整網絡結構,增加項目的數據,動態優化網絡,增強網絡計算能力。

表3 訓練樣本(部分)

圖3 隧道斷層帶涌水風險評估神經網絡Fig.3 The neural network of water gushing of tunnel fault zones
進一步采用收集的樣本進行上述神經網絡的訓練。通常,在神經網絡訓練和測試的過程中,隨機將數據集按8∶2劃分為訓練集和測試集[14-15]。本研究為確保樣本數據隨機性,應用生成的隨機數為編號,隨機從數據集中抽取80%的樣本為訓練數據集進行神經網絡訓練,訓練誤差變化如圖4所示。

圖4 神經網絡訓練誤差變化Fig.4 The training error variance of ANN
由圖4可知,在歷經9次迭代訓練后,訓練誤差迅速減小至3.596×10-5,低于程序預設誤差值。此時,可判斷神經網絡訓練精度達到要求,訓練結束。
4 神經網絡模型泛化能力測試
應用上述20%的測試樣本,對已訓練的模型進行泛化能力測試,即測試模型對新案例是否具有足夠的預測準確性。20個測試樣本的預測輸出值與目標值的對比如表4所列。

表4 預測值與目標值對照
從預測值與目標值對比中可知,20個樣本均獲得極高精度的預測,每個樣本的預測誤差均在10-3數量級。經計算,整體預測精度達99.98%。神經網路的泛化能力測試結果表明,本文構建的神經網絡模型在開展隧道斷層帶涌水風險評估時,具有較強遷移學習能力,對評估新工程案例中斷層帶涌水風險是可行、有效的。
5 結論與建議
(1) 應用神經網絡評估斷層涌水風險等級具有計算速度快、評估結果客觀準確等優點。在本研究中達到了99.98%的預測精度,說明應用人工神經網絡開展隧道斷層帶涌水風險評估是可行有效的,能夠遷移于新工程評估。
(2) 本文提出的隧道斷層帶涌水風險評估方法,在獲取上述13個涌水風險因子及評分后,即可快速預測得到涌水風險等級。因此,無論是在設計階段,還是在施工階段,都可根據勘察資料或施工現場情況,動態調整輸入,多次預測涌水風險等級,為設計優化、下一步施工調整提供實時參考。
(3) 神經網絡具有極強的非線性映射能力,能夠適用于多種地質環境下構建各類地質因素之間的映射關系,是擺脫人工經驗判斷的有利工具。未來深度學習在邊坡、隧道、地下空間等領域應用前景更加寬闊。
(4) 本研究中使用的數據集廣度略顯不足,因此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精度下降、結果置信度偏低等情況,此時可根據現場情況,適當采集項目樣本,微訓練網絡,優化網絡參數,提升網絡的泛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