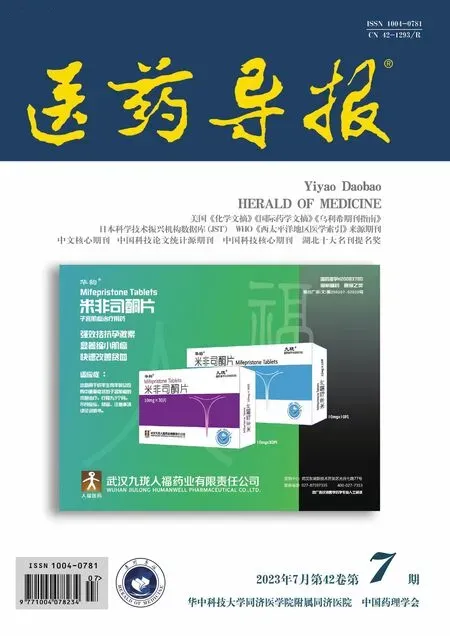中藥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對比研究進展與有關問題分析*
岳佑凇,張璐,王艷麗,謝夢迪,李海洋,麻利杰,侯富國,路露,劉瑞新,李學林
(1.河南中醫藥大學藥學院,鄭州 450046;2.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藥學部,鄭州 450000;3.河南省中藥臨床應用、評價與轉化工程研究中心,鄭州 450000;4.河南中醫藥大學呼吸疾病中醫藥防治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鄭州 450046;5.河南省中藥臨床藥學中醫藥重點實驗室,鄭州 450000)
中藥配方顆粒[1]規避了傳統湯劑服用量大、攜帶不便等弊端,目前臨床使用量大,市場需求廣闊。2021年2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等多部委聯合發布《關于結束中藥配方顆粒試點工作的公告》[2],標志著中藥配方顆粒“后試點時代”[3]的到來。自2021年4月29日起,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相繼頒布了248種中藥配方顆粒國家藥品標準,各省也相繼出臺了省級配方顆粒標準,配方顆粒的生產走向規范化。但中藥配方顆粒仍面臨諸多挑戰:①現有標準覆蓋的品種范圍有限,仍有較多品種無規范的質量標準;②現有質量標準的具體項目尚需進一步完善;③執行配方顆粒相關標準政策情況可能存在偏差,監管體制也有待進一步完善;④配方顆粒與傳統湯劑間的等效性問題仍未得到真正解決,對比研究仍需深入。
近年來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的對比研究,一定程度上為配方顆粒的臨床使用及推廣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兩者活性成分、藥理作用或臨床效果等的差異性及差異程度等問題依然懸而未決,限制了配方顆粒的推廣應用及產業化發展。因此,筆者在本文對兩者的對比研究進行綜述,梳理總結現有對比研究思路與方法中存在的關鍵問題,結合理論與實踐進行分析,以期為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的對比研究提供更完整的思路,推動傳統湯劑的劑型優化和配方顆粒產業蓬勃發展。
1 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對比研究的必要性
中藥傳統劑型理論認為:“湯者蕩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緩也,不能速去之[4]”。這一理論是古人對于不同劑型的藥性特點及釋藥特點的高度概括,對于指導中藥臨床使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配方顆粒作為一種現代劑型,目前對其藥性及釋藥特點的研究并不多,在以適量熱水溶解為配方顆粒湯劑后,相較于傳統湯劑而言,患者服用體量減少,而傳統湯劑的劑型用藥理論,是否適用于配方顆粒湯劑值得深入研究。
傳統湯劑僅需將中藥飲片煎煮即得,而配方顆粒經過提取、濃縮、制粒等環節,兩者制備工藝不同,使飲片自身的偏性與其入湯劑時相比發生了明顯變化[5]。首先,提取、濃縮階段使得飲片中有效成分的受熱時間較傳統湯劑長,可能對藥物成分造成一定影響;其次,制粒環節輔料的加入,輔料種類、用量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對藥物的吸收、分布、代謝等產生影響;最后,配方顆粒為直接開水沖服,與傳統湯劑相比,缺少組方藥物“共煎”的過程,也可能造成兩者間成分變化和臨床療效間的差異。因此,從化學成分、藥理藥效等方面研究因制備工藝不同所致的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的差異是亟待深入的重點。
2 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對比研究進展
近年來,配方顆粒湯劑和傳統湯劑間的對比研究主要從物質基礎、藥理作用及臨床療效這幾個方面進行。化學成分方面:采用高效液相色譜法[6-9]、薄層色譜鑒別[10-12]等對兩者的化學成分進行比較,發現部分單味中藥及復方,其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在化學成分的種類及含量方面并無顯著差異[13-14],而針對具有差異者,研究人員根據實驗數據對臨床建議當量進行了校正[6,8];藥理作用方面[15-22],研究數據表明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的藥理作用孰優孰劣并無規律可循。劉月波[22]發現麻黃湯全方飲片組相比配方顆粒組有更好的發汗作用(P<0.05);易成玉[20]基于體內和體外研究結果發現左金丸配方顆粒治療胃炎的作用效果優于傳統湯劑;而黃大利[18]在研究石膏-知母的解熱藥效時發現,湯劑與顆粒劑的解熱藥效無較大差異。臨床療效方面,收集并總結不同病證臨床患者服用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后的療效差異,研究發現存在以下3種情況:①傳統湯劑優于配方顆粒湯劑[22-24]。例如,比較兩類湯劑對老年功能性便秘臨床治療的效果時,傳統湯劑組臨床治療有效率94.87%,配方顆粒組臨床治療有效率76.92%,兩組間數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4];②配方顆粒湯劑優于傳統湯劑[25-27]。例如,歸脾湯配方顆粒劑在貧血女性患者中的顯效率、總有效率均優于傳統湯劑(P<0.05)[27];③兩者間并無顯著差異[28-30]。例如,獨活寄生湯顆粒劑與飲片治療腎虛血瘀型膝骨關節炎效果無明顯差異[30]。
3 兩者對比研究過程中若干關鍵問題的探討
3.1原料來源一致性問題 ①已有部分研究采用同批次飲片自制配方顆粒與其所制傳統湯劑進行比較[31-33],這一做法理論上保證了原料來源一致,具有可比性。但配方顆粒的制備屬于一個動態變化過程,若選用自購飲片自制顆粒,實驗室的制備過程與規模化的工業生產間存在較大差距,且自制顆粒質量不穩定,得出的結論并不足以為配方顆粒廠家的大規模生產及臨床科學用藥提供全面科學的參考;②有些研究中選用由配方顆粒廠家提供的配方顆粒及同來源飲片(同批次)[23,26,34],保證了原料來源一致性,但該做法實際上模糊了研究對象,使得進行兩者間比較僅僅是在比較兩者間由于劑型、制備工藝不同所造成的差異,對比內容局限,背離了進行兩者對比研究是為了能夠更好反映臨床實際用藥情況的初衷,并且以個別廠家提供的同來源飲片及配方顆粒為研究載體所得出的研究結果可能較片面,不足以代表整個配方顆粒市場;③有些研究則選用自購(藥材市場或醫院)飲片及自購(醫院)配方顆粒(不同批次)[6,8-9,35]。臨床實踐中,患者在醫院就診后,依據醫師所開處方進行飲片的購買和湯劑的制備,不論是醫院代煎還是自煎,所購飲片與配方顆粒所用飲片批次都不可能保證完全一致,且廠家所用飲片與在醫院、藥店所購得的飲片質量參差不齊。
在化學藥仿制藥一致性評價[36]過程中,也未要求待評價制劑與參比制劑所用原料要保持同一批次。保持原料來源一致這一做法本身可行性差且不合理,對于進行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對比研究并無實踐意義。因此,基于臨床實際用藥情況的考量,在進行兩者間對比研究時,不事先人為控制傳統湯劑和配方顆粒飲片來源的一致性,這樣的研究結果更能反映臨床上兩者間的質量差異。
3.2兩者間對比研究時所應關注的主要矛盾有所偏差 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的對比研究所要關注的主要矛盾存在偏差,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大部分對比研究傾向于分析單煎、共煎的不同對湯劑中成分及藥效的影響[37-40],但這并不是現階段需解決的主要矛盾,現階段需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使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在指標成分、藥理作用及臨床療效等方面基本保持一致,允許變動的范圍在某一個限定值(如±10%或±20%)內,即不論相應品種的配方顆粒是否已出臺國家標準,且不論國家標準中已經規定了濃縮比。因即便國家標準出臺了,配方顆粒的實際生產過程仍有待監管和確認。當這一主要矛盾解決后,在一定條件下,單煎、共煎的問題可能由次要矛盾轉化為主要矛盾,屆時可將更多精力放在研究單煎、共煎對于成分的影響以及如何科學合理的減少這些影響等問題上;另一方面,要開展有關單味藥[7,41-43]的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差異規律的研究,因單味藥在兩類湯劑間的差異規律未研究清楚,后續藥對、復方的研究就失去了基礎[44],當主要矛盾即單味藥的差異規律研究逐步得到解決時,受不同料液比、配伍關系、煎煮時間的影響,單味藥入藥對和復方用藥時,其物質基礎、藥理藥效還是可能發生變化,則藥對、小復方以及大復方的兩類湯劑間差異規律的研究會逐漸轉化為主要待解決問題。為指導臨床合理用藥,在單味藥的差異規律研究相對完善的基礎上,結合藥對及復方的差異規律再深入研究,兩者研究相輔相成,由簡入難,由點到面,逐步完善中藥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的對比研究內容。
3.3參比標準問題 1982年經日本各方專家討論確定了“標準湯劑”的制備方法[45],2016 年,國內有學者提出了中藥飲片標準湯劑的概念[46],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2021年1月發布的《中藥配方顆粒質量控制與標準制定技術要求》明確提出:“以標準湯劑作為衡量單味中藥配方顆粒是否與其相對應的單味中藥飲片臨床湯劑基本一致的物質基準”[1]。標準湯劑逐步得到認可,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配方顆粒相關質量標準的制定更加科學規范。然而在進行兩者間對比研究時,實際操作中使用的“標準湯劑”與政策定義的“標準湯劑”是否完全一致,在實際對比中使用“參比湯劑”是否較“標準湯劑”更為合適,值得商榷。因為“標準湯劑”本身很難做到完全標準,盡管所謂的“標準湯劑”對飲片用量、浸泡時間、加水量等一系列參數做了規定,但由于最根本的飲片無法做到標準,所以決定了“標準湯劑”無法從根本上做到標準。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有“標準品”,但并無“標準藥材”的說法,取而代之的則是“對照藥材”,因藥材本身受產地、采收季節、炮制工藝等因素影響無法做到標準,藥材既然無法做到標準,那么就無法獲得“標準飲片”,進而也無法得到由“標準飲片”煎得的“標準湯劑”。因此在今后的對比研究中,研究者們應建立一種相對比較完善可行的“參比湯劑”的制備方法,對包括飲片來源、批次數量、飲片用量、煎煮次數、加水量等在內的參數及制備流程進行規定,代表傳統湯劑與配方顆粒湯劑進行比較。
3.4基于劑型理論、配伍關系等角度聚焦藥性變化 長期以來受唯成分論思維的影響,研究人員著重從化學成分、藥理藥效層面分析配方顆粒湯劑和傳統湯劑間孰優孰劣的問題,很少從中藥藥性的角度比較兩者間的差異。中藥藥效來源于藥性,藥性、功效和物質構成中藥藥性理論的三個基本點[47],藥性相同或相似的中藥,其物質構成方面也有相似點,三者相互影響,共為一體[48]。而中藥藥性受多種因素的影響:①劑型影響藥性[49-50]。配方顆粒劑型與傳統湯劑并不相同,兩類劑型的單劑量濃度不一致,患者服用體積相差也較大,量變產生質變,可能導致藥性變化,因此配方顆粒湯劑是否可以沿用傳統湯劑“湯者蕩也”的劑型用藥理論仍需進一步研究;②藥性是方劑配伍的重要依據,由藥性層面所體現出的配伍規律與中藥方證對應的作用方式有著更直接的聯系[51],而配方顆粒作為一種“新型飲片”應用于復方時,配伍規律及機制對其成分、藥效的影響是否使其藥性發生變化也應是進行對比研究時需關注的重要方面之一;③國家標準頒布前,可能有配方顆粒生產企業在制備配方顆粒時采用的并非水提法[52],或飲片打粉直接制粒[53],含有揮發性成分的將揮發油另外收集后再濃縮制粒等[54],與傳統湯劑制備方法并不一致,對于目前還未出臺相關國家標準或省標的中藥種類,部分企業出于保持“全成分”一致的考慮,也未與傳統湯劑制備保持一致,這些對藥性是否有影響也需進一步確認;④配方顆粒在大生產的過程中,其煎煮時間(一般配方顆粒制備一煎、二煎時長為傳統湯劑的2~4倍)、加水量與傳統湯劑相差較大[54-56],對成分類別、性質產生的影響,都有可能導致藥性變化,例如對于一些解表藥[54]來說,長時間煎煮對其所含揮發性成分的保留是否有影響,是否改變其辛溫發散的藥性,進而影響其解表功效,這些都未可知。因此,在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的對比研究中,聚焦兩者間藥性變化,分析導致兩者間藥性變化的因素,基于中醫藥整體觀,完善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對比研究的思路,從藥性變化的角度綜合評判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成分、藥理藥效的不同,可為配方顆粒的科學研發、規范生產與合理應用奠定基礎。
3.5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的參考意義 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的對比研究并不能簡單套用仿制藥一致性評價方案。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即國家要求仿制藥品要與原研藥品質量和療效一致。化學藥通常成分單一且明確,劑型固定,工藝成熟,達到從管理、中間過程、質量標準等全過程一致的高標準要求完全可行,但中藥并非如此,僅就單味藥而言,不同批次配方顆粒湯劑與其傳統湯劑的對比研究涉及飲片產地、等級及采購渠道不同,不同廠家制備工藝及生產規模也不一致,兩者劑型不同等影響因素;就復方而言,中醫學講究“整體觀”,中醫用藥講究君臣佐使、七情配伍,處方用藥組分多,成分復雜。配方顆粒湯劑和傳統湯劑間的對比研究簡單照搬、直接套用西藥一致性評價方案不合理、不可行,應借鑒其基本思路,逐步建立適合中醫藥特點尤其是中藥配方顆粒湯劑和傳統湯劑特點的對比研究方法體系。
4 總結與展望
筆者在本文對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比較的必要性進行闡述,對相關研究文章進行綜述,總結現有兩者間對比研究內容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從原料來源一致性、參比標準及藥性變化等角度對若干關鍵問題進行分析,以期為今后兩者間的對比研究提供更加全面、合理的思路。
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質量的評控問題是發展中醫藥現代化的關鍵問題之一,兩者間的對比研究應基于臨床實際需求,將現階段常用的比較方法與新興科技手段結合。棄前期研究中的糟粕,取其精華,優化配方顆粒湯劑與傳統湯劑間對比研究的實驗思路,確保兩者在臨床療效上的差異可接受,使傳統湯劑及配方顆粒適應現代用藥需求,使配方顆粒這一新興劑型的生產及應用更加規范,療效更加可靠穩定,與中藥飲片并駕齊驅,促進中醫藥事業更加蓬勃有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