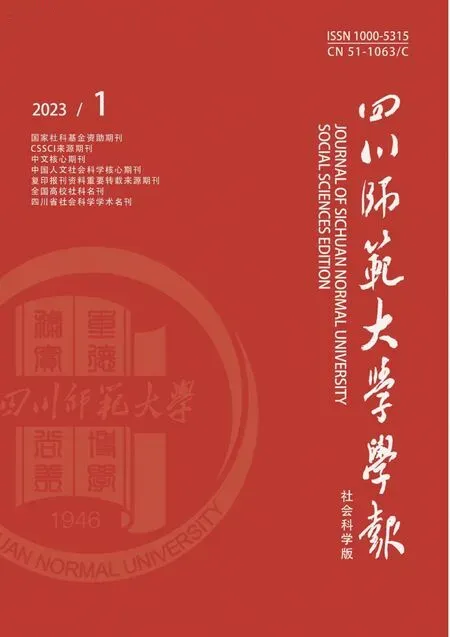論清代雍乾時期四川糧食運銷
鄧前程 朱林
清初,四川因戰亂而人口銳減,田地荒蕪,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即便是四川臨時政權所在地的保寧,軍民用糧亦“賴大清運陜西之糧”(1)費密《荒書》,何銳等校點《張獻忠剿四川實錄》,巴蜀書社2002年版,第437頁。。但是,自康熙中葉開始,隨著戰亂的平息、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秩序的恢復,特別是隨著史稱“湖廣填四川”的鄂、湘、贛、閩、粵等省移民大規模地入川插占和墾荒殖業,四川逐步從糧食奇缺、“斗米數十金”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到康熙末年漸有“產米之鄉”的美譽(2)“康熙年間戶口未繁,俗尚儉樸,谷每有余,而上游之四川、湖南人少米多,商販日至,是以價賤,遂號稱產米之鄉。”見:《清高宗實錄》,中華書局1985-1986年影印版,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第98頁。。至雍正年間,四川的糧食生產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查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3)《浙江巡撫李衛奏請借動司庫贏余銀兩赴川買米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7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頁。,且糧價低廉(4)清初四川,“州縣民皆殺戮,一二孑遺亦皆逃竄,而兵專務戰,田失耕種,糧又廢棄,故兇饑至”。到順治年間,四川各地物資短缺,物價飛漲,米價奇高,雅州“米一斗銀十余兩,嘉定州三十兩,成都、重慶四五十兩。保寧賴大清運陜西之糧,亦有十余兩”(見:費密《荒書》,何銳等校點《張獻忠剿四川實錄》,第436-437頁)。康熙初年,“斗米五錢,買無可買”[見:蔡毓榮等纂修《四川總志》卷35《籌邊》,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四川大學圖書館藏,第7頁]。到雍正年間,川米“每石尚止四五錢”(見:《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第104頁),其價格之低廉,已成“湖廣、廣東、江西等省”民眾相率遷入四川的經濟動因(見:常明、楊方燦等纂修《四川通志》卷首之二,巴蜀書社1984年版,第71頁)。糧食價格是糧食供需的晴雨表,也是顯示一個地區糧食產量多少的重要標志。,不但本省糧食供給充足,而且還有余糧接濟他省,成為國內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之一。到乾隆中后期,四川更是成為“產米最廣”的省份(5)《清高宗實錄》卷1237,乾隆五十年八月戊戌,第634頁。,長江中下游的江浙等省“全賴川米接濟”,若川米不能如期運達,則“各省米價必致騰貴,于民食大有關系”(6)《清高宗實錄》卷1286,乾隆五十二年八月甲辰,第247頁。,乃至一度形成“江浙糧食歷來仰給于湖廣,湖廣又仰給于四川”(7)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3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78年版,第400頁。的糧食產銷格局。對于雍乾時期四川糧食運銷這樣一個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問題,學界已發表過一些頗有見地的成果(8)關于清前期四川糧食貿易流通問題的研究成果,除散見于清代經濟史論著外,專題論文主要有: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糧食問題(上、下)》,《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第90-105頁、第4期第73-87頁;謝放《清前期四川糧食產量及外運量的估計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第83-89頁;等等。,但這些成果大多著力于清前期或有清一代這種長時段的宏觀考察和概論層面,而對特定歷史時段或具體問題的探討則相對薄弱。有鑒于此,本文擬就雍乾時期四川糧食運銷的區域范圍、運銷方式、交通運輸和市場格局等問題試作探討,以期推動學界對該問題進一步的關注和思考,進而深化對該時期四川作為國內農業大省和產糧大省地位的認識。
一 運銷的市場區域
清雍乾時期,四川糧食運銷有省內外兩個市場。其中,外運的主體市場通常有兩大區域:一是經打箭爐銷入衛藏,二是絕大部分過夔關,“出荊襄,達吳粵”(9)常明、楊方燦等纂修《四川通志》卷67《食貨·榷政八》,第2280頁。。四川與江浙等經濟作物區逐步形成固定的糧食供給關系,大江湖河“帆檣相屬,糧食之行,不舍晝夜”(10)《晏斯盛請設商社疏》,賀長齡主持、魏源編輯《清經世文編》卷40《戶政》,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991頁。。事實上,這一時期四川糧食的外運區域范圍要廣泛得多。
(一)運銷省外市場
關于雍乾時期四川糧食的外銷,首先需要回答的是這一時期有多少糧食運銷出省的問題。大米是糧食類中的代表性產品,也是秦嶺淮河一線以南大多數國人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雍乾時期,僅商販出川的大米,“常年動計數百萬石”(11)《清高宗實錄》卷1263,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庚午,第1022頁。,若遇他省賑災等特殊需求,外運川糧有可能達到500-1000萬石(12)彭朝貴、王炎主編《清代四川農村社會經濟史》,天地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頁。按:關于雍乾時期川糧外運量,限于史料記載闕如,很難得出一個逐年的確切外運數據。對此,學者們往往根據所能搜集到的材料進行甄別研究并作出相應的數量估計。參見:謝放《清前期四川糧食產量及外運量的估計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第83-89頁;鄧亦兵《清代前期內陸糧食運輸量及變化趨勢——關于清代糧食運輸研究之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81-82頁;等等。。從運銷省區看,在雍正四年(1726)至嘉慶十一年(1806)間,即有直隸、山東、山西、陜西、甘肅、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貴州、云南、廣西、西藏等省(區)(13)王綱《清代四川史》,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576頁;《成都通史》編纂委員會主編,張莉紅、張學君著《成都通史:卷六 清時期》,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頁。。不過,從長時段連續性的視閾看,雍乾時期四川糧食運往省外市場行銷,主要有以下幾個相對固定的區域。
一是運銷鄂、皖、江、浙等長江中下游各省,乃至廣東、福建等東南沿海省區。這是四川糧食外銷以“協濟臨省”的主要區域。有學者統計,雍乾時期,每年運銷到該區域的川糧大致在100-300萬石左右;若遇這些省因災歉收或其他特殊的需求,川糧運銷數量會更多,甚至可能高達500萬石以上(14)謝放《清前期四川糧食產量及外運量的估計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第88頁。。歷史上,江南的蘇、揚、杭、湖一帶素以農耕經濟發達和糧食豐足著稱,是京畿地區的糧食供應基地(15)時至明清,這一地區仍然承擔著漕糧北運的重任,每年通過京杭大運河,或走海路,向北方的京畿地區輸送數百萬石漕糧,以保障官民的食用。參見: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45頁;彭云鶴《明清漕運史》,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頁;范金民《賦稅甲天下:明清江南社會經濟探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4頁。。但是,自清初以來,江、浙等省工商業的迅速發展,特別是棉紡和絲織業的勃興,加大了對蠶桑、棉花等紡織原料的需求。江南農民受利益驅動,或棄農耕而從事工商業,“力田之家,十不二三”(16)《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第96頁。,或少種、不種糧食而種植經濟效益更好的桑、棉等經濟作物。乾隆年間,松江、嘉定等地,“種稻者不過十之三,圖利種棉者又十之七八”(17)《高晉奏請海疆禾棉兼種疏》,賀長齡主持、魏源編輯《清經世文編》卷37《戶政》,第911頁。,“二年種棉,一年種稻。稻較棉少,故農家恃棉為生,以種植瓜菜及喂養豬、雞為副產”(18)《民國嘉定縣志》卷5《風土志·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8)》,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768頁。;華亭、寶山一帶,“改禾種花者比比”(19)《光緒重修華亭縣志》卷23《雜志上·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4)》,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768頁。,“七分棉花三分稻”(20)《光緒羅店鎮志》卷1《疆里志上·風俗》,《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輯》,上海書店1992年版,第194-195頁。。江南地區的這種情形,也同時在廣東、福建等東南沿海省區有所顯現。雍正五年(1727)二月諭內閣云:“廣東本處之人惟知貪財重利,將地土多種龍眼、甘蔗、煙葉、青靛之屬,以致民富而米少。……此奏與朕前旨相符,可知閩、廣民食之不敷有由來矣。”(21)《清世宗實錄》卷53,雍正五年二月乙酉,第810頁。按:諭中“此奏與朕前旨相符”中之“朕前旨”,是指該年二月雍正針對廣東“一歲所產米石,即豐收之年,僅足支半年有余之食”的現象而上諭內閣:“朕思廣東之米所以不敷廣東之用者,或田疇荒廢,未盡地利;或興作怠惰,未用人工;或奸民貪得重價,私賣海洋”(見:《清世宗實錄》卷53,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版,雍正五年二月乙丑,第802頁)。江南地區及廣東、福建等省區,原本城市人口多而稠密,糧食需求量大,加之經濟作物占用了大量耕地,致使糧食產量減少,進一步加劇了糧食供需矛盾。關于清代江南因漕糧北運、工商業發展、經濟作物擠占糧田等原因而造成的糧食生產和供給不足等問題,前人已有較多研究成果。這里僅引數則史料補充說明,不作進一步考論。雍正初年,這些省區的民用口糧,即靠湖廣、江西等鄰省接濟;到乾隆時期,江南等地“每年仰資川米”(22)《清高宗實錄》卷1065,乾隆四十三年八月癸酉,第236頁。,“全賴客商販運”(23)《高晉奏請海疆禾棉兼種疏》,賀長齡主持、魏源編輯《清經世文編》卷37《戶政》,第911頁。,以致米荒或米價騰貴事件時有發生,嚴重影響到當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并危及社會安定。這一情況,使清朝廷不得不時常關注四川糧食能否順利運銷到江南等缺糧地區。如雍正二年(1724)上諭:“江浙糧食歷來仰給于湖廣,湖廣又仰給于四川”(24)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3輯,第400頁。;雍正四年(1726)六月,浙江巡撫李衛指出,“湖廣漢口地方,向來聚米最多者,皆由四川,土饒人少,產米有余”(25)《浙江巡撫李衛奏請借動司庫贏余銀兩赴川買米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第7冊,第364頁。。大致到乾隆四年(1739)前后,川糧開始大量東運,即便是素有“魚米之鄉”美譽的湖北,也有賴于川糧接濟(26)大約在雍乾之際的30年間,湖廣特別是江漢及洞庭湖平原的人口逐漸趨于飽和,城鎮人口劇增,“湖廣熟、天下足”的內涵開始發生變化。湖北雖仍為產糧大省,有糧食輸出,但也同樣需要四川、湖南等省的糧食接濟。史載,雍乾時期,每年“秋收之后,每日過夔關大小米船,或十余只至二十只不等,源源下楚”。川米落岸漢口,因湖廣糧米要接濟江浙,以致川米對湖廣糧價產生重要影響,如武漢等地“人煙稠密,日用米谷,全賴四川、湖南商販駢集,米價不致高昂”;若川省歉收或運輸不及時,則米價“每石貴致一兩七八錢,民間致有無米可糴之苦”[見:允祿、鄂爾泰等編《憲廟朱批諭旨》第8函第1冊,雍正十年(1732)武英殿刻本,第22頁]。特別是每年正、二月間,湖北米價由每石一兩四五錢增至二兩不等,常需從四川調撥或商運大米平抑糧價,致有“向來楚省民食全賴川省商販”之說(《清高宗實錄》卷386,乾隆十六年四月上乙卯,第76頁)。關于該問題的系統研究,可參: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229頁。。乾隆帝曾指出,“川省產米素稱饒裕,向由湖廣一帶販運而下,東南各省均賴其利”(27)常明、楊芳燦等纂修《四川通志》卷72《食貨志·倉儲》,第2388頁。,“閩省米糧短缺,曾諭令江浙、湖廣、江西、四川等省,撥運米石百余萬”(28)《清高宗實錄》卷1294,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上丙申,第365頁。,并屢次諭令“如川省米船到楚,聽其或在該省發賣,或運赴江南通行販售,總聽商便,勿稍抑遏”(29)《清高宗實錄》卷1064,乾隆四十三年八月丙寅,第231頁。,還賦詩云“全蜀幸逢年,教開移粟船,不因讀漢詔,拯溺應自然”(30)《清史列傳》卷16《黃廷桂》,王鐘翰點校,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176頁。。
二是運銷滇、黔、甘、藏等四川周邊民族省區。“滇、黔兩省,道路崎嶇,富戶甚少,既無商販搬運,亦無囤戶居奇,夷民火種刀耕,多以雜糧苦蕎為食,常年平糶”(31)《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第104-105頁。。這就是說,滇、黔兩省的不少地區山多田少,土地貧瘠,所產各種雜糧,素不敷本地民口食。如臨近四川的云南東川、昭通等府,“向來米價最貴”,常年都要通過金沙江,從四川運進糧食(32)《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第105頁。。乾隆八年(1743),云南“昭通、東川兩府,收成歉薄,米價昂貴”,云南總督(33)云、貴兩省總督之設置,在清前期有一個變動過程。乾隆元年(1736),分置云南總督及貴州總督,乾隆十二年(1747)仍置云貴總督,并成定制。兼巡撫張允隨撥銅息銀二萬兩,“發駐扎四川永寧轉運京銅之同知,于川東一帶買米一萬石”,“運回滇省”,“以備平糶”(34)《清高宗實錄》卷201,乾隆八年九月己酉,第593-594頁。。貴州的情況,與云南相似,一般來說,大多數年份都需從川、湘、桂等省輸入三四十萬石糧食,其中川米占有較大份額(35)郭松義《清代糧食市場和商品糧數量的估測》,《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45頁。。乾隆三十五年(1770),貴州“上年秋收,今春麥收,俱未豐稔”,巡撫宮兆麟奏請從湖南糴米12萬石、四川糴米6萬石、廣西糴米2萬石,以解決本省急需平糶而常平倉米不敷的問題(36)《清高宗實錄》卷863,乾隆三十五年六月甲午,第576頁。。特別是康熙中葉以后,滇、黔兩省大力發展礦冶業。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貴總督蔡毓榮上陳《籌滇十疏》之后,云南的銀、銅等礦冶業進入發展的快車道。康熙四十四年(1705),“滇銅官為經理”(37)趙爾巽《清史稿》卷124《食貨五·礦政》,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666頁。,云南全省有銅礦廠20處,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增至46處,“大廠率七八萬人,小廠亦萬人,合計通省廠丁,無慮數十百萬,皆各省窮民來廠謀食”(38)《唐炯籌議礦務擬招集商股延聘東洋礦師疏》,葛士濬編《清經世文續編》卷26《戶政》,上海書局1898年石印,第513頁。;貴州省則有銀銅、黑白鉛廠“十有余處,每廠約聚萬人、數千人不等”(39)《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第106頁。。滇、黔兩省礦冶業的興盛,使大批農民從農業生產中游離出來,原本不能自給的糧食缺口進一步增大。同時,人數如此龐大的礦工群體,消耗的糧食數量也不小。據記載,“廠分既多,不耕而食者約有十余萬人,日糜谷二千余石,年銷八十余萬石”(40)《倪蛻復當事論廠務書》,賀長齡主持、魏源編輯《清經世文編》卷52《戶政》,第1293頁。。這些糧食大多需從外省采辦,進一步加大了滇、黔兩省對四川糧食的依賴。
甘肅地處西北戰略要沖,軍事浩繁而土地磽確,物產瘠薄,常需從川、陜等省販運糧食,以保障軍需民食和平抑糧價。乾隆二十三年(1758)六月,乾隆帝諭令軍機大臣:“先期購辦明歲征兵口糧。如本省不敷,則移商開泰,于四川購運,務足二萬官兵一歲之用計”(41)《清高宗實錄》卷565,乾隆二十年六月辛巳,第165頁。《清高宗實錄》卷564又載:“諭軍機大臣等,前經傳諭黃廷桂,先期購辦口糧,以備明歲支給添派兵丁之用。……倘為數不敷,則應就近移商開泰,令于四川近甘各州縣,廣為先時購運,大約務足二萬官兵一歲口糧之需。”《清高宗實錄》卷564,乾隆二十年六月癸亥,第155頁。。西藏所屬地區,大多“只產青稞,不產米谷”,居民食米需從四川販運,如扎達、鹽井等地民眾“買鹽售賣,或對換油米等物,以資生計”(42)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4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版,第820頁。。為保障“習于谷食”的駐藏軍隊和民眾日食所需(43)《清世宗實錄》卷30,雍正三年三月丁未,第452頁。,乾隆五十四年(1789)曉諭四川總督李世杰,于“尋常無事,糧價平減之際”,責令地方官府“采買儲備”糧食,“擇其易于運送時,由雅州一帶,陸續運至打箭爐及察木多兩處分貯”(44)《清高宗實錄》卷1326,乾隆五十四年四月甲午,第952頁。,以備不時之需。此外,青海的蒙古族居民也利用到四川松潘黃勝關貿易的機會,從松潘轉運糧食至青海(45)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3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78年版,第712頁。。
(二)運銷四川省內糧食市場
這類市場的糧食運銷,主要有以下三個流通去向。
第一,供應城鎮居民、工商業者等非農人口的口糧。隨著移民不斷涌入四川,與清政府設官分治和恢復社會經濟的努力相結合,雍乾以后,四川城鎮已邁入快速發展的軌道。有學者統計,乾嘉時期,四川場鎮大約有3000座(46)高王凌《乾嘉時期四川的場市、場市網及其功能》,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研究集》第3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頁。。其中,省、府、州、縣治所在地,既是一級地方行政中心,又往往位于交通要沖,集聚了大量從事工商業的各種城鎮人口。據王笛按一戶五口的概率統計,雍正六年(1728),四川冊載戶為50.5萬余戶、約252.7萬余人,修正戶為67.1萬戶、人口約335.7萬人;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川冊載人口增至948.9萬人,修正人口增至1170.1萬人(47)王笛《清代四川人口、耕地及糧食問題(上)》,《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第96、98頁。。若按城鎮人口約占人口總數的5%-10%平均值測算(48)以研究近代中國人口史而著名的學者姜濤即指出,如果按照宋代城鄉人口比例,英國學者提出的宋代“城市人口至少占總人口的10%以上”的估計數據,并不比中國學者提出的唐代城市人口可能占比10%的比重更高(見:姜濤《傳統人口的城鄉結構——立足于清代的考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31頁)。路遇、滕澤之認為,“清朝末年……城鎮人口,綜合各種情況作歷史的分析,至多4000萬左右,而農業人口則在4億以上”(見:路遇、滕澤之《中國人口通史》第10卷下冊,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2頁),即約占總人口的9%。人口史研究者曹樹基研究清代北方各省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后指出,少或不足5%(如河南4.6%,山東4.9%),多或超過10%(如直隸12.5%,山西10.3%)(見:曹樹基《清代北方城市人口研究——兼與施堅雅商榷》,《中國人口科學》2001年第4期,第20頁)。由此可見,清代城鎮人口在地區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因各地人口密度、城鎮發育水平和經濟社會發展程度等情況的不同,很難一概而論。另外,目前學界是按照2000居民這一現代城鎮的標準來研究和統計古代中國城鎮人口的,但實際上,在四川等南方省區,還有數量眾多的2000居民以下的中小場(集)鎮,這些場鎮上的居民多數也不事農耕而需要買糧維持生活。據此,將清代城鎮人口所占總人口的比例確定為5%-10%,應屬合理,或可能偏低。,那么雍正中期(六年)四川城鎮居民約為16.8-33.6萬人,按其時人均年消費口糧(原糧)1100市斤的全國平均值估算,四川城鎮居民每年至少需消耗口糧(原糧)18480-36960萬市斤(約123.2-246.4萬石);乾隆末年(五十六年)四川約有城鎮居民58.5-117萬人,若按其時人均年消費口糧(原糧)1000市斤的全國平均值估算,四川城鎮居民每年至少需消耗口糧(原糧)5.85-11.7億市斤(約390-780萬石)(49)謝放《清前期四川糧食產量及外運量的估計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第85-86頁。當然,對于清代四川居民人均年消費糧食的數量,分別以雍正年間1100市斤和乾隆時1000市斤估算,只是一種理論意義上的算法。美國學者珀金斯根據1957年中國人均糧食產量572市斤的情況提出,清代中國人均擁有的糧食生產量及實際消費量應在500-600市斤,而這已是一個比較高的糧食消費水平,發展中國家很少有超過這一水平的[見: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宋海文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頁]。然而,考慮到清代雍乾時期四川社會上存在著大量的不耕而食、游手浮蕩等非農游民,故本文對于雍乾時期四川城鎮居民口糧消費總量的估計應屬明顯偏低。。而這些數量龐大的城鎮居民日食所需,只能通過市場渠道購買。質言之,城鎮居民人等的用糧,已成為雍乾時期四川商品糧流通領域中規模最大、最主要的去處。
第二,運銷到四川省內少數民族地區。四川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其西部、西北部、西南部等盆周地區,世居著藏、羌、彝等少數民族。這些民族以游牧或種植青稞、蕎麥、玉米、土豆等雜糧為生,因耕地瘠薄,產量較低,“各番收獲雜糧,每戶或收一石有余,或僅收數斗”(50)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37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85年版,第494頁。。因此,這些民族地區的民眾,大多需要從川內產糧區輸入糧食,尤其是米谷,“以資糊口”(51)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19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83年版,第304-305頁。。岷江上游保縣至茂州以及松潘一帶,重山復疊,田地甚稀,且率皆童山頑石,頗鮮樹木,加之節氣寒冷,鮮產稻谷,其“食米全賴成都府屬之灌縣,龍安府屬之江油、彰明二縣商販”(52)《清高宗實錄》卷307,乾隆十三年正月己酉,第22頁。。川西南彝族聚居的寧遠府、越西廳一帶,“山多田少,即使終歲豐稔,所產米糧尚不敷本地民食”,其不足部分亦需從成都、嘉定、敘州等產糧區輸入(53)《四川總督阿爾泰奏》,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28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84年版,第471頁。。甘孜牧區的居民,雖以肉食為主,消耗糧食較少,但因其地適宜種稻者少,故對大米等商品糧市場依賴程度,或不亞于內地城鎮居民或其他民族地區的居民。
第三,為省內各地工商業作坊提供生產生活用糧。雍乾時期是四川糖果和釀酒等食品工業快速發展的重要階段。康熙中葉以后,隨著移民的到來,四川糖業逐漸復興,至雍乾年間,沱江沿岸的內江、資中、簡陽、資陽、富順等地民眾,多以植蔗作糖致富。這些地區,既需要運進糧食補充居民日用口糧,也需要糧食完成糖果加工。也就在這一時期,四川釀酒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令人詫異的是,康、雍、乾三朝雖一直嚴令禁酒,但四川酒業恰恰是在嚴申酒禁的這段時間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得以迅猛發展起來,形成沿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和長江沿岸的川酒生產作坊(54)張學君《清代四川酒業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研究》2000年第3期,第123-127頁。。糖果和釀酒這類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商品糧支撐。道光初年,四川平武縣唐開蘭的一份條陳很能說明這一情況。茲摘錄如下:
川省每州縣城內京果鋪、糖房多二十家,鄉場市鎮亦十余家……妄費米面不止兩月之糧。川省各州縣場鎮染房染布,刷糨糊米每家數十余石,徒飾一時之偽,百姓穿衣一水洗去,有捐(損)無益。通省妄費之米,亦不止兩月之糧。更有燒房一條,除綿竹縣大曲燒房、中江縣小曲燒房耗費糧食極甚外,每州縣有名場鎮數十余處,通省約萬余處。每處燒房十余家不等,每家每日烤(酒)一桶約費糧食市斗一石余、倉斗二石余。每日一桶謂之單烤單煮,每日兩桶謂之雙烤雙煮。每日合省共計約耗糧食數百萬石,每年約耗糧食數億石,又不止兩月之糧。(55)呂小鮮《四川平武縣唐開蘭條陳》,《歷史檔案》1985年第4期,第38頁。
唐氏的這份“條陳”,雖記錄的是道光初年四川果鋪、糖房、釀酒等食品業與染房染布等輕工業的發展盛況和行業耗糧概況,客觀地說,唐氏的這些說法有夸大成分,但諸如糖房、染坊、燒房等行業的發展,按當時的生產技術和工藝,卻的確是耗糧且易造成糧食浪費的。正是由于糖房、染房、燒房等行業的生存和發展需要大量的商品糧,因此,這些行業的經營者為節約成本,每逢新糧上市,紛紛“爭囤”糧食、壓價欺民,“致掯窮民不少”(56)呂小鮮《四川平武縣唐開蘭條陳》,《歷史檔案》1985年第4期,第38頁。。由此可見,雍乾時期,四川糖果、釀酒等食品工業和染布等輕工業的蓬勃發展,業已成為川糧內銷的消費大戶。
二 運銷的主要形式
雍乾時期四川的糧食運銷,主要有官府采買和民間商貿兩種形式。
(一)官府采辦
官府采辦,通常由朝廷指令從四川倉儲調撥,或由需糧省區到四川采買,以協濟地方或供給軍需,其中協濟地方是官府采辦的主要用途。為保證這部分糧食足額,運輸暢通,清廷屢次明令四川督撫“馳禁毋遏糴”(57)趙爾巽《清史稿》卷294《憲德》,第10343頁。,同時責令沿途地方官府疏通糧食運銷渠道,“不得中途攔截”運糧船只(58)《清高宗實錄》卷1237,乾隆五十年八月辛丑,第639頁。。雍乾時期,清朝當局時常從四川調撥和糴買糧食,用于湖北、安徽、江蘇、江西、浙江、福建、云南、貴州等省區(59)王綱《清代四川史》,第574頁。,或救災,或平抑糧價,或儲備。
一是救災。自然災害往往對地區經濟與民眾生產生活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有學者統計,雍乾年間是清代自然災害頻發的時期(60)清中前期,自然災害發生的情況是“順治年間年均受災11.8次,康熙年間年均受災8.8次,雍正年間年均受災9.9次,乾隆年間年均受災18.7次,嘉慶年間年均受災18.7次”,特別是直隸、甘肅、江蘇、安徽、山東等省區幾乎年年有災。參見:江太新《清代救災與經濟變化關系試探——以清代救災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8-18頁。,史志中有不少關于官府從四川調撥或采買糧食用于救災的記載。為了籌備糧食,以應救災之急,乾隆八年(1743)諭令:川省沿江各州縣所貯米谷,“若遇鄰省需糧接濟,凡碾運各費,令該省交給委官赍帶,赴川自行領運,應還糧價,亦令該省照數解川歸款”(61)常明、楊方燦等纂修《四川通志》卷72《食貨·倉儲》,第2387頁。;乾隆十八年(1753),“江南淮揚一帶,被水成災,賑恤需米”,“酌撥(川米)二三十萬石”,“以資接濟”(62)《清高宗實錄》卷445,乾隆十八年八月壬寅,第792頁。;乾隆二十三年(1758),山東遭遇水災,乾隆帝諭令“借給川米”(63)《清高宗實錄》卷572,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丙辰,第264頁。;乾隆二十四年(1759),甘肅蘭州、平涼旱災,清廷要求就近由陜糧運甘,同時令四川總督開泰將四川就近州縣谷米運至略陽,交收分運,以便應急調撥(64)《清高宗實錄》卷587,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壬寅,第519頁。。
二是平抑糧價。自康熙中后期以后,隨著國內局勢的穩定、人口的增長,國內不少省區糧食短缺,“米價騰貴”(65)《清圣祖實錄》卷187,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版,康熙三十七年三月戊子,第996頁。。乾隆年間,糧價上漲幾乎遍存于各省,南方地區尤為突出。米價的上漲,必然影響民眾的生活,尤其是每遇歉歲,若政府平糶不及時,或商賈囤積居奇,民眾普遍缺糧,社會矛盾迭生。為此,一些缺糧省份動用官銀入川買米,以平抑糧價。雍正四年(1726)七月,浙江巡撫李衛獲準“動浙庫公項銀十萬兩,委員赴川采買米石,以備浙閩兩省緩急”(66)常明、楊芳燦等纂修《四川通志》卷72《食貨志·倉儲》,第2387頁。。這次購得川米10.5萬石,每石平均價銀九錢五分,比浙江米價便宜四五錢不等(67)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07頁。。自此之后,湖廣、云南等省大多仿效此法,相繼派員赴川買米,由此引起四川官府“遏糶”與江、浙、鄂、滇等省官府反對四川“遏糶”的矛盾糾葛。后經清廷出面干預,一方面令赴川糴買谷米的各省,縮減在川購糧規模,最高限買2萬石,其余部分可赴江西等省采買;另一方面令四川地方官府停止“遏糶”,解禁谷米輸出,由此紛爭始告一段落(68)牛貫杰《17-19世紀中國的市場與經濟發展》,黃山書社2008年版,第119-121頁。。
三是用于儲備。按制,清代各州縣均建有儲備糧食的常平倉,以備平抑糧價和賑濟災荒之用。常平倉的儲備糧,來源有官府采辦、捐監、官民捐輸和截存漕糧等途徑,但其主要來源還是靠官府動用官銀采買或調撥。如江、浙、閩、粵等缺糧大省,通常由政府出資到江西、湖廣和四川等省買糧,以填補倉貯。史載,自雍正四年(1726)準許浙江用浙庫公項銀買川米填倉之后,凡遇省份缺糧補倉,大多效仿此法。乾隆九年(1744),兩淮鹽場米糧倉儲備缺額30萬石,從“四川貯備米石內,撥米四萬石,運貯揚州鹽義倉,以實倉儲”,不足之數“仍準于四川撥運,使一時緩急有資”(69)《清高宗實錄》卷218,乾隆九年六月壬子,第809頁。。乾隆十六年(1751),從重慶府巴縣常平倉內“支谷五千石撥運楚省,轉補浙倉”(70)王爾鑒主持、張九鎰纂修《巴縣志》卷3《積貯·巴縣常平倉》,乾隆二十六年(1761)刊本,四川大學圖書館藏,第33頁。。
四是軍糧儲備。軍糧籌辦是雍乾時期官府糧食采購的又一重要事項。康熙末年的反擊準噶爾侵藏,雍正初年的平定羅布藏丹津叛亂,“所有糧運事宜,均有辦定章程”(71)《西藏研究》編輯部編《清代藏事輯要》卷4,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8頁。。這里所說的“章程”,即軍用糧草主要從四川籌措(72)民國初年,吳光耀在其《西藏改流本末紀》中說,“康、雍、乾三朝西藏有事,皇子王公為大將軍,西寧、川、滇三路進兵,督撫分駐打箭爐、察木多,躬督糧官購牛馬碾運內地倉谷濟大兵”。見:趙心愚、秦和平編《康區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上)》,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年版,第39頁。。特別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兩次反擊廓爾喀(巴勒布)入侵,除部分軍糧在衛藏就地采買外,其余部分例由“川省籌辦”(73)《西藏研究》編輯部編《清代藏事輯要》卷4,第258頁。。比如在第二次反擊廓爾喀入侵時,除在西藏就地采買軍糧外,署理川督孫士毅還在“成都、雅州、邛州等處撥碾米二萬石,陸續運爐,預備運察木多,接濟西藏兵食”(74)方略館編《欽定廓爾喀紀略》,季垣垣點校,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頁。。實際上,川糧供給軍需,遠不止用兵西藏。自乾隆十年(1745)以后,史志中不乏官府調撥或采買川米用作軍糧的記載。如乾隆十年(1745),云南總督兼巡撫張允隨動用地丁銀派人赴川買米1萬余石,以供昭通大關、魯甸、永善和東川所屬營訊官兵三年額糧(75)《清高宗實錄》卷251,乾隆十年十月戊午,第239頁。;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廷為向甘肅軍營增兵1000人,傳諭四川總督開泰購運口糧,“務足二萬官兵一歲之用計”(76)《清高宗實錄》卷565,乾隆二十年六月辛巳,第165頁。;乾隆五十二年(1787),為解決平定臺灣軍務事,“著保寧再行采買米三十萬石……一并委員運往閩省,以資接濟”(77)《清高宗實錄》卷1284,乾隆五十二年七月乙亥,第209頁。等。由此可見,四川是清雍乾時期軍糧采辦的重要供應地。
另外,四川省內駐防軍官兵的口糧,例由官府采買。自清朝入關之后,按“得一省必鎮定一省”的原則,在全國建立起龐大的八旗和綠營兵鎮守網。四川作為西南大省,戰略地位重要,駐防任務重,駐軍人數多,軍糧消費數量大。乾隆帝曾說:“川省地方,原屬邊徼。而保寧、雅、龍、茂、達等府、州,并敘永、松潘、越西、雷波各廳、衛、所,又為川省之極邊,積儲尤為緊要……或因地處邊遠,不產米谷,恐外省商賈人等爭先報捐,以致米價昂貴,有妨民食……令買本地之糧食,即充常平之倉儲,價歸于民,糧交于官,下無不足,上即有余,非販運出境者可比”(78)《清高宗實錄》卷120,乾隆五年閏六月己酉,第770-771頁。。又乾隆十二年(1747),“(戶部)議覆,四川副都統卓鼐奏稱,成都駐防兵丁口糧,共需米二萬八千六百余石……每年令成都、華陽二縣,采買稻一萬八千余石,存貯滿城,于青黃不接之時,分給兵丁,在餉銀內照原價扣還。但兵丁所領稻少,需用口糧甚多,一遇雨水,購買維艱。請將每年兵丁應領米折銀內,扣除二萬石米價,存貯藩庫,于秋收后,分發附近成都各州縣,買運滿城,酌量支給兵丁”(79)《清高宗實錄》卷297,乾隆十二年八月丁丑,第886頁。。由是觀之,官府同樣需要通過市場以經濟手段解決四川各地駐軍口糧供給,特別是駐防八旗官兵的口糧供給、糧倉儲備及其他消費開支。
雍乾時期從四川調撥和采買的糧食數量具體有多少,限于史料記載闕如,難以詳確。茲輯錄有關記載列如表1,以觀其概。從表1可見,自雍正五年(1727)以后,官府不斷在四川采辦糧食。其中,間隔時間較長的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這16年間,官方組織川米外運的次數相對較少。何以如此,因川省“辦理軍需,購糧較多,督撫請暫停夔關出米,以供軍儲”(80)常明、楊芳燦等纂修《四川通志》卷72《食貨志·倉儲》,第2388頁。。之后,川米外運一直不斷。王笛據嘉慶《四川通志》統計,從雍正至嘉慶年間,有11次官運糧食出川的記載,數量達787萬石(81)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第205頁。。此外,王綱據嘉慶《四川通志》和《清實錄》的記載,統計了從乾隆八年(1743)至乾隆六十年(1795)間調撥糧食數量的明確記載,計有20次,總量達320余萬石(82)王綱《清代四川史》,第575-577頁。。應該說,乾隆年間,清廷調撥川糧的實際數量要遠遠高于這一數字。

表1 雍乾時期官府在四川地區采辦糧食情況舉例
(二)民商販運
雍乾時期,除官方組織四川糧食運銷外,商民也廣泛地參與糧食運銷,并成為省內外糧食市場的主體運銷力量。一般來說,在省內初級市場(糧食產地)的糧食交易,通常由農民與需求者之間直接進行,而在跨地區的長距離或高層次市場的交易中,民間小販和商人的作用無可替代(83)高王凌《乾嘉時期四川的場市、市場網及其功能》,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研究集》第3輯,第83頁。。特別是四川糧食商運出省這樣的大宗買賣,更是非實力雄厚的商民莫屬。每到秋收時節,各省商販紛紛赴川買米,“常年動計數百萬石”(84)《清高宗實錄》卷1263,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庚午,第1022頁。。既有研究表明,雍乾時期,清朝對糧食貿易少有限制,“俾商賈踴躍從事,則米船多,價值自平,而民食有賴”(85)崐岡、李鴻章等修《大清會典事例》卷237《戶部關稅》,《續修四庫全書》第80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91頁。。特別是每遇豐歉不齊之年,尤為重視發揮糧食自由買賣的作用,“各省年歲豐歉不齊,全賴商販流通,有無貿遷,以資接濟”(86)《清高宗實錄》卷502,乾隆二十年十二月甲辰,第326頁。。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清廷不僅要求民商嚴格遵守市場價格,即便是官方到川買糧,也“不必先行咨會,俟委員到日,一如市集交易,公平糴買”(87)《清高宗實錄》卷323,乾隆十三年八月庚戌,第339頁。。為了保證糧食商運出川,一方面,責令四川當局開放米禁,聽商賈販運。雍正十年(1732),江南沿海遭遇特大潮災后,雍正帝諭令:“川省為產米之鄉,歷來聽商賈販運,從長江至楚,以濟鄰省之用……目今江浙有需米之州縣,望濟于楚省”,若不令川米赴楚,則湖北“何所資藉”,“著即傳諭憲德,速弛米禁,勿蹈遏糴之戒”(88)《清世宗實錄》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丁亥,第662-663頁。。同時,還責令四川督撫勸諭糧商,不準囤貨居奇。乾隆五十年(1785)八月,乾隆帝諭令川督李世杰“明切曉諭,令川省民人”,當湖北等省商人赴川采買時,“毋得居奇遏糴”(89)《清高宗實錄》卷1237,乾隆五十年八月戊戌,第635頁。。另一方面,明令楚、贛等沿江地方督撫疏通糧食運銷渠道,更不得隨意阻攔或截留川糧販運船只。雍正時,“嚴諭沿途文武官弁,遇有江楚商人至四川販米,或四川商人往江楚賣米者,立即放行,不可阻遏”(90)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3輯,第400頁。。因“恐川船到楚,僅敷該省之用,不能分運,則江南糧價或至增長”,乾隆四十三年(1778)諭令湖廣當局,“川省米船到楚,聽其或在該省發賣,或運赴江南通行販售,總聽商便,勿稍抑遏”(91)常明、楊芳燦等纂修《四川通志》卷72《食貨志·倉儲》,第2388-2389頁。;乾隆五十年(1785)又令,“遇有川省運往江南之米,不得中途攔截……聽其運赴安徽、江蘇出賣”(92)《清高宗實錄》卷1237,乾隆五十年八月辛丑,第639頁。。諸如此類措施的實施和禁令的發布,保證了四川糧食外銷暢通,由此一度形成了川省糧食轉口武漢而行銷于長江流域諸省之繁榮局面。
至于雍乾時期歷年商運出川糧食的具體數量有多少,雖無明確記載,但比官運數量大,是可以肯定的。為此,乾隆帝就說,“蜀中產米素多,常時商販搬運外省”(93)《清高宗實錄》卷938,乾隆三十八年秋七月丙寅,第649頁。。
此外,雍乾時期,民間商賈還參與了官府的軍糧、官糧等販運活動。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川總督富勒渾奏請“川省所需軍糧,除官為運送外,招集商人挽運。其腳價照金川成例,分別西、南兩路,道路險易,食物貴賤,酌量增減。按里計算,每石自六七厘至一分五六厘及二分不等。其新增糧站,日進日遠,請照美諾等處每石每站給腳價銀五錢,商人得資挽運,自當按期無誤”,戶部議覆得旨“依議速行”(94)《清高宗實錄》卷933,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丁未,第554-555頁。。
三 運銷的運輸方式
四川糧食運銷主要有水運和陸運兩種運輸方式。理論上,水運和陸運在商品運銷中同等重要,但是,糧食屬于笨重品和易耗品,在遠程運輸中更適合集中裝載,加之受制于當時“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的陸路交通條件,致使陸路運糧成本遠高于水路運輸,水運船載比陸路車載、牲馱、人背的運能運量更大、更方便、更劃算。所以,四川的糧食運銷,主體有長江干流(通往長江中下游各省以及東南、北方地區)、嘉陵江與漢水(通往陜、甘等西北省份)、金沙江與赤水河(通往云、貴等西南省份)等水運干線和川藏陸路運輸路線,形成了水運為主、陸運為輔、水陸聯運及水陸運互補的糧食運銷格局。
第一,長江干流糧食運銷路線。長江水道是清前期國內糧食貿易中集散路線最長、運輸量最大和運達地區最廣的運糧通道,也是四川糧食外運的主要渠道,即所謂“外省販運川省米糧,概由川江。經重夔一帶,順流而下。如由夔州一帶買米,逆流而上,運至成都”(95)《清高宗實錄》卷938,乾隆三十八年秋七月丙寅,第649頁。。長江在四川境內長897公里,有可通航中小支流29條,橫貫川南、川東,上接云南,下通湖北,右達貴州、湖南,左入陜西、甘肅(96)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第35頁。。特別是,川楚“一水可通,商販絡繹”(97)《清高宗實錄》卷916,乾隆三十七年九月庚子,第279頁。。四川糧食經長江干流販運至湖廣后,一是繼續沿江東下,經湖廣運至皖、江、浙等長江中下游經濟發達省份(98)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3輯,第399頁。,甚至轉運販往福建、臺灣等東南沿海省份,即“川省續運之米……由川江順流而下,亦由江浙海運抵閩可也”(99)《清高宗實錄》卷1285,乾隆五十二年七月甲午,第235頁。;二是北上,利用海路、京杭大運河、黃河淮河水系,“過淮渡黃,出入江南、山東、直隸各境”(100)《戶部采買米石》,昆岡等修、劉啟端等纂《大清會典事例》卷188,《續修四庫全書》第801冊,第133頁。,或利用湖北至山東可通舟楫的水運便利,“將川省運楚米石,即由楚交山東……以資接濟”(101)《清高宗實錄》卷547,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乙卯,第964頁。,或將川糧運銷京畿地區。
第二,金沙江與赤水河運道。金沙江起于今青海和四川兩省交界處的青海省玉樹州稱多縣歇武鎮直門達村,流經川、藏、滇三省(區),其間有雅礱江等支流匯入,至四川省宜賓市翠屏區境內與岷江合流始名長江,全長約3400余公里。赤水河發源于云南省鎮雄縣,東流至川、滇、黔三省交界處的梯子巖后水量增大,經貴州畢節市、金沙縣與四川省敘永縣、古藺縣邊界進入貴州仁懷市、習水縣、赤水市,至四川合江縣匯入長江,全長400多公里。金沙江、赤水河流域的川南地區,也是四川重要的糧食產區。川糧經由金沙江、赤水河,源源不斷地運銷云、貴兩省(102)鄧亦兵《清代前期內陸糧食運輸量及變化趨勢——關于清代糧食運輸研究之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81頁。。為加強金沙江、赤水河的航運能力,乾隆五年(1740),云南總督慶復兩次派人查勘和疏浚金沙江運道,并于“沿江險灘旱壩,酌設站船,接運川省米鹽,以濟匠食,兼于回空船內裝載銅斤,按站遞交”,俾收“水運節省之效”(103)《清高宗實錄》卷132,乾隆五年十一月丙申,第918頁。。之后,隨著金沙江水運航道的疏浚通航,“川米流通”,“滇屬東(川)、昭(通)二府,向來米價最貴之處,漸獲平減”(104)《清高宗實錄》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癸丑,第105頁。。乾隆十年(1745),貴州總督張廣泗奏請疏浚赤水河運道,解決貴州威寧、大定等府、州、縣“崇山峻嶺,不通舟楫”,“陸運為艱”的運輸困境,以便“偶遇豐歉不齊,川米可以運濟”(105)《清高宗實錄》卷239,乾隆十年四月庚申,第73頁。。
第三,嘉陵江與漢水運道。嘉陵江在四川境內由廣元至重慶1006公里,是聯結川、陜、甘等省的水運要道,這也是清代川糧運銷西北的重要通道(106)鄧亦兵《清代前期內陸糧食運輸量及變化趨勢——關于清代糧食運輸研究之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81頁。。經由嘉陵江水系,舟楫下行可將沿江各地糧食運往重慶集散,上行可將四川糧食運往陜、甘即西北地區。漢水流經湖北、陜西兩省,經由漢水運道,四川糧食也可運至陜西,但舟楫只能運糧至漢中略陽,自此之后需要陸運。乾隆二十四年(1759)諭令,“川省產米尚多,可以通融酌撥。其自川運至漢中略陽地方,皆由水運,自屬徑捷。自略陽起岸,即須陸運”(107)《清高宗實錄》卷579,乾隆二十四年正月甲辰,第386頁。。因此,略陽便成為四川糧食運銷甘肅的中轉站,“將川省附近各州縣現在米谷,仍照前旨由水路撥運,至陜省之略陽交收。分運各屬,以備儲積”(108)《清高宗實錄》卷587,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壬寅,第519頁。。
第四,川藏陸路運輸線。清代,四川與西藏交通往來的線路有川藏北道(商道)和川藏南道(官道)兩途。其中,川藏北道雖少高山峻嶺,“平衍易行”,但沿途多系草地,居民稀少,甚至于“行數程而無人煙”,加上官府的郵傳驛遞系統不健全,商賈行旅須“自攜帳篷,擁飲食各物”而行,因而交通較為冷落;川藏南道為其時內地與康、藏地區人員、物資交通往返的主要通道。自康熙四十一年(1702)以后,清廷多次整治川藏道驛站和糧臺(109)1701年“西爐之役”后,蒙古和碩特部退回雅礱江西岸,康東打箭爐等地土司重新納入清朝的直接統治之下。為加強對康區的控制和經略西藏,康熙四十一年(1702),清廷設打箭爐驛和塘汛,康熙五十八年(1719)設打箭爐糧臺。自康熙年間在川藏道上設置汛塘與糧臺之后,雍乾時期又新設五個糧臺(理塘、巴塘、乍丫、昌都和西藏)和數十處汛塘,川藏道為之暢通。參見:鄒立波《清代前期康區塘汛的設置及作用與影響》,《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第28-35頁;趙心愚《清康熙雍正時期川藏道汛塘與糧臺的設置及其特點》,《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第116-124頁。,駐藏官兵的糧餉從四川“源源買進,必不遲誤軍需”(110)《清圣祖實錄》卷278,康熙五十七年三月丙寅,第725-726頁。。從總體上看,雍乾時期經川藏陸路交通線輸入藏區的糧食,主要是以官府調撥的方式,供給駐藏官員、軍隊及川藏路沿線郵傳驛遞系統軍政人員的口糧,也有相當部分通過市場途徑糶賣打箭爐、理塘、巴塘、乍丫、昌都等川藏路沿線城鎮的商民食用或交易。如康區交通樞紐的打箭爐,“系通西藏要隘,往來蠻客赴爐貿易者,絡繹不絕”(111)《奏陳川省地方應行事宜折》(雍正元年二月廿七),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年羹堯奏折專輯》中冊,臺北故宮博物院1971年版,第1頁。。另外,巴塘、里塘與云南省麗江府維西以及西藏各寨相通。這些地區的各族居民亦“常在四川巴、里二塘所轄之擦棟安、安天柱各寨,及西藏所屬之擦瓦崗、左工(貢)、波烏〔羅〕、曲棕、工布、渣峪〔察隅〕、扎玉滾、南墩、漢人寺、江卡、扎呀、黃連山等處,或與藏來之番商,或與川屬之夷客”貿易(112)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4輯,第820頁。。
此外,岷江、沱江、涪江、渠江等河流,也是當時四川省內重要的糧食販運水道。它們與上述水陸交通干線配合,“北接漢中,南通滇黔,東流水路下楚,西抵西藏松爐”(113)丁寶楨《四川鹽法志》,《續修四庫全書》第84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22頁。,共同構成雍乾時期四川糧食販運的交通運輸網絡。
四 運銷的市場層級結構
雍乾時期,隨著常年少則數百萬石、多則上千萬石的商品糧食販運出川,四川省內各地逐漸形成了產地(初級)市場、集散市場、轉運(口岸)市場、消費市場等多層次、多功能且遍及全川之糧食運銷市場體系。為直觀展示雍乾時期四川糧食市場發育狀況,茲根據王笛的研究列如表2。

表2 清前期四川各地糧市運銷狀況表(114)本表根據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一書第209-210頁的內容制作而成。
從表2可知,雍乾時期四川糧食運銷的市場層級結構如下。
第一,重慶和成都兩大省內中心糧食集散市場的形成。重慶是長江上游中心城市和重要商貿口岸城市,同時也是四川最重要的糧食貿易中心和集散地。據乾隆《巴縣志》記載,重慶地處“三江總匯”,歷來“商賈輻輳”,雍乾時期,來自“吳、楚、閩、粵、滇、黔、秦、豫”等地的商客“舟集如蟻”,大量東運出川的糧食經過重慶中轉,使重慶成為“換船總運之所”,“米客之匯于渝者,覓朋托友,自為糴糶,頗稱便利”,“渝州每歲下楚米石數十萬計”(115)張九鎰撰《巴縣志》卷2《坊廂》,第24頁;卷3《鹽法》,第48頁;卷3《積貯·社倉》,第38頁;卷3《課稅》,第43頁。。既有研究表明,當時每年經由重慶出川的糧食有100萬石之多,這些糧食或從川西平原通過岷江由宜賓進入長江運達,或從川東北產糧區順嘉陵江、涪江、渠江而來,在此裝船出峽,呈現出“千帆蟻聚,百貨云屯”的繁盛局面。成都是清代四川乃至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成都市區有商業街道數十條,城市周邊有場鎮數十個。另外,成都平原河網密布,溝渠縱橫,依靠舟楫水運的交通運輸優勢,成都成為川西地區的糧食集散中心。據載,“附近內外兩江舟楫可通之處,軍民日食亦往往仰藉成都,而外省商販又在各處市場順流搬運,每歲不下百十萬石”(116)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折》第18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79年版,第417頁。。陸路運輸方面,以官府的官道及郵傳驛遞系統為基干,形成了以成都為中心,連接川東、川南、川北以及陜、甘、云、貴、湘、鄂、藏、青等省的道路交通和商業貿易網絡。即:以成都為中心,東路經簡州、資州、內江而達重慶,西南路經雅安、打箭爐而至康、藏,北路經德陽、綿州、廣元入陜西并可繼續北上,“經山西到達直隸”(117)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8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版,第295頁。,中路經南充、大竹、達州、萬縣到川東北,由此形成以重慶和成都為中心,覆蓋四川內地大部分境域的糧食流通運銷網絡。
第二,省內州縣區域糧食市場的興盛和糧食專業特色集散市場“米口”的形成。雍乾時期,四川糧食豐收并有大量剩余,不少產糧州縣除滿足當地民眾的基本口糧外,皆有剩余糧食作為商品糧而提供外運。有關事實,史志記載尤多。如溫江縣常年運銷成都之米,“歲值六七十萬金”(118)《光緒溫江縣鄉土志》卷12《商務》,四川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四川歷代地方志集成》第4輯第15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版,第434頁。;新都縣每年所產之米,運銷成都15萬石,運銷重慶及蔗糖產區簡州、資州等地7萬石(119)《新都縣鄉土志·商務》,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和家譜文獻中心編《鄉土志抄稿本選編》(10),線裝書局2002年版,第537頁。;德陽縣年產稻谷35萬石,大多運銷省內各州縣(120)《德陽縣鄉土志·商務》,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和家譜文獻中心編《鄉土志抄稿本選編》(11),線裝書局2002年版,第302頁。;廣安縣所產谷米,“販輸出境,幾遍巴蜀”(121)周克堃等纂《宣統廣安州新志》卷13《食貨志四》,《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58輯,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702頁。。有學者估計,雍乾時期,四川有約60-90億市斤即4000-6000余萬石的余糧需要通過水陸路運銷省內外市場(122)謝放《清前期四川糧食產量及外運量的估計問題》,《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第87頁。。清代府、州、縣治所在地,既是一級地方行政中心,又是規模大小不等的場鎮,這些場鎮即為市井,“市井者,場鎮也,利之所在,人必趨之,聚民間日用之需,入市交易,謂之趕場”(123)朱言詩等纂修《光緒梁山縣志》卷3《建置志·場鎮》,《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54輯,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82頁。。因而,雍乾時期,四川的一些州縣治所在地大多成為區域性糧食消費市場和集散市場。
糧食屬于笨重且價值較低的商品,其運銷大多采取集中裝載,盡量利用舟船水運以降低運輸成本。正因如此,四川的一些地處交通要道的城鎮和水陸路交匯處的渡口,糧商云集,既能接受四方糧,又能很快拋銷出去,年集散量少則百萬石,多的可達千萬石,逐漸成為遠近聞名的糧食集散市場,即“聚米之場”。如成都附近金堂縣沱江流域的趙家渡,就是川西平原重要的糧食集散專業市鎮,其所聚集的糧食主要來自附近的新都、廣漢、德陽及本縣。趙家渡這樣的糧食集散市鎮,它們所聚集的糧食中的大部分,又由水陸路運轉口運銷至成都、簡州、資陽、內江等地,再“由小江水次運至重、瀘二處交兌”(124)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第5輯,臺北故宮博物院1982年版,第741頁。,從而在這些地區之水陸路交匯處形成眾多“米口”。雍乾時期,四川境內的渡口,除合州、內江、瀘州、樂山等沿江中等城鎮外,岷江、嘉陵江、長江、涪江、渠江等江河沿岸的大小渡口,也多為糧食轉運的集散市場“米口”。其中,岷江上游18處渡口,有11處為“米口”(125)張九鎰撰《巴縣志》卷2《津渡》,第40-43頁。。由于四川谷米外銷之大宗乃江、浙等長江中下游各省區,致使長江干支流的渡口多成為米口,這在重慶境內體現得尤為明顯。如江北廳寸灘,“置有義渡場,通兩路口等處,米口”(126)福珠朗阿修,宋煊、黃云衢纂《道光江北廳志》卷2《輿地·津渡》,《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5輯,巴蜀書社1992年版,第472頁。。又如嘉陵江沿岸炭壩渡等16處渡口,有9處為“米口”;長江沿岸的溉蘭溪等9處渡口,全為“米口”(127)張九鎰撰《巴縣志》卷2《津渡》,第43頁。。
綜上可見,清雍乾時期,隨著糧食運銷的發展,在鄉村基層場市發展的堅實基礎上,四川逐漸形成了以重慶、成都兩個中心城市領頭,以州縣區域糧食集散市場和被稱為“米口”的糧食集散專業場鎮為骨干的多層級、多功能并覆蓋全川的糧食運銷市場體系。凡能通舟的大小河流,都有糧船往來;缺少水運的廣大地區,則用車載、馬馱、人背、肩扛。頻繁的糧食運銷活動,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不同層級的糧食市場,對滿足城鄉的基本生活與經濟投入需求,對不同地區調劑余缺以及救災賑濟等方面,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五 結語
糧食是人們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也是一種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交易物資,糧食生產及其商品化的程度亦是衡量某一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狀態和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尺度。通過對雍乾時期四川糧食運銷的區域、形式、運輸方式和市場層級結構等問題的討論,可以發現,這一時期,四川糧食的生產不僅本省供應充足,而且有大量剩余,或供政府調撥和采買,或供商民販賣。概言之,清代四川糧食運銷,初興于康熙末年,鼎盛于雍乾時期。這一事實證明,清初以來,朝廷在四川頒布和實施了一系列“安民”、“裕民”、“便民”的政策和措施(128)陳世松、賈大泉主編,吳康零分卷主編《四川通史:卷六 清》,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6頁。,激發了官員招民墾殖和從外省移民入川的熱情,快速填補了人口空缺,缺失的勞動力得到補充,土地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農業生產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雍乾時期,四川糧食的豐產和大量外運,既是四川作為農業生產大省和糧食輸出大省的重要標志,也是四川糧食商品化程度顯著提高的重要表征。
同時,也需看到,雍乾時期四川糧食運銷之興盛,是建立在本省糧食供應有余、外部又有市場需求這樣的條件之上的。當時四川人地關系較為寬松,人均耕地比較富裕(129)清前中期,四川的人均耕地一直高于全國人均耕地數,以乾隆三十一年為例,四川人均耕地面積為15.55畝,分別是湖北的2.3倍、浙江的5.5倍、江蘇的5.6倍、福建的9倍。參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梁方仲文集》,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548、549頁。和產糧豐饒,而外省甚至包括湖北在內的長江中下游地區都需要四川的糧食接濟,兩者結合,既滿足了缺糧省份的需求,又促進了四川糧食生產及其商品化的發展。但嘉道以后,四川人口無節制地增長,導致土地資源日漸緊缺,人地矛盾日益尖銳(130)到嘉慶時,四川人口和耕地成正比遞增的趨勢被逆轉,人均耕地優勢被過快的人口增長打破,人均耕地僅有2.17畝,首次低于全國人均耕地數的2.19畝。參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梁方仲文集》,第554頁。,四川開始由余糧省漸變為缺糧省,糧食外銷逐漸減少,幾至斷絕。隨著糧食商品化前提的漸漸消失,四川糧食商品化與市場化水平漸呈降低的態勢。四川糧食商品化發展的這種局限性頗令人深思,其所蘊含之歷史經驗和教訓或可引為鑒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