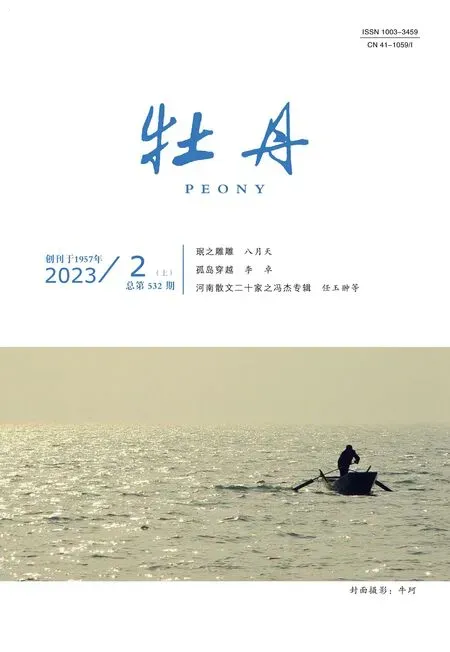提燈籠的孩子
王太貴
一
西北風呼嘯著,天空陰沉沉的,像裹著厚厚的灰毯子。這是大雪來臨的前兆,比天氣預報還要靈。十二歲的來發跟堂兄祝發一起,撅著屁股,往趙崗山上爬。
農歷正月十二,下午四點半。先是零星的雪花從空中飄落,一些掛在樹梢和灌木叢上,一些中途就被風吹走,只有極少部分,準確地粘在來發的額頭,又瞬間融化。來發學著堂兄的做法,把葫蘆頭燈籠往胸前掖,這樣可以阻擋一些風雪。但很快雪就大起來了,漫天飛舞。祝發加快了腳步,說,加把勁兒,走快點兒,再翻過兩道山梁就到了。后面的來發氣喘吁吁,他解開棉襖扣子,把燈籠扛在肩上。
兄弟倆手中的燈籠,俗稱葫蘆頭,是紅旗山一帶最為普通的燈盞。三米長的翠竹,用鐮刀在一端十字形劈開三四寸長的口子,再把頂口用鐵絲扎緊。四根寸長細樹棍,將劈開的地方撐開,一個如長矛的燈盞輪廓便出現。再糊上白紙,留一可活動的紙簾,方便掀起,裝入蠟燭,燈就成了。夜晚點亮蠟燭,插在亡者墳頭,一片通亮。
祝發來發兄弟倆這次是給本村的年吾送燈盞。年吾九十九歲,年前冬天去世,壽終時近百歲年齡,算得上一樁喜事。年吾沒有什么特殊的養生之道,喜歡吃烤紅薯和糍粑。冬天吃完晚飯,放下飯碗,就移步到火塘邊烤火。有時候還喜歡到自家稻場上走幾圈兒,消消食。
兄弟倆扛著燈盞走進年家設在稻場上的草棚時,渾身上下都落滿了雪,葫蘆頭上的白紙有的地方已被雪水漚破。他們從懷里各掏出兩根白蠟燭,連同葫蘆頭燈,遞給了年家的后人。交掉燈和蠟燭,兄弟倆松了一口氣。有人給他們端來兩杯熱茶,喝完茶,晚飯就該開席了。
那天雪大,親戚和村人送來的燈盞都擺放在草棚里,滿滿當當的,來發看得眼花繚亂。葫蘆頭是最普通的。吊子燈,花瓶,鯉魚燈,馬燈,兔子燈,各式各樣。來發第一次看見這么多燈盞,心想,如果每盞燈晚上都亮起來,那該多漂亮。年吾真有福,死了還有這么多人給他送花燈。來發想起年吾的模樣。頭發亂糟糟的,衣衫不整,身上永遠散發著草木灰味兒,這是長期烤火造成的。年吾家住在紅旗山海拔最高的趙崗山上,下一趟山,來回有十幾公里。年吾很少下山,偶爾使用的日用品都由他上小學的重孫幫忙采購。來發印象中,年吾就下過一次山,腰上束著草繩,像個邋遢的仙人。他走路慢悠悠的,似乎比蝸牛都要慢。那天有個叫小翠的小姑娘,也要經過那段路去姥姥家。她遠遠望見年吾,居然害怕地躲起來。但年吾走得實在太慢了,小翠躲在樹叢里都憋出尿來了,年吾還是沒有走完那段短短的路。小翠只好哭著往家的方向跑,路上被紙匠于德正碰見,于德正得知原委后,呵呵笑起來,他牽著小翠,把她從年吾身邊護送走。
來發想到這里,不禁暗笑起來。他往草棚偏僻角落瞥了一眼,意外地看見一盞兔子燈,他心有所動。晚飯已經開席了,人群慌亂起來,都搶著擠到桌子上。大家都想早點兒吃上飯,雪這么大,返程的路可不好走。
來發和祝發不在一桌。來發胡亂吃了幾口,就悄悄溜到草棚子里,他看上了那個兔子燈。當他把燈盞拽出來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判斷失誤,兔子燈很長,這樣拿出去,太顯眼兒了。好在兔子燈被拽出來之后,里面又露出一盞金魚燈,小巧玲瓏,便于攜帶,關鍵是它更符合來發的審美。
來發左右瞅瞅,沒有人影,幫工的都去廚房烤火了,那里有一團熱烘烘的火堆。送燈的人都在堂屋里猜拳喝酒。來發置身在五顏六色的燈盞里,他一點兒也不害怕。但如果將這些燈盞插在墳地四周,即使亮起五彩斑斕的燈光,來發也不敢去。他解開棉襖的扣子,掂起金魚燈,塞到腋窩下,又若無其事地扣上扣子。他順勢坐在旁邊的長凳上,仰頭看著棚外灰蒙蒙的夜空,雪花簌簌,屋頂和樹梢都白了。
雪,讓夜晚白亮起來。祝發踉踉蹌蹌地走出來,他顯然喝醉了。年吾的孫子把他扶著,客氣地說,要不,今晚就住這里,我們預設了幾個地鋪,稻草厚著呢!祝發直搖頭,雙手抱拳,說,謝謝啦,我們得趕回去。
上山容易,下山也容易,前提是得來一場大雪。來發和祝發幾乎是滑翔著奔下趙崗山的,像電視里的滑雪運動員那樣。他們赤手空拳,輕而易舉就完成了高難度動作,哧溜哧溜地滑到了山底。
二
扎匠家燈光暗淡,來發相信,即使周圍一片漆黑,扎匠莫綿全也能熟練地操作,甚至毫無差錯。
昏暗的燈泡下,是一張烏黑的小方桌。桌旁的火塘里燒著樹蔸,偶爾噼里啪啦響幾下。莫綿全戴著老花鏡,手持剪刀坐在桌旁剪紙,紅藍黃綠白,不同顏色的紙張在他剪刀下,像玩魔術一樣,很快就變成了條條縷縷、窟窟窿窿,一些魚的眼睛,兔子的尾巴,馬的耳朵,鳳凰的頭,還有羊的四肢,都現出雛形。莫綿全對面坐著她的老伴兒,她用食指從瓷碗里蘸糨糊,往成型的花燈“骨骼”上抹。莫綿全的老伴兒姓勞,老家在廣西,這么遠怎么嫁到紅旗山?我們無從知曉。她心靈手巧,會剪紙,會做針線活兒和花燈,我們都喊她莫嬸,而喊莫綿全莫師傅或老莫。這些“骨骼”是昨天晚上莫綿全連夜趕制的。臨近元宵節,預訂花燈的人非常多。有的買給孩子玩,有的送給死去的親人。每年從臘月底到元宵節這二十來天,是莫家最忙碌的時候,就連莫綿全讀高中的兒子,也要參與到花燈的制作中。
花燈的“骨骼”是由麻秸稈、竹絲和樹枝等材料組成,使用最多的是麻秸稈。剝了皮后的麻秸稈曬干,是絕好的引燃物,家庭主婦們的最愛。莫綿全對秸稈的愛肯定超過家庭主婦。潔白的麻秸稈,咔嚓一聲,一撅成兩截,露出細長的白芯。我們常用兩指夾起一根麻秸稈,用火機點上,學大人抽煙。麻秸稈在莫綿全這里化腐朽為神奇,他用菜刀切,一寸長,三寸長,一尺長,五尺長,長短不一,各有所用。段段麻秸稈之間用竹簽鉚上,嚴絲合縫。有的花燈看起來很大,提到手里卻很輕,主要原因在用料上。
莫綿全最拿手的是花瓶燈,因為花瓶燈深受顧客青睞,檔次適中,價格不高。花瓶制作沒有太多的花里胡哨,其形狀如立體梯形,就像盛米的斗一樣。花瓶四周要貼上福字、壽字、喜鵲或鳳凰等剪紙。花瓶燈最喜人的地方是四角還要插上帶綠葉的樹枝,松柏或女貞,更顯肅穆和莊重。遠遠望去,矗立在竹竿上的花瓶燈非常大氣,點上四根蠟燭,通明透亮。
來發走進莫綿全家的時候,那堆火都快熄滅了,幾粒火星有氣無力地閃著。莫綿全和他老伴兒正全身心投入到花燈制作中,對門外的來人毫無察覺。
室內光線暗,來發不小心碰掉了灶臺上的水瓢,水瓢落地的啪嗒聲有點兒沉悶,莫綿全和老伴兒才抬起頭來。
莫師傅,我來取燈,俺爸年前預訂的七盞燈,做好了嗎?來發說。
熊運龍家的,我叫來發,是他兒子。來發有點兒不耐煩,他想把頭頂那盞昏暗的燈泡摁掉,換上一盞電棒。他覺得在黢黑的屋子里做花燈,簡直是褻瀆。
哦,運龍家的呀,都這么大了。那些燈做好很久了,你們一直沒來取,昨天被丁埠街上的三綹子買去了,他急著用燈。明天,明天我就能把那七盞燈趕制出來。明天來拿吧,過節還有幾天呢。莫綿全說。
來發只好退回屋外。天終于放晴了,雖然遠山的雪還沒完全融化完,但至少不會影響玩燈了。
這個瘋子,去年就開始預訂花燈,看來他真快死了。莫綿全彎腰箍船燈骨架時,突然低聲冒出一句話。去去去,別胡說,熊運龍好著呢,年初一還來這邊拜年呢!莫嬸不希望丈夫在做燈時,說不吉利的話。莫綿全直起腰,搖晃著腦袋,莫嬸放下手中的物什,給他捶捶后背。他們已經形成了高度默契,夫唱婦隨。
別說拜年了,那兔崽子,居然連我家的門都沒有進,還說什么扎匠家晦氣。這不是神經病嗎!晦氣!晦氣你還買什么花燈啊,我看他死了就沒人送花燈。
莫嬸嘆口氣,說,跟他見識啥。他給錢,我們給他花燈,一清二白,其他就甭管了。干活兒吧,明天他還要來取七盞燈呢!
三
熊運龍十年前莫名其妙得了病,去了很多醫院,都瞧不好,有時瘋瘋癲癲,有時又一本正經。病沒有治好,倒是把家產搞空了。大兒子慶發第一年高考沒有考上,又復讀了兩年,還是竹籃打水。熊運龍病情加重,他砸了家里僅有的一件電器——熊貓牌黑白電視機,又三天兩頭出去尋釁滋事,鬧得家里雞犬不寧。家人實在沒有辦法,就連灌大糞這樣的土方子都使用了,依然無濟于事。母親找來家族叔伯們商量,把他扭送到市精神病院,強制治療兩個月。精神病院的集中治療初見成效,熊運龍出院后,有種脫胎換骨的感覺。
大兒子慶發見父親身體恢復得不錯,便放下心來,背起行囊,遠赴上海打工去了。兒子臨行前,熊運龍淚沾衣襟,握著慶發的手久久不松,說,兒啊,你沒有考上大學,是我最大的病,我恨自己,沒能給你創造好條件,你可別怪我。慶發哽咽著說,這是我的命,不怪你,你在家養好身體,我就放心了,讓我到外面闖闖吧。
慶發這一走,很多年都沒有回過紅旗山,與家里聯系極少,偶爾給弟弟來發寫封信。紅旗山通電話之后,他也很少打電話。一通電話,就說店里忙,今年又不能回家過年了。他在上海從美發店的學徒工干起,肯吃苦,腦子活,兩年多后就成了店里的金牌理發師,再后來獨自開了一家店,生意很好,收入頗豐。
熊運龍的病經常反彈,他時常夜不歸宿,躲在史河灣旁邊的社廟里過夜。還喜歡到處亂竄,到別人家坐下來,就賴著不走,看見餐桌上有什么,就吃什么,比在自己家還自由。有次去了屠戶業達文家,看見餐桌上有盤炒黑豆,抓起來就往嘴里塞,還覺得不過癮,叫嚷著再來一壺酒。業達文急著外出干活,但又不敢跟這個神經病硬來,就拿出半瓶臨水玉泉酒給他。熊運龍毫不客氣,非常自然地從碗柜里拿出碗筷和酒盅,吃一粒香噴噴的炒黑豆,再品一小口白酒,美滋滋的,十分愜意。他一邊吃,還一邊嘿嘿笑著招呼業達文過來,陪他喝一盅。
來發兩手空空,垂著頭回到家中。他沒有取回父親需要的燈盞,一頓臭罵是少不了的。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小算盤也落空了,他不能為自己選一盞好看的燈。要等明天,明天誰知道父親會不會臨時變卦。幸好,他還有盞金魚燈,那盞燈自從帶回家后,他一直把燈藏在自己的書箱里。書箱古樸典雅,配有一枚金黃的銅鎖,是哥哥慶發用過的。他現在成了這個箱子的主人,金魚燈放進去,綽綽有余,蓋上箱子,再扣上鎖,誰也不知道里面藏著一盞燈。
家中沒有人,但大門沒有鎖。來發悄悄推開門,溜到自己的臥室。他從墊被下摸出書箱的鑰匙,打開箱子,金魚燈還在里面。他有點兒恍惚,離家不到一個小時,感覺就像走了好幾天,他總擔心那盞燈會不翼而飛。來發覺得一盞燈未免太孤單,他想起傳說中的老莫家的船燈,小伙伴們都以有一盞老莫家的船燈而自豪。如果再來一盞船燈,和金魚燈放在一起點亮,一定非常迷人。
來發正沉湎于對船燈的想象中,后背被父親突然拍了一巴掌。他一個激靈,咚的一聲,慌忙蓋上箱子,又迅速地把鎖鎖上。
這里面是什么?拿出來給我瞧瞧。熊運龍板著臉說。沒有,啥都沒有,除了俺哥的一些破書。來發回答得急促。不要哄我了,我也喜歡看小說,這箱子里還有幾本古龍的小說,給我拿出來。熊運龍壓低了聲音,臉上毫無表情。俺哥的小說你早就給燒了,你忘了嗎?他第一次沒考上大學那年。來發突然想起來父親燒書的事情。熊運龍沉默了片刻,說,我懷疑這里還有小說書,你千萬別走你哥那條路,看小說耽誤了考大學。來發連連點頭,暗自慶幸父親沒有叫他打開箱子檢查。
父親的腳步剛跨過房門,又突然轉回身,傻笑起來,說,箱子里的那盞燈好看,我也喜歡。我需要一盞燈,晚上廟里太黑了,沒有燈,我有點兒害怕。
父親關上門出去了,把一個巨大疑問拋給來發。鑰匙藏在墊被下,這個不會有第二個人知道,箱子上的鎖也完好無損,父親是怎么知道里面的燈呢?來發撓了撓腦門,覺得實在無解。早晨父親叫他去扎匠莫師傅那里取燈的時候,還火急火燎,片刻不能耽誤的樣子,現在居然只字不提取燈一事。
四
第二天一早,來發吃過早飯,丟下飯碗,撒腿就往扎匠老莫家跑。母親喊住他,審問一大早就往哪跑。來發無謊可撒,只得如實交代,父親年前在莫師傅那邊預訂七盞花燈的事。母親搖搖頭,嘆口氣,說,去吧,快去快回,要是再不拿回來,那個瘋子又要發作了。
熊運龍昨晚一夜未歸,裹著破舊的棉被,睡在社廟里。之前他們還不能接受父親的這種舉動,找了幾個長輩族人,硬把父親帶回家,幾個人死看硬守。父親在家里看似睡得很香,但第二天精神卻十分反常。房前屋后瘋癲著亂跑,口中念念有詞,說遇見了紅毛怪要來取他性命。三番五次,家人經過這么折騰,都精疲力竭,便放棄了對他的看護。父親自從去了廟里過夜,精神反倒正常起來。
來發從家走的時候,父親還沒有從社廟回來。他疾步如飛,生怕去遲了,預訂的花燈又被別人搶走了。
老莫家的燈泡還是那樣,病懨懨的,昏暗得毫無生氣。但走廊里卻一派豪氣,各種花燈重重疊疊,風一吹,彩色穗子搖晃著,像跟他打招呼。
莫師傅,我來取燈。來發對著低頭糊燈的莫綿全說。
燈做好了,七盞吊子燈,總共七十塊錢。不過你爸只付了一盞燈的訂金。莫綿全沒有抬頭。
來發這才想起,父親只說七盞燈,卻沒有說錢的事。他的心跳加快,覺得這是件非常丟人的事。兩次來取燈,卻沒有帶一分錢。來發不想再跑第三次,就自作主張,說,那就拿一盞燈好了。剩下的六盞燈,回頭再說。
行,你自己看著辦,都拿回去也行,有空再把燈錢送來。
不了,先拿一盞吧。來發喃喃地說。
莫嬸把來發帶到后院儲藏室,讓來發自己選一盞吊子燈。每一盞燈都那么漂亮靈動,來發眼花了。但拐角處的幾盞船燈似乎不服氣,從窗口吹進的風,把其中一盞船燈吹翻了。來發只看了一眼,就覺得吊子燈略有遜色。
莫嬸,我能選船燈嗎?來發的語氣近乎祈求。
船燈比吊子燈貴兩塊錢哩!莫嬸有點兒難為情。
哦!來發這一聲“哦”似乎從嗓子里擠出來的。
來發彎腰從一堆吊子燈里選了一個紅黃相間綴著紫穗的。來發提著吊子燈,目光卻滯留在那盞彎彎的船燈上。他有點兒不舍地轉身離開。
發子,你等等。莫嬸喊住了他。莫嬸拿起地上的藍色船燈,遞給他,小聲說,算了,就給你船燈吧!你從旁邊側門出去,省得叫俺家老頭子看見,他要是發現了,肯定罵我。
來發如獲至寶,放下吊子燈,雙手捧著船燈,連連彎腰鞠躬。對這突如其來的恩賜,他不知道怎么表達感謝。
那一天是正月十四。從丁埠街到紅旗山一帶,到處張燈結彩。玩龍舞獅子,踩高蹺,耍花燈的,鑼鼓喧天,人山人海。鞭炮噼里啪啦,孩童嬉笑聲不絕于耳,熱鬧極了。
偶爾山間冒出的一處新墳上,早已插滿了各式花燈。風吹燈搖,紅綢綠紙,與兩岸青山相輝映,間或幾聲鳥鳴,把群山的靜謐意境襯托到極致。如果到了晚上,這里會燈火通明,讓人想不到是墓地,反倒像一場盛大演出。山腳下溪水奔騰,土壤開始松動,春天總是在這時悄悄來臨。
來發的心情極其舒暢,右手白繩子下吊著船燈,一晃一晃的,比自己穿上一件新衣服還要體面。他從莫師傅家后院門走出的時候,太陽已經翻過東邊的山巒,陽光穿透他手中的花燈,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影子。花燈像月牙,兩頭彎彎,中間拱起弧形的船篷。船頭還有個披蓑衣的船夫,搖著槳櫓,遙望遠方。船篷由幾道竹絲箍成,糊上紅宣紙,空間足夠放一根蠟燭。
來發想,如果把船燈點亮,放進小河里,會隨著河水一直往前流嗎?從門前小溪,流到史河灣,再從三河尖進入淮河。當然,那時候的來發不知道史河會流入淮河的。二十多年后,在陽泉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的來發,經常站在辦公室的地圖前發呆,他若有所思,目光逆流而上,尋找史河的蹤跡。他驚奇地發現,史河居然流經陽泉的某個集鎮。也就是說,他兒時游泳的溝溪,經過九曲十八彎,又來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他的腳下。那盞船燈,搖搖晃晃,在眼前的地圖里時隱時現。
來發提著船燈,與船燈的影子,在鄉村小道上一路狂奔。那時,能給孩子買花燈的極少,更何況是價格不低的船燈。瘋子家的兒子提著船燈!后來成為紅旗山的傳奇故事。
來發經過豆腐店時,故意放慢了腳步。豆腐店外等著買豆干的小翠半閉著眼睛,坐在臺階上打盹兒。來發咳嗽了兩聲,小翠微微睜開雙眼。來發手里的船燈,讓小翠的眼睛瞬間亮起來。船燈,你有船燈!小翠十分驚詫,一屁股站起來,由于過分激動,她忘了腳邊缽子里的黃豆,向前跨步,踢翻了缽子,黃豆滾了一地。
小翠顧不得四下丟散的黃豆,說,來發,把燈借我玩玩,我就摸一下。來發看著地上有幾顆黃豆滾到她的腳下,樣子很可憐,就像此刻的小翠。來發點點頭,把船燈提到小翠眼前,晃了幾下,說,看見了吧!這個可是莫師傅親自制作的,不是別人做的,莫師傅的燈!小翠胖嘟嘟的臉上堆滿了笑容,可憐兮兮地說,我回家找壓歲錢,也要去莫師傅那里買一盞。
來發提著船燈,依次路過鐵匠鋪、食品店、汪醫生診所、變電站和老紀裁縫店,他走得很慢,還不時用余光打量路旁的行人。這是誰家的孩子?這盞燈很好看,像莫師傅的手藝!媽媽,我也要一盞這樣的花燈。來發逶迤而去,但這些聲音卻在他的耳朵里揮之不去,讓他很快樂。
熊瘋子家的花燈!這個瘋子,離送燈也不遠了!如被馬蜂蜇,來發的心猛地絞在一起。他不敢抬頭尋找這個聲音的源頭。內心卻更痛恨父親。
道路崎嶇,一個越來越小的影子,提著花燈,消失在路的盡頭。
五
來發手提船燈,哼著小曲回到家里。熊運龍蹲在門前的石碾上,正捧著海碗吃玉米糊。厚嘴唇沿著碗沿,大聲地吸溜,碗口轉了兩圈兒,玉米糊見底了。他抬起頭,下巴上還粘著一塊兒咸菜。來發想躲閃,但已被父親看見了。他低著,佯裝沒有看見父親,快速溜進屋里。
他沒有想到父親居然這么鎮定,對我可以視而不見,但對我手里的燈籠,卻不能裝作看不見呀!也許父親早已忘了預購燈盞的事。可如果一旦想起來,七盞燈,變成了一盞燈,自己怎么去解釋?來發心里沒底。
熊孩子,還有六盞燈呢?來發躡手躡腳地進了房屋,他以為成功逃脫了父親的目光和詰問。
什么六盞燈,七盞燈?你要那么多花燈干什么?瞧你的記性,不就預訂了一盞燈嗎?燈那么貴,我們可以自己動手制作的。母親推開廚房的窗戶,對著外面的丈夫似怒非怒地說。
我就要七盞燈,你們都糊涂了。還有六盞燈在哪?熊運龍發怒了,他把手里的碗筷扔在石碾上,七零八碎的瓷片飛了一地。
又瘋了,又瘋了呀!我的祖宗啊,你就不能讓我們過個安心的節?母親哭起來。來發雙手攥得鐵緊,他想沖出去,給父親一拳。
兔崽子,你要兩盞燈干什么?給我一盞,你別鎖那么緊。早晚我要把那箱子拆掉。我讓你跟慶發學,不好好讀書,整天看小說。
來發把書箱里所有的書都搬出來,扔到床底,騰出更多空間,正好可以放下兩盞燈。金魚燈在左,小船燈在右。他輕輕關上箱蓋,鎖好,又用試卷把鑰匙裹起來,塞到墊被下面最深處。
六
入秋之后,史河灣的水溫順了許多,陽光灑在河面上,金光粼粼,無限溫柔。來發去了鎮上的中學讀書。學校位于史河上游,門前有一大片河灘,又叫狗頭灣,與下游的狗腿灣連在一起,彎曲如狗。
老師經常把學生帶到河灘上體育課,耍拳,蹲馬步,長跑。夏天的時候,男生還能跟著體育老師下河游泳。
那天下午,最后一節是體育課,來發頭疼厲害,請了假,趴在課桌上休息。同學們跟著老師,在操場上練習新一套廣播體操。中間休息時,遠處河灘邊匆匆走來兩個戴口罩穿白大褂的醫生和三個戴大檐帽的警察,醫生手提皮箱,蹲在河灘上。地上躺著一個黑衣人,距離較遠,看不清面容。但警察和醫生的到來,足以讓學生們興奮和好奇。幾個調皮的男生,已經飛跑至河灘,想一探究竟。
但警察在黑衣人四周拉了警戒線,幾個男生距離他們足有一百米遠的時候,警察就已大聲呵斥起來,滾,快滾,有什么好看的!
醫生把嘴巴上的口罩往鼻翼上提了提,然后戴上橡膠手套。其中一個扒掉黑衣人的上衣,另外一個醫生打開工具箱,掏出锃亮的手術刀,朝黑衣人的胸膛劃去。幾個男生第一次看見這種場景,不禁牙齒發軟,紛紛后退,逃回了操場。
不知誰在人群里喊出聲,看河邊,法醫在剖尸,像剖魚一樣,真刺激。體育老師的哨聲此刻失靈了,孩子們頭伸得老長,像鵝一樣紛紛往河灘邊望去。
下課鈴聲響起,只有三層樓的教學樓頓時喧嚷起來。教室里只有來發一人,顯得格外空曠,樓上教室里的桌凳來回挪動的聲音尤其刺耳。來發醒了,左臉頰上還印著課桌上的木紋痕跡。
幾個同學急急忙忙從操場回到教室穿外套,看來發在那里發呆,像發現巨大秘密似的告訴來發,走,咱們也去河灘上看看,那里有人在剖魚,知道嗎?那個同學用手比畫著在自己的胸前豎劃下去,然后神秘地說,警察也在,醫生給一個死人剖尸呢!
來發頭疼厲害,喉嚨里像塞了一把刀,即使輕輕咳嗽,也異常難受。幾個同學穿上外套,先后離開教室,跑向了河灘。來發拖著沉重的步子,走到操場邊,看見黑壓壓的人群在河灘邊緣駐足,場面非常壯觀。三個警察優哉游哉,而穿白衣服的醫生卻手忙腳亂,俯身地面,正給躺在地上的人套上白色衣服,那種從頭到腳都能嚴密包扎起來的衣服。
晚上七點鐘,來發被大舅用自行車從學校帶回了家。路上,大舅一聲不吭,自行車蹬得飛快,后座上的來發也不說話,屁股被顛得生疼。
到家的時候,大老遠就聽見屋里屋外亂哄哄的。石碾旁邊有個擔架,上面躺著人,被一張白布從頭到腳蓋得密不透風。
七
熊運龍揣著大兒子慶發的匯款單前往鎮上郵局。路過菜市場,在一家水果攤前逗留了一會兒。都秋天了,還有又圓又大的西瓜,熊運龍心想等取款回來,買幾個西瓜帶回家。來發母親本來不打算叫他去取款的,看他最近一段時間精神比較正常,又收到兒子的匯款,心情高興,就破天荒地隨他獨自去鎮上。叮囑是少不了的,即使她知道再多叮囑對熊運龍來說也是白搭。
水果攤的老板是個胖女人,坐在凳子上織毛衣,瞧了他兩眼,說,要不要買幾個?再不買,就沒得吃了!
熊運龍乍一聽,有點兒不快活,這個娘們,怎么咒人!便懟過去,你才沒得吃呢,你全家都沒得吃了。胖女人放下手里的針線,大叫起來,你是來買瓜,還是來找揍的?
我要買瓜,我看你身上那兩個瓜挺大的。熊運龍盯著胖女人的前胸,一邊說,一邊從口袋里掏出匯款單在她面前上下搖晃,我要把這所有的瓜都買下。
胖女人發飆了,覺得這個人是無事生非,呼天搶地喊丈夫。里面樓梯咚咚咚下來一個黃頭發的小年輕,他早已聽到了熊運龍不著調的話。年輕人二話沒說,抄起店里的秤砣,就往熊運龍身上砸去。只一下,熊運龍捂著胸口,應聲倒地。
警察很快介入調查,雙方各執一詞,難解難分。最后不得不采取法醫驗尸的辦法,以驗證熊運龍的死因。
大兒子慶發回到家中時,熊運龍都已經出過棺了,屋子里坐滿了參加葬禮的親人和鄉鄰。
母親早已哭成了淚人,她對自己沒有阻止丈夫獨自外出萬分悔恨。而那張一千元的匯款單,皺巴巴的,沾滿了泥漿。慶發拿起匯款單,攥在手里,使勁捏成了很小的一團。
慶發喊上來發,陪他去父親的墳地。剛走到路口,來發又轉身回到家里,他打開書箱,顫抖著拿出兩盞可愛的花燈,左手提著金魚燈,右手提著船燈,陪哥哥朝著父親墳地的方向走去。
慶發在父親墳前沒有再哭,他把手中的匯款單慢慢抻平,巴掌大小,放在墳頭,壓上一塊兒小石頭。來發已經把兩盞花燈掛在墳地旁的桑樹枝上,說,哥,咱們晚上再來,來點蠟燭,咱倆一人一盞。
慶發點點頭,伸手摸了摸弟弟的腦袋,幾年不見,來發的個頭跟自己差不多高了。慶發說,如果沒猜錯的話,明年元宵節上燈,咱家得上七盞燈了。
八
二零一九年中秋節晚上十一點四十分。來發在辦公室為四十萬字的《陽泉地方新志》寫完了最后一段文字。
《七盞燈》是這本新志的壓軸篇目,來發前前后后寫了一個多月。他以“七盞燈”的故事為引子,詳細描寫了紅旗山地區的人文、歷史、民俗、地理、經濟、人口和紅色故事,包羅萬象,洋洋灑灑。如果不是這篇文章,新志估計能提前一個月交付出版社。
他關了電腦,長舒一口氣。
三年前,在全省地方志理論研討會上,來發提交了一篇長達萬字的學術研究文章。他對目前地方志撰寫極為不滿,諸多弊病人盡皆知,但各級依然熟視無睹。他認為地方志辦公室已淪落到可有可無的地步。很多地區在地方志撰寫上,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習慣于向當地各部門各單位攤派任務和指標,然后再將收集來的大量圖片文字一鍋煮,不求質量,毫無創新,無常識錯誤和錯別字竟然成了底線。有的干脆外包給專業公司,當上了甩手掌柜。
來發建議要提高地方志的趣味性、史料性和文學性,將地方志寫成一本干部群眾愛讀,婦孺老幼樂見的讀物,而不是一堆又一堆的廢紙。研討會上,來發的精彩發言得到了與會專家、學者和同行們的高度肯定,他的論文也被組委會評為一等獎。但他的理論在具體推廣實施中,卻困難重重,這遠遠超乎了他的預料。
來發決定身體力行。他親自操刀,五加二,白加黑,加班加點,去民間走訪調查,翻閱大量檔案資料,嘔心瀝血,歷時三載,終于完成一部理想中的地方志。
對著辦公室墻上的地圖,來發掏出煙盒里的最后一支煙,點上。煙圈裊娜而上,地圖上的山山水水,似乎籠罩在煙嵐云岫間。
來發突然覺得《七盞燈》的結尾有些倉促。他把半截煙扔進煙灰缸,打開電腦,在文章末尾,又添上幾行詩:
燭光消失在影子里,而火焰
于灰燼中留下絕望的回眸
孩子們提著燈籠,像提著
自己的童年,他們在不停奔跑
帶著光亮、希望和漫長的道路
來發打開手機,看見妻子發來視頻。兒子和鄰居家的幾個孩子,在小區附近公園的噴泉池旁,提著閃閃發光的電子童趣小燈籠,來回奔跑,嬉笑打鬧。
看完視頻,來發的眼睛濕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