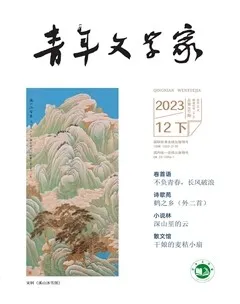賈平凹小說與西安都市風景的話語建構研究
張雅馨
本文以“賈平凹小說與西安都市風景的話語建構”為核心,立足于進入新時期后西安都市風景(主要指人文景觀)變遷背后所蘊含的公共話語空間裂變轉型實質,并試圖從話語中特有的連接客體“特定社會語境”與主體“人際溝通交往”,涵蓋“說話人、受話人、文本、溝通、語境”,映射復雜生存因素坐標的建構功能入手,挖掘客觀對象化的“景觀社會”與主體本質力量在長期物質文化實踐中與深層社會文化心理的相融、滲透,而形成的雙向主客體互動關系。同時,借鑒法國社會學家德波在《景觀社會》中將受商品資本邏輯與內在權力關系控制的現(xiàn)代性景觀社會的特點,概括為“內在權力關系下的‘看與‘被看”“生產者之外物與物的社會關系的隱性控制”“表象的增殖與欲望合謀造成自我喪失的生存迷惘與救贖”等方面的觀點,立足于“社會景觀”與“社會的真實存在”處于“應然”與“實然”張力關系的定位,分別探討“欲望”與“反欲望”話語(以《廢都》為例)及“困境”與“反困境”話語(以《高興》為例)與西安都市景觀社會作為“以影像為中介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之間的有機聯(lián)系。
一、西安都市景觀社會及其發(fā)展歷程
在賈平凹小說創(chuàng)作三大階段中的具體映射
西安都市景觀社會作為主客體交互樞紐之于賈平凹小說文本實踐的話語建構意義,可以根據相關學者的階段分層(葉瀾濤將賈平凹各個時期小說群的評論范式分為“早期—感受式”“中期—創(chuàng)作范式和心理趨向”“當下—宏觀多元批評史視角下批評與創(chuàng)作的互動關系”;李遇春將賈平凹的創(chuàng)作歷程大致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1973年至1992年—以商州世界為重點”“第二階段為1993年至2004年—以《廢都》為標志的發(fā)展探索期”“第三階段為2005年至今—以《秦腔》為標志的藝術成熟期”)作出如下討論。
首先,以賈平凹《商州初錄》《又錄》《浮躁》為代表的早期小說中蘊含著關乎商州鄉(xiāng)土風景的“戀鄉(xiāng)情結”,其作為20世紀80年代西安都市風景的參照,反映了以商州風景的邊緣性象征域為樞紐,譯解戀地情結下移民身份認同與擬象記憶模塑問題;其次,以《廢都》為代表的中期小說中蘊含的“文人話語”“本能話語”“轉型話語”“都市邊緣話語”等話語群落,以作為心性結構寄托體的20世紀90年代西安都市風景象征域為樞紐,譯解了“空間移動”與“地方穩(wěn)固”張力關系下個體信仰層域斷裂、集體地域文化向心力失語的精神性符碼;最后,以《病相報告》《高興》為代表的新世紀小說中出現(xiàn)的“生活流話語”“重復話語”等話語群落,以作為“天人合一”理念與日常敘事聯(lián)結紐帶的西安新世紀都市風景象征域為樞紐,譯解了在高速矢量流動的現(xiàn)代時間中空間與地方邊界趨于重組,內部身體從無能動性的“自然”客體層域上升至為主體心性認知建構提供媒介的“風景”層域,及“內風景”作為終極價值本質與日常實踐對象中介的語義構型潛能。
二、西安都市景觀社會中的“欲望”
與“反欲望”話語—以《廢都》為例
在賈平凹第一部以“都市社會中景觀對實體生活及人的身份價值認同的異化”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廢都》中,“景觀”這一“非生命之物的自發(fā)運動”在漂浮無根、凸顯當下而懸擱終極、凸顯感性直觀而懸擱理性反思、凸顯邊緣而懸置中心的“欲望”話語建構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現(xiàn)。
首先,“景觀”表現(xiàn)為視覺表象與社會中“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聯(lián)系的結合,德波將其描述為“以影像為中介的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景觀社會》)。其中,作為中介的“影像”首先以視覺性作為主導,而以“視覺”為切入點攝入具體社會關系中后,則會因為主體價值認同與期待視野的差異產生“看”與“被看”的分離。在《廢都》中的具體表現(xiàn)為,一是傳統(tǒng)的“男尊女卑”“紅粉骷髏”等糟粕思想,在“復雜性境遇倫理”的庇護下借尸還魂,女性成為男性視域中的“被看”方。在畸形的性別權力關系下,女性被物化為不涉及責任倫理的欲望工具,且男性只要遵守顯性正常社會規(guī)范的“最低線”,在其余方面則可以無限充當權力關系的既得者。例如,莊之蝶與唐宛兒、柳月、阿燦保持私情,卻極少受到人際圈內輿論的指責,恰是由于他雖有情婦卻仍未取消妻子牛月清的“正室”地位,而牛月清之所以麻木地默認了丈夫的混亂感情現(xiàn)狀,恰恰是因為她亦成了不平等性別秩序下,依賴于男性經驗、缺乏自我主體認知的物化對象。二是“中心與邊緣”關系的微妙逆轉,造成了集體意識與個體訴求“看”與“被看”位置的變化。宏觀公共意識的獨白“看”方,逐漸發(fā)展為宏觀公共意識與個體碎片式訴求依靠“互動”而互為“看”方,如《廢都》中被其他人作為精神坐標的“西京四大名人”—莊、龔、汪、阮,無不是高度個體化、非體制性、不以主流所推崇的“偉光正”路徑作為價值認同的閑散文士,但他們以此種“名不正言不順”的邊緣化處事風格獲得了豐厚的象征資本。三是“理性反思”的深度性開始讓位于“感性直觀”的淺顯性,“感性”在“后義務時代”的語境中獲得了一定的將“理性”納入統(tǒng)攝范圍內的“看”方地位,并逐漸反噬著“理性”在社會組構中的應有空間。
其次,正如德波將“景觀”作用于具體經驗生活的形式歸納為非強制力量的隱性干預,再次結合前述的“景觀社會”致使“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往”異化為“物與物的關系”的觀點,可以得知“景觀”通過“非生命之物的自發(fā)運動”,即獨立于人的主觀活動之外的諸要素形成的復雜適應系統(tǒng)結構,實現(xiàn)對人的隱性滲透式控制。社會學家帕森斯在結構功能理論中揭示了“社會系統(tǒng)”控制的目標在于“消除差異與對立逐漸趨同”,并將“行動系統(tǒng)”歸納為“文化系統(tǒng)—社會系統(tǒng)—人格系統(tǒng)—行為有機體”的序列分布。故“景觀”以“非生命之物的自發(fā)運動”達成隱性控制必須經歷“文化系統(tǒng)—社會系統(tǒng)—人格系統(tǒng)”三大層次。
三、西安都市景觀社會中的“困境”
與“反困境”話語—以《高興》為例
走過20世紀90年代的“頹廢”與“浮躁”后,進入21世紀的賈平凹再次回到鄉(xiāng)土景觀社會母本。但值得注意的是,鄉(xiāng)土景觀已在資源流失加速的現(xiàn)狀下暫趨萎縮,其“復興”之路任重而道遠。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鄉(xiāng)土景觀社會已由傳統(tǒng)建立在大多數(shù)人農耕生產方式及血緣家族式身份認同上的“自然共同體”,轉化為人力、物力大量流失,失去價值歸屬核心地位,淪為邊緣,漸漸只能以“文化的象征體與人造物”方式存在的“想象共同體”。
首先,城鄉(xiāng)的巨大張力表現(xiàn)在對峙“困境”與命運共同體建構“反困境”中。由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及文化啟蒙受國家規(guī)劃與“意見領袖”議程設置影響較深,而缺乏原生性、自然過渡性質的“市民社會”基礎,即馬克思所提到的隨著近代政治性革命的推動,作為集體性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國家與以私有財產與實際需要為準則的“市民社會”漸趨分離。但由于西方的“市民社會”是建立在工業(yè)及手工業(yè)高度發(fā)展及“有物質而產生的精神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礎之上的,而作為東方國家的中國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深厚的農耕生產傳統(tǒng)及以血緣宗法為核心的“家族式”社會關系,如費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提到的以“己”為中心的差序格局,可見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私域”與“公域”并沒有分離傾向,甚至是因“家族紐帶”而粘連的,故不能稱之為處于“公”與“私”之間的非政治領域性的“市民社會”。由此城鄉(xiāng)“對峙”困境便油然而生,主要表現(xiàn)為鄉(xiāng)村景觀不僅在空間上的“邊界”日益退化,往往伴隨著較為單一的生活生產方式,與都市形態(tài)所攜帶的以多元化、高效率、高轉化率為特征的生活生產方式相對比,活力缺乏。但從某個層面來說,鄉(xiāng)村景觀歷史性層累的文化認同歸屬積淀之所以被快速剝蝕,除卻“都市”的話語權日益增強外,更多的是其內部本身分裂與矛盾的逐漸顯性化,即鄉(xiāng)村景觀不可能在時代語境中再次成為主流,其必須與都市景觀尋找共同訴求與血肉聯(lián)系,建立命運共同體,方能擺脫當下“困境”,獲得未來“救贖”。
其次,城鄉(xiāng)的巨大張力表現(xiàn)在以“新都市人”身份最終確立為目的的身份認同“錯位”困境與“修復”反困境中。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鄉(xiāng)土景觀社會已由“自然共同體”漸漸轉化為“想象共同體”。故在都市景觀為主流的社會整體語境下,鄉(xiāng)土景觀的功能體現(xiàn)為尋根性質的文化記憶溯源。在“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的相關理論中,阿萊達·阿斯曼將“文明的剩余物質”的作用視為“處于功能記憶和存儲記憶之間的潛伏記憶”“一代又一代地堅守在在場和缺席之間”,堅信“文明的剩余物質”通過結合前景的重新發(fā)掘意義的途徑后會生成“代表一些不可見的、不可把握的東西,比如過去或一個人的身份認同”(《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并將“記憶”視為溝通代際,促進“集體遺忘”由斷裂走向新生的媒介。故“記憶”的最終指向為在當下維度下回溯“過去”作用于文化系統(tǒng)中“身份認同”的建構。同時,阿斯曼著重強調了“地點”對于“文化回憶空間重構”的作用,即“體現(xiàn)了一種持久的延續(xù)……比起個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為具體形態(tài)的時代的文化的短暫回憶來說都更加長久”(《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
綜上所述,在賈平凹小說與西安都市景觀社會間的話語建構(以連接客體“特定社會語境”與主體“人際溝通交往”,涵蓋“說話人、受話人、文本、溝通、語境”,映射復雜生存因素坐標為實現(xiàn)路徑)分析中,以“欲望”與“反欲望”話語、“困境”與“反困境”話語為例,可以總結出以下兩點啟示:一是由于西安都市風景(主要指人文景觀)主要受人為實踐活動所推動,是主觀改造與原生性客觀存在的結合,是符號與實在的統(tǒng)一,故應對“對象化存在物”背后的主體本質力量予以關注;二是由于西安都市景觀社會缺乏原生市民社會基礎與既成經驗,而是建立于農耕社會這一以循環(huán)時間觀、差序格局、家族血緣意識為特征的文化母本之上,故西安都市景觀社會更像一個“過去”“當下”“未來”三者既有裂隙面又有共同面的試驗期。且“當下”的踐行與“未來”的預期不可懸置“鄉(xiāng)土景觀社會”母本及其在某種意義上的象征符號功能,其在社會發(fā)展實踐層面的表現(xiàn)便是欲望話語在主流公共空間中從缺席走向在場、“進城”群體的身份認同困境與城鄉(xiāng)命運共同體價值救贖亟待建構等。故需要將“西安都市景觀社會”與“鄉(xiāng)土景觀社會”母本進行對照性研究,以避免“都市景觀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的“無根性”“邊緣化”“同質化”問題,為“當下”的踐行與“未來”的預期提供強有力的隱性母本資源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