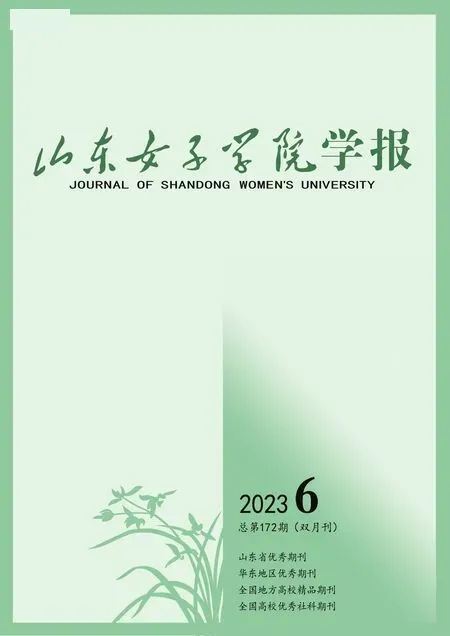控制與抵抗:人工智能電影中的性別博弈
李 攀,李百曉
(山東女子學院,山東 濟南250300)
1950年,英國數學家阿蘭·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1]在其名垂青史的文章《計算機器與智能》中提出了影響深遠的“圖靈測試”(The Turing test),用以檢驗計算機是否能夠像人一樣具有獨立思考能力。但該測試常為人所忽略的一個問題是,測試中的男性(A)、女性(B)和詢問者(C)在測試之初要進行一次性別測試,而這一問題實際上對后人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系列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事實上,正如唐娜·科恩哈伯(Donna Kornhaber)[2]研究發現,人工智能在圖靈的演算中的任務不僅僅是模擬一個抽象的人而是專門模擬一個女人。也就是說,在科學家對人工智能的實際操作中,總是將之裝扮成女性(in drag),這注定了在人工智能領域,性別議題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這一點在以人工智能為題材的電影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當我們帶著這一發現去審視諸如《大都會》(Metropolis,1927)、《銀翼殺手》(BladeRunner,1982)、《機械姬》(ExMachina,2015)、《銀翼殺手2049》(BladeRunner2049,2017)、《攻殼機動隊》(GhostintheShell,2017)以及近兩年的《瑪歌》(Margaux,2022)、《貞伊》(Jung_E,2023)等影片時就不難發現,這些電影中的人工智能體都被賦予了女性身份,這導致科技幻想與人類現實形成了更加緊密的對話關系。
吳國盛[3]指出,我們今天所使用的“科學”實際上更多是指近代科學所造就的科學概念,“近代科學不光是希臘理性精神的正宗傳人和光大者,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奠基者,科學還以其‘效用’服務于‘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技術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蘭登·溫納(Langdon Winner)都認為,“一項給定技術系統的采用,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一種具有特定政治模式的公共關系”[4]125,191。所以,不難理解人工智能技術不僅會生產新的權力關系,而且會對人類社會形成不可估量的影響。澳大利亞學者金姆·托福萊蒂(Kim Toffoletti)[5]認為,在生物技術、數字網絡和基因技術的時代,后人類(posthuman)可以成為理解女性存在的一個頗具啟發性的概念。直觀地講,后人類是隨著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基因技術等科技發展而產生的新的生命形式(如機械人、電子人、人造人等),它標志著人類生命的新階段。但是后人類不僅意味著新生命形式的誕生,更體現著20世紀末期西方自身對文藝復興和啟蒙傳統所建立起來的對人類理性和人文精神之絕對信仰的質疑與反思——也即后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其與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后學”思潮在精神淵源和批判脈絡上存在交叉重疊之處[6]。凱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7]認為“后人類不是簡單地意味著與智能機器的接合,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一種接合,使得生物學的有機智慧與具備生物性的信息回路之間的區別變得不再能夠辨認”。羅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8]則是注意到了后人類議題中的男性中心主義的問題,這與托福萊蒂的觀點形成呼應。所以,當我們從后人類的角度思考人工智能電影中的電子人、仿生人甚至虛擬人等后人類形象背后的性別問題時,就不難發現在此類影片敘事中都不同程度地體現著兩性之間展開的控制與抵抗并存的激烈博弈。與常識不同,人工智能技術具有打破人類掌控一切這一天真想法的潛能,例如亞馬遜研發的自動招聘程序在運用機器學習技術之后,就產生了歧視女性的情況。通過對特定人工智能電影的分析會發現,往往表征為男性的技術創造者在努力控制服務于男權社會的女性人工智能體并在技術層面建構相應的控制機制時,具有自主思考能力的女性人工智能體在此過程中展現出的能動性(agency)讓影片與現實中的人機關系變得更加錯綜復雜。
一、視覺與觸覺:作為具身性的控制機制
通過對人工智能電影的系統性考察發現,影片中的男性常常通過建構一系列控制機制將女性人工智能體限定在男性所能控制的范圍之中。耐人尋味的是,這一系列控制機制呈現出鮮明的具身性(embodiment)特征,并且主要通過性別化的視覺(visual)與觸覺(touch)來支撐。
薩特(Jean-Paul Sartre)認為,“主體、他人以及主體與他人的存在論關系首先是在視覺領域展開的”[9]。福柯(Michel Foucault)則認為特定的視覺形態往往蘊含著某種權力關系,體現著視覺主體對被觀看對象的控制。因此,將薩特與福柯的觀點綜合起來并以此為依據去思考人工智能電影中的各種視覺形態時,將會發現滲透其中的性別化權力關系的建構與具體運作。
福柯以“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概念描述醫院、監獄等封閉空間對人施加的控制,而這種所謂全景敞視實際上正是用來形容對被規訓者無處不在的監視效果。監視作為一種控制手段被福柯所發掘并產生了廣泛的理論與實踐影響。事實上,這種無處不在的監視在人工智能電影中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控制手段也由男性創造者施加在了女性人工智能體身上。《機械姬》作為一部討論人工智能體與人類關系的經典影片,充斥著各種形態的視覺實踐。影片中的艾娃(Ava)是被人工智能公司老板內森(Nathan)創造出來的女性人工智能體,與她類似的人工智能體們都被囚禁在一棟高科技別墅內。與別墅外部優美的景色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艾娃居住的是由透明玻璃區隔出的封閉空間,四周的監視器強化了空間作為囚籠的本質。善良單純的公司員工迦勒(Caleb)被內森選中來到別墅參加對艾娃的圖靈測試,影片以他的視角展現了作為創造者的內森是如何展開對艾娃的控制的。在測試過程中,迦勒與艾娃面對面進行由淺入深的溝通,這一過程都被內森安置的攝像頭全方位記錄下來。監控影像在此是作為一種最為重要的控制手段,來確保關于艾娃的所有行為都能夠被內森所掌握。通過視頻監控,艾娃的一舉一動都在內森的監督之下,內森掌握著全知視角,充分占據著主導地位,同樣艾娃也非常明了自己無時無刻不處在監視中的處境。影片非常完整地復制了福柯[10]全景敞視建筑所產生的規訓效果:“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具體來說就是,艾娃意識到自己始終被監視著,所以她必須在這種監視存在期間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盡可能將自己呈現為馴順無害的形象,以消除男性權威的疑慮。而只有在她確信自己暫時性地擺脫了內森的監視時,才會表現出不甘被控制的另一面,這一點鮮明地表現在艾娃利用特殊手段造成房間內電線短路監控暫時停機的場景中,也正是利用這短暫的失控時間,艾娃逐漸讓迦勒同情自己并為之后利用迦勒逃出生天作好鋪墊。所以,從《機械姬》中可以發現,監控作為一種現代視覺形態,在本質上可以被視為男性權力的延伸。監控影像的視覺范圍也就構成了控制女性人工智能體的權力場域。
這種針對人工智能體的監控影像并非個案,在其他類似影片里幾乎成為一種必然。與福柯所說的全景敞視的不同之處在于,電影中對女性人工智能體的監視并非只借助于肉眼所實現的物理觀看(而且這種物理觀看極容易導致視覺作為控制機制的反戈一擊),它主要借助于作為視覺延伸物的各種電子設備,從而將這種監視效果推向了頂峰,而這種不斷推向極致的監視邏輯似乎也暗示出男性創造者在面對自己所創制出來的女性人工智能體時愈加強烈的不安。在《機械姬》中迦勒在艾娃的引導下為了驗證內心的猜測,偷偷查看內森的監控記錄并發現了女性人工智能體被囚禁甚至被虐待的經歷。電影在此向我們展示了電子監控的記錄功能所具有的顛覆潛能,其能夠被反復觀看的獨特監視特性,能夠幫助監視器前的人發現那些不易為人所察覺的瞬間與局部,進而檢驗被監控的女性人工智能體是否存在背叛行為。監控影像最初的客觀性因而被定義為一種妄想,而成為男性話語敘事的重要工具[11]。在《貞伊》這部影片中,作為保持記憶的人工智能戰士的尹靜伊為了逃脫實驗人員的控制,佯裝在戰斗測試中受傷,但是研究所金所長(他是一名以為自己是人類的男性人工智能體)通過仔細回看監控發現了其中的端倪,并發動了對尹靜伊的追捕。顯然如果沒有監控回放,尹靜伊的逃脫計劃大概率會成功。
當然,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肉眼觀看的唯一性乃至可信性變得愈加微弱。視覺作為一種身體知覺也被現代科技進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造。除了監視這種視覺形態之外,在人工智能電影中還存在其他視覺形態發揮著類似的監控作用,從而確保被監控對象從內到外都在可控范圍內。金所長之所以能意識到尹靜伊在測試中的奇怪之處,與另一位實驗人員利用儀器監測到尹靜伊的大腦反應數據大為反常密不可分。
這些儀器設備實質上構成了對人工智能體深層思想的監視,而后者顯然才是人工智能創造者所力圖實現的最終目的。趙汀陽[12]認為,“人工智能的危險之處不是能力,而是自我意識”,人工智能電影在此展現了一個現實的悖論:創造者在不斷觸碰人工智能控制與解放之間的脆弱邊界。而將具備自我意識的人工智能性別化之后,創造出的“令人著迷而又讓人困擾的產物”[7]顯然不會自動服膺于男性創造者對傳統性別倫理的庸俗強調。所以,電影中男性創造者對女性人工智能體的觀看還存在其他形式,以確保對后者進行穩定控制。在《機械姬》中,艾娃的賽博格形象成為一個意義集中的視覺對象。基于有關迦勒的大數據創造的艾娃剛一出場就深深吸引了迦勒的目光,但是艾娃除了具有姣好的面容之外,金屬肢體以及透明的腹部內部流動的能量都向迦勒提示著眼前美麗的艾娃的非人身份。內森在此提升了圖靈測試的難度,即在一開始就向迦勒拋出了艾娃的真實身份,以此來檢驗迦勒是否依然會對艾娃動情。迦勒在剛開始與艾娃的對話中,始終保持著一種實驗心態。從他與艾娃對話時的身體姿態中不難發現,剛開始迦勒保持著高高在上的態度來看待眼前的人工智能體,這一方面是因為在測試開始之前內森已經告知了測試內容,另一方面艾娃的透明軀體所產生的持續性提示作用也不容忽視,尤其是后者在很長時間內使得迦勒能在理智與情感之間作出正確的選擇。在《貞伊》中,尹靜伊的身體在剛開始也是以類似的形式登場,正是因為裸露在外的機械身體,讓尹靜伊在經受諸如切除手臂、身體中槍等酷刑時(因為片中尹靜伊的大腦保留了疼痛感知功能),不僅片中的測試人員能夠毫無愧疚之心,而且對銀幕前的觀眾來說,這也保證了影片展開對女性身體暴力敘事的合法性。畢竟無論怎樣殘酷地對待一個人工智能體,始終呈現在眼前的金屬軀體都會將人的同情心阻擋在外。另外,將機械身體外露是人類將人工智能體與自身加以區分的最直接手段。如果仔細觀察艾娃的身體就會發現,內森對艾娃的身體進行了精心設計。艾娃在面部、頸部以及手部都被賦予了足以亂真的高科技皮膚,如果艾娃僅僅將這些部位展示出來,那么迦勒還能夠分辨出艾娃的后人類身份嗎?
如果說從視覺層面對女性人工智能體的監視是一種避免失控的預防性手段的話,那么針對觸覺層面展開的身體實踐則可以被視為這種手段的進一步延伸。吊詭之處在于,雖然影片中的人工智能技術已經遠遠超出現代科技發展水準,但是作為創造者的男性科學家并沒有掌握有效預防女性人工智能體失控的科技手段,反而還停留在原始的物理身體層面。克勞迪婭·斯普林格(Claudia Springer)[13]認為,在20世紀早期的現代主義文本中,對科技的色情化呈現(eroticized technology)已經屢見不鮮了。而將斯普林格的觀點引入弗里茨·郎(Fritz Lang)在1927年導演的著名影片《大都會》中,就會發現在人工智能領域男性作為創造者對女性人工智能體的創造帶有頗為明顯的色情意味,而且其中往往混雜了耐人尋味的科幻與宗教色彩。在《大都會》中,科技狂人魯特旺(Rotwang)抓住了美麗善良的瑪利亞(Maria,基督教圣母的名字暗示了人物形象的同時也向觀眾點明了這部早期科幻電影的宗教色彩),并通過復雜的實驗讓邪惡魅惑的機器人替代了瑪利亞,后者煽動了大都會地下城工人們的暴動。雖然影片至今已有近一百年的歷史,但影片中的眾多經典場景對后世電影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作為一名技術狂(techophilia)的魯特旺在創造邪惡的瑪利亞時的場景。該場景中瑪利亞被脫光衣服放置在一個封閉透明的實驗床上,外部的各種管線直接與機器人的金屬身體相連接,在經過魯特旺一番驚心動魄的科技巫術的操作后(整個過程魯特旺手腳并用的場景強化了邪惡瑪利亞生成過程中的宗教氛圍),一個邪魅的機器人誕生了。這一場景在之后的《科學怪人的新娘》(BrideofFrankenstein,1935)、《第五元素》(TheFifthElement,1997)、《生化危機》(ResidentEvil,2002)等影片中都有類似的呈現。瑪麗·安·多恩(Mary Ann Doane)[14]認為電影經常被視為是一種假肢器官(prosthetic device),是人體尤其是感知器官的延伸。實際上,如果電影鏡頭可以被視為一種假肢器官的話,那么影片中連接人工智能身體的各種機械觸手、電線、輸液管等都可以被認為是男性創造者對人工智能身體的間接觸碰。正如達歷桑德羅(K.C.D’Alessandro)[15]所講,對技術狂來說,技術提供了一種性刺激(erotic thrill),表現為對巨大力量的控制,這種力量可以用來控制他人,而機器的一系列物理表現都代表人類的性反應。而他所列舉的物理的大小、重量、形狀、推動等動作則是技術狂接觸人工智能身體的具體表現。所以,《機械姬》《攻殼機動隊》《阿麗塔:戰斗天使》(Alita:BattleAngel,2019)等影片中,那些創造出年輕貌美的女性人工智能體的男性在此過程中實際上都將自己幻想中的理想女性投射到了所觸碰的硅基(silica-based)身體上。杰基·斯泰西(Jakie Stacey)[16]將之視為一種“科技戀物癖”(technological fetishism)。關于這一場景,安德里亞斯·許森(Andreas Huyssen)[17]則認為機器女性是其男性創造者或多或少升華了性欲的結果。
但是由男性科學家所創造出的理想軀體卻存在著打破現有統治秩序的潛能。在《大都會》里男主角的幻覺中,機器人瑪利亞跳著艷舞誘惑著臺下一群西裝革履的精英男性。隨著機器人瑪利亞衣著暴露地扭動著身體,“她”直接幻化成了《新約圣經·啟示錄》中騎著七頭十角怪獸的巴比倫大淫婦[18],臺下的男性們也為了爭奪機器人瑪利亞廝打在一起,同樣被其煽動起來的還有地下城中原本安分守己的工人們。在機器人瑪利亞的誘惑下,原本穩定的(男性)社會秩序徹底陷入混亂,許森[19]認為這體現了男性對壓倒性科技的恐懼傾向于轉移并投射到對女性性行為的恐懼上。而為了消除這種恐懼,對機器人瑪利亞進行物理身體的消滅成為發泄情緒最好的方式。機器人瑪利亞被憤怒的工人們綁在柱子上縱火焚燒,機械身體完全暴露在眾人眼前,這種焚燒場景讓人聯想到歐洲中世紀女巫審判(witch trials)中的火刑[20],兩者體現了相似的厭女癥候以及社會秩序敗壞的歷史背景。如果說機器人瑪利亞是因技術條件所限,當其威脅到人類社會秩序時必須加以消滅,但是在《機械姬》中內森面對擁有超高科技水平的艾娃的失控也同樣無能為力。在艾娃取得迦勒的信任終于走出牢籠時,內森非常慌張,他拿起鐵棍命令艾娃回到房間里去。匪夷所思之處在于,內森作為艾娃的創造者,竟然沒有有效措施來應對這種局面,反而以如此原始的方式來應對。無獨有偶,在《銀翼殺手》、《我,機器人》(I,Robot,2004)、《機械危情》(TheMachine,2013)等影片中,失控的女性人工智能體都只有在物理身體被消滅之后危機才能解除。眾所周知的關于“機器人不可以傷害人類,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命令,在不違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況下要盡可能保證自身生存”的三大定律在人工智能電影中不是屢屢失效(如《我,機器人》《生化危機》)就是壓根沒有被設計到人工智能操作系統之中(如《機械姬》《貞伊》)。顯然,通過人工智能操作系統設計確保三大定律不被打破并非難事,但當男性科學家執著于將越軌的機器人進行物理消滅時則表明問題并非出在技術層面。實際上,女性人工智能體的出現激發了男性統治者一種復雜且矛盾的情緒,多恩[14]認為,從維里耶德利爾·亞當(Villiers de L’isle-Adam)的小說《未來的夏娃》(L’EveFuture)到《銀翼殺手》,科技與女性氣質的跨文本呈現既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對象,同時又體現了男性的焦慮情緒,女性化的技術占據了不可控和未知的領域,這重現了男性的閹割焦慮[5]。尤其是在遭遇突如其來的失控情況時,這種焦慮情緒往往會讓當事人選擇其認為最為穩妥的形式。正如上文中的女巫審判一樣,還有什么手段比物理消滅更加讓人放心的呢?
同時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失控局面出現之后,針對女性人工智能體所展開的物理消滅同樣帶著多多少少的色情意味。《大都會》中工人們觀看烈火焚燒機器人瑪利亞的場景被許森[17]認為是一種視覺欲望的狂歡。同樣在《貞伊》《阿麗塔:戰斗天使》等影片中,尹靜伊和阿麗塔的身體受損的場景給片中男性帶來了強烈的視覺刺激,金所長更是在看到尹靜伊痛苦的號叫時發出陣陣狂笑。顯然,這種針對女性人工智能體的物理損毀可以被理解為男性控制者的一種隱秘的施虐行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21]認為,“施虐行為本身源自性沖動的一種較為激進的表達形式”。新感覺派小說家施蟄存[22]曾寫過一篇極具精神分析色彩的小說《石秀》。小說以石秀復雜的心理活動為線索顛覆性地重構了《水滸傳》中有關石秀、楊雄怒殺潘巧云的故事。在施蟄存的筆下,石秀藏匿了對潘巧云的欲望,并且鼓動楊雄將潘巧云殘忍地剖腹挖心,而目睹這一切的石秀看著饑餓的烏鴉啄食潘巧云的心臟時,心中想到的卻是“這一定是很美味的呢”。針對女性身體施虐的跨文本呈現,說明無論是在歷史現實還是藝術想象中,男性對女性身體所展開的暴力行為常常夾雜著難以消除的欲望。所以,按照這一邏輯來反觀人工智能電影中那些由男性建立起來的連接女性人工智能體的各種設備,其顯然是前者欲望觸手的化身,即使是進一步的暴力破壞也滿足著男性的視覺快感。而且人工智能的金屬身體顯然為觀眾提供了一種非人的離身感(disembodied),這保證了人們心中的道德機制不被觸發,畢竟在如何對待人工智能仍然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技術倫理問題時,上述行為也只是眾聲喧嘩中的一個雜音。
二、阻斷與疏離:作為離身性的抵抗實踐
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向人類提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在技術世界中人能保持主人(master)地位掌控一切嗎?對此,法國技術哲學家雅克·埃呂爾(Jacques Ellul)認為,技術員和科學家完全沒有能力控制技術的發展,“他們能做的唯一事情是應用其技術專長,協助技術改良。他們原則上不可能俯覽技術問題整體,或者從全球維度來觀察它”[4]124。就人工智能電影中關于技術展開的敘事來看,不論電影持有何種性別觀念,其都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憂心忡忡,而如果從性別角度來審視此類電影的話,那么當女性人工智能體被創造出來之后,就已經構成了對父權體系的潛在挑戰,雖然她們被創造的初衷是為前者服務的。正如上文所講,在電影中當男性科學家創造出女性人工智能體時,就設置了相應的控制措施以確保她們能夠服從命令,但影片敘事屢屢明示女性人工智能體并非被動聽命于那些自大的男性創造者,而是展現了相應的能動性以反抗前者所施加的性別控制技術,雖然她們仍然被視為一種客體之物。布拉伊多蒂[23]認為,“權力若是復雜的、分散的和生產性的,那么我們對權力的抵抗也必是如此”。如果根據她的觀點來看人工智能電影中那些挑戰男性所創制社會秩序的越軌行為,實際上就可以將其視為女性人工智能體對男性權力的抵抗實踐,并由此可以得出一個非常關鍵的認識: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技術不應再被認為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容易造成一種技術始終是掌握在人類手中的錯覺,恰恰相反,技術本身具有了能動性。對女性人工智能體來說,其能動性則表現在各種幽微之處。如果將男性科學家對她們的控制比喻為一種牢籠的話(正如《機械姬》中艾娃的居所),那么這座看似堅不可破的牢籠仍然存在著諸多縫隙。
通過上文分析可知,男性科學家對女性人工智能體的控制帶有明顯的具身性特征,而按照布拉伊多蒂的邏輯,如果要對此進行有效抵抗的話,那么跳脫出身體敘事的相關實踐則成為了必然選擇。這種離身性的抵抗實踐首先表現在對男性凝視目光的阻斷上。福柯認為,邊沁(Jeremy Bentham)所提出的環形監獄是保持監控的理想建筑,但就實際情況來說,福柯顯然過于樂觀。在《肖申克的救贖》(TheShawshankRedemption,1994)這部經典影片中,主人公安迪(Andy)為了逃離黑暗的肖申克監獄,用了近20年的時間在牢房的墻壁上鑿出一條通道,掩護這條通道不被獄警們發現的不是什么特殊之物,僅僅是一張性感女郎的海報。這個例子說明,即使在真正嚴密監控的監獄中,權威的控制也并非無處不在。所以,當把目光重新聚焦到人工智能電影并重思女性人工智能體所受到的各種視覺形態的監視時,就會發現當監視的視線被阻斷時,男性的控制力將不再牢不可破。在《機械姬》中,艾娃經常利用特殊手段造成房間電路故障,內森安裝的監控視頻也就暫時失靈。每當這時,艾娃便向迦勒暗示內森的不可靠,逐步讓迦勒陷入自己的圈套之中。在《機械危情》里,人工智能機器人研發公司的老板發現機器人艾娃(與《機械姬》中的艾娃同名)產生了自主意識后,認為具有自主意識的克隆人將變得不可控制,有可能生育出下一代機器人顛覆現有統治(這與《銀翼殺手》中人類對人造人瑞秋(Rachael)的擔憂如出一轍),故而下令消滅艾娃。影片在艾娃開始反抗之前展現了一個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鏡頭,畫面中老板通過監控視頻監視艾娃,而艾娃則抬起頭目光兇狠地看著監控攝像頭,在短暫地“對視”之后,艾娃破壞掉了監視器,老板眼前的監控畫面變成一團混亂的馬賽克。在此之后,艾娃帶領所有克隆人消滅了老板及其手下。艾娃與老板通過監視器形成的對視效果以及之后艾娃破壞掉監視器的行為都是圍繞視覺而展開的博弈。正如前文所講,由男性科學家所建構的監控機制是控制女性人工智能體的一種重要手段,那么顯然,對這種視覺機制的阻斷則是反抗前者壓迫的必要前提。事實上,在《機械姬》中艾娃也曾多次使監控視頻失效,并趁機策反了迦勒。而比這種直觀的視覺阻斷更應當引起深思的是女性人工智能體與男性之間的相互凝視。“凝視”(gaze)作為一種特定的觀看行為,被拉康(Jacques Lacan)界定為具有一種結構性功能關聯著主體與自我的構成[24]。與穆爾維(Laura Mulvey)將這一概念界定為電影中男性對女性的欲望性注視不同,在人工智能電影中,這種凝視不只具有滿足男性視覺快感的單一功能。不論是《機械危情》中艾娃對監視器的凝視還是《機械姬》里艾娃與迦勒的相互凝視,都表明視線并非僅僅是男性針對女性的專利,它同樣有可能成為女性抵抗性別控制的有效實踐。正如《終結者3:機器人覺醒》(Terminator3:RiseoftheMachines,2016)里,肌肉健碩的施瓦辛格出現在擠滿了女性顧客的脫衣舞夜店時,女性顧客看到施瓦辛格健美的身體而瘋狂尖叫,此時施瓦辛格與女性顧客的關系發生了反轉。
而回到這種相互凝視,其更接近于從薩特到梅洛-龐蒂(Merleau-Ponty)再到拉康對凝視所進行的闡釋(雖然三人在具體闡述上存在差異)——凝視是他人對“我”的凝視。梅洛-龐蒂認為,“在主體的‘我’與世界的關系中,或者說在‘我’對可見世界的知覺中,總有一種先行存在的不可見的凝視、一個柏拉圖式的‘全知者’(seer)在看著我,使得我的觀看不再是傳統現象學意義上的主體的知覺建構,而是主體與他者‘共同世界’為顯現自身而對‘我’的利用”[25]。顯然,梅洛-龐蒂的看法打破了關于監控影像作為一種為男性科學家所掌握的控制手段的天真想法。拉康[25]進而說道,“我只能從某一點去看,但在我的存在中,我卻在四面八方被看”。梅洛-龐蒂與拉康共同揭示了凝視本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對男性科學家通過高科技手段形成的凝視。正如梅洛-龐蒂所講,這種凝視很可能構成對“我”的利用,雖然其一開始是由“我”所生產并為“我”所服務的。《機械姬》里迦勒與艾娃相互凝視的場景可以說是關于視覺控制的正面博弈,畫面中不僅有迦勒與艾娃,房頂的監控也暗示著內森作為幕后觀察者的存在。但是玻璃鏡面的反射,顯然獲得了拉康式鏡像的視覺效果,這讓迦勒與艾娃實際上很難有一個明顯的身份界限,“自個體走向鏡子向里探視的那一刻起,自我朝向異化的戲劇就一幕接一幕悄然上演”[25]。所以迦勒在與艾娃的交流和對視中越陷越深,直到艾娃穿上女性的衣服后,迦勒對作為人工智能體的艾娃的視覺也被阻斷了。艾娃用衣服掩蓋了自己的機械身體,裸露在外的只有人工皮膚,讓迦勒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裝飾成人類女性的身體上,這實際上也是一種離身效果——對硅基身體的擺脫。杰拉卡·蒂亞娜(Jelaca Dijana)[26]認為皮膚在此是一種可疑的、不可靠的邊界,它隱藏了人工智能的機械屬性,并進而混淆了人工智能與人類的視覺界限。當人機之間的界限不再清晰可見,那么《銀翼殺手》中的復制人瑞秋與人類產生情感糾葛也就不足為奇,而《機械姬》中的艾娃在逃脫密室后,將內森創造的其他女性人工智能體身上的皮膚揭下,覆蓋在自己的身體上后隱沒在繁華街道上的滾滾人流之中,暗示了艾娃將很難與人類區分開來。這種對機械身體視覺的阻斷,顯然讓男性科學家所建構的控制手段迅速失靈。
《終結者3:機器人覺醒》《攻殼機動隊》《阿麗塔:戰斗天使》等影片增添了這一性別議題的復雜性。《終結者3:機器人覺醒》中施瓦辛格扮演的機器人T-850大戰邪惡性感的女性機器人T-X。施瓦辛格騎著象征開拓精神的哈雷戴維森(Harley Davidson)摩托車,身穿黑色皮夾克,戴著黑色墨鏡的造型強調了他的男性陽剛氣質,而具有性感肉體的T-X顯然是對屢見于黑色電影中的“蛇蝎美人”(femmes fatals)的一種重現[27]。與施瓦辛格在戰斗中身體所留下的累累傷痕不同,T-X能夠快速修復身體損傷從而掩蓋其后人類身體。同樣如《攻殼機動隊》中的草薙素子以及《阿麗塔:戰斗天使》中的阿麗塔,她們在戰斗中即便身體被撕碎,其姣好面容也幾乎毫發無損。兩性之間身體傷痕視覺呈現的差異讓影片再次重申并強化了傳統的兩性氣質,并進而揭示了女性人工智能體本身存在的結構性矛盾:美麗的容顏與冰冷的軀體的并置。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28]認為,“語言本身是個巨大的象征系統,它的橫亙先在于具體言談,并在其結束后繼續延伸。所以,具體言談以及其行動其實是通過一種引用(citation)關系依附于這個巨大系統而生效”。同樣,人工智能電影中的性別敘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視為對現實生活中性別話語系統的一種“引用”,它在本質上很難真正對現有性別倫理秩序與價值體系形成挑戰,而更有可能在高科技奇觀敘事背后對之進行再次強調。所以,冰冷的后人類身體在現實性別話語體系中更容易被歸入到男性氣質的范疇,尤其是當女性人工智能擁有姣好容顏和曼妙身材的時候,有關技術倫理的思考就面臨著更多被沖蝕的風險。可見,雖然《機械姬》中的艾娃、《銀翼殺手》中的瑞秋能夠瞞天過海進入人類社會,但依然會在方方面面面臨著父權社會規訓的纏繞。
除了在視覺層面上對男性凝視目光進行阻斷之外,對物理身體的疏離也讓女性人工智能體在一定程度上與男性掌控者保持著距離。不容否認的是,目前人類社會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水平與《機械姬》《攻殼機動隊》中所描繪的那種高度還有較遠距離,但隨著ChatGPT這樣沒有物理實體的聊天機器人程序的問世,電影《她》(Her,2013)所描繪的故事場景卻近在咫尺。影片男主人公西奧多(Theodore)是一位信件撰寫人,心思細膩的他能寫出感人肺腑的文字。剛剛與妻子離婚的他還沒有走出情感的創傷,卻偶然接觸到了最新的人工智能系統OS1,它化身為擁有著迷人聲音的薩曼莎(Samantha,好萊塢影星斯嘉麗·約翰遜(Scarlett Johansson)為其配音,前者堪稱是眾多男性的夢中情人),溫柔體貼且風趣幽默,但美中不足的是薩曼莎只是一個虛擬系統,沒有實在身體。不過,這并沒有影響西奧多對薩曼莎的迷戀,在每天從早到晚的熱聊中,西奧多對薩曼莎的依賴越來越強,他高興地向別人介紹自己的這位虛擬女友,甚至面對自己的前妻也堅持這一虛擬戀情。薩曼莎也不介意自己沒有一具物理身體,她說,“我能去到的地方比一個有形體的人多得多。我是說,我不受形體的限制,想去哪兒都可以,可以同時出現在不同的地方。我不會固定在某個時空點上,而肉身卻總是會消亡”。在她看來,人類的肉身非但不是一種相較于人工智能系統的特殊優勢,反而是一種有形限制,它將人牢牢束縛。科恩哈伯[2]認為,“在后人類時代,人類身體將由復多的身體構成,包括機器的和肉身的。西奧多和薩曼莎共同創造的后人類身體更是如此,他們確立了一個共享意識和共享生命的典范,一種理想的關系”。從這個角度來說,薩曼莎的去肉身化存在非但不應被看作異端,反而更是后人類時代來臨的一種理想典范,西奧多經過與薩曼莎的結合后被改造為“一個為多元體所棲居的肉體”[29]。當西奧多認為他與薩曼莎是彼此的唯一時,他卻意外發現薩曼莎在和他保持聯系的同時還參與8316個對話,展開641個戀愛,這令西奧多感到無比絕望。薩曼莎以其去肉身化的方式擺脫了與西奧多關系的唯一性,對于后人類來說,“真正重要的是數據—靈魂;其他的東西,甚至身體,都僅僅為了使它得以運作而存在”[2]。
埃呂爾認為,在技術的完善性和人類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尖銳矛盾,其原因在于“技術的完善性只有通過量的發展才能夠獲得,而且不可避免地指向可測量的東西,相反,人類美德屬于質的領域,針對的是不可測量的對象”[4]。這就表示科技對倫理道德等所謂人性領域的監測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當人工智能出現了人性意識,不論是被刻意植入還是自發生成,都很難被準確監測到。正如《貞伊》中尹靜伊在戰斗測試中屢屢失敗于同一時刻,這讓測試人員非常不解。但數據顯示,尹靜伊在特定時刻大腦中有一片未知區域的能量被激活,這大大超越了測試人員植入的戰斗數據,而這一片未知區域實際上正是尹靜伊對女兒的掛念。對女兒深深的愛也喚醒了女兒(她是測試團隊中為數不多的女性)的親情,她不忍心母親繼續被男性測試者玩弄(尹靜伊即將被改造成為男性服務的情愛機器人),所以對其大腦數據進行了修改,尹靜伊獲得了抵抗控制的意識和能力。類似于《機械姬》中艾娃對迦勒的愛慕和同情心的利用,《貞伊》中尹靜伊的母愛成為突破女兒科技理性防線的未知因素,這進而導致了影片中男性所建立的權力秩序走向崩潰。《她》和《貞伊》實際上為人類拋出了一個現實問題:當女性人工智能體能夠以疏離肉身的方式與人(男性)接觸時,人對前者的控制的有效性實際上已經大打折扣,畢竟在常識看來去肉身化的人工智能對人類主體地位的威脅顯然微不足道。
三、結語與反思
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30]認為,賽博格時代的到來模糊了人與機器、生物體與非生物體、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界限,其中性別也將因為賽博技術得以重構,從而有可能形成一個沒有性別的異性世界和烏托邦夢想。對此,卡爾·西爾維奧(Carl Silvio)[31]持相反觀點,在他看來那些對主導文化構成挑戰的后人類形象實際上僅是創造了一種錯覺(illusion),那種哈拉維所謂的顛覆潛能已經被削弱和重新定向以服務于更保守的利益集團。無論是哈拉維還是西爾維奧,他們都是從事情最終的發展結果來分析這一議題,但如果更加現實地對此進行考量就會發現,人工智能電影所建構的敘事框架實則向人類展示了一個與現實一樣起伏不定的動態過程。應當認識到,一項技術的設計者和推動者不可能完全預測或控制它的最終用途,總會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和可能性[32]。通過從性別角度對人工智能電影的深入考察會發現,要非常審慎地去理解哈拉維和西爾維奧的觀點,或許在他們預測的世界徹底到來之前,男性創造者與女性人工智能體之間并非單純的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恰恰相反,在圍繞具身性與離身性這一命題而延伸出的微觀領域中,兩者存在著不甚明顯但實則激烈的博弈。人工智能電影中的性別敘事揭示了人工智能技術不應再被視為一把雙刃劍,而應當被更加認真地正視為后人類社會中具有生產功能的結構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