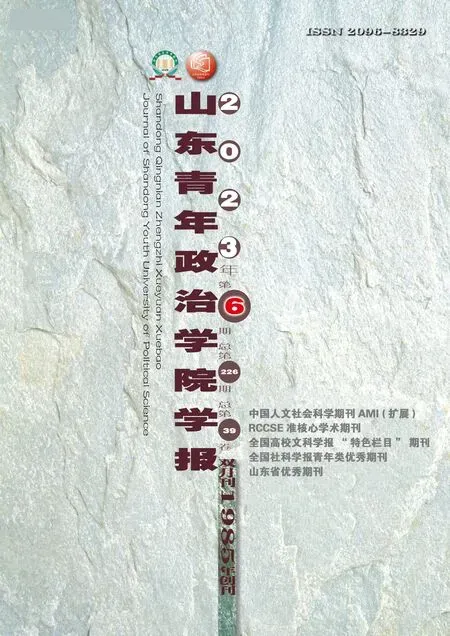虛靈、實理與氣稟:朱子論心、性、情
陳志偉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人文學院,西安 710126)
儒家心性哲學自先秦孔孟發其端,經兩漢魏晉隋唐有所中斷,到宋明理學被重新接續起來,心性問題被理學家們細致剖析,從而有更多重意義的顯發開拓,其中朱子對心性的反復闡述尤其值得關注。考察朱子的心性哲學,需要以先秦早期儒家特別是孟子對心性問題的討論為背景。孟子講心性著眼于以心善論性善,即“仁義禮智根于心”(《孟子·盡心下》),同時又不否認心還包含不善之情感與欲望,也就是耳目口鼻之欲也發于心。朱子在面對相同的問題時,以張載“心統性情”來總括心性關系,并且用理氣為核心的本體論架構統御心性,除了延續孟子性善之旨外,特別突出心性的氣稟或氣質的一面,并認為孟子對后者有所疏略,以此解決惡的根源問題。細致分析朱子對孟子關于心性問題在氣稟上有所缺失的批評,同時還原孟子在這個問題上的真面目,對于儒家心性哲學的歷史演進脈絡的澄清是有意義的。
一、問題的引出:朱子對孟子心性論的批評
朱子心性哲學根源于先秦孔孟對心性的闡發,而孔子在這個問題上較為渾圇,朱子對此討論得并不多,僅是簡單提及;但孟子哲學的核心即是心性問題,所以朱子在與弟子的相與辯難過程中不得不大量涉及孟子在此一問題上的材料,并對孟子心性論有所臧否。朱子臧否孟子心性論時所運用的標準是張載二程提出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分,并且以其理氣關系來統御心性,這一理論背景使其察覺到孟子在心性問題上的缺陷,即雖然孟子明確了性善,但對現實中人的惡來源于何處以及善惡關系卻語焉不詳。在朱子看來,善惡關系問題難以說清,必然影響到心性論在理論上的完整性和系統性。
在討論《中庸》“天命之謂性”這個命題時,朱子主要圍繞“性”這個概念來展開,但卻是在“天命”和“氣質”的對立中理解“性”。他認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袞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1]這里的“袞同”不是相同之意,而是相互混雜的意思。天命與氣質相互混雜,兩者不能相離,這是就事物上說。任何具體事物均是由天之所命的理和氣共同構成,否則“便生物不得”,物將不能生成和存在,因為沒有這個氣,天之所命的理將無處安放。由此可見,氣質在這里所起的作用是承載理。理要有個承載的載體,氣就是這個載體。此外,從“性”這個概念來看,“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之所稟,卻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但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2]如果只有天命之性,則無偏無邪,人性即善;不過一旦牽涉到氣質之性,則就會有偏邪,因為氣的特點是它“有昏明厚薄”的不同。這就如同“仁義禮智”之性,理本俱全,但惻隱、羞惡等則是心所發出來的情,是帶著氣質的,會因人之氣稟的差異而有昏明厚薄,這便使人在情感和行動中出現偏離善的表現,或者因其不足,或者因其過度。朱子認為“此理卻只是善”,問題是,既然如此,“如何得惡”?他斷定“所謂惡者,卻是氣也”。[3]這樣就引出了惡的來源問題。
很明顯,朱子的這種推理方式不同于孟子。眾所周知,“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但他也必須得面對現實中的惡,要對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惡來自于何處這個問題予以回答。孟子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與其性善論緊密相關,或者說他之所以如此回答,就是為了保持其性善論的前后一致。孟子認為一個人之所以作惡或不想為善,是因為他“失其本心”或放失了良心(《孟子·告子上》),或者是由于他對于其身之大體“不知所以養之”,根本原因是未能發揮心官之思的作用,“弗思”或“不思”從而陷溺了其心(同上)。孟子的“欲”比較復雜,指向多個方向,因此分為耳目口鼻(小體)之欲和仁義禮智(大體)之欲,但“思”的方向卻只有一個,即指向義,它是思善思惡并做出抉擇之思。[4]朱子上引同一段話中分析孟子的這一觀念時說:“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后來方有不善耳。”[5]這個分析道出了孟子論惡的根由,即他要堅持性善的前后一貫性,不能從根源上否定人性善這一核心觀點,或使這一觀點有所動搖,“其初無不善,后來方有不善”是說孟子認為人性先天無有不善,只是因為放失了本心或陷溺了自己的心才導致了惡的出現。這就意味著孟子相信人性在其根源上是純粹善的,無有一絲雜質在其中,并將此視為人禽之辨的規定根據,即“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朱子卻據此認為孟子“卻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6]①,并指出“孟子說得粗,說得疏略”[7],因為“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8],“孟子性善,似也少個‘氣’字”[9],他只“見得人性同處”[10],卻未見得人性之差異。這連續的指責表明朱子對孟子論性的方式是不滿意的,因為孟子只從本原上講性善,講人性的共同點,即“堯舜與人同”(《孟子·離婁下》)的地方,卻無視人與人之間的千差萬別。朱子認為孟子論性的這種方式是不全備的,顯得粗疏簡略,原因是孟子性善論缺乏或忽略了以氣稟或氣質闡述人性的維度從而忽略了人的差異,而這種差異只能從“氣”這個維度加以說明。[11]也就是說,在朱子看來,只有將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結合起來,才能將人性或心性問題闡述地完備、細致、清楚,既能闡釋人之共同的本質,又能講清人的差異。
但問題是孟子若以朱子所說的方式闡釋其心性論,將導致其理論出現內在矛盾,即從不忍人之心的四端到性善再到仁政、王道的政治構想,這一邏輯結構將無法成立。而在缺乏更多術語概念加以運用的情況下,這樣的內在矛盾沒有解決之道。朱子之所以在心性問題的闡釋上有了新方法,是因為在其之前,張載和二程給他提供了新的概念術語和理論框架。所以朱子對孟子人性論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涉嫌“刑求古人”。
二、虛靈之心與實理之性
伴隨著對孟子心性論的批評,朱子展開了自己的心性分析。心性本難以相區別,朱子對此有明見:“此兩個說著一個,則一個隨到,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別。舍心則無以見性,舍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更細思量。”[12]所以儒家哲學以心性論見長,而心、性往往相隨著說,于心上見性,于性上見心。朱子心性哲學以張載“心統性情”為前提,以理氣關系為框架,針對孟子心性論的問題,將氣質之性補充進對心性問題的討論之中。在朱子看來,心作為虛靈之所,起主宰作用,性是實理本具,而情則是心、性發動處,或心、性的功能,心性一旦發動,從主宰義、實理義走向功能義,就必然與氣稟或氣質相混雜,從而產生偏邪。朱子心性論與孟子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認為氣質之性也是性的一部分,因此就“性”本身而言,在其本原上就內含善惡兩種性質。所以朱子說:“性即是理。有性即有氣,是他稟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并承認“有性無仁”這種說法“亦是”,引呂氏“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故“人亦有昏愚之甚者”。[13]這就打破了孟子性純然是善的觀點。朱子這一理路當然其來有自,他自己就承認他是綜合了孟子、荀子、揚雄和韓愈的心性思想,融合張載和二程的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從而成一家之言。
朱子論心,最核心的一句應是“惟心無對”[14]。如何理解這句話,對于理解其心性論而言,是一個關鍵。朱子此句是總括地說,即他將心看作是人的整全意義的一種意象。心作為人之整全,將沒有與之相對待的其他概念。人的整全意義是指,人是一個含具善惡、情感、動靜、知覺、判斷、欲望的整體,而所有這些因素都可以綜括地包含于人心之中,其中的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可能單獨拿出來與心相對待。這就與張載的“心統性情”相一致了,同時也賦予了心以一種形而上學的絕對意義。心之所以能統性情,是因為它本身是虛靈之所,“心官至靈,藏往知來”,“靈處只是心”。[15]即使是理,也包蓄在心之中,對此,朱子舉了一個巧妙的例子來說明:猶如那寺廟里的藏經閣,“除了經函,里面點燈,四方八面如此光明燦爛”,這很明顯是將心看作是虛靈明覺的處所,正因其虛靈,才能包蓄住理之光,而“心包蓄不住,隨事而發”[16],此則是惻隱、羞惡等由內心發散而出的情。甚至氣稟物欲之私,也是出于心,則“人心亦兼善惡”[17]。有時朱子將性比作餡子,而“心以性為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18],這也是在強調心的虛靈而能包蓄得住性。因此,朱子斷定“虛靈自是心之本體”,“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19]“心之全體湛然虛明”[20],正是“以心虛靈之故”,才能“具得許多道理”在內。心具“感應虛明”之意[21],所以能統攝性情,心“是一個包總性情底”[22]。
心的另一個特點是,其具有主宰義,朱子明確認為“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心者,性情之主”,“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心是主宰于身者”,[23]“心,主宰之謂也”[24]。對于心如何發揮其主宰之功能,朱子并沒有給出具體闡述,只是強調心與性“不可無分別,亦不可太說開成兩個,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25]。結合上述心的總括義可知,這里的主宰應該主要是指心對性、情的統攝,以及通過心官之思所決定的意志方向,這兩者使得心對性、情、身體和人的行為具有一種主導的能動性②,在朱熹看來,性是寂然不動,要想使仁義禮智顯發于人的行為之中,離開心的這種能動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朱熹賦予心以主宰義,目的是為人的道德行為提供動力機制。朱熹強調心的主宰義也是為了使人心為人的道德生活負責,既為道德成就負責,也為道德失敗負責。[26]所以朱子說“主宰運用底便是心,性便是會恁地做底理。性則一定在這里,到主宰運用卻在心。情只是幾個路子,隨這路子恁地做去底,卻又是心。”[27]性理只是存于心之中,其運作卻要由心來提供動力,情是性理運作的幾種方向,或偏或正,而為其偏正負責的卻又是心。③總之,朱子的“心”是一個綜合性的哲學范疇,包含理性之思,以發揮其主宰性功能。[28]
朱子對性的理解與其心論關系密切,心作為虛靈之所,性就被包蓄其中。正因為此,在界定“仁”“義”時,朱子也是將二者視為心的功能:“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29]朱子認為性是無形影的,也就是沒有形體,這一點與物不同,故而“性不可言”,而我們要想言說性,只能通過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等四端去看,就像看到水流的清澈,就知道其源頭也是清澈的,因為性無形影,只好通過有形影的東西去感知體認,“如見影知形之意”[30]。但同時他又承認“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31],區別人與物的是氣稟的明暗和偏塞,“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32]因此氣稟概念的引入,除了要解決惡的來源以及善惡之間的關系問題之外,它還承擔著區分人、物的作用,如果只從渾圇的性上來看,人與物沒有什么不同,但涉及到氣稟時,則能明確人物之別,即人的氣稟以明暗為特點,物的氣稟以偏塞為特點;人之氣稟暗者則可通而使明,這就是“學”的效用,物之氣稟偏塞則無法通之。
朱子對性的論述最鮮明的一個特點是,他繼承了二程“性即理”的觀點,將性看作是“實理”[33]。在對比“性”和“誠”這一對概念時,朱子甚至認為“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34]譬如一把扇子,扇子本身是性,而這把扇子做得好就是“誠”。朱子此處當然不是說“誠”不實,他主張“誠者實有此理”,“誠只是實”,“誠,實理也”,[35]等等,他只是強調與“誠”相比而言,“性”更具實在性。而這個“實理”又內在于人的自我之中,所以劉紀璐將朱子視為“內在道德實在論”的持有者。[36]而江求流博士則把朱子這種理解“性”的方式看作是對佛教“性空論”和道教以無為本的駁斥和批判。[37]朱子的性理到底是指什么呢?我們注意到他在分析“性”這個概念的時候,經常使用的是“合當”這個詞,如“性是合當底”[38],又如在評價“孟子道性善”時,他將“善”看作是“性合有底道理”[39]。所謂“合有底道理”就是合當有的或應當有的道理。他還說“性只是合如此底,只是理,非有個物事”[40],性無形無影,所以“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41],它只是合當如此的道理:“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42]朱子以他對“理”的一個界定將規范性和正當性的內涵呈現出來:“至于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43]但這當然之理卻又是實在的,因為“性”是體而不是用。上述朱子之所以認為“誠”是虛而“性”是實,原因就在于性是體而誠是用,就如同扇子的例子所表明的,扇子本身是體,而扇子好還是不好,則只有在用的過程中才能被我們所辨知,因此屬于用的范疇。以“性”指當然之理,意味著朱子將“性”視為道德規范性和正當性的源頭,“性”為人的道德生活提供規范性與正當性的標準和依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性”才“純是善底”。[44]
但朱子又區分了善與性。《易傳》有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子解釋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這個理在天地間時,只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之曰‘性’。只是這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45]純然天理雖然是善的,但它不能給人的道德生活提供規范性和正當性的依據,只有當這個天理落實于人心之中,成為人的德性時,它才能為人的道德生活奠基。雖然如此,天理之善卻又為人性之善提供了形而上學的根據:就天地而言,善在先而性在后,天地之理散發到萬物,稟之而生人物;就人言,性在先而善在后,即先有那個性之理而后發為惻隱羞惡等顯之為善。故朱子強調“天下無性外之物”[46],他是將萬物之“性”理解為與人性一樣的仁義禮智信,這意味著在朱子看來,仁義禮智信遍布于天下萬物之中,并是天下萬物的本性。[47]李存山先生將朱熹的這一理路稱為“泛性善論”[48],意即將孟子性善論推及天地宇宙,從“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角度判斷天地呈現出來的也是善的。“泛性善論”或“泛道德主義”是道德實在論的一種表現形式,即主張天地萬物這樣的實體性存在也有善性,這是將道德實在論內外貫通的做法。就此而言,朱子的道德實在論不僅是內在的,而且也是外在的。如果從“性”是合當的道理來看,朱子“泛道德主義”即是將天下萬物都看作是應該以某種正當性為根據而存在,這明顯是把人的道德秩序和規范要求轉移到自然事物之上并以之來理解自然的思考路向。
在闡述心統性情時,朱子一再強調性并不是心中存在的某一個可以與心相區分的事物[49],這一點值得重視。朱子是針對佛、道兩家將性看作是一物而提出此一觀點的,他認為后者最終陷入價值的虛無。對朱子理氣關系的理解,有一派觀點認為朱子的理是客觀實體之理,可以獨立存在于心和氣之外,如果結合他對佛道將性視為一物的觀點進行的批判來看,由于性即理,那么我們就不能將理看作是客觀實體或一個事物,朱子顯然將性或理視為內存于心的規范性道理,此道理是實在的,但并不是像某個事物一樣,是實體性的。在朱子看來,真正的實在不是具有形體的事物,而是無形無影的,如性和理之類。如果能確立這一點,那么關于朱子是自律道德還是他律道德的爭論可以休矣:一個人的行為遵循內心的性理(規范性原則),必然是自律道德,而不可能是他律的。本原之性是純粹之理,而氣稟之性則與物相應而產生情,于是便有了善惡。
三、氣稟之情與人性的雙重意義
朱子一方面強調與天理同一的純然善的天命之性,從而維護孟子的性善論以及他繼承并發揮于二程的“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泛性善論”,另一方面也要解決惡的根源是什么這個問題。對此,朱子吸取了張載二程“心統性情”和“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二分這兩種觀念,輔以其“理一分殊”“理在氣先”以及理氣同異等觀點,將惡的根源安排在“氣”上,并以此來解釋人物的不同以及人與人之間個體的差異。此外,朱子在心、性、氣上的如此安排,也延續了先秦儒家哲學內外之辨的傳統,心、性屬內在,而氣稟則屬外在。自先秦以來,儒家主流的心性論就堅持內在決定或主宰外在的致思理路,朱子也不例外,他也主張內在的心為主宰,性理是道德方向,而氣稟及惻隱等情感是內在心性外發的結果,并受制于心性。
對于人,朱子認為“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50],人是理與氣相合而生,氣是天理附著湊泊處,若無氣則理不能附著,人物無以生,理也就無法呈現。性與氣的關系也是如此:“才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里。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51]由此可知,氣是性、理之載體,就像一勺水,要是沒有容器盛載,那么水就無歸著之處。朱子同時又承認有本原之性或天地之性,又有氣質之性,認為“本原之性無有不善”,而氣質之性則“有昏濁”,這種昏濁之氣能將本原之性加以阻隔,從而使天地之性的善無法顯現。所以孟子只講本原之性,而對氣質之性則不承認是性,即“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聲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孟子·盡心下》),“君子有弗性者焉”④。[52]耳目口鼻四肢等肉體欲望都屬氣質之性,但君子不謂之性,而稱之為“命”。按孟子的看法,這是因為這些是我們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所決定的,只能交給運氣或命運去安排,也就是說,凡不能由道德主體自主決定的東西,都屬于命的范疇。朱熹卻一反孟子的這一觀點,認為“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53]這里的“備”是指完備整全,由此可見,朱子認為如果不講氣質之性,對人的認識就將不完備不整全;尤其是當忽略了氣質時,本原之性也無從感知和體認,因為后者是無形無影的。在朱子看來,“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54]人物之別是由于所稟氣之精粗正偏而致,人得氣之精、正,所以擁有認知、學習的能力,而物得氣之粗、偏,就沒有這種能力。朱子認為這就是孟子所說的“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55]但眾所周知,孟子的人禽之辨是從是否存養仁義禮智等德性的角度來說的,而不僅僅局限于一種單純的認知能力。再者,就人本身而言,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也是由于所稟氣質的“昏明清濁”導致的,因此而有上知生知、學知等區別。
朱子指出這種由氣稟而致的人的屬性,也“不可不謂之性”。有時候朱子把性等同于太極,主張“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56]太極不離于陰陽,即前者要以后者為載體,無陰陽則太極無著落處,不雜乎陰陽則是指要確保太極的形而上之本體根據義。朱子堅持氣稟“不可不謂之性”,是為了解釋現實中的人“有善有不善”:“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57]無疑,朱子意義上的氣稟之性是輔助性的,而不是主導性的,因為他不止一次說“性”純然是善的,只因天命之性落實于人身之內,就必然受到氣稟的影響,從而導致清濁偏正昏明的差別,由此產生了善與不善的現象。但天命之性也只有落實到由氣稟構成的人身之內,才能實現自己,否則只是懸空的一個理在那里,無掛搭處。即使朱熹不只一次說過理能離氣而存在,但若只是理,其存在的意義將無處安頓,故理必與氣相合而生人物。人物之生成,理或本原之性起決定性作用,而所生成之人或物是好是壞,則受氣稟之性的影響。正如上文提到的朱子所舉扇子的例子,人物之生成就如同扇子,是其本體,而人物之好壞,就如同扇子使用中的表現,是本體之發用為氣稟所致。陰陽似乎是朱子意義上的元氣,而這陰陽“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乖,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稟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58]孟子只是就“極本窮原之性”來說,故無不善,但孔子卻說“性相近也”卻是“兼氣質而言”,是氣質之性。“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59]人之性與現實生活中具體的人不同,朱子仍然堅持孟子的性善觀念,但一旦考慮到現實生活中具體的人,則必然有善有惡,這種善惡差別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差異出現的原因,朱子將此歸之為氣稟不同所致。
然而,朱子還是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孟子性善論的人性敘事,他不斷強調氣稟也不能不謂之性,所以孟子人性善的結論就被改造成性善惡混的敘事方式。在朱子那里,人性中隱含著善與惡的雙重價值:“性即氣,氣即性。”“它源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60]由氣稟而導致的惡,在朱子那里主要指的是德性的某一方面過度或不及,如只有惻隱而無羞惡,或只有羞惡而無惻隱,這“便是惡德”,或叫“性邪”,所以“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61]朱子直面人性的復雜性,以天地之性或本原之性和氣質之性這雙重含義來解釋人的存在的整全性。正因為有氣稟在,所以人“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去其偏邪昏暗之害,得其中正平和之益,[62]這是朱子由人性的雙重意義所凸顯的工夫修養在成性成人中的重要作用。
朱子之所以極言氣稟之性在心性論中的必要性,是有見于歷史上心性論的得失。他認為孟子只講本原之性,“未嘗說氣質之性”[63],而荀子、揚雄只講氣稟之性,不講本原之性或天地之性,韓愈則以性三品說于人性之實情略近之,卻又不曾說得一個“氣”字,只有到了張載和二程提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才將心性論講得完備,尤其是程明道指出“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64]使朱子明白,只有兼及心性和氣稟,才能將心性論闡述得完備清晰。歷史地看,孟子強調內在心性,荀子、揚雄則偏重外在氣質,韓愈雖意在整合內外,但卻無法提供概念加以說明,只有到了朱子這里,心性情的內外關系才得以厘定,“合內外之道”成為其理論的明確指向。
朱子正是在氣稟上辨析“情”字。在承認張載“心統性情”的前提下,朱子認為性與情都源于心,而“性是體,情是用”,或者“性即是心之理,情即性之用”。[65]具體而言,性是仁義禮智,而情則是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等,“性無不善,心所發為情,或有不善”,原因是“心之本體本無不善,其流為不善者,情之遷于物而然也”。[66]就本體而言,性即理,因此無不善,但性是心之未動,而情則是心之已動,心動則欲生,欲必有善有惡,如“我欲仁”之欲是善,而欲違仁之欲則是不善,“情之遷于物”即是心所發之情受外在物欲影響而變動乃至于偏邪,就像孟子所說“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朱子用水來比喻心、性、情、欲的關系:“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卻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67]將心比作水,是強調心體及其包容性;把性比作水之靜,是強調性不能是一物,只是某種性狀;情是水之流意味著其方向不定,要由心之主宰和本原之性來來決定其善的方向,否則大多是偏邪的;作為水之波瀾的欲不僅方向不定,而且力度也難以掌控,需要由理來加以限制和調節,否則就如同決堤之洪水一樣,必將造成災害,這即是惡之所以產生的原因。
朱子對心、性、情的論述,確立了心的虛靈與主宰地位和性的本體地位,進一步解釋了張載“心統性情”的心性結構,而把情視為心之已動和性體的發用,因此屬于氣稟的范疇,從而為善惡的根源問題提供解決之道。這一解釋框架是對孟子性善論的改造,一方面朱子并沒有放棄性善的觀念,另一方面又以氣質之性彌補孟子心性論所忽略的內容,從內外兩個層面對儒家心性論予以重構,從而建立起更為全面更為清晰的心性哲學體系。這一體系的根本目的是為人的行為提供規范性和正當性根據,同時也確定了從性體到道德實踐的動力機制。朱子對氣稟之性的關注打破了孟子人性論只講“同”的一面,而將人的復雜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凸顯出來。就此而言,以心性論確立的規范性和正當性才有其適用的對象和范圍。
注釋:
①二程提出“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參見《二程遺書》卷六,二程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4:81。前者是批評孟子的人性論,后者是批評荀子、揚雄的人性論,朱子將此視為剖析“性”的基本原則,要之需將性與氣綜括地說才清晰全備。
②楊國榮教授明確指出“心”的主宰義具有統攝和主導兩個方面的指向。見楊國榮.中國哲學中的心、性、情[J].南國學術,2023(01)。另參見劉紀璐.宋明理學:形而上學、心靈與道德[M].江求流,譯.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21:192。
③有學者指出,“心的‘知覺’內在于情,構成人的生命存在之內在的主宰和定向作用。”見李景林,田智忠.朱子心論及其對先秦儒學性情論的創造性重建[J].中國社會科學,2007(03):88,轉引自王緒琴.天理與人生的貫通:朱子心性論的內在結構與雙向開展[M].北京:中華書局,2023:20-21。
④朱子在此引用了張載的《正蒙·誠明篇第六》。該篇有云:“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見林樂昌.正蒙合校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12:33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