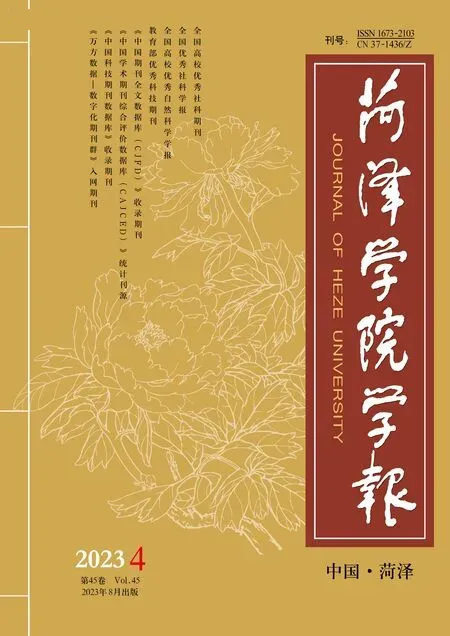英國早期女權主義的局限性之省思
——以《簡·愛》為分析中心
周 琦
(北京交通大學語言與傳播學院,北京 100044)
夏洛蒂·勃朗特的《簡·愛》是英語文學史上的名著之一。正如學者埃爾希·米基所形容的那樣,這部小說中“第一人稱女主人公的充滿激情的聲音將維多利亞文學界卷入了一場風暴”[1]。《簡·愛》中所體現(xiàn)出的追求女性獨立和性別平等的訴求是文學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突破,而其中對維多利亞時代人民生活方式的描寫也為學界研究提供了獨特的女性視角,這部小說也因此成為英國文學研究和女性主義研究中經(jīng)久不衰的熱點。長期以來,學術界對該小說的研究大都聚焦于其女權主義思想的探索,關注點主要集中于幾個彰顯女性追求的主要情節(jié),比如簡·愛選擇獨立工作、簡·愛的出走以及簡·愛對于圣·約翰婚姻的抗拒等。對于文章的對話、角色的內(nèi)心獨白等細節(jié),則沒有進行深入的探求。其實,從小說的情節(jié)、對話和角色形象中,我們可以追索隱藏在簡·愛的女權主義追求背后的種種局限性:女主人公簡愛對于宗教信仰的訴求、對羅切斯特的精神依賴體現(xiàn)了其人格獨立的不徹底性;她的自卑心理和等級意識也與其對平等的追求相沖突;她潛意識里對男權的服從進一步削弱了其女權主義者的形象。在小說的結尾,簡愛已經(jīng)從一個獨立的女權主義者變成了一個傳統(tǒng)的“家中天使”,一個需要依靠男人和家庭來獲得生命意義的女人。因而,我們不僅應該揭示這部小說的女權主義意蘊,而且應對《簡·愛》中女權主義的局限性進行省思,以升華小說的主題。
一、簡·愛的精神依賴性
(一)簡·愛對上帝的精神依賴
《簡·愛》這部小說的顯著特色之一就是貫穿于小說始終的強烈的宗教色彩。每當女主人公陷入困境,上帝的超自然的力量就開始在她的睡夢中和幻覺中閃現(xiàn),給予她心靈上的撫慰和鼓勵。許多被認為“帶有女權主義色彩”的情節(jié)都是通過上帝的頻頻出現(xiàn)而推動的,正因為在進退兩難時有著上帝的指引,簡·愛才能通過宗教信仰的“外力”來對抗她內(nèi)心中的躊躇不決和作出決定時的重重顧慮,最終走上追求獨立和平等的道路。
在小說中,當簡·愛被內(nèi)心的焦慮和迷茫所困擾時,上帝就作為精神導師的形象出現(xiàn)了。當羅切斯特與簡·愛的婚禮因為羅切斯特的妻子伯莎的存在而取消后,羅切斯特懇求簡·愛留下來陪伴他,這讓簡·愛在精神上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渴望留在愛人身邊的強烈欲望和拒絕做沒有名分的情婦的自尊自愛產(chǎn)生了強烈的沖突。正當她遭受著抉擇不定的煎熬時,“上帝幫助我!”[2]這句話從她的嘴里脫口而出。這句求助般的呼聲將她的脆弱、猶豫不決、精神的依賴性清晰地展示在了讀者面前,在做出離開的決定時,她依靠的并不是個人的信念,而是求助于上帝的指示,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她的女權意識其實并不足以說服她依靠自身的獨立思考來做出“出走”的決定。
在離開桑菲爾德莊園前的最后一晚,簡·愛夢到了一個從云中而來的白色身影,那個身影向著簡·愛的靈魂低語道“我的女兒,離開誘惑”,而簡·愛回答道:“母親,我會的。”[3]夢中的這位“母親”的身份給予了簡·愛出走的信心,也以“神”的身份為她的行為賦予了正當性:出走是為了離開“誘惑”,是正當之舉,是不應該猶豫的。這個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的身影無疑是簡·愛內(nèi)心躊躇不定的反映,因此她需要夢中的“他者”來勸說自己,以神靈和長輩的名義為優(yōu)柔寡斷的自己作出離開的決定。
當簡·愛離開桑菲爾德,開始了她漫無邊際和艱難困苦的游蕩之時,對于上帝的信念再一次撫慰了她的心靈,給予了她生活下去的信念。因為出走而被讀者看作是“追求獨立平等”的簡·愛,此時其實充滿了對羅切斯特的牽掛,但是當她感受到了上帝的“無邊無涯”“萬能”和“無處不在”,她堅信“羅切斯特先生是安全的……會受到上帝的保護”[4],從而擺脫了悲哀的情緒。宗教的力量又一次在小說中顯露,在簡·愛為了自己的決定而痛苦時撫慰了她的情緒,幫助她徹底接受出走的決定,推動了情節(jié)的進展。
在文學史上,簡·愛的出走往往被看作她女性意識覺醒的宣言。但在上述三處分析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在簡·愛作出決定的關鍵時刻,并非是從個人的信念中汲取力量,而是常常求助于宗教信仰,將自己所作出的決定看作是神靈的旨意,以神靈的全知全能性為自己追求獨立的行為“正名”。由此可見,簡·愛的女性意識并未強大到可以主宰她個人行為的程度,她對獨立和平等的追求其實是脆弱的、不堅定的、需要外力支持的。這無疑體現(xiàn)了英國早期女權主義思想的局限性。
(二)簡·愛對男性的精神依賴
簡·愛的獨立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xiàn)在她對于經(jīng)濟獨立的追求,例如,她堅持家庭教師的工作,拒絕做沒有經(jīng)濟來源、完全依附于男人的家庭主婦。但盡管如此,在精神層面上,簡·愛依然習慣全然依賴于男性,甚至在愛情的希望渺茫、自身在愛情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時,依然將羅切斯特看作生活的全部追求,缺乏愛情之外的生活寄托。
在修道院中長大的簡·愛,是自尊、自愛、自強,是對生活充滿熱情、對于挑戰(zhàn)毫不膽怯的,她最終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優(yōu)異的學習成績得到了做教師的資格,并且渴望冒險,不安于生活的一隅:“我為自由而殷切祈禱……懇求變化,懇求刺激。”[5]然而在遇到羅切斯特之后,她立刻屈服于他的男性魅力之下,完全忘記了真正的世界是一個“廣袤無垠,充滿各種希望與憂慮、激動與興奮的天地”[6]。相反地,羅切斯特已經(jīng)成為了她的世界的全部:“我的未婚夫正在變成我的整個世界,還不僅僅是整個世界,而且?guī)缀醭蔀槲疫M入天堂的希望。”[7]其實,二人之間的財富、相貌和社會地位的差距已經(jīng)預示了這段感情是不公平的、婚姻更是阻礙重重的,與其說簡·愛的心情是甜蜜欣喜的,不如說她經(jīng)歷的苦痛更甚于此。當她注視著羅切斯特時,她覺得自己就如同一個絕望的快要渴死的人,為了最后的一絲快樂去心甘情愿的飲用有毒的水,這種卑微的依賴讓她陷入到了無盡的自我折磨中,然而,她依然無法從這種痛苦的愛情中解脫出來:“我們之間永遠橫亙著一條鴻溝——可是,只要我一息尚存,還能思維,那我就不能不愛他。”[8]
更重要的是,當簡·愛得知了羅切斯特的妻子伯莎依然存活的消息后,她對他的依賴不減反增,甚至于在羅切斯特懇求她留下作一個沒有名分的地下情人時,她也無法對他生出怒火或者怨言,反而感到“我的良心和理智都背叛了我,指控我犯了反抗他的罪過”[9]。顯然,羅切斯特在婚姻狀況上對于簡·愛的刻意隱瞞和欺騙,早已經(jīng)被她無條件地原諒了。雖然她最終決定離開,但這個決定僅僅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是為了保護自身的名譽,而并非來自于女性獨立意識的覺醒。從后續(xù)的情節(jié)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出走后的簡·愛“一刻也沒有忘記”[10]羅切斯特,她對于后者仍然有著根深蒂固的精神依賴。
最終,簡·愛嫁給了因意外而變成盲人的羅切斯特,每日照顧他的起居,陪伴他的生活,就已經(jīng)成為了她“最甜蜜的愿望”[11]。對于羅切斯特的精神依賴已經(jīng)成為了她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仿佛那個曾經(jīng)對生活充滿激情、渴望擁抱廣闊世界的簡·愛逐漸離開了讀者的視野,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陷入愛情而不能自拔、在精神上完全依賴男性的傳統(tǒng)女性。這也體現(xiàn)了英國早期女權主義思想的局限性。
二、簡·愛自相矛盾的平等觀
(一)簡·愛的自卑情結
在小說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獨白:“難道就因為我一貧如洗、地位平凡、長相平庸、個子矮小,就沒有靈魂,沒有心腸了嘛?你想錯了!我跟你一樣也有靈魂以及一顆充實的心!……我是在用自己的靈魂與你的靈魂對話,就仿佛我們都已離開了人世,穿過墳墓,一同站在上帝的面前,彼此平等——而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12]
這段文字,因為明確提出了“平等”的概念,往往被視為簡·愛的女權主義宣言。但這段憤慨的吶喊,其實不是出自她內(nèi)心中“人人平等”的信念。在小說中,簡·愛之所以說出這段話,是由于羅切斯特故意顯露出對于貴族小姐英格拉姆的傾戀,這深深地刺痛了相貌平凡、身份低微的簡·愛,也使她更深刻地認識到了自己與羅切斯特之間的種種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她對于“平等”的呼聲,與其說是出于內(nèi)心的自信自強,不如說是出于對自卑情結的掩飾。
簡·愛之所以產(chǎn)生自卑的情緒,是因為她一直用英國傳統(tǒng)的女性觀來評價自己。在19世紀的英國,美麗的外貌和纖細的身材一直都是評價女性的主要標準,而簡·愛更是常常因為自己的相貌,將自己擺在卑微的地位。當她第一次聽聞英格拉姆小姐的美貌時,她的反應是克制自己對于羅切斯特的愛,因為簡·愛認為相貌的差距已經(jīng)決定了她在愛情中完全失去了競爭力。在她的獨白中,我們更可以清晰的看出她深深的自卑和消極的自我否定情緒:
“那么,簡·愛,聽著對你的判決:明天,把鏡子放在你面前,用粉筆如實地繪出你自己的畫像,不要淡化任何一個缺陷……并在畫像下面寫上‘貧窮孤苦、相貌平庸的家庭女教師肖像’。”[13]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她拒絕了圣·約翰的求婚,這其中也有顧慮相貌差距的因素:“而我吶,長得那么平庸……我們絕對不般配。”[14]顯然,她將相貌當作評判女性價值的重要標準,甚至于因為相貌平凡而主動否定了自己追求愛情和婚姻的可能,這種觀念無疑仍是一種傳統(tǒng)女性觀。
簡·愛自卑的另一個原因是她的貧窮和低下的平民身份。在小說中,當羅切斯特給她購買衣物和珠寶時,她并沒有感到驚喜和幸福,反而產(chǎn)生了“惱恨和墮落感”[15];羅切斯特的微笑,在她看來也變成了“對一個他剛剛賜予金銀珠寶的奴隸微笑一樣”[16]。盡管此時羅切斯特已經(jīng)向她求婚,她卻依然覺得自己的貧窮和低微是低人一等的。如果簡·愛真的對自己充滿自信、認為自己與羅切斯特是平等的,又如何會因為幾樣禮物,就如此敏感不安呢?正是因為她強烈的自卑心理,將自己的人格擺在了卑微的地位,所以她在收到未婚夫的禮物后,才會產(chǎn)生這種“被施舍”的憤怒和羞惱,才會以強烈的躁動來展現(xiàn)被自卑情結深深壓抑的自尊。
所以,簡·愛追求“男女平等”背后的動因是很復雜的:一方面是出于對自身女性價值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我否定的自卑情緒。正如她對羅切斯特的質(zhì)疑中所說,“跟一個配不上你的人結了婚……我才不相信你會真正愛她”[17],她其實是自信不足的。一方面,簡·愛有自己的主見,熱愛知識,勤奮工作,不貪圖榮華富貴,是一個優(yōu)秀的女性。另一方面,小說中的簡·愛將相貌、財富和身份作為評價女性的主要標準,這就使她完全忽略了自己人格上的諸多優(yōu)點,反而否定自身,認為自己配不上羅切斯特。正是因為簡·愛認為自己和羅切斯特在現(xiàn)實條件中不是平等的,所以她才要堅持“靈魂上的平等”,在形而上的層面上來填補二人的差距。因此,她強烈呼吁的“靈魂上的平等”,是愛情中弱勢方的自我保護以及對于自卑情結的遮掩。這也體現(xiàn)了英國早期女權主義思想的局限性。
(二)簡·愛的等級意識
一方面我們肯定,簡·愛以倡導“靈魂的平等”而成為維多利亞小說中獨樹一幟的主角,但同時也需要指出,簡·愛所呼吁的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指愛情中雙方感情付出程度的平等。在小說中,簡·愛在很多場合下,依然表現(xiàn)出了強烈的等級意識。
在小說中,簡·愛對于平等的追求是有條件的:只有當她自己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時候,她才會意識到平等的重要性;而面對低等階層的社會成員,她在潛意識里依然是存在著階級優(yōu)越感,不愿意將自己看作是與對方平等的人。從她的童年開始,生活在下層社會的她就將貧窮和墮落相聯(lián)系,當她離開羅切斯特、到一所鄉(xiāng)村學校教導鄉(xiāng)下兒童時,她認為自己又一次墮落了:“我感到有失身份……我懷疑我跨出的這一步不是使我在社會生活的等級上提高,而是降低了。我在我的周圍聽到的和看到的只有無知、貧窮、粗俗,我隱隱有點沮喪。”[18]在面對和自己幼年時十分相似的下層的兒童時,她沒有感到同情,而是感到“有失身份”,雖然她認為經(jīng)過幾個月的教學后,她對這些兒童的“討厭也就會被漸漸滿意而取代”[19],但這種內(nèi)心的掙扎證明了她有輕視窮困人民的嫌疑。在經(jīng)歷過桑菲爾德莊園得體的生活和與貴族們的接觸后,簡·愛在潛意識里已經(jīng)將自己看作了一個“上層人”,也忘記了在面對貴族成員羅切斯特時所喊出的“我們本來就是平等的”的話語。從簡·愛的所思所想中,我們可以看出,“平等”雖然是她心中所堅持的普遍價值,維多利亞時期的等級觀念在她心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
從簡·愛對羅切斯特的稱呼中,我們也或可看出她有等級觀念的一面。在桑菲爾德莊園時,她以家庭教師的身份受聘于羅切斯特,所以稱呼羅切斯特為“主人”,這在二人之間存在雇傭關系的時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當羅切斯特成為了她的未婚夫后,她依然時不時地自然地稱呼他為“主人”。例如,在小說的第37章中,“主人”的稱呼就出現(xiàn)了五次。當她第一眼看到羅切斯特時,她認出了他:“那不是別人,正是我的主人”[20],而在之后的交談中,她也多次說過類似的話語:“我親愛的主人,我是簡·愛”;“我親愛的主人,只要我還活著,絕不會留下你一個人孤苦伶仃的”;“(我)本能地更加緊緊依偎著我那失明而深愛著的主人”;“……我的主人繼續(xù)說”[21]。此時,作為未婚妻的簡·愛對于她和羅切斯特的等級、地位差距依然有著潛意識中的認同,也因此才會自然而然地使用“主人”這個有著自我貶低意味的稱呼。正如學者羅伯特·B·馬丁所說,盡管這部小說被譽為最早的女權主義小說,但在小說中卻看不到在政治和法律等層面上對男女平等的訴求[22]。面對擁有強烈的主仆等級意識的簡·愛,我們又仿佛看到了英國早期女權主義思想的局限性。
三、簡·愛對男權的潛意識服從
(一)男權的壓制
在小說中,男權對于女性權利的種種壓迫,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部作品的女權主義色彩。男主人公羅切斯特,就是傳統(tǒng)男權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嚴厲、專斷、常常以自我為中心,在愛情中往往不能顧及女方的感受,這從他對待妻子伯莎的態(tài)度中就可以判斷出來。雖然羅切斯特辯解說,伯莎和她的家人是看中了他的貴族身份,才讓伯莎來討好他,但他也確實沉迷于伯莎的美貌和魅力:“我發(fā)現(xiàn)了她是個美人……她恭維我,還賣弄姿色和才藝來討好我。她圈子里的所有男人似乎都崇拜她,嫉妒我。我眼花繚亂,激動不已……我以為我愛上了她。”[23]出于被女性討好的虛榮心,出于對伯莎美貌的戀慕,他娶了她,卻在婚姻變質(zhì)后將責任都推到了他人的頭上:“她的親戚們慫恿我;情敵們激怒我;她引誘我……我從來沒有愛過她,敬重過她。”[24]羅切斯特顯然是十分自私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他沒有愛過和敬重過伯莎,同意結婚僅僅是因為貪戀她的美貌,渴望享受迎娶美女的虛榮。但面對簡·愛的質(zhì)疑,他卻將伯莎形容成了一個媚俗、虛榮、與自己不相配的女人,將自己的過錯輕描淡寫地形容成“幼稚無知,沒有經(jīng)驗”[25],將他們婚姻的失敗歸咎于伯莎精神錯亂的病情,企圖為自己脫罪,毫無承擔婚姻后果的責任感。因為娶了伯莎而后悔、自覺“有失身份”的羅切斯特,將發(fā)瘋的伯莎軟禁在了陰暗的閣樓里長達十年之久,剝奪了她的自由,更剝奪了她接受治療和被人照料的權利——因為伯莎是他年輕時的污點,將她永遠藏在莊園中的一隅、抹殺她的存在,才能維持他作為貴族的體面。羅切斯特通過殘酷的男權壓制,在物質(zhì)上徹底剝奪了伯莎作為一個人的所有自由、權利和尊嚴,在情感上徹底否定伯莎作為一個妻子的存在價值。這種身體和心理上的雙重壓制,體現(xiàn)了在一個男權至上的社會里,女性的權利是如何微不足道、而婚姻中女性的低位又是多么地可悲。
為了娶簡·愛為妻,他欺騙了她,隱瞞了他已有伯莎這個法律上的妻子的事實,這使簡·愛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差點成為他的情婦——因為伯莎的存在,簡·愛無法獲得任何法律上的名分,一旦真相暴露,她最終收獲的只能是社會輿論對她不貞的指責。羅切斯特的自私和欺騙將簡·愛推到了名譽掃地的邊緣,正如后者所想的那樣,如果她留下來繼續(xù)做他的情婦,“他有一天會以此刻回憶時褻瀆她們的同樣心情來看待我”[26]。簡·愛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從羅切斯特的所作所為看來,他對于前任妻子確實沒有肩負起任何責任,對于簡·愛這個“后繼者”也并非是抱有十足的誠意的,維多利亞時期兩性的權力之不平等也就可見一斑了。
與羅切斯特相比,小說中的第二位男主人公——圣·約翰,雖然沒有對簡·愛造成任何心理上的傷害,但他對待女性的態(tài)度依然是十分專橫的。圣·約翰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一個遵循著宗教正統(tǒng)和社會習約的男人。他從來都沒有對簡·愛產(chǎn)生過愛情,他請求簡·愛嫁給他,僅僅是因為她適合做一個牧師的妻子。在他的印象里,簡·愛是一個“溫順、勤奮、無私、忠誠、堅定、勇敢”[27]的女性,是可以幫助他在印度進行傳教工作的“無價之寶”[28]。為此,圣·約翰還以上帝的名義來壓制簡·愛的個性:“上帝和大自然要你做一個傳教士的妻子……你生來就是為了操勞,而不是為了愛情。你是屬于我的……為了我主的事業(yè)而奉獻。”[29]他將簡·愛視作男人的附庸和可以利用的工具,將自己的事業(yè)追求和生活方式強加到她的身上,認為這就是她作為一個女性所應有的歸宿。有學者認為,圣·約翰是“簡·愛的身體和心靈的潛在謀殺者”[30]。如果簡·愛嫁給了圣·約翰,她就要終身面對毫無愛情的婚姻和鐵石心腸的丈夫,在環(huán)境陌生、條件惡劣的異國他鄉(xiāng)生活,更要一輩子進行她毫無興趣的傳教工作,這無疑是一種另類的精神囚禁。圣·約翰的所作所為,雖然不包含任何自私和欺騙的成分,卻讓讀者更清晰地看到了男權的運作方式——將女性打入一個黑暗的精神世界,剝奪她們的追求、自由和對愛情的渴望。遭受男權壓制的伯莎和簡·愛,雖然生活境況不同,但卻面臨著共同的精神困境。
(二)簡·愛的順從
在維多利亞社會,男性的優(yōu)越地位和男權的強勢是被默許的社會成規(guī)之一。正如學者哈默頓所指出的那樣:“以現(xiàn)代的標準來看,當時的法律是十分守舊的,反應了人們對于婚姻中男性處于優(yōu)越地位、而女性順從的狀況,是廣泛接受且深信不疑的。”[31]遭受著法律和成規(guī)的拘束的女性,根本無權在婚姻中要求平等的對待,而簡·愛在婚姻中受到男權的壓迫時,因為潛意識里受到男權至上的社會價值觀影響,也是更多地采取了順從的姿態(tài)。
在小說中,簡·愛親自見識到了因發(fā)瘋而不成人形的伯莎的悲慘生活,在恐懼之外,她卻沒有對伯莎產(chǎn)生同情;盡管羅切斯特試圖隱瞞伯莎的存在,但經(jīng)過他的自我辯解,簡·愛接受了他的說辭,將他的婚姻慘狀歸咎于伯莎的精神錯亂,而不是羅切斯特自身的冷漠無情。她對于伯莎悲慘現(xiàn)狀的無動于衷,是因為在潛意識中已經(jīng)默許了伯莎被囚禁、被冷落的事實,默許了羅切斯特對于伯莎的態(tài)度。羅切斯特的所作所為處處都體現(xiàn)著男性沙文主義的專橫和冷酷,簡·愛最終還是嫁給了他——這是她對男權主宰婚姻、女性無條件順從的現(xiàn)實的無聲的認可。
面對圣·約翰的求婚,簡·愛清晰地知道這段婚姻并不包含任何愛情,而僅僅是為了維持兩人在傳教工作上的合作關系而設立的一種法律枷鎖。但從文中可以看出,與其說簡·愛反對這項提議,倒不如說她其實是在搖擺不定、猶豫不決,甚至流露出了軟弱的情緒:“我感到他的影響已經(jīng)深入我的骨髓——他的控制已經(jīng)束縛住了我的手腳”[32]。雖然她嚴詞拒絕了他,但當圣·約翰暫時退步并允許她再考慮結婚的提議時,簡·愛又產(chǎn)生了一種類似愧疚和自責的情緒:“作為一個男人,他可能想要強迫我服從,但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才這么耐心地容忍我的執(zhí)拗,給我那么長時間思考和懺悔。”[33]簡·愛將自己拒絕求婚的行為理解成了一種需要“懺悔”的罪過,而提出無理請求的圣·約翰反倒成為了寬宏大量的一方。這足以說明,在簡·愛的潛意識中,男性依然處于更加優(yōu)越的地位,他們的要求是不容拒絕、必須順從的。也正因如此,圣·約翰的些微妥協(xié),在簡·愛看來就已經(jīng)是一種難得的高尚和寬容了。而當圣·約翰收起他冰冷的態(tài)度、露出溫柔的一面時,簡·愛的順從就更加明顯了:“我能抵御圣約翰的怒火,但在他的溫情下,我像蘆葦一樣柔順。”[34]顯然,簡·愛拒絕這段婚姻的決心,其實是不堅定的。
從這種意義上說,小說中的簡·愛雖然在行為上總是試圖逃脫男權的掌控,但她對于伯莎境況的默許、對于拒絕圣·約翰求婚時的愧疚和躊躇,都體現(xiàn)出她在潛意識中依然將女性的權利置于男權之下。正如陳姝波所言,在小說的后半部分,簡·愛已經(jīng)不再那么反抗和叛逆,也不再是那個“為了個人幸福和自我實現(xiàn)而義無反顧的人”[35]。每一次與男權的碰撞,都使得順從的心理更加深入她的骨髓,使她逐漸失去擺脫男性、追求獨立的決心和勇氣,這也體現(xiàn)了英國早期女權主義思想的局限性。
四、傳統(tǒng)婚姻觀和傳統(tǒng)女性價值的回歸
(一)傳統(tǒng)婚姻觀的回歸
在小說的結尾,簡·愛如愿以償?shù)丶藿o了羅切斯特。在女權主義的視角中,這是簡·愛通過追求獨立平等的抗爭而取得的回報,是女性勇于追求跨階級的愛情而取得的勝利,更是愛情中男女平等的象征。但不可忽視的是,在他們結婚前,他們的個人命運發(fā)生了重大轉折:簡·愛獲得了來自親戚的一筆遺產(chǎn);羅切斯特遭遇了一場大火,失去了妻子和家產(chǎn),自身也失明且殘疾了。如果沒有這些出人意料的“意外”,當貧窮的簡·愛回到桑菲爾德時,面對的依然是那個英俊富貴的已婚貴族,兩人之間的種種差距又一次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時,恐怕小說結局就只能是簡·愛的第二次“出走”了。
作者關于遺產(chǎn)和大火的巧妙設計,填補了簡·愛和羅切斯特在物質(zhì)條件上的種種差距,這才是兩人得以順利成婚的根本原因。在經(jīng)濟上,簡·愛是幸運的,突如其來的財富使她得以真正地獨立起來,這就為她自由追求愛情而提供了前提;而羅切斯特卻在一夜間失去了宅邸,搬到了貧苦的農(nóng)莊,成為了一個落魄的無產(chǎn)貴族。在社會地位上,簡·愛變成了一個富有的女性,脫離了為生計而奔波的勞動者身份;羅切斯特不但失去了財產(chǎn),其瘋狂的妻子縱火傷人的丑聞,對他的名譽造成了重大的打擊,其貴族身份已經(jīng)名不副實。在相貌上,簡·愛雖然長相平庸,卻擁有健康人的身體;羅切斯特卻失明斷肢,徹底地成為了殘疾人,連普通人也不如了。兩人之間的經(jīng)濟條件、社會地位和相貌的差距,在此消彼長之下,已經(jīng)基本持平;在此前提下,兩人的婚姻與其說是女性主義的勝利,不如說是傳統(tǒng)的門當戶對的婚姻觀又一次占了上風。
對于傳統(tǒng)婚姻觀的認可,在簡·愛對待羅切斯特境遇的態(tài)度中也可以體現(xiàn)出來。雖然羅切斯特變成了一個殘疾且落魄的男子,簡·愛在他面前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我興致勃勃……和他在一起,毫無惱人的拘束,不需要壓抑高興和快活,因為我知道我合他的意。”[36]曾經(jīng)自卑敏感的簡·愛,為何不再像以前一樣,因為愛情而患得患失、疑慮重重,反而變得如此自信呢?顯然,因為兩人在物質(zhì)條件上的種種差距已經(jīng)消失殆盡,簡·愛才能把自己擺到與對方平等的地位,更是因為兩人終于“般配”而感到如釋重負。由此可見,這場看似美滿的“跨階級”的愛情只是一場空中樓閣,在背后運作的,依然是兩人在經(jīng)濟條件、社會地位和相貌上的暗中博弈。傳統(tǒng)的門當戶對的階級觀,在簡·愛心中依然擁有重要的地位。
簡·愛對于傳統(tǒng)的反叛,實際上摻雜了一種“對于特定社會傳統(tǒng)的堅定遵守”[37]。當我們在探討小說中女主人公勇于追求平等愛情的女權主義意蘊時,我們應該注意到,簡·愛的成功實際上更多的依靠的是戲劇性的“意外”而非是自身的努力。在小說的結尾,簡·愛和羅切斯特終于在物質(zhì)條件上達到了平等,這實際上是對傳統(tǒng)婚姻觀的妥協(xié)。
(二)傳統(tǒng)女性價值的回歸
在《閣樓上的瘋女人》中,古芭和吉爾伯特提出了出名的“天使與魔鬼”的女性形象論,認為文學作品中的女性遵從男性的需求則為“天使”,反之則為“魔鬼”。勃朗特筆下的簡·愛,小說末尾就變成了一個為了羅切斯特而存在的“家中天使”。對于羅切斯特的失明、殘疾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事實,她甘之如飴:“我愿當你的鄰居,你的護士,你的管家……為你讀書,陪你散步,坐在你身邊,服侍你,做你的眼睛和手。”[38]簡·愛此時已不單單是羅切斯特的妻子,而是如同帕特摩爾的詩中所說的“女仆和妻子”[39]一樣,丈夫的需求,就是她生活的意義所在。為此,簡·愛也放棄了她家庭教師的工作,因為她的“全部的時間和精力”[40]都要用來照顧她的丈夫,這固然有羅切斯特殘疾的原因,但同時也代表著,在婚姻和家庭之外,簡·愛已經(jīng)不再具有獨立的社會身份。在小說的結局處,“家庭教師簡·愛”消失了,我們看到的只是“羅切斯特的夫人”,一個將全部生命都奉獻給了丈夫和家庭的傳統(tǒng)女性。
“社會訓練女性,使她們只為一個功能而生,這個功能就是婚姻。”[41]簡·愛的歸宿也正是如此。那個為了獨立而發(fā)奮自強、為了世界之廣大而興奮不已的簡·愛仿佛已經(jīng)成為了過去時,她最終還是變成了一個依靠親戚的遺產(chǎn)而生存、依附于丈夫、為了家庭而存在的“家中天使”。簡·愛形象的轉變無疑削弱了小說的女性主義色彩,而這部小說的主旨最終還是回歸了傳統(tǒng)的女性觀:“女性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對愛情和婚姻的奉獻。”[42]
長期以來,《簡·愛》被視作世界文學史上彰顯女權主義的代表性著作,而簡·愛的出走、拒婚、獨立工作等等行為,也被當作是女性追求獨立平等的范例。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意識到,《簡·愛》作為一部長篇小說,其內(nèi)容絕不僅僅是幾個主要情節(jié)就可以概括的。在一個“出走”行為的背后,有著無數(shù)的文本細節(jié)在填充,其中所體現(xiàn)的簡·愛的內(nèi)心掙扎和矛盾心結,是我們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可忽視的。正如伊格爾頓所說,在這部小說的背后是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在斗爭,一方面,簡·愛展示理性、冷靜、充滿斗志、激烈反抗的精神,但另一方面,她又顯得十分虔誠、順從和保守[43]。在簡·愛的出走的背后,是神力的相助以及她的依賴、軟弱和不舍;在她呼吁獨立和平等的同時,內(nèi)心的自卑和對下層人的蔑視也體現(xiàn)出了她強烈的階級觀和等級觀;反抗男權控制的她,在面對欺騙她的羅切斯特和冰冷的圣·約翰時,卻依然幾度動搖自己拒絕求婚的意志。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體現(xiàn)了簡·愛在其女權主義追求上的“二律背反”。
簡·愛在行動和思想上的種種不一致,體現(xiàn)了作者夏洛蒂·勃朗特的內(nèi)心思想與時代觀念的激烈沖突。因此,在勃朗特筆下的簡·愛是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的種種矛盾特質(zhì)的集合體:智力和感覺,熱情和理性,反叛和守禮,侵略和自守,都融為一爐[44]。在傳統(tǒng)女性觀和女權主義觀中搖擺的簡·愛,一直都受到作者所設計的種種宗教、機遇和巧合的外力的推動,這才做出了一系列彰顯女權主義追求的行為。然而,為了簡·愛最終能夠得償所愿、不負之前的努力,勃朗特設計了“遺產(chǎn)”和“大火”的雙重巧合,讓平凡而貧窮的簡·愛在這突如其來的意外中獲得了華麗轉身,卻也變相否定了她之前的種種努力。顯然,在勃朗特的內(nèi)心深處,女性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維多利亞時期傳統(tǒng)的女性觀依然根深蒂固。
作為一個女性作者,勃朗特的妥協(xié)是一種時代的必然。簡·愛在愛情中的掙扎就是她在壓抑女性的社會泥潭里的掙扎。在研究《簡·愛》時,我們不僅應該揭示這部小說的女權主義意蘊,而且應該將其放入本文所揭示的種種矛盾和悖論之中進行省思:它依然接受了維多利亞價值觀對女性的定義,即女性存在的意義依靠其丈夫而得以體現(xiàn),女性生命的意義在于其對家庭事務的投入和對其丈夫的利益的關注。對《簡·愛》中女權主義的局限性進行省思,不僅有助于我們從一個更加全面的視角來了解英國早期女權主義思想,而且對于我們觀照西方女權主義思潮的歷史流變也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