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的創(chuàng)作思維、主題意蘊(yùn)與結(jié)構(gòu)形態(tài)
——從爭議不休的第三幕談起
陳詠芹
《日出》問世之后,天津《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先后兩次發(fā)表由十五位文壇知名人士參與的集體評論。他們主要從社會(huì)劇的現(xiàn)實(shí)批判性與人物群像塑造的角度贊譽(yù)其思想與藝術(shù)成就,也有人以結(jié)構(gòu)有機(jī)性完整性的原則,質(zhì)疑第三幕存在的合理性。在《日出》的首次演出中,導(dǎo)演歐陽予倩也刪去了實(shí)在難以處理的第三幕。對評論者的質(zhì)疑和導(dǎo)演的刪改,曹禺迅速地做出了回應(yīng)。他覺得自己“執(zhí)筆時(shí)的苦心”沒人理解,感到非常委屈,甚至有被“殘忍”地“挖心”之感①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頁。。他說:“《日出》不演則已,演了,第三幕無論如何應(yīng)該有。挖了它,等于挖去《日出》的心臟,任它慘亡。”②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頁。在這之后,對《日出》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非議者有之,贊譽(yù)者亦有之;總體而言,贊譽(yù)者多于非議者但卻無法說服非議者。曹禺晚年也仍然堅(jiān)信第三幕對呈現(xiàn)劇作主題意蘊(yùn)的必要性,堅(jiān)信第三幕與其他三幕之間在結(jié)構(gòu)藝術(shù)上的協(xié)調(diào)性。③田本相、劉一軍:《曹禺訪談錄》,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頁。今天看來,評論者、導(dǎo)演與劇作者曹禺之間的分歧,可能正是我們重新解讀《日出》的出發(fā)點(diǎn)。
一
曹禺并不是不懂戲劇結(jié)構(gòu)藝術(shù),恰恰相反,在中國現(xiàn)代話劇作家中恐怕沒有人能夠比曹禺更熟悉歐洲近代以來寫實(shí)戲劇的了。曹禺上中學(xué)時(shí),就在南開新劇團(tuán)寫戲、導(dǎo)戲、演戲。研究過歐洲近代寫實(shí)戲劇的張彭春不僅親自指導(dǎo)他,而且還贈(zèng)送他一套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曹禺通讀了這套沉甸甸的全集,并且從易卜生的劇作中體悟到寫實(shí)戲劇的編劇原則與技巧。①曹禺晚年回憶說:“我是咬著牙把易卜生全集讀完的”,“他的構(gòu)思是那么精美巧妙,結(jié)構(gòu)是那么精細(xì)嚴(yán)謹(jǐn),這些都使我迷戀忘返。尤其是他的簡潔,簡直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沒有任何多余的與戲劇沖突無關(guān)的筆墨。真是大開了眼界!這些為我后來從事戲劇創(chuàng)作奠定了藝術(shù)基礎(chǔ)”,“我讀完了他的劇作,懂得了許多戲劇方面的知識(shí)和技巧,懂得了戲的結(jié)構(gòu)奧妙,以及結(jié)構(gòu)對于一出戲的作用。它在戲里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田本相、劉一軍:《曹禺訪談錄》,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頁。曹禺也并不是不重視戲劇的結(jié)構(gòu)藝術(shù)。他上清華大學(xué)時(shí),系統(tǒng)閱讀了自古希臘至現(xiàn)代的西方戲劇名著,修過有關(guān)歐美戲劇理論與劇作的課程,并且“真正研究戲的結(jié)構(gòu),對結(jié)構(gòu)發(fā)生興趣”②田本相、劉一軍:《曹禺訪談錄》,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頁。。由于具有如此堅(jiān)實(shí)的戲劇藝術(shù)基礎(chǔ),曹禺當(dāng)然十分清楚戲劇的結(jié)構(gòu)藝術(shù)在安排情節(jié)、凸顯主題和塑造人物等方面的關(guān)鍵性作用。《雷雨》的創(chuàng)作就是最有力的證據(jù)。曹禺既然對編劇藝術(shù)有著如此充分的準(zhǔn)備和如此清晰的認(rèn)識(shí),他難道在《日出》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沒有考慮到第三幕的生活場面與人物行動(dòng)會(huì)和全劇的生活場面與人物行動(dòng)之間存在著難以解決的不協(xié)調(diào)性嗎?那么,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讓他對第三幕的內(nèi)容如此看重?既然不肯放棄第三幕,他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又是運(yùn)用什么方法將其統(tǒng)一到全劇的整體結(jié)構(gòu)之中的?他的預(yù)想能夠完全實(shí)現(xiàn)嗎?
讓我們先從《日出》的創(chuàng)作心境與創(chuàng)作動(dòng)機(jī)談起。曹禺在寫完《雷雨》之后,就離開清華園,先到保定擔(dān)任中學(xué)教師,不久重返清華讀研究生,后來又到天津執(zhí)教于河北女子師范學(xué)院,最終由寧靜的書齋走向光怪陸離的社會(huì)。其間,曹禺目睹了許多他“至死也不會(huì)忘卻”的如同“夢魘一般的可怖的人事”,并因此激發(fā)了對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不可抑制的憤懣之情。③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0頁。《日出》就是青年曹禺批判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宣泄?jié)M腔怒火的產(chǎn)物。
從中外文學(xué)史與戲劇史上看,批判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作品,其思想的深刻性應(yīng)該來源于作者對生活認(rèn)識(shí)的深刻性,其藝術(shù)的完整性應(yīng)該來源于作者尋找到藝術(shù)地認(rèn)識(shí)生活、表現(xiàn)生活與評價(jià)生活的契合點(diǎn)。曹禺創(chuàng)作《日出》時(shí),所憑借的是他對于生活現(xiàn)象的觀察與感受,是他如同創(chuàng)作《雷雨》一樣的不可遏止的創(chuàng)作沖動(dòng)。正因?yàn)槿绱?他這時(shí)的創(chuàng)作思維,是以生動(dòng)而感性的社會(huì)形態(tài)為基本的思維指向,是以展覽群像與生活橫斷面為具體的聚焦點(diǎn),是以豐沛而強(qiáng)烈的情感活動(dòng)為主要的推動(dòng)力量。根據(jù)曹禺自述:“《日出》希望獻(xiàn)與觀眾的應(yīng)是一個(gè)鮮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里也應(yīng)為這‘損不足以奉有余’的社會(huì)形態(tài)。”④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頁。這就是說,他創(chuàng)作思維的指向是用舞臺(tái)藝術(shù)的形式,立體地呈現(xiàn)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北方半殖民地大都市社會(huì)的生活面貌。對于自己所觀察到的社會(huì)形態(tài),曹禺并沒有進(jìn)行如同茅盾創(chuàng)作《子夜》時(shí)所注重的從政治經(jīng)濟(jì)層面展開的社會(huì)分析,而是矚目于鮮明生動(dòng)、具體可感的印象。在這種思維指向的引導(dǎo)下,曹禺將半殖民地都市社會(huì)形形色色的“有余者”與“不足者”作為聚焦點(diǎn),并且通過前者爾虞我詐、兇殘狠毒、荒淫無恥、醉生夢死和后者被損害被侮辱的生活場面,編織成生活的橫斷面。這就是曹禺自己所說的,他是在“用片段的方法寫起《日出》”⑤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頁。的原因。很顯然,上述創(chuàng)作思維指向與創(chuàng)作思維聚焦點(diǎn),都是局限于生活形態(tài)的外顯層面,局限于曹禺對生活認(rèn)識(shí)的感性階段。這種缺乏縱深感的創(chuàng)作思維,對于生活面不廣、生活容量較小的社會(huì)劇來說,當(dāng)然問題不大;但是,對于《日出》這種試圖包羅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半殖民地都市社會(huì)高級(jí)飯店與三等妓院這兩種類型的生活場面的劇作來說,就會(huì)面臨后續(xù)創(chuàng)作過程中如何統(tǒng)一那些圍繞著由不同人物的活動(dòng)而構(gòu)成的生活橫斷面的問題。青年曹禺并不具備創(chuàng)作這種社會(huì)劇的思維能力。不過,如果曹禺能夠從容構(gòu)思、反復(fù)醞釀,當(dāng)然能夠或多或少地彌補(bǔ)自己這種思維能力的缺陷,至少能夠在《日出》的結(jié)構(gòu)形態(tài)上做到完整統(tǒng)一。但是,年輕氣盛、血?dú)夥絼偟牟茇畬?shí)在是無法抑制自己對“有余者”的憎恨,無法抑制自己對于“不足者”同情。曹禺說:那時(shí),“一件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實(shí),利刃似的刺進(jìn)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憤怒”,“這些失眠的夜晚,困獸似地在一間籠子大的屋子里踱過來,拖過去,睜著一雙布滿了紅絲的眼睛,絕望地楞著神。看看低壓在頭上炙黑的屋頂,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進(jìn)了墳?zāi)?沒有一絲動(dòng)靜。我捺不住了,在情緒爆發(fā)的當(dāng)中,我曾經(jīng)摔碎了許多可紀(jì)念的東西”,“我絕望地嘶嘎著,那時(shí)我愿意一切都?xì)缌税伞?“沖到我的口上,是……一句切齒的誓言:‘時(shí)日曷喪,予及汝偕亡!’”①上述引文參見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382頁。他迫切需要盡快地將自己猶如火山爆發(fā)般的情緒宣泄出來,他要向“蟠據(jù)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魎”呼喊“‘你們的末日到了!’”②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頁。這非常清楚地表明,曹禺來不及充分醞釀和反復(fù)思考,來不及探尋高級(jí)飯店與三等妓院這兩類生活橫斷面的內(nèi)部聯(lián)系,來不及考慮如何將內(nèi)容與結(jié)構(gòu)有機(jī)地統(tǒng)一起來,就開始了《日出》的創(chuàng)作。正是這種豐沛而強(qiáng)烈的情感活動(dòng),伴隨著《日出》的整個(gè)創(chuàng)作過程,并且成為劇情進(jìn)展的主要推動(dòng)力量。總之,曹禺創(chuàng)作《日出》時(shí),是以熾烈的情感推動(dòng)著他去呈現(xiàn)由群像而構(gòu)成的生活橫斷面,去呈現(xiàn)生活的外顯形態(tài)。這種創(chuàng)作思維狀態(tài),決定了曹禺對《日出》主題意蘊(yùn)的提煉與藝術(shù)結(jié)構(gòu)的營造。
二
在曹禺的創(chuàng)作歷程中,《日出》意味著由《雷雨》那樣的家庭劇轉(zhuǎn)向社會(huì)劇;由對人類命運(yùn)悲劇的思索,轉(zhuǎn)向?qū)Ρ唤疱X拜物教統(tǒng)治的社會(huì)世相的批判;由對人類無法突破的自由與必然矛盾的冷靜表現(xiàn),轉(zhuǎn)向?qū)淳嵊诙际猩鐣?huì)里那些魑魅魍魎們憤懣之情的宣泄。新的生活內(nèi)容的轉(zhuǎn)換,必然要求對于這些新生活內(nèi)容的把握。如果說曹禺對《雷雨》主題的認(rèn)識(shí)是觀念性的,那么他對《日出》主題的認(rèn)識(shí),就應(yīng)該隨著生活內(nèi)容的轉(zhuǎn)換而變?yōu)楝F(xiàn)實(shí)性的。《雷雨》的命運(yùn)悲劇的觀念有古希臘以來歐洲悲劇作品的演繹和歷代悲劇哲學(xué)家的闡發(fā)作為思維依據(jù)。因此,無論如何,曹禺在《雷雨》中對發(fā)生在周、魯兩個(gè)家庭之間命運(yùn)悲劇的整體認(rèn)識(shí)與深刻把握,都不會(huì)遇到太大的困難。作為劇作家,曹禺創(chuàng)作的思維指向,實(shí)際上就是尋求能夠有效地包容這種悲劇觀念的故事情節(jié)與結(jié)構(gòu)框架。但是,創(chuàng)作《日出》時(shí),曹禺的思維世界里就沒有這種現(xiàn)成的觀念了。他不僅需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生活,還需要用自己的大腦去認(rèn)識(shí)生活、評價(jià)生活。當(dāng)面對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北方大都市社會(huì)形形色色人物與光怪陸離世相的時(shí)候,青年曹禺還不具備對其進(jìn)行整體認(rèn)識(shí)的思維條件,更談不上深刻把握了。
熟悉曹禺生平的人,都會(huì)注意到,他在清華大學(xué)讀書的時(shí)候,就與處于隱蔽狀態(tài)中的共產(chǎn)黨員同學(xué)有過交往,也開始接觸到如《資本論》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清華學(xué)生運(yùn)動(dòng)和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文藝運(yùn)動(dòng)也不可能不會(huì)對他產(chǎn)生影響。從那時(shí)起,曹禺就逐漸形成了對現(xiàn)時(shí)代社會(huì)問題的看法,并開始形成了朦朧的政治意識(shí)。但是,曹禺的理論素養(yǎng)不足,再加上他本來也不擅長理論思維,他對《資本論》這類社會(huì)科學(xué)著作只能是淺嘗輒止,沒有能力真正讀懂。曹禺晚年回憶說,他在清華大學(xué)期間“讀過幾章《資本論》,可是沒有看懂”。大革命失敗后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使他“開始憎恨國民黨,同情共產(chǎn)黨”。他說:“我相信這個(gè)社會(huì)制度必須粉碎,這在我,在我們一代中的許許多多人,都是明確的。”③烏韋·克勞特:《戲劇家曹禺》,胡光、王明杰譯,《人物》1981年第4期。理論素養(yǎng)與理論思維能力的局限,使得青年曹禺對社會(huì)現(xiàn)象的不滿、對人世不公的不平,只能停留在相對表顯的狀態(tài)和感性的情緒層面上。他對于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北方的都市社會(huì),根本不可能像前輩作家茅盾對稍早幾年的上海都市社會(huì)那樣,進(jìn)行縝密的理性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分析。他在真正進(jìn)入創(chuàng)作狀態(tài)之前,甚至在后續(xù)具體的創(chuàng)作過程之中,對于即將要呈現(xiàn)的都市生活的本質(zhì),對于各個(gè)生活橫斷面內(nèi)部的有機(jī)聯(lián)系,均缺乏深刻的認(rèn)識(shí)。如果揚(yáng)長避短,曹禺就得盡量縮減《日出》的生活容量,他只要寫高級(jí)飯店里的生活場面與人物動(dòng)作,也就足以呈現(xiàn)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北方半殖民地都市社會(huì)之一角了。但是曹禺并不滿足于這些。他要把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完完全全地呈現(xiàn)出來。他看到了聚集在高級(jí)飯店華麗休息室里的交際花、金融資本家、富孀及其面首,看到了由底層往上爬的銀行職員,看到了欺軟怕硬的流氓;他還看到了三等妓院里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女性。曹禺要在自己的劇作中呈現(xiàn)這兩種類型的生活場面,要通過對這兩種類型的生活場面的完整呈現(xiàn)來宣泄自己的滿腔憤懣。
那么,從這兩種類型的生活場面中,能夠發(fā)現(xiàn)什么樣的共同性?又能夠提煉出什么樣的主題?曹禺沒有能力從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角度對社會(huì)肌體進(jìn)行整體的理性的分析解剖,而是從上古時(shí)期的老子那里尋找到了現(xiàn)成的答案。《道德經(jīng)》七十七章云:“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bǔ)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bǔ)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應(yīng)該說,《道德經(jīng)》的這段話照亮了曹禺的思維世界,他覺得這就是能夠統(tǒng)攝上述兩種生活場面的總綱和要領(lǐng)。沿著這種思路,他把陳白露周圍的大部分人物視為有余者,把陳白露、小東西、翠喜等人視為不足者。也是沿著這種思路,他還認(rèn)識(shí)到在金錢拜物教統(tǒng)治下的都市社會(huì),違背自然界的規(guī)律,有余者無休無止地掠奪不足者,這種逆天道而行之的社會(huì),再也沒有繼續(xù)存在的任何理由了。他在《〈日出〉跋》里說:“果若讀完了《日出》,有人肯憤然地疑問一下:為什么有許多人要過這種‘鬼’似的生活呢?難道這世界必須這樣維持下去嗎?什么原因造成這不公平的禽獸世界?是不是這局面應(yīng)該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這樣問兩次,那已經(jīng)是超過了一個(gè)作者的奢望了。”①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頁。要徹底毀滅這個(gè)社會(huì),這是青年曹禺對現(xiàn)實(shí)的無情詛咒。正是出于這種詛咒,曹禺重點(diǎn)展示了陳白露內(nèi)心的矛盾:一方面是她未曾泯滅的純潔天性,另一方面是她無法逃脫金錢拜物教的控制;她只能以自殺來解脫由來已久并時(shí)時(shí)刻刻在折磨自己的精神痛苦。不僅如此,曹禺像當(dāng)年許許多多血?dú)夥絼偟那嗄耆艘粯?除了詛咒現(xiàn)實(shí),還憧憬未來。他將陳白露與建筑工人進(jìn)行對比,表明自己對新興階級(jí)的希望。在第二幕的幕景說明中,曹禺寫傍晚時(shí)分,陳白露所處的高級(jí)飯店華麗休息室里黯淡無光,但“由窗戶望出,外面反映著一片夕陽”,“窗外很整齊地傳進(jìn)來小工們打地基的樁歌,由近漸遠(yuǎn),摻雜著漸移漸遠(yuǎn)多少人的步伐和沉重的石塊落地的悶塞聲音”,“這種聲音幾乎一直在這一幕從頭到尾,如一群含著憤怒的冤魂,抑郁暗塞地亨著,充滿了警戒和恐嚇。他們用一種原始的語言來唱出他們的憂郁,痛苦,悲哀和奮斗中的嚴(yán)肅”。到了第四幕,寫陳白露告別人世之前低聲吟哦:“太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就在此時(shí),室外建造大樓的工人們“早聚集在一起,迎著陽光由遠(yuǎn)處‘哼哼唷,哼哼唷’地又以整齊嚴(yán)肅的步伐邁到樓前”。他們“高亢而宏壯地”唱著夯歌:“日出東來,滿天大紅”,“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聲音傳到觀眾的耳里是一個(gè)大生命浩浩蕩蕩地向前推,向前進(jìn),洋洋溢溢地充滿了宇宙”。接下來,就是“屋內(nèi)漸漸暗澹,窗外更光明起來”。從上述的對比性描寫中,我們看到曹禺是在以建筑工人的形象、打夯歌和日出時(shí)分滿天的朝霞來象征他朦朧的社會(huì)理想:沒落階級(jí)必然沒落,新興階級(jí)已經(jīng)開始展現(xiàn)蓬勃生機(jī),未來是屬于勞動(dòng)者的。②參見拙文《作家政治思維定勢與話劇結(jié)構(gòu)形態(tài)》,《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1996年第1期。他在構(gòu)思時(shí)是把憧憬未來作為《日出》的副主題,或者至少說是把勞動(dòng)創(chuàng)造未來作為詛咒現(xiàn)實(shí)主題的必要的補(bǔ)充。既然“太陽”不屬于陳白露及其周邊的人物,那么它鮮紅的光芒應(yīng)該照耀著建造大樓的勞動(dòng)者。當(dāng)然,由于不熟悉工人階級(jí),也由于考慮到避免將來發(fā)表與演出時(shí)遭到政治審查的刁難,曹禺對未來的憧憬,僅僅是通過上述象征的藝術(shù)方法暗示出來的,《日出》藝術(shù)表現(xiàn)的重心或者說它的主題意蘊(yùn)仍然局限于對“損不足以奉有余”的半殖民地都市社會(huì)的憤怒詛咒。
三
有了生活內(nèi)容和主題,就有了將其藝術(shù)地表現(xiàn)出來的思維中心,就有了全劇通盤布局的基礎(chǔ)。我們現(xiàn)在可以考察曹禺是用什么樣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來實(shí)現(xiàn)其創(chuàng)作意圖的了。
如果曹禺形成了對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北方半殖民地都市生活的整體認(rèn)識(shí)與深刻把握,以他對于西方寫實(shí)戲劇編劇藝術(shù)的稔熟,他完全能夠營造一個(gè)契合生活場面并且凸顯主題意蘊(yùn)的結(jié)構(gòu)。戲劇史已經(jīng)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正是由于時(shí)間與空間的限制,戲劇作家才得以表現(xiàn)其思想與藝術(shù)的創(chuàng)造才華。《雷雨》就是作為杰出劇作家的逞才之作。它的鎖閉式結(jié)構(gòu),有利于包容周、魯兩家三十年來的愛恨情仇,有利于凸顯人類無法擺脫命運(yùn)悲劇的主題意蘊(yùn),有利于周樸園、蘩漪、侍萍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人們普遍認(rèn)為《雷雨》的主題意蘊(yùn)與結(jié)構(gòu)形態(tài),達(dá)到了高度的契合。但是,對《日出》結(jié)構(gòu)的評價(jià)卻出現(xiàn)了分歧。早在《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于1936年12月27日和1937年1月1日所登載的兩次“集體批評”中,謝迪克和朱光潛就指出《日出》結(jié)構(gòu)的缺陷問題。時(shí)任燕京大學(xué)西洋文學(xué)系主任的英國學(xué)者謝迪克認(rèn)為:“它主要的缺憾是結(jié)構(gòu)的欠統(tǒng)一”,第三幕“僅是一個(gè)插曲,一個(gè)穿插,如果刪掉,與全劇的一貫毫無損失裂痕”。①謝迪克:《一個(gè)異邦人的意見》,天津《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第273期,1936年12月27日。朱光潛認(rèn)為,將第一幕后部以及第三幕全部“完全刪去,全劇不但沒有損失,而且布局更較緊湊”②孟實(shí)(朱光潛):《“舍不得分手”》,天津《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第276期,1937年1月1日。。果然,當(dāng)歐陽予倩等人將《日出》搬上舞臺(tái)時(shí),就真的刪去了第三幕。對于謝迪克和朱光潛的評論,曹禺的反應(yīng)是非常激烈的。他很快就寫出長篇答辯文章,為自己鳴冤叫屈。③該文原題《我怎樣寫〈日出〉》,初載天津《大公報(bào)》“文藝”副刊第304期,1937年2月28日出版;隨后,該文作為《跋》收入1937年3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日出》單行本的第4版。那么,我們怎么看待第三幕與全劇總體布局的關(guān)系呢?
《日出》的第一、第二和第四幕,呈現(xiàn)的是出沒在北方某大都市高級(jí)飯店華麗休息室里各色人等的生活場面。曹禺曾經(jīng)說:“《日出》里沒有絕對的主要?jiǎng)幼?也沒有絕對的主要人物。”④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頁。也許曹禺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真的是這么想并且實(shí)際上也是這么實(shí)施的,但是我們從他已經(jīng)完成的作品中,還是很容易找出該劇的貫穿動(dòng)作與貫穿人物。《日出》的貫穿動(dòng)作是上層社會(huì)因金錢拜物教而造成的爾虞我詐、道德淪喪的各種行徑,其貫穿人物則是高級(jí)交際花陳白露,甚至還可以說陳白露的精神危機(jī)(內(nèi)心沖突)實(shí)際上就是劇作結(jié)構(gòu)的中心。⑤曹禺晚年也承認(rèn)“陳白露是主線,靠她把一切勾勒網(wǎng)結(jié)起來了”。田本相、劉一軍:《曹禺訪談錄》,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頁。第一、第二、第四幕,就是圍繞著上述貫穿動(dòng)作與貫穿人物而展開的。從人物設(shè)計(jì)方面看,出沒于這三幕中的方達(dá)生、小東西、潘月亭、李石清、黃省三、張喬治、顧八奶奶、胡四等人都是在陳白露所租住的高級(jí)飯店套房的華麗休息室里亮相的。金八的嘍啰們也是在這里搜查小東西的。他們都是圍繞著陳白露出場的。這就意味著陳白露其實(shí)就是這三幕戲劇的貫穿人物。從劇情設(shè)計(jì)方面看,方達(dá)生要把陳白露從高級(jí)妓女的處境中拉出來,后來也要把小東西從金八的魔掌中解救出來,這是一股要擺脫金錢拜物教控制的力量;其他人物則匯成了沉溺于金錢拜物教的力量。這就是說,高級(jí)飯店的生活場面中,對金錢拜物教的態(tài)度,構(gòu)成了這三幕戲劇的貫穿動(dòng)作。
然而,第三幕呈現(xiàn)的卻是寶和下處被侮辱被損害的低級(jí)妓女的生活場面,是翠喜有著“一顆金子似的心”,是她“同時(shí)染有在那地獄下生活各種壞習(xí)慣”,“是她那樣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幼,和無意中流露出來對那更無告者的溫暖的關(guān)心”。⑥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391頁。這一幕,由于生活場面的變化與人物的更替,全劇的貫穿動(dòng)作被中斷,貫穿人物也缺席了。就貫穿人物陳白露而言,第三幕對深化她的內(nèi)心沖突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有學(xué)者認(rèn)為第三幕里,陳白露雖未出場,但卻得到翠喜這個(gè)形象的“映襯和補(bǔ)充”,“圍繞著翠喜生活的地獄環(huán)境,不但暗示陳白露和翠喜實(shí)際上處于同樣的賣淫地位,也隱喻了陳白露悲劇的結(jié)局。……在第三幕中陳白露沒有出場卻像她的悲劇在向前發(fā)展,因之,當(dāng)陳白露帶著憂郁的姿態(tài)在第三幕出現(xiàn)時(shí),我們并不感到突然。陳白露的形象為翠喜的形象豐富著,滲透著”。①田本相:《曹禺劇作論》,中國戲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121頁。這種解釋,從戲劇文學(xué)劇本欣賞者的角度來看,的確極有見地,因?yàn)樗l(fā)現(xiàn)并指出了欣賞者心目中的第三幕與第四幕生活內(nèi)容的深層次聯(lián)系:即陳白露大紅大紫的今天正是現(xiàn)已人老珠黃的翠喜的過去。可是,這種解釋卻沒有從劇作結(jié)構(gòu)的中心人物陳白露本人的動(dòng)作線著眼。《日出》并沒有寫到陳白露與翠喜之間有任何的交集。對陳白露來說,其最終由玩世不恭中清醒過來的諸種因素中,并沒有第三幕所揭示的因素:一是陳白露并沒有到過寶和下處,沒有目睹翠喜現(xiàn)在的生活境況,甚至并不曾聽說過翠喜其人;二是小東西的結(jié)局如何,作為劇中人的陳白露并不清楚,就連特地趕到寶和下處的方達(dá)生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線索。就寫實(shí)戲劇的結(jié)構(gòu)藝術(shù)而言,第三幕的生活場面、人物命運(yùn),不僅與前兩幕的生活場面、陳白露的動(dòng)作線之間沒有建立起任何內(nèi)在的或外在的聯(lián)系,而且也無助于第四幕對加速陳白露精神崩潰過程的有力揭示。這就是說,高級(jí)飯店的華麗休息室與人間地獄般的寶和下處這兩類生活場面之間,第三幕的人物動(dòng)作線與其他三幕的人物動(dòng)作線之間,皆缺少互相聯(lián)接的最基本的契合點(diǎn)。②參見拙文《作家政治思維定勢與話劇結(jié)構(gòu)形態(tài)》,《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1996年第1期。第三幕的人物動(dòng)作線,以結(jié)構(gòu)藝術(shù)的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確實(shí)是游離于全劇總的人物動(dòng)作線的。
至此,我們還得追問,曹禺為什么對第三幕的內(nèi)容如此看重,極力為它存在的藝術(shù)必要性進(jìn)行辯護(hù)呢?我們認(rèn)為有四個(gè)方面的原因。其一,就藝術(shù)功能而言,曹禺認(rèn)為第三幕對被侮辱被損害的社會(huì)底層女性生活場面的展示,能夠表達(dá)自己對半殖民地都市社會(huì)的憤怒,能夠表達(dá)自己出之于朦朧的階級(jí)對立意識(shí)的政治態(tài)度。③參見拙文《作家政治思維定勢與話劇結(jié)構(gòu)形態(tài)》,《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1996年第1期。曹禺后來回憶說:“更為重要更為迫切的,是我要暴露那個(gè)地獄般的妓女生活。這一幕,是《日出》對那個(gè)罪惡社會(huì)抨擊的支點(diǎn),也是我的感情的支點(diǎn)。”④田本相、劉一軍:《曹禺訪談錄》,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頁。這是出之于感情抒發(fā)和政治批判的考慮。其二,就結(jié)構(gòu)形態(tài)而言,曹禺認(rèn)為第三幕生活場面與另外三幕生活場面之間,可以用“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的主題意蘊(yùn)來統(tǒng)一。他認(rèn)為這個(gè)主題可以貫穿半殖民地大都市上層社會(huì)與底層社會(huì)的兩種生活形態(tài)。曹禺說:“我想……用多少人生的零碎來闡明一個(gè)觀念。如若中間有一點(diǎn)我們所謂的‘結(jié)構(gòu)’,那‘結(jié)構(gòu)’的聯(lián)系正是那個(gè)基本觀念,即第一段引文內(nèi)‘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所謂‘結(jié)構(gòu)統(tǒng)一’也就藏在這一句話里。”⑤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頁。其三,曹禺自己堅(jiān)持認(rèn)為第三幕也有出沒于其他三幕中的幾個(gè)人物來貫穿,而這其實(shí)就是第三幕與其他三幕之間在結(jié)構(gòu)上的聯(lián)系。曹禺晚年在回答研究者的提問時(shí)說:“第三幕陳白露沒有出場,可是(在這一幕出場的——引者加)方達(dá)生、小東西、胡四和陳白露有關(guān)系。”⑥田本相、劉一軍:《曹禺訪談錄》,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頁。其四,為了寫好第三幕,曹禺特別到底層社會(huì)搜集素材,在那里,他遭受許多“誤會(huì)”“折磨”“傷害”,甚至“侮辱”。這一幕的生活是他“經(jīng)歷過而寫出來的”,這些生活中的“每一個(gè)音都帶著強(qiáng)烈地方的情緒”,“充滿了生命”與“活人的氣息”。⑦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392頁。他不情愿自己的心血付諸東流。出于上述原因,曹禺特別強(qiáng)調(diào):“如若為著某種原因,必須支解這個(gè)劇本,才能把一些罪惡暴露在觀眾面前,那么就斫掉其余的三幕吧。請演出的人們?nèi)菰S這幫‘可憐的動(dòng)物’在飽食暖衣,有余暇能看戲的先生們面前哀訴一下,使人們睜開自己昏聵的眼,想想人把人逼到什么田地。”⑧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頁。
一般來說,創(chuàng)作構(gòu)想與實(shí)際的創(chuàng)作成果之間,肯定是存在差距的。曹禺想從主題意蘊(yùn)方面來統(tǒng)攝全劇,可是他在藝術(shù)上沒有真正實(shí)現(xiàn)這個(gè)設(shè)想。如果僅僅將《日出》視為“案頭”文學(xué),通過閱讀活動(dòng)中的聯(lián)想與想象,對于閱讀經(jīng)驗(yàn)豐富、閱讀能力較強(qiáng)的欣賞者來說,或許可以用主題意蘊(yùn)來激發(fā)聯(lián)想與想象,在他們的腦海里聯(lián)結(jié)第三幕與其他三幕的生活場面;但是話劇是以動(dòng)作為主要表現(xiàn)形態(tài)的舞臺(tái)藝術(shù),必須要在舞臺(tái)上最終完成其藝術(shù)生命。①劉艷的《“案頭”文學(xué)與“場上”表演——重論〈雷雨〉的序幕與尾聲》,首次從曹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思維定勢的視角,對這個(gè)問題進(jìn)行了透徹的分析。該文發(fā)表于《南大戲劇論叢》2012年第2期。因此,《日出》的主題意蘊(yùn)必須要通過動(dòng)作在舞臺(tái)上呈現(xiàn)出來。當(dāng)全劇的貫穿人物陳白露在第三幕缺席,當(dāng)全劇的貫穿動(dòng)作在第三幕中斷,怎么可能讓劇場里的絕大部分觀眾即時(shí)地觀察到感受到思索到這一幕與其他三幕之間的有機(jī)聯(lián)系呢?因此,我們的結(jié)論是,《日出》的主題意蘊(yùn)并沒有通過其結(jié)構(gòu)藝術(shù)得到完整的呈現(xiàn)。這就是說,曹禺的創(chuàng)作構(gòu)想沒有能夠在創(chuàng)作實(shí)踐中完全落實(shí)。僅僅就結(jié)構(gòu)藝術(shù)而言,曹禺對第三幕的珍愛,是出之于他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的思維習(xí)慣。研究者為第三幕存在的合理性辯護(hù),則是誤將閱讀活動(dòng)置換成觀賞活動(dòng)了。這也可以從《日出》演出史上導(dǎo)演的二度創(chuàng)作中得到反證。
四
其實(shí),曹禺本人也多少透露了自己創(chuàng)作《日出》時(shí)的畏難情緒。他在為第三幕辯護(hù)時(shí)說:“因?yàn)樘暨x的題材比較龐大,用幾件故事做線索,一兩個(gè)人物為中心也自然比較煩難。”②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頁。他還說“《日出》并沒有寫全,確實(shí)需要許多開展”③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頁。。他甚至說他像寫《雷雨》那樣,也把“最主要的角色”即“那象征著光明的人們”給“疏忽了”④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5頁。。他還“故意叫金八不露面,令他無影無蹤卻時(shí)時(shí)操縱場面上的人物”⑤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頁。。面對比較大型的題材,面對比較復(fù)雜的社會(huì)性沖突,曹禺覺得難以按照常規(guī)來駕馭,來表現(xiàn)。這恐怕就是他在結(jié)構(gòu)藝術(shù)上,放棄劇作“起承轉(zhuǎn)合”方法,轉(zhuǎn)而改用“橫斷面的描寫”⑥曹禺:《〈日出〉跋》,《曹禺全集》第1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頁。的原因吧。
《日出》的取材范圍,對青年曹禺來說,算是比較寬廣的了。他剛剛寫完《雷雨》不久,當(dāng)然想在新的《日出》中,實(shí)現(xiàn)對自我的超越。《雷雨》的生活場景局限于家庭,《日出》的生活場景擴(kuò)大到社會(huì),單單從表現(xiàn)的生活面來說,當(dāng)然是一種突破。一般來說,社會(huì)劇的創(chuàng)作要求作家對社會(huì)的認(rèn)識(shí)越全面越深刻越好。20世紀(jì)30年代中期北方都市社會(huì)是半殖民地社會(huì),帝國主義試圖通過它的代理人買辦金融資本家控制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與文化,并且因此造就了畸形的社會(huì)形態(tài)。如果曹禺具備這種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視野,當(dāng)然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在《日出》里所呈現(xiàn)的各種生活橫斷面之間內(nèi)部的本質(zhì)的聯(lián)系。不過,我們不應(yīng)該像周揚(yáng)等左翼評論家那樣對曹禺提出這樣的要求⑦周揚(yáng)認(rèn)為:“歷史舞臺(tái)上互相沖突的兩種主要的力量在《日出》里面沒有登場。”其中,作為黑暗勢力代表的“金八留在我們腦里的只是一個(gè)淡淡的影子,我們看不出他的作為操縱市場的金融資本家的特色,而且他的后面似乎還缺少一件東西——帝國主義。”(周揚(yáng):《論〈雷雨〉和〈日出〉》,《光明》1937年第2卷第8號(hào),1937年3月出版)周揚(yáng)的論述,是從建構(gòu)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文學(xué)的理論預(yù)設(shè)出發(fā)的,而那時(shí)的曹禺并不具備這種創(chuàng)作素質(zhì)。,因?yàn)檫@種要求是更高的要求;即使是在優(yōu)秀的作家中,能夠達(dá)到這種要求的,也只能是像茅盾等極少數(shù)兼具理論思維能力與社會(huì)科學(xué)知識(shí)的佼佼者。對曹禺這種情感型作家而言,創(chuàng)作思維是以形象思維為主,只要能夠準(zhǔn)確地表現(xiàn)生活的外部現(xiàn)象就可以了;因?yàn)閺纳鷦?dòng)直觀的生活現(xiàn)象出發(fā),也可以逼近或直接抵達(dá)生活的本質(zhì)。作家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程中能夠?qū)ι畹谋举|(zhì)進(jìn)行科學(xué)的理性的分析,當(dāng)然是求之不得的;但是當(dāng)他缺乏這種思維能力時(shí),我們也不應(yīng)該強(qiáng)求。與社會(huì)科學(xué)相比,藝術(shù)當(dāng)然具有自己把握世界的方式,當(dāng)然具有自己形象思維的特殊性。明白這個(gè)道理,我們就不會(huì)對理論思維能力欠缺、社會(huì)科學(xué)知識(shí)薄弱的青年曹禺提出過高的要求了。我們只能從表現(xiàn)社會(huì)現(xiàn)象的藝術(shù)完整性方面,對《日出》的結(jié)構(gòu)藝術(shù)提出要求。
我們已經(jīng)論述過《日出》的第三幕與作為劇作主體部分的其他三幕之間的游離關(guān)系。我們也指出過高級(jí)飯店與三等妓院屬于兩種不同類型的生活場面,曹禺沒有能夠把這兩種不同類型的生活場面有機(jī)地聯(lián)結(jié)起來。現(xiàn)在的問題是,這兩種類型的生活場面,是具體的,是生動(dòng)的,除了用“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這個(gè)比較空泛的觀念來整合之外,還有沒有可能尋找到其他的途徑將其具體化?比如,有沒有可能用全劇貫穿人物陳白露的動(dòng)作線來統(tǒng)攝起來呢?當(dāng)然是可能的。第三幕寫方達(dá)生到寶和下處尋找小東西。其實(shí),這個(gè)情節(jié)可以適當(dāng)改動(dòng),可以讓陳白露和方達(dá)生一起來。既然陳白露那么關(guān)心愛護(hù)小東西,她完全有理由像第二幕結(jié)尾那樣,讓方達(dá)生陪她一起外出尋找。當(dāng)她和方達(dá)生尋找到寶和下處時(shí),就可以與翠喜發(fā)生交集,就可以了解翠喜過去與現(xiàn)在的情況。如此處理,不僅陳白露的動(dòng)作線(無論是外部的還是心理的)能夠延續(xù),其精神危機(jī)能夠得到深化,而且高級(jí)飯店與低級(jí)妓院這兩種類型的生活場面之間,也會(huì)生成內(nèi)在的有機(jī)的聯(lián)系。半個(gè)世紀(jì)之后的1985年,曹禺與女兒萬方合作將《日出》改編成電影文學(xué)劇本,就是這樣修改的。這種情節(jié)上的變動(dòng),至少可以從結(jié)構(gòu)藝術(shù)上將第三幕與全劇統(tǒng)一起來。如果當(dāng)年創(chuàng)作話劇原作時(shí),曹禺能夠這樣設(shè)計(jì),它的兩類生活場面、兩種情節(jié)線索、兩條人物動(dòng)作線之間就會(huì)因此而生成內(nèi)在的有機(jī)的聯(lián)系。它的“人像展覽式結(jié)構(gòu)”的每一幕,也會(huì)因此而融會(huì)貫通,生機(jī)盎然。
顯然,1935至1936年的曹禺,并沒有想到這些。究其原因,可能有兩個(gè)方面。其一,是曹禺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極度興奮,創(chuàng)作過程的急遽匆忙。他是太急于宣泄自己的情感了。我們完全可以想象,創(chuàng)作《日出》時(shí),青年曹禺心中那一團(tuán)團(tuán)燃燒的烈火,化為越來越強(qiáng)勁的動(dòng)力,在推動(dòng)著他急切地將自己對社會(huì)的憤怒與人世的不平,一鼓作氣地噴發(fā)出來,不能容許任何的耽擱。他沒有計(jì)劃去進(jìn)行結(jié)構(gòu)藝術(shù)上的琢磨,他甚至已經(jīng)顧不上用太多的時(shí)間去考慮結(jié)構(gòu)藝術(shù)的完整性與統(tǒng)一性。他覺得只要采用現(xiàn)有的“人像展覽式結(jié)構(gòu)”,去表現(xiàn)生活的橫斷面,就已經(jīng)足夠了,不必作太多的藝術(shù)上的推敲與修飾。當(dāng)年的曹禺不可能不明白《日出》這種“人像展覽式結(jié)構(gòu)”,照樣也需要貫穿動(dòng)作與貫穿人物。在戲劇史上,這種戲劇結(jié)構(gòu)模式比較晚出,它主要是通過主題意蘊(yùn)來統(tǒng)攝社會(huì)生活場面與人物群像的,它兼具鎖閉式結(jié)構(gòu)與開放式結(jié)構(gòu)之優(yōu)勢。這種結(jié)構(gòu)模式要求劇作的主題鮮明,要求生活場面集中,要求貫穿人物出沒于全劇各幕。比如,高爾基的《在底層》、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老舍的《茶館》等劇,都是以突出的主題意蘊(yùn)、集中的場面與貫穿的人物來營造其藝術(shù)結(jié)構(gòu)的。曹禺熟悉《在底層》,應(yīng)該了解這種結(jié)構(gòu)模式對完整性與統(tǒng)一性的具體要求。他創(chuàng)作《日出》時(shí),偏離這種結(jié)構(gòu)上的要求,不能說是疏忽,只能說是情感的力量在推動(dòng)著他盡快地進(jìn)入創(chuàng)作過程,盡快地完成大致的創(chuàng)作構(gòu)想。他沒有時(shí)間去深思熟慮,沒有來得及對現(xiàn)有的結(jié)構(gòu)設(shè)計(jì)進(jìn)行必要的優(yōu)化與完善。
其二,是邊寫邊連載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表方式,使得曹禺沒有像寫《雷雨》那樣,對《日出》的劇情設(shè)計(jì),進(jìn)行通盤考慮。他晚年回憶說:“《日出》寫得非常快,我一幕一幕地寫,刊物一幕一幕地登,就像章回小說的連載,他們催著發(fā)稿,我還要教課,只能拼命寫,有時(shí),幾天不得睡覺,我寫戲從來沒有這么干過,這是唯一一次。”①曹禺:《我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道路》,《戲劇論叢》1981年第2期。邊寫邊連載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表方式,往往伴隨著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比如,魯迅《阿Q正傳》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表就是前例。據(jù)魯迅自述,它原來是應(yīng)《晨報(bào)》副刊編輯孫伏園的邀約,為其主編的“開心話”欄目而撰寫的,并因此在開篇時(shí)“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等到寫第二章才“漸漸認(rèn)真起來”,并且被移到“新文藝”欄目里。②魯迅:《〈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頁。這是創(chuàng)作基調(diào)的不確定性,由滑稽轉(zhuǎn)到嚴(yán)肅。后來,孫伏園有事離京,臨時(shí)請他人代理編輯,魯迅就趕緊將阿Q送向末路。“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huì)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③魯迅:《〈阿Q正傳〉的成因》,《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頁。。這是小說人物阿Q經(jīng)歷的不確定性。倘若阿Q能夠多活些日子,他的“革命”經(jīng)歷就會(huì)更豐富些,他的“革命”動(dòng)機(jī)就會(huì)表現(xiàn)得更明顯些,趙太爺在他面前的精神勝利法就能夠有機(jī)會(huì)得到比較充分的表現(xiàn)。我們認(rèn)為這種邊寫邊連載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表方式,造成了《阿Q正傳》創(chuàng)作基調(diào)的不協(xié)調(diào)性,還多少削減了其主題意蘊(yùn)的豐富性與深刻性。像魯迅這樣成熟的偏于理性的作家,都難免因此而造成其作品藝術(shù)完整性與統(tǒng)一性的缺失,何況青年的偏于感性的曹禺呢?如果不是邊寫作邊發(fā)表,如果不是上海《文季月刊》的編輯章靳以很著急地催稿,曹禺也許會(huì)像寫《雷雨》那樣對初稿進(jìn)行修改、打磨,甚至反復(fù)修改、打磨。如果能夠那樣的話,《日出》在主題意蘊(yùn)與結(jié)構(gòu)形態(tài)之間不協(xié)調(diào)不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或許能夠有機(jī)會(huì)得以消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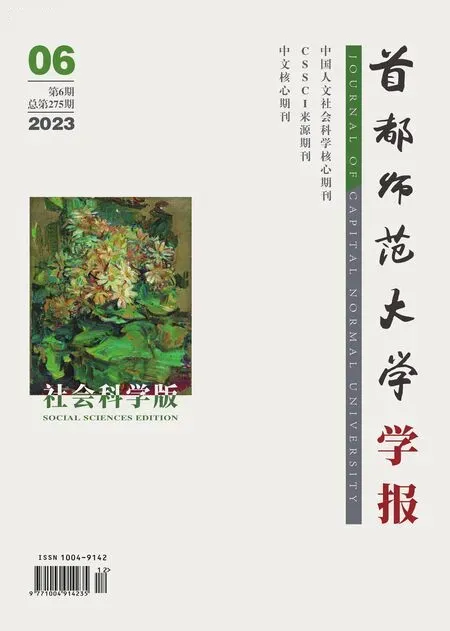 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年6期
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年6期
- 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刻板印象威脅對貧困大學(xué)生脫貧內(nèi)生動(dòng)力的影響及其干預(yù)
- 早期貧困對兒童健康的影響機(jī)制與干預(yù)
- 基于《國際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級(jí)標(biāo)準(zhǔn)》的中文文本難度自動(dòng)分級(jí)研究
——以HSK中高級(jí)閱讀文本為例 - 環(huán)評信用監(jiān)管及“信用環(huán)評”機(jī)制的構(gòu)建
- “建設(shè)明天的世界”:紐約世博會(huì)與1930年代美國的國際主義觀念
- 《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23年總目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