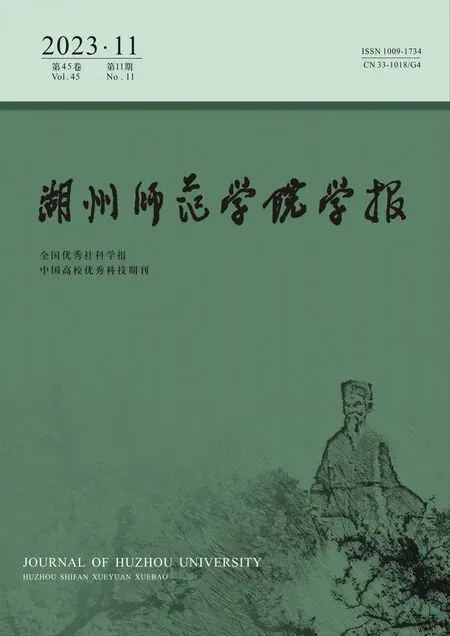嚴復對斯賓塞思想的本土化譯介研究*
金美蘭,褚慧英
(1. 湖州師范學院 國際學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2. 湖州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嚴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翻譯家和思想家。在民族危難時期,嚴復意識到西學在西方國家富強進程上的作用,并且以其獨特的翻譯西學的方式不遺余力地向中國系統地輸入西學,故被稱為“中國西學第一人”[1]113。嚴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他的諸多譯作中均有體現。蔡樂蘇指出:“在嚴復所提到的十九世紀科學家和思想家中,他最崇拜的大概要數斯賓塞,不僅在文章中到處提到斯賓塞,在譯著的按語中也隨處可以見到斯賓塞的名字。《天演論》導言十八篇,就有八篇按語中提到斯賓塞,并且不是一般的提到,而是采用斯賓塞的觀點去駁正原書的觀點。”[2]4耿傳明也認為,嚴復翻譯《天演論》,不過是假借赫胥黎對“進化倫理”進行質疑,以傳播斯賓塞的社會進化思想[3]69,70。張士歡甚至認為,在對于“人治”還是“天治”、宗教起源、道德起源、社會變法、自由或是在許多其他問題的看法上,嚴復思想皆與斯賓塞思想相通。“嚴復一生主要哲學、政治、社會思想本于斯賓塞”[4]122,123。在目前關于嚴復思想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只注意到他同斯賓塞之間的關聯或相似性,忽視了嚴復處于近代世變之亟情境下,作為譯者對斯賓塞思想實施的本土化策略。他基于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思想展開自己的學理構建,并結合中國的傳統和現實情況,進行了翻譯闡釋,構建適用于中國的群學思想和自由觀點,以在思想層面上為救國圖存作貢獻[5]15。
嚴復的翻譯策略與翻譯目的論不謀而合。翻譯目的論認為翻譯是一種基于源語文本的轉換行為,任何行為都有一定的目標或目的, 而且一種行為能產生一種結果、一種新的語境或事件[6]。翻譯的選擇問題貫穿于翻譯的全過程, 無論是“譯什么”還是“怎么譯”, 都涉及譯者的選擇[7]62。翻譯目的論把翻譯重心放在譯文的功能上,動搖了源文的核心地位,強調翻譯的目的。嚴復的翻譯正是如此。嚴復的“翻譯標準和實踐都受到功用價值觀(或‘善’)的影響和制約,從實用性的角度出發,體現出了強烈的目的性”[8]51。由于他身處民族危機深重的中國,他強烈地希望能夠讓更多人認識到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因此,他的翻譯體現了很強的政治性,即以其獨特的翻譯方式引進和傳播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為救亡圖存提供理論依據。例如,嚴復在《天演論》許多節中附加了“按語”,他用自己的方式解讀原著, 以意譯的方法傳遞其中的道理,并表明自己的自由觀、善惡觀、苦樂觀。研究嚴復翻譯的目的、價值指向等,可以發現嚴復思想盡管受到斯賓塞的影響,但是,他在許多議題的理解上與后者并不一致。本文力圖通過分析嚴復的譯作,嘗試論證嚴復在“群學”和“自由”等方面的觀點是對斯賓塞思想實施了本土化建構。
一、“群學”:“社會”之學還是“國家”之學
作為近代引介西方思想的先驅人物,嚴復全文翻譯了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研究》是近代西方社會發展的產物。斯賓塞在這本書中科學地論證了社會的特性,以及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即個體的特性;目的是借用自然科學術語和社會科學的成果,從多種角度、多種因素出發考察社會現象,尋求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結構和運動規律,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9]19,20。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處境不同,當時面臨的問題是救亡圖存、維新變法。嚴復將譯本命名為《群學肄言》,強調更多的是國家富強與否。“嚴復受到斯賓塞社會學理論的影響主要反映在他的認識框架、救國模式上。……他的救國模式雖然依據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但其著眼點在努力使中國適應這個生存競爭的世界,而不是侈談中國被淘汰,被強食的合理性。”[2]11嚴復認為,對于國家而言,其進步與否主要決定于個體的素質。個體通過自身的格物致知與誠意正心,可以逐步實現齊家、治國與平天下的目的。在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問題上,中國傳統史學主要是為了探求王朝興衰治亂。嚴復在譯文中說:“錫彭塞之書,……其持一理論一事也,必根底物理,徵引人事,推其端于至真之原,究其極于不遁之效而后已。于一國盛衰強弱之故,民德醇漓散之由,尤為三致意焉。”[10]6在《譯〈群學肄言〉序》中,嚴復再次表明:“……群學者,將以明治亂、盛衰之由,而于三者之事操其本耳。”[11]Ⅻ
《社會學研究》之所以地位特殊,是因為它宣告了歐美近代新式社會科學的誕生。嚴復翻譯此書,目的并不在于介紹書中描述的西方社會科學流派,而是要給中國治“群學”,辟“涂術”,“導先路”,給學者以“筌蹄”,為近代中國的社會科學奠定理論和方法上的基礎[11]Ⅹ,Ⅻ。在嚴譯《群學肄言》中,約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原著沒有的,原因正在于此。這些增加的篇幅涉及方面很多,既有關于歐洲科學史上的人物、事件與典故,又有關于定理、公例與界定等,還有譯者自行添加的有關中國的事例與評價等[11]12-13,38,46。甚至對于書中的關鍵思想,嚴復的理解也不同于斯賓塞。以“社會”一詞為例,斯賓塞在《社會學原理》中曾對其詳加解釋。對他來說,“社會”雖然涉及君主、議院、地方自治等政治組織,但它首先是一個由個人構成的有機體,它在發展中不斷整合。社會學的關鍵任務就是要研究“社會”的結構,以及“社會”功能的發生、發展和變化[12]2-3,7-8,154-155。嚴復繼承荀子思想,用“群”字翻譯“社會”概念,并明確提出需與“國家”觀念掛鉤。如《〈群學肄言〉譯余贅語》中寫道:“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群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于成國。”[10]125荀子在論及“群”的著眼點不在于“群”本身,而在于所謂“君”“國”“道”上,強調的是國家和君主如何“能群”,如何“制禮”,如何“生養人”“班治人”“顯設人”與“藩飾人”,等等[13]27。換言之,荀子的“群”以“國家”為本位,而斯賓塞的“社會”則以“個人”和“社會”為本位,二者旨趣明顯不同。嚴復翻譯《群學肄言》,不僅在《自序》和《譯余贅語》中反復強調原著所述學理同《大學》和《中庸》等儒家經典的關系,更將“science”,“inquire”,“observe”,“study”等英文術語譯為“格物”“格物致知”“格物窮理”“窮理盡性”“即物觀理”等,并常常在這些譯語之后加上“誠意正心”“至誠前知”“修齊治平”“中庸”等按語。眾所周知,四書中的“修身”其最終目標落實為“治國平天下”,所謂為“經綸天下”而立“大經”, 是為“天下”立“大本”。這一點甚合嚴復的翻譯主旨。“民族危機迫使知識分子有所作為,而嚴復作為譯者,選擇并翻譯《天演論》等八部譯著是對現實的積極回應。”[14]94嚴復結合中國傳統文化,采用中西會通的方式翻譯西學,宣揚合群保種、克己為群的思想,這些翻譯策略和方法反映了嚴復對于以四書為代表的儒家傳統的認同與接受,也體現了作為譯者的“高度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意識”[15]33,反映的既是翻譯的全局性、民族性與時代性,也體現了嚴復自己的政治抱負與思想主張。
二、“自由”:“利己”還是“利國”
嚴復在“自由”的問題上,并沒有完全投入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的懷抱。在“自由”問題上,斯賓塞認為,國家的基本職能是維護人們在同等自由原則下自由行使權利,一方面保護公民免受其鄰人侵害,另一方面保護他及他所生活的環境免受外國的侵略,而在基本職能之外,國家不應承擔額外職能[15]94。“作為規范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主要關心個體與國家的關系,尤其是關心國家對個人自由施加限制的合法性根據,自由主義的本質特征就是對自由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強調。”[16]302斯賓塞主張個體的絕對自由,自由乃天賦之權,神圣不可侵犯,“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10]3。西方崛起的關鍵在于“自由與否”;西方崇尚自由,自由是西方富強的根源[17]72。嚴復不能認同此觀點,雖然嚴復肯定個體權利的正當性,但是對個體的肯定并不同于西方典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嚴復指出,如果按照斯賓塞的思想行動,那么“……其群將渙。以將渙之群,而與鷙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死亡”[10]18。他進一步指出,中國道理中有“恕”和“矩”之說,這與西法之自由相似。然而“謂之相似則可,謂之真同則大不可也”。因為“中國恕與矩,專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則于及物之中,而實寓所以存我者也”[10]3。學界認為嚴復思想的絕大部分均來自斯賓塞,這其中就包括其對于“自由”的看法。現在看來,這種看法不夠準確。斯賓塞是個人主義的杰出代表,他反對國家與政府的干涉,認為社會的整體品質取決于個人品質。嚴復認為斯賓塞的“自由”是“以小己之利而后立群,而非以群而有小己,小己無所利而群無所為立”[18]315。嚴復強調的是“國群自由”而非“小己自由”;重視的是人民的義務,而非人民的權利[2]6。
對嚴復來說,“自由”不光有品,而且有量。所謂自由之“品”是指放任與干涉的對象和性質,自由之“量”則是指干涉與放任的多少與比例。換言之,“自由”其實是有界限的,這種界限正是所謂“群己權界”,亦即所謂“政界自由”,它同所謂倫理意義上的“自由”早已不是一回事。在嚴復思想中,個人自由具有終極價值,他認為個人發展的價值是要超越國家利益的,但在當時的民族危亡的時刻,提出“國群自由”應該優先于“個人自由”的觀點,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當國家不再面臨亡國滅種的威脅時,這種權宜之計應該自然而然地被淘汰[19]i。
當嚴復于1899年初譯穆勒時,曾將書名定為《自由論》。四年之后,嚴復又將其改譯為《群己權界論》,目的就是要避免對于“自由”的錯誤理解。嚴復認為,群己之間也好,或者說政府與個人之間也罷,其實都是有界限的,也是互有助益的。二者之間一方面此消彼長,另一方面又相得益彰。如國家能不受強權干涉,政府的作為自然會大,個人自由也會水漲船高。由于政府治理與個人自由可以相互鉗制,又相互牽引,因此大可不必實行完全的放任主義政策,因為純粹的自由而無治理,會導致社會不得安寧,也會導致社會無從發展,最終反而有礙于民眾享受自由。所以,問題不在于“小己”與“國群”之間能否統一,問題只在于如何把握管治的適度,也即“小己”與“國群”的權利界限。如嚴復在《法意》中說到的:“特觀吾國今處之形,則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異族之侵橫,求有立于天地之間,斯真刻不容緩之事。故所急者,乃國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又說:“前者妄言,謂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圖強,杜遠敵之覬覦侵暴,為自存之至計也”[20]98。這些思想即是嚴復從穆勒那里得到的啟示,它們在學理上已經不完全等同于斯賓塞的個人主義。對嚴復而言,群己權界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正確認識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系,而且因為它可以批判強權,維護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三、“善惡”:“進化”還是“選擇”
嚴復在“善”與“惡”到底是“進化”還是“選擇”的問題上,明顯不同于斯賓塞。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并不同于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他對善惡有其獨特的理解。斯賓塞雖然主張“適者生存”,但同時反對野蠻、暴力和專制,以及不擇手段的無限競爭,強調公正和善行的倫理意義[21]27。一方面,斯賓塞確有運用生物進化的理論,以分析人類社會與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斯賓塞認為,高級戰勝低級、文明戰勝野蠻,乃是生物界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合理的。由于適應性低,“原始的人”終究會被較先進的人改造或消滅。落后者被消滅對于人類的發展有益,因為野蠻人是一種具有“反社會性的人”。斯賓塞指出,既然“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征服,主要是社會性的人對反社會性的人的征服”,“是一個適應性強或相對進步的民族,對于適應性弱或相對落后的民族的征服”,那么其結果“必然使進步得以開始”[12]598。他認為,隨著這一過程的日益延續,人類也將步入進化至極的理想社會。而在社會的不斷進化中,只有“善”會跟著進化,“惡”則不會,即“善演而惡無從再演”。
對嚴復的譯作《天演論》進行研讀,會發現嚴復接受斯賓塞的觀點有其合理之處,所謂“善”“惡”都只是相對的、階段性的。但是,嚴復認為斯賓塞所描繪的理想社會美景必定無法達到。嚴復之所以轉向西方、翻譯西學,是為了尋找民族解放的契機,以及國家富強的路徑。這無疑是一種大善,因為它已經大不同于康德批判的面向“我者”的狹隘。作為天人關懷的具體體現,這樣的大善同陳陳相因的中國文化中,所謂“士徇利祿,守殘闕,無獨辟之慮”的士大夫陋習也有天壤之別。原因在于,傳統的士大夫脫胎于舊有的科舉制度,后者嚴重地“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是斷然沒辦法實現“今日救弱扶貧之切用”[22]1550。為了實現這種大善,嚴復認為首先應該破除傳統的“義”“利”觀念。因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利”和“義”自古勢不兩立。所謂“憂道不憂貧”,如嚴復所說,“大抵東西古人之說,皆以功利與道義相反,若薰蕕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則謂生學之理,舍自營無以自存。但民智既開之后,則知非明道,則無以計其功,非正誼,則無以謀利。功利何足病?問所以致之之道何以耳。故西人謂此為開明自營,開明自營,與道義必不背也”[23]92。
嚴復的人性論反映了功利主義的道德觀,把苦與樂作為善與惡的判別標準,人性的本質就是趨樂避苦、趨利避害。嚴復指出,所謂“利”和“損”都是雙向的,利是互利,既可利己,也可利人;損也是兩損,既已損人,必定損己。因此,“利”和“義”完全可以相互包容,并行不悖。解決了這個問題,嚴復便開始翻譯《原富》《穆勒名學》等,希望通過他的所謂“獨辟之慮”,為在“物競之烈”而國運堪憂的歷史階段,正大光明地為貧弱不堪的中國提供發展經濟和物質利益的具體方法。嚴復對善惡倫理的演繹正是秉持著“學為一切法之法,一切學之學,明其為體之尊,為用之廣”,“西學之所以翔實,天函日啟,民智滋開,而一切皆歸于有用者,正以此耳”[24]2,66。既然中國社會的弊病是愚昧、貧窮和衰弱,自然“凡可以愈愚者,將竭力盡氣頗手繭足以求之,惟求之為得,不瑕問其中若西也,不必計其所若故也”[10]171。在嚴復看來,道德是進化的產物,不道德也是,因此,不能認為進化過程就具有某種內在的善。他傾向于赫胥黎的觀點,“道德蘊涵自明的價值準則和善之指向,在道德之上構建的社會及社會倫理是具有道德情感的人類的自主選擇”[25]4。雖然嚴復對善惡問題的把握不甚圓滿,沒有完全接受斯賓塞的觀點,但是,一方面他想通過傳播社會進化規律為中國探索救亡圖存的真理,另一方面又力圖結合中國古代和其他西方思想家哲學思想,在不否定社會發展中人為的作用和人道價值的重要性的前提下,為自我尋求幸福與快樂樹立正當性和道德價值合理性。
四、結語
在“群學”到底是“國家之學”還是“社會之學”“自由”究竟是“利己”還是“利國”“善惡”是“進化”還是“選擇”等問題上,作為譯者,作為“信達雅”翻譯標準的倡導者,嚴復明顯不同于斯賓塞。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嚴復作為翻譯者的社會責任感。嚴復對斯賓塞的態度,有著高度的策略性。他的翻譯體現了匯通中西學術,創造新文化,以啟發民智、救亡圖存的變譯思想。為配合時局需要,同時也為了闡述自己的理念,嚴復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翻譯理念。縱觀嚴復一生,其所作所為堪比上古賢士。所謂逢治世不避責任,遭亂世又不偷生,正是嚴復一生的真實寫照。